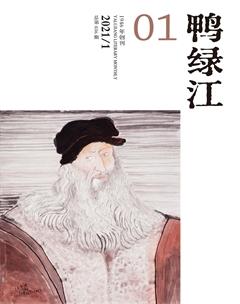下长白山
王陆
要去长白山,我选从北坡上。
走一段鹤大高速,从露水河镇下道,再奔二道白河镇。
下露水河镇时,已是傍晚,人车无序,一路坑洼。而进入二道白河镇地界,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阔道远,远近通明。能看出来,两镇虽紧挨,但各过各的生活。露水河镇属于白山市抚松县,二道白河镇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
二道白河镇是长白山北坡第一镇,住处窗户正对步行大街,虽是夜晚九点,但游人成流,更似城市景象。找一家朴姓韩菜馆,我点一锅狗肉豆腐、一碟酱狗排、一碗冷面、一碗米饭,共68元。
妻子正色,怎么能忍心吃狗肉?
我辩解,不吃狗肉,长白山人民怎么与严寒做斗争?
妻子还正色,吃猪肉不一样吗?
我还辩解,狗肉一层皮,胜过牛羊猪马三寸膘,这都是当地劳动人民的经验,咱还怀疑什么?
妻子不是脸色,只吃几口冷面。
我再深入讲,瞅这里一家挨一家的狗肉馆,都不进来吃。再看价格,吃狗肉比吃猪肉合适。
一夜有风,两人无话。
早晨上路,横风夹雨,伞都打不住。大巴从二道白河镇到天池山下要行34公里。山下树高林密,山上树矮林稀,到了山门再换小巴,沿山路盘上,都是裸岩砾灰,即使哪一处有一层薄薄的绿意,也遮不住这岩灰地貌本质。
长白山其實算不上巍峨。
天池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看。
可怜妻子,雨衣让横风乱雨给掀翻打透也不离天池栏杆,她说在网上查了,天池气象多变。果然,云霾开了。听妻子一声喜叫,我瞥见一潭天池水绿。也就五六秒钟,云霾又聚,风雨又起。
妻子握手机,不甘心,说,连个天池都没照上,就这样走了吗?
长白山是火山遗留下的残疾儿,原有的险峻、旖旎、高贵都给火山几番摧残。有记载的是三次,最近一次是1702年,喷发之时,天响地流,灰烬漫出五百里,留下长白山旷卤之躯、灼疤之肤。
不懂这,就不懂东北上半身。
懂得这,就会懂得东北下半身。天池岩砾渗雪透雨,百仗过滤,这一条是鸭绿江,这一条是松花江,这一条是图们江。生命择宜,谁也挡不住。山上毁灭,就在山下生;山下毁灭,再往远方生;地界不可限,禁封不能止,且有生殖之健。
要不然,东北大地怎么能生出这么多的健壮民族!
大荒之中,广而袤之,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等,到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所谓“壮岁经行”“立马雪空”,都在山脉草原峻岭相连里,是中国地理政治最峻冷的气象,这气象绝非中原文化里某种自负的嘲弄。
幸亏这种气象闯入!
我是汉族人,而且是祖籍山东文登的汉族人,但我并不太亲近山东。没有办法,与物竞,随天择,必然是杂交的生命。听父亲讲,祖先五百年前是云南人,随部落押迁,流入山东半岛一带有几万人,务农从贱。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学的是孔孟;母亲是文盲,缠足讨饭,所懂的一点道理也是孔孟。但他们闯荡颠簸一大圈,真正解救他们的是自我行商。而于我则是另一番经历,生长在大连,有一些东北,有一些山东,还有那么一点点日本和俄苏,蒙教于“文革”,自觉于1978年之后的思想文化解放时期。
我年届六十,自觉移植,自觉杂交,愈加认可自我的景象。
下长白山,我看到一种松。这松在二道白河与三道白河沿岸一带,形状不粗不茂,枯裸而挺拔,都有二三十米高。
木牌标明,这松叫美人松,只有此海拔、此气候和此土质才能生就,是一种娇贵松。这怎么可能?娇贵生命在东北是根本活不成的!我想,定然是火山落土之后烧灼成某些稀有尘埃,让此松为生。
仰看此松,我相信,这是劫后高松,可以叫壮松,也可以叫火山松,或叫不死松!却偏偏怎么起了“美人松”这么一个风月蛾眉之名,根本不挨边!
东北不贴风月,不挂粉黛,这正是这片土地所习惯的。
生则行,行则健,没有什么不舍,也没有什么禁忌。彼此不问你从哪里来,还要往哪里去。也不愿闲聊吃狗肉有罪还是没罪。吃则吃,不吃则不吃,当十月雪落冰结之时,各家做各家的饭,各人讨各人的路,不是紧挨着。
我这些年这么多学生,从吉林、黑龙江或辽宁北部迁移过来的,至少占一半吧。也有满族的、朝鲜族的和蒙古族的。他们体高心远,风行垒止,不惧方向,千里移到大连,也不确定这就是终点。长白山系延伸到辽东半岛,人比山系更能延伸,比候鸟更有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