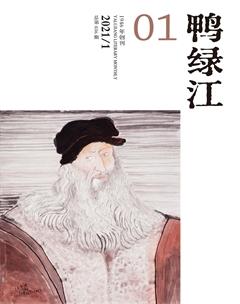花盆(短篇)
得知老莫失踪的消息,余粮人的心不是往下坠,而是向上飞,飞呀飞,好像是一只风筝飞到了天空中,嘎嘣一声线断了。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空中抓了一下,似乎是想抓住那根断了的风筝线,却抓住了一股风。
风是热的,刺溜一下从手中滑过。那台老旧的电风扇蹲在墙脚摇头晃脑地转着,每当转到左边时,就会发出吱咛吱咛的声音。余粮人觉得这台老风扇有点像自己的脖子,转动起来不那么灵活了,随时可能在某个地方卡住。
儿子说,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竟然就把他的那个小超市给兑了出去,还从医院里跑了,也真是厉害。
余粮人瞟了儿子一眼。儿子的头发被电风扇的风吹得立了起来,像一束黑色的火焰。等电风扇的头转过去时,那些头发又一下子耷拉下来塌在了头上,看起来有些凌乱。余粮人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背过风想把它点着,打火机那微弱的火苗几次都被吹灭了。他索性把打火机连同烟一块儿扔在了桌子上。那烟在桌子上跳了几下,就被吹落在地上,他也懒得去拾。
儿子说:“爸,我们的钱这次真的是完了?”
余粮人没有说话,他知道儿子心里急。儿子是经不住大事的。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能经得住大事。但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老莫就这样失踪了?
其实,余粮人知道老莫出事是在去年冬季。那时候,老莫的儿子出事了,据说欠了别人几百万。儿子出了事就跑了,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把一摊子乱账丢给了老莫。
老莫开着一家小超市,要账的人一拨一拨地往老莫的超市跑。老莫倒是不着急,把讨债人的名字、欠账的数额都一一记下,记了厚厚一本子。老莫说,大家也都不着急,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账虽是儿子欠下的,但我都认,谁让他是我儿子呢?人常说父债子还,我这是子债父还。只要我老莫不死,我都一点一点地给大家还。但大家得给我点时间,容我慢慢地还。
老莫把那个账本整理出来,他按时间顺序把欠钱人的名字一一排列下来。他得从最早拿钱的人开始还,也不是一次还清,第一个人还一点,接下来再给第二个还一点,再接下来给第三个人还一点,如此类推,先还一轮,再接着还第二轮。
老莫的小超市开在麻城西背街,越过一条马路,就是东背街,就是麻城的东客运站。当初,好多人都选择把超市开在了客运站跟前儿,老莫却选择了隔着一条街的西背街。别人都不理解老莫的做法,但老莫心里清楚,这地方虽然和客运站隔一条街,房租却便宜不少。还有一点就是,许多人对客运站跟前儿的超市都是不怎么信任的,总觉得那地方的超市都有点坑蒙拐骗的味道。老莫的超市不大,但生意确实不错。有人估摸了一下,就老莫这个小超市,一年下来也就能挣个一二十万,这几百万的账,得还到猴年马月去了。
那段时间,老莫的小超市门前总是晃荡着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有些人知道消息晚一些,他们打听到,老莫的儿子虽然跑了,可他老子还有一家超市,辗转找到这里,就打起了老莫超市的主意,他们要用老莫的超市抵自己的债。这怎么能行呢,老莫的这个小超市现在是大家的,谁也别想独自占有。老莫的这个小超市就是一只母鸡,能下蛋的,你把小超市抢去了,老莫欠大家的钱可就没了一点指望。老莫的超市在,大家的希望就在,没准这钱还真能还回来。
老莫原先也担心这个小超市的日子快到头了。那么多的债主,他的小超市随时都有被人抢去抵债的可能。没想到,这样一来,他的小超市反倒安全了,那些债主谁也不愿意老莫的小超市没了,谁都不愿意小超市被别人拿去抵债了。那些人互相监督着,但凡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老莫的小超市门外,他们就会上去盘问,就会上去阻止。他们互相牵制着,互相制约着。他们在这个冬天里,像保护着珍稀动物似的保护着老莫的小超市。
麻城这个小城处在一个风口处,霜降之后,冷风就开始呼呼地刮,街道两旁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乱飞。地上的落叶被风一吹,就像一只只蹦跳着的青蛙。
现在的老莫终于能安下心来经营他的小超市了。他从库房里将那只煤炉子搬出来,安装在了超市里。铝制的排烟管在超市的顶上绕了一圈再从窗户上伸出去。有了这个煤炉子,下雪时他不冷,来买东西的顾客也觉着暖和。他在煤炉子上再坐一壶水,来买东西的人口渴了,也能喝一口热茶。有些出门的人要在客运站坐车,在他这小超市里买一盒方便面,刚好热水泡了,热乎乎地吃下去,走时再给茶杯里续一杯热水车上好喝。出门在外的人谁都不容易。
从这个超市开业的那天起,老莫就一直是这样。周边这么多超市,人家能跑到你超市来买东西,也算一种缘分。几年下来,老莫也是靠这积攒下了不少人气。小生意也是这样,要积攒人气。
麻城的第一场雪从天空中飘下来时,老莫窗户上伸出来的铝制管子里也飘起了一股黑烟,那股黑烟慢悠悠地飘向了空中,然后,黑也就不再黑了,和一片洁白的世界融为一体。老莫给煤炉里添上了煤,生起了火。那红红的炉火,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暖和。超市的门上也挂上了厚厚的布帘子。老莫从布帘的缝隙中往外望去,有几个人在雪地里跺着脚,好像是要把身上的寒冷抖落到地上,再把它给踩到脚底下的样子。老莫想,那些人也许是他的债主。他们从他儿子一出事就时不时地出现在那里。老莫想,这些人也真是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冲着他来的,冲着他的小超市来的,他們谁都想把自己的钱从老莫那里要回去,他们软硬兼施使出了各种办法,可老莫真的是没钱呀,要是有钱,儿子也就不跑了。一个没有钱的人,你能把他怎样?都说欠钱的是爷,债主倒成了孙子。可那些人是有钱不还。可他老莫真的是没有钱呀,欠人钱财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好在老莫并没有说他不给他们还钱,他只是需要时间,他还有这个超市,有了这个超市,就有了希望。当有人想独自拿他的这个小超市去抵自己的债时,情况突然就发生了逆转。这个小超市成了所有债主的希望,是大家的,谁也别想独吞。慢慢地他们与老莫的矛盾竟然演化成了那些债主之间的矛盾了。
有一次,一个债主堵住老莫超市的门,逼老莫还债,并扬言如果老莫不给他还钱,他就叫人来搬走老莫超市里的东西。老莫正不知该如何应对,倒是那些人跑了上来,几个人架着那人的膀子把他拉进了对面的一家小餐馆里,一顿小酒喝下来,那个人竟然不吵不闹了,也加入到了那些债主的行列。
老莫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们,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有几次,他走出超市,走到他们身边,非常歉意地想让那些人进屋去喝口热水,暖暖身子。那些人倒是很客气,说,你忙你忙,不要耽误了你的生意。
不仅如此,那些人也都跟商量好了似的,要买什么东西了,也都去老莫的小超市去买。有时候,他们还鼓动身边的人也去老莫的小超市去买东西。这倒好了,老莫欠着大家的债,更欠了大家的情,那些人联合起来保护起了他。老莫成了锅里的一坨饭,大家都可以看着,但谁也别想吃到嘴。
年前一段时间,是老莫的小超市一年中生意最好的季节。一进入冬月,置办年货的人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街道上的人晃来晃去,车跑来跑去,麻城的风也刮来刮去。老百姓就是这样,平时不管多么节俭,多么省吃俭用,到了过年,个个都出手大方,好像过了年日子就不过了似的往家里买东西。老莫的超市离车站近,拎着东西过条马路就到车站了,方便得很。那些从乡下进城置办年货的大多选择在他的超市里拿货。还有那些出外打工回来的,下了车也都要给家里置办年货,也都直奔老莫的小超市。那段时间,每隔两三天,小超市就得上一次货。好在现在的超市缺啥货了,一个电话就有人给你送上门来。即便如此,老莫还是忙得跟个陀螺似的。这反倒让那些三天两头往老莫小超市跑着要债的人心安了些,老莫的生意好,他們的钱也就有了希望。
老莫毕竟年龄大了,忙忙碌碌一天,晚上往那儿一坐,手脚好像就不是自个身上的,好像是那脱了钩的车厢,任凭车头跑得再快,它在那里就是动弹不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来买东西的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债务缠身,就开玩笑说,老板呀,钱多少是个够呀,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辛苦,是不是还想养个小的呀。
老莫无奈地笑笑,说,钱再多也不会咬手呢。话虽这样说,老莫心里的苦却没有人知道。这样忙死忙活的,钱却没落下几个。老莫说话还是算数的,除了留够足够的周转资金,他开始给债主们还钱了。第一个债主按规定拿走了部分欠款,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债主早就守在那里了。债主就像是门外的冷风,总是刮个没完没了。
余粮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老莫的超市里的。这是老莫儿子出事后余粮人第一次来见老莫。按说,他早应该来看看老莫了,来安慰安慰他,来劝导劝导他,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哪怕是去坐坐,什么也不说,抽支烟喝口茶。可他不敢,他怕老莫误解他,误解他和那些人一样是来讨债的。
余粮人知道,老莫这人其实是欠不了别人的债的。四千块钱可以想办法办一个城镇户口,从农村人变成城镇居民,你就可以吃上商品粮,甚至找工作也更容易。那时候,老莫的老婆还在,余粮人的老婆也还在。余粮人的老婆儿子都是城镇居民户口,可老莫不一样,老婆儿子都是农村户口。老婆倒无所谓,儿子就不一样了。农村户口就像是长在脸上的一块胎记,说媳妇难,找工作难。老莫就想给儿子办个户口。可老莫一个人一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哪有什么钱呀,余粮人就和老婆商量,将家里的积蓄三千元钱借给了老莫。儿子的事要紧。那时候,三千元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老莫又从别人那里凑了些钱,总算给儿子把户口办了回来。刚把户口办回来时,一家人确实高兴了几天,好像弄回来了一本通关文牒似的。仅仅过了两天,老莫就陷入惶恐不安之中。几千元的外债,对于一个月只有几十元钱工资的老莫来说,那简直是压在胸口上的一块磨扇,弄得他寝食难安。那弄来的简直不是户口,而是病。
那些日子,老莫真就跟病了一场一样,没精打采,精神萎靡,神情都有些恍惚了。
老莫还是有办法的,在给儿子办回户口半个月之后,他不顾老婆和儿子的反对,竟然又倒腾着将户口“卖”了出去。老莫的儿子一生中,竟然只拥有了半个月的城镇户口,他还没有尝到居民户口给他带来的半点好处,那块农民的胎记重又贴到了他的脸上。
老莫把三千块钱还给了余粮人。
余粮人想,如果那时候老莫不把给儿子买来的户口“卖”出去,也许儿子就会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或许也就不会给他惹下这么大的麻烦,欠下这么多的钱。卖掉户口之后,儿子和老莫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有些紧张。儿子发誓要挣钱,他要用钱来改变他的人生。
那天,余粮人一走到老莫的超市门口,就感觉后背上贴上来许多双眼睛,余粮人立马明白老莫现在的处境了。这一片祥和的背后是暗流涌动。余粮人心里有些酸酸的,老莫呀老莫,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竟然被人包围着监视着。
余粮人刚进门,就看见了老莫,老莫也看见了他。他本来想喊一声老莫的,老莫的表情里却是全然不认识他的样子,说,先生,请问您想要点什么?余粮人一愣,但马上就明白了老莫的用意,他是不想让那些人知道他们是认识的,或者让他们感觉出他余粮人也是老莫的债主。就说,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超市里还有几个顾客在货架上挑选东西。余粮人弄不清这些人当中会不会有老莫的债主,就闭着嘴在货架间转来转去。还别说,老莫的这个小超市,货品还真齐全,要啥有啥,也都是些价格便宜老百姓日常离不开的东西。余粮人看见本地产的“象园茶”也摆上了货架。余粮人不想买什么东西,他只想等超市里人走了,和老莫说上几句话,老莫也许不需要安慰,人在这种环境下,安慰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就好比久病的人对于药物,已产生抗药性一样。但他还是想和老莫说上几句。
老莫的超市生意还真是不错,这拨顾客还没走,又来一拨。老莫站在收银台后面,不停地忙碌着。余粮人觉得没有这个超市,老莫的日子或许过得正常些,那些债主没了指望,反倒死了心。正是有了这个小超市,老莫的日子才过成了现在这样。
这时,一个人拿着一只大水杯从外面进来,大概是个老顾客,他径直走到门口墙边的煤炉子前,掀开坐在炉子上的水壶的盖子,水却没开。老莫走过去提起水壶给炉子里加了块煤,再把水壶放上去时,水壶里仿佛跑进去了几只小老鼠,吱吱地叫了起来。那个人提起炉边放着的电壶,给杯子里倒满水,又走出超市。都没有说话,但一切好像都在情理之中。
余粮人觉得今天是没有和老莫说话的机会了。正准备走时,门帘掀开了,一辆轮椅被推了进来。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头上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灰扑扑的,有点像外面天空的颜色。老人穿着蓝格子病号服,身子斜靠在轮椅上,抽抽的右手举在空中,像是一节脱掉了枝叶的树枝。他的嘴眼歪斜着,嘴角还吊着一串哈喇子。推车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显然是老人的儿子。他把车子刚推进门口,就停在了那里,那轮椅刚好堵住了超市的门。
老莫显然认识那对父子,他连忙从收银台跑出来,说:“相东,你爸这是怎么了?”
那个叫相东的男子说:“脑梗,半身不遂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医院让交费,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了嘛,就把他从医院里推出来。”
老莫说:“相东,这事咱再想办法,你先把门给让开吧。”
相东却没有动,他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烟点上,目光在超市里逡巡着,好像是想在那货架上寻找能救他父亲的良方妙药。
老莫上前将轮椅推到了收银台前,他低下头,对轮椅上的老人说:“老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前一阵不是好好的么?怎么突然就半身不遂了?”轮椅上的老人嘴张了张,发出的却是哇哇的声音,那舌头就跟在冰箱里冻了一晚上一样,根本没法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老莫刚把轮椅推开,就从门外拥进来几个人。那几个人走到货架前,手里挑选着东西,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老莫。
老莫走到收银台后面,犹豫了片刻,还是拉开抽屉。他先把里面的百元大钞归到一起,再把五十元的归到一起,把那些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抬起头一脸歉疚地对相东说:“相东,是我对不起你们,我这也实在没办法了,这是我这几天的营业款,本来是给明天来送货的人的货款,你先拿去給你父亲看病吧。”老莫正要把手里的钱递给相东,突然一只手插在了老莫和相东两只手之间。
“莫老板,你这就不对了,凡事得讲规矩,讲个先来后到。这钱你不能给,你给了他,我们怎么办?我们还等着钱过年呢。”老莫说:“这不是人家病了吗?”那人说:“病了也不行。”老莫说:“你们别担心,我只是把你们的钱推迟几天,我该给你们还多少,一分都不会少的。再说,只要我老莫在,只要这个超市在,你们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的。”
“不行。你不是说这是进货的钱吗?这货不进怎么能行呢?没了货,拿什么东西卖?”那人说着,就把那钱从老莫手里接过来,他把钱在空中扇了扇,放进老莫收银台的抽屉里。
老莫说:“你看人都这样了,算我求你们吧,我欠着你们的钱,也欠着他们的钱。人都病成这样了,还是看病要紧。”说着老莫又把钱拿出来递给了相东。
相东赶紧接过钱,什么也没说,或许是怕再生出什么是非来,推着轮椅出了超市的门。
余粮人还是被眼前这一幕感动了。他走到收银台前抬起手想拍拍老莫的肩膀说一声老伙计保重,手抬刚抬起又放下了。他跟着那辆轮椅出了超市的门。
余粮人出了超市的门,身上就一个激灵,外面的天真冷。其实在麻城冬天最冷的是风,簌簌的像是小刀子。天空中又零零星星地飘起了雪花。这鬼日的天,昨天还有太阳呢,说下雪就下了。昨天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说有雪,他还有些不信呢。
街道上的人依旧是多。快过年了,客运站一车一车地把人拉回来撒向了这个小城。余粮人跟着人流往前走,转过一个弯,余粮人又发现了那对父子——相东和他的父亲。相东推着轮椅,他的父亲,那个坐在轮椅上手抽抽着、嘴眼歪斜、嘴角还吊着一串哈喇子的老头,此时正跟在相东的身后,手也不抽抽了,嘴也不歪眼也不斜了,腿脚麻利地走着呢。他身上的那身病号服也不见了。那顶灰扑扑的帽子上落满了雪花。
雪越下越大了。雪花纷纷从空中飘下来,仿佛一张白色的网。
余粮人回到家,儿子躺在沙发上。余粮人明白,儿子现在和老莫一样,天天在为钱发愁。儿子住的是单位的福利房,房子面积小。孙子上小学了,儿子想换套面积大一点的带电梯的房,到时候也好将他接过去一起住。房子已看好,就是首付钱不够。当初把手里的一点积蓄交给老莫的儿子,也是想再生点小钱出来,没想到小钱没有生出来,大钱也没了。
余粮人有些后悔。当初,为了这二分钱的利息,他去求老莫想把钱放进老莫儿子的公司,老莫还劝过他,说他总觉得儿子做事不靠谱。余粮人硬是不听,还说我相信的是你老莫。结果就出事了,放狗逮兔,兔没逮着,狗也没了。余粮人知道儿子懂事,他只是想让余粮人能从老莫那里给他把首付款凑够就行了。可老莫都这样了,他真不好意思在老莫面前开这个口,现在去找老莫要钱就是雪上加霜。儿子现在只是小房换大房,不换又怎么样?
儿子见余粮人回来,立马从沙发上坐起身。他一看余粮人脸上的表情,就知道没什么戏。儿子从沙发上站起身,指着茶几上的一袋水果说,小慧带你孙子去周末补习班补课去了,这些水果是她给买的,你记得吃。说着就出了门。小慧是儿媳妇,为钱的事一直在和儿子闹别扭,好久没回他这里了。
儿子下楼的脚步声很响,好像是带着气,一步一步踩在余粮人的心上。余粮人脑子里就想起了在老莫超市里见到的那对父子,他们为了讨点钱,竟然想出了那样的点子。人都是被逼的,好点子是被逼出来的,歪点子同样是被逼出来的。人在没办法时,总是歪点子比好点子多。
第二天,余粮人没有出门,外面的雪扯天扯地,越下越大。站在阳台上看出去,麻城到处白茫茫一片。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的雪都被铲了堆在一起,有人把堆起的雪做成了一个雪人,冷瑟瑟戳在那里。
那天中午,余粮人意外地从身上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是从一张废纸上撕下的一片,由于匆忙,撕得并不齐整。纸条是老莫写给他的。他想不起来在超市时,老莫是什么时候把这张纸条塞进他的衣袋里的。
看完纸条上的字,余粮人连忙找出黄历,戴上老花镜查看日期。查完日子,余粮人心里竟有点激动,还有点期待,是的,明天就是二十五号。
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余粮人就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出了门。雪停了,可路上到处是积雪,一坨一坨的,好像是不小心遗落在地上的棉花,脚踩上去嘎吱嘎吱作响。余粮人觉得奇怪,这城里的雪踩上去怎么会叫呢?乡下的雪脚踩上去松松软软,无声无息。记得有一次和父亲上山狩猎,刚下过雪,一脚下去,雪就拥到了膝盖上,半天拔不出来。父亲站在那里吆喝了几声,便见一只只鸟飞到雪地里,把头扎进雪里,高高地撅起屁股。父亲带着他走过去,只需抓住那鸟的屁股轻轻一提,猎物就到手了。后来,余粮人问父亲,那是什么鸟呀,怎么那么笨呢。父亲说,那鸟叫雉鸡。余粮人就这样在街道上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着,一直走到老莫的超市前。
老莫的超市已关了门。东客运站最后一趟班车八点半回来,老莫的超市一般晚上九点就关门,最后一趟班车一回来,超市几乎就没什么生意了。
余粮人在老莫的超市前站了一会儿,确定周边没人后,走到老莫的超市跟前。超市的那扇窗户上放着一只花盆,里面栽着几棵吊兰。现在吊兰早已枯死了,垂头丧气地耷拉在那里。余粮人轻轻地抬起花盆,将手伸到花盆底部,果然在花盆下摸到了东西。看来,老莫没有说假话。余粮人把那东西揣进衣袋就迅速离开了那里。
余粮人回到家里才把那东西掏出来,是钱。余粮人数了数,整整一千块。老莫在纸条上说,以后每个月会给余粮人还点钱,数额不确定,有了就多还,没了就少还,他每月二十五号会想办法将钱放在超市窗台上的那只花盆底下,让余粮人到时去取。
看来老莫真是被那些债主们控制住了,连给他余粮人还钱都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就跟地下党接头似的。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不是老莫垮掉,就是他的超市垮掉。老莫的儿子一去无踪,儿媳妇将家里唯一的一辆车开走后,也一去无踪。好在老莫还有这个小超市,现在看来,这个小超市既是老莫的希望,也成了祸害,如果没有这个小超市,债主们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人常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连庙都没得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开春后,老莫小超市的生意一下子清淡了下来。债主们反倒多了,他们没事了就在老莫超市的外面晃荡。那段时间,余粮人也天天往老莫的超市里跑,每次去了,也不进老莫的超市,只是远远地站在超市对面老莫看不见的地方。他还是有些担心那些要债的人,他怕他们要不到钱,会做出过分的举动。只是等到每月的二十五号,他会乘着没人,偷偷地跑到老莫超市前的花盆下取走老莫给他还的钱。有时候是一千多,有时候只有几百,但老莫从没食过言。
到了淡季,老莫的生意本来就不怎么好,偏偏这个时候出了些意外。那些债主之前去老莫超市里拿东西都是给现钱的,不知从哪一天又是从谁开始,他们再去老莫超市拿东西时,就不再给现金。他们拿了东西让老莫把账记到账本上,到时再从欠他们的钱数里下账。有了这样的开头,就一发不可收拾。有些人不仅自己在老莫的超市里拿东西记账,连同他们的亲戚朋友来拿东西,也都让老莫记账。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余粮人有时想上去和那些人说说理,可老莫是欠着人家的钱呀,怎么个说法?
终于有一天,早上到了超市开门的时间,超市的门却紧紧闭着,迟迟不见打开。那些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情况以前可是从来没出现过。难道是老莫跑路了?这样的事可是没少发生,要是老莫真的跑路了,那可真是连点希望都没了。这之前虽然老莫并没有给大家还多少钱,但只要能天天在超市里看见老莫,这希望可就在,老莫呀老莫,你可不能连大家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苗都给掐灭了。
这一等,一天就过去了。老莫超市的门始终没开。
第二天早上,大家早早就守候在老莫的超市门口。八点一过,超市门开了。所有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想,是我们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来开门的却是一个女孩。女孩个子高挑,面容姣好,一笑起来就露出一对小虎牙。那些被老莫欠着钱的人,现在俨然是小超市的股东,小超市的一举一动,他们比谁都关心,这一夜之间怎么开门的就变成一个女孩了?并且谁都不认识。他们跑进超市里想找老莫问问是怎么回事,超市里却连老莫的影子都没见。这些人一下子急了。
他们围住女孩问:“你是谁?”
女孩咯咯地笑時,就露出一对虎牙。她说:“我是我呀!”
“老莫呢?”
“病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他请来给他帮忙的,他病了,超市总不能关门吧。”
老莫病了?得的是什么病?要紧不要紧?这一连串的问题像一群乱飞的燕子,让每个人都理不出个头绪来。
那些债主们终于放弃了对超市的看守。他们打听到老莫的住处,其实不用打听,老莫住在哪里,一些人早就知道。老莫现在就像明星一样,是没有隐私的。
老莫现在的房子是租来的,一个大单间。刚出事时,老莫就把他原来的房子卖了。他以为把房子卖了,就可以堵住儿子的窟窿,就可以救儿子。可没想到,房子卖了,却是杯水车薪。好在那时他死死地守住了这个小超市。
那些债主找到了老莫时,老莫像条死猪一样躺在床上。老莫确实病了,他浑身酸痛,头晕,还发着低烧。以为是感冒了,就自己从药店买了些药吃了。可病情并没有好转。老莫可不能出事呀。那几个债主七手八脚地把老莫弄进了医院,医生一查血压,老莫的高压都上了二百了。
老莫住院了。
那些天,余粮人也混进了债主的行列。他对那些人说,老莫欠着他五十万,那些人就信了。他在老莫面前装作他们并不熟识的样子。老莫被送进医院时,没钱交住院费,超市的钱刚刚进了货。余粮人就动员大家先将老莫的住院费垫上,他说:“这是拿小钱救大钱,住院费相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小钱,老莫欠着大家的可是大钱,如果老莫的病不看,出了问题,那就是大损失。”
没想到那些人居然同意了。
老莫的住院费不仅解决了,那些债主还像照看自己的亲爹一样照看着老莫,生怕老莫有什么闪失。他们轮流在医院照看老莫。
那天,是余粮人和另一个人在医院照看老莫。余粮人趁那人不注意,就趴在老莫的耳边说:“你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日子啥时是个头呀。”
老莫握着他的手,没有回答他,眼睛望着头顶上的吊瓶,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吊瓶的药一滴一滴地流进老莫的血管。
老莫是在住院的第六天失踪的。看守他的两个债主坐在老莫病房门外的长条椅上,一刻也不曾离开,可老莫还是不见了。医院里炸了锅,医生护士里里外外找了好多遍,也没见老莫的踪影。其间,几个债主还跑到老莫租住的房子去找过,还是不见。他们抱着最后的希望跑到老莫的超市去找。守着超市的还是那个女孩。她说,老莫怎么会来超市呢?这超市已不再是老莫的了,老莫把超市兑给了她,说着她还拿出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的名字叫吴永莉,超市的名字也改成了永莉超市。
老莫失踪二十四小时后医院报了案:病人莫忠失踪。
老莫失踪二十天后,是那个月的二十五号。那天晚上,余粮人不知怎么就跑到了老莫的超市前。不,现在应该叫永莉超市了。那时,超市已关了门,空空的超市门前没有一个人。余粮人走到窗户前,站在那里犹豫了好久。二十多天了,老莫像是死了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有了一点音信。余粮人觉得自己有些可笑,人都没了,怎么还把希望放在那只花盆下呢。想到这儿,他折回身又回到超市门前的那棵树下,从身上掏出一支烟点着。
儿子自从老莫失踪后,也从他眼前消失了。儿子把订好的新房退了。他明白,儿子是在用这种方式责怪他。他觉得他和老莫一样,也是欠债人,不过,他是欠儿子的债。老莫可以跑路,可他跑不了。
余粮人一连抽了两支烟,然后才站起身,他又走向了那个窗台。他轻轻地抬起那个花盆时,既希望花盆下有钱,又怕花盆下没钱。他将手轻轻地探进去,好像花盆下有条鱼,一惊动那鱼就会游走。他的手慢慢地向花盆下游走。当他的手触碰到那迭钱时,余粮人心里一阵欢喜。他赶紧将钱揣进衣袋里。
回到家,余粮人将钱拿出来一数,这一次竟然是两千块。余粮人有点不相信,好像是在做一场梦。老莫或许就在麻城,只是躲在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他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接下來的几个月,余粮人每个月的二十五号都去永莉超市,而且每次他都从那只花盆下拿到了数额不等的钱。
又一个春天来临,余粮人把那辆放置在阳台上好多年都没有骑过的自行车翻找了出来。自行车的轮胎有些跑慢气,链条也断了。他将自行推到西街那家自行车修理铺,让修车师傅把自行车修理了一遍,给轮轴上了黄油。他上去试着骑了一圈,真还不错。余粮人从那时开始,就骑着那辆自行车,在麻城的大街小巷里游转。他想,或许有一天,在某个巷子里就遇见了老莫。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芦芙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陕西省文学艺术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雨花》《长江文艺》《作品》《小说选刊》等刊。出版《一条叫毛毛的狗》《袅袅升起的炊烟》《扳着指头数到十》等多部小说集。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商洛文化》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