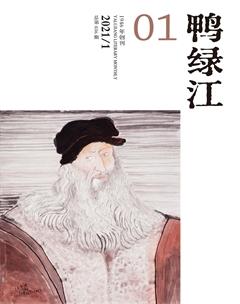旅顺灰
莫奈有两幅小画,一幅是《圣达特里斯海滩》,另一幅是《勒阿弗尔港的郊外》。法国诺曼底的风光与旅顺非常像,礁石、港湾、住房和路径都像。我看这画,就想旅顺,想旅顺路口海风的声音。
其实相像止于表面。
勒阿弗尔(LeHavre)港适宜用散漫的文字和模糊的油彩。那里生产出莫泊桑和莫奈,他们所见证的是自我的海蓝色。
但旅顺则是海灰色,不适宜文艺,它适宜战事、政事、史料、墓碑和累累骸骨。多少战争见证,要塞四处是云海的色系。
从大连到旅顺有一条铁路,我从小去旅顺就走这条线。从周水子上车,经革镇堡、夏家河子、水师营,平缓慢行,最后到旅顺火车站,要走1小时50分钟。每年过完“五一”,樱花缤纷的时节,学校就组织我们去,举着红旗,唱着凯歌。
第一个地方肯定是去万忠墓。万忠墓是一个大墓园。大墓园里有一个大石碑,纪念战争中被杀害的中国人。那里尸骨无整,灵魂无名。记得我们小学有一批红小兵就是在那里宣誓入伍的。
第二个地方肯定是旅顺日俄监狱。从万忠墓上一个坡,走几条街,那一围的建筑就是。囚服灰色,俄式高墙。1902年由沙俄始建。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再建,是东亚当时最大的监狱。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战事与政事是历史的主要课题”,这话放在旅顺是可以得到全解的。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最终的落脚点就在那间绞刑室里。绞刑室的墙根下有一片潮湿,散发着霉味,还有消毒水,至今还在我头脑里萦绕。
所以,理解当年,理解当时的教育。那是一代的我们。
后来我们一代更新,发现旅顺比仇恨和斗争要大,而且大很多。看日俄战争的二〇三高地,看俄军少将、旅顺要防司令康特拉琴珂的官邸,看乃木希典给小儿子乃木保典少尉题写的墓碑,看最早的关东军司令部,看最早版本阿·斯捷潘諾夫的《旅顺口》,那些可寻到的见证,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性的。
反复性,才能看实质。
战争与政治从来都是实质,但实质之下,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无论百姓还是贵族,都归于大地泥土。
大地泥土集聚在战争中,成为战壕掩体,成为堡垒工事,成为军港堤坝,但也留存泥土的湿润与生殖。我凝视旅顺半个世纪了。比如樱花,比如炬松;比如地板,比如棱角窗户;比如哥特式穹顶;比如折中主义天井;比如浮士绘明信片;比如1905年圣彼得堡第一台巴扬;比如1917年前田松韵设计开馆的旅顺博物馆。虽不过是废墟上几样奇异的建设。
请原谅我那时年少,容易把海灰想成海蓝,耽于感性,行于倔强。
六年级那次去旅顺回来,老师要我们写参观体会,同学都写旅顺承受的苦难,我写的是旅顺的美丽,“……我要是能生活在那里就好了,我会每天画画,画樱花,画炬松,画好了寄给毛主席看。将来我还想当瓦匠,也能建那样漂亮的房子和街道,让劳动人民享受。”
老师在全班念了,同学都笑了。老师动了感情,启发着我:“咱们中国有梅花,有松柏,有翠竹,咱们是不是更应该去画咱们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一个孩子才慢慢懂得一个被殖民过的土地有着怎样的伤痛与敏感!
那时最明确的认识就是,旅顺是军事禁区。前后多少生命逆孽啊!进,进不来;走,走不了。
我少年时有一个朋友,叫李赫,就称他为旅顺孽子吧?
李赫1956年生于旅顺,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苏联人,他有一头密实的波浪卷发,绰号“瓦西里”。他上学时全家从旅顺搬了出来,从此再没机会回去。但他对旅顺像对生身母亲一样,一切有关旅顺的东西都珍藏好。俄国作家阿列克山大· 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写有两卷本《旅顺口》,我就是在他那里知道的。那个时代,他大概视这本书为自己的前世今生吧?我几次都没有借出来。
李赫1975年秋下乡在海猫岛,离旅顺城区二十多海里,养海带与收海带。1977年春,渔民捕捞时捞出一枚苏联水雷,他去摆弄,给炸死了。生在旅顺,又死在旅顺,都不是他自己决定的。思想起前因,我心有哀悼。
《旅顺口》再版,我买来读了,里面讲日俄战争时期沙俄海军在旅顺口的活和死。有这样的句子:“太阳刚升出海面,并不鲜红的光芒照着平静的水面。西方,直到海天一线处,都是一片茫茫,而在东南方向,那波光闪耀的海面,却清楚显现了日本整个舰队,分成三个纵队向旅顺驶来……黄金山峦和老虎半岛掩住了海岸炮垒与驶到外面碇泊场去的舰队……”
了解作者阿·斯捷潘诺夫是后来的事情。我在悄悄接近他,也称他为孽子吧!
斯捷潘诺夫生死不在旅顺,但那部长篇《旅顺口》却最能见证他生命的体验。对我而言,一想到旅顺烽烟,就想到《旅顺口》。他父亲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斯捷潘诺夫是旅顺老虎炮台司令,双腿炸断,终成战俘,1905年底被押解到日本长崎并死于那里。小斯捷潘诺夫也被押至长崎,他随身藏着一张照片,是他12岁时跟母亲在旅顺普希金小学门前的合影。他后来回忆道:“战争很长,很长,所留下的只有这张照片。而幸福生活则很短。因为很短,几乎每天发生的事情我都能够说出……窗户朝南的餐厅……听到父亲坚实的皮靴脚步,往往是母亲先进来向我和哥哥使了一个喜悦的眼色……”
童年心有千千结,但终躲不过战争、战役、战略战术和你死我活。他后来回到故乡——乌克兰敖德萨,后来又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1965年,他病逝于乌克兰的克拉斯诺顿。孑然一身苦,只剩《旅顺口》。思想到这如此的生命后果,我心有惺惜。
战争是残暴的战争,和平是敌意的和平,一百多年,在国际关系史和旅顺地方志里,只见背景、条款和战争进程,只见胜利者的意志,只见强权的智慧和力量。之外的男人、女人和他们孕育的生命及其未来统统风过水沉。比如背景,比如产房,比如课堂,比如爱情,比如家舍院落,比如尸骨落处。斯捷潘诺夫一家居住的那条街,地方志记载,沙俄时期叫普希金大街,日据时期叫乃木町四丁目,解放后叫得胜街。
但要说,旅顺之地还是宽容。
罗曼·伊西多洛维奇·康特拉琴珂的墓穴至今还在。他是俄国陆军少将、旅顺要塞陆防司令官,1904年冬天就埋葬在旅顺白云山,与海角平面。最后一次祈祷会,康特拉琴珂领喊“皇室万寿无疆”。参加祈祷会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武威”号舰几百个官兵,没过几天都葬身在旅顺老虎尾海域。都是谁家的儿子?都是为何而来?
乃木保典的坟墓在二〇三高地的山脚下,有墓碑,没尸首,碑字是其父乃木希典手书。春夏还好,有树荫庇,还有虫鸣;秋冬寒风北来,它就孤零零了。旅顺大地慈祥,它肯于收留。黃土少,石砬多,一样可以安魂。
2005年,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我领日本和韩国留学生来过这里。让青年看战争死者,一直是我的用心。乃木保典是少尉,死时十八岁。当初如果不这样死,他们应该有第五代了,乃木家族也一样会有樱花丛一般的景观。
其父乃木希典是日本第三军司令官,旅顺要塞夺取了,伯爵荣誉也获得了,这等“辉煌”的背后,有在金州葬身的长子乃木胜典,有在旅顺葬身的次子乃木保典。乃木希典是他们的父亲,也是他们的长官。长子死了,他写下“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次子死了,又写下“有死无生何足悲,千年不朽表忠碑”。都是高高在上的长官口气。
乃木希典的阴魂是旅顺无法躲过的陈列。在云海雷电里,日本人把他看作战神;在我眼里,神和鬼是一个意思。
日俄战争围攻总共332天,多少万战死骸骨埋葬在旅顺就不说了,就说中国一炬焦土,就说俄国灾难相接,就说日本经济败衰,1905年一张《朴茨茅斯条约》,被沙皇占领的南满和辽东半岛又被日本侵占。列宁写《旅顺口的陷落》,称其为“粉饰的坟墓”。
“粉饰的坟墓”,谁逃得出?话说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死,乃木希典一直静默守灵。9月13日,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与其妻静子一道剖腹自杀。
寂生不如血死。静子文疯,每天跪对墙角说:“你是胜典,你是保典,你是樱花又开,这次都不要谢啊,要等我,一定等我,我一个人过去,不让军舰去,不让你父亲去,咱不让他去。”这话语重复了整整八年!
乃木希典其实心比妇人。他看到妻子的血色暖暖流出,一下子闻到了儿子们,都是胎育挑破的味道。他这一刀自剖明明是要乞获双子的宽恕,却偏要说什么为圣忠天皇!可那一时刻,静子也好,乃木希典也好,听没听到中国无数父母儿女在阴间的呻吟?
战争岸然,基本是这种本质!与谢野晶子(Akiko Yosano,1878—1942)1904年写下反战诗《君勿死去》,公开寄给去旅顺打仗的小弟。今天再读来,有同感泪流。
我为小弟泣啊,泣弟勿战死;
家中最幼是你,父母最念是你。
父母何曾这般教你,这般拿尖刀,这般杀死人家兄弟?
父母养你二十四载啊,我的小弟,
哪里是要你这样去异国他乡,先杀人,后葬己?
……不要说旅顺城失陷,不要说旅顺城夺取,
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天皇不会去那里,不会靠近战役。
如此皇恩啊,如此的圣旨——
让你们流血,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在那边异国的荒野啊,却说那是什么英名传世。
哭天抢地!嘶哑成诗!
我在想,能不能有一天,把这首诗雕刻在石碑上,用中文、日文、朝鲜文、俄文和英文并排写出,就矗立在旅顺城区的入口处?海灰色作底,云白色作字。
这肯定是幼稚的思想,或者说幼稚的心性,但我觉得坚持这种幼稚会很醒心,你看海灰色是不是比海蓝色更能有压力感?
【本辑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王陆,祖籍山东文登,1960年生于大连,1982年7月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从事中学教学和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现自己开办“王陆教育坊”。2003年开始在《散文》《南方周末》《青年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先后有《1978年之恋》《朝鲜之歌》《蝴蝶有声》《讲汉语》《如果精神可以停泊》《否定》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