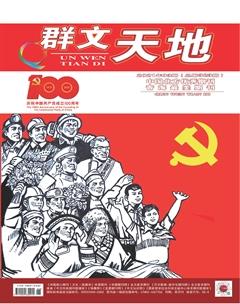忠诚铸春秋
李海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习主席的这段话有力地诠释了核铸强国梦的深远意义。“两弹一星”事业培养出了一支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科技和建设队伍;创造了国际科技史上的不平凡,为中国国防安全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这项艰苦卓绝的事业中所孕育出来的红色精神,永远值得中华儿女代代弘扬与传承。
——题记
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来之际,笔者深入采访了居住在全国各地近百位“两弹一星”建设大军的亲历者,其中点火装置组的孔祥顺、郝金玺、赵炯、王自和等就是这支科研建设大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研小团队。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他们默默无闻地投身于这一伟大壮丽的事业中,他们是茫茫人海里最平凡的一员,他们是大海里最美的一朵浪花,他们以无声的誓言使青春绽放了最绚丽的色彩。
1960年7月,孔祥顺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四室一组工作,组长是宋家树。
“其实,刚到九所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单位保密要求很严格,上班必须拿着出入证和工作证,才能进出单位大门,门口都有解放军站岗。我们每天到所里上班时,得先把保密包从保密室拿出来,保密包都是用橡皮泥封好的,上面有戳有印。我们打开橡皮泥封印,记录每天的工作问题,下班后,再用橡皮泥将保密本封起来,交给保密室。必须做到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不能说。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坐在对面的同志干啥我不知道,我干啥他也不能问。比如到书店找出要看的书,首先得看看周围有人没,没有人才能拿出来看,有人就得躲避着点儿。”孔祥顺回忆道。
进入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的孔祥顺除了上班,只要有空就赶紧跑到情报所、图书馆等地努力寻找、查阅相关的资料,为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大量的储备。不久,所領导派孔祥顺到二机部五所(通县)去实习,任务是了解掌握铀的冶炼知识及学习氧化铍坩锅制作,主要学习铀-238,还没有接触铀-235。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饭,五所自然也不例外,刚到那里实习的孔祥顺和同事们,虽然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没有力气,但是,每天还得到地里打猪草喂猪,完成领导规定的60斤猪草任务。他们从夏天到冬天干了将近半年,直到没有猪草可打时,才进试验室实习。当时,五所的试验室只有一个从苏联进口的小钨丝炉,100毫米直径,高约400至500毫米。在试验室科研人员的带领下,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铀,接触到了提纯铀的坩锅,将坩锅放在钨丝炉上提纯铀,加1000多度高温使铀溶化,挥发杂质,提纯,制成铀锭。他们跟着五所的科研人员认真学习,虚心请教,从不懈怠。一年后孔祥顺返回九所四室。
二
其实,二机部九所四室当时也没有什么试验设备,一台进口的5公斤真空感应炉是他们唯一的设备。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条件,组长宋家树积极调动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自己动手制作试验所需的一切工具。孔祥顺小组的任务是制作提炼铀的氧化钙坩锅。刚接到领导命令时,孔祥顺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在五所实习时见过氧化铍坩锅,但氧化钙坩锅是如何制作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面对班组成员们的一脸茫然,孔祥顺经过冷静思考,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试验室搞调研。于是,他孤身一人跑到北京大学、原子能所等单位去调研、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多方请教与学习,终于搞明白了制氧化钙坩锅所需要的材料和粘结剂等成型及烧结工艺。然后,他就带着研究小组人员,开始了艰苦的筹备工作。首先购买材料,模具由小组成员动脑筋设计,然后再找加工厂加工出来。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开始摸索做试验,他们先将氧化钙材料就像蒸馒头和面那样和成块,反复揉搓成软硬均匀的团,然后放进模具里压制成形,按照试验需要,将其制作成一个适合提纯铀的坩锅。
上世纪初的东北大地,因为拥有丰饶的土地,招致外国贼子的极度垂涎,而使之沦为灾难深重之地。处于内忧外患中的祖国,遍体鳞伤,极度羸弱。1935年5月30日,在长春大地上,一个聪慧的男婴孔祥顺降生了,这对于给资本家、日本人扛活儿,靠出卖苦力艰难养活家的年轻的孔父,无疑是十分幸福的,望着初到人间的儿子,孔父的心里流淌着喜悦,他暗暗下决心,无论吃多少苦,都要将儿子培养成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境的贫寒,反而锻炼出孔祥顺刚毅的性格。弟兄俩,作为老大的他很小就非常懂事,他知道父亲出去扛活儿很辛苦,幼小的年纪就开始替母亲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比如扫地、喂鸡等,稍大一点后就什么活儿都得干,比如买柴、劈柴、担水等。长春的冬天特别冷,马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一个冬天都不会融化。在那滴水成冰的冬天,他经常拉架子车到木工厂去买板皮当烧柴。由于天太冷,他的手指头经常被冻僵,回到家后,无论冻得多么厉害,母亲总是先用雪使劲给他搓,每次都会把他那双稚嫩的手搓烂,但必须得慢慢让手指头缓过来,从不敢用热水洗,否则,双手就会被废掉。幸好母亲有经验,才使他的手没有落下冻疮顽疾。
尽管家庭条件很艰苦,但颇有远见的父亲尽力供他们弟兄俩念书,希望他们能够学点文化。到了入学年龄,被母亲牵着手领进小学校的孔祥顺,心情是忐忑的,学校里那么多学生,令他有些不知所措,他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母亲将他松开。母亲柔声安慰他:“儿,不要怕,到学堂要听先生的话,与其他人好好处,好好念书,进去吧。”那时候还是伪满洲国,小学是日本人办的,得学日语,孔祥顺很快就熟悉了念书环境,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得到老师的夸赞。到他念初中时,长春解放,他进入公办学校念书,学费不高,为家庭减少了很多负担。上大学时有助学金,吃饭不花钱,他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1953年,我考入哈工大金相热处理专业,班里共有50多人。1958年,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下调令,从哈工大抽调了10个人,到北京学习第二专业,其中就有我。那天系主任把我们10个人一起叫到他到办公室,正巧赶上学校停电,主任点了根蜡烛,除了那点烛光,房间四周黑咕隆咚的,他严肃地告诉我们:‘这件事儿很秘密,中央组织部下调令让你们到北京学习第二专业,到那儿后,除了好好学习之外,你们还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其实,别的不说,我觉得当时点着蜡烛的那种气氛就很神秘。第二天,我们10个人从东北坐火车赶往北京,经过两天的颠簸后到达,下火车时,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接我们,10个人就那样嘁哩喀喳地把行李往大卡车上一撂,大卡车从北京站一直开到清华园。一进清华园,我立刻明白了,心里既惊讶又很自豪:哎呀妈呀,我这是到这儿学习来了。当时,从清华大学抽调了8个人、从北京钢铁学院抽调了9个人,加上我们10个人,共27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班,学习反应堆活性材料及结构材料专业,代号230专业(核材料)。校长是蒋南翔,系主任是何东昌。在清华大学,同时抽调进来的同学也都是在其他院校学习4年有余,基本临近毕业,学校将我们230班叫跃进班,因为正值大跃进时期。当时清华大学这个专业只有三年级的学生,四、五年级还没有学生,所以,我们到那里学习两年后就可以参加工作,比清华大学本专业的学生早一年毕业。我从1953年考上大学一直到1960年毕业,整整深造了7年。”孔祥顺说。
西北工业学院航空材料专业的郝金玺也与孔祥顺在一起工作。他们在九所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与锻炼后,1963年,领导交给他们组一项任务,即研制代号9502部件。生产部几乎没有任何加工设备,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试验室。“既然自己没有生产条件,就得想办法创造,那就是利用外部条件搞自己的试验。”诚然,原子能所(401所)是他们搞试验的最佳去处,那里有与他们研究专业相对口的科研团队和试验场所。那是1963年底,隆冬季节,幽燕琼花飘,长城雪茫茫。冒着极度严寒,带着试验任务,汽车把他们拉到房山县坨里镇原子能所。王树仁,1956年北京钢铁学院毕业,是六室攻关小组组长,带领他们攻关。顾问李林(李四光的女儿),是六室主任,何泽慧是技术顾问。他们去的5人分别是王凌峰(六级车工,手艺高超,从无锡调入)、刘雨林(钳工,志愿军侦察排长,转业后做钳工)、郝金玺(大学生、党小组组长)、孔祥顺(组长)、晁富海(中专生)。最初派的技术攻关小组三人中只有郝金玺是党员,王凌峰与刘雨林是后来派的两位技术工人。刚去时,他们5个人配合六室攻关小组同志一边搞科研,一边努力学习。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将9502部件做出来,由于科研任务非常紧,他们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连过春节都在攻关。整个科研小组的人基本是连轴转。“一开始我们谁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部件就像乒乓球,但比乒乓球还要小,我们严格按照领导的要求,先采用紫铜管,用液压吹出个泡,装入9501粉末后,再将其封起来。制作出来一看不合格,就再改,如此反复。但是,这样制作出的壳不均匀,厚薄不一样,形状尺寸都不规则,更谈不上精密度,最后这个方案被否定。后来改成用机械加工这个方案,即用金属材料制作成两个半球壳。在车床上加工,对這个球壳有很高的尺寸精度要求,有形状公差的要求,要求十分严格。首先把两个半球壳加工出来,然后把两个半球壳对合粘接,再在一个半球顶端切一个小口,目的是装入9501粉末(9501粉末是由九所的王方定小组研制成功的。)最后,用一个小塞子密封口。”孔祥顺回忆说。但如何解决小球内装入材料的密度,因为尚处在研制阶段,大家谁也不知道。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晁福海说:“如果想要将小球里的粉末装实,我看采用墩的办法最合适。”郝金玺也觉得此法可行。“但问题是用手墩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用力不均衡,会导致小球内所装粉末密度不均匀。”孔祥顺说:“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仪器震动的办法,控制住同等速度和同等时间,这样就可以保证小球受力均匀,从而保证每一个小球内所装粉末的密度均匀。”郝金玺说:“仅震动这一环节,究竟该怎么做、怎么去完成?我们还必须得再仔细研究琢磨,研究所不就是要搞研究制作的嘛,不行,不行就另行改进。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到图书馆找资料,根据资料再做试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之后,终于找到了可以用磁铁伸缩的原理,给磁铁组通上交流电,使其震动。这些工作经验都是我们通过无数次试验慢慢摸索出来的,而做震动所需的仪器全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因为那时候根本没地方买去。经过多次讨论与试验后,我们最终采用仪器震动的办法,解决了装材料的密度与密度均匀这个难题。”
“因为9501粉末性质活泼,具有放射性,操作时需十分谨慎,因此,装入小球时不能在正常的空气条件下操作,必须在不锈钢制作的密闭的手套箱内进行操作。操作箱三面密封,在前面的透明玻璃窗下面留两个口,由操作人员带上厚厚的橡胶手套将两只手伸进去操作,其操作难度相当大。另外,操作箱内还必须充满氩气,操作过程对氩气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的工业氩气不行,就连提纯度99.9%都不行,必须是99.99%。要攻克这道工序其难度也非常之大,怎么办?还得出去学习,搞调研。于是,我们就到哈尔滨等地继续进行调研、学习,经过反复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想出办法将氩气中的活性气体、氮气和氧气等杂质去掉,最后达到提纯99.99%的要求。”孔祥顺接着回忆道。
1963年12月7日,是个令郝金玺终生难忘的日子。他们在对9502部件进行检漏测试时,曾出了一个大事故,这个事故的主角就是郝金玺。原子能所二室有一台从苏联买的氦质谱检漏仪,在当时是属于高科技产品。当时,在全国也只有原子能二室有这个仪器。那天,郝金玺在做9502小球检漏测试,如果小球漏的话,检漏仪器就会报警;如果不漏,仪器就不出声。结果仪器出现了既像响又不太像响的那个样子。郝金玺知道,这个小球的密封是不能出一点问题的,必须要做到100%。当时郝金玺心存怀疑,拿不准。便与孔祥顺组长商量:“组长,似漏非漏的,你看这个小球该怎么办?”孔祥顺说:“那就用温水煮的办法,再检查一下,之前我们也用过这个方法,虽然土但很直观。”于是,郝金玺将小球拿回办公室里,用烧杯盛上水,放在电炉上加热,然后将小球放进去,他就站在烧杯跟前认真观察小球冒不冒泡儿。非常不幸的是,在煮的过程中,小球意外炸开了,里面装的9501粉末全都喷出来了,不但扑了郝金玺满脸满手,连整个办公室都是黑色粉末,他的脸被烧伤了,手也被烧伤了,吸进体内的粉末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孔祥顺正在手套箱跟前正往小球内加粉,有位同志跑过来喊他:“孔组长,可了不得了,出事了,郝金玺出事了!”他赶紧跑过去,到办公室一看,哎呀妈呀,好家伙,满屋子都是粉尘,看到那个阵势,孔祥顺懵了,大伙都慌了,赶紧向所领导汇报。401所的领导们很及时地把郝金玺送到北京的解放军307医院,在医院住了21天。医院上下,从院长到专家都围着他,为他做了最精心的治疗,当时他的右脸颊上被烫伤一大片,右手烧伤严重。出院后,单位还安排他到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去疗养了三个月。
三
在接通我的电话时,电话那端传来了郝金玺老人洪亮、底气十足的爽朗的声音,一口挺标准的普通话。
“我在西北工业学院上大学的时候,被分配在炮弹引信专业,一年以后炮弹引信专业被撤,将我转到金属材料专业,学航空材料专业,毕业后又偏偏搞核材料专业,我这辈子就是与这个点火专业分不开。令我感到无比荣幸的是,研制点火装置组只有我一个人从北京到草原,再从草原到九院,从开始做到底,一直到退休我都在负责研制这个产品部件。我这一辈子主要就干了这一件事!”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郝金玺老人非常自豪地对我说。
郝金玺,原籍河南人,6岁随父亲到西安,在西安铁路小学、铁路中学上学,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弟兄六个,两个妹妹,他是老二。父亲在西安铁路局工作,是个扳道员。拿他的话说:“就和《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干的一样的事儿。”
在大学里郝金玺是班长,表现很好,积极进步。1960年5月光荣入党,先后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学生会委员,同年被作为学校预备教师留校。1961年大学毕业时,二机部到西工大招收毕业学生,结果,审查后有很多人没有通过政审,他们要求学校再补充。因为当时都已经分配完毕,没有人可做补充,只能从留校的学生中抽人补充,郝金玺就这样被抽调到二机部。
当提到那次事故时,郝金玺老人说:“那一瞬间我也傻了,我才23岁呀,还没有谈恋爱、没有娶媳妇呢,这要是身体被毁了可咋办?说实话,处在当时当地,说不怕,那是假的。但又一想,我是共产党员,这事幸亏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换成别的同志,还真不好向党交代呢。”郝金玺爽朗地笑着回忆道。“后来,经过307医院精心治疗后,我的脸上留下一片深色的疤,就像一片胎记,大夫说没有事,半年后慢慢会消,以后不会留下疤痕。果然,慢慢的淡了,也没有留下疤痕。出院后,组织上又让我疗养了三个月,恢复得很好。后来。四室的书记佘平(刁军寿的爱人)找我谈话,问我是否需要换个岗位,我说:‘不,我要求继续回401所攻关,因为我是党员,9502部件是核试验中的重要部分,只要做事就会有牺牲的,能够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来,是我的荣幸,我很高兴做这份工作。就这样,我有幸继续参与9502的研制工作。经过我们大家一年多的不懈攻关,到6月份终于拿出合格产品。”郝金玺自豪地说。
“在原子能所我们只制作了5个合格的9502小球,由我提着装有5个小球的保密包,坐在北京吉普车内,再由两位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端着冲锋枪保护,前座上还坐着一位保卫科的保卫人员,三人全副武装地押着我将小球送到了九所。当时,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呢!其实,押的不是我而是那宝贝小球。我亲自将小球交给九所三室的胡仁宇,由三室对小球进行物理测量。当时九所领导、专家开会,最后决定的时候让我去参加,会议最后选出一个正品,一个备品。1964年9月,要将9502小球运往核试验基地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王淦昌亲自抱着装有9502小球的保密包坐在飞机上,连警卫员都不让接手,任何人都不让碰一下,由他小心翼翼地将其呵护到核试验基地。
后来,关于这个9502还出过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将9502小球从401所交到九所的时候,用一个小木盒子装着,木盒大小约100mm×100mm,是一个约3寸多的方盒。将这个小盒子装上运输车,由保卫科押运,等到目的地时,众人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小盒子了,这下押运人员可急坏了,大家都着急啊,后来,将车厢里的东西全都搬出来后,才找到它。因为它太小了,车在行驶过程中将它颠到地上了。就因为这件事,保卫科专门下了一个规定,以后运输这个9502必须做一个965的大箱子!在箱子里面的四个角用弹簧将其拉住,防止它乱跑,就害怕再找不到它。这是发生在221基地的真实故事。”郝金玺回忆说。
四
“1964年8月份我们将合格产品交给所里以后,10月份我们几个就背着行李上草原了,到221基地去。当时,就把那些不用的、不合格的、有问题的小球装了一个箱子,由我带着,有两个保卫科的人员护送着,坐着软卧,还带着免检证,这东西后来都上缴给保卫部了。这些东西平时打炮用得着。到这里,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因为从北京到草原上的就我们几个人,从401出来,就一个脑袋装着那么点技术,其余我们什么也没有。到草原上后,102车间就给我们了十几间工作间,里面的设备等,都需要重新购置,有些需要自己制造,有些需要订购。当年我们组18人,搞工艺的人占一半,其余一半都是搞检测、测量等工作的。我们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将工作间搞起来了。”郝金玺自豪地回忆道。
“那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其他的,什么危险和害怕都放在脑后了,只想着为党、为国家完成任务。这就是我們所谓的‘干中学,学中干。将我们制作的9502小球内装入9501粉末后,通过‘尺寸精度、检漏测试、密度均匀度、含氘量测量四项检测合格后,这个部件就算加工完成,然后入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国务院给我们小组发来贺电,由周总理签名,大意是祝贺我们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直到接到贺电,我们才知道这9502是做什么用的。非常遗憾的是电文原稿没留下来。”孔祥顺自豪又不无遗憾地回忆道。
“我们在北京将9502部件研制成功后,1964年年底,整个研制小组就到221基地去继续工作。设计部、试验部和生产部三大部迁往青海,理论部依然留在北京。1964年10月下旬,我和我的科研小组来到草原,一分厂厂房建好后,我们直接被分配到一分厂的核心车间102车间点火装置组(工艺四组)。用于原子弹、氢弹核心的部件都是在102车间完成的。102车间放射性和毒性是最大的,所以,当年我们车间职工享受的保健费也是最高的。初到草原,重工段的机床都已经安装到位;轻工段还没什么设备;点火装置组也就是只有几间空空的试验室。我们再次开始白手起家,陆续买回了大小机床、测试用的射线测试仪器、放射源、设备仪器以及必要的物资。不到半年,大伙加班加点地将车间工作的架子搭起来。这中间,我到大连等地考察如何制作手套箱,兄弟单位大力协同,积极配合,给予我们最大力度的支持。只要看到代号是03任务、02任务,一律都给开绿灯,要求他们啥时候做好就啥时候做好,速度非常快,绝不耽误事。因为这些产品做好后要交给部队使用,所以二炮也派了个大校在我们组实习。当年,在原子能所我们是靠外部条件在搞研制,转到221基地102车间后,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产线。之前,检漏用的是原子能所二室的氦质谱检漏仪,现在,我们终于采购回了属于自己的仪器设备以及必要的生产所需物资:大小机床、手套箱、振动台、气体净化装置和气体分析仪、英国进口的氦质谱检漏仪、性能测试用的射线测试装置、放射源、手摇计算机等,9501粉末制备装置也移交给我们,并入工艺四组。经过紧张的调试,各小组基本达到开工生产条件。1965年开始9502产品进入试生产和批量生产阶段,直到交付部队使用从未中断过。随着核弹小型化、武器化,9502产品也有所变化,在后来的多次核试验中,我组都有人随行跟踪测试,圆满地完成了历次的任务。”孔祥顺自豪地回忆说。
“1969年3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草原,作为先锋到四川筹建九院,在那里搞9502工号的设计、设备、订购等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奋战在点火装置这个岗位上,可谓是为核武器事业做出过无悔的奉献,直到1997年退休。”郝金玺老人自豪地回忆说。
“虽然当年我曾受过伤,但是党和国家给予我很好的治疗,我非常感谢党、感谢解放军307医院,他们的医术水平高超,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再加上出院后的3个月疗养,使我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心灵上也没有留下任何阴影。到现在我已经活了80多岁,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两个姑娘一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两个外孙两个家孙,外孙已经工作,一个在成都当律师,一个在澳大利亚读研究生,毕业后已在那里工作。两个孙子健康聪慧,正在读书。”老人幸福地倾吐着自己的心声。
五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铁骨男儿既然选择为国尽忠,就不能在家为父母尽孝、为妻儿尽责。1971年,孔祥顺收到父亲病重、盼儿速归的家书,等他辗转赶回家时,已经离世9天有余的老父亲竟一直被放在太平间里等他,见此状况,这个七尺男儿再也无法忍住那埋藏在心底的悲痛……
为了完成祖国交付的这项无上荣光的事业,孔祥顺与爱人分居12年之久,期间曾有三年没有回过家,但他们对爱的这份执着与守望,的确令人感动。1972年,孔祥顺调入锦州变压器电炉厂工作。刚转到地方的孔祥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如设计、画图等,从组长到科长,再到厂长与总工程师,1984年光荣入党,完成了他人生至真的追求。其爱人是锦州市合成纤维厂化验室工人,他俩是经亲友介绍认识的。婚后夫妻感情笃深,两地分居12年,依然不弃不离地坚守着彼此的承诺。他们的两儿一女均由妻子独自抚养长大,其中的艰辛与苦楚只有妻子自己明白。孩子们在艰苦中健康长大而且都很有出息,小儿子在民航工作,大儿子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女儿一家定居天津。如今,87岁高龄的孔祥顺老人,儿孙绕膝,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点火装置组在五所完成最初的研制工作后,从长城脚下迁移到金银滩草原,他们不但建立起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产线,还扩大了人员队伍,由最初的5位扩大到18位。王自和与赵炯就是1964年随着大队人马来到这里的。当年在北京时的5个人,到基地后就成为组里的老技术骨干,他们积极推行老人带新人,师傅带徒弟。车间新分配来了大学毕业生、老工人(车工、钳工等)、青年学徒工等,扩充到18人。这18个人,又分为加工组、粉末填装组、检漏组和含氘量测试组等。王自和与赵炯就是这时期分配到这个组的,王自和在含氘量测试组,赵炯在粉末填装组。
六
赵炯是河北石家庄人,父亲是军人,驻军北京。于是,全家人随父亲迁入北京生活,从小学三年级他便开始了在北京念书的经历。1964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后,当时曾被两个学校录取,一个是首都体育学院,还有一个是某高校的會计专业。拿现在的话说那些都是三本学校,而当时人们的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赵炯感觉他考的这两个学校离他心目中理想的专业和学校都相差甚远,极不满意,那两个大学他都不想上。也正巧赶上二机部招工,他一想:远走高飞吧。所以,当年10月份,他被招工到青海的221基地。
“我到102车间时,孔祥顺和郝金玺等老一辈技术员们已基本将这套技术研制成熟,所以,我只是跟着他们干就行了。别看这个东西小,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没有它,就无法产生核爆炸。
从理论到变成产品,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的组长孔祥顺,就是将中子源从理论变为实际东西的牵头人之一,这套工艺最开始就是由他们三个人(孔祥顺、郝金玺、晁福海)与五能所的科研人员一起研制的。我到草原上时,正赶上与他们一起购置、安装设备、仪器等,班组人员配齐后,就严格按照任务要求、工艺流程要求进行制作。
我主要做的是装填料这道工序,即先将9501粉末放入手套箱里,再装入9502小球内。从9501的制备,到装入9502,最后把它密封起来,这就是我的工作。仅这套工序,想要将它做好也是很费劲的,因为必须得在手套箱里操作,手套箱里的手套很厚很大,而9502小球就像一个乒乓球大小,平常拿在手里就很难,放进去后戴上手套拿就更难,不但拿住难,手套箱还得充氩气,净化,如果里面有空气,一打开马上燃烧,只有先将箱内环境达到要求标准以后,再将9501粉末瓶子打开,将其装进像黄豆大小的孔里。操作时需带手套、口罩和眼镜,所以,操作起来其难度相当大,从充氩净化,装粉末,到震动其密度均匀性是否合格(要求装填的越满越好,密度越大越好),到粘胶密封,再将其擦干净,烤干,到开箱取出来,完成这一套过程起码需要两三个小时。这还得是技术熟练工,如果技术不熟练,有时候半天甚至一天都完成不了一个。粉末有放射性,一遇空气就燃烧,如果操作不当,一旦吸入体内,便很难被排出,对人体有伤害。这是操作者必须克服的一个难关,首先心里不能惧怕核辐射,要勇敢面对它;其次要胆大心细,技术熟练,这样完成操作就会轻松自如很多。有一次我们在搬迁设备,抬手套箱时,不小心压住了我的脚指头,当时疼得我冷汗直流,再后来就变成了灰指甲,至今一直没有好。这是金银滩草原给我留下的一个永久纪念。”赵炯平静地回忆说。
“‘草原上没有树,我摘一片云朵遮凉;草原上没有水,我却听到了麻匹河的浅唱;草原上没有雨,我就借柳枝将净瓶之水泼洒……当年,草原上没有一棵树,50多年前的草原干旱又少雨,为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为了让后人能够更好地享受绿荫,厂领导年年都号召我们植树,但那时候,我们种的树都不活,无论种什么树都种不活。虽然当时很年轻,20多岁,但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地区挖坑、担水,又抡镐头又抡铁锹的,很费力气,我们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的,关键是还种不活。当时流行一句话:‘头年青,二年黄,三年进炉膛。
我在高原工作10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1975年5月份调回北京。换了新单位,就得适应新环境,自我感觉文化程度不够,就到空军政治学院挂职念书深造。期间我先在北京宣武区文化局上了几年班,后来恢复国家工商总局,我又调到那里去,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后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退休。
2004年,我到草原开会,还专程到纪念碑下拍了照,还雇了个车,专门到一分厂去看了看,当时一分厂是空着的,大门紧闭不让进,我深表遗憾。听说现在那里改成什么火电厂被地方利用了。这挺好。回来后给同事们讲了这个故事,他们非常羡慕:‘说你做的这个事儿很光荣。在我人生的青年时期,能够到221基地工作,这是一种缘分。生命里有这么一段经历,有这么一段过程,自己能够在最美的青春岁月里为国家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每每回忆起来,光荣与自豪便涌满心间。”赵炯的回忆里充满了对祖国、对这片草原的无限热爱。
七
“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是中国历史画卷上最绚丽的一页,也是最令人难忘、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它既创造了奇迹又孕育了精神,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当祖国母亲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科学家们纷纷归国、工程技术人员义无反顾、解放军战士、工程兵、莘莘学子全都听从党的召唤,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从长城脚下转战到青海大草原,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严冬酷暑,集全国之力,集大家智慧,以高度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精神创造出了人类科学技术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有一个美丽的高岭——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河北北部山地交汇,是一处水草丰美、森林繁茂、禽兽群集之地,是辽、金时期的“千里松林”, 历史上作为皇家狩猎之所,曾被誉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清朝著名的“木兰围场”便是此地。
1938年5月,王自和出生在这个美丽的高岭之地。王家世居塞罕坝,农民出身。王自和弟兄5个,他排行老二。家中清一色男孩,其家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其父母负担之重也可想而知,但是,其父母目光之远更让人钦佩。
解放前的塞罕坝,美丽的容颜被外强铁蹄践踏,丰饶的土地被日本鬼子掳掠。出生于美丽高岭的王自和,苦难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但是,性格朴实而坚韧的父母,没有向苦难屈服,他们在苦难中寻着希望的曙光,那就是让孩子读书,读书是他们在黑暗中所能触摸到的唯一光亮!
从被父亲送入私塾开始,王自和也开始了他那艰难的但又孜孜不倦的求学之路。“小时候家境贫穷,不怕姑娘你笑话,我小时候就没穿过囫囵裤子,那时候,在村子念私塾的有20多个小孩儿,我们可都是光着屁股在念书啊。”王自和在电话那端心酸地回忆道。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父母竭力供孩子读书的心情亦可见一斑。大不幸的是,1953年3月5号,年仅42岁的父亲英年早逝,这个日子对于尚未成年的王自和来说是刻骨难忘的。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家庭重担自然就落到了母亲柔弱的肩上,带着他们5个孩子,柔弱的母亲真是受尽了苦难。为此,他刚20岁的大哥就过早地成家,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家,由他大哥和大嫂帮着母亲一起支撑,一家人勉强度日。
在困苦中煎熬的王自和终于考入初中,后来他的三弟也考上了初中。但家里實在太困难,大哥出于无奈,只好到学校找领导谈,让他俩其中一个回家,留一个念书,于是他的三弟无奈休学,回家放羊。弟弟的成绩也很好,每每看到不能上学念书的弟弟,王自和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总感觉是自己欠了弟弟。好在一年之后弟弟返校复学,这令他开心得不得了。弟弟初中毕业,被保送到承德师专,1961年师专毕业后,光荣入伍,在齐齐哈尔服役16年后,复员到承德市公安局工作。上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家里更加困难不堪,所以,最小的两个弟弟没有机会念书,至今在家务农。那是在吃大食堂的时候,母亲在食堂做饭,需要经常推碾子磨高粱面,由于出汗着凉,从此一直咳嗽,由于家贫没钱医治,最后发展成哮喘病,最终带着没有看到儿女全部成家的遗憾去世,享年69。“我一直非常感恩哥哥嫂子支持我们上学,如果不是有哥哥嫂子的大力支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王自和感恩地说。
1959年,王自和考入太原机械学院机械专业,半学期后,即1960年1月学校选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师资代培班进修,学业四年,专业物理,毕业后回原校当教师。进入哈工大,他们班有20多个人,学校没有为他们单独开课,跟着原招生的本科生一起上课。
“经过三年困难之后,国家进行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当时有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高教部作出规定(部长蒋南翔),凡在外校代培的学生原则上一律归所在院校。鉴于这种情况,哈工大就撤销了物理师资代培班,按规定当时到哈工大进行代培的学生都要返回到自己原学校。因为我原来的学校与哈工大是一个系统,当时学校派了我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到哈工大进行代培的,那个同学现在江油。记得太原机械学校给我们来信说:‘你们的出路有三条,一留在哈工大念书;二回太原机械学校等安排;三学校不给安排工作,你们被下放回家。我们考大学就是为了念书,下放回家算干什么的?于是,我和那个同学商量:‘咱们不回去,就留在哈工大继续念书。就这样,我成了哈工大工程物理系试验核物理系的学生。”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政治思想进步,王自和光荣入党。进入大学后,很快就成为学生骨干,担任了班干部,当了四年支部书记。在大学里,无论学校有什么重要的学生工作,都靠学生干部积极配合去完成,王自和是政治思想进步的学生干部之一。“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的思想都很单纯,政治工作比较好做,同学们都积极要求入党,作为班干部,我除了努力搞好学习外,就是全力配合学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王自和谦虚地说。“在大学里,学校每月给我发13.5元助学金(一等),就是我全部的生活费,没有其他零花钱。当时正遇到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每人每月定量30斤粮食,我们班有5个党员,全都以身作则,带头吃29斤。因为在那个年月,除了主食,没有任何副食,人人都饥饿难当。记得很清楚,冬天我们吃的是附近农村种的小白菜,后勤负责人将小白菜从地里拉回来垛在食堂的后院里,那白菜冻得硬邦邦的。吃的时候,用镐头刨下来,搁锅里一煮就是一顿菜。当年我们正值青年时期,每天活动量很大,吃不饱饭,就喝酱油汤或喝盐水充饥,好多同学都浮肿。等到1963年时,助学金提高了3元。这就好多了,紧紧手,积攒一段时间,还可以利用这3元钱买一些书和其他必须品。在大学期间,放寒假我从不回家,一是交通不方便,那时候哈尔滨火车站一天就有6万多人进出,回家一趟相当不容易。二是利用寒假在学校里勤工俭学、努力学习。
那时候因为家里贫穷,大冬天只能穿单裤子,连秋裤都穿不起。哈尔滨那彻骨的寒冷,王自和的腿被冻成了严重的关节炎,毕业后又直接分到青海去,那里依旧是高寒之地,在高原寒冷的地方工作生活,当年的医疗条件落后,没有机会治疗,这个病便一辈子就好不了。在青海到6月份他还得穿棉裤,如今随着年龄的老化,他的腿疾也越来越严重,成为陪伴他一辈子的顽疾。目前只能采取保暖的方法,吃药打针等都不管用。
笔者与这些老人采访、沟通的过程,就是揭开每一位老人那平凡而又波澜壮阔人生的过程,这一过程仿佛是在品鉴一首苍凉悲壮的史诗、翻阅一本厚重的史书、查看一部跌宕起伏的鸿篇巨著!
八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随着大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起奔赴青海金银滩草原。被分到102车间的四工艺组(小球组),参加9502小球制作。当时很保密,小球组是干啥的我不知道,我们平常上食堂吃饭、参加职工娱乐活动时,都是一个车间职工一起玩的,但是谁是干啥的,那是不能说也不能问的,所以,彼此之间除了一个组的人知道,其余组的还真不知道都是干啥的。”王自和说。
“在制作小球的过程中,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首先车工得将半球车出来,要车出合格的半球,还得改进车刀,即将车刀改进成能够车出半球的刀,此工序非常复杂,由技术员和车工师傅们自己想办法设计完成。其二就是对包装组工序要求最高,小球不能出现一点泄漏。
包装组将密封好的小球交给检测组,我们再进行检漏、密度均匀性与药粉的成分分析和测量,分析它是否达到工艺指标的要求。因为要不断地将9501粉末放入小球内,为此,技术员设计了个专门置放小球的震动装置,小球在震动仪器上放够一定时间后,将它翻个个儿,再做不同方位的检测,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操作,不断地接近放射源。最后通过用放射源照射小球,用计数器计数,半小时做一次,再根据多次取得的计量数据,用手摇计算机算出平均数作为它的参考指标数。然后从众多小球中挑选出质量最好的,完成这几道工序后,才可完成交付。
我们在操作时都是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去做的,穿白大褂,戴铅玻璃眼镜,戴含铅护大襟等。含铅护大襟是挡中子、X射线和贝塔射线用的。贝塔射线是电子流,电子伤眼睛,要用石蜡挡,我们戴的眼镜就是挡贝塔射线的;阿尔法射线怕吃到肚子里去,理论上说是一张纸就能挡住它。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核物理,其中就学过如何防护的内容。知道一个人在一天里接受多少剂量是安全的,超过之后,第二天就不能再接受,尽量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王自和认真地一边回忆一边叙述。
通过在五能所出的那场事故之后,四工艺组的技术员们一直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对小球的制作工艺进行摸索与改进,为保证小球的密封性更好,也为了增加其安全系数,决定不再采用胶粘,而是决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办法——电子束焊法。而这个电子束焊机当时只有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有。
1968年,遵照上面的要求,为改进小球粘接这道工艺,车间领导就联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他们那里有一台电子束焊机,组长派王自和与车间的一个同事(晁福海)到北京电子所出差。这次出差他们在北京待了十来天,那时候王自和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家住东高地。十来天里,他俩跑这儿跑那儿地办事,又累又顾不上喝水,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纪,他更不懂爱惜自己的身体,结果导致得了肝炎而自己还不知道。
“12月5号那天早晨,我们办好事情准备回青海,邓稼先和马所长他俩却在花园路3号院里等我们俩。见到我俩,邓稼先就问我:‘你们买火车票了吗?我说:‘买了。他说:‘你们马上去退票,再买飞机票,坐飞机回去,前方急用你们的东西。我说:‘那好,我们马上去退火车票,赶紧买了飞机票,票价141.7元钱。我们乘坐的214次航班,这是小型飞机,可乘坐24位乘客,当时都是客货混装。我们回去那天,飞机上坐了12个人,还装着大麻袋,也不知道麻袋里都装的是啥,12个人都是221基地的人。飞机是早晨8:40分从北京起飞,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在飞机上,更是难受得不行,一路飞机还一老起飞再降落的,到包头降落,到呼和浩特再降落,到银川又降落,吃过中午饭起飞,最后到兰州降落,一路飞得很慢,每小时飞350公里。当时我特别不想坐,就想下来。在兰州,我们住进机场招待所,当晚,机场的保卫人员立刻就向当地的保卫部门反映,保卫部门马上就派人来到我们的住处,因为我们有正常手续,兰字839部队、总字819,看过证件,他们问:‘部队还有研究院?我说:‘有啊,部队里这院那院多了!
回到厂里后,有一次我们在开会,郝树深(现在居住在北京燕郊)看到我眼睛黄了,说:‘哎,王自和,你小子眼睛怎么黄了?你赶快上医院去,看看是不是得肝炎了?因为熟悉,我们之间说话那是太随便了。检查结果是我住院了,一下子住了三个月医院,经过治疗才慢慢康复。”王自和感慨地说:“这兩件事值得我回忆。”
九
“我与爱人冉兰平是太原机械学院的同学,她一直在太原机械学院念书,当时我们班只有3个女同学,她是党员,我还是预备党员。我到哈工大上学以后,班上那几个已经结过婚的同学,老张罗着要给我介绍对象,我都婉言拒绝。他们就问我,你在太原机械学院时就没有个要好的女同学?说实在的,在我心里还真觉得与她比较要好。于是,我就给她写信并提出这件事,她也没有意见,就这样,我们彼此确立了关系。我从1960年与她分开,1961年确立关系,一直到1967年才与她见了第一次面儿,中间隔了整整7年。当时,由于她母亲患青光眼,摘除了一只眼球,哥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无奈的她只好放弃学业回家照顾母亲与哥哥,为此耽误了一年学业。幸亏那时候教育部有要求,尽量不要丢失应届毕业生,因为考上大学不容易。所以,校领导安排她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后,让她恢复念书,因此,她比我晚一年毕业。毕业之后,被分到七机部,主搞火箭地面设备。
从1961年到1967年,整整7年,天各一方的我们才见了第一次面儿。我俩都是党员,在对待党的事业的忠诚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彼此之间信任可靠。7年期间我们从未相见过,仅仅依靠通信联系。1967年她写信告诉我她要到太原出差,我一想,太原离青海比北京近很多,就赶紧向单位请了年休假,准备到太原去看望她。整整7年,我俩从青春年少到即将迈入30岁的门槛,都不知道她如今长啥样子了。我从221乘坐火车到西宁,但买不上快车票,只好买了慢车票,先从西宁坐到兰州,再从兰州转车到西安。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1967年1月24号,很无奈,只得在西安住了两宿,然后又从西安到临潼,从临潼又到风陵渡(三省交界地方),这一路都是坐汽车。到风陵渡再乘船过黄河,乘坐的是像大笸箩似的船,那船能坐100多人,过黄河后进入山西地界。哪知道下船后,离火车站还很远,那时候,特别不好坐车,就连行李架上都坐着人。我只得扛着行李步行到火车站。经过近10天的颠簸与周折,总算到了太原重型机械厂。但是,仅在太原招待所住了3天,她们组就接到速回北京的通知,我只好跟随她们组一起到北京。在北京仅住了两宿,我赶紧返回老家探望老母亲。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光在路上就耽误了差不多有10天。
1968年1月27日,我利用攒了一年的探亲假到北京与爱人结婚。那天,我买了一些糖,两条烟招待客人,来来去去的都是她单位的同事和朋友,我也不认识,女的来了就让人家吃块糖,男同志来了让根烟,我们俩就算是结婚了。我患有扁桃体炎症,经常化脓,在青海一个月就犯一次,结婚没几天,这毛病又犯了,在医院做了扁桃体手术,住院15天,出院后,又赶紧回老家看望母亲。回到家里,嫂子听说我的情况后,就说我:‘哎呀,你快赶紧回去吧!就这样一直到有孩子后,我才带着她回了一次老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既然牵手,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王自和平实地讲述着他们的爱情故事,没有小说里那般华丽的渲染,没有小儿女般令人羞涩的软语呢喃,但却令我从中感受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情感、对家庭、对社会的忠诚与担当。在之前的采访中,我未曾敢去触碰父辈们的情感这一页。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伟岸的山、他们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们豪情万丈、他们侠骨丹心,却从不知他们既有侠骨也更具柔情。至此,我才真正看到了生活中平凡的、有血有肉的父辈们!在捍卫祖国国防、在党旗下宣誓时他们是铁骨男儿!在生活中,他们是温情的丈夫,更是慈祥的父亲!
十
“1970年8月15号,北京召开国防科委计划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作为车间选的会议秘书参加的),九院去了70多人。10月21号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我们,所有参会人员都在,我坐在二楼第二排头上,神情专注地望着主席台,不一会儿,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到主席台上,他从容地作报告。记得很清楚,总理先从国际形势开始,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半小时。今生我很荣幸听了周总理作报告,时长达两个半小时,人生遇到这件大幸事,很自豪,终生难忘。
102车间是特殊材料加工车间,对工作人员的技术要求非常高,而所有技术员与技工师傅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是万分谨慎与严格的。记得孙文志师傅他们在制作小球时,特别仔细认真,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精确。他们都是用千分尺(1毫米的十分之一)对每一个小球的尺寸进行精确测量,将多余的部分用砂纸细细打磨,务必做到不差毫厘。对于车工的技术要求也严苛,更加精湛。根据不同型号的工艺要求,技术员和工人师傅们一边干一边想尽办法改进车刀,以适应车出尺寸越来越小的小球部件的工艺要求。
王凌峰师傅,六级车工,所有高难度的活儿,都由他主刀。徐仁智,在四川江油,他也是当年的车工。还有一位是上海崇明岛人,当时他年轻,后来也调走了。”讲到在102车间工作时的经历,王自和的口吻中满是自豪与怀念。
王自和在青海工作了10年,因为高原反应严重,心率过缓,每分钟最多46次。就是静坐在那儿都能听到心“蹦、蹦、蹦”的跳声,数脉搏不用按手腕,直接就能看到脉搏跳。由于心率过缓,后来还得了肝炎,再加上腿疾一日重似一日,无奈只有离开高原,离开他钟爱的事业调回内地。由于种种困难,他当时先调到承德,后来才从承德调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后来在这个单位退休。王自和夫妇有两个儿子,老二儿子自己开公司,离家近,经常回来看望、照顾老人。大儿子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可谓子承母业,干的就是母亲原来所干的工作,经常出差,工作太忙,照顾老人的时间相对较少。老大是孙女,在迪拜读研究生,老二是孙子,才上初中。冬去春来,人生短短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爱侣已经去世7年,说到这里,电话那端的老人沉默了许久。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保存下来的几样东西,成了极为珍贵的資料。因为它是核基地广大基层工作人员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建设添砖加瓦、做出应有贡献的见证。2015年10月29日,筹备原子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等4人,千里迢迢从青海来到北京。由221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衍同志(退休后生活在北京)带领他们来到我家,取走了我的收藏之物(免检证、进京证明、出差介绍信、住宿介绍信、飞机票等)。
1974年,当我从老谢(谢建源)的办公室取回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纪念章时,我感觉这枚纪念章比任何金质奖章都要有价值。因为这枚纪念章包含着我们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王自和的话,令笔者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作为他们的后代,面对这支浩瀚的221大军,感觉自己就像茫茫大海里漂浮的一片叶子,茫然又惶恐,这是整整一代人为之付出宝贵青春的事业啊!我没有能力为他们留住任何东西,只有尽可能地多采访几位老人,尽可能地多听一听他们的讲述,用我粗浅的文字留下他们青春岁月里最动人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