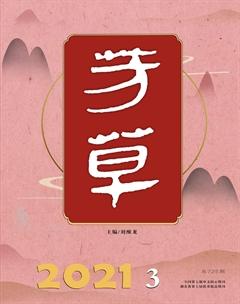有限的谈话
李伟长
一
我早前读过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印象最深的是她作品中独特的叙事语调,一种看似并不热烈的书写,那些克制冷静的词语具有覆盖力。付秀莹建立了属于她的言说方式和观察方式,借由记忆复活了她的乡村日常生活。
獨特性是写作者的良好品质,即我们可以在众多作品中抑或成群结队的写作者种辨认出她来。被认出就意味着某部分文学传统的苏醒和复活,付秀莹是一个受传统叙事影响的小说家。借由布罗茨基的名篇《取悦一个影子》所言,一个写作者多少都在取悦谁,可以是一段文明,一种传统,一类意境,抑或一个他心仪的同行,否则写作的影响并不会发生于现实中。付秀莹作品的语调,有凭吊乡村宁静生活的意图,有描绘城乡生活不同秩序的潜意,她所取悦的是一种雅序,天然秩序,造法自然,各自有其归处,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相宜。
取悦也意味着,一个写作者完全不同的独创性是不存在的,他总有来处。只要能识别出来,就意味着其来处一定存在,只不过因为我们自身的阅读窄门或者纯粹的懒惰,而无暇去寻找这一来处。当然,对于忙碌的解读者而言,寻找来处是性价比多么低的一件事。相比于此,我们更愿意重新命名一样事物。因为命名就意味着占据,甚至是发明,就像在物件上贴上一个个分类标签,昭告过往的朋友: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奥登是幸福的,他有布罗茨基在身后喋喋不休地表达仰慕。仰慕的方式既庄重又戏谑,即学习用奥登的母语而不是他自己的母语进行写作。一则说明奥登的影响之深,二则说明布罗茨基的语言天赋非凡。
将自己归入某一种传统,并尝试在新的时间和空间里赋予其新生,是许多写作者都在致力于破局之事。他需要在传统和个人才能中找到汇合点。
二
一个有来处的写作者是值得谈论的,不承认有来处的写作才需要警惕。从更大的范围而言,一个作家总会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但在中国多少是个例外。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像是西方文学的遗腹子,比如法国文学的拥趸在接续法国文学的命脉,英国文学的粉丝在操心延续英国文学的血种,美国文学多少有些尴尬,既有大师又有美式短篇,更别说拉丁美洲文学的喧嚣和正确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写作者既信心满满,又自卑自怜。比如说起文学的日常生活,张口就是普鲁斯特的蛋糕,要么就是福克纳的南方或者加缪的冷漠荒唐,从来不曾想起《儒林外史》里的生活场景。
承认一个写作者的来处和指出其受影响的传统,并不是揭开面具的武断之举,反而是标出清晰的创作之路,不然丛生的歧路和山僻小路、难以为继的绝路就可能横亘在面前。许多写作者的日常叙事并不值得信任,就在于日常被描述为意外之后的斑斓色彩。叙事语调的独特是一句难以深入推进的描述。在流行对比的评论年代,谈论一个人的写作,必拿另一群人作为对照,这另一群人是不具姓名的泛指,非如此似乎不能立言,非如此似乎不能正名。对比是一条评论方法,但是这条方法则多少显得高低不就,与更高的文学传统对比则有奉承之意,往同代的同行对比则有毁及其余的嫌疑。
谈论一个写作者语调的困难在于赋形,即说清楚这一语调为何物,独特在哪儿,否则就是一句不及物的清辞,听上去有道理,实则无物。如果说评论文章还有一些价值,也就在赋形之能的清晰。和创作一样,评论借助同一种语言来思考问题。付秀莹的叙事语调在“轻”,既有轻盈的意思,也有举重若轻的姿势。不论是苦心经营的“轻”,还是若无其事的“轻”。“轻”就可以是一种语调,当然也是一种观察视角和看待世事生活的态度。与重相比,轻多少受人误解,以为是没有力量的表现。付秀莹小说的“轻”多在回旋之地,在冲突和迂回之间的盘桓,在藏起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之浪的大海深处。
三
以短篇小说《地铁上》为例,篇幅不长,内容却有来处,取其轻,量其重。一个常见的上班族挤上地铁,遇见曾经的男同学,展开了一段谈话。
谈话中,往事与近情相互缠绕,事实与虚构彼此呼应,问题和答复共同跃迁,都在这让人感到窒息的空间里展开。行驶中的地铁车厢不是理想的谈话空间,拥挤,晃动,人来人往,声音嘈杂,给人压迫感。关于这样的题材,我们自然会想起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在小说人物看来,电车里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就是一个不切情理的梦,就像是上海打了一个盹。电车上的男人是在谈情么?未必,可能就是一种想象。难怪小说最后说这是一个梦,而梦总是多情的,也多是自我的。付秀莹将如何处理这个新的旧故事?
小说家做了减法,减掉那些戏剧性的部分,比如男女之情,职场人的苦闷,看看还能剩下什么。相遇在地铁里的男女,并不必然地涉及隐秘的情感,更不必像张爱玲一样拎出极端的情事,一位已然三十五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谈论着要娶一个二房的事,似乎女人还能接受这一层意思。地铁上的两个人没有打开各自心扉,反而是相互试探,这就有意思了。试探式的谈话,还算是有效的谈话么?试探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短篇小说的魅力也就在此,未曾说出的那部分内容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虚构,也可视之为谈话的外围。行走的地铁与停下来的电车不同,地铁终会抵达,而封锁则意味着不可知性。男女相遇,开头所谈,无非近况,再不过是谈一些彼此熟悉的人。
减法之后,剩下的谈话内容就变得苍白,但又不是乏味,而是信任未曾建立的空洞。当两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迅速就以否定的方式进行补救。这是一场无意义的谈话,谈话内容的真实性有几何,我们作为读者,抑或作为地铁里的听者,都难以察觉。事实上,真不真实有多重要呢?但我们依然抑制不住地想知道,这两个人的谈话有哪些是真实的,有哪些是虚构的,又有哪些是编造的?闪烁其中的试探由此就变得意犹未尽却又心照不宣。这场对话的开启者,不自觉地就扮演了一种终结者的角色。试图构建某种统一的关系,一旦被弹回就迅速调整,进入另一种统一性的话题。男人先说了自己的离婚,但是在听到对方说也离了但刚进入新的婚姻,就迅速退回,解释其实自己并没有离婚,不仅没有离,还说妻子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女人,为此还换了大房子。这场谈话的趣味就在这里。
小说家构建了一种短暂关系,又拆解了它。这种短暂关系的本质就是轻,如风过处,雨淋处,事后阳光普照,下了地铁便会结束,似无痕迹,但词语所建立的文本世界不会消失。小说家捕捉到了这点,一种极端情况下的普遍关系。轻不再是相对于重的词语,轻关系就是轻关系,其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不是深厚关系的反面。可视之为小说家的发现。在加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关系的建立常常处于来不及加深的状态,就像朋友圈里的“朋友”,加过微信之后,就算确立了联系,却多止于确立,而少有发展。
四
必须注意到空间,地铁里的特殊空间。
地铁的特殊性在于,合法地压迫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人与人不得不靠近,贴近,甚至相拥。距离本该有的排斥性,在地铁空间中失去了意义,人的防范意识也变得不起作用。经过压缩后的空间,让人失掉距离感之后,并不会变得无所不能,相反是无能为力。
这依然是一种假象,除了可能激发某些意外的欲望之外,大部分陌生人在挤压中变得无所适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依旧难以建立。这意味在人与人离得最近的地铁里,人与人反而离得更远。分离反而在这近距离关系中得以确立。这才是现代社会关系的本质,关系的亲密已经不再依赖距离,近距离可能会促进亲密的分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秩序,谈话双方都没有努力将对方纳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小说家观察到了这方寸之间的躲避和摊开,可见小说家的娴熟技术。尽管情节是老情节,故事却不再是老故事。
紧接着就是时间,不是流动的时间概念,而是另一种被速度裹挟的时间。和空间捆绑在一起的时间,在地铁上被同时快速移动。与《封锁》的暂时停止不同,地铁上的时间依然在流动,因为车在快速流动。时间被速度所抽离,从而悬停在空中。只要速度足够快,时间就会有停止的假象。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时间感。在小说中,这种感觉被赋予了悬置功能,将说话的两个人放置一段被隔离的时间线上。因为是快速流动的地铁上,也因为是在被悬置的时间内,小说中的两个人迅速度过了相识、试探、退守和分离的整个过程。两个人都有目的地,除非约定,他们很难下一次在地铁上相遇。这便是时间的魔力,也是生活的常态。
这次相遇是一个意外。谈话的中间,不是没有可能使这份意外变成常态,但两人的谈话最终没有延续下去。谈话中的交换功能没能实现,即一个人说完之后,另一个人没有沿着谈话的河流继续往前走,期间出现了断裂。双方在特殊空间中建立的关系场域,出现了一个弯曲,阻止了一场直接的交流和后续发展的可能。况且,当一方不再回答,以沉默应对对方的等待,谈话也就只停留于谈话,是词语的散乱对打,留下小说家的左右顾盼。
小说家对待谈话的设计需要像建筑师对待一幢建筑一样,在动工之前,尽可能地设计好施工图,大到结构,小到门窗,微至螺钉,都得万事齐备,不可以随心所欲,凭着脑中的念头,就贸然施工,其结果多半不会工整。经验老到的写作者,凭借经验能大致不差地完成,但经验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特殊空间里的谈话,就得仔细考虑空间的特殊性和旁观者们参与的可能。一旦小说家对此有预设,谈话也就失去了自我生长的可能。
五
相比《地铁上》,付秀莹的另一短篇小说《金色马车》,同样呈现出一种对峙。得体而努力生活的母亲,茫然无所谓的女儿,以及隔壁粗糙的叫骂——冯玉才,你个混蛋。多种叙述声音杂合一起,相互支撑,生成了奇妙的秩序。
生活秩序自身有一种美。疫情之后的生活回到了正常,也就回到了日常。从文学的意义而言,回到了日常则意味着挑战和逃避。关于文学日常的探索,实在过于丰饶复杂,有太多的内容可以缠绕进来。日常到底是什么?是一日三餐,还是每日都有一日三餐?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两年,写了一年生活的详细笔记,第二年就没再写下去,他说第二年和第一年类似,那便是重复,也是日常的精神核心。日常可以被理解为没有主体的参与,每个人都是主体。可以被描述为无聊,无聊又是日常的表象。日常不是可以被抓住的事物,日常就在我们身边围绕,但又以无形之物的方式离我们很远,令我们无法亲身感知。日常无法被任何人抓住,只能被描述一二。日常是一個巨大的陷阱,如果没有准备足够精良的户外装备,不要贸然走入那片日常的森林。
此时吸引我们的不是疫情之后的文学描述,而是生活重回到文学难以描述的状态。金色马车可以飞跃在梦境里,隔壁传来的叫骂声可以警醒梦中人。雅致的对面是粗鄙么?日常幸福的反面是吵闹么?依然是一个特殊空间,依然有对话发生于墙的两面,一面是安宁,一面是诅咒。有一种可能是,“你个混蛋”听上去更像日常生活——
“每一场咒骂的开场白,总是这一句。节奏,语气,腔调,从未改变。通常,骂过一个段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停顿。仿佛是重新上台之前的酝酿,或者是另一场戏剧之前的整理,然后,第二场正式开始。王小红,不要脸。王小红,不要脸。王小红,不要脸。在一连串漫长的重复之后,忽然间爆发出一个高音,王小红,你个婊子养的——之后,又是一个长时间的停顿。”
谁才是日常生活的见证者?如果我们宽容一些,就可以说上面这段对话才是真正意义有效的谈话,尽管用词粗鄙,态度急切,但意义清晰,双方释放的语言信息,都被完整地接收到,并且在停顿和等待之后,得到准确的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讲,吵架是这个世界上最合格的对话,针锋相对,来回自如,又言之有物,不和绝大多数谈话一样意义寥寥。
这是一个黑色悖论式的幽默。
六
被审美化之后的生活和生活中人,已然与他们自身真切的命运无关,他们变成了被牵进小说围栏的宠物,从此得扮演被豢养起来、逗主子高兴的符号——见证者。有理想的小说家就得从这些被豢养的见证者们中,挑选出尚未完全驯服的对象,进行清洗还原出他们原来的样子。因为与记忆搏斗的不止是写作者,还有见证者们的道德水准。
奥登评论卡瓦菲斯说,一个不道德的见证者会说一半真话或者完全说谎,但如何裁决又不关一个见证者的事。证词和裁判的分离,造成了见证者不用承担责任而可以自由行事。把公正的希望寄托在见证者的道德上,和寄托在规则不透明的裁判身上,一样让人无望。何况,有道德的见证者又将如何?抒情化的见证词,和不道德的说谎,一样糟糕,甚至更糟。见证者和见证词并不必然地值得信任,所以选择信赖他们,是我们过于迷恋所谓的事实。一旦当我们能够甄别文学的真实,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供养着见证者们。
付秀莹作品里有限的谈话,是对约定俗成的背离,也是对见证词的告别。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