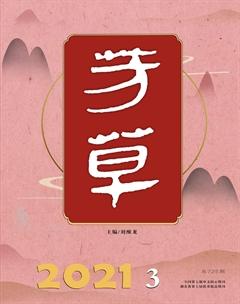或者慰藉,或者馈赠
付秀莹
新长篇完成后,我以为我会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一部,就像以前那样。激情的余烬还在,而灵感的焰火缓缓升腾。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自由出入,我迷恋那种激情燃烧的状态。这是生活的馈赠,慷慨而美好。事实上,我已经开始了。正是岁末,新春在望。春到山河逐日新。这是我当时给《学习时报》写的新年特稿。然而,疫情来了。
我再没想到,疫情竟然改变了我的写作计划。我放下手头的长篇,开始写短篇。疫情期间,我一口气写了十多个短篇。仿佛同一个久别的老友重逢,在多事的不平凡的庚子年,我回到短篇小说,在多年老友那里获得温暖的慰藉,以及绵长的情义。
《地铁上》,写的是地铁上的一段偶遇。封闭的空间,飞驰的地铁,熟悉的陌生人,变与不变,真实与谎言,时间与命运,青春、梦想、记忆以及爱。窗外是北京的夏日,窗内是喧嚣的人间。人物之间的对话漫不经心,牵扯出驳杂丰富的现实人生,挣扎与呼喊,泪水与微笑,心事微茫,泪水飞溅。主人公梧桐与张强的邂逅,看似偶然,其实可能包含着生活的某种法则吧——我不想说生活的可能性。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他们匆匆赶路,来不及诉说,甚至来不及倾听。是地铁,这现代交通的铁兽,城市文明的标志物,为我们的主人公提供了诉说与倾听的可能。他们的对话漫无边际,不时被外界打断。车站,乘客,广告牌,风景,车窗上的映像堆积,汹涌而来的往事。人物對话之间的缝隙,仿佛比对话本身更具有丰富复杂的意味,这是小说内部的张力一种吧。我喜欢呈现这种张力。命运的琴弦在慢慢绷紧,即便是轻轻的触摸,都会发出意想不到的声响。小说最后,人物对话还在继续,却在轻而易举的拨动中,把之前的叙事戏剧化地颠覆了。我不认为这是生活的荒诞。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梧桐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千差万错,来不及修改。张强在短暂的叙事中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修改,仿佛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在一个短篇里虚构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对不圆满的现实生活的弥补吧,亦或是对充满缺憾的命运的抚慰。《地铁上》写得极为放松。时隔多日,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写作情境。几乎是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任何修改。我漫不经心地开始,漫不经心地结束。我在这种漫不经心中获得难以描述的愉悦,以及满足。窗外是庚子年的新秋,果实累累,沉静而斑斓。
《金色马车》中的老太太,其实是我们现实中的邻居。多年来,我们一直深以为苦,后来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候听不见她的动静,我们会觉得纳罕——我不想说是牵挂。这么说吧,这位邻居的喊叫,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这位老太太,称得上是一位芳邻。她容貌清雅,气质斯文,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度。即便是骂人,也是书面用语,显示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良好的教养——我敢断定,她是一个读书人。在电梯间碰上,她微微颔首,算是矜持的问候。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这两年,我们没有看见过她。这两年,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她的声音依然高亢,却渐渐有了力竭之感。间歇时间越来越长,而喊叫的内容经年不变。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人从隔壁进出,中年女性,或许是女儿吧,而那年轻姑娘,应该是女儿的女儿。她们见了邻居,大多是避让的。我猜测,这避让里有歉意在里面,为了老人的扰邻。当然,也为了那歇斯底里的咒骂,不堪入耳的内容。一直以来,我想写写这位邻居,尝试想象一下她漫长的一生,一生中经历的人和事,爱和恨,伤害与谅解,破碎与完整,安慰与救赎。我设想着,应该是一部长篇的容量,用想象和虚构,勾勒一个女人蜿蜒曲折的一生。疫情期间,竟日困在家中。隔壁的呼喊和咒骂如此清晰,如此频繁。高亢的激情中的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中的绝望与无助。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在命运的深渊面前彷徨无地,而夜空苍茫,没有星和月。人心是多么浩瀚的海洋呀,可以容纳那么深刻的痛苦和欢乐,哀伤和忧愁。那些呼喊和诅咒,爆发的泪水,骤起的哀嚎,是理性的崩溃吧,是痛苦的溢出吧。命运的风暴来得如此激烈,在风暴中走失的人,我们该如何用文学把她召回?
我喜欢金色马车这个意象。金色马车,不过是卧室窗帘上的一幅图案。在无数个深夜,窗帘意味着庇护,意味着安宁。外部世界的风雨,被窗帘遮挡。而金色马车,是飞驰和远方,是逸出和越轨。我,母亲,隔壁老太太,女性情感和命运,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逻辑。我不知道,《金色马车》这个短篇能给读者提供什么。我也不敢确定,生活的门轴轻轻转动,转瞬即逝的刹那间,我们能否蓦然惊觉,发现深藏生活中的某些秘密,或者玄机。
值得一记的是,这次写作计划的改变,令我重新发现了短篇小说的魅力。我发现,她自始至终吸引我,吸引我去探索,在人生的狭窄处寻找宽阔,在命运的幽暗处寻找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