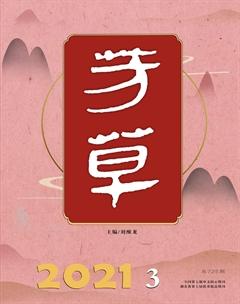地铁上
付秀莹
一大早,梧桐出门赶地铁上班。他们家离地铁站挺近。以梧桐的速度,大概不过走上七八分钟吧。在北京,交通便利顶重要。当初她买房子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这个季节,马路两边的槐树都开花了。槐花的香气很特别,有一种微微的甜腥,丝丝缕缕,直往人的肺腑里钻。那家老魏羊汤门口,早点摊子早已经摆出来了。油条豆浆,烧饼羊汤,包子小米粥。老板娘有三十多岁吧,胖胖的,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围裙,人长得干干净净,叫人觉得放心。梧桐买了油条豆浆,装在袋子里拎着,往地铁站赶。今天有点晚了,她可不想看头儿的脸色。
地铁口附近,停着一大片共享单车,挤挤挨挨的,几乎把味多美的门口给堵住了。有的单车倒在地上,跟着多米诺骨牌似的倒了一片,朝着一个方向,好像是被一阵风吹倒的。人们来来往往匆匆走过,看都不看它们一眼。
地铁里人很多。据说五号线是北京最拥挤的线路,它贯穿城市南北,最北边是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已经属于昌平了。这一站在北五环边上,客流量巨大,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刚才的那趟车没有挤上去,梧桐只好等下一趟。又等了一趟,还是没有挤上去。
这一段地铁在地面以上,从天通苑,一直到惠新西街北口,再往南,就钻入地下,成了真正的地铁。巨大的弧形顶棚覆盖在头顶,太阳透过穹顶照下来,把偌大的站台烤得闷热潮湿,叫人窒息。这种露天站台不像地下的,有空调制冷,凉爽舒适。不断有乘客的脑袋从自动扶梯口升上来,升上来,潮水似的,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车厢口的队伍越排越长,歪歪扭扭,有的还拐了弯,看上去乱哄哄一片。对面的列车轰隆隆开过来,停靠,门开启,一批人上去,一批人下来。站台内回荡着乘务员高亢的声音:请自觉排队,先下后上——一遍又一遍,机械而娴熟。梧桐感觉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来,雪纺衬衣被濡湿了,贴在身上,痒索索地难受。她疑心自己的妆也花了,借着手机屏幕照一照。还好。
直到第四趟车过来,梧桐才被强大的人流推动着,稀里糊涂挤上去。车厢里人挨人,她个头小,被两个高个子夹峙在中间,动弹不得。她把包紧紧抱在胸前,感觉站立不稳,后悔怎么就穿了高跟鞋呢,找罪受。后头是一个健壮的中年女人,印花连衣裙上,开满了藍色粉色的花朵,浑身上下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混合着车厢里的汗味脂粉味大葱味花露水味,叫人头疼。前头是一个男人,牛仔裤白衬衣,背对着人群,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梧桐试图把身子转过来,往旁边挪一挪,却听见那印花裙子哎呀一声尖叫起来。梧桐刚要说对不起,却发现那裙子旁边的一个棒球帽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连好几个不好意思。那印花裙子瞪了棒球帽一眼,没有说话,自顾打开手机,埋头刷起来。经过一阵骚乱,人们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车厢里很安静,也很凉爽。空调制冷的声音嗡嗡响着,听起来一点都不叫人烦躁,倒有几分悦耳动听。窗外,夏日的绿荫大片大片闪过,夹杂着锦绣一般盛开的鲜花。六月阳光下的北京城,显得明亮耀眼,散发着勃勃生机。
梧桐喜欢这段地上地铁。老实说,她喜欢火车,喜欢窗外短暂的一掠而过的世界,世界的片段,像断章,又像是漫不经心的咏叹。坐在火车上,可以看风景,也可以发呆,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铁轨向远方不断延展延展,直到消失在地平线神秘的遥远的阴影中。过往的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抛弃,而无限的可能正隐藏在无尽的远方。她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一种,怎么说,一种不确定的确定,已知中隐藏着未知。梧桐心里笑了一下。她是在笑自己。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居然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忽然有人叫她的名字,竟然是白衬衣。白衬衣说,怎么,不认识我了?梧桐惊叫一声,张强!张强笑得眼睛亮亮的,可能是因为兴奋,脸颊通红。旁边那印花裙子不耐烦地看了他们一眼,嫌他们声音大。梧桐抿着嘴儿笑,压低声音,你也住这边?怎么咱们以前没碰上过啊?张强说,是啊,我还纳闷呢。张强说刚毕业的时候我在方庄那边住,搬过来好几年了。梧桐说,是不是?张强说自从那次吃饭以后,就再没聚过了。梧桐说,都十年了吧?张强说,差不多。
窗外,夏天的北京绿烟弥漫,好像是哪个莽撞的画家,不小心打翻了他的绿油彩,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色块恣意流淌着渲染着,把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弄得蓬勃而柔软,湿润而富有诗的情味。张强看上去变化挺大,人胖了些,脸上学生时代的棱角都不见了,变得圆润,中年人的圆润。下巴刮得青青的,一直蔓延到铁青的两颊,叫人惊讶怎么会那么一大片。眼镜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戴了隐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算不错。干净的衣着,随意却得体。头发依然乌黑发亮,夹杂着少许的银丝,倒平添了一种成熟的稳重的气质。张强说,老啦。梧桐说,你没怎么变。张强说,你倒是没变化,刚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梧桐说,真快啊,一晃十年了都。张强说,一眨眼的事儿。梧桐说,我还记得上回吃饭,大家都喝高了。你酒量挺不错。张强说,你也喝多了,哭了好大一场。梧桐说我怎么不记得了。脸上有些发烧。张强说,你忘了?那一回,你一个人喝了一打啤酒,把我们都给震了。大勋不让你喝,你非要喝,谁都拦不住。大勋。梧桐心里跳了一下。张强说,后来,大勋说,干脆他陪你一起喝,你一瓶他一瓶,那阵势!大勋。梧桐心想,这名字怎么觉得这么陌生呢。张强说,结果,你们俩都喝高了,互相对着脸儿哭。张强说,哭得那个痛哇。把服务生都招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张强说,你不记得了?梧桐却忽然指着窗外,你看,喜鹊!一只喜鹊好像是受了什么惊吓,扑棱棱飞起来。窗外的林木渐渐变得茂盛幽深,好像是一个什么庄园。园子挺大,一眼看去,只见草木葳蕤,遮天蔽日,叫人心里顿生凉意。
又一个站台到了。车厢里小小地骚乱了一阵子,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更多的人依然留在车上。车门关闭,继续行驶。车厢里又渐渐安静下来。梧桐往边上挪了挪,正好跟张强并肩站着,脸朝着窗外。光线明暗交错,混杂着乱七八糟的阴影和光斑,在张强脸上变幻不定。窗玻璃上映出他们的影子,一时清晰,一时模糊。头顶的通风口呼呼呼呼吹出一股股气流,把梧桐的头发弄得有点凌乱。张强说,那什么,你还在学校?梧桐说,对,教书。你呢?张强说,我啊,我这故事就长了。A Long story。梧桐说,是不是?张强说,我都换了好几个地儿了。惊讶吧?梧桐说,有点儿。张强说,当初能留校,多少人羡慕啊。本来都打算好了,边工作,边读研,再读博。这年头儿,在高校,博士是必要条件。梧桐说,要想搞业务,肯定是。张强说,后来,研也考了,可我还是换了工作。梧桐说,不懂。张强说,我考了公务员。当时倒也没抱着多大希望,没想到,居然考上了。梧桐说,厉害啊。张强说,公务员,你知道的,按部就班,做一只螺丝钉,转啊转,转一辈子。梧桐说,稳定啊。张强说,我痛恨这种稳定。梧桐说,所以呢?张强说,我辞了职,到一家国企,干宣传。梧桐说,国企?张强说,待遇不错,国企嘛。就是那几年,我买了房子,按揭。梧桐说,不错嘛。张强说,天天写材料,那一套话语体系,刚开始挺新鲜,后来,哎,没劲。梧桐说,不会吧,难道你又?张强说,最近,我忽然对艺术有了兴趣。具体一点,就是画画。张强说,你知道,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过他们的艺术社团。梧桐说,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张强笑笑,好像是原谅了她的健忘。你知道吗,画画是需要天分的。不只是画画,一切艺术,天分是最关键的。有的人就是天分好,悟性高,老天爷赏饭吃,你怎么办?没办法。梧桐说,那么,你现在是,画家?张强说,准确地说,曾经是。
惠新西街北口到了。车门打开,一批人下去,另外一批人上来。因为是换乘车站,车厢里秩序有点混乱。车厢门口有志愿者在维持秩序,耐心引导乘客,这边走,那边走。有个盲人,戴着墨镜,拄着一根拐杖,哒哒哒哒上车。志愿者小声提醒他注意脚下,想要搀扶,却被盲人客气而坚决地拒绝了。车厢里人们霎时间安静下来。有个女孩子站起来让座,那盲人却不肯,点头说谢谢。那女孩子一时间有点尴尬。又有人站起来,引导着他,在供人停靠的地方站住。那盲人立定,戴着墨镜的脸入神地对着窗外。梧桐看着他那神秘的墨镜,心想这上班高峰,乘地铁够危险的。张强忽然小声说,说不定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盲人。梧桐啊了一声。张强的声音更低了,他看得见。梧桐说,你怎么知道?张强说,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猜测,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梧桐说,可能性?张强说,比方说,你。梧桐说,我?张强说,对。你。你看起来还不错,其实——梧桐忽然紧张起来。其实什么?张强说,其实你并不是你看起来的样子,我是说,也许,你并没有你看起来那么,那么幸福。梧桐说,你什么意思?张强说,别生气啊,实话就是不中听。梧桐说,你从哪里看出我不幸福?你凭什么妄自揣测别人的生活?车厢里忽然变得特别安静,一点声响都没有。人们惊讶地朝这边看过来。张强小声说,你看你,那么大嗓门。梧桐尴尬得不行,对不起,我刚才,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两个人一时无话。
窗玻璃里映出车厢里人们的脸,重重叠叠的,显得有点怪异。有的人脸上长出了树木,有的人眼睛里忽然冒出一座高楼,有的人下巴颏儿上打上了几个大字,中国银行。车里的脸和窗外的城市交错混杂在一起,有一种魔幻般的不真实。张强松松垮垮站着,一条腿稍息,有点吊儿郎当。三十多岁的人了,身材保持得还不错。牛仔裤紧绷绷地勾勒出一双长腿来,衬衣是棉布的,圆角下摆,细细碎碎的褶皱,有一种皱巴巴的高级感。手上没有戒指。梧桐猜测着他的婚姻状态。仿佛是听到了梧桐心里的疑问,张强说,我离婚了。好几年前的事儿了。梧桐哦了一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张强说,你肯定是在想,这时候是该安慰呢,还是该祝贺呢。梧桐说,那么我是该安慰你呢还是该——祝贺你呢。窗子上映出后面谁的一副眼镜,却跟一个女人猩红的嘴巴重叠在一起,仿佛是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张强笑了一下,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都过去了。他说。看着窗外的城市不断向后退去退去退去。你认识的。就是小蔡。梧桐想起来了。小蔡是外文系的,瘦瘦高高,有点弱不禁风。有人背后说她挺厉害的,别看那么瘦。身边男孩子一直不断,还老有社会上的人过来,为了她打架滋事。张强那时候一点儿都不起眼。乡下出身,穿衣打扮也土,说话一着急就结巴。成绩嘛,倒挺优秀,出了名的学霸。可大学里,谁还光看你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姑娘们。张强说,我爱她。张强看着窗外,好像那里就站着他的小蔡。我整整追了她两年。张强摸了摸衣兜,大概是想抽烟。他把一根烟抽出来,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又放回去。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命运吧。梧桐看着他。她不知道他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命运。命运这东西,有时候我们相信它。有时候我们反抗它。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小孩子忽然哭起来,肆无忌惮的,是忽然爆发的那种。做妈妈的哄不住他,只好任他哭。张强说,做个孩子真好啊。大人太累了。想哭的时候装着笑,想笑的时候还得忍住,不能任性。梧桐心想,您还不够任性?张强忽然问,对了,你有孩子吗?抱歉,其实我应该先问,你结婚了吧?梧桐被他逗笑了。说,你猜?
过了惠新西街南口,地铁由地上转入地下。车厢里忽然暗下来。几乎是报站的同时,灯被调亮了。灯光仿佛星光,在幽暗的地下粲然绽放。车厢里亮如白昼。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黑暗。不时有巨大的广告招牌闪过,色彩明亮。化妆品,汽车,包包,高端别墅,私人订制服装,光华照人,充满了浓郁的奢华的物质的气息。列车仿佛一头巨大的野兽,在城市的腹部轰然穿过,呼啸着,挟带着凛冽的浩荡的风声。车轮碾压过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从地下传到地面,传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写字楼,商场,游乐园,各种不同档次的居民区。张强换了一种姿势,靠着车厢门口那根栏杆。栏杆上面写着一行字,危险!禁止倚靠。梧桐想提醒他,张了张口,却说,后来呢。我是说,小蔡。张强说,离了。我們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但我一点都不后悔。你信吗?梧桐不说话。张强说,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生活的本质就是,千差万错,来不及修改。梧桐说,是吗?张强说,这要是在年轻时候,我根本不服。梧桐看着他的脸,心里说,那么,现在呢?
雍和宫站到了。乘务员的播报声在车厢里回荡,好像是一块石头投进水里,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跟地铁里巨大的空洞的回声碰撞在一起,交织成一种辉煌的华丽的轰鸣。梧桐说,你去雍和宫许过愿吗,据说挺灵的。张强说,你也信这个?站台内的装修都是中国风,雕梁画栋,飞檐下挂着大红灯笼,朱红的柱子,回廊曲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靠着一根柱子打电话,忽然间,她放声大笑起来,毫无顾忌地露出一嘴粉色的牙龈。哭和笑,大约是人类最通用的语言了吧。不用解释,不用翻译,一听就懂。张强说,对了,你哪站下?梧桐说,我灯市口。你呢?张强说,我得终点站了。张强说你怎么不问问,我现在干嘛呢。梧桐说,那,你现在干嘛呢?张强就笑了。梧桐忽然发现,张强眼角的鱼尾纹挺细挺密,笑起来,好像是一把小扇子忽地打开。那些细细密密的纹路里,藏匿着什么呢。现在,我又回炉了。梧桐说,回炉?张强说,重新回到大学课堂,学管理。我准备自己创业,开公司。对面的一趟列车开过来,巨大的影子把窗玻璃整个覆盖,先是车头,然后是长长的车身,最后是车尾。当你感觉漫长的黑暗总也看不到头的时候,刷的一下,眼前一亮,列车已经错身而过了。梧桐说,你真,真行。张强说,你是想说,真能折腾吧。张强换了一条腿稍息着,一只手在窗子上漫无目的地画着。窗玻璃上是一幅北京地铁线路图,花花绿绿,弯弯曲曲,乍一看,好像是一张印象派油画。这么多年,你也变了。张强说,我记得,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姑娘。梧桐说,你就是说我直肠子呗。张强说,没什么不好。直来直去。老同学还藏着掖着,忒累。梧桐说,没错,我是觉得,你挺能折腾。张强的手指沿着图上的地铁线路缓慢地经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好像是在辨识,又好像是在确认。有个女人打电话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敢不敢再说一遍?梧桐说,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真心话。那个打电话的女人忽然哭起来,这么多年,我坚持了这么多年——哽哽咽咽的,泣不成声。张强叹口气,笑笑。车窗上,映出那个打电话的人的背影,是个短发女人,穿着剪裁得体的裙装,两只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好像胸膛里埋藏着一个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梧桐说,小蔡,她后来怎么样了?——我是不是挺八卦的?张强说,有点儿。你怎么不问问大勋。梧桐不说话。窗外,大团大团的黑暗往后方退去,退去,叫人感到没来由地一阵阵窒息,好像是,那黑暗是有重量的,隔着窗子,都能对人造成强大的压迫。半晌,梧桐才说,都过去了,不是吗。梧桐说,好像是一场梦,你在梦里哭啊笑啊,跟真的一样,醒来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张强说,幸亏还有梦。人这一辈子,要是连个梦都没有,也挺没意思的。那打电话的短发女人还在哭泣,好像是已经挂了电话,不知道是对方挂了,还是她挂了。一侧的直直的短发垂下来,齐刷刷遮住她的半张脸。耳环一闪一闪,随着抽泣的节奏和列车节奏激烈晃动着,仿佛是另外一种诉说。张强说,有人通知你了吗,咱们班拉了个群,毕业十周年,说要搞一次聚会。梧桐说,回学校聚?张强说,还没定。梧桐说,很多人都没联系了。张强说,武建伟,你还记得吧。梧桐说,又高又壮,我们背后都叫他武二郎。张强的声音忽然低下来,他走了。梧桐说,走了?张强说,听说是车祸,好几年前的事了。车窗外,又一辆列车从对面呼啸而来,先是车头,然后是长长的长长的车身。好像是庞大的笨重的野兽,拖着巨大的影子,在地下横冲直撞。车厢里陷入长时间的黑暗,叫人难以忍受。梧桐想起来,她们宿舍那些女生,对高大的武二郎是有些暗暗的喜欢的。私下里,她们喊他二郎。二郎这个,二郎那个。二郎是篮球场上的明星人物,矫健的身影,敏捷的奔跑,凌厉的动作,汗水飞溅,热血奔腾,淡淡的荷尔蒙的气味,草地上露珠滚动被女生们的尖叫声震碎了。梧桐忽然觉得胸口发紧。张强说,我也是刚知道的。这不是要聚了吗,大家才开始联系。张强说,有的人死活联系不上,你说怪不怪?大约是发觉自己这话说得不好,又找补说,我是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世界就这么大。梧桐说,世界太辽阔。张强说,看怎么说。这不,坐个地铁都能偶遇。梧桐说,也是。张强说,李静一,小个子,洋娃娃似的,你还记得吗。梧桐说,她好像是南方人。张强说,她出国了。梧桐说哦。张强说,还有欧阳老师,升官了,刚提了副校长。梧桐说,上学那会儿倒没看出来,一身书生意气。张强说,学术带头人,也是领域内大牛了。梧桐说,确实挺有才的,你记不记得他有个口头禅?张强说,开什么玩笑!两个人一齐笑起来。
这一站是张自忠路。上车的人很多,下车的人也很多。站台里,人群潮水一般,汹涌着朝着四面八方流去。新的人群又汹涌而至。早高峰时段,地铁好像是庞大的钢铁的怪兽,吞吐着呼啸着奔跑着,把人群送往他们各自的目的地。张强说,我是不是有点话痨?梧桐笑起来。我记得你以前话很少。张强说,一着急还有点结巴。梧桐说,现在都好了?张强说,诡异吧?我也觉得纳闷儿。说实话,我跟生人话也不多。我嘴笨。窗外,大幅广告牌一闪而过,跟大片的黑暗不断交替着。窗玻璃上,很多人的脸重叠在一起,消失,出现,消失,出现。梧桐说,我离了,刚又结了,就这个五一。张强说,是吗,其实,也正常。梧桐笑起来。张强说,你灯市口,是吧?梧桐说,还有两站,下站东四。张强说,还挺快。东四站到了。窗玻璃上出现了站台,柱子,人群,扶梯,乘务员穿着制服,笔直站立着。张强说,其实,我还在咱学校,搞行政。梧桐说,哦?张强说,我跟小蔡——我们也没有离婚。她的公司做得不错。我们,怎么说,我们刚换了大房子。张强停顿了一下,说,有空来玩吧。
灯市口马上就到了。乘务员的播报声响起来,是催促,也是提醒。车厢里又是一阵骚动。梧桐说,我下车了,祝你——一切都好。张强说,新婚快乐。
六月的北京城,阳光明亮。行道树巨大的树冠支撑起大片的绿荫,叫人觉出夏日的清新可爱。梧桐这才发现,早餐一直还在手里提着,塑料袋子内壁被水蒸气弄得湿漉漉的。她拿出油条豆浆,边走边吃。油条已经有点皮了,豆浆却不凉不热正好。一个学生从背后叫她,老师好!清脆稚嫩的声音,毛茸茸的,叫人心里痒酥酥地舒服。
她拿出手机看时间,忽然想起来,她跟张强还没有加微信。电话也没有。她喝着豆浆,看着阳光下的背着书包上学的学生们,叽叽喳喳,仰着新鲜的明亮的脸。灯市口这一带,种了很多槐树。蝉在树上热烈鸣叫着。梧桐第一次发现,蝉鸣声中有一种金属的质感,清脆亮烈。有槐花簌簌落下来,落在马路牙子上,落在行人的头上肩上。
上课预备铃响了。梧桐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