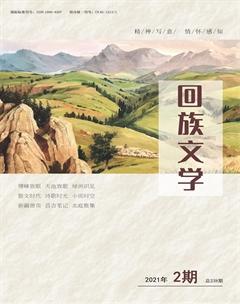纸短情长
孔立文
一
唐素英发誓这辈子就跟定武靖轩了是在那个中午。
那个中午天刚刚下过一场暴雨,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淡淡的苇香味。被淋得像从苇湖里捞出来的唐素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烦躁。她摘下军帽,解开辫子,甩着潮湿的头发,像是要把烦躁也一并甩掉似的。
一阵轻风拂过,芦苇荡轻轻晃动,这使她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随风飘舞,荡漾起恐怖的涟漪。
果然,那只狼不声不响地出现在离她六七十米的地方。那只精瘦的狼轻仰着头,漠然地注视着她。那样子根本没把她这个黄毛丫头放在眼里。
路两旁苇丛里,蛙声响成一片。
这是唐素英头一次单独遇到狼。以往的几次看到的都是奔突的狼,只要有人一吼,狼逃跑的速度极快,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独自面对这只狼,唐素英心头掠过一丝恐慌,脸上的汗滴如串珠般滚落下来。
她深吸一口气,让自己趋于平静。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女兵,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沉稳。她把长发盘了个结,戴好军帽,然后用一种近乎相同的目光蔑视着那狼。
狼可能被她的从容给镇住了,只冲她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和她无声地对峙。
“滚!”唐素英突然声嘶力竭一声吼,那吼声仿佛在空中劈开一道口子。狼惊得抖了一下身子。第二声吼比第一声更响亮,但狼的身子没动。第三声吼过之后,狼竟大摇大摆向她逼过来。它已经感受到她的恐惧。
这里距连队还有两三公里,看来只有赤手空拳来一场肉搏战了。唐素英从军衣口袋抽出那支唯一可以利用的钢笔,那是武靖轩出院的时候送给她的。
她快速拔掉笔帽,右手举起那支笔。她紧紧地握着,就像握着一把匕首,更像刚学护士时握的那个注射器。
可能是钢笔尖炫目的烁光让狼止住了脚步。
有了笔就如同有了枪,唐素英的镇定自若再一次压住了狼的杀气。
那狼眼神里出现一丝迷茫。它发狠地冲她嗥叫了两声,慢悠悠地钻进芦苇荡去了。
这反倒让唐素英不知所措。狼通人性,那只狡猾的狼,保不准跑到身后等着她呢。
她不能往回返。这条连接三连跟营部的路,是官兵们专门割了苇子踩出来的。本来离开营部时教导员让文书送她,可她坚决推辞了。她说:“教导员,你不是常说战场上和劳动场上不分男兵女兵吗,你要是让人送就是小瞧人。”唐素英可是个从来不服输的人。
一阵轻风拂过,芦苇荡又晃动起来。路两边仿佛到处晃荡着狼的影子。
唐素英明白,狼恃强凌弱,人和狼斗,既要斗智,也要斗勇。横竖是一搏,定下继续向前走的决心,唐素英并未感到特别紧张。
不出所料,那只银灰色的狼果真绕到了唐素英的身后。她走,它就走。她停,它也停。距离一直保持五六十米的样子。唐素英的衣服已经湿透,可是她的步伐坚定有力,不时还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当连队大片的苇棚子终于出现的时候,唐素英再回头,哪里还有狼的踪影。
她就是握着那支钢笔,无比勇敢地走回连队的。那支笔给了她信心和勇气。唐素英知道,给她信心和勇气的,除了那支笔,当然更是武靖轩这个人。
二
第一次见到武靖轩是在师医院。
师医院是个四合院,清一色的土坯房。那一次医院交班,老院长非常郑重地说:“这个病号可是个大英雄,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和平津战役,军龄长,党龄也不短,也算得上是老革命了,你们可要给我照顾好,不能出半点差错。”
院长的话给了刚从卫生训练队毕业才一个星期的唐素英不小的压力。
端着注射器械走进武靖轩住的特护病房,病房里显得有些冷清,只有一个左肩缠着绷带半裸上身的小伙子,斜靠在病房正中间那个单人土炕上。小伙子面色红润,眉宇间英气逼人,尤其他那嘴唇红得像涂了唇膏,这让唐素英一下子就联想到姐姐,姐姐出嫁那天的唇就特别红,可那是涂了进口的意大利口红,而这个小伙子的唇,竟也红成这样。凭经验,唐素英知道,那是发高烧才有的症状。
小伙子见到唐素英,一双眼睛犹如打火石被猛地划燃了,一下子就亮起来,炯炯有神的目光在唐素英的脸上停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要遮上身,可能由于掖被角用力过猛,右手打到了左肩的伤口上,他疼得龇牙咧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疼痛,他竟然向唐素英挤了一下眼睛。
唐素英的心猛地颤了一下。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后来她曾无数次地回想这种感觉,那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她喜欢那眼睛里放射出来的醉人的光。
那一丝慌乱也就是极短的一瞬,唐素英不可能让面前的这个人察觉。她摆出一副护士特有的表情问:“武靖轩同志不在吗?”
“在!”小伙子回答得干脆利落。
“出去了吗?”唐素英面露疑惑。房间的五张单人土炕床位,其中的四床被子可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小伙子羞赧地笑了,他笑的时候牙齿雪白,一脸孩子般的灿烂。
“这个老革命怎么这样,有伤还乱跑。”
小伙子忽然咳了起来,并且咳得很厉害,厉害得让唐素英觉得该给他一点安慰,当然这也是护士的责任。
唐素英一边轻轻拍他的背,一边问:“同志,你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我们院长交班的时候不是说特护病房就武靖轩同志一个人吗?”
“护士同志,我就是武靖軒。”小伙子一本正经地回答。
她扑哧一声笑了,特意摸了下那小子的额头,用调侃的语气说:“你烧糊涂了吧,人家武靖轩同志可是老革命、大英雄,开什么玩笑。”
“那你就叫我老革命得了。”他诡秘地笑起来。
从那时起,她就经常开玩笑叫他“老革命”。唐素英当时确实没把这个毛头小子和“老革命”联系到一起。后来她才知道,武靖轩当兵早,年龄不大,参加的战斗却不少,小小年纪时已经是副营长了。
唐素英对武靖轩表现出的乐观态度很是钦敬。据院长讲,在指挥博尔塔拉剿匪战斗中,武靖轩被匪徒打伤,子弹从其左肩胛穿过,肩胛骨被打穿,伤情很严重。入院前武靖轩的伤口已严重感染,高烧不退,曾多次陷入昏迷。经过一晚上的保守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高烧一直未退,如果伤口继续恶化,他随时都会有失去左臂的危险。只是,武靖轩好像对自己的伤情不是很在乎,只要醒来,只要身旁有人,他始终表现得很淡然,脸上总挂着那特有的灿烂微笑。
让唐素英钦敬的还有他惊人的毅力。她觉得武靖轩对疼痛的承受力让人难以置信,过去她只听过关公刮骨疗伤的典故,但在武靖轩身上,她见识了一回真正的刮骨疗伤。由于武靖轩对麻醉药有過敏反应,而当时师医院医疗条件有限,后送迪化(今乌鲁木齐)军区医院,汽车最少要走上七八天,针对其伤口感染已相当严重的情况,最后院里决定,在不施行麻醉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去腐接骨手术。
手术是在下午进行的。
武靖轩赤裸着上身,坐在一个极其普通的木椅子上,面对身边一脸肃然的医生护士,他显得十分平静。手术开始,他微闭双眼,嘴角挂着笑,没过多久,汗就冒了出来,汗水一道又一道地从那张年轻的脸庞滑过。后来,一滴接一滴的汗珠儿开始从他前额的头发尖上滴下来。
空气好像凝固了。手术室里静得只有手术刀“咔嚓咔嚓”的声音。唐素英一直屏住呼吸,她只向伤口处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因为她看到一片血肉模糊的鲜红。
如果不是发现武靖轩紧握的右手无意识地剧烈抖动,她可能不会这么做。也许是在不经意间,她发现他右手的抖动,她知道那是因为疼痛。不知是为什么,她忽然就感觉自己的心尖也跟着一起抖动起来,于是,她伸出了她的右手。
触到她的手,他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就一直被他潮湿的大手握着,紧紧地握着。他默默地凝视着她,那种掺杂着诸多复杂情感的凝视,她一辈子都不会忘。他的眼神传递着一种无声的语言,那是一种复杂的语言,这让她感到害羞。
汗珠从武靖轩的睫毛上滴落下来,他紧闭一下眼睛,然后便马上睁开,依然是一动不动凝视着她。
手术很成功。
整个手术,武靖轩未发出一声呻吟,院长说这简直就是奇迹。
为了尽快治好武靖轩的伤,医院让唐素英做他的专职特护。她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清洗伤口,换药,静脉注射也格外用心。为了减轻他的病痛,他高烧未退时她还用热毛巾或酒精棉给他擦脸擦脚。
短短几天时间,他和她之间就有了某种默契。高烧减弱时,他和她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互相讲当兵的历史,讲入疆以来的感受,讲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武靖轩还专门给她看了他的特等功勋章。几天下来,唐素英感到她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依恋。她喜欢听他讲话,她觉得他的声音充满磁性,那么好听。她也喜欢他讲话时一本正经的样子。有时,她跟他开玩笑,他也是一本正经地微笑,这让她觉得武靖轩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武靖轩就要出院了。一想到他要离开,唐素英内心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他临出院前那个早晨的一句话,才让她的失落感有了些许减少。
那个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的清晨,她进病房送药,他一直躲闪她的目光。她刚要离开,他却像鼓足很大勇气似的冒了一句:“我只比你大五岁。”这句普普通通的话本来没有什么,但他紧张慌乱的样子却让唐素英涨红了脸。他接着说,虽然声音很小,但她还是听得真真切切:“昨晚我一直没睡好,我一直在想,我只比你大五岁。”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有一丝甜蜜的念头动了一下,她好像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那一年,他二十二,她十七。
出院那天,在病房门口,她帮他打点行装。她想听他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她一个红皮子笔记本和一支金星牌钢笔。直到所有送行的人离开,那辆笨重的苏联吉普和飞扬的灰尘一起消失,她才跑回宿舍倒在床上痛哭起来。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仅仅是普通战友间的离别,她不会哭得那么伤心。哭完了,她打开笔记本,发现里面夹了一张信纸,纸上只写了三个字:等着我。
三
唐素英回到连里正赶上连队出工,她跑到自己的苇棚子取了镰刀就直接进了队列,指导员悄悄把她叫到一边问:“教导员找你没大问题吧?”
“没事,教导员让我别有什么想法。”
“那就好。”
可能是新下过雨的缘故,下午割苇子时蚊子就越发猖獗。蚊群的嗡嗡声比群狼的嚎叫声还让人恐惧。唐素英忘了带头围,只一会儿工夫,她的脸就出现了几个大疙瘩,连左眼皮也肿了起来。照这样下去,等不到晚上收工,她的脸差不多也就成马蜂窝了。为了屯垦拓荒,师里每个月只发三分之一的津贴,服装也是冬夏各发一套,节省下来的钱说是为了修水渠建工厂,她现在只有一件贴身军衣。
当她又一次狠劲拍打脸上的蚊子,副连长张俊虎递过来他的头围,“你用吧。”
“那你呢?”
张俊虎也不答,径直走向一个小的沼泽边,俯身抓起一把淤泥往脸上脖子上猛抹,连眉毛眼角也不放过。如果不是那雪白闪着光泽的牙齿,他的脸简直就是一尊泥塑的雕像。张俊虎冲她做了个鬼脸,“我们男人,好办。”
蒙上头围的唐素英顿时来了精神,一株株两三米高的苇子顷刻间倒在镰下。这个头围是统一用旧军衣改制的,围在头上,只露两只眼睛,防蚊子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太热,割了没多久,唐素英的汗水就淌开了。
9月初的苇湖子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蒸笼,空气要是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官兵们身上的衣服早就被汗液浸得能拧出水来了。
割苇子的活连队干了才不到一个星期。前段时间连队一直在支援机炮营修公路,眼见着自己开荒第一犁种下的上千亩玉米就要熟了,大批人马才返回营地,除了几个专门负责编背筐的男同志,全连的官兵都投入了割苇子大战。
休息的哨音终于响了,事先准备的几大桶凉开水一会儿工夫就见了底。女兵优先,唐素英她们四个女兵不愁喝不上水。
刚喝了水,连长就把女兵们叫到一边,说:“你们四个女兵回连里编筐子吧,现在就走,不会编的话给他们会编的当个下手,玉米也快收了,再说这里实在是太闷热,不是女同志干的活。”
“连长,热都是一样的热,我们不怕。”
“我们割得不比你们男同志少。”
徐秀琴和桑丽丽表示不满,唐素英和张亚楠也很不服气。
“就这么定了,回吧。”连长的脸黑红黑红的,满是汗水滑过的痕迹。
回连里的路上四个女兵都觉得气恼。
“这明摆着就是看不起我们女兵。”桑丽丽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不行,我们得找连长论论理,编筐子咱们都是外行,如果再不让干同样的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评上先进。”徐秀琴割苇子的热情一点未减。
当四个女兵返回芦苇荡时,她们却看到惊人的一幕。
炎炎烈日下,一群只穿了短裤赤身裸体的男人,正在奋力挥舞着镰刀。他们说说笑笑,干劲十足,成片成片的苇子在他们的面前倒地。
这些人遍身涂满了泥巴。
这些与大自然作抗争的人。
唐素英仿佛看见这一大片的芦苇荡已然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黑土地又变成了一望无边的稻田。
四
唐素英睡不着。这个“人”字形苇棚子简直成了蚊子的栖息地。蚊子的叫声几乎要吞噬了她。
而周围却是此起彼伏畅快的鼾声。那是男兵的鼾声,四个女兵住的苇棚子就在男兵旁边。
唐素英睡不着还有一个更深的来由,那就是教导员半晌午时问她的那些话。上午她正在热火朝天割苇子,营部文书专门过来说让她到营里接受政审。
从当兵那天起,她接受了多少次政审已经记不清了。
教导员非常严肃地问她那些不知有多少人问过多少次的问题——家庭出身,入伍动机,社会关系……
每一次她都认认真真地回答,这一次也是一样。但这次她却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这可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单独接受政审,而且是越级政审。
家庭出身是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的。
她痛苦地蒙上被子,闷热和黑暗笼罩了她。半梦半醒中,报名参军的唐素英,千里入疆的唐素英,抢救伤员的唐素英,开荒劳动的唐素英,一个一个向她拥过来,争先恐后地与她对话,向她倾诉心声。
1951年3月,正在长沙女中读高二的唐素英,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她把这个消息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其中“不论家庭出身,一律欢迎”这个条件,让她兴奋得感到心都要蹦出来了。
当她把要到新疆当兵的想法告诉父亲,本以为父亲会支持,没想到一向慈爱的父亲却是坚决反对。相反,倒是向来严厉的母亲圆了她的军人梦。
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级将领,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因为反对民族内耗,最后解甲归田。后来,政治斗争复杂,一向豁然大度的父亲忽然间变得谨言慎行。而母亲则看得长远,女儿当了解放军,他们家就是革命军属,她不希望这个家一直生活在无形的阴影里。
唐素英从小就崇拜湖南的左宗棠,也知道左公抬棺西征的故事。卫国戍边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呀。她在填写入伍动机时写道:我向往大漠落日的壮观,向往天山草原的神奇,我志愿参军到新疆。
就是这些纯洁的文字,后来却被无数次地说成是入伍动机不纯,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的小资情调。
天啊,这又是什么样的小资情调。
进疆路一走就是两个月,一路颠簸,颠翻了五脏六腑。没有家乡的大米饭,吃的是又黑又硬的干馒头。宿营无定所,住牲口圈,睡戈壁滩。尘土塞满了耳朵鼻孔,浑身结满了泥垢。没有洗澡的地方,甚至几天洗不上一次脸。入疆后,她学了三个月的护士,又干了七个多月后,就被分到了苇湖子生产一线。即使这样,也从没熄灭唐素英心中的革命热情。
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些呢?
夜色,是那么宁静。
五
教导员的出现,总让唐素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
早晨连队正要出工,指导员把唐素英叫到了他的苇棚子办公室。教导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外面,旁边还立了一位陌生的军人。那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好像很不自然,低着头如一穗垂首的谷子。
“小唐同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团里的军需股长张满君同志。”教导员格外亲切。
唐素英给两人敬了个军礼。
“小唐同志出身不好,但是听你们连长指导员讲,你的工作表现还是蛮不错的嘛,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资产阶级大小姐的作风,难得呀,难得。”
唐素英不知教导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小唐同志,组织上对你们这些女兵还是很关心的,你今年十八了,对吧。”
唐素英点了点头。
听到这儿,那个军需股长悄悄地离开了苇棚子。
“怎么样?”教导员问。
“什么怎么样?”唐素英答。
“刚才那个张股长。”
唐素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个预感让她的脸色唰一下就白了。她刚一入疆就听说了“拉郎配”这种包办婚姻的事。
教导员继续说:“张满君同志家庭出身是贫农,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立了不少战功。组织上决定,你和他接触接触,国庆节的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解决了。”
唐素英的头嗡一下,险些站立不住。
教导员那张嘴还在不停地说着,表情很是丰富。唐素英恍然看到教导员那张脸由一张变成两张,由两张变成三张,更有无数张嘴巴在那几张脸上叠画般翕动着。
“教导员同志,这太荒唐了,我不会答应的,你们就死了这个心吧。”唐素英感觉受到莫大侮辱,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出来的。
到了自己的苇棚子,她取了镰刀就向芦苇荡跑。
她又忘记了带头围,但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她一边割苇一边流泪,任凭蚊群的围攻。
“给你这个。”副连长张俊虎又一次递过来自己的头围。
见到张俊虎,她一下子扔了镰刀,一屁股坐在苇滩子上,埋着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副……连长,你说,教导员……他……他怎么能这样呢?”
张俊虎一直沉默。这个也才只有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内心里一直暗恋着唐素英。
“副连长,我可不想这么早结婚,你帮帮我行吗?”
“快起来吧,我去跟教导员讲,你不同意就行了嘛,他也没命令你,何况这种事也不存在谁命令谁的问题。”
休息的时候,在芦苇荡中间那个波光潋滟的苇湖边,唐素英无意间听到了张俊虎和指导员的对话。
“你不想让教导员管这事,除非你和她好,就说你和她早就有了婚约。”这是指导员的声音。
“那不好吧,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那你看着办吧。到时候上面报告一批,什么可都来不及了。”
苇湖无声。
唐素英欲哭无泪。她知道,其实她心里面装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武靖轩。
六
让唐素英诚惶诚恐的国庆节终于到了。
这一天收工比平时早,太阳还没落山。太阳悬浮在草原上,如同一个被左右挤压不规则跃动着的鸡蛋黄。
一回到营房,唐素英就注意到最东边的两间苇棚子有些特别,这两个棚子比其他的都多了一个漂漂亮亮的门。门是用一束束金黄的芦苇编成的,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烁着刺目的眩光。
一下午没参加劳动的张亚楠和徐秀琴,站在她们四个女兵住的苇棚子前面,脸上都溢满了笑,老远就冲着唐素英和桑丽丽招手。桑丽丽笑嘻嘻地跑过去,唐素英则面无表情,内心充满疑惑。
这二十几天唐素英是在沉默中度过的,除了拼命干活,她不跟任何人讲话,包括张亚楠她们三个姐妹。
“谁结婚?”桑丽丽在苇棚里传出一声惊叫。
唐素英早觉出不对劲,但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苇棚子的地铺上,几张大红的“囍”字剪纸分外扎眼。
唐素英的眼泪无声地滑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她可是做好了保卫尊严的准备。
张亚楠和徐秀琴都是一副害羞的模样。
“素英、丽丽,你们快帮我们把‘囍字贴到最东边那两间苇棚子的门上去。”副班长张亚楠的声音总是大姐般温柔。
连长和张亚楠,副指导员和徐秀琴的婚礼让整个连队都充满了喜庆洋洋的气氛。
营长和教导员都满脸绽笑,皱纹舒展,那种感觉就像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农民,终于给自己家的儿子娶上了媳妇。
婚礼很简单,但嘻嘻哈哈的笑声从未间断。
唐素英也很为两对新人高兴。
四个女兵住的苇棚子,现在只有她和桑丽丽两个人了。桑丽丽紧挨着她,平时爱说爱笑的桑丽丽不知那晚为什么心事重重,一句话也不多说。
“你之前也不知道她们结婚的事?”唐素英轻轻地问。
“不知道。不过,教导员带那个军需股长来给你说媒那天晚上,指导员把我们都叫了去,张亚楠和徐秀琴可能就签了字。听说只要在申请结婚报告上签了字,团里一批就行了。”
“那你呢?”唐素英问。
“素英,说心里话,我只对咱们副连长有感觉,要是他,我绝对也签了,但指导员说的不是他。别的人,我谁都不会同意。”
原来是这样。唐素英忽然感到有些累。
唐素英后来才知道,副连长张俊虎为了帮她,真的按照指导员的意思,找教导员讲了。教导员让他打结婚报告,趁国庆节一块把婚结了。张俊虎说:“唐素英同志还小,我们俩再等等。”
这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在国庆节后不久也就不再是秘密了。
反应最强烈的是桑丽丽,她痛恨的表情让唐素英感到自己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唐素英再遇到张俊虎就显得很尴尬,张俊虎也是一脸羞红。
唐素英对武靖轩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减少。在她的潜意识里,他就是自己全部的精神寄托。
这个武靖轩,怎么连封信也没有呢。
张亚楠和徐秀琴倒是对她和张俊虎的事很上心。
婚后的张亚楠更平添了几分大姐的爽直,“素英,我们四个女兵家庭出身都不好,不然也不会到这基层连队,找个出身好的,不会错。你不是说崇拜左宗棠吗,左宗棠比不过我们,我们可是要在新疆扎根,根是什么,不结婚哪来的根。”
徐秀琴更是现身说法:“素英,我也只不过比你大三个月。张副连长哪一点配不上你,人家年轻,长得也没得说,你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桑丽丽喜欢副连长,我看他们两个挺合适。”一直未说话的唐素英平淡地回答。
“可人家张副连长喜欢的人是你。”张亚楠和徐秀琴异口同声。
“你们不要乱点鸳鸯谱。”
“张副连长喜欢你,全连哪个不知道。这回张副连长替你挡下那个军需股长,连里的兵都认可了你和她的事。”张亚楠认真地说。
“我不考虑婚姻的事,谁都不行!”唐素英斩钉截铁。
七
让唐素英没有想到的是,连长竟也加入了劝婚者的行列。
为了准备过冬,连队开始挖一眼一眼的地窝子。那个下午唐素英正在给一个地窝子修床台子,连长来到了她跟前,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说:“素英同志,我看入冬前你和桑丽丽同志都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这样连队也好安排住处。”
唐素英气得说不出话,她怒气冲冲地盯着连长,嘴巴一直张着,好像忘了合上似的,老半天才吐出两个字:“不……行。”
其实,唐素英也觉着挺对不住张俊虎的,毕竟他對她的心事一无所知。
当然,不知道她心事的远不止一个张俊虎,而是整个连队的官兵。她痛苦地发现,连里的男兵们渐渐对她疏远,他们觉得她清高孤傲。
每个周日晚上的班务会,更是让唐素英如坐针毡。班长讲评本班问题时,几乎每次都要讲个别同志还存在资产阶级思想问题。虽然从不直接点她的名,但那直视来的目光比点名还让她难受。
她见到张俊虎时却没有一丝怨恨。
光明磊落的张俊虎总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每次见她还是一脸羞红。
整整一个秋天,割苇子,收玉米,修公路,官兵们起早贪黑没有一点空闲。感情的事对处于高强度劳动的人来说多少有点奢侈。而张俊虎对唐素英的关心,却有点像雨中伞雪中炭,让人拒绝不得。
唐素英割苇子割出一条大花蛇,最先跑过来打蛇的,是张俊虎。
唐素英掰玉米掉了队,早有人在垄前头掰好了迎着她,那个人是张俊虎。
唐素英被玉米茬子扎烂了脚,有人扯了自己的背心给她包扎,然后还硬要背着她回连队,那个人当然还是张俊虎。
秋去冬来。一纸命令,指导员上调团机关,副连长张俊虎升任指导员。
张俊虎终于在宣布命令的那个傍晚,在漫天飘雪的地窝子外面,向唐素英表达了爱意。
“唐素英同志,我……我喜欢你,你现在可以出嫁了吧?”
唐素英没想到张俊虎会如此直接,直接得几乎让人无法拒绝。她想,可能这么多天来,在他的心中,早已把她当成新娘子了吧。唐素英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但她拒绝得却同样直接,“指导员,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请你原谅,我对你没那种感觉,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次求爱的结果,对张俊虎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多少年后他对唐素英说:“当时我怦怦跳着的心就像被直直地捅了一把刀子,那是一把伤人心的刀子,我当时怎么拔都拔不掉。”张俊虎望着唐素英,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那是一种僵硬的表情,是一个心灵受了伤的男人才有的表情。
唐素英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跑开了。只有飞扬的雪儿,知道她的内心。
唐素英和桑丽丽的关系随着唐素英对张俊虎的拒绝得到彻底恢复。两个人的话题再也不避讳谈张俊虎,桑丽丽总是把“指导员”三个字挂在嘴边,每次谈到这三个字,桑丽丽总显得特别虔诚,好像不这样,那三个字就会被唐素英抢走似的。桑丽丽开始频繁地找张俊虎汇报工作,请教问题,周末更是抢着要给张俊虎洗衣服。张俊虎不拿眼看她,话也是冷冰冰的,“桑丽丽同志,洗衣服的事你甭管,我自己能干。”
桑丽丽红着脸,“指导员,人家愿意帮你洗嘛。”
张俊虎一脸严肃,“你愿意,我不愿意!”
为了桑丽丽,唐素英搬来张亚楠和徐秀琴,当这两个女人一起以红娘的身份找到张俊虎时,张俊虎一听到桑丽丽的名字,马上回应:“以后别跟我提这事。”
对于桑丽丽的心事,张俊虎早就知道,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唐素英的心事。他不明白这个唐素英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一点感觉,自己在她心中,难道就没有一点余地。他对唐素英的关心有增无减,然而换来的,却是唐素英越来越深的冷漠。是那次水渠落水事件,解开了张俊虎心中的谜团。
八
那次水渠落水事件,可以说是张俊虎救了唐素英的一条命。
1953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机炮营修了一年多的水渠终于要开闸放水。作为加强支援最多的连队,唐素英所在连参加了隆重的开闸放水仪式。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也可能是那天出席仪式的领导讲话时间过长,唐素英觉得头重脚轻不舒服。
当铺天盖地的水像狂风中的绸缎摇晃过来的时候,唐素英有一种被压迫被淹灭的感觉。晕水的她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然后柔弱的她便随着渠边松软的黄土掉进了滚滚的渠水中。而此时,官兵们还全都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
张俊虎第一个发现状况,他边喊救人边向下游狂奔。他是迎着渠头跳下去的,被又急又猛的渠头旋了几个来回之后,硬是站在没腰深的渠水中,拦下已经失去知觉的唐素英。在众人的急救下,唐素英终于有了呼吸,但随即便陷入昏迷。
在师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昏迷七天的唐素英,忽然开始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她的呼唤时断时续,每一次呼唤前都仿佛受了惊吓一般。她的声音沙哑,语速很快,呼唤几声之后,随即便陷入深深的昏迷。
她呼唤的名字是武靖轩。
这让一直陪护在身边的桑丽丽感到莫名其妙,更让专程赶来探望的张俊虎摸不着头脑。
医院的老院長知道这个名字,她知道唐素英呼唤的应该就是两年前在这里住过院的武靖轩。
在唐素英处在昏迷状态的第八天,武靖轩竟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身戎装的武靖轩显得更加英武,他刚从北京回来,是专程来找唐素英的。
当从老院长那里听到唐素英的情况,武靖轩火速赶到病床前,大声地呼喊:“素英,素英,我是靖轩,我回来了。”
武靖轩半蹲在病床边,他全身抖动,抖动着一个男人的悲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两年不见,他日思夜想的心上人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有着红苹果一样脸蛋的唐素英不见了,那个笑起来让人着迷的唐素英不见了,那个眼睛会说话的唐素英不见了。病床上的唐素英脸色紫黑,安详得像一个熟睡的婴儿。
他一直握着唐素英粗糙的手,紧紧地握着。他流着泪向唐素英诉说他的思念和爱恋。他不断地说:“我知道你会等着我的,我知道你会等着我的……”
武靖轩从师医院出院后不久,又指挥了一次山地剿匪行动,然后突然接到命令被派往沈阳指挥学院学习。入校不到十天,他便申请入朝参战,直到战争结束。作为抗美援朝的功臣,他放弃了随参战部队留在北京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到新疆。他人未回疆,已经被任命为新疆军区某师副参谋长。这期间他从未给她写过一封信,但那份爱却一直藏在心底。
而此时,唐素英正在做着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梦很长,也很恐怖。他看见一个肩部流着血的男人在前面走着。那个人走过一条河,她就追过一条河。那个男人爬过一座山,她就追过一座山。她跟在那个男人后面不知过了多少条河,爬了多少座山。走累了,她就一直在后面喊,喊得嗓子都哑了,却喊不出来一点声音。后来,她实在是太累了,就身子软软地倒在了草地上。在迷迷糊糊中她几乎就要睡过去了,但冥冥之中她忽然感觉有人抓住了她的手,那只潮湿的大手紧紧地拉着她,剧烈地抖动着。
这只大手的抖动让唐素英如此熟悉,这么剧烈地抖动,那是因为疼痛。她感受到他的疼痛,这让她感觉自己的心尖也跟着一起抖动起来。
她终于苏醒过来。是的,她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一串泪珠儿从眼角边滑落。
“靖轩,是你吗,你怎么哭了?”她轻轻地说。
“我知道你会等着我的,我知道你会等着我的……”武靖轩语无伦次,像孩子一样灿烂地对着她笑。
“是的,其实我也从来没承诺给他什么,只是为了那三个字,为了他走之前夹在笔记本里的那三个字,我宁愿等他一辈子。”
这句话是1953年夏天说的。
今天,我的岳母唐素英,也是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这个浪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