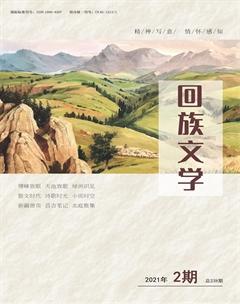我的三位老师
王凌云
钱老师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过粮食关,大家都挨饿,而教师首当其冲。其他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腾挪变通一下,而教师整天在学校里教课,哪儿也去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干挨饿。
那时,我的班主任姓钱,是从南方调来的。他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南方音很重,大家都叫他“蛮老师”。不过,他心地善良,脾气很好。他全家都在江南,只有他一个人来到北方任教,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支教。他住在学校里,自己做饭吃。粮食标准低,一天三顿稀饭,不到月底,粮食就没有了。他饿得受不了,就在麦收的时候,到收割过的麦地里拾些遗落的麦穗,作为口粮的补充。但那时候是人民公社制,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生产队对大大小小的事都管,而且管得有些不近人情。比如遗落在地里的麦子,宁愿烂掉,也不让私人去拾。钱老师不知道这个情况(也可能知道,因饥饿难耐,他顾不了那么多),放学后,他到村子南边的麦田里,拾了一些散落麦子,夹在腋下,高高兴兴、唱唱念念地往学校走去。正巧,迎面碰上蛮横暴烈的生产队长王大头。王大头一把夺去了钱老师的麦子,还声色俱厉地教训钱老师:自私自利,不顾大局,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这样怎能教好学生,不如趁早滚蛋。钱老师气得翻白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跟钱老师说:“老师,明天我领您去拾麦子,保险不让王大头把麦子夺走。”
“你……”钱老师半信半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我找了两只大篮子、两把镰刀,来到学校,给钱老师一只篮子一把镰刀,然后把他领到村外小河边的麦地里,每个人拾了满满一篮子麦穗头,然后割了一些青草盖在麦子上面。我们俩挎着篮子,不慌不忙地往回走。在村边,又碰见在那里转悠的队长王大头。我紧走几步,到他跟前朗声说:“队长,你看,钱老师也来帮我们生产队割草了。”王大头见钱老师挎着一大篮子青草,吃力地跟在我的身后,竟伸出大拇指,夸奖了钱老师几句,说这才像一个老师的样子,我暗暗好笑。
回到学校,我把青草下面的麦子拿出来都给了钱老师,再把青草送到生产队的牛棚。
钱老师找来一根棍子,把麦穗儿放在学校的院子里摊开,晒干,用棍子敲打。然后,他又把敲打下来的麦粒儿簸干净,装进口袋,背到我家的磨盘上开始磨面糊,烙煎饼。那时既无畜力也无电力,都是用人力来推动那沉重的石磨盘。我要求帮他推,他说不用,我还小,累着了就长不高了。于是,他一个人抱着粗壮的推磨棍,像老牛一样喘息着,在磨道上慢慢地走了起来。
面糊糊磨好了,他请我的三婶子帮他烙煎饼。第一张煎饼他没有吃,而是卷得整整齐齐的塞在三婶子的小儿子手里;第二张他还是没有吃,又卷得整整齐齐的塞在我的手里。第三张煎饼卷好了,他才迫不及待地送到自己嘴里。这时,我见他的眼圈红了一阵,接着,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他见我睁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连忙用手指把眼泪抹掉了。
孙老师
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姓孙,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人说他久闯江湖,经历复杂,三教九流都交,黑道白道皆走,也有人说他当过土匪。但我觉得孙老师是一个很平常的好人,很和蔼的老人,很称职的老师,不像人们说得那么神乎其神,不过,有时会冒出一些“匪气”罢了。
孫老师在我们学校任教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生活十分困苦,连饭也吃不饱。孙老师想了一些办法,他在学校的花池里种蔬菜,种南瓜,作为代食品。但蔬菜还没长大,南瓜还没成熟,就被附近的饥民偷走了,而且还踏烂了菜叶,扯断了瓜蔓。这下,惹得他“匪”气冲天,“匪”性大发。他跳起脚,挥着手,咬牙切齿地大骂偷瓜贼太无耻,太卑鄙,太不是个东西了,并扬言,如果抓住偷瓜贼一定要把他的腿打断。后来,他真的抓住了偷瓜贼——一个四十多岁的乡村妇女,他不光没有把她的腿打断,还让她把摘下来的嫩南瓜拿回家去,煮给她的小孩们吃了。
还有一次放学后,我和我的伙伴小三子到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拾些遗落的红薯,用以补充家里的口粮。但不巧的是,我们的行动被生产队长王大头发现了,他夺去了我们拾的红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讨厌鬼,小混蛋!”我们很气愤,就一边逃跑一边回骂:“大头鬼,大混蛋!”王大头火了,气急败坏地追上我们,一顿拳脚把我们打翻在地。这时,孙老师路过这里,见王大头在没头没脑地打我们,就一把抓住王大头的胳膊,十分恼火地说:“你这么个大人,为什么打小孩?”“他们到地里拾红薯,我不让拾,他们还骂我!”“这么多红薯,落在地里多可惜,他们正挨饿,让他们拾吧。”“你说得倒轻巧,大家都像他们那样为自己捡红薯,生产队里的活谁干?再说,公家的东西,宁可烂在地里,也不能让私人拾!”孙老师一听火了,他的“匪”气又上来了,他甩开王大头的胳膊,用手指着他那硕大的脑门,“你说话简直像放屁!为什么宁愿烂掉,不给人吃?”“好呀,当老师的不好好教育学生热爱集体,还来骂人,真是反动至极!”“骂你说屁话又怎么样?你这样的 人,就该骂!”
队长王大头可不是好惹的,他身强力壮,五大三粗,生性鲁莽,是当地一霸。他见孙老师不把他放在眼里,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晃着拳头向孙老师扑来。别看孙老师身体单薄,但面对气势汹汹的王大头,他毫无惧色。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拉开架式,用左手隔开王大头的双拳,右手半握拳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的一下,打在王大头的鼻子上。王大头觉得鼻子又酸又疼,又麻又木,忙用手去摸。孙老师见他精神分散,赶紧飞起一脚,正踢在王大头的裤裆上。王大头“啊”的一声,捂着裤裆蹲下了,孙老师对吓傻的我们说:“还不快走!”我们拿回被王大头夺去的红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去了。孙老师也沿着乡间小路,不慌不忙地走了。
过了一年,孙老师辞职不干了。有人说他回家种地了,也有人说他去做买卖了,谁也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当老师了。
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我,孙老师成了羊贩子。之前,孙老师赶着几只羊,路过这里,到从前同事——一位大眼睛的女老师家里找水喝。“大眼睛”说没有开水了,他说没有开水凉水也行。于是他从同事手里接过来一瓢凉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抹了抹嘴唇,赶着羊走了。
赵老师
赵老师叫赵鹤琴,又叫赵云飞,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当过旧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不像个囚犯,却像个儒者,吟诗作赋,弦歌不绝,被当时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县长看中。于是,就把他释放出来,作为留用人员,没有工资,只发给他一点生活费,而且一留就是十几年。他生活费少,除了吃饭,所剩无几。没钱添置新衣服,他就用旧衣遮体,为了节省开支,他不进理发店,让朋友用剃头刀为自己刮了一个“光葫芦”。于是,当年这位风光十足的教育科长,后来穿着破衣烂衫,耸着消瘦的肩膀,晃着光光的脑袋,怀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理想,以灵魂工程师的身份,徜徉于堂堂学府之内,“隐匿”于莘莘学子之中。
我刚考入那所中学的时候,他没有教我们的课。据他的学生说,赵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特别好,深入浅出,明白如话,毫不做作,不愧是全校第一流的语文老师。同学们不光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在课余时间,也随时向他请教,他也乐于传道解惑。那时,在校园的花圃药径旁,白杨绿柳下,青松翠柏间,经常见他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挥洒自如,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谈笑风生。有时候,我也混迹其中,洗耳恭听,觉得他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都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后来,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调走了,赵老师担任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听了他的课,我觉得自己走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确有“听君一节课,胜读十年书”之感。特别是他的作文课,也和别的语文老师不一样。他有时出题目,有时不出题目,只划个范围,从来不讲中心大意、主题思想,只是让你自己去想,去做。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给一个人物画像》。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怪题目,许多同学写不出来,有的同学干脆画了一个人的头像或全身像。然而,我却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短文:“农民李老九,五十多岁,满脸刀刻似的皱纹,一部络腮胡子。他大嘴大眼,大手大脚,身材高大,往你面前一站,犹如半截铁塔。”他看了我写的短文,大加赞赏,给了很好的评语。评语中说:“读了你作文的最后一句,真有如见其人之感。”就这样,我和赵老师的关系密切起来。
那时候,我家里很穷,中午,带到学校里的午餐,除了野菜饼子,就是秕糠窝头。我怕同学们笑话,就避开大家用餐。有一天,我正躲在校园的一棵大柳树后面偷偷地啃我的野菜饼子,忽然,一只温暖的大手搭上了我的肩膀。我吃驚地抬头一看,是赵老师站在我的身边,他含着慈祥的笑容,对我点了点头,把一卷饭票轻轻地塞在我的手里。我连忙说:“老师,您的口粮也不多,我怎么能要您的饭票呢?”赵老师爽朗地笑了:“我已老朽,行将就木;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你对文学很有悟性,经过努力,定能成功。保重!”说完,他慢慢地转过身,走了。我望着他消失在柏树丛中的瘦瘦的背影,视线渐渐地模糊了。
不久,赵老师被批斗了,时间大约在1965年底或1966年初。校方组织召开了几次批斗会,学校的黑板报上出了大批判专栏。一些老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在专栏上写批判文章。其间,我也被迫写了一篇批判赵老师的文章,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贴到大批判专栏上。
对赵老师的批斗结束后,学校收回了他的生活费,把他遣回原籍监督劳动。
赵老师离开学校的那天,不少老师和同学前去围观。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夹在人群中间,想看看赵老师的现状。我看到赵老师比以前老多了,他那短短的头发全白了,面庞清瘦,两腮下陷,但那对不大的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庄严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校园里的砖墙瓦舍和依依杨柳,看了看周围无数双充满迷茫的眼睛,然后郑重其事地,深深地向在场的人鞠了一躬,然后恋恋不舍地走出了校门。我像被人劈头打了一巴掌,满面通红,冷汗直冒,惭愧地低下头去。自始至终,我都没敢迎视他的目光。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赵老师,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来到新疆,更是与他天各一方,形如参商,但赵老师离开学校时的眼神和鞠躬的身影,至今还历历在目。
尊敬的赵老师,请您原谅我吧!我写的那篇批判文章是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从此,我砸了笔,撕了纸,跑到遥远的新疆,自称一字不识的文盲,在一个偏僻小村子里务农。自责深省,洗心革面,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晃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重新提笔展纸,将我心中的激情和我们的新生活形成文字,诉诸笔端,了却您和我的心愿。
啊,赵老师,您在哪里?您能原谅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