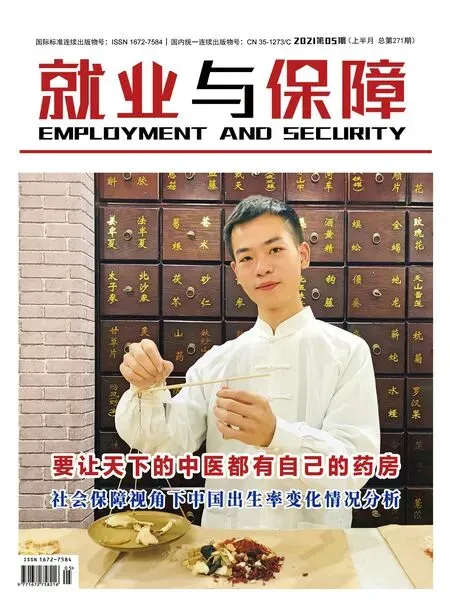社会保障视角下中国出生率变化情况分析
——以2010年~2019年数据为例
文/周含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1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0.48,连续三年下滑。本文试分析2010年~2019年中国各省出生数据及变化趋势,探讨低出生率的成因,对未来出生率进行简单预测和政策建议。下文以“两孩”简称代表2016年以来的“全面两孩”生育政策;“一孩”代表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二孩”代表家庭中第二个孩子。
中国生育研究一般将地区经济发展、城镇化、个人职业、家庭收入等作为自变量。在“两孩”放开之前,总生育率与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显著相关,而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生育政策的多样性共同对生育水平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1]。
“两孩”放开后,经济要素更受关注。当房价收入比率较低时,房价收入比率的增加会提高城镇人口出生率升;当房价收入比较高时,会导致城镇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员工、家庭主妇和事业单位员工选择二孩生育占比高于其他职业类型员工[3]。二孩生育间隔呈现明显的城乡、民族和地区差异,城市妇女推迟二孩生育的现象更加普遍。养老保险与人口出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不再受养儿防老等思想的束缚。
地域文化和地方政策也不可忽视。中国人口出生率的空间正相关性具有逐渐增强的态势,且出生率高低的空间聚集性越来越明显。作者发现,之前几十年不同地区的经济参与主体和计划生育力度不同,生育观念已经出现了显著差异。
从总结来看,国内外学者们对国家或城乡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出生率的研究较多,以地区和地方政策为中心的研究较少。本文意图通过分析多地区年出生率的连续变化,了解和展现近几年不同地区出生率变化的整体过程。
二、2016年~2019年生育数据简析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有28个省份的出生率低于2018年。例如,山东省在放开“单独两孩”的2014年和放开“全面两孩”的2016年,出生率显著提升;但从2018年起,出生率大幅回落,到2019年已经基本回到“单独两孩”放开之前的水平。可以认为,即使是传统观念认同度最高、再生育意愿最强的山东,也在2014年到2017间释放了大部分生育堆积。从全国近两年的数据显著下滑来看,中国计划生育几十年积攒起的生育堆积基本释放,短期内不会重复,2019年及之后的生育主力必定还是育龄高峰夫妇。连续四年出生率显著低于预期,应当认识到居民生育意愿不高的现实。
近几年,“二孩”与“一孩”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也值得注意。2000年~2016年,中国“一孩”出生数基本在1000万人左右,但之后逐年减少,2017年约840万人,2018年约761万人,2019年约593万人。这几年中,每年二孩出生数在700万人~900万人之间波动,尽管波动幅度较大,但没有明显的增减趋势。二孩的生育时间选择比较自由,一孩的生育数量更取决于育龄高峰人口的数量。2017年相比2016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2018年减少500余万人,2019年减少600多万人。独生子女更有可能推迟生育,延后一孩到来的时间。一孩出生数显著减少,二孩出生数波动起伏,共同导致了总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国家统计局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会继续减少,但二孩的增加缓解了一孩减少的影响。
三、“六普”以来各省生育数据走势分组分析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面临育龄妇女减少,但各省多年来的出生率变化趋势却出现了显著不同的特征。本文观察了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来的历年出生率,发现不同地区的出生率走势变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根据其走势,可以划分为五组。
(一)提升回落组
指2010年~2017年年度出生率呈上升态势,但2018年~2019年下滑明显的省份(见图1)。本组各省的2019年出生率均低于2018年,但也均高于全国放开“单独两孩”的2013年之前的平均水平。相比2017年~2018年的走势,2018年~2019年的回落趋势有所放缓,且2010年以来的出生率几乎都在9‰以上。

图1 提升回落组出生率走势图/‰
这些省份同样面临着生育高峰期人口的减少的问题,出生率提高却显著多于其他地区,即使是回落后也明显高于逐步放开“两孩”之前。可以认为,这些省份的育龄夫妇无论年轻年长,生育意愿都比其他地区高一些,即使集中的补偿生育已经结束,之后的正常二孩生育也能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二)总体平稳—高组
指2010年~2019年期间年度出生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超过10‰),且长期维持稳定的省份。该组省份出生率波动较小,多年都维持在较高且平稳的水平。本组中的宁夏甚至是2019年全国唯一一个出生率有显著提升的省份。
本组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和海南,此前实行农业人口可以生育两孩的政策;广西此前实行的是农业人口独女户可以生育两孩的“一孩半”政策,但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估测为2.333,足足高于政策生育率0.806(王金营等,2005,后文中提及的估测总和生育率均出自该文,不再逐一标注);江西和贵州2000年估测总和生育率均超过政策生育率1以上。同为“一孩半”政策的陕西则要低得多,估测总和生育率仅高于政策生育率0.199,其他省份居民则在多年中始终保持着比较旺盛的生育意愿。
(三)总体平稳—低组
指2010年~2019年年度出生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低于10‰),且长期维持稳定的省份。该组省份出生率波动不大,并且多年都维持在较低且平稳的水平。
江苏此前实行“一孩”政策,但2000年估测总和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0.459,实际生育水平与“一孩半”地区相似,明显高于东北。东北三省此前均实行“一孩半”政策,但东北城镇化早,享受“一孩半”政策影响的人口少,计划生育严格,2000年估测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相近甚至略低。独生子女的数量在略多于一代之后,多生育的意愿较低。然而,在东北育龄高峰妇女减少的情况下,出生率却没有进一步显著降低,说明“两孩”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
(四)近年下滑组
指2010年~2019年年度出生率总体平稳,但在“全面两孩”后呈下降态势的省份(见图2)。除新疆外,其余几省具有共同特征:2017年之前与总体平稳-高组非常相似,维持着较高(平均超过11‰)的出生率;但2018年~2019年明显下滑。这四个省份此前均实行“一孩半”政策,但2000年估测总和生育率均为略高于2,高于政策生育率的同时又低于总体平稳—高组的估测总和生育率。

图2 近年下滑组出生率走势图/‰
可以认为,是未严格贯彻的“一孩半”政策使得这些省份居民的生育愿望没有显著降低,但相比实行“二孩”政策的省份,本组省份的育龄高峰人口规模仍有一定程度的缩减。本组省份的出生率下滑,主要是因为育龄人口减少,而非生育观念变化导致的。以此为例,即使在下滑之后,本组省份(除新疆外)的2019年出生率仍然均保持在10‰以上,远远高于总体平稳—低组的平均水平。
四、“六普”后出生数据特征总结
综合总结以上五组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各省近年的出生率基本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两孩”政策在部分地区取得一定效果
“两孩”政策在提升回落组和总体平稳—低组的省份均取得了一定效果。尽管近两年的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出现下滑,但幅度小于育龄高峰人口数量的减少幅度,且大部分此类地区减少趋势有所放缓。其中,辽宁育龄妇女减少,但在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后,出生率出现回升,它的激励方式值得其他地区参考借鉴。由于“二孩”数量增加,在短时间内,这些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改善。
(二)地区出生率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
从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总体出生数据来看,在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几年,有至少17个省份没有经历出生率的大起大落,而是趋于平稳;如果把仅在羊年下滑的省份也计入,则多达24个。在这些省份,出生率主要随着育龄高峰人口波动,“两孩”虽然是政策大调整,但对于大部分省份影响微弱。本文预测,这些地区将在未来数年中的出生率将继续随育龄高峰人口数量小幅波动,直至政策再次调整,或普遍接受了新生育观念的青少年进入育龄高峰期。
(三)大部分省份的居民生育观念渐趋稳定
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影响出生率的主要因素就不再是政策的限制或鼓励,而是育龄人口的主动选择。“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在部分地区仍然有一定市场,但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这种观念将逐渐淡出主流视野。“两孩”政策的放开,只是让那些此前想多生而不得的居民能够生育二孩,短时间内却不能改变那些不想多生的居民的生育行为,而从数据来看,前者的数量比较有限。想要切实增加人口出生率,需要更实际的配套措施。
五、政策建议
(一)维持“两孩”生育政策稳定
生育观念受到政策、公共服务、医疗、教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更包括每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和耳濡目染。相比经济、房价、职业等变化较快的要素,生育观念和文化的变化要缓慢得多,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往往起到关键作用。鼓励生育切不可操之过急,必须慎之又慎。因此,社会保障性的政策应当具有连贯性,人口政策作为根本政策更是如此,唯有维持稳定才能让未来可期可控,频繁变化会让居民和用人单位无所适从,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没有明确稳定的发展目标。“二孩”既符合当前居民普遍的生育期望,又符合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学理论,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在新的人口常态形成之前,不宜再进行大的变动。
(二)完善有关政策,理性促进设施建设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需要尽快落到实处。由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能力养育二孩的通常是双职工家庭,但两孩政策使得妇女面临更多的就业歧视,一旦生育二孩更可能面临职业中断,即使没有中断,双职工家庭也会面临精力不足以养育两个孩子的问题。即使交由祖辈抚育,“一孩”时尚且算是年轻力壮的祖辈在“二孩”时也年龄更大,更难以承担抚育重任。育龄妇女就业歧视问题和二孩婴幼儿时期的抚育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极大降低二孩生育的积极性。
(三)合理宣传,调整青少年生育观念
未来十五年,计划生育执行相对严格时期出生的青少年将陆续进入育龄期,他们中包括大量可能是唯一一代的独生子女,观念与上一辈和下一辈有所不同。在观念尚未改变时,强制性方式不应提倡。想要真正改变青少年的生育观念,除了出台相关政策外,国家还应该通过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环境、进行合理的文化宣传、在义务教育中适当提倡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帮助青少年调整生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