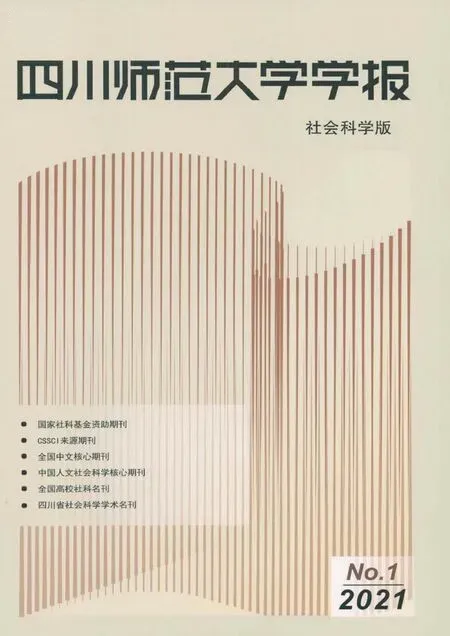汉画的空间特征述论
“空间问题”是汉画理论研究一个非常核心的范畴。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于该方面多有思考,各成一家之言,但却往往忽略了对其最基本的概念进行辨析。换言之,要对汉画的“空间问题”做出任何形式的回答,首要之务是对汉画的“空间”概念进行衡量。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汉画的空间特征进行重新的审视、梳理与界定。一方面,图像性是汉画的根本特质,其造型、线条、纹饰等元素塑造了汉画区别于其他器物的图像空间;另一方面,器物性是汉画的物质形体,其在预先设计的丧葬建筑中以装饰材料存在,并在特定的位置组构建筑空间;再一方面,丧葬性是汉画的价值选择,无论是图像叙事的主题与内容,还是器物装饰的配置与规律,都要吻合汉代丧葬礼俗对丧葬建筑的空间要求。这种纠缠的三重性,不仅昭示了汉画与建筑共生、并存、互动的辩证关系,而且它们共同组成了汉代丧葬礼俗的特殊场域。
一 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汉画的空间生成意义
想要探讨“汉画的空间究竟是什么”,必须先要回答“汉画是什么”。然而,学界对“汉画”概念的使用并不十分严格,如顾森先生称:“汉画是中国两汉时期的艺术,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画绘(壁画、帛画、漆画、色油画、各种器绘等)、雕像(画像砖、画像石、画像镜、瓦当等浮雕及其拓片)。”①顾森《中国汉画图典》,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序。常任侠先生则认为:“汉画艺术是多样发展的。就今所知,有下列各种:一为绘在缣帛上的;二为绘在粉壁上的;三为绘在各种工艺品上的,如铜盘、漆盘、漆奁、玳瑁制的小盒、竹编的小箧等;四为刻在石材建筑物上的;五为印在墓砖上的。”②常任侠《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艺术的发展与成就》,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这些定名大致是以汉画的载体材料和造型技术为标准,其合理之处在于,不同材料与技术组合而成的汉画往往有着自身的小传统,在建筑空间中亦有相对稳定的分布区域,方便于进行某一类型的独立研究;但不妥之处是,即使不同类型的汉画在材料与技术方面有差异,但是在图像的内容与丧葬的使用层面,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它们同属于汉代丧葬文化的大传统。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汉画”定义为有图像的丧葬器物,亦称“图像性丧葬器物”,以此来尽可能克服概念使用上的矛盾,并全面地覆盖汉画的诸种类型。
学界由于汉画定性产生的分歧,将问题带入了汉画的专门类型研究中。比如郑岩先生提出使用“墓葬壁画”去替代常用的“墓室壁画”一词,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使用“墓室壁画”的概念无法涵盖汉代墓葬中墓门与墓道处装饰的壁画,而且忽略了对同样拥有绘画特征与壁画装饰形式的画像石、模印画像砖等的考察。因此,他主张打破材料的界限,将画像石、画像砖等具有绘画特征的图像也容纳到“壁画”的概念中,以便于观察不同形式的壁画在内容等方面的联系①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6页注释①。。而在更早的时候,杨泓先生亦在《汉代美术考古绘画篇》中使用壁画概念囊括了画像石与画像砖②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44页。。由此可见,学界也一直试图在强调汉画材料与技术方面的特性的同时,打破单一类型汉画研究导致的片面性与断裂性。在此类已经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是以“壁”为载体,将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共同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但是对意义同样重要的帛画、漆画、铜镜画等却选择了搁置,因为这是“壁”的载体形式无法涵盖的类型区间。
而将汉画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定性,则能最大程度上支撑起汉画的广泛定义。就“图像”的界定而言,是基于汉画中“画”的定义,这沿用了金石学家的考证,如宋人洪适《隶释》卷十六在著录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画像题记时,提到武梁碑中“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一句,曰:“似是谓此画也,故予以武梁祠堂画像名之。”③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第168-169页。又如山东苍山东汉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题记亦称墓中画像为“画”④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2页。。显而易见的是,汉画与一般器物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其视觉图像所赋予的特殊涵义。再就“器物”的界定而言,无论是作为丧葬建筑中陈设的随葬品,还是丧葬建筑的一个构件,汉画的载体形式皆是丧葬礼俗中具有特定功能性的器物。巫鸿先生在对墓葬“物质性”的研究中,已经关注到作为器物的随葬品的物质和视觉属性⑤巫鸿先生认为:“墓葬‘物质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明器’。从功能上说明器是专门为死者制作的器物(包括墓俑),但是它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其特殊的物质性来理解。”又说:“明器所保留的仅仅是日常器物的外在形式,而拒绝了原物的实用功能。在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内,这种对功能的拒绝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材质、形状、色彩和装饰来达到。”见:〔美〕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梅玫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75页。。在此概念中基本涵盖了帛画、漆画、铜镜画等丧葬建筑中的陈设器物。而将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同样置于器物的视域,是因为三者的载体形式并非天然的物质材料,而是经过人工制作的物品,即一面平整后的墙、一方烧制的砖、一块被打磨的石头,它们以用具的方式直接参与到丧葬建筑的构筑中。因此,可将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称为丧葬建筑中的构件器物。虽然陈设器物与构件器物在物质实用性上有所差异,前者往往讲究“貌而不用”,后者则要求始终为建筑的稳固发挥作用。但它们均被统摄在汉代丧葬礼俗的意义圈层中,并叠加图像的象征性作为丧葬建筑的“装饰”。正是在此意义上,汉画的图像性、器物性与丧葬性混合与纠缠在一起,它不再是单纯的人工造物,而是图像的形式存在、器物的物质存在与丧葬的价值存在共生的意义物。
首先,汉画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实用功能,是扎根于它的物性本质与丧葬建筑的共存和构建关系。汉画绝不是因艺术目的而被制造,在汉代它是丧葬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其首要任务是满足建筑空间所需。一方面,陈设器物是在丧葬建筑中充当间接组成部分,其实用意义不在于物质材料本身,而是它的外在形式以及在建筑空间中占据的位置。譬如满城一号汉墓的左耳室摆放了四辆马车和十一匹马,右耳室摆放了大量陶器和陶缸。据考证,左耳室当为车库,右耳室则作府库。可见,陈设器物被墓葬场合选用的原因,与墓主在死后世界的使用需求有关,也与设计者隐含的对建筑空间的划分有关。另一方面,构件器物是在丧葬建筑中充当直接组成部分,它的实用性能关乎到丧葬建筑的实际构建与竣工后的持久性,因此对其物质材料有特别要求。以画像石为例,多选用石灰岩和砂岩,再在其中尽可能选择没有自然裂缝与驳杂斑点的为刻画做准备,如山东嘉祥县武氏家族墓地的“从事武梁碑”的记述:“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⑥洪适《隶释·隶续》,第75页。可见对其材质的采选标准的严格和细致。概括而论,二者都涉及到器物与器物之间、器物与建筑之间在物质层面的联系与呈现。

图1 市楼
其次,汉画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审美功能,是产生于它的图像内容本身以及对丧葬建筑的装饰效果。正是因为汉画在一定物质材料表面彰显出有意味的图像形式,令其本身具有了艺术的潜质,从而在观赏的角度天然地与审美联系起来。一方面,汉画的图像可作为一幅平面性的绘画,在技法与内容上显示出结构与表意的美感。譬如四川广汉市新平镇罗家包汉墓出土的“市楼”图(图1)①高文主编《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95图,第96页。,它是镶嵌在墓壁的一横排画像砖的其中一枚,画面中有人登石楼,有人坐宅院,有人穿市门,还有犬飞奔。图像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汉代市井生活的部分场景,一股生机勃勃的浓郁生活气息穿透出画像砖的表面,给观赏者以审美的愉悦。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汉画制作的目的始终是从属于丧葬建筑,并以其装饰特性塑造建筑的整体美感。譬如西汉晚期的卜千秋墓,其主室顶部绘满壁画,东端绘有伏羲与日象,西端则是女娲与月象。显然,这是根据墓室总体设计的需要,以对称构图的方式来进行装饰,以此令墓室呈现出平衡与有序的视觉效果。又如山东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墓中室西壁,上面刻有“聂政刺侠累”图,下面则是“荆轲刺秦王”图,两幅图以共同的历史主题,在丧葬建筑的同一区域进行组合装饰,以产生连续性的美感。可见,汉画的图像虽可独立表意,但其在丧葬建筑中则往往是以“系列”的形式陈列,由此形成某一特定主题或风格的组图。
最后,汉画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象征功能,是源自它的图像内容与丧葬建筑共造的象征性宇宙。这种图像象征层面的效能,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观物取象”。至少从伏羲对天地的“仰观俯察”并以八卦的基本图式笼罩天地万物开始,图像便具有了以有限的形式对无限的世界进行象征的功能。进而,汉画通过自身的造型图案在丧葬建筑中进行有规律的配置,以隐喻与暗示的方式将一座死寂的丧葬建筑,变成了一座以墓主为中心的生意盎然的微型宇宙。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秦汉时代的人们基于经验,以为象征和象征所模拟的事物或现象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系,于是那些画像图像类的东西可能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品,而有某种神秘的实用意味。”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以汉画中的四神图像为例,通常所见的四神画像是按东、西、南、北的四方次序进行排列,比如对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椁墓的还原中,其椁内四壁按方位完整地刻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画像。显然,这种神兽的形象组合,将椁内的空间转化成了四方天地。又如河南南阳汉画像馆所藏的唐河针织厂汉墓“四神”汉画像砖,其以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的位置布局,一幅图像便预示了一个微型宇宙。当然,还有更复杂的组合形式,四象、日月、星宿、仙神等元素,被共同组构进这一个时空交错、琳琅满目的宇宙中。
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汉画的空间意义,发端于其图像性、器物性、丧葬性叠加的三层属性中,并具体呈现出三种层次的空间视域:第一层,是器物表面的平面性图像空间;第二层,是丧葬器物的布局与三维建筑空间的互动;第三层,是丧葬空间中具有汉画的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些,为探寻汉画在汉代宇宙观、生死观、礼乐观的上下文中的可能意义提供了内在逻辑。
二 扩张、压缩、均衡:汉画的空间构图特征
若将汉画视为空间结构的主体,图像就是分析汉画的空间含义的视觉证据,此时,汉画的空间建构直接指涉图像的空间构图。但汉画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复杂性,一方面令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平面性绘画,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其“画”的观念所遵循的传统艺术观念,再一方面则是其图像空间与丧葬建筑空间的交互原则。因此,对汉画的空间构图的研究,需将特性与共性兼顾起来,可从其成型形态、透视法则与装饰技法予以考究。
其一,从汉画的成型形态来看,体现出空间构图的放大性,即将二维的平面图像放大为三维的立体造型。已有考古资料表明,在流传至今的诸种汉画出土文物中,画像石、画像砖的数量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①中宣部组织编撰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是目前我国最完整的“中国美术全书”,以其中收录的汉画拓片数据为标准进行统计,可基本勾勒出汉画目前的出土与整理情况。就汉画像石而言,集中收录于《中国画像石全集》(8卷本)的前7卷,共计拓片1676幅。就汉画像砖而言,则集中收录于《中国画像砖全集》(3卷本),共计拓片444幅。二者的数量均远超其他种类的汉画。。从现代美术的角度看,雕刻是将物质材料本身变成可视、可触的三维空间,而绘画则是在二维的物质材料表面创造出虚拟的三维空间,因此,就汉画像石的成型技术来说,它显然应是属于雕刻。但是,这却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在汉代人的艺术观念中,画像石并不被称为雕刻,而是直接称为“画”。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画像石的制作程序中,画师会先于石师在打磨后的石面用线条绘出画像的底稿,这是汉画成型的基础。如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尚可辨识出一些墨线的底稿。另一方面,画师会对石师雕刻好的画像进行施彩涂色,令其具有和帛画与壁画一样的色彩要素,这是典型的彩绘呈现。如南阳石桥画像石墓中的彩绘画像石上,尚遗存有多种矿物质造成的调色效果。再一方面,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上,题记铭文所载“调文刻画”②朱锡禄《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第63页。的文字,直接佐证了汉代人对汉画的“画”观念的认知。但是,若轻视汉画像石中雕刻的层面也是大不妥的,因为汉画像石基本属于线刻或浮雕作品。这种雕刻的属性,导致画像石彰显出一种新的图像空间特征,即以物质材料平面为载体的二维图像被扩张为一个三维造型,并且绘画创造的虚拟三维空间被叠加上雕刻创造的现实三维空间的效能。由此似乎可以大胆推测,或许在汉代,绘画与雕刻正处于“刻画一体”的交融状态,在创作阶段二者并没有鲜明的独立意识。汉画像砖的成型技法与画像石也异曲同工。它是以拍印或模印的方法制成的一种图像砖,在制作模塑时均需勾勒出墨线画稿,再用刀刻图像模板,其最终成型的产品,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上具有绘画与雕刻的双重性。因此,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兼具绘画与雕刻、二维与三维的空间属性,它们首先以线勾画,进行二维空间的形象设置;接着以刀刻琢,用凹凸阴阳让二维形象立体化,并辅以色彩铺陈;最后整个作品由二维平面统摄,局部形象呈三维立体效果,形成了二维与三维交织、三维扩张了二维的奇妙的空间效果。这种扩张了的空间,有平面的包容性,也有立体的典型性,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加丰富厚实。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丧葬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墓室的内部空间、整个建筑的组织构造相交织容套,即大空间中有小空间,以及整体架构中的构件穿插,造就了汉代丧葬建筑空间玄迷幽深而又不乏生动有趣的意味。
其二,从汉画的透视法则来看,体现出空间构图的压缩性,即将事物的三维真实压缩变形成二维呈像。对于汉画像石的空间透视法问题,信立祥先生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将其分为两类,即等距离散点透视构图法与焦点透视构图法,前者又细分为底线横列法、底线斜透视法、等距离鸟瞰斜侧面透视法、上远下近的等距离鸟瞰透视法四种③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9页。。比较而言,这是两类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透视法体系。一方面,等距离散点透视讲究的是将事物按照同一角度和相等距离的视觉原则绘制在画面上,事物整体呈横线或斜线排列。这是整个汉画的核心透视法,基本承袭了中国早期的透视传统,早在战国时期出土的图像器物上就已经有广泛的实证。另一方面,焦点透视构图法讲究的是将画面中的某个事物作为一个固定的焦点,其余事物根据远大近小的原则分布,最远处的事物会被逐渐缩小为一个灭点。这与西方绘画透视法的核心原理遥相呼应,但是这类型的汉画像石目前发现的数量极少。继续比较,前者不符合真实透视,后者则强调人的视觉真实;前者符合的是审美习惯,后者符合的是物理规则;前者克服了物理空间观念的限制,适合于建筑装饰的需要,后者则从科学的视域表现空间的规律,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产物。总的来说,汉代人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画面中体现出真实空间的三维遮蔽现象,或者说,他们关注的重心始终是画面的内容意义而不是再现意义。因此,汉画的等距离散点透视法虽然缺乏焦点透视的科学性,但是对于具有特定功能意义的丧葬绘画来说,它却更适合主题的表达。根据丧葬建筑的空间结构和内容要求,汉画通常多是长卷式或分层分栏式组合构图,这便要求数块砖(石)或几面壁以连续性的结构组成画面。若是焦点透视的构图,首先便要求克服砖(石)与砖(石)之间、壁与壁之间空间的相互融通问题,当内容越丰富和图像越庞杂时,便越难以在几幅分隔的三维图像中寻找到统一的焦点,并将其组合进一个符合视觉真实的整体三维空间中。然而,散点透视原理则没有这种烦恼,它只需要关注物象之间相互关联构成的画面意义,用简单的二维层面的左右、上下关系,便可表达三维空间的纵深与远近。在长卷式构图中,连续性的长条结构画面往往具有绵延奔腾的节奏感,如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中的出行场面,营造出一幅场面宏大、气势壮观的空间感。而分层分栏式构图,虽然以边框将丧葬建筑的四壁分成了若干部分,各层也或许描绘不同的内容,但是仍可将一层或几层图像连成一片,其整体表现某一个丧葬建筑特定区域所需的主题。如打虎亭墓就很好地协调了画面空间的这种分隔与联合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和谐统一的空间秩序感(图2)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彩版六。。进一步讲,等距离散点透视法通过将事物从三维向二维的压缩,实则是要用二维呈像的方式,克服丧葬建筑的结构障碍,并在“装饰”层面彰显出古朴雄浑的空间排列质感。可以逆推的是,这种整体美感及节奏感,或许更符合汉代人对空间秩序的审美要求。
其三,从汉画的装饰技法来看,体现出空间构图的均衡性,即使用纹饰令画面保持视觉和审美心理上的平衡。纹饰作为一种图像符号,是先祖对自然万物的抽象总结,在上古时期的彩陶和青铜器上就已经有简单的花纹,最常见的题材是鸟兽草木,其作用除了传达信息与美化器物,还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比如夏代所谓“远方图物”,就是要“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32页。。换句话说,纹饰造型的简约并不代表其意义的简单,反而是一种高度抽象与凝聚的结果。在汉代,纹饰图像主要呈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作为器物的主题图像。比如汉代铜镜上多装饰有四神的纹饰,其不仅通过视觉的张力让观者收获审美的享受,而且通过本身的图像符号赋予了铜镜象征的功能。更巧妙的是,天地四方的四神象征与铜镜的圆形体例融为一体,令它不仅在器面布局上流畅而有韵律,更吻合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第二种形态是作为装饰图案填充画面的空白,以此衬托主题或者烘托氛围。如在汉画的神话类题材的图像叙事中,画面的中心通常是伏羲、女娲或者东王公、西王母等,围绕核心形象则常环绕点缀有各式的云纹,使得画面呈现出云雾环绕的仙境效果。其对云纹的运用方式,一种情形是基于画面上下左右对称感的考量,另一种情形则是,虽然以非对称的组合出现,却能将画面内部的所有形象串联在一起,实现整体美的均衡。譬如山东武斑祠的一块画像石(图3)③傅惜华、陈志农编《山东汉画像石汇编》陈志农绘,陈沛箴整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页。,其第三列出现了三处云纹装饰,虽非对称,却令画面整体饱满而平衡。第三种形态是作为画面的边饰,其以带状的形式,整齐地围绕在主题图像的周围。泛览陕北画像石中的边框,多以蔓草状与流云状为主,其对边饰的使用常超过其它地区的惯例,整体凸显出画面空间的匀整感。而河南画像砖的边饰则凸显出对常规模式的变体,如洛阳出土画像砖上的变形柿蒂纹、方块“S”形纹等,郑州则有变形虫纹与乳丁纹、变形山树纹、变形柿蒂云朵乳丁纹等④张文军、田凯、王景荃《河南画像砖概论》,《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河南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显然,边饰在汉画构图空间中的大量使用,是因其可以将画面的内容有序地收束进一个稳定的框架之中,令画面呈现出形式的整齐与匀称,并且以分层与分格的布局,令汉画在丧葬建筑中具有统一性与连贯性。
汉画的空间构图的扩充性、压缩性和均衡性,基本勾勒出以其自身为空间主体所显现的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汉画的空间构图特征与建筑空间的联系是断裂的。进一步讲,空间构图的放大性将使汉画与丧葬建筑呈现更强烈的三维交互效应,压缩性令其在建筑的壁面呈现出古朴雄厚的艺术风格,均衡性则使各式各样的图像在建筑的整体布局中被有秩序地编排。可见,汉画与丧葬建筑的空间是相辅相成的。

图2 密县打虎亭二号汉墓中室甬道券顶壁画全貌

图3 武斑祠画像(其五)
三 程式、连通、模件:汉画的空间位置特征
若将丧葬建筑视为空间结构的主体,对汉画的空间特征的考察,便转变为对汉画在丧葬建筑中空间位置的探究。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汉画与丧葬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指向附有汉画的丧葬建筑与丧葬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换言之,不仅汉画以“系列”的方式在对丧葬建筑的空间组织中发生效能,丧葬建筑也是以“组群”的概念在整个汉代丧葬礼俗的特殊场域中具有各自的逻辑与关联。以下将从汉画对建筑的配置情况、对建筑之间关联结构的塑造以及对不同建筑的文化意义的契合三个角度,介入其空间位置特征的考察。
首先,就汉画在丧葬建筑中的配置情况而论,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程式性。山东省嘉祥县武宅山村汉代武梁祠前的墓碑记载:“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①洪适《隶释·隶续》,第75页。可谓直接佐证了考古学家与美术史家对“汉画在总体空间中的配置具有规律性”的推测是符合汉代的真情实况。这样来看,汉画不仅仅只是作为建筑材料充当整个丧葬建筑的一个组成构件,更是将混乱无序的丧葬建筑空间细化与重构为一个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特殊意义场域。这种规律性,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法则密切相关,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谓“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②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纵观出土的汉画遗址,其在丧葬建筑中的空间配置情况,已经体现出依据章法对空间进行建构的历史事实。通常的情形是,就墓地祠堂而言,汉画作为建筑构件主要配置在面对祠堂入口的后壁、祠堂左右侧壁以及祠堂顶石内面,因祠堂内壁平面往往形制规整,常常形成横贯多壁而连成一体的整幅画像。就墓地墓室而言,则因多柱、梁、门道等结构,空间变化多端,于是其汉画往往布局在墓门、墓道和墓室壁面上。就墓地石阙而言,它是成对建立在墓室建筑群入口两侧的建筑物,汉画主要配置在阙身,也见于基座、枦斗与正阙重檐顶之间的枦柱上,往往讲究画像雕刻与建筑造型的融合统一。可见,这种“经营位置”的绘画理念被充分推衍进了整个丧葬建筑的空间建构中,令每一幅汉画的位置都讲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搭配关系。进而,当汉画的位置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固定化,章法即成。不仅如此,汉画在丧葬建筑中所在的区域,还被进一步分割并约定俗成地对应某一特定的题材内容,如“(陕西、陕西汉画像石墓的图像配置规律)门楣上一般刻画有墓主车马出行图、祭祀图或升仙图;门柱上部一般刻画有东王公、西王母等仙人图像,下部有门吏或其他神兽;门扉则刻有铺首衔环和朱雀等图像”③信立祥、蒋英炬《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综述》,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5 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8页。。显然,这已经形成了一条规律性极强的空间配置程式。这种有规律、有秩序的图像配置,在艺术表现的层面难免显得雷同与缺乏变化,但是却能在有限的建筑空间中明晰地表达出图像的意义。
其次,在汉画对丧葬建筑之间关联结构的塑造方面,体现出汉画的空间连通性。将目前已有的历史遗址、出土文物与文献典籍纳入共同的研究框架,是可以基本还原汉代以墓地为核心的丧葬建筑群。进一步讲,若汉代墓地的每一座丧葬建筑都是总体设计之后具体建造的结果,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应该是若干割裂的界域,而是一个统一的建筑群落系统的不同单元。在汉代丧葬场域中,最为汉人重视的自然是墓室的修建,如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墓地:“(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8页。。而在墓上往往会起坟,坟的高度则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如“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⑤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03页。。在墓地上亦有种树的惯例,常见有松柏、梧桐、杏树等,如《盐铁论·散不足》载:“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①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又会绕墓筑垣,作为整个丧葬场所的边界,汉哀帝对宠臣董贤的恩典之一便是:“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②班固《汉书》,第3734页。在墓旁通常会建造祠堂,壁间亦往往雕刻人物画像,如山东省肥城县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有石室三间,石壁有雕画,有汉人来游题字。墓前又会建造阙,其建筑表面往往雕镂得精致华丽,今在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阙便是一例。墓前亦会筑造神道,上面或有刻画,只是比较少见,《隶释》记载了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有云“其下又刻龟蛇虎首,所画甚工”③洪适《隶释·隶续》,第145页。。又会在墓地设石兽、树石柱,霍去病的陵墓便是如此,《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骠骑将军“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司马贞《索隐》引姚氏案语云:“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57页。然后按礼制通常都会刊石立碑,当东汉农学家崔寔的父亲去世后,他便“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⑤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31页。。这些丧葬建筑如蛛网般编织成了汉代丧葬空间的整体。虽然建筑之间可能存在物理的距离,但是其在象征层面的一体性却可以在汉画的空间位置中获得支持。比较典型的是车马出行图,一般见于地上的祠堂和地下的墓室,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配置在祠堂后壁“祠主受祭图”的上方,譬如孝堂山祠堂后壁该部位就有“大王车马出行图”;二是配置在祠堂“祠主受祭图”的下方,譬如胡元壬祠堂刻有“车马出行图”便在后壁石的最下面;三是配置在墓室较高横梁上,譬如宿县褚兰一号墓,其南北壁的横梁各有一副墓主车马出行图。第一种类型的车马出行图通常代表祠主在生者世界的身份,而第二种与第三种则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循环交通。正如信立祥先生所言:“由于地下墓室与墓地祠堂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墓葬建筑,两者的画像内容在图像学意义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联系的纽带就是墓主(即祠主)的车马出行图。为了表示墓主是从位置较低的地下灵魂世界到位置较高的墓地祠堂去接受子孙祭祀,墓室中的车马出行图一般配置在位置较高的前、中室横梁上,而在祠堂中则配置在后壁及左、右侧壁的最下层。”⑥信立祥《苏、皖、浙地区汉画像石综述》,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4 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0页。显然,图像中的车马成为了墓主在地上世界与地下世界互通的工具,这克服了物理空间的阻隔,通过汉画的空间连通性,丧葬建筑以关联的结构疏密得当、错落有致地布局在墓地中。
最后,在汉画对不同丧葬建筑的文化意义的契合方面,则显示出汉画的空间模件性。从汉画的图像内容性质看,李发林先生将其分为四类:一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二是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三是刻画祥瑞、神话故事的;四是描绘自然景物的⑦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蒋英炬、杨爱国先生也分为四类:一是社会生活;二是历史故事;三是神鬼祥瑞;四是花纹图案⑧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5页。。从汉画的图像配置主题看,巫鸿先生将武梁祠分为天界(屋顶)、仙界(山墙)、人间(墙壁)⑨〔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杨、岑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2页。。信立祥先生则将汉画像砖的题材分为天上诸神世界、昆仑山仙人世界、现实人间世界以及地下灵魂世界10信立祥《中国古代画像砖概论》,《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汉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由此可见,汉画在不同丧葬建筑中的图像内容与主题都大致相似并高度重合。这便导致出一个新的问题产生,即相同内容或主题的汉画配置于不同的丧葬建筑时,其图像意义是否会有变化?雷德侯在研究中国艺术时提出的“模件化”概念11〔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页。,对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思路。换言之,在汉画的图像系统中,其中任一单独的抽象图案或装饰纹样,皆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模件,而这些模件既可以独立成图表意,也可以在相互的变化与组合中创造出极为复杂的图像。而当更高层次的模件包含低层次的模件时,它将主导低层次的模件涵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此类推,汉画本身是属于丧葬建筑装饰体系中的模件,丧葬建筑又是属于汉代丧葬场域(即丧葬建筑的总集)的模件。在这种由简而繁、不断叠加所构成的形式系统中,仍然要遵循高序列对低序列模件的意义改造规律。譬如祠堂与墓室,虽然都属于丧葬场域系统中的一个建筑模件,但是其空间功能上却各有侧重。墓地墓室的重心在于为墓主营造死后世界的日常生活,包括对升仙的渴望;而墓地祠堂则更强调对死者的祭祀,以及对生者的教育。因此,在墓室或者祠堂中,相同内容或主题的图像,其意义也会发生相应的偏移。比如墓室中的“狩猎图”,如陕西米脂官庄墓门楣画像①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5 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40,第30页。,画面中狩猎的队伍十分庞大,十多个强悍骁勇的猎手,有刺熊者,有射狐者,有搏虎者,有操弓者,飞禽走兽则散落其中,仓皇逃命。这种狩猎的精彩场面,应反映了墓主日常生活所需,如桓宽《盐铁论·刺权》云:“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②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121页。正说明了狩猎是汉代贵族的风尚,墓室既然是现实世界的镜像,自然要将墓主日常所享受的生活尽可能地映射入死后的世界。再观祠堂中的“狩猎图”,如孝堂山石祠西壁画像的第五层③蒋英炬等著,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图22,第40页。,画面左右各有数人,持器驱犬,相向而行,中间则是由左向右奔跑的大批野兽,中央靠左还有一牛车,车后已悬挂有猎物。这热烈紧张的猎物场面,和该祠东壁画像中的“庖厨、百戏”图④蒋英炬等著,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孝堂山石祠》,图18,第30页。遥相呼应,生动地还原了在祠堂的文化意义中,从生者为祠主准备“血食”,到祠主享受“血食”的过程。可见,将丧葬场域的系统拆分成不同的建筑模件,其每一类型的建筑具有各自的功能侧重。而作为建筑的装饰模件的汉画,其图像意义也将根据这种“侧重”被修改。此时,正体现出汉画的空间模件特征对特定丧葬建筑空间的文化契合。
由此可见,汉画空间位置既赋予丧葬建筑象征意义,将其从视觉和物质空间推升到抽象和经验空间,又将建筑与建筑有序地交织起来,使单个建筑突破了物理限制而获得意义层面的相互连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建筑物的装饰模件,汉画在不同建筑的文化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是有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又统合进了汉画的空间位置所具有的多重效能中,进而将整个丧葬建筑场域建构成形态各异而又和谐统一的空间。
四 结语
总之,所谓的汉画的“空间特征”,是在汉代丧葬礼俗的特殊场域中,由作为图像性丧葬器物的汉画与丧葬建筑共同塑造的。如同宗白华先生所说:“一切艺术综合于建筑,绘画雕刻原本建筑之一部,而礼乐诗歌剧舞之表演亦与建筑背景调协成为一片美的生活。所以每一文化的强盛时代,莫不有伟大建筑计划以容纳和表现这富丰的生命。”⑤宗白华《〈我国都市计划溯源〉编辑后语》,《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无论是汉画的空间构图特征,还是其空间位置特征,都需纳入到丧葬建筑的空间环境中才能真正呈现其特质、功能以及意义价值。而在器物、图像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中,显而易见地渗透着汉代人对天道与人事的认知,这是今人倒推“汉画的空间究竟是什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