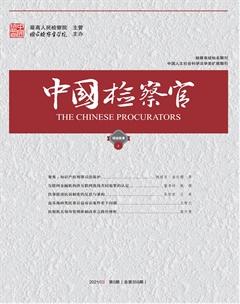互联网金融机构涉互联网洗钱共同犯罪的认定
董李培 姚理
摘 要:近年来涉互联网洗钱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以行为共同说共犯理论为基础,界定互联网金融机构在涉互联网洗钱犯罪活动中的作用,结合其反洗钱义务判断机构及相关人员的主观故意,准确认定该类机构参与洗钱的共同犯罪责任,可精准打击涉互联网洗钱犯罪活动,并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司法保障。
关键词:涉互联网洗钱 互联网金融机构 共同犯罪
惩治洗钱犯罪是打击和预防上游犯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重要方式。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反洗钱在完善国家治理、维护金融安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近年来我国网络支付业务金额持续较快速增长,第三方支付与第四方聚合支付迅速普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7.68亿,占网民整体的85%。[2]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多元化支付新场景,为资金转移需求大、隐蔽性与快捷性要求高的上游犯罪者创造了新的犯罪机会。从犯罪机会论的角度看,涉互联网洗钱犯罪数量上升、手段翻新在一定时期内会成为趋势,不但增加打击上游犯罪和追赃的困难,也可能诱发新的上游犯罪。[3]
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以下简称“从业机构”)包括在我国境内经批准或者备案设立的,依法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和其他从业机构。若此类机构有意识地参与洗钱活动,危害性将会因互联网的产业化运营模式和指数级运作效率被放大。因此,有必要研究从业机构及人员涉互联网洗钱共同犯罪责任问题,从通道出入口堵塞涉互联网洗钱路径,通过“断路”反向遏制并预防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
一、互联网洗钱行为的典型样态
传统洗钱行为阶段相对明晰,一般分浸泡、分根、甩干三阶段[4],实质是资金运作,目的是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混同于正常经济生活往来资金,以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实现非法占有。就互联网洗钱行为而言,“浸泡”是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移到互联网金融场景内;“分根”是通过互联网金融交易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与非法来源相脱离,隐身于正常互联网金融业务中;“甩干”即是犯罪所得经过互联网金融场景清洗漂白后,改头换面为合法资金,继续在互联网金融场景或回到线下正常流通。互联网洗钱借助互联网科技,利用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多样性、非接触性,跨越空间实现高频次资金运作。洗钱操作在各阶段高度混同,浸泡、分根、甩干有可能一步到位、同步完成,甚至与上游犯罪获取犯罪所得混同而难以区分。
(一)混同交易型洗钱
混同交易型洗钱利用互联网金融手段进行资金混同进而转移,较之依托传统金融机构账户更加隐蔽,如利用网络支付混同。第三方支付及聚合支付方式普及以来,扫码支付因其便捷性和低成本,迅速成为日常线上及线下最常见的支付场景。2018年以来,网络上出现以“抓蛋APP”[5]为代表的一类智能众包型非法资金结算模式。行为人编写程序平台,以返佣吸引用户注册,收集并利用注册用户的个人第三方支付账户收款码作为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入口,再通过用户提现、转账将资金汇集至指定账户。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分散在大量正常用户的支付账号而与正常个人收付款高度混同,第三方支付平台和金融机构均难以监测。
还有利用网络支付业务中“二清”模式逃避反洗钱风控监管,实现洗钱目的。[6]存在“二清”的电商平台,其交易资金和信息均脱离监管,为洗钱提供渠道。洗钱人通过虚设订单、虚假交易,自买自卖即可完成黑钱洗白,而其异常交易信息与资金流则借平台“二清”脱离正常的反洗钱监管。
又如利用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业务服务平台,以“自贷自借”“自融自投”等方式将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混入正常互联网金融资金流转,利用从业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及可疑交易监测报告等反洗钱风控机制的执行漏洞达到洗钱目的。
(二)虚拟商品交易型洗钱
虚拟商品交易无需实物交割。线上高频交割虚拟商品,不但成为上游犯罪的线上入金渠道,也成为其流转结算道具。完全意义上的虚拟商品,如游戏点卡、比特币等,或有实体权益支持的线上商品,如话费、油卡、视频会员等,均可成为道具虚拟商品。如洗钱行为人利用比特币匿名、去中心化等特点,用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在比特币交易平台为租借、收购的他人正常用户账号充值购买比特币,后提币在境外卖出提现。[7]
又如在“922”跨国网络赌博案[8]中,犯罪分子通过勾结话费充值渠道商,从话费充值渠道商批量、实时获取正常用户的充值订单信息,并从赌博平台获取赌资充值订单信息,利用充值服务响应平台技术将赌资支付与正常话费充值相匹配替换,从而让赌客为正常用户充值话费,拦截正常用户支付的话费资金,扣除手续费后通过网银转账结算给赌博团伙,为赌博入金的同时洗白赌资,逃避反洗钱风控监测。
(三)接口移植型洗钱
网银支付、第三方支付等主流网络支付手段都已纳入国家反洗钱监控管理体系。但随着网络支付市场逐渐饱和,部分支付服务商为了超额利润,挪用其控制的正规支付接口,绕开监管体系,使用自己注册和控制的商户为不法行为提供支付通道和資金结算。如深圳爱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非法经营案[9],该公司利用其聚合支付技术和平台,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接入其聚合支付接口,以空壳公司资金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将支付入口提供给网络赌博等网络黑灰产商户,代其收取用户付费。收取的资金经爱贝公司资金账户扣除服务费后,清分结算给各商户。无支付牌照的爱贝公司实际上已构成“二清”违法。
二、互联网洗钱行为典型样态的因果关系分析
从业机构在互联网洗钱犯罪活动中的资金通道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所涉资金浸泡、分根、甩干创造条件,与洗钱犯罪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在不同互联网洗钱样态下,其原因力有所差异。
(一)混同交易型洗钱中的因果关系
混同交易型洗钱样态中,黑钱分根混同于正常交易资金主要借助从业机构提供的互联网支付结算通道。黑钱之所以可通过此类平台一进一出实现混同洗白,与该类平台强调服务体验、交易便捷直接相关。互联网金融平台资金支付规则和监管漏洞很大程度决定了该模式洗钱活动的完成度,因果关系较为直接。
智能众包型资金运作略有特殊,依靠灰色平台获取海量个人和商户的第三方支付账户信息,通过“入口”混同实现资金“混同”,之后从各第三方支付账户提现、转账汇集则与平台相对剥离。资金混同在资金流入阶段已经完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通道在此互联网洗钱模式下所起的作用和贡献相对有限,就洗钱结果而言属次要、间接原因力,一般不宜直接归责。
(二)虚拟商品交易型洗钱中的因果关系
虚拟商品交易洗钱样态中,从业机构既可能是虚拟商品提供者,也可能是交易平台或资金结算提供者。从业机构提供虚拟商品,本意服务于互联网金融市场,其虚拟商品与线下流通的传统商品并无本质差异。与特定情形才能将出售菜刀行为归因于菜刀伤害结果同理,原则上不宜将从业机构无差别提供虚拟商品的行为视为该类洗钱犯罪的原因力。而虚拟商品交易的资金结算,是该类洗钱犯罪活动实现洗钱目的的关键。从业机构为虚拟商品交易外表下的上游犯罪及其收益资金漂白提供结算,与资金漂白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接口移植型洗钱中的因果关系
接口移植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浸泡、分根、甩干完全依赖于正规支付接口的资金汇转结算。在聚合支付场景下,支付服务商在监管体系之外利用其正规支付接口帮助洗钱犯罪,与黑钱漂白的犯罪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互联网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涉互联网洗钱犯罪的有责性分析
从业机构对所涉资金性质的认识状态决定了从业机构是否构成洗钱犯罪共犯,抑或仅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中立提供者。
(一)有责性以反洗钱义务为起点
一般认为,构成洗钱犯罪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要求包括明知肯定或可能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即行为人的故意,可以是不确定的间接故意。[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洗钱犯罪解释》)第1条规定,“明知”应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掩饰、隐瞒财物的具体方式,对上游犯罪了解程度等主客观因素认定。从业机构由于其行政许可性、专业性,和在涉互联网洗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均依法负有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等反洗钱义务。从业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是防范、发现和打击涉互联网洗钱活动的第一道防线。反洗钱义务履行状况,如疏于或怠于甚至故意不履行反洗钱义务,可体现从业机构对所涉资金交易情况的认知,从而反映其对资金性质的认识。因此,反洗钱义务是推定从业机构及人员对所涉资金性质认知、界定其在涉互联网洗钱共同犯罪中责任性质的起点。
(二)不同洗钱样态下的有责性分析
1.混同交易型洗钱样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规定,基于反洗钱义务,网络支付机构应当按勤勉尽责原则落实客户身份识别机制措施,监测、分析全部交易并報告可疑交易。若因从业机构未有效识别客户身份,为洗钱提供便利,根据《洗钱犯罪解释》规定,“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资金混同行为,可推定其“明知”所涉资金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洗钱犯罪共犯。
2.虚拟商品交易型洗钱样态。支付宝、快钱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应严格执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对全部交易进行监测,分析报告可疑交易。若同一商户短期内同类商品被相同或批量用户频繁购买,交易对手、收付款账号、交易频次等信息显示为虚假交易,而平台未履行监测和报告义务,则客观上与《洗钱犯罪解释》第2条规定的“通过虚构交易等方式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合法财物”的作用相同,可推定平台对交易所涉资金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明知”。
若交易平台为保有业务量赚取手续费而常态化怠于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导致虚拟商品交易频率、金额出现异常或大量用户账号被冒用于虚拟商品交易,通过该平台转移可疑资金,可推定该机构“应知”所涉资金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放任,为资金转移提供帮助,进一步考虑追究该机构或其负责人参与洗钱犯罪(片面共犯)的刑事责任。
若从业机构无法根据交易特征判断所涉资金性质和来源,但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导致洗钱犯罪证据灭失且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则涉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从业机构对反洗钱义务一贯履行情况也影响对其在个案中的责任认定。
3.接口移植型洗钱样态。支付服务商为额外手续费,挪用自身或控制的接口为洗钱提供支付通道,一般可推定其明知所涉资金系犯罪所得或其收益,涉嫌洗钱共犯。若无牌支付平台为特定资金提供非法支付结算并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亦可推定其明知,构成洗钱共犯。“手续费”是否明显高于市场,可参考合法支付结算业务或正常聚合支付通道的手续费率判断。在上游犯罪为洗钱罪的特定上游犯罪时,则构成非法经营罪与洗钱罪的想象竞合,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从一重罪处罚。
还需注意,为涉互联网洗钱犯罪提供资金结算通道的从业机构若与上游犯罪人“通谋”,一般认定为上游犯罪共犯,其洗钱行为成为自洗钱,不再单独构成洗钱犯罪。对“通谋”一般理解为事先或事前通谋。而对走私犯,刑法第156条拟制了因通谋而以走私共犯论的特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规定,与犯罪行为人事先或事中形成共同的走私故意,均属于“通谋”,即在走私过程中明知且同意为走私活动提供资金、账号等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例如行为人明知而为走私犯罪提供网络聚合支付渠道帮助收取走私物销售款,构成走私罪的共犯。[11]还应注意上游犯罪为开设赌场罪等特定罪名时,从业机构也可能构成上游犯罪共犯,“两高”、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明知是赌博网站而提供资金支付结算并收取费用1万元以上,或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如“922”跨国网络赌博专案中,话费充值渠道商协助赌博网站转换赌资并收取高额手续费,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四、结语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其潜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因此,互联网洗钱犯罪活动对金融管理秩序、司法活动正常秩序的危害和其打击难度也会被放大。精准打击从业机构涉互联网洗钱共同犯罪,可倒逼从业机构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推动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强化刑事合规管理,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同时,也需注意结合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态势,探索金融创新和金融违法犯罪的界限,审慎把握出入罪标准,为维护金融安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注释:
[1] 参见刘宏华:《全力推动反洗钱工作向纵深发》,《中国金融》2020年第11期。
[2] 参见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8日。
[3] 参见皮勇、汪恭政:《新机会理论视角下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洗钱犯罪及其防控》,《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 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8页。
[5] 参见《用手机转账竟悄悄帮人洗黑钱 抓蛋App涉案金額15亿》,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puguangtai/2020-01-02/doc-iihnzahk159398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7日。
[6]《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无证网络支付机构为客户非法开立支付账户,客户先把资金支付到该支付账户,再由无证机构根据订单信息从支付账户平台将资金结算到收款人银行账户”的“二清”模式系非法经营。
[7] 参见肖飒、马金伟:《利用比特币洗钱必须严防共管》,《证券时报》2017年7月29日。
[8] 参见广东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超100亿赌资利用话费充值“洗白”!广东特大网络赌博团伙被摧毁》,广东刑警微信公众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296540593309999&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8日。
[9] 参见邵克:《走账”生意:赌博色情等网络“黑产”资金“地下通道”调查》,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79029,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8日。
[10]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2页。
[11] 参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9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