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与秩序重建
陈明胜 张春梅
抗战结束后,处理汉奸成为至关重要而又颇为复杂的问题。言其重要,是因为它关涉战后国民政府的秩序重建,新旧秩序能否顺利交接,汉奸处理实乃关键所在。言其复杂,是因为它涉及方方面面,如何处理普遍存在于收复区的汉奸及其财产?在有关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民意、人情与法理之间如何取舍?因鼓励检举汉奸而导致的诬告之风应如何遏制?这些问题都需要国民政府审慎对待。以往学者或者通过接收与肃奸的内在逻辑探讨国民政府合法性削弱的根源,①或者对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学理性分析,②或者通过个案研究详述国民政府惩奸过程及其失策之处。③那么国民政府处理汉奸失策的根源在哪里?在制度设计与践行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漏洞?对国民政府秩序重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分析、厘清。
一、战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陷入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伪国民政府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两者同根同源的历史却难以否认。前者坚持抗战,后者屈膝投降,皆因对抗战前途认知不同,导致国民政府的大分裂。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又使两个政府难以做到泾渭分明,如周佛海既是汪伪集团的得力干将,又曾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还是CC 系的旧人。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国民政府与部分伪政府要员“合作”的客观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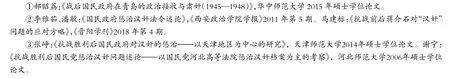
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利诱、威压两手政策对汉奸进行拉拢、策反。1937 年10 月,国民政府在《惩治汉奸条例》(五条)的基础上出台《汉奸自首条例》,通过减轻或免除汉奸罪吸引叛国投敌人员反正。随着汪精卫集团投敌,国民政府派遣军统人员与部分有意“合作”者秘密接触,许以立功赎罪以策反之。据陈公博之妻李励庄所述,1940 年戴笠曾密电陈公博,要求其“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保护电台”并“详报汪氏与敌所订密约内容及交涉经过”,陈公博答应“照办”且大部分能够“如约履行”。①周佛海在审判期间亦供述:“三十一年十月派程克祥、彭寿到重庆,向戴局长笠转呈委员长,请求自首,效命中央。”②后重庆国民政府在1943 年与他取得联系,“自三十二年二月电台叫通后,即电讯往来”。此后几次秘密接触皆为“配合反攻及保全上海计划”。③怀柔的另一端则是威压。1938 年8 月,国民政府颁布修正的《惩治汉奸条例》,通过重罚汉奸罪给予通敌卖国者以警示。如其规定,对通谋敌国且有实际行为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等。④另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暗杀以威慑伪政府人员,其中派军统特务在河内对汪精卫展开的四次暗杀行动就颇有敲山震虎之意。
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确保对沦陷区的接收权,1945 年8 月11 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缩”。⑤拉拢与监视成为战后国民政府针对伪政府部分要员的主要手段。如周佛海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行动总指挥,以“维持京沪治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则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九路军总司令。⑥伪特工主任丁默邨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伪方面军、集团军总司令任援道被任命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第五方面军司令庞炳勋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等。国民政府所执行策略效果明显。1945 年8 月,伪南京国民政府解散。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暂以政务委员会名义维持治安,静待中央接收”。⑦而其他伪员为了减轻自身罪行,亦纷纷登台,各逞其能,以至于出现某些伪组织要员“荣膺新职,或握政柄,或受兵符,升官进职”的怪现象。⑧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加强对伪政府要员的监视,即使“尽职尽责”的周佛海亦不能幸免。1945 年9 月,戴笠告诉周佛海,蒋介石“必力保全”之。而等戴笠到达上海后,却加强对周佛海的监视,“此后几每日必来谈,如不来必通一电话,盖此时中央军到沪者极少,危疑震撼,雨农如此,盖安慰与监视兼而有之也。”⑨
但是,国民政府利用日伪接收胜利果实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不满与猜忌。时人批评说:“八年以来,收复区一般人民,受尽重重压迫,敌人、汉奸以及为虎作伥的地痞流氓,勒索掠夺,无所不为。今天胜利到来,明旌在望,大家终以为可以给些喘息的机会。然而,不,一切都还依旧。过去参加伪组织的,现在摇身一变,仍不失为‘朝廷命官’。刀俎还是刀俎,鱼肉还是鱼肉。老百姓拥护胜利,到今天却落得一个‘胜而不利’的结果,这是谁都不及料的。”并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明辨忠奸、甄拔真才、严明纪律、恢复秩序。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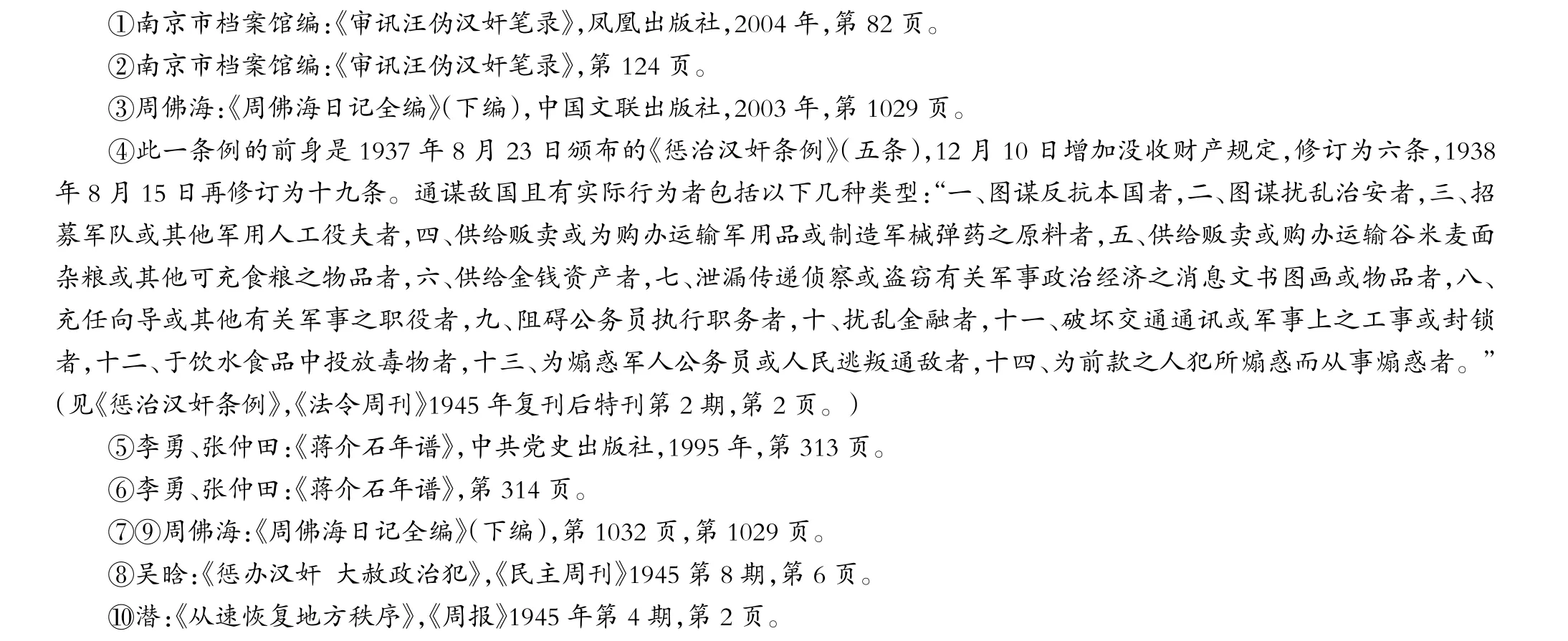
人们从不同层面指出严惩汉奸对秩序重建的重要性。重庆人民“集体要求政府严惩汉奸,就是代表了我们民意的一般,汉奸如果不加以肃清,则新中国的内层是无法健全起来的,他们是一种毒素,阻碍人类生存的毒素,必须完全铲除才是!”①当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汉奸被抓捕后,人们呼吁政府“拿出事实来止谤,来立信,来发扬正义!来激励人心!”②对于国民政府处理汉奸过程中“抓而不审,审而不判”的怪现象亦有人质疑并提出四点意见,要求从速处理汉奸案件:第一,汉奸案件的处理为人民所关注,而当前进程迟缓,足以使民气消沉。因此,在处理汉奸案件时,一切均应合乎法度,依法处断,才能振奋人心。第二,汉奸地位虽有高低,但其性质同为叛国。所以在审理汉奸案件时,头号汉奸应与次号汉奸一样,由高等法院依法公开审理。第三,处理汉奸案件应该加速。对于已捕获的汉奸,应该迅速法办,对于此后续有捕获的汉奸,也应于捕获后尽快公开审讯。第四,各地一律从严缉捕汉奸,汉奸案件条例虽有立法从宽的意思,对于其他附逆人员不予深究,但执法必严的精神却要遵守的。总之,从速严办汉奸案件,不仅关乎法纪,而且“人心的振奋与颓唐,道德及正义的维系与沦亡,其关键均在乎此”。③1945 年8 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9 月下旬,国民参政会常委会通过《请政府严惩汉奸,本忠奸不两立之训,贯彻到底,以伸张正义,而维民族气节案》和《请政府迅将惩治汉奸法规切实执行案》,并提交国民政府。陆诒直接批评国民政府对汉奸过于宽容,“忠奸不能两立!难道这般民族的败类,人群的渣滓,还应该保存他们的性命,以作下一代的榜样么?不肃清败类,依然这样藏垢纳污,还能建设得起‘新中国’吗?”④由此可见,处理汉奸问题关系民心向背,实为国民政府战后秩序重建的关键。
面对民众要求从速从严惩治汉奸的呼声,国民政府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不得不违背最初承诺,从严处理汉奸。如周佛海,虽然在合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仍被判处死刑,将功赎罪的期望最终落空。此一结果令周佛海大失所望:“高等法院对余协助抗战、维持治安之功一概抹煞,故宣判后舆情及政府要员均觉量刑过重而对余表同情。”⑤而对于陈公博的死刑判决,陈妻李励庄亦强调,陈公博“不仅秘告敌方机密,确有利于本国,且进而实行与中央合作”,因而对判决表示不服。⑥
总体来说,对于战后国民政府而言,恰当地处理汉奸并非易事,一方面是国民政府与部分伪政府要员秘密交往而形成的“合作”情结;一方面是民众要求从速从严惩治汉奸的呼声与要求。“从严则失信于人,从宽则失信于民”,国民政府的两难困境由此形成,而此一困境对国民政府审判汉奸政策的制定与践行均产生重要影响。
二、法令歧异、言行不一对国民政府公信力的冲击
民意虽然要求从速严惩汉奸,但绝非草率从事。其需要经过法律制定、类型界定、依法审判等复杂的程序。虽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已经颁布若干汉奸处置条例,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仍需制颁新的法令条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和《惩治汉奸条例》。两个文件相继颁布于1945 年11月23 日、12 月6 日。仅隔十数日而颁布两个重要条例,可见国民政府顺应民意、惩治汉奸的急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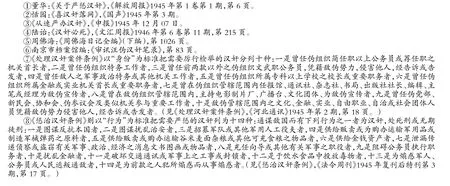
不可否认,两个条例存在互补之处:前者是根据身份进行检举,⑦后者是根据行为进行惩罚。⑧但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之处。首先,《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三条规定:“前条汉奸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证据确凿者,得减轻其刑。依前项规定,减处有期徒刑者,仍应褫夺公权。”①而在《惩治汉奸条例》中却没有给予明确说法。到底如何量刑?颇让人费解。譬如在周佛海的审判过程中,有不少机构与国民党要人如第一保安纵队司令部、第三保安纵队司令部、马元放、吴文化、周镐、李明扬、吴开先、戴济民、顾祝同、陈宝骅等均为周佛海出具有功于抗战的证明。②周佛海的辩护律师章士钊亦在辩护书中明确指出周案与其他汉奸案有本质区别:“盖他案止于论罪,而本案功罪相掩,惟二者之轻重大小,掩迹何以,至烦司谳明察耳。”③但最高法院特种刑事认为虽然周佛海有“微功”,但审判官有“自由裁量之权”,根据周佛海所作所为,“虽事后稍树微功,仍不足以蔽其过,乃处以极刑,于法并无不合”。④如此说法,显然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六条规定“汉奸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后自首者,不适用自首减免其刑之规定”。而对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前自首汉奸应该如何处理,《惩治汉奸条例》亦无明文规定。根据周佛海的供述,他是在1942 年10 月首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自首的。但首都高等法院的解释是:周佛海不适合《汉奸自首条例》(1937 年10 月颁布)第一条之规定“汉奸于发觉前自首,且合于所列各情形之一者,始得免除其刑或免其刑之执行”。因为周在1939 年11 月4 日“已经最高法院检察署明令通缉有案,与发觉前自首之条件不合,自无适用该条免刑之余地”。在《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与《汉奸自首条例》产生矛盾时,选择1937 年旧条款而弃用最新条例,颇有因人设法的嫌疑。
再次,关于汉奸财产的处理问题。《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四条规定:“汉奸所得之财物,除属于公有者应予追缴外,依其情形分别予以没收或发还被害人。前项财物之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或不能没收时,追缴其价额,或以其财产抵偿。但其财产价额不足应追缴之价额时,应酌留其家属必需之生活费。”⑤而《惩治汉奸条例》规定:“犯第二条第一项(即图谋反抗本国者)之罪者,没收其财产之全部。前项罪犯未获案前,经国民政府通缉,而罪证确实者,得单独宣告没收其财产之全部。第一项未获案之罪犯,虽未经国民政府通缉,而罪证确实者,得由有权侦讯之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准,先查封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如系军人,报由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核准之。前项财产查封后,应即报请国民政府通缉。”“依前条没收或查封财产之全部时,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⑥一个问题,两种法律解释:《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中规定汉奸财产是指犯汉奸罪所得之财物,并不包括其他原有之财物;而《惩治汉奸条例》第八条则规定汉奸财产为汉奸的所有财产。⑦于是有论者建议,是否可以根据所犯汉奸罪的轻重分别进行处罚:严重者没收全部财产,稍轻者没收一部分财产。⑧对汉奸财产定义的变化,实则表明国民政府惩奸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宽松到严厉的过程。
综上所述,《惩治汉奸条例》比《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更加严厉。根据两个条例颁布的时间、内容以及国民政府陷入的两难困境可以推测:《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的颁布,不排除国民政府借机给予部分“合作者”减轻罪行的想法;⑨而《惩治汉奸条例》的进一步严厉,则与民众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日高相关。国民政府的两难困境不但反映在法律条文制定的过程中,还反映在惩治汉奸的过程中。
首先,个人干预司法。接续前文,虽然有诸多国民党要人的证明,周佛海仍不免被判处死刑的命运。而事情的转机是在蒋介石直接干预之后。1947 年1月25 日,陈果夫、陈立夫联合呈请蒋介石为周佛海“减等处罪”,“惟周于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依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长,丁默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杭一带暗中布署军事颇为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拟请于日内面饬司法行政部长设法准予缓刑或减等处罪”。为此蒋介石给司法行政部的指令如下:“关于汉奸犯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似可免予一死,可否改判,即希司法院核办可也。”最终结果是“由国府于三月二十七日明令减刑,改为无期徒刑,并已送监执在案”。①以蒋介石一人之力便予以改判,此种经历颇具戏剧性,必然导致人们对国民政府的司法独立与公正产生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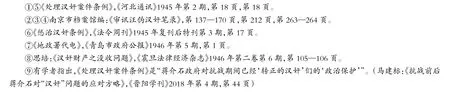
其次,法律条文朝令夕改。就汉奸财产的处理来看,最初是关于汉奸财产属性的争论,后来又因为汉奸家属酌留生活费标准而产生争议。为解决此一问题,行政院增订《执行没收汉奸财产应注意事项》,其中明确规定:“汉奸家属生活必需费,应根据客观需要,参照左列标准,于不超过所在地一般平民生活水准范围内酌定。并一次发给之:(甲)汉奸家属之范围,以汉奸依法负抚养义务之亲属及配偶为限。(乙)汉奸家属生活必需费,以发给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原则。其有谋生能力而在执行时,尚未就业者,酌给三个月之生活必需费。(丙)汉奸家属未成年者,其生活必需费给至届满成年时止。其已成年而无谋生能力者,推定其整个生存期间为七十岁,给以未来期间内之生活必需费。若执行时年龄已达或超过七十岁,或离七十岁不足五年者,其生活必需费均以五年计。”②对于此一规定,苏浙皖区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提出异议:“查酌留汉奸家属必需生活费,虽不必持之太苛,亦不宜过份宽大。……但如推定整个生存期为七十岁,似嫌过长。且汉奸判处徒刑期间,长短不等。若对其家属之生存期间,一律推定为七十岁,恐与实际情形不符。又汉奸家属,往往虽未成年,而实际已有生活能力者,颇不乏人。对于此类家属,似无再为酌留生活费之必要。”司法行政部的训令则坚持按照原来规定办理。③1947 年12 月,该标准再次发生变化:“甲,汉奸家属之范围以汉奸依法负抚养义务之亲属及配偶为限;乙、汉奸家属生活必须费以发给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至于酌留多少,“应就汉奸全部财产变卖价额内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酌给之,其财产数额特多或特少者不在此限”。④法律随时势变化而不断完善是法的内在要求,但朝令夕改的结果却会削弱其权威性。
再次,汉奸假释过程中的反复。1947 年,“韶”以“人才缺乏”为理由,呼吁为“被判徒刑而有特技之汉奸办理假释,保外服役”。⑤据《申报》披露,上海市“高等法院,以当兹人才缺乏之际,被判决徒刑之汉奸,具有专长才能者,似不可埋没,应给予工作机会,俾得展其所长,藉图戴罪立功,特依据‘假释’及‘保外服役’办法,于日前单行颁发表册,令被判刑之汉奸,自行填具特长,如精通外国文字,擅著作,翻译等特才,皆可填具,该院将依具填表,分别考查,转呈司法行政部核夺”。⑥后又有论者评论道:“传中国司法部将批准上海高等法院之计划,该计划包括与日本人合作之汉奸,如有专长者,将被释放,并由政府录用。据报载,法院已分发表格于犯通敌罪的犯人,填写彼等之能力,如外国语文写作及其他专长等,表格上说明给以戴罪立功之机会,高等法院对此事曾作奇妙解释,谓此项计划为对中国人才缺乏的有效补救办法。”⑦在多次讨论之后,重新启用一事无果而终,但大批汉奸提前保释却是事实。⑧另外,国民政府除了在前期处理部分大汉奸外,后来干脆念起了拖字诀。《天津益世报》对于这种行为揭露说:“胜利已经三年,许多巨奸已经被捕,但是多数尚未定谳,有的虽已定谳,尚未执行。”⑨
毋庸讳言,个人干预司法、法律条文朝令夕改都将严重削弱国民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战后秩序重建;而重新启用汉奸的企图与战后初期争夺胜利果实时重用汉奸不同,如果说彼时国民政府还有难言之隐,那么此刻重新启用汉奸则是对民众底线的挑战,这种看似有利于社会秩序重建的做法,实则与民意背道而驰。
三、劫收、诬告对国民政府秩序重建的挑战
惩办汉奸本是为了申正义、正纲纪,但汉奸财产接收过程中的不法行为与汉奸检举过程中的诬告行为对国民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形成新的挑战。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规定军政大员前往沦陷区,接管敌伪政权全部公、私产,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进行查封,清点财产数额,查明财产归属、来源等。但因为责任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实际上各地均产生了“劫收”的恶果。高检处首席检查官杜保琪指出:“条例上虽规定财产移交检察官,但是我们没有接收一件,不知道这些汉奸财产落在什么人手里。”①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述:“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匀,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②在济南,“较好的公寓住宅、车辆、什物,早就被党政军接收大员及其他实权人物所瓜分据为私有,或被机关所占有”。③在厦门,“所有厦门市日伪各军用物资仓库及其它的仓库,均被各单位抢劫一空,变为私有”。④如此事例,遍布大江南北,不可胜数。至于接收人员舞弊手法更是层出不穷,如威吓讹诈,先占后交,对移交底册偷天换日,对接收物改新为旧、改旧为废,串通业主私分资产,以接收之名行贿赂之实等。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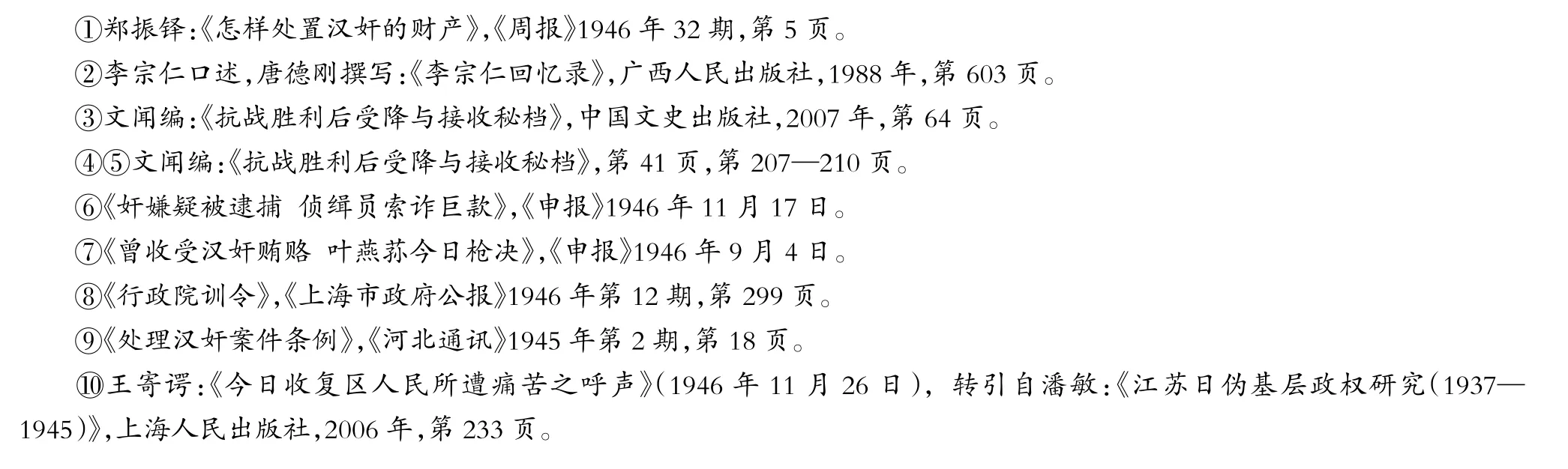
除了接收大员的劫收,还有某些基层行政人员趁机勒索的行为。如上海闸北蒙古路开理发店的盐城人陈均庆,因有汉奸嫌疑被人检举,后由上海县政府警察局派闵行警察所侦缉员赵步高、徐立和会同闸北分局将陈逮捕。赵、徐二人借机向陈均庆的弟弟索贿一千万元作为酬劳,以保证陈均庆无罪开释。后经双方谈判,以五百万元成交。陈弟一面准备钱款,一面据情报告闸北分局,最终赵、徐二人反被拘捕。⑥又如抗战胜利后,叶燕荪到上海出任主持检举汉奸之某军事机关秘书,其利用职权先后向上海市景纶文记钱庄经理余延辅勒索黄金一百四十两、国币八百八十万元,又收受汉奸表鸿福贿赂国币二百万元。后被主管当局发觉,将其撤职扣押,并解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死刑。⑦江苏省监察区监察过程中对该监察区惩处汉奸的情形如此评述:“一若漫无标的,张弛不一,甚至借名恫吓,巧取豪夺,民情怨愤。”⑧就实际情形看,针对部分基层行政人员的趁机勒索行为,国民政府还能够依据相关法令加以惩处;而对于军政大员的劫收行为,则往往鞭长莫及,望洋兴叹。
为肃清汉奸,国民政府赋予人民检举汉奸的权力。《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明文规定“对于左列汉奸,应厉行检举”。⑨当赋予人们检举汉奸的权力时,也就难免宵小挟私报复、借机自肥的行为。“‘是以现在汉奸案件之检举法,不啻授贪官污吏及奸诈子民以最新式之敲诈武器,故不论对任何人欲加以敲诈,只须凭空加一汉奸之名,且可很快达其目的。’”⑩事实证明,在战后汉奸处理的过程中,检举与诬告往往相伴而行。
首先,工商从业人员成为不法分子诬告、敲诈勒索的主要对象。如上海市益丰棉织厂职员张关生、周一峰于闲谈中获悉潘友标、赵月笙有被人检举汉奸情事,于是起意诈财。1946 年3 月间,双方三次约会,张、周向潘、赵索要五百万元运动费。后赵月笙报告警局,由便衣警察将周、张二人拘捕。①又如1946 年6 月17 日,有穿军装男子与一便衣到上海市越东香烟厂营业主任朱永年寓所,自称是蓬莱路宪兵团人员,指朱有汉奸罪嫌疑,意图恐吓诈财。朱永年将此事密报泰山分局,后将苏星三、曾湘楚、王吉安、崔春汤四人拘获。②再如冯震与天一染织厂厂主唐松荣相识,且知唐松荣富有,后冯串通朋友周揖卿、曹铭传、黄云鹏、冯一新等人,向江苏省高检处控唐汉奸罪。后唐至常熟路警局报案称遭到吓诈。经该局侦查,结果将冯震、曹铭传、冯一新、周揖卿拘获。③如此案例,不胜枚举。
其次,县区长及乡镇自治行政人员亦屡被诬告。如战后江宁县的两任县长蔡为端、黄相忱皆因任用“奸逆”“敌伪”被检举,而调查结果皆因无实据而告终。④江宁县各区区长中亦有数人被检举与“日伪”有关,如梁道恕、张实夫、吴凌云等,在调查取证之后,结果证明:梁道恕确曾任伪职,被撤职查办;所控吴凌云各节皆不实,出任伪职显系诬告;张实夫与非法处理汉奸案有关,是否确实,没有结果。⑤在基层社会,对现任或前任自治行政人员的检举则更加频繁。如汤山镇前伪保长徐华林因“凭藉敌伪势力毁拆公物,串买日人物质”而被江宁县民周义烔检举,调查结果是汤山镇并无周义烔其人,所呈各事实均不属实。伪同扬乡乡长夏明金被江宁县民王长雨以“变卖枪支、舞弊军米、侵吞公帑”举报,调查结果为所呈各件或无实据、或无事实。伪乡长张道艺、副乡长张道立被“黎民”以“在敌伪势力时期无恶不作、搜刮民膏、以致巨富”等检举,调查结果为所控各节查无实据等。⑥
诬告原因,或因诈财,或因私仇。对于急欲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国民政府而言,检举汉奸政策成为双刃剑。为了限制诬告,国民政府的措施大致有三:
一是依法惩办。《惩治汉奸条例》明文规定:“故意陷害诬告他人,犯本条例之罪者,依刑法规定从重处断。”⑦如苏州人杨济良在战后以控告汉奸为常业,但大部分为诬控,趁机敲诈是实。后经侦讯,认为杨济良诬告罪证确实,实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七条及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项之罪,因提起公诉。⑧
二是限制匿名举报行为。1945 年初,上海市对于市民告发汉奸的行为有若干规定:“由告发人开具真实姓名住址并取具铺保;但事实确凿而有证据者,得列举事实检同证据告发免予具保。”对于告发人姓名严格保密,而对于挟嫌诬告者则依法究诬。⑨至1946 年5 月,上海市高等法院检察处因受理汉奸案件繁多,人民检举控诉中匿名挟嫌诬吿者不在少数。因而再发布一文告:“查奸逆祸国殃民,原许人民厉行举发,以振纪纲。然举发亦应依照刑诉法之规定,用书状或言词为之,方合程序。乃近查本处收有匿名告发函件,日必数起,激于公义举发奸伪者固有其人,而虚构事实、挟嫌诬告者亦属不少。迨经本处依法侦查,甚有不但查无其事,亦且查无其人,一纸空函,颠倒是非,影响人权,殊非浅鲜,若不加以限制,实不足以杜滥诉之风。嗣后凡举发奸逆,及其他一切奸案,应具真实姓名,详细住址,本处于可能范围内,当代为守秘密。如无名或捏名者,槪不受理,特此布告。”⑩
另外,为了限制检举,国民政府1947 年12 月训令:“人民或团体对于抗战期间汉奸案件之告发以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为限,逾期之告发检察官不予置议。但国家之追诉权及被害令告诉权不因此而受影响。”①而之所以定此一期限,主要是为了避免“人心动荡不安”。②

事实证明,劫收与诬告对国民政府的秩序重建产生负面影响:任由劫收泛滥,沦陷区秩序重建将无从谈起;而任由诬告盛行,则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虽然国民政府颁布条令、成立机构,但劫收行为却难以做到令行禁止,以至于严重影响国民政府的形象。依法惩办诬告与限制匿名举报有利于减少不法行为,但将检举期限限定在1946 年12 月31 日,显然有因噎废食之嫌。总之,处理汉奸失策所产生的链式反应,在不同程度上消解着国民政府秩序重建的努力。
结 语
秩序重建是战后国民政府的既定国策,在唐纵给蒋介石的建议中提到对于重要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北平、天津等,应迅速确定发表市长人选,“并令各沦陷区省主席、市长从速前往抚辑流亡,恢复秩序”;对于乡村社会,则应该全体动员,中央委员与各级党部应“深入农村协助指导地方秩序之恢复。”③另外,国民政府惩治汉奸从战时行政军事机关特别制裁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审判刑罚的过渡,④也表明其努力秩序重建的意图。一般意义上讲,秩序重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二是收复人心。而战后收复区的制度设计绝非简单复制战时国统区的制度体系,经过日伪若干年的蹂躏,收复区显然存在诸多特殊之处,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日伪政权的存在及其影响。欲使新旧秩序顺利实现交替,首先要对旧制度及其影响进行清理,汉奸处理是制度设计的第一步。“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此一立论出发,国民政府欲重塑民族精神、收复人心,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舆情民意,恰当地处理好汉奸问题。
综观国民政府处理汉奸的过程,其确实虑及此一问题。但实际情况却因国民政府与伪政府要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变得相当复杂。在战后初期沦陷区接收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汉奸处理政策以利用为主。就战后国共两党所处实际情形看,利用日伪维持秩序以确保国民政府的接收权,虽然“无可奈何”,而实际上却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败笔。民众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与大小汉奸粉墨登场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与质疑。因此,在汉奸处理之初,国民政府就罔顾民意、人心尽失。随着对收复区控制的基本完成,汉奸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国民政府的汉奸政策开始转变到以惩治为主。但因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国民政府在处理汉奸的过程中陷入从严还是从宽的“两难”。这一点反映到制度设计上,则是顾此失彼、前后矛盾。在审判汉奸的过程中,则是犹疑不定,忽而从严、忽而从宽,让人无所适从。当利用与严惩的选择取决于当局的功利性目标而非民意时,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必然会遭遇严重挑战。与此同时,接收过程中的劫收行为、检举汉奸过程中的诬告行为更是推波助澜,使国民政府秩序重建的努力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