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 年德国汉堡瘟疫大流行探析
顾 年 茂
对于德国自由市汉堡来说,1892 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汉堡成为欧洲瘟疫流行的中心,短短四周多时间就有8594 人染疾身亡。①此后,直至2020 年新冠病毒侵入,汉堡再没有发生重大疫情。关于1892 年汉堡瘟疫大流行的具体情况,前人已有不少调查和研究。例如,德意志帝国卫生局的细菌学家格奥尔格·加夫基(Georg Gaffky)就曾在1892 至1895 年间广泛征引医学资料,对汉堡及其周边地区的疫情进行过详细统计和描绘,从官方角度对疫源、死亡人口等做了说明。②德国汉堡医学专家和政治家约翰内斯·赖因克(Johannes Julius Reincke)更写了一系列著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1892 年瘟疫流行与城市公共卫生的关系,并将重点集中在社会赈济、应急管理、公共环境和医疗卫生制度方面。③德国历史学家戈登·乌尔曼(Gordon Uhlmann)则依据影像图文资料,从社会日常生活史角度对汉堡瘟疫进行了学术性考察。①从政治、经济、社会史角度系统考察1830—1910 年间汉堡医疗卫生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之间联系的则有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等人。②这些研究基本廓清了1892 年汉堡瘟疫大流行的背景、过程和结果,但也有一些疏漏,甚至是故意隐瞒和曲意辩解。本文拟从信息沟通角度出发,在描述瘟疫发生过程的基础上,对汉堡市政当局隐瞒疫情的事实加以批判审视,进而阐述公共舆论的批评监督作用,以及在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德意志帝国“独特”体制内,③卫生防疫制度改革问题。

一、城市环境与瘟疫流行
19 世纪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英国执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之牛耳,截至1850 年,世界贸易中制成品总量的40%产自英国。④从19 世纪中叶以后,法德等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城市人口在欧洲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城市生活方式取代了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城市成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城市飞速发展的后果很快开始显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传统疾病减少,新的疾病出现,而且因为工业污染,毒性更强。“城市环境……通常比乡村更不健康。在乡村传染病更可能是地方病,在城市疫病则更为频繁和易于潜伏,恶劣的卫生条件意味着食物、牛奶和水的供应容易受到污染;而城市人满为患既提供了心理压力的来源,也有助于疾病的传播。”⑤此外,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和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原本地方性疾病经由全球流动人口迅速向外传播,其中源自印度北部的霍乱成为世界许多地方的健康新威胁。霍乱传到欧洲后,通过公路、河流和铁路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在新工业化社会人口拥挤、环境肮脏的城镇和海港的人群中传播,或通过污染的水源和食品,或通过直接的人体接触传播。⑥
霍乱感染者的皮肤呈蓝色,发病突然,患者上吐下泻,体内液体大量流失,从最初表现出症状到死亡常常不超过24 小时。霍乱死亡率极高,感染的人死亡率平均50%。⑦1892 年之前,汉堡已经遭受五次霍乱侵袭,分别是1831—1832 年、1848—1850 年、1853—1860 年、1866—1867 年、1873 年。因感染霍乱的死亡人数,1831 年498 人,1832 年1652 人,1848—1850 年分别是1772、593、440 人,1853—1857 年分别是301、311、204、78、491 人,1859 年1285 人,1866—1867 年分别是1158、74 人,1873 年1005 人。⑧历次霍乱威胁中,汉堡受到外部霍乱侵袭之余,城市内部的公共卫生、居住环境、城市治理等也是突出的问题。

易北河支流阿尔斯特河下游城市汉堡,地处中欧,地理位置优越,途经基尔运河即可方便快捷地到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经由发达的水陆运输通道直抵中欧和东欧广袤的腹地。历史上,1189 年5 月7日,汉堡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获得特许权,可以在易北河下游至北海之间自主征税,这被视为汉堡港的正式诞辰日。作为“汉萨同盟”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汉堡享受了三个世纪的“自由贸易”特权,成为同盟最重要的北海港口。1510 年汉堡成为“帝国自由市”,欧洲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开通亚洲航道之后,汉堡又跃升为欧洲最重要的输入港之一。①18世纪之前,汉堡的商人和制造商住在汉堡靠近港口的老城区,通常是自己办公室楼上一层,紧挨着仓库。城市日益扩大之后,他们迁出了市中心,搬到旧城区阿尔斯特湖一带,或是易北河的下游地区,住在宽敞的别墅里。临水的半木质的房子被分割成合租房,供工人阶级居住。这一带也很快成了著名的“陋巷区”,卫生条件恶劣,人满为患,房子年久失修,肮脏不堪。②1842 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汉堡大片市区,重建计划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英国工程师威廉·林德利(William Lindley)说服汉堡参议院新建一批水库,用蒸汽浆把位于城市北边易北河的河水通过输水管道送到千家万户。1890 年,汉堡城市输水管道超过400 千米,汉堡市的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个水龙头,要么装在室内,要么装在院子里。③
1885 年汉堡市议员海因里希·吉森(Heinrich Gieschen)声称:“汉堡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一定是世界城市中最干净的。”④但事实上,汉堡市民的饮用水未经过滤,浑浊不堪,有时水龙头放出的水里还混杂着小鱼。1885 年,一位动物学家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题为《汉堡城市供水系统里的动物群》。他从一段供水管道里辨识出了几十种蚯蚓、软体动物和其他动物。⑤19 世纪汉堡城市街道通常是肮脏不堪,直到1892 年汉堡市内和城郊还有大约1.2 万匹马,许多廉租房街区充斥着马粪的恶臭,街上到处是倾倒的腐烂垃圾。理论上,依据1875 年《下水道法》规定,所有市民生活污水必须与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相接。但是实际上,市民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常常未经处理便倾倒入河,使得气候温暖、地势低洼的汉堡,空气中散发着恶臭,水里滋生的蚊子四处传播病菌。1892 年罗伯特·科赫视察瘟疫最重的港口一带的贫民窟时,想起了他在埃及和印度看到的贫民窟,转身对同行人员说:“先生们,我忘了我现在是在欧洲。”⑥在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之时,汉堡的城市污染和居住环境问题十分严峻。
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经验的积累和细菌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清了霍乱传播途径并找到了防治办法。第一,1848 年英国内科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发表了《论霍乱的传播方式》,认为霍乱通过饮用水传播,其后发展为霍乱传播理论。⑦1866年英国爆发第四次霍乱时,英国政府采纳斯诺的理论,其后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5)和《河流污染防治法》(1876),综合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和水污染问题。第二,19 世纪70 至80 年代,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医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在细菌理论上取得重大发现。1884 年罗伯特·科赫在印度发现霍乱弧菌,找到了霍乱交叉感染的途径和有效控制霍乱蔓延的办法。1884 年7月,德意志帝国卫生局召开了首次霍乱会议,科赫在会议上制定了防止霍乱的方针,该方针后来证明是极好的。⑧19 世纪中期以后,信件、报纸、医学期刊等非常快速地将医学研究信息传播开来,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促进了各国医学知识的沟通,医学科学与国际主义共同发展。⑨各国医学科学家之间逐渐形成医学知识和人脉关系的国际网络。此外,作为“欧洲大陆最英国化的城市”,⑩汉堡一直与英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频繁的人员往来。因此,英国防治霍乱的立法措施和德法最新的细菌学研究成果应当早已为汉堡所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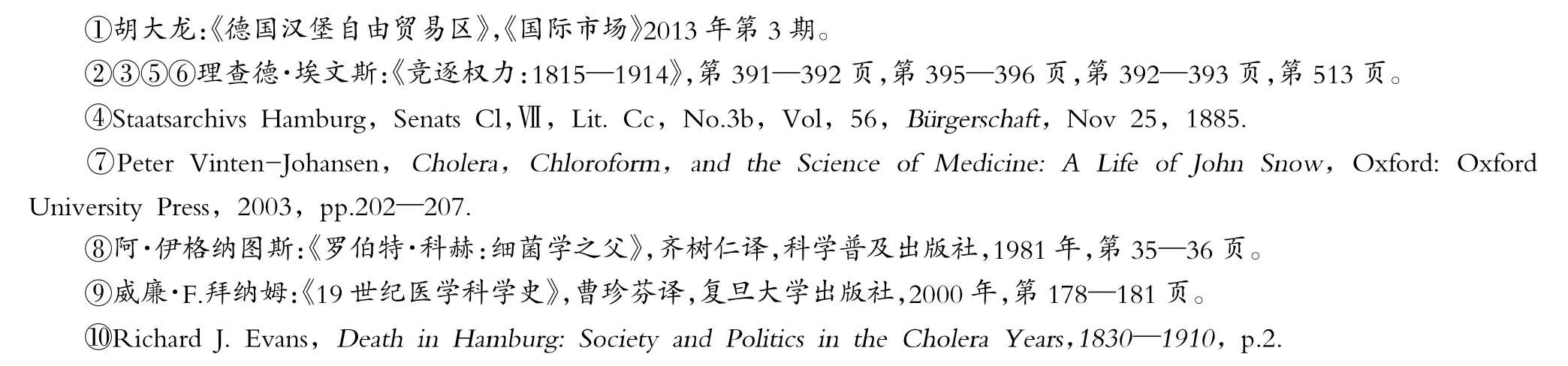
总之,19 世纪末的汉堡城市环境卫生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卫生状况尚可,本来可以阻止瘟疫流行;这一时期取得的医学进步更为阻止瘟疫创造了条件。1892 年汉堡霍乱大流行,更多的是人祸。
二、从隐瞒到灾难
1892 年,霍乱开始了新一轮爆发,1892 年7 月传染到莫斯科,8 月中旬传染到基辅。德意志帝国卫生局和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建议东普鲁士地方当局封闭边境防控疫情,取得积极的效果。①虽然东普鲁士地方当局防控得当,但仍有未经常规医学检疫的移民乘坐铁路来到德国汉堡。②1892 年1 月至8 月,东欧的移民经汉堡、不来梅离开欧洲人数多达102059 人。③1892 年8 月3 日,汉堡参议员约翰·费舍曼(Johannes Versmann)私下表达出对霍乱临近的担忧。④
1892 年8 月14 至15 日夜间,在汉堡米特区从事建筑工作的萨赫林(Sahling)下班路上突然发病,有剧烈呕吐和腹泻症状,邻近阿尔托纳(Altona)的一名医生雨果·西蒙(Hugo Simon)博士诊断后,立即认为萨赫林得了霍乱。但是西蒙与他的上级医务官瓦里希斯博士(Dr. Wallichs )产生分歧。曾因西蒙反普鲁士立场,瓦里希斯将其排斥出汉堡医生俱乐部。此次,瓦里希斯以没有细菌证据为由,拒绝接受西蒙的诊断。⑤但相同症状的病例接踵而来。8 月16至17 日夜间,同样出现剧烈呕吐和腹泻症状的建筑工人科勒(Köhler)住进汉堡的埃彭多夫(Eppendorf)综合医院,并于次日夜间因病去世。8 月17 日则有4 例以上、18 日12 例以上、19 日31 例以上,感染人数开始迅速增加。⑥15 日、16 日汉堡医务官员极力避免承认发生霍乱疫情,当上报到汉堡首席医务官约翰·卡斯帕·克劳斯(Johann Caspar Kraus)时,他认为孤立的病例不能诊断为霍乱疫情。⑦
1892 年8 月19 日,汉堡的卫星城市阿尔托纳又发现一名瑞典的水手和一名汉堡的雪茄工人出现霍乱的发病症状,军医魏瑟尔博士(Dr.Weisser)很快怀疑两人染上了霍乱,随后马上报告给阿尔托纳的地方医务官。地方医务官发现了更多的类似霍乱的病例之后,8 月20 日把爆发霍乱疫情消息告知行政当局,8 月21 日再上报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总督。总督立即报告给柏林的帝国首相和帝国卫生局。与阿尔托纳截然不同,8 月22 日汉堡的首席医务官约翰·卡斯帕·克劳斯和汉堡市议会医疗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格哈德·哈赫曼(Gerhard Hachmann)仍旧拒绝公开承认汉堡爆发了霍乱,同日格哈德·哈赫曼明确向美国驻汉堡副总领事查尔斯·布克(Charles Burke)保证汉堡没有发生霍乱。⑧
柏林的帝国卫生局局长卡尔·科勒(Karl Köhler)博士收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总督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阿尔托纳把培养的病菌送到帝国卫生局罗伯特·科赫的实验室检验,并且动员帝国卫生局做好霍乱流行的应对工作。8 月22 日,阿尔托纳的魏瑟尔博士把培养的霍乱病菌送到柏林,随后科赫在帝国卫生局实验室中将魏瑟尔培养的病菌确认为霍乱弧菌,并向帝国卫生局局长报告霍乱已经在汉堡地区爆发。8 月23 日帝国卫生局命令科赫立即动身前往汉堡调查出现的霍乱病例。柏林帝国卫生局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汉堡主动报告之前。

8 月23 日,约翰·卡斯帕·克劳斯和格哈德·哈赫曼被迫向柏林报告汉堡发生霍乱。8 月24 日,即霍乱疫情发生8 天之后,汉堡参议院才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霍乱疫情,并向公众发出警告。⑨8 月25 日,罗伯特·科赫在给女友黑德维希·弗赖贝格(Hedwig Freiberg)的信中说道:“当我来到汉堡时,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些病人,因此,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患有霍乱。现在我发现实际情况非常严重。几天之内,疾病就大大扩散,已经有一百人死了。昨天,我从一所医院到另一所医院,一直视察港口和船上的移民。我感觉好像正走在战场上。到处都有人病倒,几个小时前仍然健康、充满欢乐的人们,现在正一排排地躺着,好像被看不见的子弹击倒,其中有些人出现霍乱受害者特有的僵硬的目光,其他人眼睛破损,有的人已经死了。没有人听到哀叹声,到处是死亡的声音。”①
从8 月15 日出现第1 例霍乱“疑似”病例,到8月24 日参议院商讨应对措施,汉堡市政当局和首席医务官一直未告知汉堡市民采取预防措施,诸如煮沸饮用水等。8 月下旬的热浪使得霍乱弧菌极速地增殖,酷热的天气和易北河的臭水为病菌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环境。细菌从移民居住的廉价房子和设备简陋的肮脏营地进入河水,被潮水冲到了上游流域,8 月19、20 日污染的河水已经蔓延至汉堡自来水厂的进水口。②而汉堡自来水厂水质处理未达标,1890年开始修建的沙滤器未能有效控制微生物污染,使得受污染的水通过水泵进入千家万户。到8 月23日,霍乱疫情已经蔓延至汉堡全城。1892 年8 月26日至9 月2 日,霍乱病例每日新增人数在1000 人上下浮动,直到9 月2 日才迎来霍乱疫情拐点。从8月12 日到9 月19 日,共有16944 例霍乱病例,死亡8594 人,③汉堡霍乱疫情已经发展为灾难。④
1892 年,西欧和中欧地区许多城市都受到了霍乱侵袭,临近汉堡的不来梅(Bremer)也是如此。同为帝国自由城市的不来梅和汉堡一样具有很多的流动人口,同样承受全球流动的传染病风险,比较1892年不来梅的防治霍乱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汉堡霍乱大爆发的独特现象。
与汉堡相比,1892 年霍乱基本没有给不来梅带来冲击。作为贸易港口城市,不来梅城市面积约是汉堡的三分之一,1890 年约有18 万人口。1881—1885年间通过不来梅移居海外的总共有12.7 万人,19 世纪90 年代每年有近2.5 万人从不来梅离开欧洲大陆,1892 年霍乱大爆发期间依旧有如此规模移民人口。⑤市政管理主要也是由律师和商人组成的18 人参议院管理,但是1892 年不来梅因感染霍乱而去世的只有6 人,其中2 例为不来梅本地病例,其余均为输入病例。⑥
面对东普鲁士和俄国的霍乱疫情,1892 年7 月15 日不来梅参议院计划建立霍乱专门医院,7 月21日参议院宣布组建特别行政机构负责即时报告任何霍乱疑似病例。⑦7 月27 日,不来梅开始加大力度控制来自东普鲁士与东欧边界疫区的移民,进入8月后,不来梅加大警示力度。8 月11 日不来梅参议院开始通过当地的新闻报刊向市民宣传霍乱预防知识,比如不吃水果、煮沸牛奶和水、勤洗手等。⑧8 月23 日汉堡霍乱大爆发后,不来梅参议院在霍乱感染病例不多的情况下,关闭市场和舞会,⑨从24 日开始对来自汉堡的火车一律检疫消毒,紧接着严格执行来自柏林帝国卫生局的各项防疫措施。8 月27 日不来梅参议员参加帝国卫生局在柏林召开的帝国防疫会议,9 月3 日帝国卫生局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视察不来梅的卫生防疫工作时,对不来梅的防疫措施深感满意。⑩

综合观察,我们可以看出,克劳斯和哈赫曼的隐瞒霍乱爆发的行为与汉堡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根据1860 年的宪法,汉堡的城市权力机构由参议院和市民议会组成;参议院由18 名参议员组成,市民议会由192 名议员代表组成。任何法律都需要两者通过才能执行。①参议员主要由法律专家、商人组成,终身任职。市民议会由市民普选产生,192 名市民议会议员中,84 名由在汉堡居住5 年以上的纳税市民普选产生,60 名由市政官员、法官产生,48 名由财产所有者产生,市民议会议员任期为6 年。由于选举资格的资本限制,获得市民权利需要纳税30 马克,绝大多数劳工阶层负担不起。②1892 年城市总人口大约622530 人,③但是只有23000 名市民有选举权。④其中,参议院在市政管理中处于主要地位,而参议员则与汉堡的富豪集团有密切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汉堡的政府和城市治理由富豪政治集团所主导。
克劳斯和哈赫曼对1892 年霍乱疫情心存侥幸,希望它像之前的霍乱一样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他们害怕采取罗伯特·科赫的积极防治霍乱措施,影响汉堡的经贸活动和航运业发展,损害富豪政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隐瞒疫情未能及时将霍乱疫情信息告知市民和上报柏林帝国卫生局,霍乱流行的早期未能引起公众的警觉和防护意识,错失防止霍乱大流行的机会。
三、公共舆论与公共卫生改革
1892 年汉堡霍乱大流行发生后,市政当局明显的隐瞒疫情和防疫不力,引起人们强烈不满。1892年8 月24 日,汉堡参议院开会商讨疫情的应对策略之时,参议员中不少人仍幻想霍乱不是非常严重,无需使用设立检疫区、隔离等措施。议员们主要担心隔离检疫措施会对汉堡港口贸易造成巨大损失。随着霍乱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批评汉堡市政当局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主要来自三个层次。
首先,柏林的帝国中央政府对汉堡市政当局卫生防疫工作严重不满。1892 年8 月29 日,德意志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在写给汉堡市长约翰·格奥尔格·蒙克伯格(Johann Georg Mönckeberg)的亲笔信中,以愤怒的语气批评汉堡议会延迟宣布疫情。⑤帝国卫生局则越过汉堡参议院提前开始在汉堡地区采取防疫措施,并派遣帝国卫生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前往汉堡监督各项防疫措施。帝国卫生局和罗伯特·科赫不相信汉堡市政当局提供的疫情信息,在视察汉堡埃彭多夫新综合医院时对同行人员说,埃彭多夫新综合医院院长是说出霍乱实情的人。⑥某种程度上,罗伯特·科赫逼迫汉堡参议院采取了许多防疫措施,比如:8 月26 日关闭汉堡所有学校、禁止公共舞会、禁止公共集会等。9 月7 日,汉堡首席医务官约翰·卡斯帕·克劳斯被迫以健康为由向汉堡市议会申请离职,但其离职并没有平息人们的不满。社会民主党呼吁更多人承担霍乱大流行的责任、必须解除更多人的公职,⑦批评汉堡被“特殊利益集团”所统治。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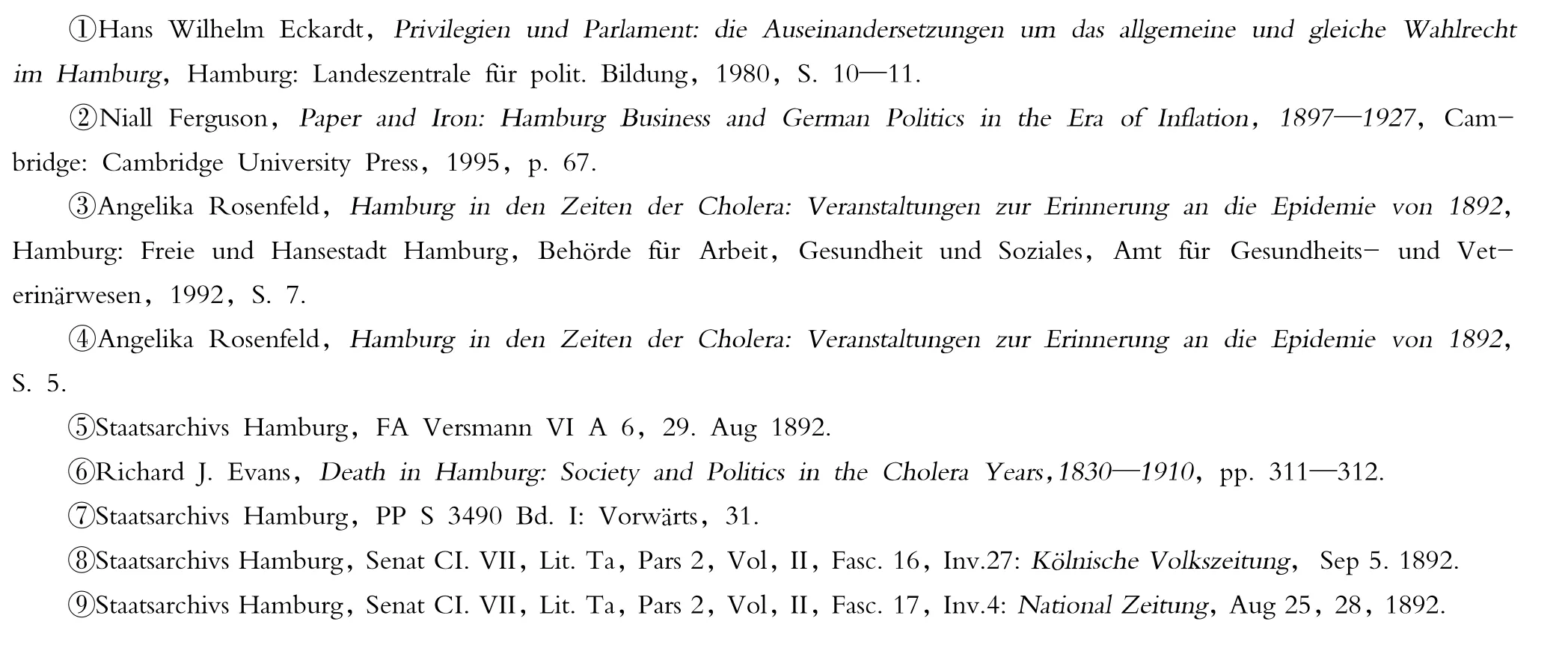

最后,市民阶层对汉堡市政当局隐瞒疫情和防疫不力普遍感到愤慨。最早知情的是医生群体,其代表哈格多恩博士(Dr. Hagdorn)在汉堡市民议会上斥责汉堡首席医务官克劳斯博士说,培养细菌只需不到24 个小时,克劳斯领导下的汉堡医疗系统花了3 天多。“鉴于8 月21 日阿尔托纳当局已向柏林报告发生霍乱,24 小时后克劳斯博士才允许发送类似的报告。这样一来疾病的宣布就不可避免地延迟了,这使汉堡遭受了可怕的疫情。”⑤不单是哈格多恩博士如此不满,几乎所有汉堡的医生都同样愤慨,“所有的医生……都一脸惊恐,谈论这种疾病被不同寻常地扭曲,或者说在他们人生经验从未经历过,并认定官方正在伪造数字。”⑥神父朱利叶斯·荣格劳森(Julius Jungclaussen)亲眼看到有的霍乱感染者等待了12 个小时才被运到医院就医。⑦汉堡显然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把感染者运送到医院,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只有4 辆救护车和6 位救护人员。⑧医院也是人满为患,“病人和死者躺了5—6 个小时后才有人医治和处理”。⑨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汉堡市政当局解除了首席医务官克劳斯的职务,并开始对汉堡城市公共卫生系统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首先,汉堡市政当局成立了两院联合委员会(Senats- und Bür gerschafts-Commission),帝国卫生局局长、汉堡市市长、罗伯特·科赫等成为委员。联合委员会开始调查城市的卫生健康情况,⑩其后认定受污染的城市饮用水是霍乱的主要来源,汉堡市政当局开始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住房情况和市民健康等。其中,改善城市饮用水质成为重点项目,1890 年已开始施工的沙滤系统在军队的帮助下完成,1893 年5月提前向汉堡市民提供干净安全的饮用水。①
其次,联合委员会派遣细菌学家、流行病专家详细统计汉堡霍乱大流行的医学数据,并由帝国卫生局出版。该备忘录详细记录了霍乱的信息和帝国境内其他各邦的防疫措施。⑫为了帝国范围内更好地控制传染病,帝国卫生局趁机要求各邦、各自由城市以后任何传染病都应建立报告制度。1893 年各邦和自由城市出版了详细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手册,指导杀毒、病患运输、尸体处置等。城市各区的医院严格按照传染病级别分级处理,低于200 人为小传染病,多于350 人为重大传染病。手册还提供医院床位、内科医生、培训自愿者等信息。①

最后,成立一系列新的机构——汉堡卫生局和专门的海港医院,以及细菌研究实验室。细菌研究实验室负责检验医院的病原细菌、分析易北河的水样和城市饮用水质。此后,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卫生意识的增强,原本只是分析病菌和水样的实验室,很快将监测扩展到食物卫生、居住环境、学校工厂等范围,最后成为囊括组建消毒队、培训人员等业务的庞大公共卫生部门。②海港医院则专门负责检疫海港,包括检测船员健康、海港淡水供应和废水处理等公共卫生事务。海港医院的首任主任是伯恩哈德·诺特(Bernhard North)。③1892 年以后汉堡公共卫生制度不断完善,赋予了医生更多独立性和责任;市政当局聘用专门医疗管理人员,组建了更加高效的市政公共卫生体系,④城市的卫生环境、公共卫生制度和市民的健康水平都有显著提升。
四、帝国体制与卫生防疫
1871 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初期,每个邦有自己的君主、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掌控教育、卫生、警察等部门,征收大部分赋税。但中央政府权限不断扩大,逐渐削弱了各邦的自主权。⑤卫生防疫原本是各邦的地方事务,属于地方自治权利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邦逐渐将许多权利让渡或委托给帝国中央政府,成立了包括帝国法院、帝国军事法院、最高海事局、帝国保险局、联邦最高行政法院、标准委员会、私人保险监管局、帝国卫生局等部门。然而让渡和委托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充斥着经济利益纷争、人事冲突、派系斗争等因素,各方常常借助一些人事变动、突发事件、法律争端等展开激烈的斗争。1892 年,汉堡霍乱大流行成为帝国卫生局大力拓展中央权限和职能的典型个案。汉堡官方宣布发生霍乱之前,帝国卫生局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已经带队前往汉堡地区,代表帝国卫生局和帝国卫生局细菌实验室参与霍乱疫情的控制和治疗。在罗伯特·科赫积极防控方针指导下,帝国卫生局的权力大为延伸。
首先,帝国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和科学研究的权威性得到验证。在帝国卫生局的协调下,8月27日帝国各邦召开特殊会议之后,各邦很快严格执行一系列的隔离或病毒消杀的公共卫生制度。为了严格控制易北河流域霍乱传播,9月12日帝国卫生局成立了易北河流域帝国特别委员会,9月13日到11月29日间,帝国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易北河上57000艘船只,近33000艘接受了卫生消毒。易北河流域帝国特别委员会有如此强的执行力,主要来自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和帝国卫生局的全力支持。类似的卫生检疫制度在奥得河和莱茵河流行同样严格执行。9月11日成立的帝国霍乱委员会协调帝国内所有的卫生检疫,帝国霍乱委员会的主席是帝国卫生局局长。而帝国霍乱委员会执行的霍乱防疫措施主要由帝国卫生局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具体负责制定和监督执行。⑥1892年11月1日,科赫向帝国霍乱委员会解释道:“与汉堡的往来使得霍乱传播到了近300个地方,一开始似乎整个德国很快会感染霍乱。为了防止疫情传播至全国,我们采取了与以前不同的步骤:人流量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限制,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用这种方法收效甚微。现在我们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措施(对其他流行病也有效),尤其对已确定的发病地方的最早病例进行彻底治疗,以免发生局部流行病。几乎所有从汉堡传播的病例中,我们都以这种方式成功地遏制住霍乱。”⑦罗伯特·科赫采取的防疫方针收到了明显成效,1892 年9 月15日后帝国范围内新增霍乱病例显著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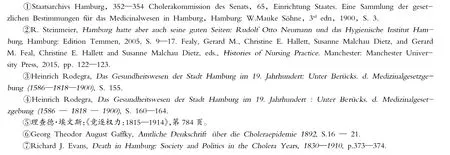
其次,帝国卫生局直接参与管理汉堡城市内部事务,甚至强制汉堡参议院和市政当局采取帝国卫生局和罗伯特·科赫的积极防疫措施。霍乱大流行爆发后,参议院-市民议会组成的两院联合委员会成员中,帝国卫生局局长卡尔·科勒博士和帝国卫生局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也赫然名列其中。然而,各邦国各自由城市在加入北德意志联邦及后来于1871 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之前,都享有完全主权性的国家权力。加入之后,各邦国权限和自由决定权因其从属于帝国而受限制,不再具有主权特征,但仍在广泛领域里享有权力,其权力通过司法和强制力得以保存。这些法律权力并非新成立的帝国所赐,帝国也不能撤销,它们源于历史、传承下来的固有权力。①汉堡参议院和市民议会是汉堡地方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核心,非汉堡市民选举产生的帝国卫生局局长和罗伯特·科赫位列两院联合委员会,这成为汉堡政治新生态的重要象征,标志着柏林-汉堡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显著变化。
帝国卫生局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从事的病菌学说标志着一种决裂,一种与体液学说、瘴气论为基础的既有医学的分道扬镳。病菌学说认为病菌是真正的敌人,可以通过病菌学说来辨认与消灭;病菌学说将实验室置于公共卫生政策政策的核心。②汉堡实验室是帝国卫生局实验室制度、公共卫生权威与医学现代性的的综合体现。1870 年至1890 年间,罗伯特·科赫从事的细菌学研究逐渐建立了病菌学说的普世性和科学性,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疾病都可以找到致病的病菌,并可以用疫苗加以扑灭。这为更加侵入性的公共卫生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国家和医生可以将抗原注入公民的身体里。③以防治传染病和阻止公共卫生灾难再次爆发的名义,罗伯特·科赫代表帝国卫生局和科学权威干预汉堡城市内部事务,全力推行公共卫生制度改革,例如卫生防疫、实验室制度、传染病立法、住房建筑法等,无形中削弱和压制了汉堡原有统治阶层垄断性的市政管理权限。
再次,帝国卫生局和罗伯特·科赫的卫生防疫改革契合了民族团结与受灾城市团结的情感诉求。1892 年汉堡霍乱大流行正值德意志帝国大规模医学专业化的开端。大量散发的防疫手册、全面的消毒措施和海量的新闻报道,广泛而深入地宣传了帝国卫生局和罗伯特·科赫的光辉形象和科学权威。在柏林中央政府和帝国卫生局支持下,大规模医疗化时代导致了对大规模死亡的普遍谴责,而这种谴责压倒性地针对汉堡市政当局。

最后,汉堡的商业市民社会的自治传统与普鲁士的官僚政治制度开始合作与融合,共同构建德意志帝国共同体,汉堡商业市民社会与柏林的帝国官僚政治社会结合起来共同塑造新帝国。在此之前,汉堡内部凝聚程度远超帝国的其他城市,其他帝国自治城市,例如不来梅或吕贝克,缺乏维持其独立性的财政力量;而资产阶级的财富和繁荣中心,例如法兰克福或莱比锡,1866 年之后缺乏将其经济实力转变为政治力量的制度化空间。1892 年汉堡霍乱大流行改变了汉堡政治走向,释放了政治变革的力量,汉堡城市内部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权力发生了重大变化。汉堡城市贸易至上的普遍共识受到社会民主党的严重挑战,而这些涌动的力量当时不少人已预见到了。


结 语
汉堡霍乱大流行后,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新闻媒体和汉堡市民都批评汉堡市政当局隐瞒疫情,由此形成的公共舆论,使得公共卫生制度改革获得了自官方到民间的广泛认同。1892 年后更是卫生防疫帝国化和制度化的形成期。作为由具有主权国家组成的联邦,各成员国仍然保留原有宪法及议会立法机构,汉堡对霍乱大流行的隐瞒,表明德意志帝国内部其实有着很复杂的情况,除了影响最大的普鲁士外,各邦国各自由城市亦非常值得注意。
霍乱大流行与公共卫生是一体两面。帝国卫生局依据首席科学家罗伯特·科赫的细菌学说,以1892 年汉堡霍乱大流行为突破口,直接指导汉堡城市内部的公共卫生改革,汉堡实验室是帝国卫生局实验室制度、公共卫生权威与医学现代性的综合体现。它们都以罗伯特·科赫的细菌学说为据,凸显了德意志帝国内部中央-地方之间的政治生态,表明汉堡公共卫生改革为罗伯特·科赫的细菌学说发展提供了普遍道路。汉堡霍乱大流行加深了我们对19世纪欧洲防治霍乱的曲折历程的认识,揭示了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内部演变的复杂性,给我们留下了卫生防疫与构建帝国密切联系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