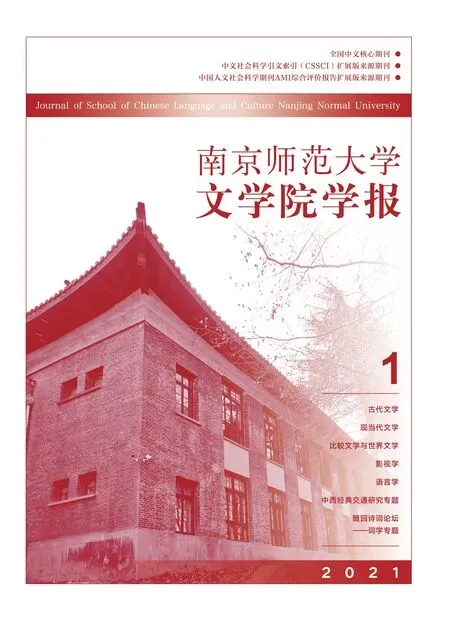根柢《风》《骚》 涵泳温、韦
——陈廷焯艳词理论概述
黄青绿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又字伯与,清丹徒人。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主要继承与创新张惠言、张琦词论,推崇与强调以“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韦”的“风骚”精神,发展并丰富张惠言艳词理论。陈廷焯词论在艳词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里程碑式意义。
一、艳词词体:根柢于《风》《骚》
“风”即《国风》,“骚”即《离骚》,并称“风骚”。历来被以儒、道等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认同为文化正宗。《诗经》首篇、首章、首句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河洲雎鸠比兴淑女是君子的红颜知己、美好配偶,并寄托贤臣君子是君主王侯的忠臣良将。《离骚》的“比兴寄托”,相对于《国风》的题材具体、片段简单,发展成为题材抽象、长篇巨制,常以男女关系比兴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兴群小嫉贤,以婚约盟誓比兴君臣遇合同心,推进了托物言志、寓情于景等文学表现手法的广泛运用。
陈子龙曾经于《三子诗余序》中强调:“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1](P27)以《诗经》中《国风》与《楚辞》中《离骚》为代表的一切诗词,皆以言情为本,而言情之作,必须依托于女子、闺阁的言辞。词承继这种模式,但在艺术形式上更讲究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表面看似写闺阁之事,这正是词传统的书写方式,而在本质内涵上,却必须要有弦外之音,即“风骚之旨”又称“风人之旨”,即重视比兴寄托。陈子龙于《三子诗余序》中举例强调:“或曰:是无伤于大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不淫,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则元亮闲情不能与总持赓和于临春结绮之间矣。”[1](P28)词体本质在于将别有寄托的深刻寓意,通过美丽或看似轻佻的外在形貌予以书写表现。
艳词,是“表现”女性体态或男女之情的词。“表现”一词是强调对描写对象与内容的审美体验,那些仅仅从生理体验出发以通过描写女性体态或男女之情而获得生理快感的词必须作为淫词而遭唾弃与摒弃。换言之,那些未从生理快感体验出发而通过描写女性体态或男女之情借以展示个性或表达社会诉求或寄托之义的词,不仅视作是从审美体验出发的艳词,而且要作为艳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阐述与诠释。艳词,在于将别有寄托的深刻寓意,通过美丽或看似轻佻的外在形貌予以书写,是表现得最典型、最本质、最完美的词体。
张惠言于《词选序》中承袭“风骚”,推崇“比兴寄托”,明确标举“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的理论旗帜,其振聋发聩之音,对艳词乃至词的创作与评论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张惠言《词选序》中“变风之义”可溯源自《诗大序》,《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乃作矣。”[2](P195)孔颖达云:“变风、变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治平累世,则美刺不兴。……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恶则民恶,善则民喜,故各从其国,有美刺之变风也。”“变风之义”,特指国政衰败之际作品中深蕴的美刺、讽谏、教化之意。张惠言《词选序》中“骚人之歌”即为传承《离骚》的精髓。王逸《离骚经序》云:“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3](P3)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说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词不可径也。故有曲而达,情不可激也。”[3](P3)“故有譬而喻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为小人。”[3](P3)“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谗构。”[3](P3)魏源表达的观点与王逸的观点完全一致,仅仅言辞有别。“骚人之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文士心中,代表着国政衰败或时运不济之际的一腔“忠爱之忱”、满腹“感士不遇”。张惠言于《词选序》中明确阐述的艳词运用“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表现手法寄托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正是指向“感士不遇”与“忠爱之忱”交织缠绵的相关情感。这些相关情感,与《国风》、《离骚》的美刺、讽谏、教化传统一脉相承。
陈廷焯前期词论体现于1874年编定的词选《云韶集》及其卷首语《词坛丛话》中,后期词论体现于1890年编订的词选《词则》及一年后对应此词选创作的词论《白雨斋词话》中。编词选、论词作,贯穿陈廷焯词学活动终生。陈廷焯前期编词选、论词作,借鉴浙西词派鉴朱彝尊、汪森编选《词综》经验,崇尚艺术形式层面的“清空”“醇雅”;陈廷焯后期编词选、论词作,借鉴常州词派张惠言、张琦编选《词选》经验,崇尚思想内容层面的“比兴”“寄托”。浙西词派宗南宋词,力主“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词要清新,不要质实”[4](P16)等艺术形式;常州词派尊北宋词,力主通过“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现实。或重形式,或重内容,此起彼伏,盛衰交织,历来是文学包括词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反映并见证着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时代需要。在清代特定历史时期与词学自身发展背景下,陈廷焯受常州词派著名词人庄棫影响,其词论由前期师承浙西词派,与时俱进发展成为后期师承以张惠言、张琦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在兼收并蓄对南、北宋词论的基础上,独树一帜,于《白雨斋词话》中创立了“沉郁”说。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关于“沉郁”说云:“所谓沉郁者,以为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5](P1165)显而易见,陈廷焯“写怨夫思妇之怀”,即张惠言“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陈廷焯“寓孽子孤臣之感”,即张惠言“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陈廷焯“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即屈原开创的首用于《离骚》创作中借“香草美人”比兴寄托“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的表现手法。“风骚之旨”又称“风人之旨”,也即张惠言所论“变风之义”、“骚人之歌”;陈廷焯“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即张惠言所论“低徊要眇”“义有幽隐”等艳词审美特征、鉴赏原则[5](P1165)。这说明:“‘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就是承袭了张惠言的‘意内言外’说。”[6](P65)“‘沉郁’的核心乃是‘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7](P112)综上所述,陈廷焯“沉郁”说,与张惠言词论如出一辙,都立足艳词词体本质阐述,建构词学理论,其实质为艳词词论。
《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指要》中从“体”“用”两方面论述陈廷焯词论,“温厚”为“体”,“沉郁”为“用”,所谓“沉郁”,即“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表面上是描写“怨夫思妇”的情状,实质上寄寓“孽子孤臣”的感喟,“于一草一木”中缠绵悱恻、含沙射影即“若隐若现”“不许一语道破”地反复表现冷淡的交情与飘零的身世,而这一切“性情”流露与宣泄的源头活水都是“本诸《风》《骚》”。《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指要》中追根溯源陈廷焯的词学理论即所谓“沉郁之说”是继承、推广、弘扬与发展“二张之旨也”,二张即张惠言、张琦,因陈廷焯是接受庄棫的词论,庄棫的词论“接迹于常州二张”。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中记载着陈廷焯一段自述:“自丙子年(1876年)与希祖(庄棫字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已卯(1879年)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庄棫著有《蒿庵词》),其成茗柯(张惠言著有《茗柯词》)之志。”张惠言对词的里程碑式意义,是以温庭筠及《花间集》词作为立足点,通过剖析、概括、归纳艳词特征,把以儒、道等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诗教精神即“风骚”精神,铸造为词尤其艳词的精神本原。陈廷焯则在继承与创新张惠言艳词理论基础上,于《白雨斋词话》中以“沉郁”为词学思想核心,深化并完善了对艳词的精神本原的系统阐述。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多次论述涉及到“风骚”,譬如强调“作词之法”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首贵沉郁”,并进而连用两个双重否定句式的强烈反问强调“风骚”即“沉郁”的核心,“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不究心于此,率尔操觚,乌有是处?”紧接着又以《国风》《楚辞》为例强调“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其主要意思为:词学的中心思想归结为“沉郁”,“沉郁”归结为“风骚”,“风骚”是“沉郁”的根源,“风骚”是奠定“沉郁”的基础。再如论及善于作词的人总是讲究历久弥新,即使历经千年光阴的洗礼,依然可以找到知音,“陈、朱之词,佳处一览了然,不能根柢于《风》《骚》,局面虽大,规模终隘也。”言下之意,陈、朱词作佳者固让人一目了然,但一旦不以“风骚”为精神本原,即使词作局面很大,规模也终将狭隘。《白雨斋词话》在谈及“作艳词,以何为法”时,陈廷焯自问自答“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韦”,一言以蔽之,强调必须须以“风骚”为精神本原,以温庭筠、韦庄为词作的正宗源头。
二、艳词词史:涵泳于温、韦
陈廷焯于其《白雨斋词话》的《自序》中曾盛赞温庭筠与韦庄及周邦彦、秦观、姜夔、王沂孙等词人,通过对《骚》《辩》的不断演绎、推断进而阐发词的主要旨意,而《白雨斋词话》的标新立异之处就在于其着眼于从整个词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理解并阐释“风骚”。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与张惠言《词选序》一脉相承,都盛赞温、韦,称颂他们的艳词具有“风骚”精神,乃至词之正宗。陈廷焯将艳词发展分为三个经典时期:晚唐五代时期、北宋中后期、清中后期,皆沉潜、揣摩、玩味温庭筠、韦庄词作,汲取其“风骚”营养。艳词词史,一言以蔽之,即涵泳于温、韦的艳词发展史。
(一)晚唐、五代:以温、韦为正宗的发轫期。
《白雨斋词话》中多次高度赞扬“花间鼻祖”温庭筠,陈廷焯认为自古历今“得《骚》之妙”的文学作品只有“陈王之诗”与“飞卿之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艳词既“得其神”又“不袭其貌”。陈廷焯盛赞温庭筠几首代表性词作如《菩萨蛮》《更漏子》为“楚骚变相,古今极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断言其艳词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境界,陈廷焯不惜溢美之词,“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杜绝千古。”
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也多次盛赞韦庄,譬如“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剖析后主李煜词作风格与温庭筠词作风格的不同可概括为“合而离者”,剖析韦庄与温庭筠词作风格的不同可概括为“离而合者”,在此比较基础上凸显韦庄艳词“一变飞卿面目”。
后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收录温庭筠、韦庄等晚唐五代十八位词人五百首词作,十八位“花间”词人均处上起晚唐下迄后蜀广政年间,百年之中,他们共处一个极为动荡的历史时期,有着相似的境遇和情感体验,十八家词有着相似的题材、风格和价值取向,由此结成《花间》并非偶然;“花间”一词,本就象喻了词之意旨所在,它不在家国天下,而在闺阁内帏,也意味着十八家词业已构成一个整体性的世界。[8]
如追根溯源,自艳词诞生,《花间集》乃“倚声填词之祖”[9](P496),晚唐、五代温庭筠为“花间鼻祖”,以温庭筠、韦庄艳词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艳词,是艳词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后世艳词自此正式发轫的起点时期。
(二)北宋中后期:与温、韦并行不悖的发展与高潮期。
北宋中后期的词坛,是词的发展与高潮期。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两大词派竞相争艳,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盛赞的苏轼、辛弃疾为豪放风格,周邦彦、秦观为婉约风格,陈廷焯认为四者词作皆与温庭筠、韦庄词作并行不悖,并都具备“风骚”精神,同属名垂千古的经典词作。
陈廷焯认为苏轼词作深得温庭筠、韦庄词作的精妙,例如苏轼《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花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这首词单就题材内容来看,写“云”,写“雨”,写“楼”,写“水”,写“柳”,写“花”,写“酒”,写“月”,写“扇”,写“风”,写“晚烟”,写“残阳”,写“帘钩”,写“巫山”,写“美人”,写“星眸”,写“金瓯”,写“春愁”,写“江南”,写“扬州”,表面上看似写的是风花雪月的艳情,而实质上只要我们结合苏轼当时的人生际遇来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来探索苏轼这首词中所寄寓的个人诉求或社会理想,方可明白这首艳词的精致微妙,一代词宗苏轼,扬州深烙心胸,坦诚浮沉悲欢,其词语言精练,其情沉郁深厚。像这样精准并且艺术地选取、剪裁、移植《花间集》中的题材内容,表现个人诉求或社会理想(即前文又称骚人之歌、风人之旨)的书写形式。模式或方式,其精髓正是陈廷焯予以肯定并积极推崇的“本诸《风》《骚》”。
陈廷焯盛赞辛弃疾为“词中之龙”,极言辛弃疾词作气势恢宏、雄壮博大,辛弃疾词作的意境堪称极其“沉郁”,溯其源头,也是脱胎于温庭筠与韦庄的风格。譬如其以辛弃疾《菩萨蛮·书西江造口壁》为证,强调其“用意用笔”,“洗脱温、韦殆尽”,言下之意,辛弃疾这样的词作,与温庭筠、韦庄词作风格是一脉相承的。
扬州高邮词人秦观,宦海浮沉,几经贬谪,羁旅行役中常常魂牵梦萦家乡扬州,多有词作。其《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既怀念昔日扬州男女之情、青楼旧好,也怀念同时遭贬谪的知己故人、良师益友。秦观艳词的字斟句酌深得温庭筠、韦庄艳词遣词造句的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历来口耳传颂,为后世奉为圭臬。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盛赞秦观,赞誉秦观自从迈入词坛“近开美成,远祖温、韦”,“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这一词句尤其含蓄蕴藉,联想与想象极其丰富神奇,妙不可言,深得温庭筠、韦庄艳词精髓,而又不着雕琢痕迹。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给予其词“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的至高评价,并以《满庭芳》词作为例,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称赞其虽然被贬谪流放,却眷念故国,忠厚深远,深沉、含蓄又豪迈地通过艳词寄寓关于身世浮沉以及家国情怀之类的“风骚”之旨,因此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极言秦观的词作“最深厚,最沉着”。
周邦彦《少年游·檐牙缥缈小倡楼》词云:“檐牙缥缈小倡楼。凉月挂银钩。聒席笙歌,透帘灯火,风景似扬州。当时面色欺春雪,曾伴美人游。今日重来,更无人问,独自倚阑愁。”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盛赞周邦彦,如:“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味,亦尽于此矣。”以周邦彦《齐天乐》为例,其中名句“绿芜雕尽台城路,殊郎又逢秋晚”,一个“尽”字,令人无限怅惘,然而一个“又”字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令人唏嘘不已,其中世事的浮沉悲欢、起伏顿挫,演绎与释放着极其深厚的人生况味。“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一句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如果说晚唐、五代时期是艳词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其后至两宋,经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先、秦观、周邦彦、柳永、姜夔、王沂孙、张炎、陆游、李清照等重要艳词词人对艳词不断继承与创新,两宋时期尤其以苏轼、张先、辛弃疾、秦观、周邦彦、柳永等为代表的北宋中期,则成为艳词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甚至单就艺术形式上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其一定意义上堪称整个艳词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乃至巅峰时期。回顾与总结艳词发展的这个高峰时期,艳词的题材内容不断扩大,尤其艳词的表现手法不断细致入微,可以说这个高峰时期的艳词,是在紧紧围绕与继承以温庭筠及《花间集》为中心的内容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壮大的。
(三)清中后期:振兴温、韦的中兴期。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认为:诗衰败于宋代,词没落于元代,但是自清代中叶乾隆、嘉庆时期开始,能够扛起“风骚”精神大旗重整晚唐、五代以及两宋词风的重要词家就是张惠言与庄棫。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喟然长叹“复古之功,兴于茗柯,必也成于蒿痷乎?”即是这种确认的深刻感慨。
陈廷焯在梳理词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于《白雨斋词话》中得出结论,自古历今的一切词作,都是温庭筠与韦庄“发其源”,周邦彦、秦观“竟其绪”,姜夔、王沂孙“各出机杼”,其后六百多年几乎没有词人推波助澜,词坛陷入颓败,直至清代常州词派奠基人张惠言及其后学庄棫,陈廷焯在继承张惠言词论基础上详细介绍庄棫及其著作《蒿庵词》,并以“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肯定庄棫在继承、发展艳词“风骚”精神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陈廷焯目睹清代艳词的当代繁荣,并认定自己生活的时代是艳词的振兴期,有一定历史背景与依据。以王士禛、邹祗谟、陈维崧、董以宁等为首的清初广陵词坛词人群体,在云间派前辈尤其陈子龙词学思想的深重影响下,在基于对艳词创作的长期自我深刻反省下,尤其再加之在顺康易代之际历史巨变的触发下,在顺康之际的清初词坛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艳词唱和活动,为清代艳词的实践创作与理论总结从不自觉的蒙昧状态到自觉的清醒书写提供了广阔的时空与持久的动力。活动不仅集中训练了大量广陵词坛词人艳词创作的技能,也为清中后期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的相当一批卓尔不群的优秀艳词词人通过精准并且艺术地选取、剪裁、移植《花间集》中的题材内容从而书写即表现骚人之歌、风人之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毋庸置疑,清代艳词的题材内容十分宽广丰富:既可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时弊、歌颂太平盛世、赞扬圣主明君,也可表现男欢女爱、男女相思、爱恨恩怨;既可思归怀乡、伤时感事,表现个人儿女情长,也可忧国忧民、吊古讽今,书写一代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清代艳词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个人诉求与社会寄托已经包罗万象、融会贯通、水到渠成、浑然一体,清代艳词词人所理解并付诸于笔端的所谓骚人之歌、风人之旨已然不再仅仅拘泥于国家荣辱、民族存亡等大事件、大主题,也包括今天时人所津津乐道的小秘密、小确幸、小情绪等以个性化生活为中心的真情流露或情感宣泄。
三、艳词词品:入门之始,先辨雅俗
“入门之始,先辨雅俗。”[10](P1310)判断艳词词品优劣高下,肇始于此。陈廷焯关于艳词分类与批评的词论,对于后世艳词理论与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奠基意义,不仅从宏观而且从微观上给予艳词研究重要方法论层面的指导。
(一)艳词分类标准
其一,“正声”与“浮艳”“变体”“别调”。
张惠言确认“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11](P1617)可视为有寄托的艳词,有寄托就可供效法,可视为正声。相反,如毫无寄托,或一味描写男女之情只为生理感官的艳词,就是浮艳的词作。陈廷焯承袭张惠言观点认为:“晏欧词,雅近正中,然貌合神离,所失甚远。盖正中意余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若晏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尚安足重!”[10](P1168)晏即晏殊,欧即欧阳修,正中即冯延巳,皆北宋著名词人。“貌合”,指晏殊、欧阳修、冯延巳词作皆为表现女性或男女之情的艳词;“神离”,指“若晏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盖正中意余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究其原因,冯延巳艳词“思君之词,托于弃妇。”[10](P702)显而易见,冯延巳艳词为“正声”,晏殊、欧阳修艳词为“浮艳”。张惠言《词选》收录“正声”舍弃“浮艳”,众所皆知。
张惠言《词选序》中阐述:“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11](P1)陈廷焯参照张惠言《词选》及《词选序》,通过对古今词作的全面梳理与深入甄别,编《词则》四集,其一《大雅集》、其二《放歌集》、其三《闲情集》、其四《别调集》。[12](P1)《大雅集》中选录的词为“正声”即视为“源”,可视为《词选》的扩展补充;另外三集中选录的词为“变体”即视为“流”,依次与张惠言不认可的“傲而不理”“荡而不反”“枝而不物”词一一对应。“其中《闲情集》收录自唐至清的艳词217家655首,对张惠言舍弃的艳词给予了独立的关注。”[13](P76)不难发现,相对而言,《放歌集》对应“变体”、《闲情集》对应“浮艳”、《别调集》对应“别调”甚至直接以“别调”命名。陈廷焯《词则》各集选词依据、标准或分类,于此管窥一斑,可见端倪。
其二,“言情”与“体物”。
艳词,或侧重表现女性,或侧重表现男女之情。陈廷焯比较朱彝尊与董以宁的艳词认为“言情者远胜文友。而体物诸篇,则文友为工。”[10](P1306)陈廷焯是按照艳词表现题材与内容侧重点的不同,把艳词明确划分为“言情”与“体物”这样两个不同类别。毋庸置疑,“言情”与“体物”艳词,若别有寄托,则皆雅为“正声”;反之,则皆俗为“浮艳”。
“言情”类艳词,侧重表现男女之情,自古历今,数量较多,良莠不齐。“体物”类艳词,侧重表现女性,多表现女性体态及其衣着、佩饰、化妆器具等。陈廷焯的“体物”类艳词就表现对象而言类似于“咏物”。肇始之词,莫过于脍炙人口的南宋刘过的《沁园春·美人足》与《沁园春·美人指甲》二首。紧随其后的词人,有元代的邵亨贞与明代的瞿祐、马洪等词人。其后,趋之若鹜,至清已蔚然大观。
其三,“歌妓”与“闺襜”,“泛设”与“确指”。
“将婉娩风流,写成轻薄不堪女子,吾不知此辈是何肺腑。即以之写歌妓尚不可,况闺襜耶!”[10](P1261)陈廷焯依据艳词所表现的男女之情的不同女性身份,又具体细致地把“言情”类艳词划分为“歌妓”与“闺襜”两类。“歌妓”,指歌妓、妓女等风尘女子;“闺襜”,指少妇、少女等良家女子。
词人朱彝尊的纪实词集《静志居琴趣》是实录与其妻妹的不伦之恋;赵文哲《祝英台近》也是实写与自己不期而遇的一个美丽少女堕入爱河直至生死离别的经历;董以宁《东坡引》一共九个章节都是写给他的女仆。显而易见,这些艳词都是词人自己某段艳遇或风流故事的实录。陈廷焯云:“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10](1209)“若竹垞《静志居琴趣》一卷,璞函《祝英台近》八章,文友《东坡引》《鹧鸪天》诸阕,俱实有所指,又当别论。”[10](P1263)毋庸讳言,与朱彝尊等人“确有所指”的艳词相比,传统的“闺襜”之作多为“泛设”之词,即艳词中女性的形象、情事、口吻出自男性词人的想象与虚构。因此“闺襜”类艳词,又有“泛设”和“确指”的区别。
下图特以表格形式呈现陈廷焯《词则》中词尤其艳词的分类情况:

《词则》:词雅词(源)《大雅集》:“正声”(含有艳词)俗词(流) 《放歌集》:“变体”(傲而不理) 《闲情集》:“浮艳”(荡而不反)收录唐至清艳词217家655首言情歌妓闺襜泛设确指体物 《别调集》:“别调”(枝而不物)
陈廷焯的艳词分类,也仅依据表现侧重点不同大致归类,没有绝对界限,只有相对划分。但相对于陈廷焯之前古代词学家,陈廷焯的艳词分类方法已将对艳词的理论认识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毋庸置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艳词鉴赏原则
其一,“入门之始,先辨雅俗。”
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云:“将婉娩风流,写成轻薄不堪女子,吾不知此辈是何肺腑。”[10](P1261)陈廷焯深恶痛疾将“婉娩风流”亵渎为“轻薄不堪”,表现在把娇宠误导为轻佻,把情欲降格为性欲。如牛希济之“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陈廷焯评点为“一味纤巧,不可语于大雅”;又如柳永“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语言因为过于刻意浅显直白以致艺术效果未能自然朴素,反倒俚俗不堪,陈廷焯评点柳永此句为“着力写去,适形粗鄙者”。陈廷焯概括俗词典型的三类症状,为轻薄之态、纤巧之思、粗鄙之辞。陈廷焯云“入门之始,先辨雅俗。”[10](P1310)言下之意,即使具有寄托之意归属“正声”的艳词,一旦堕入以上三种症状也为俗词。而归属于“浮艳”之流的一般艳词,本来都为张惠言舍弃与不屑,陈廷焯认为只要不为轻薄之态、纤巧之思、粗鄙之辞,也可免俗,至少不以淫亵、鄙陋、浅俚之词视之。陈廷焯进而针对不同类别的所谓“浮艳”之词,提出不同的审美原则,深化并拓展了对艳词理论认识的空间与水准。
其二,“惟其情真”。
针对“闺襜”类“确指”艳词,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中云“竹垞眷所戚,璞函眷一姝,文友则眷一婢,惟其情真,是以无微不至。”[10](P983)陈廷焯言下之意竹垞朱彝尊、璞函赵文哲、文友董以宁都是眷念真爱着一位女性,并在各自的艳词中真实记录着眷念真爱的情感体验。这些艳词分别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赵文哲《祝英台近》八章,董以宁《东坡引》九章、《鹧鸪天》七章。“闺襜”类“确指”艳词的显著特点就是感情实录、情真意切、至情至性,“惟其情真,是以无微不至。”此类艳词的艺术形式亦随之异彩纷呈、可圈可点,陈廷焯对“闺襜”类“确指”艳词评价极高,如“璞函《祝英台近》八章,遣词闲雅,用笔沉至。艳词中运以绝大笔力,真千年绝调也。”[10](P1235)如“文友《鹧鸪天》诸阕,婉雅芊丽,艳词之有则者。”[10](P982)如“《东坡引》九章皆示婢词,细意熨贴,无微不入,不及秀水之清雅,而韵致过之,亦秀水之劲敌也。”[10]( P983)如“《静志居琴趣》一卷,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尝梦见,真古今绝构也。”[10]( P1209)赵文哲毫不掩饰娓娓道来与邻家妹子的浪漫艳遇,董以宁直截了当深情诉说与侍婢的柔情密意,至情至性,感人至深。相对而言,朱彝尊与妻妹的的私情有悖封建纲常,确为不伦之恋,是一种时时受到舆论压制、道德绑架却又时时无法自抑的真情。这正是《静志居琴趣》言情含蓄蕴藉、曲折幽深的原因,“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词,故为隐语,所以味厚”。[10](P1209)陈廷焯不仅认为朱彝尊艳词超越赵文哲、董以宁艳词,甚至认为在整个艳词史上独占鳌头。陈廷焯云:“艳词至竹垞,扫尽绮罗香泽之态,纯以真气盘旋,情至者文亦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洞仙歌》其最上乘也。”[10](P970)言下之意,朱彝尊《洞仙歌》为空前绝后的极品艳词。针对“闺襜”类“泛设”艳词,陈廷焯云:“古人词如毛熙震之‘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似此则婉转缠绵,情深一往,丽而有则,耐人玩味。其次则牛松卿之‘强攀桃李枝,敛愁眉’,……均不失为风流酸楚。”[10](P1261)虽表现对象非确指女性,但依然在“不失为风流酸楚”基础上标榜“情深一往”。[10](P1262)
针对“歌妓”类艳词,陈廷焯云:“至赠妓之词,原不嫌艳冶,然择言以雅为贵,亦须慎之。若孙光宪之‘醉后爱称娇姐姐,夜来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长么’,真令人欲呕。魏承斑之‘携手入鸳衾,谁人知此心’,语亵而意呆。林楚翘之‘重道好郎君,人见莫恼人’,亦俚鄙可笑。”[10](P1263)言下之意,相比于“闺襜”类艳词,“歌妓”类艳词原本可以允许较大尺度的情欲描写,但是仍然需谨慎运用不失雅致的言语。诸如运用“娇姐姐”“好哥哥”“好郎君”这样言辞赤裸裸描写男欢女爱场景的艳词,都是涉嫌淫亵,“真令人呕吐”与“俚鄙可笑”。陈廷焯深刻地认识到“歌妓”与“闺襜”的身份毕竟大相径庭,“歌妓”与男子包括词人的交往大多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即便是一见钟情也多为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一晌留情,纵然感情真挚,也不一定能与“闺襜”真情同日而语、见证地久天长。大多词人与“歌妓”交往并流露于艳词之中的男女之情,显然与夫妻之情或确指的情侣之情泾渭分明,因此陈廷焯并不局限于从爱情角度对“歌妓”类艳词进行审美,而是另辟蹊径确立并倡导“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14](P24)作为对“歌妓”类言情之作的更高审美要求。如赵文哲《绮罗香·席上》:“乳燕栖梁,丝莺坐槛,曾记看花同住。十载蓬飘,那分者回重聚。浑已换、款柳心情,犹未减、咒桃眉妩。向芳筵、粉箑轻招,剪灯还认旧题句。相看惟有掩袖,无限鸳思凤想,都随飞絮。选婿窗边,可忆断魂柔路。纵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无干处。怕明朝、刬地东风,钿辕吹又去。”当辗转漂泊的词人与曾经真心挚爱的歌妓不期而遇,十年往昔已不堪回首,虽然女子依旧温柔如初,而词人却早已颓唐沉沦。词中虽难免流露男女艳情,但更多充斥借歌妓抒发“我未成名君未嫁”的郁闷与悲哀。此情此景,亦是至情至性,只不过已然不是当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浪漫情愫,而是“恰道天凉好个秋”的那种深沉感喟。陈廷焯对此大加激赏:“淋漓曲折,一往情深,较古人赠妓之作,高出数倍。”[10]( P1008)“情深文明,自是绝唱。作赠妓词者,要当以此为法,则不病词芜,亦不患情浅矣。”[10]( P1264)张海涛于其《陈廷焯的艳词理论及其在词学史上的意义》一文中对陈廷焯的这段评语剖析认为:“所谓‘法’,就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叙写模式。凡是这样来作赠妓词,都会为陈氏所激赏。”如陈廷焯评点刘过的《贺新郎·老去相如倦》:“亦只从‘同是天涯沦落人’化出,而波澜转折,悲感无端,改之艳词中最雅者。”[10](P925)如评点吴伟业的《临江仙·落拓江湖常载酒》:“一片身世之感,胥于言外见之,不第以丽语见长也。”[10](P946)显而易见,陈廷焯推崇的“歌妓”类言情艳词所表现出词人的“一片身世之感”是超越男女爱情的“惟其情真”。
其三,“风趣绝胜”。
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是陈廷焯认为的“体物”类艳词的代表性词集,陈廷焯于《茶烟阁体物集》中选取八首艳词录入《闲情集》。陈廷焯以《茶烟阁体物集》与《静志居琴趣》相比较云:“诸篇各有机趣,较《静志居琴趣》一卷,情虽不及,趣则过之。”[10](P970)如《茶烟阁体物集》中《沁园春·背》》中词句:“每到嗔时,抛郎半枕,难啮猩红一点唇。堪憎甚,纵千呼万唤,未肯回身。”[14](P1011)词人并没实写女性背部,而是虚写女性嗔怪生气,即使她的爱人情郎千呼万唤,她也没有转身相见,可以想象,情郎一直凝望女性背部百般甜言蜜语期盼爱人转身相视而笑,背部是什么样子,给读者留下无穷无尽联想与想象的空间,这种女性娇嗔任性、男子殷勤讨好的情形,生动传神,情趣盎然,总会令人心有灵犀、如临其境、会心一笑。陈廷焯盛赞曰:“风趣绝胜,是谓艳词。”[10](P971)显而易见,陈廷焯认为,“体物”类艳词相对于“言情”类艳词最明显的的审美特点是“趣”大于“情”,即陈廷焯所云“情虽不及,趣则过之。”“言情”类艳词鉴赏原则“惟其情真”,“体物”类艳词鉴赏原则必然强调“风趣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