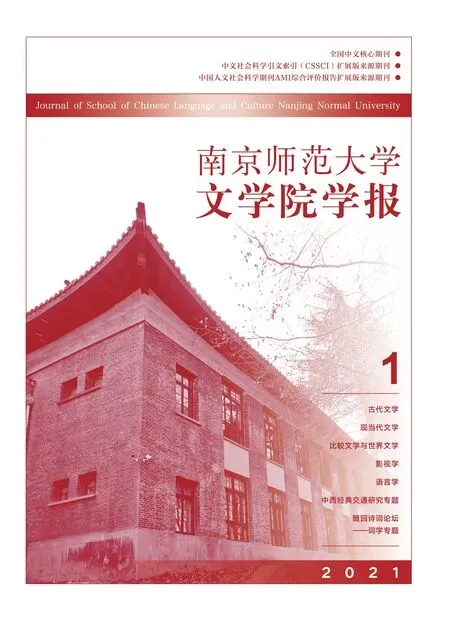明清之际西学汉籍重印初探
——以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为例
谢 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明万历至清康乾间,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在中国士人的协助下,以中文撰述著作,介绍西方哲学、宗教、历史、科技等内容,而一部分中国学者亦著书阐发或反击其说。大批以西方知识为中心的“西学汉籍”,即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对于此批典籍的刊刻,目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如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何朝晖《论晚明至鸦片战争前天学文献的刊刻出版》(《第三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肖清和《刊书传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编辑与出版活动初探》(《天主教研究论辑》2011年第8辑)等。但上述研究多从出版史、书籍史的角度出发,关注此批典籍刊刻的数量、种类、地点、刊行者,以及刻印活动与西学传播的关系等内容,而略于版本考察与特征分析。如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对存世诸本作逐一检视,便可发现,西学汉籍刻印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修版重印现象。尤以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所著《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以下简称“出像经解”),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印,最具代表性。有鉴于此,本文即通过对《出像经解》刷印情况的个案分析,进而窥测明清西学汉籍重印的整体面貌,并探究其背后的推动因素。
一、《出像经解》书板在明清时期的刷印
《出像经解》为描绘耶稣生平事迹的版画集。其书约成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翻译自耶稣会副会长纳达尔(Jerónimo Nadal,1507-1580)的《福音故事图像》,以图像配合简要的文字说明,形象地描述耶稣自降生至复活升天的全过程。因其艺术性强,且直观易懂,故成书后即大受欢迎。目前所知,世界各地藏本不下三十部,但基本都出自崇祯间晋江景教堂所刻的同一套板片,其刷印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明崇祯末年。这一时期的印本,以梵蒂冈图书馆藏本(馆藏号Raccolta Prima 339)较具代表性。此本卷前有耶稣会徽章页,继为明崇祯十年(1637)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引》,末题“天主降生后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大明崇祯丁丑岁二月既望,远西耶稣会士艾儒略敬识”,及“耶稣会中同学阳玛诺、聂伯多、瞿西满仝订,晋江景教堂绣梓”[1](P15-16)。全书共五十七幅图。其板框已有明显断裂,似非初印。但封底内页有拉丁文题识,谓此书为弗朗索瓦·韦洛(Franciscus Vello)神父约在1639年赠送给梵蒂冈图书馆[1](P75),距序言所题不过两年时间。由此可见,此本仍当是本书的最早印本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馆藏号为Chinois 6750者,经目验亦是此本。据著录,其原藏于巴黎阿瑟纳尔图书馆,乃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所有[2](P2868)。与梵蒂冈本相比,此本第二图《天主降生圣像》置于第一图协露撒棱都城图之前,第四十五图《系鞭苦辱》与四十六图《被加莿冠苦辱》倒置,余无明显差异。又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馆藏号Sin 106-C)、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劳伦兹图书馆(馆藏号Rinuccini 24)、西班牙弗兰西斯卡诺·伊比利亚东方档案馆(无馆藏号)[3](P325-326),所藏者大致亦均为此本。此外,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尚藏有一部(馆藏号Sin 23),其卷前引言、诸图次序,断版漫漶之处,均与梵蒂冈藏本大致相同。但在全书之末又增出一图,上题“耶稣受难圣堂帐幔自裂”,下题“耶稣圣魂降临灵薄救诸古圣”,刻印风格与前图不类,似是后来补入。可见此当是一种稍晚出的增补本,但总体而言,仍应印于这一时期。
第二,清代初年。此时期印本,仍以梵蒂冈所藏三部(馆藏号Barberini Orientale 134.1、Rossiani Stampati 3476、Borgia Cinese 410)为代表。该本卷前无艾儒略《引》,全书亦五十七图,但自第十七图至第四十一图,次序与前本不同。与前本相比,此本断板处多能与之吻合而较严重。最明显者,如前本第二十六图《五饼二鱼饷五千人》,中已横断一道。此本为第二十五图,在横断的基础上,又损右上板框。由此可知,此本与前本实为一板所印。在清初重印时,因卷前引言中有明代年号而将其撤去,又调整诸图次序。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 Chinois 6751)、意大利西西里图书馆(馆藏号3275)、米兰Trivulziana图书馆(馆藏号B 752.7)等,亦有收藏。此外,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有一本(馆藏号MS 119),乃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寄归。该本阙《天主降生圣像》与《纳婴起寡婺之殇子》二图,诸图次序排列混乱。又日本东洋文库藏本,亦五十七图,然无第一图协露撒棱都城图,而多出前述巴伐利亚藏本之最末一图,图序亦颇错乱[4](P73-106)。但从断版的情况来看,此二本也都印于这一时期。
第三,清康熙年间。此时期印本存世较多,其中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三部(馆藏号BARBERINI ORIENT 134.2,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6.3、289.3)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馆藏号52-1049),诸图次序前后一致,编次合理,可作为代表。其签题“天主降生言行纪像”,卷前有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引》,然末仅题“远西耶稣会士艾儒略敬识,同会阳玛诺、聂伯多、瞿西满仝订”,而未署年月与刊刻地,字体亦与崇祯印本不同。全书五十一图,乃在清初印本的基础上又抽去六图,并略调整次序而成。此本的断板漫漶处,较前两个时期的印本更甚。如前二本《耶稣十二龄讲道》有横断一道,然仅自右至中而止。此本则自右至左,横贯板片。又前二本《救伯铎罗妻母病疟》,有极细之横断一道,至此本则发展成为贯通板片之明显断裂。但前二本皆损坏明显的《五饼二鱼饷五千人》,此本反而较完好。经仔细对比,细节与前二本有所不同,当是后来补刻。总的来看,此本当仍是主要利用旧版而略作抽换,并重刻卷前引言而删去明代年号。梵蒂冈藏本中之第二部,乃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2)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带往罗马,可知其刷印时间不会晚于此。此外还有一些编次混乱之本,主要包括:
1.梵蒂冈图书馆藏,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47.6。其卷前有艾氏《引》,正文亦五十一图,而排列次序颠倒错乱,各图上且有前人据清初印五十七图本对该本次序所作墨笔校正。
2.梵蒂冈图书馆藏,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47.7。其卷前无艾氏《引》,而有耶稣会徽章页,正文五十一图颠倒尤甚。以上二本皆为传教士康和子(Carolus Orazi de Castorano,1673-1755)捐赠。
3.梵蒂冈图书馆藏,馆藏号BORGIA CINESE 443.1。此本为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旧藏。卷前无艾氏《引》,正文仅四十三图,排列次序与前述具备代表性的五十一图之本基本相同,而阙其中《播种喻》至《起三十八年之瘫》、《预告宗徒受难诸端》至《以宴论天国谕异端昧主》共计八图。
4.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馆藏号Jap.Sin. I 187。此本无卷前引言,全书五十三图,《耶稣步海》与《起三十八年之瘫》二图重出,次序与五十一图本颇有不同[5](P527-582)。

以上各本所收诸图或多或少,或排列次序错乱。此或是因重新装订之故,但也有可能是重印时发生的错漏。由此推测,康熙二十一年或只是此本刷印时间的上限,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此本仍在不断刷印。另有部分传本未能亲见,如意大利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馆藏号72 C.653),据著录为五十一图[6](P40),当印于此时,但具体情况不详。
上述三次较集中的刷印,所印诸图虽有多寡,但大致仍为《出像经解》全书。约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又有人利用《出像经解》的部分书板,印制了一部新的著作《显相十五端玫瑰经》,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有藏。其书于《玫瑰经》十五节的每节之后,均附图像一幅,计有《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等十五幅[7](P263-293)。其经文部分可能为新刻,但此十五幅图像,其断板漫漶处与前述康熙间印本《出像经解》大都相合,特别是《耶稣十二龄讲道》中间横断一道全同,可知即是出于《出像经解》旧板。该本书名页题“泰西耶稣会值会德玛诺、同学毕多明我阅订”,按德玛诺(Romain Hinderer, 1668-1744),约于1706年来华,1721-1724年、1725-1729年任中国和日本巡按使[8](P187),即此本所题“值会”,可知本书当成于这一时期。又题“云间敬一堂梓”,敬一堂在今上海市,《出像经解》的书板,可能后来迁移至彼。
二、西学汉籍重印现象在明清时期的普遍存在
由上文论述可知,《出像经解》一书,约于崇祯十年在福建晋江刻成后,其书板经明清易代而仍旧保存了下来,至少在清康熙末年还在不断刷印。其集中刷印的时期虽大致有三,但每一时期并非只印一次,且还有抽印部分板片的情况,具体印行的次数可能远超想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书主要为版画,较受欢迎,需求量大,且翻刻也比较困难,有其特殊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反映出以旧版重印的行为,在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刻印中颇为普遍。
通观目前存世的西学汉籍诸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与《出像经解》的情况类似,刻成之后基本再无翻刻,存世诸本皆出自同一套印板。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所译《超性学要》即是如此。该书三十卷,又《目录》四卷,自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陆续在北京翻译刻印。今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一部全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04-211),字迹清晰,序言、目录、书名页等齐备,且编次合理,应是早期印本。此本为柏应理带归,而本书卷十一前题“柏应理、闵明我订”[9](P232),可见柏氏为本书订正者之一,故能拥有此早期印本。其余传本尚多,经目验者,即有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Chinois 6906-6909)、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138650)、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藏本,皆为后印本,部分版面漫漶不堪。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卷一第十三页正面一、二行“而知人福者未必知天主盖有多多人以财以乐以名等为福云”二十余字不可辨,三十二页正面大半不可识。此大约是因为本书卷帙较繁,且内容艰涩,读者不多,故无人翻刻,旧板尽管损坏严重,仍不得不用以刷印。至于三百余年后的民国时期,本书方有北平公教教育联合会与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铅印本,而其所据者,仍是前述后印本(1)按:据张金寿《论超性学要各版本之同异》(《善本书题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701-719页),北平公教教育联合会铅印本乃以西湾子天主堂旧藏本为底本排印。西湾子本今不知去向,但检北平本,其阙文处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全同,可知所据者必为后印本。土山湾铅印本据张金寿文,乃以徐家汇藏本为底本。徐家汇本今尚存,字迹多漫漶,亦为后印本。。另有一些著作虽有翻刻,然所据者乃后印之本。如意大利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著《圣教四规》,初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有藏(馆藏号Chinois 7217),书名页题“云间许府藏板”。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二部后印本,第一部(馆藏号BORGIA CINESE 324.15a)书名页已无刻板地,当是修去或作了撤换,但字迹尚清晰。第二部(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4.12)则无书名页,版面已开始漫漶,刷印时间较第一部为晚。梵蒂冈另有翻刻本一部(馆藏号BORGIA CINESE 324.15b),明显是自上述第二部后印本出,因本书第十页正面二至三行“必应守吾王耶稣所定之规”,初刻本与后印本之一皆同,第二部“守”字已残损,至翻刻本则“守”误作“官”。此必是据后印本翻刻时,因此字不清而致误。由此可见,本书当是刻成后在一段时间内经过若干次重印,方出现翻刻之本。当然,也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著作,出现后较短时间内即有多种版本问世。如西班牙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著《七克》,仅在明代后期即有至少三个版本:一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汪汝淳杭州刻本,后被收入《天学初函》。二为樊鼎遇四川德阳刻本,其本已佚,仅有樊氏跋文保存下来[10](P243),刻印时间大约与汪本相去不远。三为明末福建钦一堂刻本,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Chinois 7179)。至于清代,又有自钦一堂本出之康熙三十三年(1694)北京领报堂本。但尽管有如此之多的新刻之本,汪本于明末清初却仍在重印,似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且在清代也出现了根据重印本翻刻的版本(2)重印本与翻刻本今均藏梵蒂冈图书馆,详细情况可参见谢辉《陈垣校勘〈七克〉述略》,《汉学研究》总第26集,学苑出版社,2019年,第305-314页。。重印行为在明清西学汉籍刻印过程中的普遍存在和重要作用,也由此可见。
《出像经解》的书板在清代刷印时,因有所忌讳,故对带有明代年号的序言作了处理,或将其撤去,或予以改刻。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经历明清易代的西学汉籍重印本中亦有体现。例如,同为艾儒略所著《性学觕述》,于南明时在福建刻印。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馆藏号Chinois 3409),其卷前有朱时亨序,末题“丙戌春三月”,“丙戌”上空二格,且有修板痕迹,很可能是原有“隆武”二字而被修去,已经是入清后的印本,但书名页背面犹题“隆武二年岁次丙戌正月既望”。至于梵蒂冈图书馆藏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3.3-4),则在其基础上又重刻并抽换了书名页,删去“隆武”二字[11](P446)。同时,《出像经解》在重印过程中,曾调整图式数量与次序,并修补更换板片,此种伴随着内容修订与补板的重印也颇为常见,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调整内容。例如,前述《超性学要》,梵蒂冈图书馆藏较早印本有《目录》四卷,按照支、段、论、章四级,列出了全书详目。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后印本,则在详目前增出简目一种,只有支、段、论,而无论下各章之标题。如第一大支第一段第一论为《天学论》,详目此下有《性学外尚须有他学否》至《天学为辩驳之学否》五章标题,简目则无。此可能是因为详目太繁,故重印时别刻简目,方便检索。
第二,增补阙文。例如,意大利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著《真主灵性理证》,梵蒂冈图书馆藏清初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3.1)卷下第三十页正面,有七字墨钉:“三,天□□人□图荣名之□者,因宇内诸人有不识真主,亦不识人灵永存,□□□图荣名之心,□□进于善而退于恶焉。”[12](P291)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后印本(馆藏号Chinois 6931)则已将阙文补足,作:“三,天主予人以图荣名之性者,因宇内诸人有不识真主,亦不识人灵永存,故予以图荣名之心,使之进于善而退于恶焉。”
第三,修正讹误。例如,意大利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6-1640)所著《童幼教育》,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明末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2.3),卷中有不少朱笔校正讹误之处。如卷上《教之主第三》“为亲之爱,为邦之戮”,“爱”字改“忧”[13](P36),甚是。同为梵蒂冈所藏的后印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4.5)即将此字挖改成“忧”。
第四,修补板片漫漶处。例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天主实义》之后印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2.1-2),本书曾被收入《天学初函》,经对比,梵蒂冈藏本即是用《天学初函》旧板刷印者。《天学初函》本卷下第五十七页正面五至八行板片损坏,“为本业”、“最尊位”等字均有残损[14](P603),而梵蒂冈藏本此处即有修补痕迹。
此外,《出像经解》在重印过程中,板片曾有迁移,此种现象亦不少见。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庞迪我《七克》之明刻清印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3.1-7),乃用明万历间汪汝淳杭州刻本旧板刷印。而书衣多钤“敬一堂印”,并贴有刻印识语,末署“敬一堂识”。此敬一堂应即前述《出像经解》书板在清代的存放地,盖《七克》书板后亦由杭州迁至彼处,并于此刷印。
三、西方传教士对西学汉籍重印行为的推动
从中国印刷史的角度而言,《出像经解》等一批西学类典籍的广泛重印,在印刷事业发达的明清时期,本身并非十分特异的现象。但如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推究其背后的原因,便可发现,一部分明清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刊刻西学著作过程中,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原理已有清晰的认识,并主动地保存书板以供反复刷印。由此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西学汉籍重印行为的大量出现。
作为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利玛窦对雕版印刷术,即已有详细描述。其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记载:
他们最常用的方法是斫取一块梨木或苹果木板,板面要平滑无节眼。或取一块枣木板,把一张想刻的字或画反贴在上面,然后极熟练地将白纸挖下来。除要印制的字画部分之外,板上不留任何别的东西。接着,用铁制刻刀刻掉所有板边缘与字中的部分,要稍有些深度,为的是只凸出字和画的痕迹。最后,在这样的板子上想印多少张就可以印多少张[15](P16)。
从此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利玛窦不仅知晓中国常用的印书法为雕版印刷,且对其具体操作也比较了解,如在刻板前需先有写样,所刻之书板为阳文反字。利氏之后,其他来华的传教士对雕版印刷术也多有提及。如西班牙庞迪我谓:“每张书页使用一块板,上面排满双页的汉字。这种方法看似十分困难,但他们使用一套简单易行的手段完成,既省时又经济。”[16](P521)葡萄牙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则谓:“他们的字刻在木板上,作者可要求他想要用的字体,或大或小或中等;要么他把手稿交给刻印匠,按手稿大小制版,把手稿反贴在板上,然后按字刻印,极方便和准确,不致出错。他们印的书不像我们的有两面,只有一面,但他们的书看起来像两面刻印,其原因是,白的一面折叠在内。”[17](P43)与利氏相比,庞、曾二人进一步阐明,每块雕版所刻者为两个半页,印成后的书页自中间折叠,使有字一面向外,对利氏未涉及到的细节又有补充。
正是在对雕版印刷术具备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利氏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此项技术的一个优点,即可以比较方便地挖改并多次刷印。如利玛窦即说:
用他们的方法印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木板长期存在,什么时候想印刷都很容易,即使三四年或更长的时间后想要进行修改也不难,易一字轻而易举,同时改几行也只需裁接木板即可。因此,中国印制了大量书籍,任何人在家里都可以印书,还有相当多的人从事这项刻板工艺。当一部书的版刻好之后,印起来很省钱,就像我们某些人家里刻过的几部书一样,需要多少,家仆就能印多少[15](P16)。
类似的说法,在曾德昭《大中国志》中也有出现:“(他们大量印刷的)著作一直完整保留在木板上,可以随意重印,不必再花费什么,也不必再费力制版,像我们的印刷那样。”[17](P43)另有些传教士虽然所述不如利、曾二人清晰,但仍可窥出其对雕版印刷这一特性的熟悉。如法国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说:“(印刷用的)刻字木板是整片的,它们被刷子磨损后,就再刻新的。”[18](P284)换而言之,如果板片未磨损,就可以用之反复刷印,对这一点,马若瑟应该是清楚的。其在给法国学者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信件中,曾详细介绍过雕版印刷术[19](P59),通晓此理也并不意外。甚至一些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也通过传教士的介绍,明白书板可以多次印刷。如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即提到,尽管雕版印刷需要刻制很多板片,但板片一旦刻好,便可随时用于刷印更多部图书,而不必再行排版。即使在印制三四万部之后,仍可以通过修板,使板片使用更长时间[20](P373)。
在与中国士人交往的过程中,传教士出于传播天主教与西方知识的目的,常常要赠送其所译述的西学类典籍。故一些熟悉雕版印刷术特性的传教士,即有意识地将书板保存下来,随用随印。如利玛窦提到《天主教要》时说:
我们常把此书赠给那些有希望归信的人。这本书的印版在我们寓所,归我们所有。但除了印书所用的纸张外,我们就没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家中就有会印刷和装订的人。有一些教友和教外人士还给我们送来了优质的纸张让我们印书,并让我们把教理手册和我们的其他著作免费分发给所有人[21](P230)。
《天主教要》今传本多为后世翻刻,内容也有增删,利氏所述印本可能并未流传下来。但其记载的拥有书板、纸张与印刷工人,可以方便地刷印此书的情况,当属实情,且重印次数也应不少。类似的情况在当时颇不鲜见,如比利玛窦来华还要稍早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所著《天主实录》,刻成后大受欢迎,故“神父们又增印了数千册,使我们圣教的名声得以更快、更远地在对他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中传播”[15](P103)。这显然是因印板保存在其手中,故可以随时增印。今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有《天主实录》初刻本二部,一部印较早,另一部为修板后印[22],可证其至少刷印过两次。戴遂良(LéonWieger,1856-1933)曾引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之说,谓江南的传教士曾保存《天主实录》的书板并多次重印[23](P95-96),则由传教士主导的对此书的重印行为,可能远不止两三次。甚至可能到利玛窦《天主实义》出现并取而代之,《天主实录》方停止重印。而《天主实义》的早期刻本同样有重印现象。今日本内阁文库与意大利卡萨纳特图书馆,各藏有明刻《天主实义》一部。经比对,此二本乃一板所印,但卡萨纳特藏本有修板痕迹,乃后印本[24]。卡萨纳特藏本之后附有拉丁文手书十余页,学界多以为出自利玛窦之手,故此本即便非初刻,也是利氏曾经手过的早期刻本之一,此修板重印行为大约亦由其主导。
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保存西学书籍雕版并以之重印的行为日益普遍,并逐渐形成了以教堂为主的书板储存中心。以北京而言,德国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在明清易代之际,曾从宣武门天主堂抢救出“约三千卷的欧洲书籍,以及为印刷中国书籍所用之刻板”[25](P223)。这其中应包括《崇祯历书》的板片,故汤氏在顺治元年上清廷奏疏中即言“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26](P2045)。此套板片后经挖改增补,更名《西洋新法历书》,于清代重印。而道光二十年八月,清政府在北京正佛寺起获西学书籍板片多达一千五百余块,此批板片即清代前期北京耶稣会天主堂所刊刻并收藏者,至道光间屡次易手,且已被劈去烧火数千块[27](P106-107)。可见禁教之前教堂储存书板之多。又如,意大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于清顺治末年,曾在巡抚佟国器的帮助下,在杭州建立了一所教堂,并“请人修建了一个宽敞的房间,位于花园的一角以避免火灾,用来保存珍贵的木版。这些木版上刻有神父们许多优秀的作品,总价值超过2000两银子”[28](P177)。至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抚张鹏翮下令杭州禁教时,特意提出“毁教堂,破书板”[29](P357),由此可推测其收藏书板之规模。清代收藏《出像经解》与《七克》书板的上海敬一堂,也应是一处比较主要的板片储存地。传教士正是依托这些历代积累下来的书板,大规模地开展西学汉籍的重印、挖改、抽印等工作。
结 语

此外,因西学汉籍的重印极为普遍,故在此类典籍的版本鉴定中,应注意对重印本的甄别。目前学界对西学汉籍的版本鉴定较为滞后,或以其序跋所题著录“某某年序刻本”,或以其馆藏著录“某某图书馆藏本”,或笼统著录“明刻本”、“清刻本”甚至“旧刻本”。上文已阐明,以旧板反复刷印的现象在西学汉籍中广泛存在,甚至如《出像经解》般始终一板的情况都时有出现,故鉴定时应对是否为重印本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通过对现存诸本的比对,相当一部分传本不仅能知其为重印,且可考得其印行的大致时间,从而使其在版本序列中获得明确的定位,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