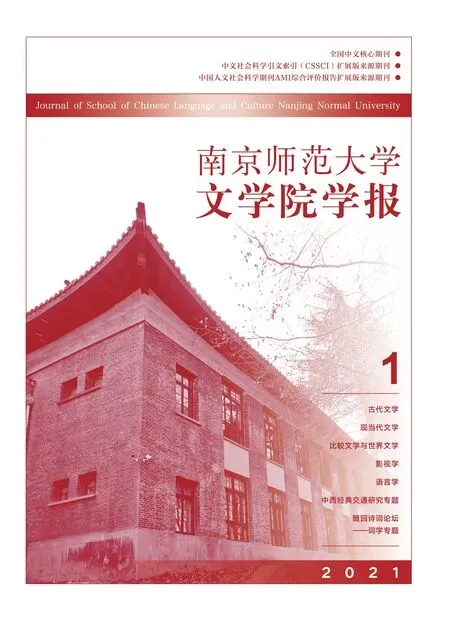里尔克对毕加索的凝视
——《杜伊诺哀歌》第五歌释读
赵山奎 朱程子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里尔克与毕加索《杂耍艺人一家》的缘分来得很巧。画作1905年完稿于巴黎,1914年底被荷塔·珂妮茜(Hertha Koenig)购入,私藏于慕尼黑的寓所。里尔克与珂妮茜交好,1915年6月11日,他致信珂妮茜借住她在慕尼黑的寓所,正是为了观赏毕加索的画作。[1](P243注1)据信件可知,里尔克共住了四个月,直至10月10日离开。[2](P144)持续的凝视终于留下日后可供琢磨的素材,《杂耍艺人一家》最后被里尔克写进《杜伊诺哀歌》(以下简称《哀歌》)的第五歌,而珂妮茜自然成了这一歌的题献对象。
《杂耍艺人一家》是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画作的特点是对于暖色的使用以及频繁出现的杂耍艺人形象。玫瑰时期上承蓝色时期,荣格(Gustav Jung)在一篇评论里分析过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画作,认为其中包含着鲜明的精神分裂症结,而画中的丑角(harlequin)则是毕加索沉向无意识的黑暗灵魂的变形[4](P132、136)。从蓝色时期到玫瑰时期,色调从寒到暖的转变显示出毕加索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但绝没达到痊愈的程度。在玫瑰时期的画作中,仍存在蓝色时期里的那类沮丧人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荣格的说法对这一时期的画作同样适用。《杂耍艺人一家》是很好的例证,画中表现了一个“丑角家庭”,而这些画中人的情态,这个艺人家庭的情态,完全符合荣格对毕加索蓝色时期画作的评价:散乱、无目的、无意义。
这正是里尔克观画时的精神状态。1915年对里尔克来说是一段消沉的岁月:他无法完成《哀歌》;他最初对一战爆发的热情业已褪去,自暴自弃地希望应征去澳大利亚服兵役;他发现激发起自己的诗兴越来越难了,同年借住珂爱妮茜寓所期间,他将大把时间花在会友、听演讲和看戏上,却极少写诗[5](P186-187)。里尔克对毕加索画作的浓烈兴趣,不仅出于对画作本身美感的赏味,更大程度上也由于它牵涉到他最为切己的生命体验。里尔克曾特别强调说,“杂耍艺人”自他头一回到巴黎以来即与他休戚相关,是他的一项任务。[2](P290-293)其实,早在1915观画之前,里尔克就对杂耍艺人有所“凝视”,八年前,也即1907年,他就写了篇关于杂耍艺人的散文。由此可见,这项“任务”长年占据着里尔克的心神。这项“任务”最终作为《哀歌》第五歌得以完成。第五歌对《杂耍艺人一家》的借鉴非常明显。其中,弥漫画作的无意义氛围和艺人家庭的困厄处境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但诗中还展现了画作中所没有的“超越”意味。第五歌的写作是里尔克对毕加索画作所映照出的他自身消极状态的一次克服性尝试。这一过程在第五歌里的演进是曲折的,其中,“无意义”和“超越”这截然不同的两极将展开持久的拉锯战。
一、无意义—超越
他们又是谁,告诉我,这些游走的,这些比我们自己还要飞逝些的[……](5.1-2)(1)表示第5歌,1-2行,引文及编号, 参见:刘皓明《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述评:文本、翻译、注释、评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

图1.
很奇怪地,起句就是一个关乎身份的问题,似乎不应该,因为里尔克当然知道他们就是杂耍艺人。这个问题的指向因此由外转内,直击“存在”这一大命题,因为艺人们“比我们/自己还要飞逝”。这里的“飞逝”首先指艺人们漂泊不定的表演生涯,其次指他们上下翻腾的演出状态。[1](P245)两者都提示着毕加索画中艺人模糊的生命存在意义,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是无根的流浪者,将生命耗在取悦观众上面。艺人表演生涯的这一特征,使他们跟“我们”都不一样。《哀歌》中,代词“我们”几乎都指代人类整体[5](P192)。这样看来,杂耍艺人“飞逝”的存在方式竟使得他们被孤立出了全人类,他们生命的存在意义比所有人都模糊不定,这确是非常极端的处境了。

图2.
对杂耍艺人存在状态的描绘,毕加索的画作更为触目(见图1)。画中,艺人们滞留甚至被囚禁在一片酷似沙漠的荒芜中间,天空和地面成一比三的比例,造成强烈的压抑感。艺人们虽簇拥在一处,却被隔在人世以外。画中有个灵异的细节:胖男子缺了右脚。而在草图(见图2)中,胖男子两足俱全。毕加索为这幅画劳作了九个月,不可能漏掉这一草图里本就有的细节。这里,除增添不祥的诡秘调性外,失踪的右脚更暗示出胖男子动荡的存在状态,而这一状态波及所有艺人:他们不稳固,他们都在“飞逝”。“飞逝”还体现在小女孩的右脚上,衬着周遭的沙土,这只脚看着似乎已变得半透明。[5](P190)沙漠的荒芜正侵入艺人中最柔弱的一个,而她对面那个扛鼓的男孩已彻底融入荒芜的色调,眼睛也陷进深重的阴影。
“飞逝”也体现在画中艺人模糊的状态上。他们脚踩芭蕾舞步,身着戏服,胖男子和他左边的少年肩扛道具,正是预备演出的姿态,似乎随时准备跃动起来。但其中又有着矛盾,因为他们迷离失神,彼此回避着视线,丝毫没有表演所要求的默契,况且荒芜里根本没有观众:他们表演给谁看?草图内,背景是赛马场和观众,艺人们站在高出赛马场的坡上。不论完成品里才添上的女子,着装上,只有壮年男子不同,他穿着一套旅行装束,暗示艺人们已结束演出。这一点到了完成品中则彻底模糊了:赛马场被沙漠景观取代,男子则从旅行着装变为演出打扮,我们不能确定艺人们的演出是否完成。我们还注意到,完成品中,胖男子没了笑容,头掉转向另一边,不再看着壮年男子,草图中那只营造出些微温馨氛围的狗也被抹掉了。荒芜的沙漠景致是艺人们真实处境的心理呈现,他们的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由观众的喝彩、掌声和赏钱赋予。但由于观众的失缺,艺人们的“存在”便成了一个问题,他们困在荒芜里,困在“飞逝”对他们自身存在性赤裸裸的追问中。画中女孩肩上的翼状坎肩强调了她逃离的愿望,但在她父亲与祖父,还有两个兄弟沉郁情绪的压迫下,这对羽翼颇具反讽意味,她右手撑住的花篮正是她内心理想的外现:美丽但不牢靠。
《哀歌》第五歌对艺人“飞逝”状态的追问与毕加索的画作有所不同,其中艺人打破了画中的静止姿态,得以灵活无滞碍地进行杂技表演。但他们的处境并未因此转好,反更加令人不安。为说明艺人们存在意义的缺失,诗中公然出现了一个非人的“意志”:
[……]这些从很早起就为
一个为了取悦于某个他、他却
从不满意的意志强行扭曲的人们?它于是扭曲他们
弯折他们,缠裹他们,旋转他们,
抛掷他们再抓他们回来;仿佛自润了油的、
平滑的空气中他们降落
在这张磨旧的、被他们永恒的
弹跳踏薄的地毯上,这张在宇宙中
失却了的地毯上。
(5.2-10)
原来,杂技演出本质上是为取悦一个不可见的、客观的、非人的“意志”,而它从一开始就没满意过。但艺人们真正的困境在于,连取悦行为——即杂技表演本身——都是那个意志的施为,它“扭曲他们/弯折他们,缠裹他们,旋转他们,/抛掷他们再抓他们回来”:艺人们不过是它用以自娱的傀儡罢了。“地毯”是第五歌的一个关键意象,因为演出就在上面进行。地毯框定了艺人的表演范围,其局限性同大开大合的杂技表演动作之间形成巨大张力,暗示着艺人灵活表演所展现的自由不过是戴镣铐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同样是这块拘定艺人的地毯,又给予他们的表演以超越意味,因为这是一块“张在宇宙中”的地毯。宇宙是时空的总和,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人类经验的认知范畴,是一个“超验”的场域。在和地毯一起失却在宇宙的同时,艺人以及他们的表演行为也分沾了这个场域的超验性,这样一来,我们似乎不好再说艺人们的存在是无意义或模糊的了。但问题是,那幅地毯为何忽然就张在了宇宙?“谁”张的?又是“谁”将艺人们掷入其中?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施为者,就只能是那个非人的“意志”。它操纵艺人表演是为取悦自己,将艺人们掷进宇宙,也属于它的自悦行为。“意志”既然能将艺人们掷进宇宙,说明它自身也是个超验存在。我们看到,由于这个超验客体的存在与护持,艺人得以分沾超验性。如此一来,艺人们的存在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超越意义。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意志”。他们陷于取悦一个不可能被取悦的“意志”的恒久苦差,在某刻终于获得报偿,被“救”出原本有限的时空。宇宙中的艺人们忧喜俱灭,超越了主观而达到存粹客观的层面(一如那个“意志”),好像太空天体,永恒运转在“人”的彼岸。这里的超越意味是毕加索画中没有的东西,“超越”在此获得了对“无意义”的暂时性胜利。但紧接着,里尔克笔锋一转,又回到毕加索画作中的“无意义”因素,显然还没说尽画中杂耍艺人的困境。
二、超越—无意义
而且还没到那里,
站着,就在这儿被展示:这个立定的
大写首音字母…,就连这些最强健的
男子们,为了逗乐儿,也一再总是被迎上来的
抓握翻卷起来,如同壮汉奥古斯特在餐桌上
手里的一个锡铁盘子。
(5.12-17)
这里描写的,正是毕加索《杂耍艺人一家》中的人物。“立定的/大写首音字母”指画中艺人们的站位:除右下角的女子外,他们恰好构成一个大写字母D。“还没到达那里”和“站着,就在这儿被展示”是对艺人们迁移和滞留状态模糊性的描述。[1](P246)联系上节诗,“那里”就是“意志”被满足的那个饱和点。我们看到,上节的超越意味在“还没到达那里”的讽刺力量里失了势:尽管艺人们被“意志”掷进超验场,但这无益于目的的达成,即满足那个“意志”。艺人们跌出超验界,回到5.14-17的现世杂技表演之中,继续面对存在之无意义的困境。5.1-12展示了超越感崩溃的情状:
啊围绕着这个
中心,这观赏的玫瑰:
绽放又凋谢。围绕着这
夯杵,这花蕊,这个沾着自己
绽放着的花粉的,结出了
再一次是无欢的假象果实,它那
从未意识到的,——最薄的表皮
熠熠闪光的淡淡地假笑着的无欢。
(5.18-25)
“观赏的玫瑰”即观众,“绽放又凋谢”指观众聚散不定的状态,或对观众音容笑貌的形象描摹。“夯杵”指画中穿方格戏服的壮年男子,对应D字母的垂直轴,这也是支撑构图稳定的主轴,暗示着作为最健壮者,男子是艺人家庭的顶梁柱。[1](P246)“自己/绽放着的花粉”指艺人演出时凭借戏服和动作散发的光彩与活力,但“假象果实”一说又否定了它的实在性,“再一次”使否定性扩散至艺人的整个表演生涯。“假笑着的无欢”则是对画作的忠实描摹:艺人们通过表演博得观众喝彩,看似丰满,实则是在上演着无意义。里尔克运用授粉的比喻形象化了这一观点:不论自花授粉的例子,绝大多数植物花卉都需沾上异株的花粉才能结果,所以沾着自身花粉而结出的,自然就是“假象果实”了。这层意思也能从里尔克对“花粉”(Blühenden Staub)一词的使用上看出。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诗-哲学”断章集就叫《花粉》(Blütenstaub),里尔克将这个词转写为一个逻辑上不成立的词“Blühenden Staub”,字面义是“盛开的尘土”[5](P194),这在生殖根源上就否认了果实的真实性。
对于毕加索画中的D字形构图,里尔克看到了更为本质的东西,他在原文中用以D开头的“Dastehn”(5.13)一词来暗示艺人们的处境。“Dastehn”一词直译为“站立着在场”,首先对应毕加索画中艺人们或是演出完成,或是准备演出的“动静结合”的模糊状态。[6](P200)其次,我们知道,艺人们在完成一小段表演时,往往摆出一个结束姿态,但这一姿态马上又会被打破,承接上下段表演。这就是5.40-57中艺人男孩在“坠落上百次”(5.43)间经历的“半休止”(5.46)。由此看来,“Dastehn”一词再次强调了第五歌开头艺人们“飞逝”而模糊存在状态。同时D也是Dasein(存在)一词的首字母,这样一来,“飞逝”、模糊的意味将直击主体,艺人们存在意义的缺失将更加明确。他们的存在意味在一定程度上也由这个家庭的完整性和内部成员对表演生涯所表现出的一致认同所决定。首先,他们本身就构成一道壁垒,抵挡着外部无意义的入侵(在画中表现为荒漠景观)。其次,只要艺人家庭内部对表演生涯表示出一致、哪怕不是那么高的认可度,便能产生“有意义”的内部认同,就会有家庭温情,就如毕加索玫瑰时期许多画作内展示的那样。但是这个壁垒由于女人的出离而开了缺口,这一弃绝性行为表明她并不认可表演生涯,她看着画外的荒芜,好像那反倒是她认可的东西,即存在的无意义,这无意义便从她打开的缺口处涌进艺人家庭内部。
这名离群女子最本质的属性在5.87-94中得到揭示,画中那顶标志性的帽子让她在这里变成一位名叫“死亡夫人”的女帽商。[5](P189)这一揭示直接给艺人们无意义的存在状态打上了“死亡”印记:
各样的空场,巴黎的空场,无终止的剧场,
在那儿那位女帽商,Madame Lamort[死亡夫人],
将地上不安宁的道路,将无尽的发带,
缠绕卷起,再从中新
织出丝绦、穗坠儿、花卉、绣徽、人造水果——
全都
不同的CFAR检测区域的协方差矩阵和MPWF检测量是不同的,估计得到的等效视数L和Fisher分布参数u和v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利用式(20)得到的检测门限是自动调整的,以此保证CFAR检测的恒虚警前提.
染上了假色,——都是为命运的
廉价冬帽准备的。
(5.87-94)
“空场”和“剧场”狭义解作艺人的表演场,广义解作“尘世生活”。这里,后者的意味明显更浓些。因为从艺人家庭中的离群女士到名为“死亡夫人”的女帽商,是从特殊到普遍,相应地,这一角色对无意义的提示也从先前的艺人家庭扩散至整个人世的范围。“无终止”“不安宁”和“无尽”都是消极形容,修饰无意义的生命,暗示它不过是个无实意的假象。女帽商在这里充当了命运女神一类的角色,她编织着的“道路”是“庸俗人生”的隐喻。“死亡女士”借浮世假象之丝织出的种种饰品,虽然光鲜在外,实质上也属于假象,“染上了假色”,准备装饰上“命运的/廉价冬帽”。命运借以御寒的居然是一顶装饰着虚假饰品的“廉价冬帽”,这样的御寒物显然不能保住真正的温暖,“虚假”的御寒物只能抵御住“虚假”的严寒,而命运真正的严寒仍然侵入内里。
此处,“无意义”又压过了“超越”。5.18-57充分展现了毕加索画作的影响,对画作中艺人家庭成员的形象进行了想象性扩写:5.26-32中敲鼓的昏聩老者,33-35中紧绷一身徒然得来的肌肉的男子;特别是5.40-57中渴望母爱的艺人男孩,他在希望落空的同时仍要承受高强度表演所带来的苦累和疼痛。艺人们虽进一步摆脱了画中模糊的静止状态,却深陷于无意义的困境。这一困境,诗歌通过由对画中艺人D字形站位的注意所引出的关于那位离群女士的暗示得到充分展现,她的本质身份在第五歌临近结尾处被揭示为“死亡女士”,在给艺人的生命存在意义打上否定标签的同时,也将“无意义”扩散至整个人世。在藉由“意志”的超验属性所获得初次胜利后,“无意义”反扑,在最普遍的“人世”范围内倾覆了“超越”。
三、无意义—超越
天使!哦拿着,采撷它,这株开小花的药草。
找个花瓶,养起它来!把它摆在那些尚未向我们
开放的欢乐中间;在可爱的瓮中
用花体的奔放铭文赞颂它:“Subrisio Saltat.[艺人的微笑]”。
(5.58-61)
写有花体铭文的瓮指草药罐,[1](P253)“艺人的微笑”向5.40-57里“盲目地,/微笑”(5.56-57)的艺人男孩,药罐的治愈性提示着他满含痛感的杂技动作(5.54:“脚跟的烧灼”)。根据花粉联想一节(5.20-25),“艺人的微笑”作假象解,而假象似乎不可能有治疗作用。但我们得考虑到这里首次引动的《哀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天使。《哀歌》的语境内,天使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使,而是已经完全转化为“宇宙类”的“本质”性存在(2.14中称之为“本质成就的空间”),凭借宇宙整体去感觉。[7](P213、224)换言之,《哀歌》中天使已不是权柄持有者上帝和信徒间的“中介”,而是权柄的直接持有者。宇宙贴近天使的感官,是它感受的空间,所以天使是属于“宇宙”这个超验场的存在。这么一位大能的存在者采撷了艺人男孩的微笑,其珍贵性和治疗作用毋庸置疑。这微笑反映艺人男孩过早就承受了生活的苦难,睁着一双噙泪的眼睛。除了痛感,泪中更有男孩对母爱的渴望:这是爱的眼泪,包含着“真”的成分。此外,艺人男孩尚处于童年阶段也是促成天使现身的原因。里尔克认为,儿童能把握住神[8](P36),也就是说,童年是跟超验接通的。因此,艺人男孩受到天使眷顾,噙泪的微笑成为和结出“假象果实”(5.23)的“观赏的玫瑰”(5.19)对立的、具有治愈“无意义”效果的“开小花的药草”。和艺人男孩形成对比的,是以《杂耍艺人一家》画作中女孩为原型的艺人姑娘,她满足于“丝绦”(5.65)和“绿色金属般的丝绸”(5.67),而这些正是女帽商“死亡夫人”织出的虚假服饰。她还进一步满足于假象,享受着无意义表演所带来的“无限宠幸”(5.68),因此被“最销魂的欢乐”(5.63)——即天使的宠幸——“跳跃过去”(5.64)了。
其实天使在这里现身一点也不突兀,我们从它的“超验”性上已有所预感。事实上,第五歌起头天使就在场了,它正是操控艺人的“意志”。于是,前面降格为庸俗观众的“意志”又升格回它的地位并坦露了真正身份,前面结出“假象果实”的“观赏的玫瑰”(5.19)也变为具有治愈“无意义”的“开小花的药草”。这药草被天使采撷,养在瓮里,被摆在“那些尚未向我们开放的欢乐中间”。“那些尚未向我们开放的欢乐”指向超验界,那是天使放任自己的美洋溢的地方。如此一来,前面被界定为无意义的表演最终还是被赋予了一定意义,艺人们用纯粹运动所取悦的客体现身说法,部分(到第五歌末节,“部分”将突转为“全盘”)肯定了他们“反复”的效力:艺人男孩的微笑被天使采撷,成为具有疗效的药草,而且一般人无法获得。那些能获得它的“不一般的人”,只能是向艺人男孩那样包含着爱意苦苦侍奉“意志”的艺术家,而它治愈的病,就是无意义的存在处境,这一处境被在“死亡夫人”那一节中(5.87-94)被扩大至整个尘世和人生。在此,里尔克借杂耍艺人探讨了艺术家(也即他本人)的处境,以及艺术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只有反复取悦一个似乎不可能被取悦的、纯客观的、超验的“意志”,才可能越过临界点,受到艺术的回馈。这或是罗丹给予的启迪,里尔克从他那儿体验到创作的本质及其永恒意义[8](P13-14):即一种“艺术的”生活模式,里尔克在一篇关于罗丹的演说词中提到,工作占据了这位雕塑大师的所有生命(后来塞尚吸引里尔克的也是这点)。[9](P167-168)只有通过这样高强度的奉献,艺术家自身才可能像那只被天使捧进超验界的草药瓮一样,也成为具有疗效的艺术品。
到了第五歌末节,一直维持着的艺人主题似乎发生了断裂,因为艺人忽然不见了:
天使!但愿有一个广场是我们所不知的,在那里,
在那不可言述的地毯上,那对恋人儿,那对在此地永远
也达不到能够的,会表演他们令人心脏为之悬起的
种种大胆高耸的造型,
他们由快感成就的楼台,他们久久的,
因为根本没有地面,仅倚架在
彼此身上的梯子,颤抖着,——而能够了,
在围拢的观众面前,无数无声的死者:
那么他们会把他们最后的、一直储蓄着的、
一直秘藏着的、我们不认得的、永恒
通用的幸福硬币扔到那张满足了的
地毯上那一对儿终于发自内心微笑着的
情侣脚前吗?
(5.95-107)
杂耍艺人的消失是个突然事件,但与此同时,有关艺人的一切都在延续:广场、地毯、演出和观众。唯一的差别是“艺人”换成了“情侣”。其实,一如“意志”和“天使”是对等物,“艺人”和“情侣”也是对等物。情侣的现身源于有关性的联想,在诗中有多处或暗或明的提示:5.20-23中可以归入性的范畴的授粉和结果;写到那名作为花蕊的男子时,诗中用了“夯杵”一词,或在喻指勃起的阳物;[1](P248)公然的性联想出现在5.74-76,艺人们的杂技配合和过程中调整身位的细琐动作被比作交配的动物。有了这些性联想作为铺垫,末节中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性欲主体——情侣——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当“艺人”和“情侣”成为对等物时,两者和“天使”也成了对等物。这在第四歌中就已点明。4.52-57中,一位“观众”在戏台前观看傀儡无意义的演出,在某一刻,忽然“一位天使/扮成演员冲过去”,扯走傀儡的壳套并参与进演出。当天使抓起傀儡的外衣自己穿上,傀儡就不再是傀儡,而是天使或天使与傀儡的合一。[1](P239)“傀儡”是这一歌中的重要意象,而它正是第五歌开头被“意志”操纵的艺人的对等物。所以,天使和艺人是对等物。由此可见,这段诗描绘的并不是纯粹肉感的性欲,其中,情侣展示的性爱非比寻常,有明显的超验意味。在里尔克看来,执着于某一固定爱情对象的爱情终是局限,完美爱情应是主体的延伸,向更大的空间开放:被爱者应被废除,人要一直成为爱情主体,而非交互的一方。[10](P101-102)第五歌开头,“艺人”是受“天使”的对等物“意志”所操纵的傀儡,因为他们尚处在“永远/也达不到能够的”(5.96-97)此地,对应交互式爱情“被爱”的一方。但在此处,蜕变为“情侣”的“艺人”已位在“达得到能够”的彼处,即“天使”所在的超验场中。这时,交互的模式就打破了,天使披上傀儡的外衣,“艺人/恋人”同“意志/天使”相合为一个单体的“爱者”。最后这段诗描写的正是里尔克所认可的完美爱情,是在超验场内进行的性爱[1](P257)。情侣以“快感”搭建超验性爱的空中纪念碑(“由快感成就的楼台”),不假外物,彼此以为阶梯向上升攀。情侣的超验性爱甚至有宗教仪式的效用,能从围拢的观众体内召出死者,令他们成为兼有生死的“还魂者”。在里尔克的“哲学”里,生死并非对立,而是个“连续统”[1](P198)。在答波兰译者信内,里尔克说对生与死的肯定在《哀歌》中显示为同一件事,而真实的生活延伸进这两界,这其中,天使自如地存在着。[1](P362)没有经历过死的生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天使”则“常常不会知道,它们是跻身/于生人还是死者中间”(1.82-83),生与死的界限对“天使”来说并不存在,因为它就存在于由生和死构成的连续统之中。上文已经讨论过“天使”与超验界的密切关联,它正是超验界的存在,因此这里涵括生死的“连续统”即指超验界。和“天使”一样,“还魂者”也是超验界的存在,恋人们从有限(仅作为生人的观众)中召出无限(兼有生死的观众),终于令“观赏的玫瑰”(5.19)成为“超验的玫瑰”。与5.20-25中结出“假象果实”的授粉相对,这是一场结出“真果实”的授粉。这里,情侣具有了5.59-61中天使的大能:天使携“艺人的微笑”飞升入“那些尚未向我们/开放的欢乐”,情侣也提携观众体验了一把这些“欢乐”。跨界后的“情侣-艺人”成为人与天使间的灵媒,向凡俗开示超验界的智识。当这一转化告成,在第五歌末尾,情侣,连同他们的另一身份——艺人——一起获得了休憩。他们的反复运动告一终结,那张被“永恒的/弹跳踏薄了的”(5.8-9),“在宇宙中/失却了的地毯”(5.9-10)终于和他们一起“满足了”。这是“超越”对“无意义”在顶点处的完胜,“从不满意的意志”(5.4)终于被取悦;5.13中还未达到的那个点终于达到了。
结 语
第五歌在“超越”对“无意义”的胜利中宣告结束,里尔克对于毕加索画作的“改写”也告以终结,迎着画作无意义逆流,他抵达了完全是超越性的终点,第五歌就在一场盛大的喜乐消歇下之后那恒久延续着的完满氛围中结束。——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能忘记最后整一节诗的生成前提,它伴随着一个祈愿者对天使,也即对超验的直接呼喊开始,我们可以将他同里尔克本人不完全地等同起来, 他的呼求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里尔克的愿望。“但愿”(5.95)以下都是这个祈愿者的美好设想,那个“我们所不知的广场”(5.95)压根就不存在;那场超验的性爱也没有发生。事实是,这段呼求前的“死亡夫人”才给第五歌作了一个异常消极的总结。而对里尔克来说,事实则是,在1922年完成《哀歌》与《商籁致俄耳甫斯》后,他就此搁笔,几乎再没新的创作,终于1926年末患白血病逝世,年仅五十一岁。直到死前,生命对里尔克来说仍是令他困苦不堪的难题。[10](P83-84)这不由得又引起我们对于生命之无意义的思考。事实上,里尔克本人对此是很清楚的,在写于1908的《祭一位女友》中,有这么一段:
[……]对于每一个将血液
提升到一个必将漫长的工作里的人,
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不再将血液高举,
血液依照自身的沉重而行,毫无价值。
因为一个古老的敌意在某处
存在于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10](P809-810)
“古老的敌意”即指生活的平庸本质,它就是滋生“无意义”的土壤。这段诗或许道出了里尔克的创作机制:必须要有一种“跃升感”助力,作品才能诞生。实际上,里尔克的工作并不漫长,除去搁笔的滞留期,他的重要诗作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由此可以推测,作为写作动力的这种“跃升感”,很可能脆弱而不持久,因为它是带有“自欺”性质的幻想,在现实“古老的敌意”中频频失灵。第五歌末节便是“跃升感”达到最高强度时所产生的美好设想,被那个祈愿者呼出,其假想意味几乎被祈愿的强度遮去;但诗节又以疑问结句,加以提示:这一切果真可能吗?能或不能,超越或无意义,构成第五歌的思辨张力,乃至整首《哀歌》的思辨张力,因为《哀歌》也正是以一个祈愿者对天使的呼求为开篇:
谁,若是我呼求,会从天使的班列中
听到我?[……]
(1.1-2)
天使无非是这个祈愿者的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