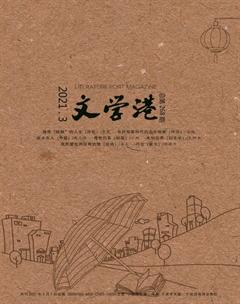好戏如佳人
储劲松
在青阳听青阳腔
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
最近两年,我三次到皖南的青阳县,也三次到陵阳镇,这个在春秋时期即为江南名邑的小镇子,有徽墨歙砚的静逸气,清婉淋漓的水气,也有梨花入井栏的人间烟火气。传说古之仙人陵阳子明于此地得道成仙,镇子因而得名。仙人的居所,自然是上佳福地,陵阳镇往古来今富贵安乐,每次来都生欣羡之心。镇上的谢家村却是第一次来,走在被脚板磨得发亮的青石路上,看瓦舍人家古祠石狮,如入南朝深处。
村子以谢为名,因为村子里的居民是东晋名将谢石的后昆,村中谢氏宗祠里就供奉着谢石的塑像。他是谢安之弟,曾与侄子谢玄、谢琰等人,以八万精兵大破前秦苻坚百万之众于淝水,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但风流二字作何解释?众人论说纷纭,也多遐想。我以为当作“江左风流”来解,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江南“旧时王谢”两家历时五朝,不单功勋卓著权倾朝野,而且文采风流名公辈出,谢家村的风流,当指风度、气韵和文采。
村子古老而安静,皂角树千柯万叶如此地谢氏人家。风从村庄背后的九华山来,簌簌吹人衣衫,凉意自两腋生起,以为将要长出翅翼,化作田間的一只白鹭。在村头溪边看见几树桃,几树毛桃仍青涩,如少年胡须初绒绒,一树五月桃已七八分熟,淡绿养眼,桃尖一点嫣红如美人臂上守宫砂,端的婉媚风流。有人说,那是美人尖。
忽然想起昨夜听青阳腔小戏《美周郎》,那扮小乔的青阳女子,眉梢上的风情娇娇俏俏,亦如桃尖一点红,戏台上的周郎,虽然姿貌稍欠英武,慷慨恢廓和风流蕴藉仍直追“公瑾当年”。
很早就知道青阳腔,乃因吾乡名戏岳西高腔为青阳腔遗脉,与之有戏曲流变和文化传承关系。
明代中叶,中国戏曲中的南戏,在民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明传奇,名家名作辈出。嘉靖年间,余姚腔和弋阳腔流传到池州府青阳县一带,与青阳方言、土戏和民间音乐结合形成青阳腔。到了万历年间,青阳腔红遍江南江北,人称“徽池雅调”,又与昆山腔并称“时调青昆”。所谓时调,时兴的小调小曲,足见其风靡的程度。明末清初,青阳腔传入与池州一江之隔的岳西,本地文人组班结社,请专人教习,并将其与本土民歌小调相融合,孕育出岳西高腔。岳西高腔生根并活跃的主要土壤是民间灯会,其戏曲文学、戏曲音乐、表演艺术和基本活动形式都自成体系。至今,岳西民间仍有十多个高腔剧社,县里有高腔传承中心,戏曲学者还整理出版了厚厚两大本《中国岳西高腔剧目集成》和《中国岳西高腔音乐集成》,搜寻到众多珍贵的高腔词曲古抄本。
少年时每逢过年,岳西城乡都有灯会,从正月初一一直演到上元节,高腔戏是灯会的保留节目。只是我那时懵懂无知,无论是黄梅戏、高腔、京剧、昆曲、梆子还是山歌,一概是催眠利器。看戏或者说听戏,是需要年纪的,阅历渐长人生渐老,渐渐能听出戏味,渐渐也能入戏了。有一年在剧团看黄梅戏《小辞店》,至殉情那一段,柳凤英“一见坟台珠泪洒”,我不知不觉泪满眼眶,心也如伊似刀挖。有一年在绍兴沈园听越剧《沈园情》,飘飘然以为身在天上人间。有一回在固镇垓下,听皖北人唱淮北大鼓《战垓下》,以为有风云之气萧杀之声。有几回看岳西高腔《拜月记》《龙女小渡》《天官赐福》,身上像有百虫一齐抓挠,很想穿上戏衣在戏台上扭捏念唱一番。
听一听岳西高腔源头的青阳腔,是我的一个心愿。此次来青阳,托同道诸师友之福,终于在青阳腔博物馆小剧场里看了一回。青阳腔戏歌《画里青阳》、青阳腔表演唱《拜月》、九华民歌《乔木的菊花会说话》、青阳腔小戏《美周郎》里,都有熟悉的声腔熟悉的味道。尤其是压轴戏《美周郎》,周瑜与小乔新婚之夜相互试探、相互表白的一场戏,让同行诸君和我大受感染。
华堂瑞霭烛摇光,画屏巧绣凤谐凰。百年好合的大婚戏够传统够古老了,千百年来戏人不知道演绎过多少回,“小乔初嫁了”,更是古今人熟得不能再熟的陈年故事,青阳腔《美周郎》却古韵翻新声,听得人心儿拎、肠儿颤、眼儿热。
一个扮相闭月羞花欲迎还拒,莺莺燕燕地唱:“我恋那卿卿我我长相守,夫唱妇随琴瑟和同。我不要那打打杀杀,争霸天下的英雄。家家太平九州安宁,才是我的梦。”一个扮相倜傥风流自负文武全才,大马金刀地唱:“罢罢罢!她若是弱不禁风小女子,燕雀心胸又怎能伴大鹏搏击长空?周瑜不愿玩世不恭,宁缺毋滥不要木俑。”
明知是戏,是男女调情忸怩作态,心里眼里却都在泛潮。
戏唱到末了,周郎小乔两情相悦你侬我侬,小乔纵身投入周郎怀中,那周郎来了个结结实实的公主抱,插科打诨惹人发笑。正经戏台上不可能有的情节,说是荒诞不经也好,谓之神来之笔也未尝不可。
演员谢幕的时候,我转头看邻座的魏振强兄,他还沉浸在戏里出不来。后来他说,那晚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和优雅。
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人生不如戏精彩,不如戏风雅,也太拖沓太混沌,爱恨情仇是非成败都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水里。这几天重翻庄子《齐物论》,至罔两问景和庄周梦蝶两个桥段,以为庄子是个戏精。他看得通透,演得绚丽。
在青山之阳,九华山麓,青阳雄健又灵秀。我到过青阳很多地方,喜爱这里的清美山川、幽邃村镇、淳古人情和文章元气,也爱这里戏台上的青阳腔,以及当地友人所说的青阳腔。他们的乡语有吴音亦有楚风,温婉、柔软而内敛,像《美周郎》里的念白。
在青阳,富贵的不止陵阳镇,风流的也不止谢家村。
听 戏
寒雨接连下了好些天,日夜沥沥如嫠妇,不下雪怕是不得晴了。雨滴持续砸在塑料遮阳篷上,哐哐,砰砰,硿硿,像小区拐角那个雄武屠夫操刀剁大骨,耳膜里轰隆震颤如案板,嘈杂无趣得很,夜里听来更觉得兴味索然。
想起少年时冬季在故园听雨:木格子窗外雨亮如蛛丝,黑松、毛竹和刺杉经雨水一洗,越发显得精神也越发苍翠养眼,草垛如黄袍老僧在山坡上打坐参禅,掉光了叶子的木梓树枝杈瘦劲如铁画。冬雨都不大,筛在鱼鳞瓦上,细细碎碎的声音幽闲而绵软,像村里的女孩子们说悄悄话,又像众多蝽象列队旅行,好听也耐听。荷尔蒙在体内噼啵燃烧的青春时代,除了上个清闲的班,似乎一年到头我都无所事事,也似乎总是郁郁寡欢,大把的青春、力气和雄性激素无处挥霍。水寒山老的冬天尤其感到幻灭和寂寞,下雨天就坐在东厢房的写字台前,看雨水从瓦沟里慢悠悠地落下来,滴到院子边沿的一溜水宕里,叮叮然,嗒嗒然,水宕里的水泡陆续鼓起来又依次破裂。雨声小的时候,常常会听到邻家程奶奶的收音机里,隐约传来锣鼓铙钹的声音,以及装腔作势啊啊呀呀的戏文。记得当年我写诗,在习作里曾经这样写过:
寂寞是冬日的雨丝
忧伤是雨点里的戏词
程家奶奶瘦小而清秀,识得文断得字,七十多岁了还戴着老花镜坐在天井边的小马扎上,津津有味地阅读《三国演义》和《海上花列传》。她有一只袖珍收音机,平素从不离身,听广播剧《西游记》,听单田芳评书,尤其爱听戏。听戏并不稀奇,当年村子里的大人都爱听戏,听的是本乡本土的采茶调,也就是黄梅戏,男女老少也都能唱几句《打猪草》《王小六打豆腐》《夫妻观灯》《女驸马》。但程家奶奶听的却是高大上的京戏,《智取威虎山》《霸王别姬》或者《锁麟囊》。这些足以把她与村里其他只会东家长西家短儿女如何如何媳妇如何如何的老奶奶区别开来。她是大户人家的闺秀出身,卧房里藏着一对玉镯子,几十块袁大头,均用绸布包着,还有十几个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罐子,里面装着粗盐、冰糖、霜果、云片糕、菜种子和豆种子。我和她的孙子是发小,所以我都见过,然后悄悄告诉了父母。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富家有旧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从程家奶奶那里得到的直接教益,一是人要读书,二是知道除了黄梅戏之外,还有一種戏叫京剧。
童年时心如麻雀叫喳喳,少年时心若野马哒哒哒,都是极不耐烦听戏的。戏台上的人,穿那样洇红滴绿可笑古怪的服装,涂那样白一道黑一道紫一道蓝一道的大花脸,拿鞭子当马骑,七八个人冒充百万雄兵,走三五步当作打遍天下,木头做的棍棒刀枪上戳下戳左舞右舞就算恶战了三百回合,甩着水袖捏着嗓子假模假式地说白,拖着极长尾音的忸怩唱腔半途像要断气似的,这些统统无趣得很,咭咭哐哐、咚咚将将、仓才台台的音乐尤其聒噪,比乌鸦叫还难听。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大人们都听得如醉如痴如泣如慕,就连拖着两挂鼻涕说话都不利索的二傻子,也抖动着嘴唇跟着鹦鹉学舌。
但在我的童年时代,对乡人来说,听戏仍然是一件大事,是开洋荤。
当年,吾乡岳西有一个黄梅戏剧团,团里好几十号人物,导演、编剧、作曲、演员、舞美、乐队一样不缺,是安庆地区人才最齐全的县级剧团之一。剧团就设在县城十字街的中心地带,一大片仿古木结构建筑,既古色古香又鹤立鸡群,把它周围那些砖混结构的破败民居全部压了下去。剧团不单有山城最高级的房子,也是本县的文化中心。里面有一个大剧场,两层看台,二层是木阁楼,总共能容纳千把人。戏台很是宽大,地上铺着木地板,唱武戏时演员把舞台踩得轰隆轰隆一片子响。舞台左右厢里,藏着拉胡琴、敲锣鼓、吹笛子的乐队,演员像变戏法似的出出入入,幼儿时觉得特别神秘。
那个戏台上,严凤英、王少舫演过《天仙配》,马兰演过《红楼梦》,韩再芬演过《女驸马》,黄梅戏的三代代表性人物都曾经在这个台子上粉墨登场,引发一次又一次轰动。一直到今天,曾经看过他们演出的乡里人仍然引以为荣,说起那时百村上锁万人空巷看戏的事情,眼里有无限向往,心中也生出许多惆怅。
我幼年的时候,乡下实在穷得很,穿破衣烂衫不说,粮食也不够吃。男女老少肚子里无非园蔬、红薯、芋头和野菜,在南方已经生长了几万年的大米平常很难吃到一顿。红烧肉只有过年时才有,切成斧头脑一样的大块头,谓之“斧脑肉”,三五块堆放在蓝边老海碗头上,下面垫着干茄子、豇豆角或者腌菜叶,家境稍好的人家也垫黄豆。那肉藏在竹碗柜最里面,来了拜年客才端出来。切得大不是因为慷慨,反而是因为寒酸,除非不识相的人,谁会打“斧脑肉”的主意呢?饭桌上,虽然主人家一直在殷勤相劝:“吃肉哇吃肉哇,莫客气,莫见外!”客人被劝不过,本来在夹青菜萝卜的筷子终于犹犹豫豫地举到肉上头,一两寸距离,停一两秒,然后坚决地拨开肉,搛下面被油润过的干菜吃。来客里若有小孩子馋不过,不小心搛了一块肉吃了,主人家表面上波澜不惊,心里肯定咯噔一下:坏了,哪里找另一块肉补上缺呢?孩子的父母则面红耳赤,恨不得地上忽然裂开一条缝,自己好钻进去,因为孩子没教养,就等于父母没教养。那时候的人虽然贫穷,却是要脸的,有廉耻。所有人包括三岁小孩子都明白,那肉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吃的,古代有看鱼下饭,我们当时是看肉下饭。饭吃完了,斧脑大肉完好无损,主客都如释重负偷偷嘘一口气。后来我上小学,在语文课本上学到“心照不宣”这个新词,脑子里闪现的自然不是“心照神交,唯我与子”,而是污垢满面的饭桌上那一碗“看肉”。
长年无肉吃,嘴里不只是淡出鸟来,而且淡得冒酸水。不过没有人有怨言,因为家家户户如此。那时候村民组一二十户人家,谁家有几只腌菜缸几只陶瓮子,放在哪个角落里,别人都是清清楚楚的。贫寒不是顶可怕的事,可怕的是富足之后被荤腥喂养得过分膨胀的贪婪之心。物质上贫困,精神上也贫乏,偶尔去县剧团听一场戏,或者村里放露天电影,就算是饕餮盛宴了。电影不常有,一年最多一两次。宽白的屏幕下午就挂在大操场上,被风吹得微微地鼓起来,像一道招魂摄魄令,惹得全村的人以及远近几十里的乡亲魂不守舍,黄昏时就扛着板凳竹椅候在屏幕前面,等待放映机的那一束幽蓝的光呈放射状打到银幕上,里面出现风景和人物,上演和素常生活完全迥异的奇妙事件。看一次电影算过了一次年,而且是杀猪烹羊的肥年。我记得村里放过的电影,除了抗战片,还有《刘三姐》。剧团倒是经常唱戏,但看戏是要花钱的,除非安庆来了名角儿,或者上演新戏,乡亲们才舍得去听一场。
有一年寒冬,天下着大雪,剧团新排的一部戏首次上演,似乎是《西楼会》,要么是《碧玉簪》,村里的老少大清早就相约着晚上去听戏。我们家离县城不远,三四华里,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机耕路直通城中,路两边是水田和溪流。天黑得早,胡乱煮一锅南瓜蒸一锅红薯吃了,一队人马在竹林窝路口集中后,个个举着葵骨火把,用稻草绑住脚上的解放鞋来防滑,浩浩荡荡向剧团进发,人人心里也有火把在燃烧,郎里个郎,浪里个浪。大人们确凿是去听戏的,听的是门道,孩子们纯然是凑热闹,何况大人还早早就许诺给买瓜子糖果吃。
那天的戏主角是谁,唱得如何,何时开演何时谢幕,我第二天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知道戏台上花团锦簇热热闹闹,戏台下人头挨着人头好比冬天地里的萝卜。只记得戏开演之前,照例有剧团杂务打着手电筒挨个查票,对逃票混进来的毫不客气地撵出去,双方争嘴吵架,另有调皮的逃票者与杂务满场兜圈子,死活不肯出去,好笑得很。
我不是去听戏的,是去戏耍的,也是去睡觉的。正戏开演之前通常有小丑上台暖场,那小丑蒜頭肉红鼻子,上面刷一团石灰,两腮涂着胭脂红得像猴子屁股,他在台上不停地翻斤斗,挤眉弄眼,一番杂耍百般搞怪,惹得观众喜笑颜开。暖场之后,小丑打恭作揖退出舞台,正戏开锣了,戴方巾拿纸扇的小生和穿绫罗绸缎甩水袖的正旦甫一亮相,才唱了三五句戏文,那些台词就幻化作一群瞌睡虫子,嗡嗡营营地飞上了我的头。旦角生得再美,生角长得再俊,都勾不起我的一点兴致。剧场里真暖和,比家中四壁漏风的泥巴屋要舒适多了。
半夜醒来的时候,在父亲的臂弯里,一队人马仍然打着葵骨火把回村,纷乱杂沓的脚步把地下的积雪踩得吱吱响。我手里还紧攥着两颗舍不得吃的水果糖。
第二天,几个昨夜听过戏的发小聚在竹林里打雪仗,然后坐在草垛下谈论那场戏。平素,连坦克能不能爬上直立的悬崖,母鸡吃蚂蚁会不会死,我们都要争得面红耳赤,但那天大家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小丑好戏,斤斗翻得好,说的话惹人笑;正戏一点都不好戏,什么才子佳人,什么出将入相,全都是假的,远远不如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过劲、来事。好戏、过劲、来事,均是吾乡土语,意思大致是:好玩、牛逼、有意思。
县剧团也出过好几个本地过劲的名角儿,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那十二分的风光可不是假的。许多人从百里之外的乡下,带着干粮爬山涉河徒步赶来,就只为亲眼一睹他们舞台上的风姿神韵。假若上厕所时碰巧遇见演员本尊,回到家是可以夸耀很长时间的。若是有人有幸嫁了或者娶了其中的一个,简直是齐人之福,必遭大众艳羡和妒忌。
后来我工作了,接触过当年的几个本地名角儿,虽然黄梅戏风光已经不再,剧团也解散了,他们作鸟兽散,有的进了文化馆,有的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有的下海经商,有的靠卖早点、开饮品店谋生,但言谈举止之间,仍然戏味十足。好比写文章的人一辈子都有写作的情结,唱戏的人即使离开了戏台,他们依然是戏人。只是没有戏台的戏人,神情是落寞黯然的。这些年各地都重视城乡文化建设与发展,列入民生工程,当年的角儿最年轻的也接近花甲之年,城乡文化的再度繁荣让他们再次找到了位置,担当起培育新人的任务,有时县里的大型演出他们也登台表演。偶尔和他们闲聊,谈起剧团和他们自己的前世今生,也像戏一样。
剧团其实还在,或者说,剧团的房子仍然还在,只是早就被一把锁锁住了,灰扑扑地夹在琼楼玉宇之间,仿佛卑微的仆役。剧团解散后,剧场作过几年会场,县里的两会和三干会都在里面开。再后来,被鉴定为危房,会也不能开了,于是干脆关了门。因为处在老城区的中心,那一块还是非常繁华,毗连剧团东门的那条一两百米长的剧团巷,成为美食一条街,南北风味汇聚,整天整夜热气腾腾食客满座。昨晚饭后,我散步经过那里,想起当年进城听戏的事,恍然如梦中,耳边依稀还传来啊啊呀呀的戏文。
许多年里,我还是不听戏,还是像少小时一样听不进去。忽然到了中年,有一天夜里读书时,为了找个伴,无意中点到了网络上的戏曲按钮,是昆曲《牡丹亭》,姑且听之,然后一直听到入睡前,觉得其间滋味好,其间好滋味。第二天清晨醒来,又打开手机听大弦子戏。从此以后,伴我夜读伴我晨醒的,不再是流行歌曲,而是戏曲。戏比歌妙,水袖舞、小脚点、纱帽闪,皇亲国舅、小姐书生、市巷托钵僧“乞我一文大光钱”,戏文里尽是人间兴味。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李渔要写戏、唱戏、办戏班,为什么唐玄宗李隆基要在听政之暇亲自教授太常乐工丝竹之戏,为什么《红楼梦》里一再写到唱戏、听戏、梨园弟子。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像提鸟笼子进茶馆吹嘘顺治爷初入关时如何如何的晚清遗老遗少一样,以听戏为雅好。听戏好比读史,是需要年纪或者说阅历的。
今夜冷雨敲窗,我读古人碑帖,听《做文章》选段,川剧的、豫剧的、琼剧的、黄梅戏的以及大弦子戏的《做文章》,一一依次听来,急管繁弦浅唱低吟里,有无边风月,有往古来今,亦有雨雪霏霏,也唱尽了古今文人的穷形尽相。写文章的人,不就是戏文里被“之乎者也、兮哉夫维、诗云子曰”逼迫得几乎要投井上吊的徐子元么,那般犯难、痛苦、欲死还生。起先一想,戏文戏文,戏与文,文人与戏人,从来都是相依相附惺惺相惜,无文不成戏,戏为文添翼,戏人为何要唱戏为难文人?转念一想,自己又噗嗤而笑:娘的,那台词还是文人写的。
想起六年前的一个下午,山中雪花纷扬银堆白磊,百竿翠竹潇潇如魏晋六朝人物,我在一座亭子下面写《作不出文章》。当时好风景,快意如何之,若给我白宣一张湖笔一支,东坡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又有何难?无纸也无笔,只好在电脑上这样敲打:
作不出文章,就读读书吧,养养气,也养养器。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系辞》说“形乃谓之器”,我姑妄解之:气是元气,器为识量。文章,一气以贯之;待人,一量以容之。少年时好大言,好文学,好在柳荫月色下卧沙滩上与众少年侈谈人生。后来不敢了,人生这个词太重、太浓、太正,写文章时自觉地全部换成人间、人世、人间世或者人世间。
那篇旧作,我现在想补上一句:文章就是生活的兴味。而生活,就是教训和曲折。古今戏文唱尽了大江东去,也唱尽了江流宛转。
人间雨淋漓,不如听戏吧。
好戏如佳人
说起来有些滑稽,我少年时读书,根本不看作者姓甚名谁,一本书读完,作者全然被忽略了。鸭蛋好吃,未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鸭。不像后来,读书挑剔,专奔有名有姓的母鸭而去。万家宝更是一个陌生得古怪的名字,虽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剧本早早读过,舞台上的话剧也看过,而且印象深刻。及至后来知道这四部戏是曹禺写的,曹禺就是万家宝,万家宝就是曹禺,竟然惊诧莫名。
曹禺的话剧实在是极好的,少年时读觉得好,中年时再读仍然觉得好。不像有些书,有些作家,放十年二十年再看,以为不过是哄孩子。23岁写《雷雨》,25岁写《日出》,26岁写《原野》,30岁写《北京人》,至此,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曹禺人生中最重要的四部作品全部完成。所谓天才作家,所谓年少英雄,无非如此。自古文章作手,有年少了了大未必佳者,有少时稚嫩老更成者,有连绵山峰时峰时壑者,曹禺属于第一类。四峰矗立,他自己也是迈不过去的,近现代与其剧本相颉颃的,只有老舍。
旧中国,黑暗糜烂的地狱,以金八和阎王为代表的群鬼猙狞可怖,以鲁大海和小东西为代表的草民鲜血淋漓。在上个世纪初叶,雄鸡未唱,晨曦未露,是连鲁迅、曹禺和老舍也看不到光明的,只隐隐约约觉察到日出之前混沌里的一丝希望,而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一个生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的青年,孤独,苦恼,茫然,左冲右突,找不到光明和出路,因为跟继母看过许许多多的戏,京剧,梆子,落子,文明戏,一场场看下来,动起心思,于是写起戏来,试图在戏里找到苦闷的出口。不料戏是一个酱坛子,他掉了进去,融了进去,依然找不到出口,就像《日出》里陈白露的话,“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曹禺这个人,我以为有点像《雷雨》里的周冲,有点像《日出》里的方达生,有点像《原野》里的仇虎,又有点像《北京人》里的曾霆,然而仔细一想想,又都不是,甚至全然不像,相似的只有痛苦。
曹禺在《日出》的跋文中,引用了《尚书·商书·汤誓》里的一句誓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誓言是毒誓,是血誓,是痛誓。好文章都是痛出来的,要么痛苦,要么痛快,要么既痛苦又痛快。鲁迅写《狂人日记》是痛苦,王勃写《滕王阁序》是痛快,张岱写《陶庵梦忆》是既痛苦又痛快。有人曾经问曹禺,《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较好些,这自然如同问一个母亲大儿子好还是小儿子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曹禺为难半天,终于还是说,“比较说,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其实他的四部曲无一不是痛苦的,写的人痛苦,读的人也觉得十二分压抑的痛苦,有一团黑漆漆的郁结在胸臆里翻滚,像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肠胃里翻滚,像新死的鬼在油锅里被炸着翻滚,既不会随一口气呼出去,也不会随一个屁放出去。然而即使如此痛苦,还是舍不得释卷,悲剧有着巨大而可怕的力量,如同山蚂蟥的吸盘,何况,四部曲写得这样好。好的著作如佳人,眉眼鼻子青丝胸臀都是好的,又像一团气,浑元真气,结构章法对白独白旁白,无一不好,说不出来的好。
见过曹禺出演《雷雨》周朴园的一张剧照,据说是演员因上火眼睛红肿无法登台他临时披上戏衣替代的。照片上的周朴园,绝望而悲凉。是的,他写的和演的都是毁灭。旧的毁灭了,新的才会从灰烬中萌芽。是的,他写的也是萌芽。他写的还是预言,原本有些懵懂的周冲、鲁大海、方达生、仇虎、袁任敢、袁园、曾瑞贞、愫方他们,如新年的第一线阳光,破旧立新。
很喜欢关于曹禺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病榻上还在认真读《托尔斯泰评传》一类的书,读着读着,忽然大叫,“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写的戏是精彩绝伦的,他活到了86岁,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阅人阅事无数,所演的人生的戏也是精彩的。
戏,本来是一种兵器,上古时部落先民祭祀山川鬼神,戴猛兽面具持“戏”而舞,于是有了戏。远古的戏是图腾崇拜,是迎神祈福,类似今天的傩戏和跑五猖。戏院,戏楼,戏台,戏具,戏衣,戏人,戏子,戏法,仓才才才,台才才才,人到中年迷上戏,人生的戏台上却只想清白如葱蒜,不大愿意演戏了。
幼时县城有剧团和剧院,少儿心性,不耐烦看戏,京戏、评戏、昆戏、黄梅戏、高腔戏都是上好的摇篮曲。往往随了大人走好几里山路进了戏院,先是小老鼠似的嘎吱嘎吱吃瓜子花生糖果,甫一吃完,瞌睡虫立刻嗡嗡起来,盖过了台上的锣鼓铙钹和念唱做打。尤其不乐意看话剧,寥寥几个人在台上走来走去白来白去的,直如听道士念经文,没有小丑插科打诨,又没有骑马耍花枪打斗的戏份,枯索无味得很。
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县剧团早已解散,剧院成了早点一条街,这几年却对戏上起心来。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近现代戏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的剧本都读过一些,看严凤英和韩再芬演的黄梅戏《小辞店》眼睛会湿,在绍兴沈园看越剧《沈园情》心如撕裂的帛,翻来覆去地看经典元杂剧、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老舍和曹禺的话剧、本土的青阳腔遗脉岳西高腔,如中魔怔。看戏,品戏,懂戏,修为之外,大概的确也是需要阅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