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
邓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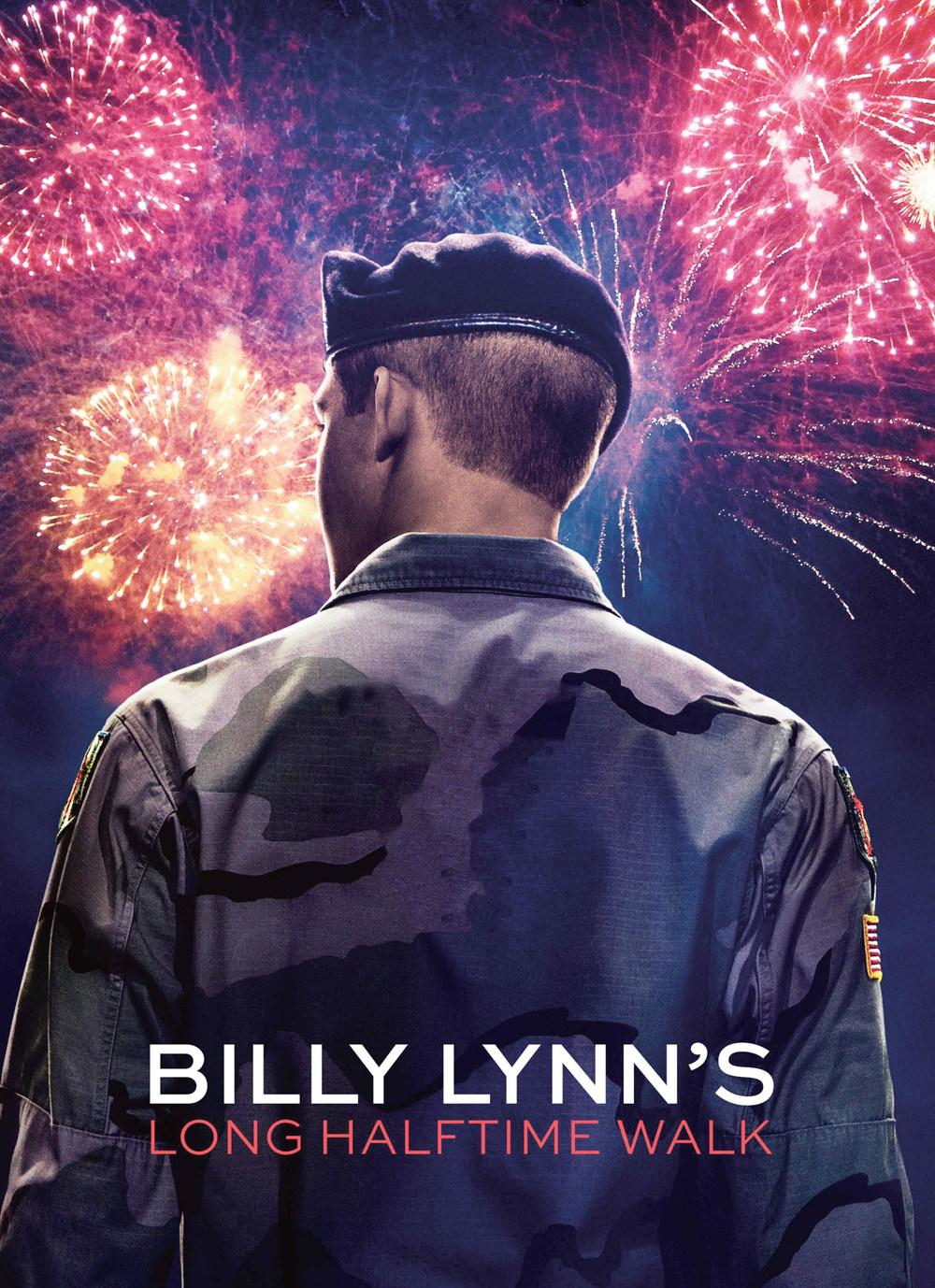
关于“电影是什么”这一问题,60多年前,安德烈·巴赞从“摄影影像的本体论”“电影语言的进化”“其他艺术形式与电影”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佐以案例进行分析。国内电影理论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聚焦于电影的社会功能,没有真正涉及“电影本体”的讨论,直到1979年,“电影理论开始谨慎地转向对电影自身规律的摸索”。[1]进入21世纪,国内理论界从美学、技术、产业等诸多方面入手展开涉及“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由“魔幻影像的思考”[2]到“综艺电影的反思”[3],从对“影院本体”[4]到对“电影制作放映”[5]的考察,再到“技术冲击”[6]、“媒介考古”[7]视角下关于电影本体问题的思考,众多研究者都围绕“电影是什么”这一问题阐释了各自的观点。D.N.罗德维克在《电影的虚拟生命》[8]中将这一问题转化为对历史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前瞻,从承载电影的“物”的维度探讨“新”媒介冲击下电影本体是否存在。理论界关于电影本体的讨论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本文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出发,探析电影在当今技术革新背景下的变与不变,以期进行一次对电影本质属性的探寻。
一、突进与改造:电影感官革新的两种路径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纵观电影的历史,一路上都在进行着视听革新。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电影机将电影这一新奇事物带到人们面前,1927年《爵士歌王》的出现(艾伦·克罗斯兰,1927)标志着声音正式进入电影。此后,不论是面对其他媒介的冲击还是自我更新的需要,电影始终在视听上不断拓展边界,寻求新的可能。不论是从黑白到彩色的跨越式发展;还是IMAX放映系统对视听效果的改良;乃至具体作品对于视觉呈现的形式探索:《快乐结局》(迈克尔·哈内克,2017)中社交媒体竖屏画面展示,《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2016)中由方到圆的画幅转变,《解除好友》(列万·加布里亚德兹,2014)、《网络谜踪》(阿尼什·查甘蒂,2018)中全片“桌面视点”的尝试。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影对感官的革新已不再局限于视觉和听觉,而是呈现出追求多重感官体验革新的趋势,实现这种革新主要有以下两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突进式的,它以技术变革为支撑,不断推进观众在观影时的沉浸感与超真实感官体验。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不是简单地将媒介视为人的“体外器官”,它们在服务人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并反作用于现实。“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得了行动时不必反应的能力……在电力时代,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靠技术得到了延伸。”[9]电影作为媒介,由2D到3D乃至4D的升级,是对身临其境感官体验的不断追求。“3D电影……从电影的本体特征来讲,就是将原本在平面上通过传统透视关系模拟表现三维世界的方法,革新成为了现在让观众能真实感受到三维空间的方法。”[10]4D电影在3D电影的基础上通过晃动座椅、喷水、喷雾等环境特效增加了触觉、嗅觉等感官体验。技术带来的突进式的对感官的革新,其目的是令观众在观影时达到更深层次的沉浸。3D版《头号玩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2018)令观众与主角一同沉浸于虚拟现实打造的“绿洲”探险;4D版《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则让观众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模拟空难。影院之外,流媒体推出的互动叙事电影,也在形式创新中召唤着观众的“深度参与”:在Netflix平台播出的《黑镜:潘达斯奈基》(大卫·斯雷德,2018),电脑端的观众可以通过按键来决定主角的命运和剧情走向,虽然这是一种无法逃脱创作者预先设定的“虚假参与”,但其与3D、4D电影一样,均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观众的沉浸感,实现了对电影感官的革新。
每一次技术变革不单为观众带来了更加舒适、新奇的观影体验,同时也让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复刻与还原现实,他们开始探索那些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体验。李安通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2016)开启对3D、4K、120帧的影像探索,实现了电影在延伸感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感官的目的。高清晰度、高帧率下,观众可以清晰看到平时不易察覺的人物微表情,现实生活中肉眼无法捕捉到的火花喷溅过程也在电影中得到还原与呈现。电影画面的特点也在强化感官的技术变革中发生变化:画面中的细枝末节得到充分展示,传统电影讲求纵深的主次分明变成了毫发毕现的“等量齐观”。在技术的加持下,电影由复制现实走向了超越现实,更清晰的人物、更丰富的画面细节,再加上激烈的动作场面,电影对视觉感官的强化,让观众经历了多重奇观下的超真实冒险。
第二种路径是改造式的,以现有技术为基础,通过对技术运用形式的创新达成对观众感官体验的刷新。正如学者尹鸿在论述电影叙事技法时所言,“世界上没有被使用过的技巧几乎没有了,但艺术的能力就在于我们永远能让技巧花样翻新。”[11]与此类似,跨越式的技术变革不会常常发生,但对现有技术进行花样翻新的应用同样也能达到更新观影体验的目的。手持镜头拍摄并不是一种新的拍摄技术或手法,但娄烨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中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极致。电影首映时“呕吐袋伴手礼”似是噱头却也是部分观众的必需,大量的手持晃动长镜头在灰蒙蒙的城市穿梭,迷幻眩晕,虽是2D电影却达到了4D电影的观感。在某种程度上,长镜头对普通观众来说是一种折磨,而毕赣在《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电影放映时间过半时,以戴3D眼镜这一动作再次向观众强调——要“入梦”了。戴3D眼镜“入梦”的仪式感不仅是一次指涉“元电影”的尝试,更召唤着观众跌入创作者营造的双重梦境,经历感官与情感的浮浮沉沉。再如前文所提到的社交媒体竖屏、由方到圆的画幅、以及摄像机视点的转变,都是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形式创新带来的对电影感官体验的影响。
如果说以技术变革为支撑的感官革新类似于“硬件升级”,那么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运用形式上的改造所达成的感官革新便接近于“软件更新”,但不论是突进还是改造,电影都在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多重感官革新,它在召唤观众沉浸的征途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由此,观众从观看逐渐转向体验,电影也逐渐从复制走向生成。
二、“热”与“冷”:电影媒介属性的重新划分
冷媒介与热媒介,是麦克卢汉横向比较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调动受眾感官参与程度的不同提出的理论,虽然曾因论述与划分的不够明晰而备受争议,但关于冷热媒介划分的基本原则却值得我们在审视媒介时借鉴:“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12]按照这一原则,电影被划分为热媒介。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的电影较之当年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电影是热媒介的属性划分似乎也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再也无法笼统地将它直接划进热媒介的子集。
沿袭是否需要受众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填补信息的原则,电影这一曾经的热媒介如今需要在内部被划分为“热电影”与“冷电影”。从叙事层面来看,“热电影”的故事往往清晰明了,无需动脑;因此,《人在囧途之泰囧》(徐峥,2012)等欢乐而通俗易懂的喜剧片可划归为“热电影”。从技术层面来看,3D、4D、4K、120帧甚至VR等技术加持下的电影不断推进“真实感”并给观众带来多重感官刺激,看似调动了观众的多种感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多重感官体验并非是观众主动调动并发挥想象参与信息填补的,而只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被动刺激。“生理唤醒,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自愿行动。”[13]观看4D版《中国机长》时颠簸的感觉主要来自座椅的晃动而非视觉触发的想象;3D、4K、120帧的《双子杀手》(李安,2019)无需观众费力去辨认和思考,画面充盈到分毫毕现,观众再也无需填补任何信息……因此它们属于热电影。
“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与其最终呈现的形式截然相反,这条原理是一条古老的原理。”[14]好莱坞大片通过赛车美女、超级英雄、视觉奇观打造出一个个精致刺激的美梦,令“热电影”的风潮席卷全球。我们纵然可以在“热电影”中纵情笑泪,感受刺激,也无法否认这些电影所带来的情感宣泄作用。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感官强化式观影,看似是“人的延伸”,实则是“人的退化”,借用麦克卢汉的话说便是“人的自我截除”。在这些模拟真实或“超真实”的技术辅助下,观众无需调动任何感官与想象,全部的感官刺激由技术与设备操控。正如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所说,“工业社会具有一些工具,可以把形而上的东西转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探索转化为技术的探索。”[15]技术加持下的沉浸式与超真实观影体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观众感官的封闭,其本质是技术的增强而非人的增强。技术暴政控制下的“热电影”,让观众沦为“被动人”。看似惊心动魄的观影体验,不过是外在环境与特效作用的结果,主动的情感体验退回为被动的应激反应。
然而,这样的批判并非代表“热电影”一无是处,而是这种“热”应与放映环境和观众能力相匹配,全社会影院系统的更新与完善以及观众对于新媒介技术的理解与应用在感知电影之美中同样重要。只为售出高票价而粗糙转制的伪3D、4D影片是对电影和观众的双重伤害;而在AR、VR等新奇的交互叙事体验中,观众对视角和叙事机制的理解与把控至关重要。否则,观众对电影的信息获取和美学感知都将大打折扣。
与“热电影”相对,“冷电影”在叙事层面上往往结构较为复杂,或者令人难以立刻明白故事原委,也即人们常说的有“烧脑感”。因此像《信条》(克里斯托弗·诺兰,2020)这样的电影,虽有大量刺激的动作、场面奇观,却需要观众高度集中注意力、调动感官补充大量信息才能理解,通常可划归为“冷电影”。另一方面,“冷电影”脱离了新技术带来的“超真实”与“强刺激”,它们甚至是悠长、缓慢的。在这类电影中,观众对电影气质、情感的体味再也没有外界的物质辅助,需要主动调动起全身心才能浸入电影中的世界。《路边野餐》(毕赣,2015)中慢悠悠的摩托车和梦幻的雾;《山河故人》(贾樟柯,2015)中沈涛在飘雪冬日里的起舞;《无问西东》(李芳芳,2018)中课堂上的静坐听雨;《六欲天》(祖峰,2019)中长沙夏日的闷热潮湿;《地久天长》(王小帅,2019)中刘耀军与王丽云时常放空的神情……它们均展现出“冷电影”的静观之力。“视觉的使用是由过去所看见的形象、个人体验、记忆和意图塑造的,如同由我们眼前的物理形式和物质性空间塑造一样。”[16]在这些静观电影或静观场景中,听到雨声感到的凉,通过天气所透露出的人物情绪,与电影人物的情感共鸣,均需要观众积极调动自身感官并发挥想象来达成。如果说,“热电影”带着一份殷勤和事无巨细;那么“冷电影”则多了一分神秘与高深莫测。
就如冷媒介与热媒介在不同时代和语境下划分的相对性与可变性,关于“热电影”和“冷电影”的划分也并非非此即彼的铁板一块,这仅仅是就媒介与电影都急速发展的背景,尝试提出的一种对电影媒介属性重新划分的可能,同时也是我们反思电影的一个切入点。
三、回归本体:生成“中间空间”的电影
刻印在胶片上的是电影,被数字化存储在硬盘中的也是电影;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是电影,在艺术馆屏幕、电视、电脑、手机中播放的也是电影;在技术飞速发展、形式千变万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定义电影,电影又如何确立自身?
莫里斯·梅洛-庞蒂和阿兰·巴迪欧分别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梅洛-庞蒂认为“电影不是被思考的,而是被知觉的;”[17]巴迪欧则认为“艺术作品自己在思考,并且生产真理。”[18]他们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却共同指明了电影的本质属性。在梅洛-庞蒂看来,观影的时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用“左手触碰右手”的例子阐明了主客体之间并非截然分明的特质,主客体接触的时刻,彼此交互的“混沌性”由此生发。电影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向观众诉说的同时又被观众感知。电影的诉说与观众的感知发生作用之处便是梅洛-庞蒂所言的“之间的世界(intermonde)”,即“中间空间”。它是一个非物质性的空间,在“观影”这一动作发生的时刻被激活。巴迪欧认为电影与哲学具有某种同构性,都是从断裂之处建立起新的关系。因此,两人的观点共同指向了电影作为媒介的本质属性,即让不同的人、事、物产生联系,产生联系的瞬间,“中间空间”便生成了。
首先,诸多电影运用“中间空间”架构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无敌破坏王》(瑞奇·摩尔,2012)中的游戏世界让来自不同游戏的角色碰面;《无敵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菲尔·约翰斯顿/瑞奇·摩尔,2018)让来自游戏机时代的游戏角色闯入当下的互联网世界;《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杰克·卡斯丹,2017)和《勇敢者游戏:再战巅峰》(杰克·卡斯丹,2019)将来自不同时代的玩家集合到同一游戏中;《头号玩家》则用虚拟现实技术开辟出一个几乎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游戏世界。这些电影不仅将归属于不同世界的人物聚合到一起,碰撞出新奇好玩的故事;同时,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亲身进入的世界全部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非物质的“中间空间”通过电影获得了“虚拟肉身”。
其次,观众在观影时所激活的“中间空间”,是电影与观众进行对话并完善自身的场域。电影从被观看的那一刻起,才算实现了自身的完整性。“人的经验赋予了性质某种情感意味,所以一旦我们把一个性质放回人的经验之中,那么这个性质何以能够和其他那些原本与之毫无关系的性质发生关联也就变得开始能够理解了。”[19]虽然这是通过知觉探寻“物”与“我”之间的关系,但知觉具有破除外在干扰认识事物本质的恒常性,可破除技术带来的迷幻与狂热,从而抵达电影隐藏的本质属性——生成“中间空间”,由此可以反观电影诉说与观众感知之间的关系。电影诉说与观众感知的结合处所激活出的“中间空间”的大小,不在于电影所展现的故事与观众经验或经历重合度的高低,而在于电影的情感内核获得观众的共情与共鸣的多少。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你好,李焕英》(贾玲,2021)采用了不寻常经历加普遍情感的组合,收获了高票房和好评。“母亲车祸去世”属于与观众重合度较低的经历,但电影中所蕴含的母爱与母女情却是令多数人都会产生共鸣的情感。因此,电影诉说与观众感知激活的“中间空间”几乎取得了所有解中的“最大公约数”。反观一些国产青春片饱受诟病的原因,是电影中的经历与情感均未引起观众的共鸣。夸张的情节、失实的造型、矫揉造作的台词不仅与大部分观众的经历无法对接,逻辑不严谨的叙事也令本就悬浮的爱情主线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经历与情感的双重陷落势必压缩电影与观众对话的“中间空间”。
“热电影”往往通过技术的突进不断强化观众的感官体验来拓宽“中间空间”;“冷电影”也通过手法与技巧的创新在兼顾艺术表达的同时试图在“中间空间”与观众有更深层次的共鸣。虽然技术突进带来感觉的无所不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观众知觉的不信任,并存在令观众走向“惰性”的风险,但不论是技术的突进还是对其创新性的应用,都是对“中间空间”的守卫与维护。
需要明确的是,“中间空间”并非一体化的“大集合”,而是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小子集”,它对接不同的感知与体验。不同的观众被同一部电影感动,但每位观众所动情的点各不相同;不同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理解也千差万别。电影在向不同人诉说的同时,也通过“中间空间”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分身”,这些分身是构成电影本质的灵魂。因此,不论未来电影的形式如何变化,因为“中间空间”的存在,电影拥有了突破物质载体实现永生的可能。
结语
从媒介视域对技术革新背景下的电影本体问题进行考察,突进与改造是其革新感官的两种路径;在对电影媒介属性的重新划分中,也完成了一次对电影与观众关系的反思;而不论技术如何变革、电影形式如何变化,电影作为媒介最本质的属性是生成“中间空间”,这一本质属性不仅是催生新颖故事的锦囊妙计,更是电影与观众获得联结并完善自身乃至超越物质载体获得永生的关键。就如“热电影”需要配套设施与观众对新技术的了解,“冷电影”需要观众全方位调动自身感官,在技术不断革新、技巧和手法被不断翻新的今天,“中间空间”的拓展与维护也需要创作者与观众双方的努力。电影作为媒介,聚合了不同维度的人、事、物;电影作为“综合”的艺术,令万事万物互联。
参考文献:
[1]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19.
[2]王宜文.来自魔幻影像的思考:电影是什么?[ J ].中国图书评论,2008(6):16-21.
[3]赵正阳.本体论视域下的综艺电影[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07):86-90.
[4]尹鸿,袁宏舟.影院性:多屏时代的电影本体[ J ].电影艺术,2015(03):14-18.
[5]陈晨.数字时代电影的再认识:论电影制作与放映的改变对观众感知的影响[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6-13.
[6][10]付宇.3D电影:本体美学的改变与视听语言的变革[ J ].电影艺术,2012(05):54-58.
[7]缪贝.“电影是什么”——一次电影媒介观的历史考察[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9):13-22.
[8][美]D.N.罗德维克.电影的虚拟生命[M].华明,华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9][12][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51-52,66.
[11]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1.
[13][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M].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41.
[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
[16][英]凯·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M].李蕾蕾,张景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1.
[17][19][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电影与新心理学[M].方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5,30.
[18][法]阿兰·巴迪欧.论电影[M].李洋,徐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