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驱动下的互动影视剧之形态分析
孙可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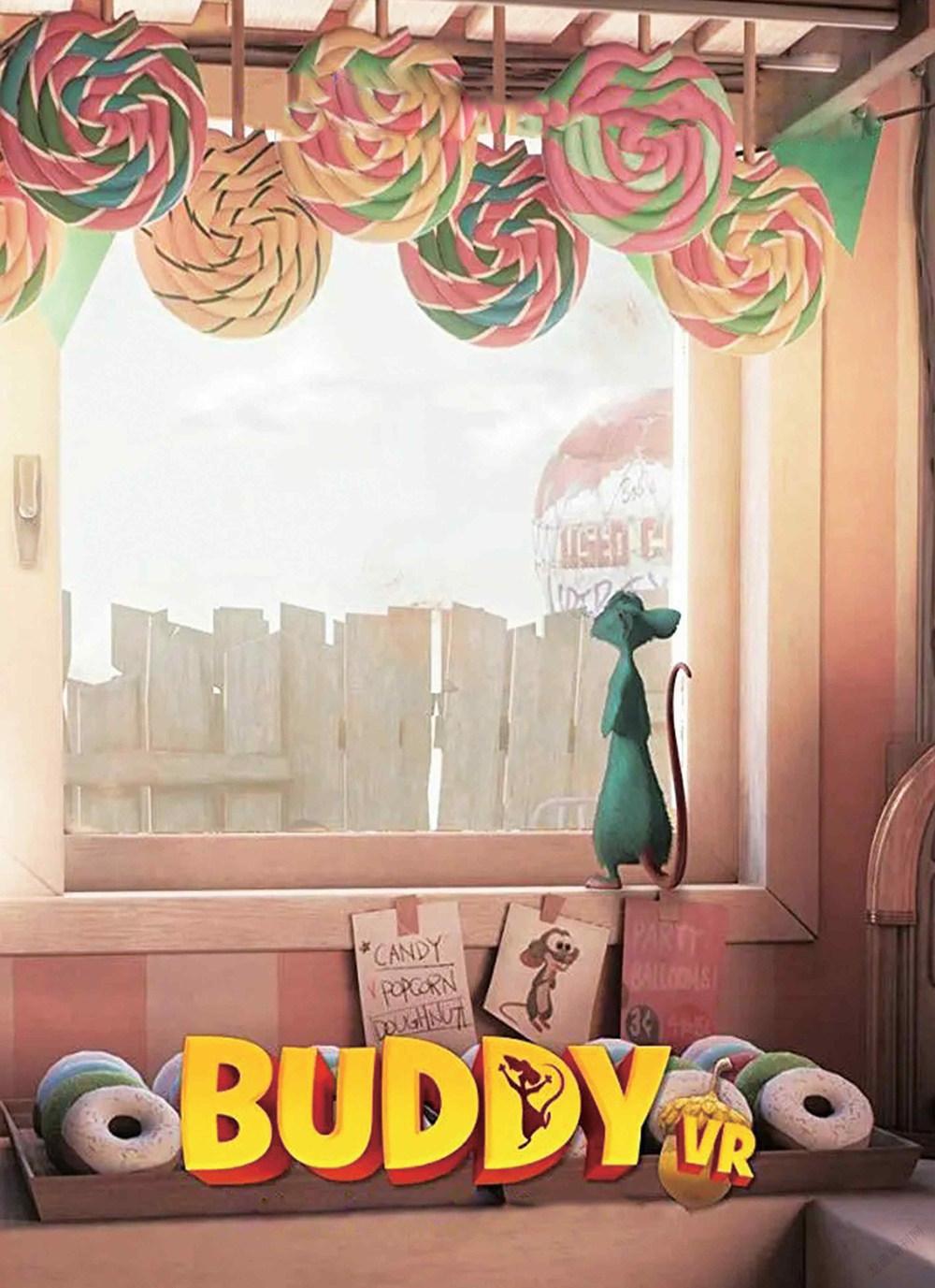

近年来,互动电影和互动剧的出现为影像艺术带来了新的变革:这种将交互叙事和游戏式的主动参与渗入影视剧的影像媒介形式可提供多线结构来多重选择和反复体验,也可让观众参与剧情发展。给予观众选择、参与、影响甚至决定剧情内容等体验的,是交互技术。“互动”或者说“交互性”居于互动影视剧的概念核心。英语语境将《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Bandersnatch,大卫·斯雷德,2018)等互动影视作品指称为“Interactive Movie”或“Interactive Drama”,“Interactive”一词即交互性。广义上,自然与人类社会中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可称为交互,克劳福德(Chris Crawford)的定义为大于等于两个主体间的循环过程并形成一种对话形式[1]。狭义上,交互被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媒体生态意义上的交互是围绕传播进行的人与交互性媒体之间;媒体与媒体之间的交互;精神生态意义的交互是围绕人的自我意识进行的,观念的交互通过叙事这一中介进行。”[2]在媒介艺术领域,英国学者桑德拉·高登西(Sandra Gaudenzi)认为交互性指的是文本与观众间的互动关系,观众以此与作品所真实传达的内容进行沟通和协商。[3]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则将交互性视为不同层面的关系:最外层关涉故事再现,中层是用户进入故事,这两层内,情节都是事先决定的;最内层是故事通过用户和故事系统交互形成的一种创造。[4]
大部分的互动影视剧作品以互动视频为载体,如2019年爱奇艺首部互动剧《他的微笑》(邱晧洲,2019)在视频中有21个互动选择点和17个结局供观众体验;2020年《龙岭迷窟》(费振翔,2020)衍生互动剧《最后的搬山道人》(王子,2020)在视频中设置了断崖、利刃、飞刀等闯关游戏般的按键选项。交互式电影游戏的互动方式与此类似,也被许多学者纳入“互动电影”/“互动剧”的研究范畴。
基于交互性本质,互动影视剧的形式不限于互动视频,还包括了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互动探索的VR互动电影、以网页为载体的一些交互纪录片项目和个别互动影像装置。它们不仅让观众通过选项来参与和决定,甚至能以感官体验增强代入感和沉浸感。
交互式纪录片(interactive documentary)的非虚构影像叙事探索相对成熟,观众可通过超链接、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等方式展开互动。例如交互纪录片《最后一代》(The Last Generation, Michelle Mizner & Katie Worth,2018)以超链接将马绍尔群岛上三个孩子的日常经历组织成一个在线数据库,讲述全球变暖之下低海拔地区的生存危机,观众点击链接选择观看对象和顺序。到《全球生活》(Global Lives,Glenn Fisher,2009,https://globallives.org/),观众还可以上传内容并进行公共讨论。而AR、VR技术带来了更深层次的交互:吉拉米﹒亥特(Jeremy Hight)等人于2001年制作的《北纬34度,西经118度》(34 North 118 West,http://datenmafia.org/gpstron/index-english.php)以AR技术让带着平板/手机的观众在移步中亲历旧日的洛杉矶故事。新闻作品《饥饿的洛杉矶》(Hunger in Los Angeles,Nonny de la Pe?a,2018)更进一步,观众头戴VR设备便可置身灾民队伍。
以上两部作品也是VR/AR互动影像作品的代表,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观众以自己的视角取代了摄影机,以自己的感官实现交互体验——又如Google Spotlight Stories工作室的VR影片《球体》(Spheres,Eliza McNitt,2018)、动画短片《精灵鼠伙伴》(Buddy VR,Sooeung Chae,2018)等作品。从交互概念出发,这类作品更应该被纳入互动影视的范畴。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发展整合过程中的互动影视之形态具有变化性、复杂性,需要抽象、概括地进行分类,以助于具体的研究和探索。
一、理论回顾:互动模式及分类
交互行为使互动影视区别于以往的电影和剧集作品。作为新类型或许尚显稚嫩,但交互叙事与互动媒介已历经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和研究。学者特金巴斯(Katie Salen Tekinbas)和齐默曼(Eric Zimmerman)根据用户涉入互动媒介内容的深浅,将互动性划分为认知互动性(Cognitive interactivity)、功能互动性(Functional interactivity)、直接互动性(Direct interactivity)与文化互动性(Cultural interactivity)四个层次。平面媒介等大多内容都具备认知互动性与文化互动性,解读之中便有认知上的互动。而对于游戏、数字文本、互动影视剧而言,还有着功能互动性和直接互动性。改变情节等直接干预显然是直接互动性,接口、遥控、触屏则产生了“功能互动性”[5]。类似地,英国艺术家阿斯科特(Roy Ascott)也由浅到深划分出交互艺术的五种形式:①操作,如点击、跳转;②选择,用户在既定程序中操作;③航行,用户沉浸于虚拟环境;④生成,用户通过续写、改写等方式提供、改变甚至创造作品,使之随时可能变化;⑤外部,远程环境下用户与作者或彼此间交流[6]。互动叙事的理论先驱瑞安将“互动性”定义为用户与文本之间的各类关系的概括[7],提倡将互动小说、浸没式戏剧、互动影像游戏这些跨媒介文本纳入叙事学,建立一个经典叙事学之外的全新理论体系。她将互动性分为內在互动性(Inner interactivity)与外在互动性(Outer interactivity)、探索互动性(Exploratory interactivity)与本体互动性(Ontological interactivity)这两组二元关系:内在/外在的区别在于,观众是自己代入故事中的人还是以上帝视角操控情节;本体/探索互动性的区别在于互动行为是否能决定故事终点,后者在既定世界中游荡而不改变既定设计。[8]
以上理论其实是对各类互动文本的总体概括。具体到互动影视剧,雷建军对视频互动媒介的分类或许更具针对性:根据界面两端互动主体的身份,可分为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两种形态。[9]但若推及交互纪录片、VR影片等互动视频之外的形式,又需要新的概括。
本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根据互动的实现手段、层次深浅和达成效果,立足影像-媒介-观众/用户之间的关系,将互动影视剧分为三种形态:基于互动视频的人机交互形式,基于网络平台的创作和人际互动形式和基于设备的深度沉浸互动形式。
二、基于互动视频的人机交互
以视频界面为中介的人机交互是目前互动影视剧的最常见形式。作为交互环境和媒介的界面通常是影像所附着的屏幕[10],互动影视剧的界面就是互联网/移动端上的互动视频。而各大视频平台所围绕互动视频作品打磨的互动体验链路就是人机交互的具体方式。例如优酷根据观众参与表达的程度将互动玩法归纳为三类:①剧情互动:观众决定剧情、人物塑造和结局;②快捷操作互动QTE(Quick Time Event):帮助角色进行操作,完成任务;③体感互动:亲身完成动作。[11]下面结合具体例子进行分析。
(一)剧情互动
2019年9月在腾讯视频上线的5集互动剧《因迈思乐园》(王启明,2019)虽仅有5-10分钟的单支线时长,30多个互动节点、3种结局,但最终播放量超1600万。这个母亲寻找女儿的悬疑故事用了大量限时的剧情选择,放大了紧张感。对于超文本形式的交互纪录片,剧情选择是最主要的互动方式或者说访问路径。以前文提及的《最后一代》为例:二级菜单界面包括马绍尔群岛的现状、历史、未来,由三个孩子的第一人称自述呈现气候问题对岛上居民的影响,点击选项即观看某个孩子的经历。链接的页面在跳转中构成了多方向多路径的叙事文本,每一次观看都会指向新的体验和意义,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剧情选择”。
(二)快捷操作互動(QTE)
QTE是电子游戏通用的操作模式,玩家操作引擎帮助角色完成任务。在《古董局中局》(五百,2018)的衍生互动短剧《佛头起源》(袁菲,2019)中,真人影像不时穿插着游戏化操作的界面,让观众根据提示完成任务:蓄力释放或左右滑动;和游戏类似,观众点击鼠标的速度、准确度对剧情至关重要,造成了深度沉浸的独特感受。这常见于惊险题材,如《因迈思乐园》便引入了丰富的互动玩法以增强体验感,许多惊险时刻都要求快速反应和操作。当观众以女主角视角开车时,也可随时点击“查看路况”切换视角。视角切换也不限于点击选择,在VR全景视角下的限时找寻更能形成戏剧张力。
(三)体感互动
市场中率先使用体感互动体验的是2020年2月底优酷上线的《娜娜的一天》(韩忠羽,2020),由6集*10分钟、200余互动节点、22个结局组成。简单的故事包含了丰富的体感互动设计。大量关键节点用了语音识别的互动方式,引导观众开口与主角对话,根据所说内容决定剧情走向,营造面对面聊天的沉浸感;也有的节点需根据引导或提示,在手机屏幕前做出指定脸部动作,根据动作确定是否符合要求进入后面的故事。
三、基于网络平台的创作和人际互动
故事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互动影视剧的选项力争做到与人本身产生互动。当界面两头的对象由人和机器变为人与人并发生交流,人际互动便发生了。数字媒体与互联网的兴盛,让人们得以远程交流,以各种方式与遥在出现的他者产生联系。数字时代的人际交互不仅意味着交换信息,还可能是意义的共同书写与生产,形成“精神交互场”[12]。新媒体更以可视的方式,让作者与读者在文本、视觉与听觉等各要素的创作方面得以通过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平台共同创作和交流。
这种由创作者提供情境、设好参数、将作品通过互动平台交由用户创作完成的方式常见于交互纪录片。如前文提到的《全球生活》允许用户上传影像内容甚至改变界面呈现及交互结构,复杂的网站结构既可检索观看,也可在线交互、事实上是一种数据库式的作品。
而互动影视剧的人际互动并不止于此,本文将其分为创作、反馈、信息交换和用户生成角色四种,接下来具体分析后三种方式。
“反馈”体现了观众历来渴望参与内容的诉求,美剧通常的制作模式正是根据观众反响随时调整剧集,观众的呼声可能会扭转原本结局。类似案例又如东芝的社交互动剧《奇幻心旅》(The Beauty Inside,德雷克·多雷穆斯,2012)、边征集观众意见边拍的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黄文利,2006)和《pk.com.cn》(小江,2008)等。而科幻剧《贝肯菲尔徳》(Beckinfield,鲍勃·格伯特,2010)是一个“多用户交互性”(multiuser interactivity)的典型案例,作品中部分人物是世界各地的观众把自制视频上传到制作方Theatrics的平台上而参与塑造的。
创作、反馈这两种方式其实都存在时间差。对于目前的互动影视剧,实时的人际交互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换其实已具备了实时人际交互的潜力。例如交互纪录片《骑士物语》(Rider Spoke,Blast Theory,2007)中,观众穿戴相应设备骑着自行车穿行伦敦,在车把放上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通过语音问用户问题,回答时需要找到特定地点录下来;当其他骑行者到此也会遇到同样问题,并可浏览以往的录音答案。再如加拿大广播公司、瑞士电视广播公司等多方出品的系列交互纪录片《不追踪》(Do Not Track,Brett Gaylor,2015),观看时浏览器和Facebook上的个人资料信息同时连接和交换,就这样以信息交换的方式实现了人际交互,切身地让用户感受到互联网隐私安全的风险。
最后是“用户生成角色”(User-Generated Characters)这个从游戏领域移植而来的方式:互动影视中的观众即数字媒体用户,意味着他们也是参与者(interactor)和化身(embodiment)。首先,当观众扮演角色成为叙述主体,可以是单独的个体,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群体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主体。其次,现代通信技术使得身处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化身进入到叙事进程、与其他用户在故事空间中交互。莫里(Janet Murray)认为,交互视频和数字游戏中,化身是像人的图形,人们通过化身进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13]。故事可以预设角色的性格和背景,但过程到结局的人物形象则受观众影响。互动影像游戏《隐形守护者》(New One Studio,2019)中,观众化身抗战时期的地下党员肖途,他是忠于祖国还是叛变革命掌握在每个互动选择中。在《底特律:变人》(Detroit: Become Human,大卫·凯奇,2018)中,仿生人康纳能否逐渐获得人性,观众的主体性选择起决定性作用。观众与所塑造的故事中人之间的互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人际交互。
许多创作者对人际互动抱有期待,著名编剧白一骢说,“未来的玩法是对内容的革新。我们希望未来观众在观看以外,能够去参与创作整个‘观看性的创作,就好像真正的乐高高手一样,不是按照说明书去组装,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组合成新的东西……希望以后能有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一个发展的可能性。”[14]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内容的革新,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人际互动。
四、基于设备的深度沉浸互动
在媒介生态意义上,媒介是人类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途径;如果将互动影视剧以媒介视之,用户不仅可与之产生交互,也会沉浸在其虚拟空间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VR互动影片。英国学者布赖斯(Richard Price)指出:“虚拟现实的目的是建构浸没的感受,产生近乎于脱离真实所处的外部世界、沉浸在被建构出的虚拟世界的幻觉。”[15]
什么是沉浸?英文immersion是浸入水中的体验,这种生理状态后来成为了人类一种精神感受的描述,人的注意力、精神、感受甚至思想几乎全部集中在某种意识层面的活动或境界中[16]。布罗克(Staffan Bjork)与霍洛派宁(Jussi Holopainen)将沉浸分为五种:感觉-肌肉运动沉浸、认知沉浸、情感沉浸、空间沉浸和心理沉浸[17]。莫里研究了数字媒体制造的沉浸体验后认为,人们可在其中亲历仿真之境甚至将幻想付诸实施。[18]
VR的沉浸感依然需要界面作为媒介,其互动体验包含操作/体感输入以及操作输出。操作输入设备有游戏手柄、操纵杆、方向盘、射击步枪等,体感输入设备包括摄像头、跑步机、数据手套、数据鞋、遥感座椅等。而输出方式有头盔、眼镜、屏幕和耳機等。观众与仿真环境间的人机互动产生了其他一切视听手段都无法比拟的身体的真实在场感受。这种交互可以发生在用户与周围环境/其他用户/界面应用程序之间。本文参考布洛克的分类,将VR互动的沉浸体验分为空间沉浸、情感沉浸和感官沉浸三种。
空间沉浸意味着用户在知觉上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仿真世界。1966年,被誉为计算机图形学奠基人的苏瑟兰(Ivan Sutherland)发明了头盔显示器,1970年进而拓展成为头盔显示系统“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让观者沉浸在虚拟的三维环境中[19]。如今,VR、AR技术让空间沉浸得以真正实现,如前文提及的《饥饿的洛杉矶》、《北纬34度,西经118度》;再如2016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最佳沉浸式作品《死亡体验》(Deathtolls Experience,Ali Eslami,2016),用户戴上头盔设备便可体验到叙利亚难民迁徙欧洲、葬身海洋和内战等悲惨经历,深刻地认识中东数十万死者背后血淋淋的现实。
情感沉浸是一种依靠想象力实现的,与作品在心理上、精神上交融和移情的感受。VR深层互动可类比游戏的情感沉浸——或来自于故事、或来自于互动本身。例如第59届“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最佳沉浸类故事奖作品《绝望穿越》(Desperate Crossing,Paolo Pellegrin,2016),观众宛如置于孤独的渔船之上,感受利比亚难民的漂泊而获得情感共鸣。
感官沉浸顾名思义意味着感官的体验。造成深层交互的VR影片往往能触及多个感官的体验:视觉的、听觉的、触感的,甚至嗅觉/味觉的;并且感官之间产生联动,交叉混合,进一步又进入到心理层面的反应。传统艺术作品需要通过想象而感受到的一切可以直接通过沉浸体验来实现。
由三种沉浸方式也可看出,跨越时空的互动交流一方面借助了界面;但另一方面,深层的沉浸互动中,界面在心理层面消失了。大多互动影视剧都需要键盘、鼠标配合,观众不断点选以完成叙事。而VR互动电影的互动引擎基本上均需要手柄,如2018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VR奖作品《球体》《精灵鼠伙伴》等作品均需观众用手柄操作互动,但这些操作更大程度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例如《精灵鼠伙伴》中,当Buddy向观众递过卡片,接下来就要用手柄作为“笔”在上面签名。
沉浸的最终目的向着消除人与界面之间的壁垒演进,极致形态是无界面之界面,即观众在营造情景中忘记了界面的存在,那便是一种深层的互动沉浸。甚至,如果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界面甚至可能在物质层面被隐藏至不为人感知;或者说,把界面隐藏到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之中。例如依托眼镜的视频交互系统等,使界面在物理层面上消失,一直是MIT媒介实验室等研究机构的研发方向。[20]
总之,VR互动影视作品所具有的深层互动形式及其造成的空间、情感和感官沉浸体验,是其他互动影视剧难以企及的。它呈现出一种发展趋势:通过VR、AR技术为交互式叙事提供全感官沉浸的环境,将现实世界的一切转移进虚拟空间中,与这里面的人物、虚拟环境本身、或是其他用户展开互动。
结语:从技术变革到影像变革
总结起来,互动影视剧可以被概括为人机互动、人际互动和深层沉浸互动三种形态,每种形态的技术基础和观众介入渗透的深浅程度不同,在多重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以往的影像叙事,增强着影像的视觉化和体验感。这与整个影像技术进步方向是一致的:3D、4D电影,VR、AR、MR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创作出更多渲染性、沉浸性的场景,促使更多崭新的影视剧作品和形态出现。
正如学者尹鸿指出,电影美学始终是在技术推动中不断发展的[21],影像艺术是商业、艺术和技术彼此之间的融合,而具有交互性的影视作品仰赖技术进步才得以实现,并且正在对影像美学、传播与生产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交互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影视剧的形态呈现、媒介特征、叙事特征和创作方式,互动影视剧因而有了成为一种新型叙事艺术形态的潜力。
参考文献:
[1][美]克里斯·克劳福德.游戏大师Chris Crawford谈互动叙事[M].方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43-56.
[2][16]黄鸣奋.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66,393.
[3]Gaudenzi S.,Aston J.Interactive Documentary:Setting the Fiel[ J ].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2012,(6):125-139.Doi: 10.1386/sdf.6.2.125_1.
[4][7][8]Ryan M.Avatars of Story[M].Columbu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107,233.
[5]Tekinbas K.,Zimmerman E.Rules of play:Game design fundamentals[M].London:The MIT Press,2004.
[6][12]Ascott Roy.Behaviourist Art,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1996),in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Technology,and Consciousness[M]// Edited and with an Essay by Edward A.Los Ang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377,178-182.
[9][10][20]雷建军.视频互动媒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9-32,19-24,63-65.
[11]AlibabaDesign.实战案例!优酷首部互动剧背后的核心体验设计复盘[EB/OL].(2020-04-22)https://www.uisdc.com/youku-interactive-drama
[13][18]Murray J.,Hamlet on the Holodeck[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114,98.
[14]爱奇艺行业速递.關于互动剧,你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都在这儿了[EB/OL].(2019-07-01)https://new.qq.com/omn/20190701/20190701A0RUYH.html?pc
[15][英]理查德·布赖斯.多媒体与虚拟现实工程[M].史萍,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4-5.
[17]Bjork S. Patterns in Game Design[M].Boston:Charles River Media,2004:423.
[19]Sutherland I.,The Ultimate Display(1965)[M]// In Multimedia:From Wagner to Virtual Reality,Expanded Edition by Randall Packer & Ken Jordan.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2:252.
[21]尹鸿.电影的技术美学:变与不变[N].中国艺术报,2021-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