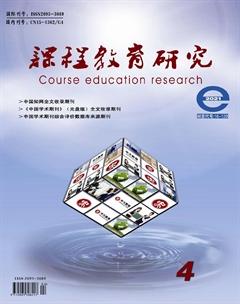于诗歌中回望道不尽的爱情
张铮
【摘要】诗歌中的爱情是不竭的创作源泉,诗人用或精巧或朴拙的修辞来表达自己关于爱情的理解,代入自身关于爱情之路的感叹。在不同时空的诗人笔下,爱情的呈现和理解各有异同,可以说在爱情的反复无常的外衣之下,诗人们殊途同归的展现出了爱情永恒缠绵的内核。李商隐和穆旦是不同时期不同经历下的古典与新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于典型意象均有超越多数诗人的敏感性,对于语言的序列也有如同密码一般的重组和演绎。本文试图由分析《锦瑟》与《春》中语言和意象的不同形式,来探寻两位诗人的爱情理解。
【关键词】《春》 《锦瑟》 意象 想象 联想 爱情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1)04-0095-03
一、古典诗歌侧重典型意象的个人化阐述,现代诗侧重意象的个性化。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 《锦瑟》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一团花朵挣出了土地,
如果你是女郎,把脸仰起,
看你鲜红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為关紧的世界迷惑着
是一株廿岁的燃烧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穆旦《春》
《春》中的“泥土”显而易见的带有发掘和启示的功能,被赋予了某种思想和特性。“绿色的火焰”“花朵”都是泥土中来,这是新的希望和春天的生命得以绽放的根基,与此同时,泥土还是那“鸟的歌”,是“谁家新燕啄春泥”中鸟儿的新巢,新的希望。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泥土是女娲造人的来源,是落地即活的肉体。泥土是肉体,在其中生长蔓延的绿色的草、红色的花,都是新鲜的生命力和蓬勃的欲望。在这浓烈的颜色撞击中,诞生了一尊廿岁的青年人的肉体。这新鲜的肉体在花草之间,恰如苏轼所言春天之美是“一朵妖红翠欲流”,是新鲜奔腾的色彩。年青人的灵与肉不断对抗和消解,探索着爱的意义,然后陷入长久的迷茫和痛苦。肉体承载了诗人的幻想,与此同时又是禁忌而难以突破的。肉体若没有承载着爱情,就是贫瘠而苍白的,是一座荒城,而现如今爱情这一肉体的春天蓦然奔袭而来,在天地间所感而开合,恰是“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生命从此有了依托。落地生根,蓬勃不息。
“锦瑟”是开篇之物,这是《汉书·郊祀志》中素女的瑟,是传说中的瑟。素女用此瑟弹奏哀伤的歌曲,而这种哀伤凡人难以承受。这一传说在观念上已经确定了锦瑟的器型和内核:哀伤之物。而弦乐器在古代诗歌意象中一直以来和爱情均有联系,爱情的落空恰如弦断无人听,在中国古人关于婚姻的叙述中,亦有续弦一词。弦之器物独有的幽深绵密的声音被认为触动心灵之音。由锦瑟发端,显见叙述之情是哀情。也可见这是荡涤了岁月后的曲调,深沉缥缈,不似年青人的炽烈和反复,已经停止了追寻,而是静默的喃喃自语。开篇“无端”二字,无理之问,仿若思念情人至极而百无聊赖的下意识的低吟,似一声叹息,但听不到,为锦瑟的弦音所掩。如同一切无可言证的感情,于缥缈里暗藏浓烈。先秦诗作《越人歌》里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先从山上的树木起兴,也是无端之言,这一如爱的萌发,不知为何而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无法用逻辑来推导说明。然而听来不觉无理,反而心证其理,理所应当,那山上的木枝在春天也会萌蘖,上古歌谣里,人们已经发现了木枝本身暗含着的生命力,并将其和人相比,人内心关于爱的体悟也如林木不断滋生发展,呈现多种形态。《锦瑟》中的蓝田玉暖,暗合《搜神记》中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故事,紫玉由爱而死,无法回应韩重的拥抱,化为了烟尘,爱而不得,无望无着。可以看到,《锦瑟》通篇都用这种极致之美的事物和传说来展现内心对于爱的理解——这爱是回忆中的爱,隔着茫茫的时空,蒙上了怅然若失的迷离意味。李商隐在他的另一首《马嵬(其二)》中谈到对于杨贵妃和唐明皇之间生死两隔的爱情的理解,说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异曲同工的表达了他对于无望之爱的深刻解读,或许可以认为李商隐诗中的爱的最高形式就是未完成。《锦瑟》之爱未曾道尽,没有具象,或许是诗人自身爱的过往,又或者是无数个爱的故事中抽离而出的岁月的歌谣。
二、传统诗歌重联想与想象,现代诗歌重直觉与幻想。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李商隐《锦瑟》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一团花朵挣出了土地,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女郎,把脸仰起,
看你鲜红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关紧的世界迷惑着
是一株廿岁的燃烧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是火焰卷曲又卷曲。
呵,光、影、声、色,现在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穆旦《春》
诗歌主情。传统诗歌尤忠于此。
李商隐诗歌纯为抒情体,全诗整体为一。其中四句似不可读,也不能解,解读即是美的毁灭。其意象的神秘和统一使其成为唯美典范。庄周梦蝶,杜宇化鹃,人与物合二为一,我是周遭之物,物也即我,不分彼此,相互融合。古典诗歌含蓄唯美,用山水来托情,用典故来遮盖未尽之言,留下迷思,催人一读再读。让读者得以拥有多层欣赏视角,人人皆可通过这一语言密码来打开内心,比照自身关于爱的理解,若合一契,不能不有所感慨。“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意境扩大,虚实幻境,海天一色,珠玉相合。重的是意境的营造,情已无人诉说,但一如爱情的如泣如诉,珠泪之美,玉烟之暖,读来从舌尖渗透进骨髓,通体都柔软起来,进入迷离之境。如一头扎进太虚幻境的贾宝玉,俗舌眼饧,悠悠荡荡。在迷幻和想象里荡涤身心,忘却凡俗之事。真真假假,无人追寻意象的一一指应,而是通篇读来顿感万千红尘中柔情万丈,不禁心碎至此。
穆旦的《春》对于爱情的描绘,更多是依靠直觉的搜索。意象中的象,即为形象与视觉现象中的投射。诗人让春天的典型意象悉数登场,看似如朱自清的《春》一般热闹喧腾,而细究这些意象的刻画,却超越平常的认知。他没有选择传统意象中唯美的存在,反而单刀直入,只取春天的景物来描绘。按照常规的阅读顺序,绿色的火焰对应着燃烧的肉体,都在拥抱、摇曳、卷曲;女郎的脸是花朵,是鲜红的欲望,它们在关紧的世界里赤裸的展现着,又欢乐又痛苦。诗歌用散文化的方式打乱了排列,凭借着幻想让爱从土里挣扎着冒出来,让爱情的无望和诱惑沾染到春天的一切事物之中。把意象的封闭静止完全打破。让二十岁的青年爱情有了温度和质地。好比握雪之后的触感,痛苦而炙热,这种奇异性在文本中自然的排列铺陈,用身体的经验来直接抒写,新颖奇异,扩大了文本张力。文中点明的:光、影、声、色,是感官的一次集体释放,由“火焰”而产生了动态感,大地上生长的一切本来就有动态性,而此时的火焰更是加深了颜色的对比,空间的折叠,人和物在火焰之光中变形,展现出其他的形态。原本一目了然的油画变得抽象离奇。“光、影、声、色,现在已经赤裸”直接大胆的表达了青年人在爱欲中的沉沦,年轻的诗人在模糊重叠的意象里铺陈思想的矛盾,拉着读者一起进入焦灼而热烈的心理世界。这一“燃烧的肉体”中有绿草,有红花,有暖风和鸟鸣,这一身体就是春天,诗人将两者糅杂一起,不分彼此,眼前之景就是心中之境。
三、作为高度凝练的文学形式,传统诗歌侧重于含蓄写意,现代诗歌更加直白。
《锦瑟》开篇和结尾直接抒情,传达对于华年逝去的追思和情感的惘然。由身边围绕的天地万物发端,可心里眼里不见万物,一个劲的只指内心,这才可见“为情所困”,将抽象之情爱寄寓具象之万物。让情感有迹可循,落地寻踪。但这种“情”不知具体年月,也不能确定深度重量。最妙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待指向未来,追忆暗合现在,当时又指过去。一句之中,过往如今未来三个时间点纷繁交错,避无可避,正如《百年孤独》首句的撰写“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由时态的多重复合来扩大空间和时间的边界,此情的厚度和广度无边无际,这才证明情网恢恢,难以消解。张爱玲的散文诗《爱》里,也将这爱形容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用时空的广袤拉长爱的阈值。作者自己对于爱也难以捉摸,这和《锦瑟》的无端之爱,有所照应。
相对于《锦瑟》里无可发端,充盈天地的情愫,穆旦的《春》却是把情感倏忽拉下,寄托在沉重的肉身之上。这恰是“灵与肉”的分界,《锦瑟》之美在于空中楼阁,半壁海日。《春》中处处都是招摇的情爱,“渴求着拥抱你”“鲜红的欲望”“燃烧的肉体”,分明是二十岁的青年炙热的爱,是情欲,是泥土里的原始欲火。这爱不是“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的哀怨缠绵,而是充满了初次感受爱的滋味的新奇和苦痛,青年之爱是冒失无理的,缺乏考量,随心所欲。但这爱让初尝滋味的诗人并不好受,“一团花朵挣出了土地”中的“挣出”是肉体的自我觉醒,是生命的力量。而“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快乐”则暗示着“暖风”作为外因在诱导着诗人的爱的觉醒。作为二十岁的青年,对于世界还是外放型的,他们不停的感受身邊之物,由他物而观照自我。《春》中的爱并不收敛,但却单纯。它藉由春天的景色而尽情挥发。“女郎”“泥土”“花朵”的组合,并不是穆旦这一新派诗人的独创,而是糅合了古典美学和新派主义的一次尝试。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牡丹亭》中杜丽娘第一次踏入家中花园,发出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感叹,这是生命的感叹,杜丽娘这一怀春的女郎,游园惊梦,为这春花春情而感动,她眼中所见也即自身之美,那千古一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不正是“燃烧的肉体”和“鲜红的欲望”的胶着。在这一刻人和春天之物合二为一,由赏春景中惊觉自己也是春的一部分,在她的身体中原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未曾展露于世的春天。而我们的诗人穆旦沿袭了古典美学中关于春情的颂扬,但是他大胆的将这一内心中的春天泼洒出来,他不再隐晦,而是直言春天的美,那美便是春情,便是年轻人熊熊燃烧的心火,他直接道出这哪里是满园的花朵,分明就是满园的欲望。那“为关紧的世界迷惑着”的肉体也正是为爱苏醒的蓬勃的欲望的载体。诗人穆旦将古诗歌中隐藏的情感从意象的掩映里解放出来,让花、草、女郎、鸟等蓬勃的春天之物象悉数出场来佐证这情意,诗人眼中可见之物全是爱情,全是色彩,全都动起来,探索着爱。而意象的选择甚为巧妙,让这万物都在燃烧。爱情一如吻火,光热太甚,疼痛也甚,却光芒大盛,无法回避。这是大胆的爱情之火的纵情高歌,待火烧尽,人也老去。暮年的诗人李商隐早已不是需要他物来印证自身的青年,藉由阅历,他已和世界相融,那汹涌的爱也静止下来,在爱的灰烬里回望的才是《锦瑟》。
参考文献:
[1]裂帛:现代诗与思维的野性
[2]《穆旦诗文集》(修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3]《叶嘉莹说中晚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148—156.
[4]张丹.重弹《锦瑟》——一种文本中心主义的分析[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2):52-54.
[5]吴投文.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J].北方论丛,2016(06):36-41.
[6]《牡丹亭》(明)汤显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张爱玲散文》张爱玲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