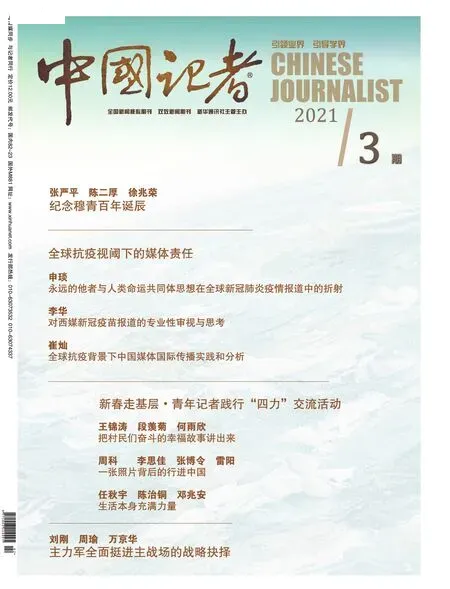“引流”还是“服务”:国外网络舆情概念研究
内容提要 当今数字时代,网络信息跨国界流动,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领域影响深远,掌握信息的多少正成为各国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把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话语权,抢占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因此,国内外都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研究。研究发现,国外网络舆情概念的界定主要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为政治服务的民意;二是对网络民众情绪的引流。
“网络舆情作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概念”,是极富有中国特色的抽象概念化词汇。“综观国内外文献,舆论、舆情和民意仍在用同一个英文词表示,在引用西方有关论述时经常会带来困惑和认识上的歧义。”在非中文国家中,网络舆情的对应翻译与中文的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差异,如以中译英为例,网络舆情可翻译为internet public opinion,internet public mood,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等。基于internet public mood,网络舆情体现为“发生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事件确实对公众情绪产生重大、直接和高度具体的影响,因而,对公众情绪的分析可以得到对现在社会和经济指标变化趋势预测的趋势。基于internet public opinion,绝大多数集中于中国作者英文写作的文献中,集中于“以中国网络舆情事件为实例的具体研究”。而public sentiment则更集中于网络情感表达方面的研究,“数以百万计的Twitter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观点分享,是公众情感表达的宝贵数据,可为各个领域的决策提供关键信息。”
“网络舆情在近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中,由于涉及学科的广泛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分散性等特点,已发展成为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局面。尽管网络舆情研究已发展了很多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形成一个全面、明晰、清楚的认识。”这种差异的认知,其一,不利于中国相关研究的发展,有自说自话故步自封的嫌疑。其二,不利于国外学者对现今在中国学术或者实际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舆情研究进行了解和传播,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缺失,不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笔者查阅了国内研究网络舆情研究,以最近几年权威期刊发表的关于网络舆情的综述文章为例,发现其参阅参考的文献大多局限于中文,且对网络舆情概念的界定不一致。对此,重点梳理国外对网络舆情概念界定的相关研究,试图尽可能多地展现网络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网络信息传播所汇集的舆情研究,为中国网络舆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弥补中国学术界在网络舆情方面看世界的“短板”。
一、网络舆情的概念及其历史
自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发行《Public Opinion》以来。国内学界对Public Opinion的翻译主要为“舆论”“舆情”“民意”“公众意见”“公共意见”等多种译法,其定义尚未统一、规范。从中可见,舆情与Public Opinion所表达的范畴既有交叉又有重叠,在中文表述方面常会与其他几个词汇互通互用。类似的,网络舆情也存在类似的模糊性表述情况。
1994年4月20日,互联网正式接入中国,互联网空间中的舆论、舆情、民意表达天然地被冠以网络舆情的帽子。就全球而言,最早开通互联网的国家是美国,源于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的ARPANET。当时是为军事应用设计和研制的,目的是把不同类型的计算机互联成为网络,再通过不同的节点把各个网络互联起来,用以传送和共享军用信息。网络的这种连接方法,可以达到一个节点的网络遭到破坏后,其他网络仍能照常工作的目的,从而适应军事应用的特殊需要。之后,随着网络从军用到商用再到民用,直至80年代后期,美国民众可以大规模地使用网络进行网上信息交流,至此,源于社会生活中的public opinion被冠以Internet or network public opinion。同时,依赖中文中舆情对应英文的释义,除去public opinion,还应关注public mood、public sentiment等释义,简言之,网络舆情英文释义还需关注Internet/Network public mood/sentiment。
二、不同观点争议的焦点
在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时代,网络舆情研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研究,国外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也都广泛关注。英文文献中涉及“internet/network public opinion”的研究是否与国内学界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真正相对应?“存在概念表述模糊的问题。虽然网络舆情已成为跨学科的研究内容,但涉及该领域的术语表达非常灵活,特别是英文词汇Public Opinion的中文翻译更是五花八门。此外,目前能够被广大学者所接受的网络舆情概念表述的范畴界定过于狭窄,其涉及的学科边界比较模糊。”
public opinion作为社会科学中最古老但最不被理解的概念之一,困扰着来自传播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关于“public opinion”在英文中词义的演化历史,Binkley在1928年指出其从一个有着哲学主体内涵的的词,向具有社会科学系统化研究意义的词转变。
这个术语可以定义为是一种对相关群体对特定问题持有的观点和情绪衡量。public opinion具有一种语法的内部矛盾:虽然“公共”代表群体和普遍性,但“舆论”本身通常与个人相关,并被认为是一种内部、主观的表述。20世纪初调查研究的兴起,进一步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将量化公众舆论作为个人调查反应的简单汇总,并将之作为测量群体社会力量的标准。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延续对公众舆论的量化级定义,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魏格尔在2008年提出,通过一种实证的方法,在互联网上测量公众舆论,首先就关注的事件或者话题用搜索引擎检索所有网页,之后对这些网页中呈现的内容进行分析。为了回答应用这种方法反应了哪种公众舆论的理论问题,他讨论了到那时为止几乎没有联系的两种基本的舆论范式,即作为话语的舆论和通过调查来衡量的舆论。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又基于搜索引擎进行内容分析,这是第一次对两种舆论研究的范式进行经验性比较。以餐馆禁烟这项政策的实施推广为研究案例,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另一方面通过网络舆论文本的内容分析,最后揭示出两种方法对于本案例中舆论的相似和差异,得出与理论假设非常吻合的结论。论证了在网络舆论研究中对具体案例的网页文本做内容分析的科学性,在之后的十年间,该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在世界网络舆情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此外,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团队,在2019年最新的研究《“挑选和选择”的意见环境:通过对政治信息的浏览,如何塑造公众舆论的看法和态度》,指出算法选择推送信息的媒体环境,使人们只愿意浏览自己愿意阅读的新闻信息,形成了信息茧房。这就可能形成个人态度的偏见。这项研究建立在积极的认知和沉默螺旋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判断如何浏览政治信息(公众是阅读通过算法推荐的、选择性曝光的文章还是阅读未经算法筛选的、偶然遇到的文章),测量如何形成公众舆论和公众态度。参与者(N=115)浏览有争议主题的在线文章,相关态度和舆论观念被先后搜集,通过多级建模证明了确认偏差,研究结果表明选择性曝光的文章和偶然性阅读的文章,都会影响公众对每个消息的态度。但是,选择性曝光被推荐阅读的文章中的观点,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更大。即意见环境中对政治信息态度的认知,与信息的选择性推送有显著联系。
基于这些研究,部分学者将网络舆情的概念定义为,可以量化的网络公众舆论,用于反映部分社会真实,指导实践。一方将公共舆论视为公众反映的集合,而另一方则认为公共舆论是通过对媒体的使用,形成对社会建构的力量。基于此传统,延续到网络时代,国外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在大方向上也认为:有网络舆情可测量、可验证,网络舆情是民意情绪的反应两种概念路径。
三、界定路径:“为政治服务的民意”,还是“对网络民众情绪的引流”
根据出发点不同,国外网络舆情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是为政治服务的民意,二是对网络民众情绪的引流。鉴于此,了解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中对网络舆情概念的认知,并对其研究的具体实例进行阐释、对比和广义范围内的分析,对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就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一)引流——对网络民众情绪的引流
基于网络舆情是民意情绪反应的概念,并根据所搜集的在线数据,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视为“引流”。2011年约翰·博伦等三位学者,就2008年下半年微博平台Twitter上发布的所有推文进行了情绪分析。研究者使用心理测量工具,从汇总的Twitter内容中提取六种情绪状态(紧张、抑郁、愤怒、活力、疲劳、混乱)。计算时间线中每天的六维情绪向量。之后,将结果与从媒体收集的热门事件的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事件,确实对公众情绪的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直接和高度具体的影响。最后结合对情绪的大规模分析,根据对现有社会和经济指标的预测,来模拟集体情绪趋势,判断网络舆情的走向。该研究迄今在网络舆情研究中,引用次数多达1000+,由此推之,网络舆情概念认知的一个分支,即为网络民众情绪认知趋势。在对此概念的研究中,还有学者依据网络中民众的情绪,进行股票趋势预测指导民众投资,依据网络民众情绪进行医学研究,包括对癌症的一些前沿研究,对疫苗信息语义网络进行情感分析,并协助相关公共卫生医疗机构进行沟通等。
同时,将公众情绪作为分析概念,依赖于个人情绪的研究,以此来探索公众的情绪,成为网络舆情研究中的一个落脚点。此外,还有学者以公众舆情中的情绪研究为出发点,构建语料库,用以评测新闻传播中的情感、个性和网民互动风格的界定,研究网民在阅读相关文章时,产生共同或者相同情绪的相关性等。
另外,公共舆情聚焦最多的网络驻足点为社交网络。有学者讨论将社交网络(SNS)作为虚拟公共领域的想法,通过民意调查和社交网络情绪分析之间的关系,探讨是否将来政治家能够“以情绪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将美国现存的政治体系转变为“情感民主”,同时还讨论了社交媒体在塑造政治机构组织,特别是政党方面的潜在作用,建议社交网络可以为党内互动提供虚拟空间,这可以促进一定程度透明度的提升和问责制的形成。以此窥见网络舆情概念中情绪“引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络。
(二)“服务”——社会长治久安对网络舆情的要求
沿用美国实证主义研究的习惯,新闻媒体至今存在着导向性的影响,被称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即是舆情的一类研究导向。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广泛关注。自Maxwell McCombs(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和Donald Shaw(唐纳德·肖)的开创性实证研究以来,截至上世纪90年代,已出版了100多篇期刊文章,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Sage,在1996年将这些研究加以整合,出版了议程设置合集,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了,“对议程设置中基本假设的测试、影响这种影响力的偶然条件、公共问题产生的自然历史条件、大众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总统团队中的公共关系人员在新闻议程上所形成的作用等相关的研究”。而后舆情研究延伸至网络时代,从线下延展至线上空间的网络舆情,天然地延续了之前的传统,它是与“外交政策、重大改革、民生事务、热门产品等事物形成联结的议题。这样的研究都是基于社会长治久安对网络舆情的要求,视为为政治“服务”。
例如在《利用社交媒体衡量外交政策动态:对伊朗与以色列对抗的实证分析(2012-13)》一文中,重点将网络舆情聚焦于社交媒体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即社交媒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讨论,是否是有意义的政治竞争的反映?如果是这样,它可以揭示什么样的关系,以及社交媒体上产生的内容,作为学者数据使用的局限性是什么?这些问题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很重要,因为社交媒体及其衍生的数据,在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者用在Twitter上使用关注者关系,来构建伊朗和以色列不同外交政策讨论网络的地图,以及来自伊朗和阿拉伯博客圈的数据,分析关于此事件的网络舆情走向。”同时,哈佛大学学者马修·鲍姆关于特朗普时代外交政策的研究,就是基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体、网络舆论和外交政策为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展开的。
基于此,研究者展示了学者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数据和网络,对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做出有意义的推论。而且,还概述了如果学者在研究时不小心可能导致的陷阱和不正确的推论。这样的研究,就是基于对网络舆情概念理解,最重要的站位,是为政治和统治服务的。

因此,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互联网评论是网络舆论的晴雨表——研究者开发了一种新方法,用估测的方法,来跟踪特定发展的新闻故事,它在互联网社区的社会影响。该技术源于磁系统的平均场处理的方法,提供了一种互联网社区稳定性的测量方法,分析了CNN新闻网站发布新闻故事的几个实例。例如,在宣布重要信息(例如法律案件中的陪审团决定)之后,观察到社会影响力与时间的连续动态,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显著增加。这项工作使通过估测有序发布信息改变网络群体的意见成为可能。因而认为,互联网评论可能预测社会反应的程度,类似于晴雨表,预测在仍然平静的环境中风暴的强度。以网络舆情研究为立场,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推行和落实效果、口碑意见的评测,有技术上的优势和积极调节作用。
从联邦宪法法院判案的角度,学者本杰明恩斯特纵向观察思考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对现代法律体系的影响,对引用互联网的2000年至2013年联邦宪法法院所有222项决定,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判出互联网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决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借鉴于哈贝马斯“公众在产生主流观点或通过理性话语产生的公众舆论意义上具有整合或中介功能”的观点,菲利克斯克雷伯声明,“公众应被理解为现代社会的产物”。
在《衡量传播通信科学的状态和特征》一文中,关于网络舆论,弗兰克M.施奈德等三位德国学者指出,沉默螺旋理论在现今网络时代的发展,可借鉴潜伏状态-特质理论(LSTT)在调节心理状态和人格特质发挥关键作用方面的内容。该文指出LSTT理论对当前网络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的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参照。借鉴了LSTT理论的简要概述,指出其与传播研究的相关性和应用潜力,对政治传播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LSTT的优势,并讨论出LSTT对最小媒体效应的价值。
还有,就基于社交网络所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也是在试图探讨舆情作用于政治,促进现代政治发展的实际影响等内容。以此为目的的研究,还有学者使用将网络超链接分析,与定性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分析了2014年1月至11月,关于美国网络中立性的公开辩论,得出通过互联网公共领域共同合作的各个参与者,在扭转联邦通信委员会关于网络中立的政策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对网络舆情研究在互联网公共领域进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
同时,有学者专注于使用新技术,将网络舆情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加以落地,让生活更美好。如以芬兰奥卢市为例,使用了城市普及技术,即将网络数字时代的技术,与公民对这些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和城市规划相结合。在智慧型城市的社区中,公民利用网络与新技术,来听取和表达意见,应用了公共交互式众包技术,提供让公民与官员合作参与政治的网络技术平台。
立足于“服务”政府的网络舆情研究,不仅仅聚焦关注线上社交媒体中的民意,还扩张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范围,包括新闻、各类信息积聚的平台中,民众的评论与辩驳;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对现代法律体系的影响;网络舆情在线上空间中所蕴含的关系,到线下能对政府的管理产生什么样实际意义的“服务”等。
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最新研究指出,互联网及其周边技术,有望重振公共领域。然而,这些新技术的几个方面,既一边削弱又一边增强了这种潜力。首先,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存储和检索功能,将政治讨论与其他方面无法获得的信息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和新媒体素养的能力高低,损害了虚拟领域的代表性。其次,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可以促进全球各地人们之间的讨论,但也经常使政治话语破碎化。第三,鉴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基于网络的技术,有可能适应当前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互联网和相关技术,为政治导向的对话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是否超越了公共领域,取决于技术本身。
基于本文研究者所选取对国外网络舆情研究的两个不同的研究立场,只是现今国外网络舆情研究中运用和关注度较高的方向,除此之外未能涵盖。但是在国内被归于网络舆情研究的商业舆情等内容,并未纳入这两个具体而微的研究分支中。二分法的使用,不是为了大全,而是为了突出重点,展现本研究在最为重要的两个研究方向上的专注性,更能体现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四、网络舆情概念研究总述
基于国外在网络舆情大内涵之上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在为了政治统治需要所进行的网络舆情的研究立场,其所界定的概念是网络舆情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运用可测量、可观测、可预测和可以控制的各种手段,去维护现有统治,或更好地帮助稳固现有统治的稳定性的研究。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网络舆情的研究,对其概念的立场界定是引流,即在尊重网络舆情不论是情绪还是心情或是民意等的立场上,借助有效科学的评测研究,用以指导经济生活发展、促进医学科技进步等。
不论是基于“引流”,关注网络舆情中民众情绪、心情趋势的研究,还是基于“服务”,关注导向正确,以政治统治为导向的“服务”研究,对网络舆情概念的研究,都是立场不同的导向所致。国内也有学者在探讨“媒体审判”与“舆论审判”的关系,但由于资料获取的难度、研究方法的滞后等原因,未有运用实证方法,对媒体报道与法律判决之间的隐形勾连,做出有着实际参考意义的研究,基于此,可借鉴德国学者本杰明·恩斯特最新的研究成果《现代时代:联邦宪法法院之前的互联网》,来看待国内由线下事件暴发引爆网络舆情的判决,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给中国现代法制化进程做注脚释义。
另外,德国学者在舆情研究中,运用最小媒体效应的研究、潜伏状态-特质理论(LSTT)等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视角,也是我们国内网络舆情研究未有涉猎的,值得探讨深挖。欧美国家基于技术的角度对网络舆情研究的视角,也是国内舆情研究值得借鉴的角度。还有学者提出了全交往时代公众审判的概念,在研究中介绍和发展了“全交往或译为充足交流(communicative plenty)”的概念,用来支撑当代民主国家在线面对面交流中不断增加的影响。借鉴最近在协商民主中的思考,研究认为,交流充足可以为大规模的公共审议提供可行的背景,条件是:声音和表达的空间伴随着充足的反思和倾听空间;并且集体决策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表达,然后是倾听和反思。分析表明,设计反思和倾听的空间,是增强公共审议和民主的实用手段,特别是在容易受到表达超载和交往充足的民主病态的情境中。
结合国内对网络舆情概念的界定,“从广义上讲,网络舆情是以互联网为载体,是广大网民针对特定关注对象所产生的所有看法、认知、态度、意见、情感、思想、意愿、心理、观点等具有倾向性意识形态的网络表达、互动、传播和演化等活动的集合。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只是社会舆情的局部映射,与社会整体的全局性意见或情绪不同,它只能反映网络上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意愿或情感表达。”笔者认为,网络舆情概念因其所生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土壤”的不同,内涵和外延有着极深极为复杂的认知。但是,网络舆情这个概念一定不是现在国内学界所认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抽象化概念”,而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网络普及的国家,和网络迅速发展的国家中,都存在并被广为关注,且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进行研究的焦点研究所在,是处于秉轴持钧的地位。依据此核心焦点的关注,国内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持下,都在一边抓技术一边抓数据,甚至会有“信息革命中最重要的资源是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的论断。但不论是何种概念界定,或概念立场的分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网络舆情研究是当今社会最为重要的研究热点和焦点,把握网络舆情的主导权、话语权是推动社会经济科技等进步的一大动力支持,且对此研究的关注,是现行世界范围内各个政体的聚集发力点之一。
【注释】
[1]左蒙,李昌祖.网络舆情研究综述: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J].情报杂志,2017(10):75-82+144.
[2]邢梦婷,王曰芬.国内外社会舆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11):139-144.
[3]Bollen,J.,Mao,H.,&Pepe,A.Modeling public mood and emotion:Twitter sentiment and socio-economic phenomena[C].In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2011,July.
[4]Shih,H.,&Xue,J.How China Monitors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D].2018.
[5]Tan,S.,Li,Y.,Sun,H.,Guan,Z.,Yan,X.,Bu,J.,...&He,X[J].Interpreting the public sentiment variations on twitter.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2013(5):1158-1170.
[6]王连喜.网络舆情领域相关概念分布及其关系辨析[J].现代情报,2019(6):132-141
[7]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 B/O L].新华社,20180822.h t t p://w w w.g o v.c 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8]资料补充,发表于2010年《现代传播》中的《网络舆情的概念解析》,参考文献共计5个,全部为中文文献;发表于2015年《情报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内外社会舆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参考文献共计32个,其中20个中文文献,12个英文文献;发表于2018年《情报杂志》中的《移动环境下网络舆情研究进展及述评 》,参考文献共计55个,全部为中文文献.
[9]郜书锴.“公共舆论”还是“公众意见”?——兼对 Public Opinion 术语不同翻译的商榷[J].国际新闻界,2009(10) :22-26.
[10]史文静.近现代中国“舆论”语义内涵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5 (2) :77-88.
[11]王连喜,曹树金.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研究主题比较分析——以国内图书情报学和新闻传播学为例]J].情报学报,2017 (2) :159-169.
[12]王连喜.网络舆情领域相关概念分布及其关系辨析[J].现代情报,2019(6):132-141.
[13]王连喜.网络舆情领域相关概念分布及其关系辨析[J].现代情报,2019(6):132-141.
[14]Binkley,R.C.The concept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J].Social Forces,1928(6):389-396.
[15]Glynn,C.J.,&Huge,M.E.Public opinion[M].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2008:101.
[16]Schweiger,W.,&Weihermüller,M.ffentliche Meinung als Online-Diskurs-ein neuer empirischer Zugang[J].Publizistik,2008(4):535-559.
[17]Sude,D.J.,Knobloch-Westerwick,S.,Robinson,M.J.,&Westerwick,A.“Pick and choose”opinion climate:How browsing of political messages shapes public opinion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J].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19:1-22.
[18]Glynn,C.J.,&Huge,M.E.Public opinion[M].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2008:132.
[19]Bollen,J.,Mao,H.,&Pepe,A.Modeling public mood and emotion:Twitter sentiment and socio-economic phenomena[C].In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2011,July.
[20]Bollen,J.,&Mao,H.Twitter mood as a stock market predictor[J].Computer,2011 (10):91-94.
[21]Rodrigues,R.G.,das Dores,R.M.,Camilo-Junior,C.G.,&Rosa,T.C.SentiHealth-Cancer:a sentiment analysis tool to help detecting mood of patients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2016(1):80-95.
[22]Kang,G.J.,Ewing-Nelson,S.R.,Mackey,L.,Schlitt,J.T.,Marathe,A.,Abbas,K.M.,&Swarup,S..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of vaccine sentiment in online social media[J].Vaccine,2017(29):3621-3638.
[23]Ringmar,E.What are public mood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18(4):453-469.
[24]Celli,F.,Ghosh,A.,Alam,F.,&Riccardi,G.In the mood for sharing contents:Emotions,personality and interaction styles in the diffusion of news[J].Information Processing &Management,2016(1),93-98.
[25]Ceron,A.Conclusion:A Sentiment Democracy?--I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197-210.
[26]Dearing,J.W.,Rogers,E.M.,&Rogers,E.Agendasetting[M].Sage,1996 (Vol.6):55-106.
[27]王连喜.网络舆情领域相关概念分布及其关系辨析[J].现代情报,2019(6):132-141.
[28]Zeitzoff,T.,Kelly,J.,&Lotan,G.Using social media to measure foreign policy dynamic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ranian-Israeli confrontation (2012-13)[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15(3):368-383.
[29]Baum,M.A.,&Potter,P.B.Media,public opinion,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J].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9(2):747-756.
[30]Oster,E.,Gilad,E.,&Feigel,A.Internet comments as a barometer of public opinion.[J].EPL (Europhysics Letters),2015(2),28005.
[31]Engst,B.,&Hönnige,C.Modern Times Das Internet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M].Netzpolitik 2019:163-187.
[32]Habermas,J.,&Philip Brewster and Carl Howard Buchner.Special walter benjamin issue || consciousness-raising or redemptive criticism:the contemporaneity of walter benjamin.[J].New German Critique,1979(17):30-59.
[33]Theis-Berglmair,A.M.Öffentlichkeit und öffentliche Meinung.[M].In Handbuch der Public Relations,2015:399-410.
[34]Schneider,F.M.,Otto,L.,&Bartsch,A.Das ist doch kein Zustand! Zur Messung von States und Traits in der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J].M&K Medien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2017(1):83-100.
[35]Faris,R.,Roberts,H.,Etling,B.,Othman,D.,&Benkler,Y.Score another one for the Internet? The role of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in the US net neutrality policy debate[M].Berkman Center Research Publication,2015(4):251.
[36]Hosio,S.,Goncalves,J.,Kostakos,V.,&Riekki,J.Crowdsourcing Public Opinion Using Urban Pervasive Technologies:Lessons From Real-Life Experiments in Oulu[J].Policy &Internet,2015(2):203-222.
[37]Papacharissi,Z.The Virtual Sphere.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M].In Praktiken der berwachten,2019:43-60.
[38]赵金.从“媒体审判”到“舆论审判”——信息社会化传播中的传播伦理和法律建设反思[J].青年记者,2018(36):88-89.
[39]Engst,B.,&Hönnige,C.Modern Times Das Internet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M].Netzpolitik 2019:163-187.
[40]Ercan,S.A.,Hendriks,C.M.,&Dryzek,J.S.Public deliberation in an era of communicative plenty[J].Policy &Politics,2019(1):19-36.
[41]王连喜.网络舆情领域相关概念分布及其关系辨析[J].现代情报,2019(6):132-141.
[42]王连喜.网络舆情领域相关概念分布及其关系辨析[J].现代情报,2019(6):132-141.
[43]孙正义:信息革命中最重要的资源是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EB/OL].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4DF75HM0514BS3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