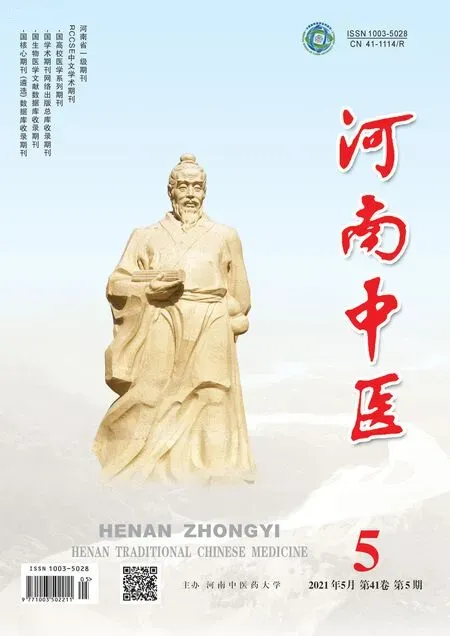刘健从“太少两感”辨治急性脊髓炎所致神经源性膀胱
常宁,刘健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刘健教授是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师承全国名老中医李七一教授,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30年,经验丰富,精通经典,擅长运用《伤寒论》经方治疗疑难疾病。笔者2018年冬季罹患急性脊髓炎,导致以神经源性膀胱、尿潴留为主要表现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以致无法工作,生活失能,幸得刘健教授诊治,得以痊愈,至今无反复和后遗症,兹将其对该病的诊治思路介绍如下。
1 急性脊髓炎所致神经源性膀胱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神经源性膀胱诊断治疗指南》指出:神经源性膀胱是一类由于神经系统病变导致膀胱和/或尿道功能障碍(即储尿和/或排尿功能障碍),进而产生一系列下尿路症状及并发症的疾病总称。反射过程由交感、副交感和脊髓神经支配,并受到脊髓中枢和脊上高级排尿中枢控制,脊髓中枢位于圆锥(骶2~4),脊上中枢位于大脑皮质、丘脑、基底核、边缘系统[1]。一般膀胱容量200 mL时会有尿意,达到400 mL以上急需排尿。兴奋冲动主要由盆神经的感觉支经脊髓中枢传入大脑皮层,条件允许时,脊上中枢解除对脊髓中枢的抑制,脊髓中枢兴奋以盆神经为主的运动神经,使膀胱逼尿肌收缩,膀胱颈部、会阴部肌肉松弛开始排尿。尿液排空后,盆神经的感觉支将信号传到大脑皮层,脊上中枢又重新控制脊髓中枢[2]。所有累及储尿和/或排尿生理调节过程的神经系统病变,都有可能影响膀胱和/或尿道功能[3]。
急性脊髓炎是指各种感染后引起自身免疫反应所致的脊髓炎性病变,以病损平面以下肢体瘫痪、传导束性感觉障碍和尿便障碍为临床特征[4]。病变局限于脊髓的数个节段,以髓鞘肿胀、脱失、轴索变性、周围淋巴细胞显著增生及血管周围炎症细胞浸润为主要病理改变[5]。分子模拟学说认为,病原微生物的抗原和人体髓鞘蛋白存在同源片段,可以刺激产生免疫T淋巴细胞,在清除病原微生物的同时,损害了中枢神经系统髓鞘蛋白,引起多发的播散性脱髓鞘病变[6]。病损在骶髓平面以上时由于骶髓内的排尿中枢失去了脊上中枢的控制,表现为逼尿肌反射亢进及反射性排尿;若发生在骶髓部,则因排尿中枢受损而表现为逼尿肌无张力,形成低张力、无反射的弛缓性膀胱和尿潴留[7]。神经源性膀胱导致患者工作生活障碍,引起反复的尿路感染、泌尿系统结石、肾积水和肾脏功能衰竭[8-9]。
2 中医病机与伤寒“太少两感”相关
急性脊髓炎症状复杂,诊疗困难,无中医病名与之相应,但其发病前多有感冒、发热、腹泻等外感病史,随后出现程度不等的神经系统炎症损伤,表现为严重的运动、感觉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据此,刘健教授判断其病机应为体虚内伤,感受外邪,越经而传,直中少阴,以致表里同病,真阳失运,形成《伤寒论》所谓“太阳、少阴两感”的中医病理状态。中医大家戴丽三认为,少阴里实,太阳方能主表,而太阳表固,少阴即可主里,若太阳失固、少阴里虚,则可见“太少两感”之证[10]。
少阴病为里虚证,以虚为主,证候复杂。《伤寒论》第281条言:“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为少阴病提纲,病理特征是心肾阴阳俱虚,以肾阳虚衰为主,具体分为本证、兼变证和咽痛证。“太少两感” 属于少阴兼变证,即“少阴病阳虚兼表证”,相互表里的阴阳两经及所属脏腑同时感受寒邪,营卫气血因寒凝而不畅,导致脏腑俱伤,气血俱虚,病情复杂,病势较重,传变迅速,易出现亡阳脱液或阴液消亡的危重证候[11]。《素问·热论》有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
神经源性膀胱的典型症状有尿急、尿频、小便不利、排尿困难、尿液潴留等,《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膀胱是肾之腑,肾阳是膀胱气化之源,同时膀胱又属于足太阳经,太阳经亦称巨阳,是人身经脉阳气最盛之处,《素问·热论》言:“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伤寒论》也将小便不利及水气内停的病证归于诸太阳病证中,说明太阳经气盛衰对于膀胱的气化功能具有重要影响[12]。因此,刘健教授指出体虚外感,或寒邪过甚,内舍于太阳经膀胱之腑,少阴经肾阳虚衰,以致太少两感,经气闭塞,膀胱气化无力,水道失司,而成膀胱蓄水之证,其临床表现多与少阳虚衰,太阳膀胱气化不利有关。
3 治当温补肾阳,固本祛寒,化气利水
急性脊髓炎等神经系统炎症的治疗主要采用类固醇皮质激素如甲泼尼龙抑制炎症反应,或者联合免疫球蛋白等抑制免疫、减轻炎症[13],但同时也削弱了免疫系统对病毒等外源致病微生物的清除,引发继发损害和并发症,对治疗可能有害[14]。刘健教授基于“太少两感”病机,运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真武汤、五苓散等经方组合化裁,效果满意。其中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散寒,助阳开表,祛除外邪,是《伤寒论》第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的经典治法,可交通表里,祛邪外出;真武汤温肾阳制寒水,可补阳固本,温暖心脾;五苓散通阳化气,促进膀胱气化,恢复排尿行水功能。
钱潢《伤寒朔源集》释义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发太阳之寒,以解其在表之寒邪;以附子温少阴之里,以补其命门之真阳;又以细辛之气温味辛,专走少阴者,以助其辛温发散”。针对体虚外感,寒入骨髓,太阳、少阴两感合病,当以麻黄、附子、细辛、干姜、吴茱萸温阳祛寒,内补少阴肾阳,外开太阳卫阳,表里两经同治,“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佐以桂枝、茯苓、白术、芍药、杏仁等交通心肾,化气利水,助膀胱气化。熊兴江[15]用《千金要方》小续命汤治疗面神经炎、四肢无力、急性脊髓炎、急性神经根炎、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等神经系统疾病,麻黄是起效关键。
刘健教授指出,治疗疾病不可被表面症状迷惑,要准确推求病机,立法选方,纠偏制衡,如《黄帝内经》言:“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同时要注意疾病发展的具体阶段,辨别轻重缓急,灵活论治。若阳衰欲脱,当急救其里,纵有表证,亦不可发汗。待病因祛除,病情稳定,以党参、黄芪、山药、山萸肉、薏苡仁、五味子等温养脾肾,益气固本,巩固善后,可获良效。
病案:常某,男,50岁,ICU医师,2018年12月初夜间感受风寒,畏寒乏力,未在意。3 d后出现发热,头痛目眩,浑身疼痛,甚至翻身、起坐困难,乏力,体温39 ℃,恶寒无汗,疲惫虚弱,梦扰难眠,不欲饮食,自行服用感冒药。1周后出现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查血钾3.24 mmol·L-1、钠123.3 mmol·L-1、氯90.2 mmol·L-1、肌酸激酶528 U·L-1、肌酸激酶同工酶18 U·L-1、肌红蛋白150.5 μg·L-1、D-二聚体1.17 mg·L-1、白细胞计数6.34×109L-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58.7%、血红蛋白136 g·L-1,于2018年12月16日住院治疗。当时低热乏力、肌肉酸痛、尿频,1~2 h 1次,每次量少,夜不能寐,无便秘。查体:体温37.3 ℃、心率80次·min-1、呼吸18次·min-1、血压122/67 mm Hg(1 mm Hg=0.133 kPa),神清,皮肤黏膜无黄染、皮疹及出血点,口唇无紫绀,两肺呼吸音清,心律齐,心脏无杂音,腹软无压痛,肝脾肋下未及,双肾区叩击痛阴性,双下肢无水肿,无病理反射。诊断为中医:淋证(湿热下注证);西医:急性前列腺炎。予头孢曲松、钾剂、热淋清颗粒、滋肾通关胶囊、琥珀酸索利那新、盐酸坦索罗辛、锯叶棕果实提取物软胶囊等治疗。B超发现:“膀胱残余尿约900 mL、双侧肾脏集合系统分离”,予保留导尿,甲钴胺片营养神经,配合雷火灸(气海、中极、关元、足三里),耳穴压豆(三焦、肾、输尿管、尿道)等治疗。中医方面:舌淡胖,苔薄白,脉数,辨为脾肾气虚,气化不利,治以益肾健脾,化气利水,以五苓散加减。一周后见舌淡胖边有齿痕,苔薄黄腻,脉虚数,辨为脾肾气虚,湿热下注,改为益肾健脾,清利湿热法,但症状依旧,拔除导尿管失败,又重新导尿。复查肌酸激酶226 U·L-1、肌酸激酶同工酶16 U·L-1,柯萨奇病毒、EB病毒、巨细胞病毒及结核检测阴性,肌电图示:“双侧下肢体感觉诱发传导通路障碍”,不排除病毒感染侵犯神经系统致脊髓损伤,但头部、颈椎、胸椎、腰椎核磁检查未发现明确相关病变。由于诊断存疑,导尿后无排尿感,反时有尿道刺激和膀胱痉挛,下腹部憋痛难忍,心中忧虑,畏惧腰穿、尿动力学等检查,不敢轻易使用激素,于2019年1月2日行“膀胱造瘘术”后带造瘘管出院。
患者患病后体质量骤减20 kg,头痛失眠,心慌低热,目眶胀痛,久视则头眩,手颤致写字不清,站立不稳如踩棉花,畏寒无汗,皮肤干燥,双腿大量脱屑,溲清便软,舌淡苔薄白,脉细数。刘健教授结合院内外专家意见,诊断考虑未明确的病毒感染引发急性脊髓炎,骶髓损伤可能,导致神经源性膀胱和尿潴留。中医病机为冬季体虚复感,寒中受寒,侵入骨髓,太阳、少阴两感合病,以致阳虚寒盛,膀胱气化失司,小便不利,以真武汤合五苓散加减温补肾阳,化气利水,药物组成:制附子(先煎)10 g,肉桂3 g,茯苓 15 g,生白术10 g,泽泻10 g,猪苓10 g,桂枝6 g,炙甘草3 g,细辛3 g,白芍10 g,炮姜10 g。7剂,日1剂,水煎服。服药后患者自觉腹中温暖,精神好转,食欲改善,渐有气力,头眩、手抖减轻,小腹不再憋痛,能耐受膀胱造瘘管,小便量多,颜色清。2019年1月11日复诊,舌淡苔白腻,脉小弦,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五苓散加减,温经散寒,助阳开表,化气利水,药物组成:制附子(先煎)10 g,茯苓15 g,生白术10 g,桂枝 10 g,白芍10 g,炙甘草6 g,细辛3 g,麻黄10 g,吴茱萸3 g,柴胡15 g,猪苓10 g,泽泻10 g,杏仁10 g。7剂,日1剂,水煎服。2019年1月21日复诊,病情明显改善,有汗出,发热肌痛消失,双腿皮肤脱屑现象减轻,定时夹闭膀胱造瘘管时出现了轻度尿感。舌淡胖,苔白腻,脉稍弦弱,调方续服,药物组成:制附子(先煎)10 g,细辛3 g,薤白10 g,吴茱萸3 g,当归10 g,柴胡15 g,茯苓15 g,猪苓10 g,泽泻10 g,桂枝10 g,黄芪15 g,白芍10 g,炙甘草 8 g。7剂,日1剂,水煎服。药后夜寐安和,进食量增,夹闭膀胱造瘘管后可自行小便,于2019年2月1日拔除膀胱造瘘管,但拔管后又不能排尿,残余尿量近 500 mL,再次留置导尿管,继续服用中药温阳固精,益气行水,药物组成:制附子(先煎)10 g,茯苓15 g,猪苓10 g,黄芪15 g,麦冬10 g,党参10 g,五味子 10 g,桂枝10 g,生白术10 g,白芍10 g,怀山药 20 g,山萸肉10 g,炙甘草8 g。服药至2019年2月下旬,成功拔除导尿管,未出现反复。平素易感疲乏,尿频,夜尿多,舌淡苔稍腻,脉弦弱,改服下方善后,药物组成:制附子(先煎)9 g,桂枝10 g,柴胡 10 g,吴茱萸 5 g,当归10 g,生薏苡仁10 g,怀山药30 g,山萸肉10 g,党参10 g,五味子10 g,白芍10 g,炙甘草8 g。30剂,日1剂,水煎服。
按:发病初始,类似严重流行性感冒,发热身痛,头痛目眩,肌酶、肌红蛋白升高,很快出现神经源性膀胱和尿潴留,可能为病毒感染直接侵害或诱发炎症损伤骶髓。伴有皮肤无汗、下肢干燥脱屑等交感神经功能障碍表现。由于脊上中枢不能感知膀胱充盈后的排尿冲动,不能解除对脊髓中枢的抑制,同时脊髓中枢也不能兴奋膀胱的运动神经,逼尿肌无收缩排尿。尿液潴留超过膀胱容积,导致充溢性尿失禁,出现频繁小便,每次尿量却极少,伴有皮肤无汗、下肢干燥脱屑等交感神经功能障碍。留置导尿管后,由于异物刺激和继发感染,反而引起强烈的尿道刺激症状和难以抑制的膀胱挛缩。
虽然膀胱造瘘暂时解除了排尿困难,但是病邪未去,头痛失眠、心慌低热、目眩手颤、畏寒无汗、皮肤干燥脱屑、消瘦乏力、舌淡苔薄白、脉细数。《伤寒论》第82条言:“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患病后畏寒无汗,刘健教授认为不存在汗出伤阳的情况,说明寒邪过甚,肾阳虚惫,水气泛逆,浊阴上扰,而舌淡脉细数提示体虚正伤,虽有表寒也不宜匆忙解表发汗,当用真武汤温肾阳制寒水,补阳固本,温暖心脾,扶危济困,联合五苓散化气行水,增强肾脏、膀胱的气化功能,方中肉桂、桂枝同用,补火助阳,又以细辛通经祛寒止痛。
药后渐感胸腹变暖,精神转振,头痛目眩消失,手抖减轻,食欲改善,仍有低热怕冷,倦怠无汗。针对“太少两感”的基本病机,刘健教授以麻黄附子细辛汤散表寒,利内湿,柴胡、吴茱萸畅达肝气,疏肌解表,佐用杏仁推动气机升降,白芍防止辛热伤阴。服用该方后少阴经肾阳渐强,太阳经卫表得固,腠理开阖有度,水液气化循行,伏邪得以透发消散,方证相符,切中病机,因此自感低热畏寒消失,皮肤见汗出,双腿干燥脱屑明显减轻,尤其是夹闭膀胱造瘘管时出现尿感,意味着脊髓神经功能开始恢复。
为防止汗出有损,10余剂药后减去麻黄,予黄芪、当归益气祛风,散寒通络,益气扶正,薤白通阳散结行滞,促进膀胱功能逐渐改善,慢慢可自行排尿。虽然过早拔除造瘘管后出现反复,但病情总体向好,再次留置导尿后,也明显有膀胱收缩时的排尿感。随后又以党参、怀山药、山萸肉、薏苡仁、五味子补益脾肾,固本培元,病终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