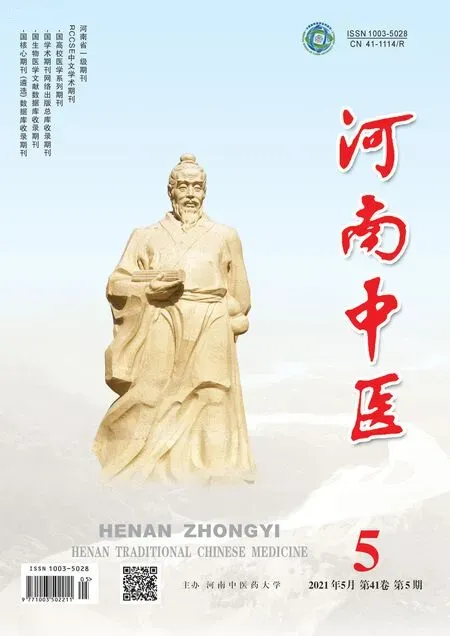燕树勋应用黄药子治疗甲状腺疾病经验*
巴明玉,余丹丹,王娴,万红,潘研,2,陈亚琳,郭盼盼,燕树勋,2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湖北陈氏瘿病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河南工作站,河南 郑州 450001
中药黄药子始载于宋代《开宝本草》,为薯蓣科植物黄独的块茎。其可治疗甲状腺疾病始载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月令》,“万州黄药子,可疗忽生瘿疾一二年者”。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其效能:“凉血降火,消瘿解毒”,为后世治疗甲状腺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其药用历史悠久,作为一味具有独特性味和功效的中药,在中医药治疗甲状腺疾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本草汇言》中就明确记载:“黄药子解毒凉血最验……今人不复用者,因久服有脱发之虞,故其为凉血散血明矣。”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药子可引起肝肾功能损伤的报道屡见不鲜,严重者可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1],使其在中医甲状腺疾病治疗中存在较多的桎梏。燕树勋教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陈如泉教授,是湖北陈氏中医瘿病学术流派主要传承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科技创新杰出青年,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根据甲状腺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证候特点,临床应用黄药子辨证治疗甲状腺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黄药子的药性
1.1 性味归经其性味,《开宝本草》记载:“黄药子苦,平,无毒”,《滇南本草》载:“性大寒味苦”,《食物考》曰:“辛,寒,微毒”,1963年《中国药典》记载,其性平,味苦,(《中国药典》1977年版收载)性气微,味涩,苦。其归经,《神农本草经疏》载:黄药根“入手少阴、足厥阴经”,《罗氏会约医镜》云:“入肺、肝经”,可见,黄药子味苦,性寒,归肺、肝、心经。《滇南本草》云:“攻诸疮毒,止咽喉痛,利小便,走经络,治筋骨痛、痰火、手足麻木、五淋浊白、妇人赤白带下,治痔瘘亦效”,《药性论》记载:“治水气浮肿,下小便,治嗽逆上气,项下瘤瘿”。燕树勋教授认为,其主入肺、肝二经,具有清热凉血、化痰散结、解毒消瘿之功效,临床常用于痰热瘀结等病证。
1.2 毒性《本草拾遗》云:“土芋蔓生,叶如豆,其根圆如卵,食后弥吐,人不可食”。可见,人们已经认识到黄药子的毒性,在此之前的《证类本草》《本草经疏》及《开宝本草》均认为其无毒。《有毒中药大辞典》明确将黄药子纳入有毒中草药的行列[2]。临床上,黄药子的煎汤内服常用量为3~9 g[3]。燕树勋教授临床应用黄药子入汤剂,剂量多以9 g为主,并注意药物之间的配伍以减轻其毒性,自拟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活动期的泻火平突散及稳定期的活血平突散,其黄药子的剂量均为9 g。
2 黄药子的功效
黄药子又名黄独,《本经逢原》载:“甘辛寒,小毒,不可溺灌,灌之则苦”,主入肺肝二经。苦味药能泻、能燥、能坚,具有清泻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等作用,所以临床上苦味药多用治热证、火证[4]。苦寒可泻火、解毒、消肿、凉血、止痛等[5]。故黄药子具有多种功效,如清热凉血、化痰散结、泻火解毒、消肿止痛、消瘿散结等。燕树勋教授在甲状腺相关疾病的辨证论治中,多着眼于肝络,正如《知医比辨》云:“五脏之病,肝气居多”,多选用黄药子清肝泻火止痛、化痰散结消瘿、利水通络消肿。
2.1 重在走肝络,连目系《灵枢·经脉》云:“肝足厥阴之脉,……属肝,络胆,……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6]。根据甲状腺的生理解剖位置,肝经同时连接甲状腺与目系,中医学认为,甲状腺疾病归“瘿病”“瘿瘤”之范畴。依据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燕教授认为,甲状腺相关疾病与各个脏腑均有关系,但主要责之于肝,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云:“瘿之为病,其症皆属五脏,其源皆为肝火”。因肝开窍于目,足厥阴肝经连目系,所以五脏中以肝和目的关系最为密切,《审视瑶函》载:“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从肝胆发源,内有脉道通窍,上通于目为光明”。目之所视,依赖于肝的疏泄及肝血的濡养,如果肝的疏泄功能异常,会导致肝气郁滞,气有余便是火,肝火上炎,则目赤肿痛,肝受血才能视,如果眼睛失去肝血濡养,则出现视物模糊不清等。《本草经疏》载:黄药根“入少阴、足厥阴经”“解少阴之热,相火自不妄动而喉痹瘳矣”,可见,黄药子用于治疗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相关眼病可作为引经之药。
2.2 重在走肝络,清肝泻火止痛燕教授认为,甲状腺疾病多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重定严氏济生方·瘿瘤论治》载:“夫瘿瘤者,多由喜怒不节,忧思过度,而成斯疾也。大抵人之气血,循环一身,常欲无滞留之患,调摄失宜,气凝血滞,为瘿为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瘿瘤证论》谓:“此乃因喜怒忧思有所郁而成也。”[7]情志过极又归因于肝,肝失畅达,则气机郁滞,气郁化火,上扰咽喉、肝目,导致甲状腺部位肿胀疼痛及目赤涩痛,且发病之初,多以实证为主,实证又以气郁痰阻、肝火旺盛多见[8]。燕教授认为,黄药子苦、寒,入肝经,“解毒凉血最验”,具有清肝泻火止痛的作用,临床治疗甲状腺疾病凡属肝经郁热,致咽喉肿痛及目赤肿痛,则需泻肝火止痛,常选黄药子,可与龙胆草、黄芩等配伍,自拟泻火平突散[9](方由龙胆草、黄芩、黄药子、青黛、夏枯草、栀子、牡丹皮、白蒺藜、青葙子、赤芍、菊花等组成)。实验证明,泻火平突散可明显抑制γ-干扰素刺激后球后成纤维细胞ICAM-1、HLA-DR、CD40的表达,从而阻断甲状腺相关眼病免疫信号传递,进而抑制T细胞活化、细胞因子的产生,最终减轻眼眶局部的免疫反应[10]。
2.3 重在走肝络,化痰散结消瘿人体气血津液的运行均离不开肝的疏泄功能,肝的疏泄功能异常,导致气机郁滞,气为血之帅,气郁导致血瘀,气血郁滞阻碍津液正常运行;肝郁导致脾虚,脾虚运化水湿及水谷功能异常,聚湿生痰,两者均可导致痰瘀互结,结于颈前,乃成瘿瘤。《丹溪心法》云:“痰挟瘀血,遂成窼囊。”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瘿瘤论》提出,瘿病的主要病理是气、痰、瘀壅结而成,“夫人生瘿瘤之症,非阴阳正气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11]《绍兴本草》载:“黄药子治瘰疬及瘿气”。燕教授认为,在甲状腺疾病病机演变中,血停气滞,因实致瘀,需施以化痰散结消瘿之法,常选黄药子,并配伍赤芍、三棱、莪术等活血化瘀药及浙贝母、穿山甲、鳖甲等软坚散结药,自拟活血平突散[12](方由赤芍、泽兰、三棱、莪术、黄药子、生牡蛎、浙贝母、穿山甲、鳖甲、玄参、山慈菇、泽泻等组成)。实验研究表明,活血平突散能够通过抑制RFs增殖和HA、Ⅰ型胶原、Ⅲ型胶原的异常合成,逆转MMPs/TIMPs失衡,抑制CD40、CD50、HLA-DR的高表达来起到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的作用[13]。
2.4 重在走肝络,利水通络消肿《诸病源候论·瘿候》曰:“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长期情志不舒,肝失条达致气机郁滞,气不布津,易凝聚成痰,痰气胶结颈下成瘿。肝旺侮土,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气失于散津,致津停液聚,痰气津液阻碍血液正常运行而成瘀,痰气瘀搏结项下成瘤,如《仁斋直指方论》言:“气血凝滞,结为瘿瘤”[14]。痰瘀相互化生,正如唐容川《血证论》所载:“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陈如泉教授认为,甲状腺疾病相关性水肿往往兼有瘀血征象,若只利水而不化瘀,实非其治,及时运用活血利水法,不仅有利于消除水肿,还能断其源,以防积重难返[15]。黄药子可以利小便,通经络,正如《唐本草》言:“黄药子主十二水满急痛,利膀胱、大小肠,”《滇南本草》云:“利小便,走经络”。燕教授在甲状腺相关疾病出现水湿停驻的辨证治疗中,尤其重视利水通络,同时不忘疏肝、平肝,常选用柴胡疏肝散合二陈汤[8]及活血类药,方中常佐黄药子以达通络祛瘀,利水消肿之功效,又能作为引经药,引其他药物直达病所,使邪无藏所。
3 黄药子的用法用量
自宋代《开宝本草》始载以来,黄药子临床多以块茎入药。古人对黄药子用量早有注释,如《本草经疏》记:“药子之类,少服,止可外敷”。《扁鹊心书》也有黄药子散治缠喉风、颐颌肿及胸膈有痰的记载,“汤水不下者:黄药子一两,为细末。每服一钱,白汤下,吐出顽痰。”《圣惠方》所载:黄药子治热病、毒气攻咽喉肿痛:“黄药子一两,地龙一两(微炙),马牙消半两,上方捣细罗为散,以蜜水调下一钱。”《中药学》教材规定黄药子的用量为5~15 g,但黄药子有小毒,长期服用对肝脏会产生损害,需慎用,《中医内科学》教材建议,黄药子的一般剂量不宜超过10 g[16]。因其有毒,长期服用会对肝、肾功能造成损害,燕教授指出,中药复方通过合理的配伍可以达到减毒增效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芩和黄柏对黄药子的配伍减毒机制可能涉及提高肝GSH抗氧化水平,抑制肝脂质过氧化损伤[17]。有研究表明,当归用量为黄药子2倍时可显著降低黄药子主要成分黄独乙素和儿茶素的质量分数,可能会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18]。华碧春等[19]研究发现,黄药子、甘草12配伍可通过抑制CYP1A2的mRAN表达,对黄药子致肝损伤有保护作用,因此,燕教授临床应用黄药子,常配伍黄芩、黄柏、当归、甘草等,因其药性偏苦寒,攻散之性较强,易耗正气,故临床用药时间不宜过长。另外,燕教授应用黄药子治疗甲状腺疾病时,常内服联合外敷,以提高治疗效果,正如《理瀹骈文》所言:“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