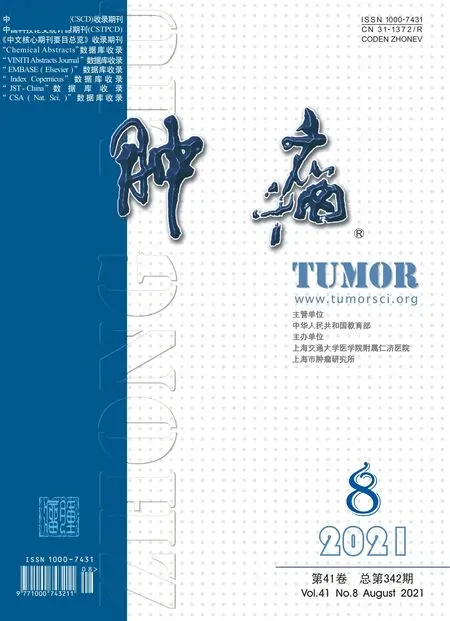多不饱和脂肪酸与肝癌发生和发展关系的研究进展
计晓薇 ,项永兵
脂肪酸是指具有长烃链的羧酸,其生物反应性取决于碳链的长度及双键的数量和位置。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PUFA)是指具有≥2个双键且碳链长度为18~22个碳原子的直链脂肪酸。PUFA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也是参与细胞膜磷脂构成和细胞内代谢调控的重要结构性脂肪酸。根据碳链羧基端起最后一个双键相对于分子末端甲基碳的位置,PUFA可以分为n-3、n-6、n-7和n-9 PUFA,其中n-3和n-6 PUFA相关的研究最多。
n-3 PUFA是人体必需脂肪酸,也是细胞膜磷脂的主要成分,其第1个不饱和键位于碳链甲基端第3个与第4个碳原子之间。n-3 PUFA主要来源于深海鱼类,包括α-亚麻酸(α-linolenic acid,ALA)、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1]。ALA是EPA和DHA的前体物质,可在去饱和酶和延长酶作用下转换成EPA,进而延伸为二十二碳五烯酸(docosapentaenoic acid,DPA),最后在去饱和延长酶的作用下转化为DHA[1-2]。ALA在体内无法合成,而EPA和DHA转化率又极低,因此均无法满足人体的需要,必须从食物中摄取n-3 PUFA。
n-6 PUFA主要包括亚油酸(linoleic acid,LA)、γ-亚 麻 酸(gamma-linolenic acid,GLA)和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其第1个不饱和键位于碳链甲基端第6个与第7个碳原子之间,主要包括亚油酸(linoleic acid,LA)、GLA和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人体无法合成LA,必须从食物中摄取。LA是GLA和AA的前体物质,LA在去饱和酶的作用下生成GLA,然后通过延长酶的延伸作用将GLA转化为二高GLA(dihomo-GLA,DGLA),最后通过延伸和去饱和作用循环生成AA[3]。
PUFA在人体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n-3 PUFA主要发挥抗炎作用,避免炎性反应的过度激活,抑制肿瘤形成;而n-6 PUFA主要发挥促炎作用,可激活免疫系统,促进炎症发展[4]。因此,有研究提出多摄入n-3 PUFA以及少摄入n-6 PUFA对健康有益[5]。本文对PUFA与肝癌发生和发展关系的营养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及其机制以及PUFA的治疗作用等进行文献综述,探讨PUFA与肝癌发生和发展的关系。
1 PUFA与肝癌发生和发展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1.1 营养流行病学研究:膳食PUFA与肝癌发生的关系
1.1.1 膳食PUFA与肝癌发生的关系
膳食脂肪酸与肝癌发生和发展的关系正日益受到重视。2018年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发布的《食物、营养、身体活动与癌症预防》第3版专家报告指出,低脂饮食与肝癌关系证据的等级有限,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6]。
一项来自意大利的病例对照研究提示,膳食PUFA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发生呈负相关[比值比(odds ratio,OR):0.60;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40~0.88],其中LA的OR为0.58(95%CI:0.30~0.86),亚麻酸的OR为0.75(95%CI:0.52~1.09)[7]。相较于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队列研究的证据等级较高,但目前有关PUFA与HCC发生风险的队列研究的证据并不多,结果也并不一致。2015年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and Nutrition,EPIC)发现,PUFA与HCC发生风险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其最高四分位数vs最低四分位数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0.86(95%CI:0.55~1.35),趋势检验P=0.349[8]。一项来自新加坡的队列研究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未发现n-3 PUFA与HCC发生风险之间存在关联,其最高四分位数vs最低四分位数的HR为0.99(95%CI:0.70~1.39),趋势检验P=0.80;但发现n-6 PUFA可能与HCC发生风险呈正相关,其最高四分位数vs最低四分位数的HR为1.49(95%CI:1.08~2.07),趋势检验P=0.02[9]。然而,美国护士健康研究与卫生人员随访研究(Nurses Health Study &Health Professionals Follow-Up Study,NHS-HPFS)的结果显示,n-3 PUFA和n-6 PUFA均与HCC发生风险呈负相关,HR(95%CI)分别为0.63(0.41~0.96)和0.54(0.34~0.86),趋势检验P分别为0.14和0.02[10]。
1.1.2 不同食物来源的PUFA与肝癌发生风险的关系
鱼类中富含EPA、DPA和DHA等n-3 PUFA。一项日本的队列研究结果提示,尚不能确定鱼类来源的n-3 PUFA能否增加HCC的发生风险,其最高四分位数vs最低四分位数的HR(95%CI)为0.51(0.20~1.32),而ALA、EPA、DPA和DHA的HR(95%CI)分别为0.70(0.29~1.71)、0.62(0.28~1.39)、0.80(0.34~1.85)和0.63(0.27~1.49);但在丙型肝炎病毒阳性人群中,EPA和DHA与HCC的发生风险呈负相关,其最高四分位数vs最低四分位数的HR(95%CI)分别为0.33(0.12~0.92)和0.30(0.10~0.88),对应的趋势检验P分别为0.03和0.02[11]。除鱼类以外,肉类也是PUFA的重要来源之一。FREEDMAN等[12]利用NIH-AARP队列数据分析了红肉和白肉来源的PUFA与HCC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其最高四分位数vs最低四分位数的HR(95%CI)均为1.06(0.74~1.51),趋势检验P值分别为0.63和0.62,提示无显著性关联。此外,一项荟萃分析的结果显示,n-3 PUFA与HCC发生风险降低有关,其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为0.49(95%CI:0.19~0.79),而ALA与HCC发生风险之间无显著相关性[RR:0.70(95%CI:0.30~1.10)][13]。
上述研究提示,膳食PUFA与肝癌发生风险的关系在不同研究人群中的结果并不一致,推测其可能的原因包括:(1)不同种类的PUFA(如n-3 PUFA和n-6 PUFA)与肝癌发生风险关系的结果不一致;(2)不同食物来源[包括鱼类、肉类(红肉或白肉)和全食物来源]的PUFA与肝癌发生风险关系的结果不一致;(3)存在人群异质性,如美国的人群研究发现PUFA可能降低肝癌的发生风险,而新加坡和日本的队列研究却未显示存在此种关联。基于以上,可以推测种族和饮食习惯差异均可能影响PUFA与肝癌发生风险的关系。
1.2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血液中的PUFA与肝癌发生和发展的关系
早发现和早治疗对于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极为重要,因此发现肝癌的早期生物学标志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血液中特定脂肪酸能否作为肝癌的预测指标及早期指标的研究较少,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检测了HCC患者血循环中的脂肪酸水平。一项研究发现,HCC患者血浆异油酸(n-7)和芥酸(n-9)水平升高,而十七酸和LA水平降低;鉴于该研究样本量较少,仅纳入15例HCC患者和15例肝硬化患者,因此尚需对初步结果在大样本中进行验证[14]。PATTERSON等[15]采用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发现与肝硬化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相比,HCC患者血浆二十四烷酸和神经酸水平下降。另有研究指出,与健康对照者和肝硬化患者相比,HCC患者血清AA水平较高[16]。韩国的一项肿瘤预防前瞻性队列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该研究纳入75例HCC患者和134例健康对照者,结果显示HCC患者血清AA水平高于健康对照者,提示血清AA水平可以作为HCC的生物学标志物[17]。然而,也有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HCC患者血清AA、肌酸和神经酸等多种脂肪酸的水平均较低[18]。另有研究探讨了HCC、肝硬化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与健康对照者血浆游离脂肪酸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与健康对照者相比,HCC患者血浆游离脂肪酸(包括C16:1、C16:0、C18:2、C18:1、C18:0、C20:5、C20:4、C20:2、C22:6和C22:5)水平均显著升高,但与肝硬化患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此外,LIU等[20]采用核磁共振联合液相色谱质谱方法,对HCC患者、肝硬化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血清进行代谢谱分析,结果发现肝癌引发的代谢变化表现为酮体合成、柠檬酸循环、磷脂代谢、鞘脂代谢、脂肪酸氧化、氨基酸分解代谢和胆汁酸代谢的紊乱;与肝硬化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相比,HCC患者血清LA、异丁酸和反式LA的代谢水平较高,酮体中β-羟丁酸水平也随着糖代谢的变化而升高。在欧洲EPIC队列中,采用核磁方法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结果发现脂肪酸氧化等代谢变化与HCC发生风险显著相关[21]。另外也有研究指出,PUFA(包括EPA、DHA和亚麻酸)水平的降低是肝癌早期复发的特异性代谢特征[22]。
上述部分研究采用代谢组学(包括脂质组学)方法对HCC患者、慢性肝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进行游离脂肪酸检测,寻找可能作为潜在的生物学标志物的差异性脂肪酸。然而,有研究指出,膳食类型及状态能够影响HCC患者的血脂肪酸代谢水平[23],如果在研究时未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则会降低相关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此外,样本量过小可能是该类型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局限。
2 PUFA与肝癌发生和发展关系的机制
2.1 n-3 PUFA
目前的研究证据显示,n-3 PUFA可能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并且诱导肝癌细胞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涉及多个方面。首先,n-3 PUFA能够影响细胞膜的构成。研究发现,以鱼油为基础的脂肪乳可以降低小鼠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这可能与n-3 PUFA改变前列腺素的表达以及细胞膜磷脂的构成有关[24]。其次,n-3 PUFA诱导肿瘤细胞凋亡。n-3 PUFA可以抑制多种恶性肿瘤细胞的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并降低其侵袭能力。一项探讨EPA在肝癌中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EPA可能通过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Ca2+-JNK线粒体途径诱导HepG2细胞凋亡,抑制HepG2细胞增殖,但对正常肝细胞LO2的活性无显著影响[25]。第三,n-3 PUFA通过环氧合酶2途径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LIM等[26]发现,DHA和EPA对3种人肝癌细胞株(Hep3B、Huh7和HepG2细胞)的增殖均有抑制作用,其中DHA的抑制作用最强,究其原因可能是DHA和EPA可以同时抑制肝癌细胞中环氧合酶2的表达以及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激活。第四,n-3 PUFA能够调节肿瘤细胞脂质过氧化。体外实验发现,n-3 PUFA可以增强肿瘤细胞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导致过氧化产物积聚,从而产生细胞毒作用。
脂质过氧化产物的主要作用是抑制DNA合成、细胞分裂和肿瘤生长[27]。LEE等[27]研究证实,将DHA加入HepG2细胞培养基后,发现细胞内氧自由基含量增加,同时细胞存活率下降,说明DHA可以增加细胞脂质过氧化产物,促进其细胞毒作用。在结直肠癌中,也发现n-3 PUFA能够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调节miR-126对DNA甲基化的调控作用,并以细胞类型特异性方式降低结直肠癌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水平,其中以DHA的作用最为显著,提示n-3 PUFA可以作为抗血管生成剂,在结直肠癌治疗中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28]。然而,肝癌中n-3 PUFA是否也发挥类似作用,尚需进行验证。
2.2 n-6 PUFA
有研究认为,n-6 PUFA具有促炎作用,其机制可能是n-6 PUFA代谢可以促进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和类花生酸类化合物的产生,导致肝脏库普弗细胞生成白细胞介素以及激活核因子κB,进而加重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29]。类花生酸类化合物是AA以及所有源于该物质的化合物的总称,其中前列腺素和白三烯是AA的重要衍生物,是重要的免疫炎症因子,具有促炎作用[30]。
目前,对于n-6 PUFA与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癌关系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研究的肝脏疾病是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NAFLD是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伤肝脏因素以外,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以及脂质代谢紊乱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包括单纯肝脂肪变性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NASH是脂肪变性进展至肝硬化或肝癌过程中的重要中间步骤,也是NAFLD的阶段性病变[31]。研究发现,除传统的致病因素以外,NAFLD可以增加肝硬化和肝癌等终末期肝病的发病风险,逐渐成为终末期肝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32]。
有研究对NASH患者肝脏中的n-6 PUFA水平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健康对照者和NASH患者肝脏中的LA和ALA水平相似,而NASH患者肝脏中的AA水平降低[33]。作为促炎因子的前体物质,一般认为AA水平升高可能与炎症加重有关;但是在NASH患者中观察到肝脏中AA水平下降,可能与长期炎症导致AA耗竭有关,但这一观点尚未得到证实。从理论上而言,LA在体内转化为AA,可导致促炎因子(包括前列腺素E2和血栓素)增加。然而,有研究发现富含LA的膳食不会显著改变血浆AA水平,而补充LA却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慢性炎症的发生风险[34]。此外有研究指出,健康人群摄入大量LA或AA不影响体内炎症细胞的数量或炎症反应[35-36]。因此,目前LA和AA对肝脏有慢性炎症作用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GLA是n-6 PUFA的一种,用GLA处理肝癌细胞系后,可降低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37]。也有研究指出,GLA对二乙基亚硝胺(diethylnitrosamine,DEN)诱导的HCC具有化学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DEN诱导缺氧微环境改变、线粒体凋亡和抗炎通路有关[38]。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目前尚未完全阐明n-6 PUFA的促炎作用及其机制,n-6 PUFA促进炎症发生和发展的证据不足。在研究n-6 PUFA与疾病的关联时,应考虑单一类型n-6 PUFA的影响[39]。
3 PUFA作为肝癌的辅助治疗手段
近年来,已发表多项旨在确定补充PUFA是否可改善疾病预后的研究。研究发现,n-3 PUFA可以调节血浆血脂,可能对NAFLD具有治疗作用[40]。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补充n-3 PUFA可能会降低肝脏中脂质的含量[41]。一项纳入PUFA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显示,补充PUFA可能降低NAFLD患者血清ALT、AST和脂质水平,改善肝功能[42]。NASH是NAFLD重要的病变阶段,其特点是肝脏出现脂肪变性、炎症、氧化应激和纤维化,是肝硬化和HCC的危险因素。有研究采用LDLR基因敲除小鼠,建立西方膳食模式诱导NASH临床前模型,证实在膳食中添加DHA可以阻断西方膳食模式诱导的NASH进展,但是DHA不能促进NASH完全缓解[43]。另有研究发现,在膳食中添加DHA或单独添加EPA均可有效降低NASH患者肝脏中的脂肪含量[44]。
超重和肥胖与肝癌的发生和发展有关,而慢性炎症则在肥胖与HCC的关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白细胞介素6可以促进肥胖相关HCC的发展[45]。喂饲添加EPA的高脂饲料的小鼠的肝癌发生率低于仅喂饲高脂饲料和致癌物的小鼠,提示EPA可以延缓肥胖相关肝癌的发生和发展,对于治疗肥胖相关HCC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46]。n-3 PUFA还可以改善终末期肝病或HCC患者接受肝移植的预后。有研究对66例接受原位肝移植的终末期肝病或HCC患者进行术后免疫营养治疗,结果显示肠外营养支持联合补充n-3 PUFA可以明显减轻肝损伤、降低感染发生率以及缩短肝移植后的住院时间[47]。另有研究对98例接受原位肝移植的终末期肝病或HCC患者进行术后免疫营养治疗的疗效评估,结果发现肝移植后给予肠外营养支持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蛋白质代谢和营养状态,补充n-3 PUFA可以显著缓解肝移植引发的肝损伤、降低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以及缩短肝移植后的住院时间[48]。
4 结语
综上所述,PUFA作为重要的营养成分,参与体内代谢的重要过程,其与肝癌的发生和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流行病学研究提示,不同种类的PUFA与肝癌发生和发展的关系不同。对肝癌患者血液进行游离脂肪酸检测时,也发现HCC患者血液中的脂肪酸代谢紊乱。PUFA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或调节体内代谢,其对HCC发生发展的相关作用机制及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n-3 PUFA对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在评估n-6 PUFA的作用时,应进一步确认其对健康有益或有害的具体种类。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n-3 PUFA对包括肝癌在内的多种疾病均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提示未来应进一步探索PUFA对肝癌的具体治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