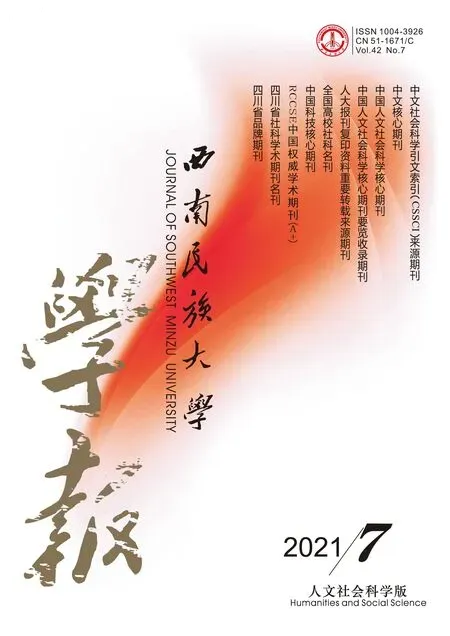“褐色语法”与生态语言——梭罗自然写作探讨
李 莉 曾繁仁
[提要]“褐色语法”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梭罗在其作品《漫步》中所提到的重要的语言观,但并未得到研究者们的持续关注。本文试图从“褐色语法”这一概念的解读出发,并运用生态话语批评来对梭罗自然写作中的自然有声、有机语言以及野性语言来进行探讨。“褐色语法”并非是一套真正的语法系统,而是一种生态的语言观。这不仅为我们理解梭罗自然写作中的生态语言与生态意识拓展新的途径,而且也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浪漫主义作家梭罗是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他独特的语言创作风格影响了后来诸多自然文学作家。其中,“褐色语法”(tawny grammar)是他在《漫步》中提及并写道:“西班牙人有一个好的术语来表达这野性且模糊的知识——褐色语法,一种天生的自然智慧,源于我之前提起那同一只美洲豹。”[1](P.239)在这之前,他曾写道:“我们这位巨大、狂野、咆哮的母亲——自然如此美丽,如此喜爱她的孩子们,犹如美洲豹一般。”[1](P.238)梭罗将美洲豹比作自然母亲,并认为“褐色语法”是一种来源于自然的智慧,是一种自然的语言。它不仅与美洲豹那般拥有自然的颜色,而且也与其一样具有自然的野性与生命力。本文将通过解读梭罗的“褐色语法”来探讨他的自然写作及其所蕴含的生态语言①——自然有声、有机语言以及野性语言。
一、自然有声
在“褐色语法”中,梭罗表达了自然有声的立场,他认为自然与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声音。这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语言观一致。热爱自然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他们相信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这一亲近感可以通过语言的交流来维系。因此,浪漫主义者在创作中将自然作为书面语言的一手材料的同时,也承认自然本身拥有自己的语言。梭罗则在褐色语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然语言的概念,提倡将“褐色语法”运用在自然写作中,以第一手资料为创作源泉,运用这样一种更贴近自然的语言,即用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自然。这样能够使得读者在阅读中更容易融入作者的写作情境,置身于自然体验中以听见真正的自然之声。在梭罗看来,自然本身拥有自己的语言,如在《瓦尔登湖》中聆听森林中生灵的“声音”,在《缅因森林》中感受“嚎叫的荒野”。作为浪漫主义作家,梭罗认为“自然是有人性的”[1](P.242),始终将自然看作是可以互相平等交流的对象,是可以和谐相处的邻居、朋友与伴侣,是与他共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正如在《野苹果》中,梭罗将牛与野苹果树视作能够言说且具有意识的主体,描绘了二者的“主体间性关系”[2](P.131)。在梭罗看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灵之间能够实现双向交流、互动的前提是双方均需具有语言言说的能力。
在梭罗的自然世界中充满着各种声音,他的文学文本中随处流动着生态的语言。梭罗在《日记》中写道:“自然总是能发出某种声音。”[1](P.239)这些声音包含了自然的声音,代表了自然的语言。如果自然没有语言,那么《瓦尔登湖》中的“声音”一章又从何而来?如果自然没有语言,梭罗又如何与自然万物结交朋友、与它们为邻?梭罗认为,作为所有生命个体之间交流的载体,语言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如各种声音、符号以及景观等等。正因为与自然在语言上得以交流,梭罗才能够对自然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并将其与自然相融的审美体验以自然书写的形式呈现。承认自然有声是梭罗与其和谐相处的前提,这与自然无声的观点相对。一般而言,在西方文化中,只有人类才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主体,而自然却是无声的他者,并不具有语言言说能力。一直以来,在与自然零交流的情况下,我们人类常以统治者的姿态来控制与征服自然。显然,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独白语言观”[3]。
此外,梭罗认为自然有声的这一立场也受到了万物有灵论的影响。在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看来,十九世纪以来,正是因为工业文明的无孔不入致使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愈发疏离,这成为越来越多的浪漫主义者们纷纷重新支持万物有灵论的原因。②梭罗便是这些支持者中的一员。在十七世纪的万物有灵论的文化中,“不仅人类而且动物、植物甚至是‘不活泼的’实体,如石头与河流都被认为是可以言说并且有时可以被理解的主体,能够与人类沟通交流。”[4](P.15)万物有灵论者们相信语言包含了人类语言在内的所有自然万物的语言,如飞禽走兽、山川河流以及树木花草等等的语言,人与自然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在梭罗的作品中,树木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意象,也“是他生命的象征”[5](P.4)。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D.Richardson)在为《梭罗与树的语言》作序时写道:“树木对梭罗言说,并且梭罗了解它们的语言。”[5](P.X)正因为语言的存在使得他能够与树交流,并将树木看作他的朋友,甚至是“远房亲戚”。梭罗不仅能听懂包括树木在内的自然生灵的语言,而且也在交流中向它们谈及自身的同时也在“言说着它们的语言”[5](P.1),在作品文本中为它们代言。由此而看,梭罗所持有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观,将自然放在平等位置进行对话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除了对“万物有灵论”的推崇之外,梭罗还始终对自然抱有虔诚的信仰以及浓烈的生态情怀,并对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严肃思考。自然的声音与人为的声音在梭罗的笔下正是自然与工业文明之间的鲜明对比。如在《瓦尔登湖》“声音”一章中,梭罗就描绘了这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火车头的汽笛声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之声;另一种是以旋律优雅的牛叫声为代表的自然之声。两者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梭罗对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自然万物的关注。在一个恬静的夏日午后,梭罗坐在窗口,正惬意地欣赏“邻居”们的日常活动,如鹰盘旋于林中空地,疾飞的野鸽呼声于长空等等,突然一声火车的汽笛声闯入这个安静的田园世界,惊扰了鹧鸪扑翅,打断了他的沉思。原本悠闲的下午被忽近忽远的火车轧轧之声打扰。人们好像在用刺耳的汽笛声强势闯入自然静谧的花园,并以这种方式来疏离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伴随这种声音,梭罗为我们讲述了他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已经完全开始,机械化愈发地控制了人们基本的生活模式。他写道:“‘火车式’作风,现在成为流行的口头禅。”[6](P.132)虽然火车的到来拉动了城市与乡下的商业经济,但梭罗也并不愿意让自己的“眼睛鼻子给它的烟和水汽和咝咝声污染了”[6](P.137)。虽然梭罗并不反对科技的发展,但相比工业文明笼罩下的人为的声音,他更喜欢自然万物的声音,因为它们是他内在脉搏的悸动,能够使他沉醉于美好的健康与兴奋中,如牛叫的天籁之声、猫头鹰的小夜曲以及潜水鸟的哗笑等等。
此外,“声音”一词在这里亦有一语双关之意。英文单词“sound”除了有名词“声音”之外,还有形容词“健康的”的意思。梭罗认为自己感官存在的健康与自然声音的健康息息相关,这是人类对自然万物言说的最好回应。只有这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是和谐、健康的。正如沃斯特所说:“梭罗……认为一种新生的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是治疗那种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志的精神和肉体弊病的唯一药方。”[7](P.110-111)同时,“动物的声音也代表了自然的健康与美好”[1](P.246)。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旅行一周后,梭罗写道:“凡此种种声音,鸡啼、狗吠以及正午的虫鸣,都是大自然健康或健全状态的佐证。这就是语言永不消逝的美丽与精确,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8](P.38)。因此,梭罗渴望通过声音与自然进行交流以建立这种和谐、健康的关系。此外,梭罗在“声音一词中懂得了美与全部的意义”[9](P.226-227),这一切的发现有赖于他对听觉在自然审美体验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视。通过听觉,他倾听自然万物的声音,使他发现了一个新奇的自然世界,并通过语言使其以文本的形式得以表达。语言作为人与自然言说的共同载体,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密相连。作为人类,梭罗不但认同非人类声音的存在,而且还将其纳入语言之列,而不是把它们归入不能言说的“他者”一列。在梭罗看来,非人类声音的存在代表了自然的健康。因此,语言与自然的关系唇齿相依,不再是割裂的关系。正是对于人与自然交流表达的共同载体——语言的认可,梭罗才能运用文本更进一步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二、有机的语言
梭罗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机的”[10](P.340),语言也不例外。他在《日记》中写道:“[语法的]第一要求与规则是语言表达应该是有生命力且自然的。”[11](P.386)同时,20世纪兴起的生态语言学中也认为语言是一种有生命的生物种,[12](P.177)这是以豪根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对语言进行的一种生态隐喻。回到梭罗的文本中,他的具有生命的“褐色语法”与有机的语言观也密切相关。从文学背景来看,梭罗有机语言观的形成与他浪漫主义者的身份分不开。“浪漫主义……作为文学运动,有机整体的自然规则是它最鲜明的特征。”[13](P.5)这时期大多数的浪漫主义者们都赞同充满生命力的有机的语言观。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梭罗也不例外,他的语言观同样具有有机整体的特点。在梭罗看来,用以表现各种生命存在的语言如同人与自然一般也是有机的,如植物的生长的过程一般具有整体性。浪漫主义有机整体的语言观是对十八世纪机械论语言观的突破,反对工业文明割裂下的主客二元论。从文学方面来看,浪漫主义者们渴望将自然中有机的生命力植入到文本创作中,而非延续机械的、固定的、毫无生机的语言创作模式。从物质世界来看,浪漫主义者们则希望重新调整日益分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希望建立一种和谐统一的相处模式,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传达这一理念。梭罗的“褐色语法”兼具这两方面的革新,通过自然体验中的第一手资料将语言、人、自然三者相融相生于有机整体的体系之中。
美国学者弗莱德·洛克(Fred W.Lorch)对梭罗诗歌中的有机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梭罗的有机观主要受到了柯勒律治与爱默生的有机语言观的影响,而非直接受到德国的有机理论家们的影响,如歌德、谢林等。与机械论的语言观相反,柯勒律治认为文学艺术并不存在固定的机械形式,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有机形式,如植物般呈现生命生长的态势,强调了文本的有机整体性。爱默生同样也受到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国浪漫派的有机观的影响。在爱默生看来,包括文本在内的所有艺术都应当是有机的。他认为,文本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关系,即文本对自然进行有机的表达。这样的文本才能称其为一本真正的书。③作为爱默生的朋友,梭罗所提倡的“褐色语法”便是对人与自然之间有机整体性关系的表达,认为文学与艺术如“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一样发展”[14](P.287),富于生命力。如洛克所言:“梭罗相信所有真正的诗歌一定具有生命力,并且在诗人与他的表达之间存在一种亲密的有机的关系。”[14](P.287)在他的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与人以及自然之间形成了有机整体的关系。
在梭罗的有机语言观中,他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描述成一个“活的地球”[10](P.341)。他认为这个“活的地球”是一个有机的身体,这有机的身体包含了人类所有的生命,与梭罗万事万物的有机观一致。与机械论语言观不同的是,梭罗的有机语言观认为自然不是毫无生命力的机器,而像一个活的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地球不是化石,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球。”“大地……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球;和它比较,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不过寄生在这个伟大的中心生命上。”[6](P.339)此外,“叶”是梭罗作品中重要的意象,是整个活的地球的象征。《瓦尔登湖》中有一段著名的有关叶形沙子的描述。当梭罗看到细沙裂成叶子的形状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是站在了大艺术家的画室,感到自己“仿佛和这地球的内脏更加接近起来,因为流沙呈叶形体,像动物的心肺一样。……难怪大地表现在外面的形式是叶形了,因为在它内部,它也在这个意念之下劳动着”[6](P.336)。在这叶形中,梭罗看到了自然万物存在与发展的原则。之后,梭罗将人类语言与这叶形体的“叶”字进行对比研究,并认为“无论在地球或动物的圣体的内部,都有湿润的,厚厚的叶”[6](P.336)。他将这“叶”与“肝、肺和脂肪叶”相联系,通过追溯词源,梭罗将“叶”一词逐步衍生出“地球”一词。此刻,语言与自然万物一样如同这“叶”一般,回归地球。在这里,“叶”这一意象将语言与地球紧密相连。
此外,万事万物的“生命力”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浪漫主义作家——梭罗的有机语言观中,他相信这个“活的地球”上的所有事物犹如有机体一样自内而外滋生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且循环不断。梭罗的这一观点不仅受到上述柯勒律治与爱默生等人的有机语言观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生机论”的影响。“生机论”又被称为“生命力论”或“活力论”,认为“生命具有一种自我的力量或是称为生命力......这种力量是非物质的,因此生命无法完全以物理或化学方式来解释它。”④梭罗相信这样一种无法解释的特殊生命活力存在于自然之中,他认为“大自然并不存在衰退的迹象,存在的只是普遍的不间断的生命力。”[15](P.73)在他看来,万物寄居之地是一个生命源源不竭的地球,他能够感受到其很强的繁殖力。同样,对于人类的生命,梭罗则认为它的“消亡只是大自然的表面现象,它的绿叶却伸向了永生。”[15](P.73)面对自然中强大的生命力,梭罗相信他的超验主义信仰能够为其作出解释。然而,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对“生机论”的冲击与突破,在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梭罗对“生机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转而投向达尔文进化论,这也促使他对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并写道:“发展理论暗示了在大自然中有一种更伟大的生命力,它是更灵活的、更包容的,等同于一种持续的新的创造”[16](P.103)。此时,梭罗有机语言观下的自然中的生命力不再是神秘的超验力量的创造,而是一种科学能够解释的不断发展更新的生命力。因此,梭罗的有机语言观至始至终都坚信人与自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并将其体现于文本的表达中。
梭罗的有机语言观相信自然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是有机的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同时,人类在自然这个有机的生命存在中与其他生命相互联系,如他通过文本有关叶形的表达为我们所呈现的大自然这个整体与其包含的植物、动物、非生物以及人等个体之间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呈现的关系,并能够进行交流。在这个“活的地球”上,语言使我们与自然万物之间能够得以交流,文本再现了作者自然体验中语言、人与自然三者的有机关系,如植物的生长过程一般具有整体性。自我与世界始终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供给的有机的关系。然而,人类却逐渐在挣脱与自然万物的这种联系。梭罗认为人类有必要重新建立这份联系。
三、野性的语言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6](P.234)这体现着生态语言学批评中多样性的生态特点。在他的自然文本语言中,我们既能看到自然的静谧之美,也能够看到其狂野的壮美。梭罗认为,壮美的荒野之地能够让他更接近善良,并希望“为自然代言、绝对的自由与荒野代言”[1](P.205)。在梭罗所认为的“更高的规律”[6](P.234)中,向往充满野性的自然与探索内心善良的精神生活同样重要,这两者他都很尊重。基于对野性的热爱,他的语言观也始终坚持着对野性语言的呼唤与运用,体现在他的“褐色语法”中。他认为人类的语言犹如“自由、野性的美洲豹一样”[17](P.157)。在斯奈德看来,这种野性的语言观“不仅仅是关于语言,而且也与文化与文明本身有关”。它根植于自然之中,“与布满苔藓的林中小溪以及荒漠中的砾石一样遵循相同的秩序”,无法被任何其他的文化所取代。[18](P.76)
首先,野性的语言观作为“褐色语法”的一部分,它的形成不能说与梭罗的荒野情结无关。在美国的历史文化中,美国人的荒野情结最早可追溯于清教徒移民时期。作为新大陆的第一批移民,清教徒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早期美国人荒野情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荒野是全部自然的地理代名词,而在心理上,自然则永远是令人生畏的“嚎叫的荒野”,充满了凄凉,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困苦乃至生命的威胁。因此,艰苦的自然环境成为清教徒们艰难开拓、创建家园的阻碍。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征服自然,自然成为他们不断与之斗争的对象,而非可以和谐相处的朋友。“嚎叫的荒野”成为美国人心目中自然的形象,并一度成为诸多作家文学创作的母题。这一观念持续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即以爱默生、梭罗等人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悄然兴起,一场被认为是挑战清教徒教义的宗教运动。一方面,不可否认,超验主义者们继承了他们祖先们在“咆哮的荒野”中自力更生的开拓精神,并鼓励美国民众依靠自我来实现个体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祖先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认知,在对自然中的荒野保持敬畏的同时不再将其看作被压制与征服的对象。自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不再只是充满凄苦与悲凉的意象,而是可以为人们带来心灵慰藉的精神源泉。除此之外,我们在梭罗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人类在包括荒野在内的自然中能够与其为邻、为友并和谐共居。
同时,在梭罗的“褐色语法”中,荒野是他语言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步》与《缅因森林》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对“嚎叫的荒野”的态度更多的是赞美与敬畏,通过“褐色语法”中野性的语言来表达着自然的这份魅力。梭罗不希望美国的文学创作像英国文学那样只充满了被驯化了的语言,缺乏了野性。在他看来,“华兹华斯的诗歌太温顺了。”[9](P.273)梭罗在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派文学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只是人类对自然温和、美好的一面给以单向的友好的热爱,却看不到完整的自然本身,呼吸不到自然中的狂野之风。梭罗希望运用一种野性的语言来“为自然代言、为绝对的自由与荒野代言”[1]((P.205),即具有梭罗特色的荒野文学。在这里,人类的语言就像未被驯服的荒野一样,没有任何的组织形式。这与超验主义所反对固定形式的创作理念一致,但这绝不意味着语言与自然没有任何联系,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任意且空洞的符号。这与西方近代语言观中的“词物对应论”相契合。不少浪漫主义作家也“坚持语词与事物、语言与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19](P.87)。同时,作为浪漫主义者,梭罗认为自然景观具有潜在的象征性并且语言能够表现自然事物的象征意义。他曾将自然中的星星与云朵来比喻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星星就是那铅印在天空的蓝色羊皮纸上的书面语言;而为我们视野忽略的变化无常的云朵……正是我们的日常谈话”[9](P.369)。梭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语言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深度关联的赞同。
其次,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梭罗野性的语言观不仅包含了对荒野的敬畏,而且还表达着“文明与野性并存”[20](P.477)的美好愿景。十八世纪晚期,“文明”作为一个与“野蛮”相对立的词汇出现。一直以来,人们都乐于将自己划进文明的、有教养的或是不野蛮的围墙之内,以将自身与围墙外的“他者”——“野蛮人”区分开。⑤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所谓“文明人”的白人抱着创业与冒险精神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大刀阔斧不断向世界证明他们是“文明”的同时,也将作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推向社会的边缘。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和他们居住的原始森林一样都是野蛮的、落后、未开化的。文明作为一个高级存在,站在野性的对面。因此,这种文明观也随之反映到文学世界里的语言中,文本语言表达中的“文明人”与“野蛮人”被自然地割裂开来。然而,在梭罗文学作品中野性的语言所表达的文明与野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文明与野性并存”的关系。正如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不能只有白人的诗歌,我们同样也需要印第安人的诗歌”[9](P.273)。梭罗认为褐色语言更多地存在于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是一种属于自然的语言,植根于自然的语言。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与现代城市社会里稳定且具有模式化的语言相对。他建议“诗人就应该走一走伐木人的路,追寻一下印第安人的足迹,到荒野中寻个僻静之所,在彼处畅饮凉爽的缪斯之泉,从中获取力量,也感受真美”[21](P.154)。在梭罗看来,文明与野性所代表的文化不分优劣而存在,而是共生于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之中。
面对文明,梭罗并不排斥它的存在,同时也承认文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6](P.234),但他又表示自己只不过是文明中匆匆的过客。在整个国家迅速文明化的过程中,他看到白人已经把生活在森林中的“野蛮人”连同猎物赶走,疯狂砍伐森林,“文明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土地永远清理了,开垦出开阔的土地,不但如此,森林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们驯化栽培的对象”,“取而代之的仅仅是在一美分的硬币上印上印第安人的头像”[21](P.144)。同时,梭罗认为通过文明人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对荒野的入侵,文明的国家正是依靠原始森林的原材料才得以维持。文明人离不开荒野的供给,充满野性的原始森林为文明人提供着赖以生存的资源。文明人在发展自己家园的同时,也应留住“野蛮人”——印第安人的家园。另一方面,梭罗提出要保护荒野,认为“这个世界保存于野性之中”,“在最蛮荒的自然界,那里不仅有最文明教化的生活素材,有一种对最终结果的期盼,而且早已有一种比人类曾达到的更高级的高雅。”[8](P.331)在他看来,我们文明人心中实际上都住着一位野蛮人,文明、野性与人类都深深地植根于自然之中。“我坐在荒野里,不远处是巍峨的青山,我的旁边是波光粼粼的河水,还有画眉鸟的歌声相伴,这应该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吧!”[21](P.272)从生态语言学批评来看,梭罗的野性的语言观表达了生态多样性中文明与野性缺一不可,在“文明与野性并存”中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承认自然有声,还是提倡有机整体的语言以及“文明与野性并存”的语言,梭罗的“褐色语法”实际上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褐色语法并非梭罗为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所制定的一套语法规则,而是一种生态的语言,是其始终坚持的语言观。“这种语法不但关乎语言,而且也关乎文化与文明本身,它与长满苔藓的森林小溪、荒漠卵石一样有着相同的自然法则。”[18](P.76)在梭罗看来,“语言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品。”[9](P.172)这种完美体现在梭罗对语言的运用上,并希望通过语言来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绿色的语言,梭罗的“褐色语法”始终根植于自然之中,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的生态语言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友好共存的生态文化。因此,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梭罗的“褐色语法”并运用生态话语批评来对梭罗的自然写作进行探讨,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梭罗自然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语言与生态意识。这对人类认识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构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关于生态语言的概念,参见赵奎英《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②沃斯特关于浪漫主义对万物有灵论呼吁的论述,参见Donald Worster.Nature’sEconomy:AHistoryofEcologicalIde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年,第83页。
③洛克关于爱默生对梭罗有机语言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论述,参见Fred W.Lorch.“Thoreau and the Organic Principle in Poetry”.PMLA,1938(1)。
④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B%E5%8A%9B%E8%AB%96.
⑤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论述,参见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刘文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