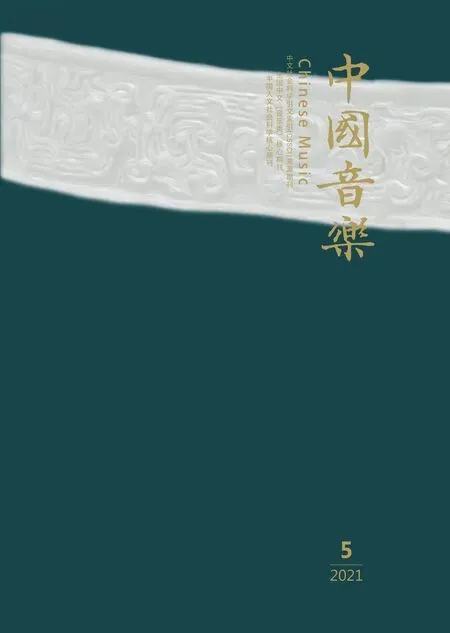音乐教育作为国家资产
——走向共同建构与协商的社群主义
○ 林小英
引言:从音乐活动到音乐教育的追问
把音乐教育与国家联系起来并不新鲜。新世纪以来,比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突然兴起了一股对“国家”的兴趣。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被用作解释研究者感兴趣的现象的原因,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或一种制度组织的国家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来自所有主要学科不同理论倾向的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为数已十分可观,所探讨的领域也非常宽广。①〔美〕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美〕埃文斯、〔美〕鲁施迈耶、〔美〕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3页。在这些学科中,与音乐的亲和力比较相近的文化人类学家探究的是非西方背景下“国家”的特殊含义和行为特征,如格尔茨探讨的“19世纪巴厘岛的剧场国家”。音乐这个学科也不例外,也可以参与到“从社会中心理论到重新对国家产生兴趣”②〔美〕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美〕埃文斯、〔美〕鲁施迈耶、〔美〕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3页。的道路上来。
首先从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考察。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所见的与音乐教育相关的一些现象碎片可见,音乐活动展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学校音乐教育的“课外化”。过去20年实行素质教育政策以来,学生在校时间缩短,音乐类课程教学时数和师资投入勉强满足国家规定。能代表学校音乐教育水平的就是经过选拔和课外特定训练的音乐团体,其主要功能在于代表学校参赛并作为遴选学生个体升学的额外指标。而在“课后330”政策③“课后330”政策,即解决学生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后怎么办的问题,政府对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建议时间段一般为15︰30—17︰30。实施以后,大量学校就开始名正言顺地将音乐类课程进行教学外包,强化课外培训。第二,音乐学习的“家庭化”。简言之就是每个孩子从小就被期待学习一门乐器或者一种能进行当众表演的音乐技能。个体被当作音乐活动参与者的唯一维度,群性的发展在个体的竞争之中逐渐衰减。第三,音乐表现的“公共化”。歌手选秀节目、广场舞、快闪之类的节目弥漫在公众的公共生活之中,却并没有成为音乐教育研究领域严肃的研究主题。第四,音乐品味的“考级化”。无级别,就无水平。与“公共化”相反,这种对音乐活动的个体参与者的评价体系,一方面推动了音乐技能的全面普及,另一方面是“竞技场”走到极致后带来的“零和博弈”——一些人的成功就必须伴随另一些人的失败,这使得音乐作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共鸣”载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五,音乐水平的“比赛化”。比赛才有名次,有名次才有名望,满墙满柜的获奖证书证明的更可能是有“打败”别人的能力。鉴别是必要的,但把鉴别代替了表现,恐怕就是本末倒置。第六,音乐素养的“无脑化”。音乐是否无需懂,会玩就行?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高精尖”,而大众的音乐素养似乎在这种高门槛之下无所适从,也无从认定。音乐专业教育和音乐普通教育两个体系之间是越来越分野,还是应该越来越融通?
这些现象的碎片所引发的思考,归结起来就是雷默(Reimer)与其他音乐专业领导者的警告:当今音乐教育中潜藏着精英主义,尽管很少有学者将这种精英主义与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④Reimer,B..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2nd ed.).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89.学校音乐方案分不清教育、职业训练和娱乐功能之间的不同取向:如果取“娱乐”的一端,则音乐称不上值得学术探究或严谨调查的东西,只是娱乐时光的陪衬而已;如果取“职业训练”的一极,那么音乐教育无可避免地沦为功利主义;如果认为音乐具备独特的“教育”价值,那么现有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不是对音乐的教育价值视而不见了?⑤〔美〕珍妮特·巴雷特、〔美〕彼得·韦伯斯特:《音乐的经验:重新思考音乐教学与学习》,余丹红主编,梁菁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7-29页。特别是在普通的基础教育学校和普通高校之中。
回到一开始的多学科关于“国家理论”的关注点。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开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问题。超越公民的身份和政治生活的成员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是探究人群的善。⑥吴恩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导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viii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几乎用整个第八章来讨论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教育在国家政治的范畴内究竟何为。在他看来,就像体育的目的绝不是训练冠军,而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一样,音乐教育也应该断然弃绝与职业艺人一较短长的虚荣心,转而培养有教养、有品位的业余性的音乐实践者,而这些人从事音乐的唯一原因是因为直接的艺术经验有助于培育自己的判断力。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24–426页。
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得到了许多现代音乐家的支持。他们一致认为,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必须是实践者,不能只坐在音乐厅的观众席上或者守在电唱机旁,而是必须亲自演奏和演唱,哪怕他们永远都只有笨拙的办法。⑧〔法〕马鲁:《古典教育史》(希腊卷),龚觅、孟玉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不看重技能,而看重亲身的参与和实践,这就是音乐教育的公共性维度。而公共性,是现代国家的首要性质。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至后世的音乐古风浓郁,不尽在技艺的层面,它负载着一种天真质朴的观念,即音乐必须具有功利性,有益于道德的建构,能促成个体和社会自律人格的养成。教育变得越来越知识化,只有与社会生活真正连接起来,音乐的真正面貌和最活跃的样子才能负载其功能。⑨同注⑧,第299;293–294;294–295页。
音乐教育的“社会公正”之问
问题由此转入音乐教育的范畴之内,从跨学科比较的角度,借用贝蒂·安妮·杨克勒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沉思⑩同注⑤,第11–18页。,我们可以展开一系列的发问,然后再探究问题的根源与可能的转向。
音乐教育的“永恒之问”:如何提高学生的音乐经验?如何让学生们直接参与音乐活动?
音乐的“审美教育”之问:为什么以及如何让学生参与到音乐实践中?
音乐教育的“自由主义”之问:如何让学生不受一种方法的制约?如何超越表演经验,以更多方式参与音乐?如何从作曲、即兴、评论和聆听中获得经验并产生意义?
音乐教育的“女性主义之问”:我们应该聆听谁的声音?演奏何人的音乐?谁应该执掌指挥棒?音乐经验如何能得到释放,又是如何受到压抑?
音乐教育的“族群主义”之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去扩宽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让他们的眼中不再只有传统的西欧音乐艺术?
上述发问从音乐教育直接面向个体的经验探究渐渐转向集体的经验选择,而越偏向后者,在音乐教育中越走向式微。这个变迁过程并不只是当代的中国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在《古典教育史》中,法国学者马鲁论述了音乐在文化教育中的隐退过程。
“曾几何时,音乐在古典时代曾和文学、体育并列为教育的三大传统分支,但到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按照当时公共学校的规章,每一所学校应该配备3位文学教师、2位体育教师和1位音乐教师。一般来说音乐教师是一位游离于学校体制之外的专家。其教学并非面向所有年龄段的学生,而是仅仅针对将要进入青年学校的最高两个年级的学生或未满18岁的青年。教学内容被严格限定:对于后者,讲授七弦琴技法和乐理,对于前者则只讲授乐理。此时的乐理几乎与纯数学无异。音乐会也不会列入青年学校参加的种类繁多的竞赛之中。”⑪同注⑧,第299;293–294;294–295页。
“在音乐领域里发生的现象与体育竞技经历的变故近似:技艺的进展推进了整个领域的专业化,随即导致了与大众性的文化和教育的脱节。当梅拉尼皮德斯、基内西亚斯、福里尼斯、提摩泰斯等大作曲家引入了精美的和声结构、旋律和完善的器乐技法,原先存在于音乐与文化教育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希腊音乐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精密复杂的技艺,一般大众则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雅典和斯巴达的保守派们指责音乐的演变导致了趣味的腐化,但大势所趋已无法挽回。到了希腊化时代初期,分离最终完成:少数职业音乐家垄断了这一伟大的艺术,使那些即便教养良好的音乐爱好者也彻底沦为与创作无缘的纯粹欣赏者,这种变迁与体育爱好者在职业选手面前的弱势如出一辙。”⑫同注⑧,第299;293–294;294–295页。
体育领域好歹最后通过创设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部分解决了这种对立,音乐教育由此不得不持续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选择,如何解决参与者的分化问题?“古典音乐”的程式、框架和势力已然形成,并且越来越走向以乐理和技法为目标的科学测量主义,但社会生活川流不息,多姿多彩,断然不会按照古典音乐的体系来构建人们的音乐生活。那么,音乐教育是否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追随“现代”音乐的演变?如果放弃这样的努力,会不会从此远离这个时代活生生的文化,从而无法完成音乐启蒙的使命?
因此,接续上述发问,我们还可以发出音乐教育的“社会公正”之问:当我们融入群体时,我们可以期待学到新东西、参与新的音乐活动吗?我们想要进入“他人的世界”,是否应该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如何构建音乐学习环境,教学生与他人协作?这就把音乐作为一个学习科目从古典音乐的体系中拖拽出来,从现代教育原理中极为关注的“社会化学习”⑬“社会化学习”关注的焦点从内容的主题学习转移到围绕内容的学习活动和人与人互动,从而可以解释小组学习的绩效。学生在学习小组中可以提出问题,以澄清不确定的领域或困惑,从同伴那里听取该问题的思路和答案,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甚至可以取代教师的作用,还可以帮助其他小组成员,并从他们的理解中受益。“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是社会化学习的重要议题。观念来看,来探寻以教育之名而建立的人际关系中开展音乐教育的可欲性。
音乐教育的复杂性在于,在西方古典教育中,被当作人文教育的支撑科目,负载多元化的价值,后来隐退;在现代教育中,被当作审美教育的科目,负载的是艺术性的功能。特别是在当代,当消费社会已经涤荡各个领域时,创意文化产业经常成为一个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经济体的发力点,音乐在其中向来被期待承担极其重要的功能。审美资本主义说明了一种经济的变革,在艺术和时尚相结合成为主要潮流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在本质上不是有用的商品流通和购得的问题,而是一个服从审美判断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审美空间。⑭〔法〕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姜丹丹、何乏笔主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实际上,在审美资本化所助推的经济增长之中,已经融合了公共性的维度,也就是说,这种增长绝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一个国家的人朝向一种增长方向的迈进。
本文故而要追问的问题是:在审美资本化的一端,和公共领域融合的另一端,音乐教育的上述问题可以得到解答吗?结合音乐活动的个体化特征凸显,如果将“音乐考级”作为音乐水平的鉴定手段,那么这种基于科学测量运动而诞生的人文事件,能否自然而然地拯救音乐活动的公共性?进一步,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从来都是作为可见的、大范围的公共空间,音乐也从来都是作为国家认同和社会融合的重要手段。这并不是不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所构建的超越国家的、虚拟的、想象的音乐共同体⑮专门研究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的美国学者苯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讲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即“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不但没有像一般社会科学家那样以实证主义式的傲慢忽视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反而直接面对这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性问题,并在他的架构中为之赋予适当的诠释与意义。这个途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的箴言。把民族国家当作想象的共同体,这对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古典音乐体系、理解音乐共同体、音乐教育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参见〔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然而音乐的全球化并不能取代和遮蔽其独有的“国家资产”的性质。把音乐教育置于一国之内来考察,具有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就此,本文一直想要追问:音乐教育作为国家资产,如何从科学主义走向社群主义(communism)?
现代音乐教育伴随追求社会正义的历史进程
在20世纪,进步的教育家们公开批评教育在维护社会不公方面的作用,以及教育体系对社会公正缺乏关注。教育改革的话语焦点从自上而下的公平理念转向了一种社会信念,即“创建公正的社会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民主进程”。⑯Boyles,D.,Carusi,T.,& Attick,D..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Justice.In W.Ayers,T.Quinn,& D.Stovall (Eds.),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Education.New York: Routledge,2008,pp.30–42.根据杜威的观点,学校应该是一个活跃的、积极的社区,对与社会不平等有关的问题进行审议。学校应该成为培养儿童社会意识和社会理想的一种手段。⑰Kahne,Joseph.Reframing Educational Policy:Democracy,Community,and the Individual.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6,pp.25–46.
在20世纪前20年,美国涌入大量的新移民,要求学校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纳不同种族的学生。将移民融入主流文化,通常被称为熔炉理论,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成立于1907年的全国音乐督导会议(The Music Supervisors National Conference,简称MSNC)于1914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为深入学校社区,发展歌唱文化,促进学校与社区的关系。这种活动与杜威的教育哲学相一致,包含了文化和解放社会正义的种子。涂尔干是社会学领域的创始人物,他认为:“社会只有在其成员中存在足够程度的同质化才能生存;教育通过从一开始就将社会生活所需的基本相似性固定在孩子身上,从而使这种同质性得以延续和强化。”⑱转引自Mccarthy,M.Understanding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History.Benedict,C.,Schmidt,P.,Spruce,G.and Woodford,P..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Music Education,2015,p.35.涂尔干的功能主义教育观符合美国化的社会理想,即所有移民通过学习语言、参加国家假日和庆祝活动、上公立学校和学习公民的价值观而成为国家公民。
在公立学校音乐教育中,音乐被视为一种活动,通过唱歌和演奏乐器,将不同种族背景、社会阶层和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从而灌输国家民族的理想。音乐教师通过演唱爱国歌曲和各种西欧国家的民歌来吸收移民,而这些歌曲在当时的学校音乐中占了主导地位。⑲Volk,T.M..Music,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44.利用国际性的民歌来实现民族主义目标是出于善意的。然而,它回避了一个问题:谁的历史在民歌转译中得到了体现?民歌是如何在公立学校使用的?“异域音乐”与学校社区文化多元化的现实有什么联系?重点不是学生在社区中的身份认同,而是通过音乐教育实现文化同质化和国家公民身份。⑳Mccarthy,M.Understanding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History.Benedict,C.,Schmidt,P.,Spruce,G.and Woodford,P..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Music Education,2015,p.35.
社群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教育组织和实施方式上是显而易见的,注重的是同质性和分配正义,由此质疑教育实践在社会公正的背景下的作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个人和群体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差异的科学测量支持了种族排名,并为种族和族群体之间的智力和道德差异提供了“科学证据”㉑Williamson,J.A.,Rhodes,L.,& Dunson,M..A Selected History of Social Justice in Education.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2007(31),pp.195–224.。智力测验、排名与剖析等教育常模(norm)对音乐教育中的思维产生了影响,这在音乐天赋与能力测试的公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随后,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教育的社群主义方法和在战时团结人民的必要性。20世纪前40年的战争气候和民族、公民教育目标影响了音乐的发展方向,保持了音乐教育作为国家资产的地位。音乐的普世价值以国际和谐、正义与和平的名义,将各国人民和国家团结起来㉒McCarthy,M..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1953–2003.Nedlands,Wester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2004.。在此时期,音乐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的强大隐喻,被音乐界和教育界人士作为一种证明音乐在国家、社会、族群、国际交往中的合理性方法而流行开来,音乐跨越国界的性质几乎不言而喻,毋庸置疑。音乐教育既是一种国家资产,也是一种国际性的公共文化产品。
总之,音乐在教育中的方向与占主导地位的社群主义社会理论是一致的。简言之,音乐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族群之内乃至跨越族际之间的人们能够有一种“共通感”,认为自己和他人在某种范畴和意义上是同一类人。然而,为什么现在要如此强调音乐教育的这种作用呢?这难道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拥有音乐时就具备的功能么?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恰好是社群主义走向单一化的极致所导致的。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尤其值得今天推进公共音乐活动的主导者警惕。在希腊文化和教育传统中,音乐的重要性绝不在体育之下,而各种音乐之中又首推器乐。当然,在器乐之外也学习歌唱。与独唱相比,希腊人最喜欢的还是合唱。从乐理上看,希腊式的合唱十分简单,因为当时没有复调,合唱队要么同音齐唱,要么以差八度音混声合唱,无论哪种情况,总会以乐器伴奏。到了后期,随着人们对合唱艺术质量的日益重视和演唱技巧的不断完善,合唱队员不再从爱好音乐的普通公民中临时选拔,他们越来越专业化,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出现了真正职业化的合唱团。合唱的功用主要是让青少年参与祭神大典,这既是法律的命令,又是神圣传统的要求。宗教典礼在希腊化时代青年教育中有着不容轻视的作用,合唱充当了发挥这种作用的桥梁。历史的吊诡就在于,鉴于典礼音乐的实用性和单调性,只需事先让一位专门的合唱教练对参加合唱队的青年们进行快速培训即可,而不需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音乐教育。进而,合唱教学也无需被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㉓同注⑧,第286–291页。音乐的典礼和仪式功能既然可以如此速成和交易,那么学校的音乐教育就可以收工了。音乐在文化教育领域就此隐退。
音乐教育作为国家资产:呼唤共同建构与协商的评价模式
对任何国家的公共空间来说,社会公正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缓解不公平、无力和歧视一直是公共教育政策的目标,音乐教育中追求社会融合不仅仅意味着承认差异,并应该允许课堂和其他教育空间具有更大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追求社会公正是十分复杂和高难度的一连串活动,涉及对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利益的裁决,对政治行动和对公众福利的关注,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或受压迫的人的福利。在音乐活动的参与者被历史性地区分为职业音乐家和业余欣赏者之后,这项任务尤其艰巨。如果要避免自以为是和过于简单化,那么这个议题必须从认识社会生活和分享经验的复杂性开始,同时要关注整个“命运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群体,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教育。现实情况经常是,追求社会公正只会使少数幸运的人受益,以其他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为代价。对某些人的正义很容易导致或被视为对其他人的不公正。
此外,社会正义理想本身有时被利益集团作为修辞手段加以利用,它也确实可以用来掩盖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因此,这种紧张关系将社会公正定义为一种道德和伦理上的代言,而将其定位为一种理想、一系列取向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并将其置于音乐教育改革的中心。
对于音乐教育来说,当下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公平问题。尤其是在这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时代,音乐的可获得性、音乐训练的昂贵性、音乐教育的准入性等等,都涉及音乐教育实践为什么、如何追求理想的美育目标乃至社会功能,这一点对于音乐教育的从业者来说尤其重要。对实现社会公正的关注和实践有助于减轻社会和教育达尔文主义的恶劣影响,在教育内卷到极致的情况下,“丛林规则”曾经那么有效地通过竞争提高质量,而现在则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崩溃和逃离。在统一的、标准化的、严丝合缝的科学测量指标之下,每个胜出者都越来越相似,如出一辙,看似是一个严整的共同体,实际上已经在内部缺乏交流的必要了。
如何评价的问题呼之欲出。著名的评估专家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㉔Guba,E.& Lincoln,Y..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1989.依据建构主义方法论,针对前三代评估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出“评价就是对被评事物赋予价值,它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建构,评价描述的并不是事物真正的、客观的状态,而是参与评价的人或团体关于评价对象的一种主观性认识,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建构’”。和前三代评估比较起来,第四代在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协商确定评估参数和界限,互动过程产生一个或多个构建”;在评估产出上是“多方协商的共识”;在意义上是“提出一种全面的积极参与,各利益相关者在评估中地位平等”的评价观。在第四代评估提出之前,教育评估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代:测量时代、描述时代和判断时代。存在的不足是: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太浓;忽视价值的多元化;过分强调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而忽视其他方法的使用,使评估过程形成了严格的、固定不变的程序,从而使评估活动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和弹性。
第四代评估的出发点是对利益相关者各方评估要求的“回应”。评估并没有固定的问题、指标、方法,而是广泛动员所有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提出自己的关切,形成广泛的议题,达成共识并不是唯一目标,因此第四代评估的本质是共同建构。参与评估与评估有关的人或团体基于对评估对象的认识,通过不断的协商、对话和交流,不断发现新问题,协调教育价值观,缩小关于教育评估结果意见的分歧,最后形成新的共识。
第四代评估者强调,心理建构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形成的,应该在“自然情境”中进行探究和评价。由于探究在自然情境中进行,这就决定了探究需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必须更多地依靠人的感官和思维来做研究和评判,包括通过观察、座谈、阅读文献、记录未被人注意的迹象、重视人的非言语意向等来探究问题。这种心理建构与音乐的本体论和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不谋而合的。“探究过程”究其本质而言是建构性的,是一个“诠释性辩证循环圈”。其运作原理是,尽可能吸收各方对评价活动的意见和见解,各方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其他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形成所谓的“共同建构”。音乐向来是多向度阐释和表达的活动,形成一致性评价并不是必然结果,反而更可能是一致的教育过程和评价指标体系“造就”的结果。诠释性辩证循环圈也许会带来音乐参与者的多元智能的释放、解放和怒放,特别是解决当下的音乐教育在激发学习者表演尚且乏力之余,这种评价过程还有可能带来普通音乐教育中学习者的音乐创作的潜能。“探究结果”是经过多重诠释辩证的循环过程,评价的最终结果是参与评估及与评估有关的人或团体基于对对象的认识,通过协商而整合而成的一种共同的、一致的看法。这说明第四代评估充分考量评估过程所引发的社会融合功能,尽管有分歧,尽管各个评估参与者对主观性、客观性的追求各有不同,也会导致在评估过程中很容易滑入“绝对标准”和“第三方客观”的老路,但这也并不表明第四代评估走向了相对主义,而是将评估过程本身当作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不是独立于被评估者和被评估活动的,而是相互嵌套,相互纠偏,特别是被评估者自身的声音应该被充分重视。
在把学生削平成一个样子之前,必须先考虑学生的差异,同时确保哲学家罗尔斯所谓“公平的机会均等”㉕〔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根据学生的需要更公平、公正地分配教育资源。我们把这一点与被相当简单化理解,而且往往是有害的“机会平等”概念对立起来,以便提请注意:一个倾向于让有才华和文化特权的人获利的过程,他们被认为最有能力从稀缺的教育资源中获益,然而被屏蔽的才华和文化担当者可能更多。思考社会融合和社会正义等社群主义的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打破长期主导和持续的以“教育赤字”模式为前提的经济学逻辑。这种经济学逻辑认为,优质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不足的,那么某些个人和社区如果被视为持续缺乏资源,就顺理成章地、似乎无能为力地被甩出去。然而,音乐的最首要的特征是声音,声音的传播本来可以做到跨越边界,在不同的人之中、心之内产生共鸣,而共鸣是当代批判教育学面对个体化、原子化社会所提出的最高追求。恰好,音乐作为教育的独特途径,在这方面可以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音乐教育内部来说,就得和陈规决裂,彻底摆脱自奥林波斯教的时代(公元前7世纪)起一直把它禁锢在狭小古旧的圈子里的那个狂热传统,进而将反映日新月异的、活生生的艺术作为己任—哪怕这种反映总是滞后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变形。㉖同注⑧,第296;296;298–299页。泥古不化造就了学校音乐与现实艺术之间日益疏离的结局,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原本如此独特和生动的音乐教育,到了希腊化时代却变得如此苍白,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
事实上,今天也还是这样的,早早地让孩子练习按照难度和比赛级别而编排的曲目,似乎只是为了让他们熟悉音乐家的语言。这也不奇怪,和众多的教育理论家一样,亚里士多德未能从他深刻而推理严谨的学说中提炼一套可供指导实践的策略。他们除了坐等音乐教育陷入传统的泥沼,什么也没有做。㉗同注⑧,第296;296;298–299页。既然如此,音乐从教育中被弃绝,教育从生活中被弃绝,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诧。
然而,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音乐虽然在过去从通识教育中隐退了,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文化领域的消失—尽管林谷芳曾发出喟叹:谈中国文化,为何独缺音乐一环㉘林谷芳:《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音乐越来越成为技艺精湛的职业人士的专属,人们对职业艺术家的观感总是爱憎交织。一方面,他们因其才能而受到众人的倾慕,观众愿意为他们的演出付出好价钱;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被鄙视的对象,被排斥在只有“高雅人士”方可自由出入的社交圈之外。㉙同注⑧,第296;296;298–299页。要化解这两方面的冲突感,我们对音乐教育的评估过程如果采取上述社会功能和社会心理建构的取向,那么就会了解,呈现不同的声音相比达成一致性共识可能更加重要。如果我们相信一个社会的正义首要的途径是发出声音,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共同建构与协商的评估能够挖掘普通的音乐参与者的多元化音乐表现,音乐教育也可以开创多姿多彩的路径,结出丰硕的令人惊奇的果实。
结 语
正如教育哲学家马丁(Jane Roland Martin)所言,“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采用一种思想框架,其精神前提是稀缺性,我们忘记了对于文化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大富足(super abundance)的问题”㉚Martin,J.R.The Wealth of Cultures and Problems of Generations.In S.Tozer (Ed.),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Yearbook (pp.23–38).Urbana,IL: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1998,p.24.。在正规的音乐教育中,这种缺失的教育模式往往是基于合法音乐知识的过分狭隘的定义,这一认识使得缺乏适当文化资本的儿童望而却步,而音乐教师却忽视了在这个国家之内、不同的族群之中存在的音乐财富。文化财富确实不同于物质财富,丰富的文化构成了音乐课程源源不断的基础:它不仅是课程内容和主题的来源,也是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来源。这里的重点不只是在于包容性和多样性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在关键的参与、授权和创造力上。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课程和教学实践有助于对任何音乐和音乐教育方法进行批判性审查,从而也有助于更广泛的参与和交流,更有可能提高个人和集体的能动性和满意度,同时也有助于更具创造力、公平性和生产力的社会。任何国家和小世界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其特点往往是冲突和分布式的知识乃至某种程度的无知,我们在倡导从科学主义走向社会社群主义的时候需要非常谨慎。面对那些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成功地运用传统音乐或方法来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政策是否需要对他们提供资助或仓促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应该纳入第四代评估的途径和方法,尽可能地让评估所涉及的参与者都纳入进来,让不同的声音有发出来的机会。这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纵观不长的历史,测量的科学给音乐教育带来一种广为人知的观念,如音乐作品习得的数量、唱奏技巧的精确等级、音乐从业人员的区分类别、音乐衍生品的社会区隔空间等等,这些概念构建了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以描述的方法为表征的第四代评估可能给音乐教育带来一些有吸引力但还在悄然生长的可能性,如模糊的音乐专业性地带、多元的音乐空间/声景、以音乐记忆的自我叙事作为身份认同、人群的社会区隔以音乐作为黏合剂等等。其实,这些可能性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音乐进入人类社会生活并成为一种专门的实践领域之时,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教育伴随着追求社会正义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提问的方式来得出:音乐教育是否应该重返原初就具备的社会功能?
新世纪以来,诸多研究者公开批评教育越来越缺乏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学校致力于让自己变得更有特色的同时也着力让每个孩子变得与众不同。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学校系统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纳不同类别的学生,然而,各阶层、各地区、各学校乃至个人之间差异越来越大,并没有带来教育系统对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强调。如果将音乐视为一种活动,那么学校应该通过唱歌和演奏乐器,将不同差异背景的师生团结在一起,让学校成为“包含多样性的整体”。
一个社会只有当其成员中存在足够的同质化时才能存续,教育通过音乐这种特殊而又普遍的工具,从一开始就可以将社会生活所需的基本相似性固定在孩子身上,从而使这种同质性得以延续和强化。因此,音乐教育作为国家资产,要有助于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需要换个角度审视其独特的本体论价值,从之前强调用科学测量的工具区分音乐等级和能力差异的技术取向,重返其以描述确认自身和群体属性的“社会熔炉”的功能取向。
在“正常”和传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参数内外,有许多令人鼓舞的音乐教育行动途径,可以帮助我们将杜威关于参与式、协商式的社群作为一种伦理理想和共同生活方式的理念具体化,从而释放人的能力。替代方案和教学模式可能会对教师和其他人提出挑战,让他们重新思考他们对音乐教育机构、音乐教育项目的社会融合功能和公民责任的理解,从而为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共同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理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