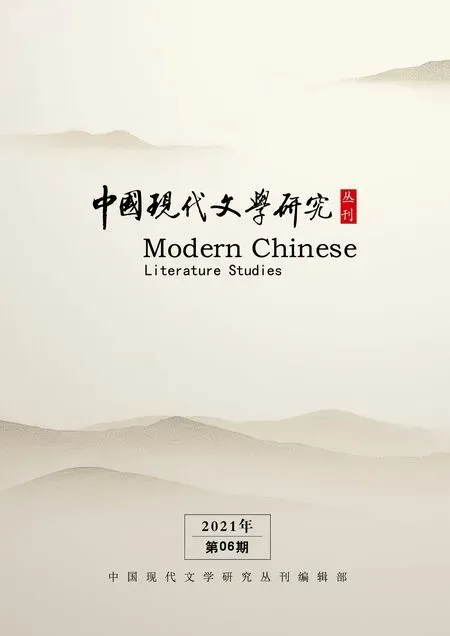论日本“二二六”事件对郭沫若的影响※——以考证郭沫若致《宇宙风》五函的写作时间为基础
廖久明
内容提要:《宇宙风》乙刊第2期发表的郭沫若五函的写作时间分别为:1935年8月中旬,1936年3月上旬、3月上中旬、3月下旬、6月1日。以前人们对这五函写作时间的认定要么错误,要么没有达到可以达到的精确度。郭沫若在1936年1月18日写作的《论“幽默”》对幽默小品文进行严厉批评后,却在一两个月后写作的第二、四函中呼吁团结御侮,致使幽默小品文论争没有再次发生,其原因是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后,郭沫若也“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将导致向中国扩张”,所以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1936年日本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二十世纪国际问题词典》是这样介绍的:
.....二二六事件.日本皇道派法西斯军人未遂武装政变事件。1936年2月26日凌晨,安藤辉三、村中孝次等20余名不满政府政策的青年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在东京发动叛乱,占领陆军省、警视厅等许多重要行政机关,袭击首相等高级官吏住宅,杀死内大臣(前首相)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并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独裁统治,以便更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未取得东京驻军支持。29日,在政府军队的镇压下,叛军束手就擒。10余名军官被处决,陆军中央对全军的统制确立。军部乘机操纵在军部占主导地位的广田弘毅组阁,基本建立法西斯统治。1
该次“未遂武装政变事件”也被称作“二二六”兵变、“二二六”政变、“二二六”暴乱等。该事件不但使日本“基本建立法西斯统治”,并且对正流亡日本的郭沫若造成了巨大影响。
要论述该影响,必须从考证《宇宙风》乙刊第2期(1939年3月16日)发表的郭沫若致《宇宙风》五函的写作时间入手。这五函发表时题为《作家书简(二)》2,无收信人和写信时间;在《郭沫若研究专刊》第2辑(1980年11月)发表和收入《郭沫若佚文集》(1988年)时未标明写作时间,标题均为《致〈宇宙风〉信》,题注中有这样的文字:“据查,信是写给《宇宙风》社编者兼发行人陶亢德的。”收入《郭沫若书信集》(1992年)时,将《郭沫若研究专刊》第2辑发表的《致陶元惪信》和《致〈宇宙风〉信》合并在一起,认定收信人为陶亢德,认定这五函的写作时间分别为:第一函为“193×年×月×日”,第二至第五函为“1936年×月×日”;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认定这五函的写作时间、收信人分别为:1935年7、8月间致陶亢德,1936年2月下旬致林语堂,1936年3月致陶亢德,1936年4月致陶亢德,1936年5月底致陶亢德。3现在,笔者对发表在《宇宙风》乙刊第2期这五函的写作时间和收信人进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日本“二二六”事件对郭沫若造成的巨大影响。
一 郭沫若致《宇宙风》五函写作时间考证
第一函
惠书收到。承询《海外十年》之作本是前几年想写的东西,但还没有动笔,如在现在写起来,要成为《海外廿年》了。所想写的是前在日本所过的生活,假如尽性写时总当在廿万字以上,这样长的东西怕半月刊不适宜吧。
《浪花十日》之类的文章可以做,但如不从事旅行便难得那样的文章。因此我希望你们按月能寄两三百元的中币来,我也可以拨去手中的它事来用心写些小品,按月可以有两三万字寄给你们发表,你们觉得怎样呢?假使这样嫌松泛了时,按字数计算,千字十元发表费亦可,但也要请先寄费来后清算。请你们酌量一下罢。专复即颂
撰安。
郭沫若顿首
关于郭沫若致函事,陶亢德有如此回忆:
语堂和我与鼎堂本不相识,所以办《论语》时未尝请他撰文。后来办《人间世》,有一次冰莹来信说起鼎堂在日本经济不大宽裕,《人间世》《论语》能不能请他撰文(其时冰莹也在日本)。约人撰稿本来是我的事,语堂也决不会反对,鼎堂的文章求之无方罢了,现在既有冰莹作介,我就立刻复信请她代为恳切求稿。后来鼎堂来信,说是有一部《离骚》的白话译稿,不知要否。和语堂一商量,大家觉得恐怕太长,而且既是诗,出版者方面也许不大称心,于是回他一信,婉请撰惠别的文章。结果也就没有下文。此后又办《宇宙风》了,这杂志我是把他当作性命看待的,血心要办它成为一个“精彩绝伦”的散文半月刊,在盘肠大战的想人约稿中,不由不想到有过上述一点因缘的郭鼎堂。于是在决定杂志创刊之前,就写了一信给他,并且指定要他写长篇自叙传《海外十年》,或如不久之前登在《文学》上的他的游记《浪花十日》两类小品。这《海外十年》的题目是他以前在一篇什么文章里提起过的,总算我那时候记性不坏,竟还记得。他的回信是说《海外十年》现在成为《海外廿年》了,写《浪花十日》之类的文章也须先有钱旅行。后来一说两说决定写《海外十年》,我也先汇去了一百元国币作预支稿费。现在大家看到一百元三字也许要笑话我何必郑重其事,殊不知姑不论当时的一百元钱胜过现在的几千,就是只要知道《宇宙风》的全部资本不过五百大元,而一个作家的稿费预支一支就支去了五分之一,也当原谅我今日回想起来怎不大书特书一下的私衷了。4
根据引文可以知道,第一函为陶亢德回忆中的以下信件:“他的回信是说《海外十年》现在成为《海外廿年》了,写《浪花十日》之类的文章也须先有钱旅行。”
现在看看郭沫若1935年8月24日写在明信片上的以下文字:
陶元惪先生的信和款子均已奉到,我决计写“海外十年”,分段地写,写完留学时代的生活为止。第一段是“初出夔门”,今日动手写,大约三五日内可以写出。怕你们悬念,特此写一张信片来报告。5
由于该明信片的开头直呼“陶元惪”的姓名,可以认为是写给《宇宙风》编辑部的。根据该函中的“我决计写‘海外十年’”可以知道,陶亢德在上一函中并未指定郭沫若写什么,只是希望在《海外十年》或者“《浪花十日》之类的文章”中任选一种。结合上引文字可以推断出如下的写信经过:一、《宇宙风》创刊前,陶亢德致函郭沫若,“指定要他写长篇自叙传《海外十年》,或如不久之前登在《文学》上的他的游记《浪花十日》两类小品”。二、郭沫若复函道:“《海外十年》现在成为《海外廿年》了,写《浪花十日》之类的文章也须先有钱旅行。”三、陶亢德复函中由郭沫若自己决定写什么,并“汇去了一百元国币作预支稿费”。四、郭沫若于1935年8月24日致函《宇宙风》编辑部“决计写‘海外十年’”。在这四函中,陶亢德写作的两函迄今未见,郭沫若写作的第一函即需要考证写作时间的这函,第二函已知写作时间。
首先考证一下郭沫若与陶亢德通信一次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郭沫若和这几个“文学大师”》除影印了郭沫若1935年8月24日致《宇宙风》编辑部的明信片外,同页还影印了郭沫若致《宇宙风》的一个信封。6信封上日本邮戳时间是“10.10.23”,中国邮戳时间是“十月廿八”,日本邮戳时间只能释读为昭和10年10月23日即1935年10月23日,才能与中国邮戳时间衔接起来。如此算来,当时从郭沫若将书信交到日本邮局、盖上邮戳,到送抵上海、盖上当地邮戳的时间是6天——反之应该亦然。不管是急需用钱的郭沫若还是急需稿子的陶亢德,收到对方来信后都会立即回信,收到对方来信后立即复信、投递到邮局并盖上邮戳应该需要一天时间。如此算来,郭沫若与陶亢德书信往返一次需要7天时间。再看看郭沫若1933年4月3日致叶灵凤函的以下文字可以知道,笔者根据邮戳的推断是正确的:“今天是四月三号,此信到你手里当在十号以前,我将特别提醒你,请你于四月十号务必将二百元寄出。”7郭沫若如此肯定地告诉叶灵凤收到自己该函的时间,很明显是基于以往的经验。
现在,通过倒推便能知道该函的大致写作时间:1935年8月24日郭沫若通过明信片告诉《宇宙风》编辑部,谈收到稿费事和自己的写作计划;8月18日陶亢德复函中由郭沫若自己决定写什么,并“汇去了一百元国币作预支稿费”(该函迄今未见);8月12日郭沫若致函陶亢德同意写作并提出条件;8月6日陶亢德致函郭沫若向其约稿(该函迄今未见)。如此算来,该函写作时间为1935年8月12日。由于实际情况与理论计算之间总有差距,并且往返之间延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该函的写作时间最好确定为1935年8月中旬。
第二函
二月十二日信接到。《日本之春》不能写,但《海外十年》是可以续写的,大约在贵志十四期上便可重与读者见面。但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希望你和××先生能够采纳。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拢统的谩骂。(以前的左翼犯有此病,近因内部纠正,已改换旧辙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请你们回我一信,如以为我这种意见值不得采纳的,也请你们明白地回答一句,我好把前所预受的五十元稿费立即奉还。如以为是可以采纳,那是最好也没有的。《海外十年》的第六节是《在朝鲜的尖端》,可登预告也。此复即颂
安好。
郭沫若
考证该信写作时间有两条线索:一、“二月十二日信接到”,二、“《日本之春》不能写,但《海外十年》是可以续写的,大约在贵志十四期上便可重与读者见面”。现在据此进行考证。
根据第一函的考证可以知道,郭沫若与《宇宙风》编辑部书信往返一次需要7天时间,一般情况下,陶亢德2月12日发出的信,郭沫若收到时间当为2月17日,如果立即回复,落款应为当日——盖上邮戳的时间很可能为次日。为保险起见,可以认为郭沫若立即回信的时间为1936年2月20日左右。
1936年2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第11期《编辑后记》有这样一段话:“下下期即第十三期拟出一春季特大号,先此预告一下。”3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第12期《编辑后记》继续预告:“下期本刊是春季特大号,也是本刊出版半年的一个纪念,将以最丰富最精彩的内容与读者诸君相见。”3月16日,作为春季特大号的《宇宙风》第13期出版,发表了丰子恺的《春人四题(画)》、知堂的《北平的春天》、木石的《春在东京》、姚颖的《南京的春天》、春风的《沈阳的春天》、施蛰存的《春天的诗句》。由此可以明白郭沫若复函中的“《日本之春》不能写”的意思:在确定《宇宙风》第13期为“春季特大号”后,陶亢德于2月12日致函郭沫若请写作《日本之春》,郭沫若则在复函中告诉陶亢德:“《日本之春》不能写,但《海外十年》是可以续写的,大约在贵志十四期上便可重与读者见面。”《宇宙风》第14期的正常出版时间是4月1日,现在来考证郭沫若写作该函的大概时间。
郭沫若在1935年8月24日致《宇宙风》编辑部的明信片上如此写道:“第一段是‘初出夔门’,今日动手写,大约三五日内可以写出。”取中间时间,假设4天写成,完成时间当为1935年8月28日。刊登有《初出夔门》的《宇宙风》第1期的出版时间是1935年9月16日,意味着郭沫若完稿后立即寄出并立即登载需要的时间是20天左右。那么,为了确保在4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第14期发表,郭沫若需要在1936年3月12日左右寄出。假设写作《在朝鲜的尖端》同样需要4天时间,意味着郭沫若写作该函的时间是1936年3月8日左右。
根据函中的两条线索考证出来的写作时间相差半个多月,笔者可以肯定写作时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理由为:陶亢德来函时间是1936年2月12日,假设郭沫若2月17日收到来函后便决定写作《海外十年》的第六节《在朝鲜的尖端》,那么,他应该在复函中写,“大约在贵志十三期上便可重与读者见面”,引文却是“大约在贵志十四期上便可重与读者见面”,由此可以断定该函写作时间是1936年3月8日左右。同样,考虑到误差,最好将该函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936年3月上旬。
现在来看看陶亢德的以下回忆文字:
天下事往往难于逆料,我们虽以一番诚心十分力量请鼎堂撰文,谁知《海外十年》登了没有多少字之后,他竟在一篇什么小说书(只记得书名中有个铁字的)的序文中把我们臭骂了一顿,说幽默和小品之类是四马路上的卖笑妇。这篇文章转载在《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上,后面还有不知什么人的后记,说是郭公的为《宇宙风》写文章,是不知国内文坛状况,受人之愚,今已明白,故《海外十年》已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云云。鼎堂原文和什么人的附记,我们看了自然“为之大怒”,我一面写信询鼎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面写了篇《鼎堂与宇宙风》,一述他给《宇宙风》写稿的经过,拟刊出以明事实。语堂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记得是《我要看月亮》,是讽刺左派的禁谈风月的。不久鼎堂回信来了,措辞并不如那篇序文的杀气腾腾,而只责语堂文中常多“左派左派”字样,后来似乎是语堂回他一信,告以所以“左派左派”者,是“左派”先太欺人了,别人可噤若寒蝉,我林语堂做不到云云。接着是鼎堂又来一长信,痛言国事之亟,大家不应再作意气之争。这封信是教我转的,当时读了很为感动,字迹和信纸样子也历历如在目前。只是此信今日我处固然不见,即语堂赴美前托我保存的“有不为斋书简”中亦无其踪影,假如尚在人间的话,真是后人写中国文坛史的绝好资料,同时也可见鼎堂为人之如何可敬可爱。
根据该段文字可以知道,郭沫若的《论“幽默”——序天虚〈铁轮〉》(以下简写为《论“幽默”》)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0期(1936年2月4日)发表后,“为之大怒”的林语堂、陶亢德与郭沫若的通信情况为:陶亢德“写信询鼎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久鼎堂回信来了,措辞并不如那篇序文的杀气腾腾”—“语堂回他一信,告以所以‘左派左派’者,是‘左派’先太欺人了,别人可噤若寒蝉,我林语堂做不到云云”—“接着是鼎堂又来一长信,痛言国事之亟,大家不应再作意气之争”。很明显,前三函迄今未见。根据内容可以断定,第四函当为本文考证写作时间的第二函。由此可知该函收信人当为“陶亢德并转林语堂”。而第二函的写作时间当为1936年3月8日左右,而不是2月20日左右,因为在写作该函之前,郭沫若不但与陶亢德有过一次信函往来,并且还未收到林语堂的来函(郭沫若始终未收到该函,详见第三函考证)。对于引文中的“只是此信今日我处固然不见,即语堂赴美前托我保存的‘有不为斋书简’中亦无其踪影”,笔者做出如下推测:该函1939年拿出来在3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复刊第2期发表后,可能连同另外四函一起遗失了。
第三函
今天接到你的信使我打破了一个闷胡卢,我还以为是你们有意和我决绝,故不回我的信,原来你是写了回信而在望我的回信吗?你的回信我却至今没有收到,大约是在前月尾上这儿发生事变的时候有了浮沉吧。你的意见是怎样的,我自无从知道了。目前你们的经济如难周转,前次汇来的稿费,自当如命奉还。别纸请持往内山书店索取吧。将来你们如需要我的助力时我是随时可以帮忙的。再者,我的原稿(使用了的)如蒙保存,请便寄还,因我手中未留副稿。专复即颂
著安。
郭沫若
该函内容很明显与本文考证写作时间的第二函没有直接关系,在笔者看来,该函与陶亢德的以下回忆文字有关:
上面所引知堂信中的云云,就正指鼎语二堂相争的一回事,他之所以劝架,是由于我在去信询鼎堂以究竟,同时写了一信给他,一面告诉这回事,一面询鼎堂究是何等样人,因为此时不久以前,知堂恰去日本一行,我在报纸或刊物上见到二堂相见晤谈的消息,想想彼二堂既可畅谈甚洽,何以这二堂就水火如此,所以想问个究竟。回信就如上引。语堂的《我要看月亮》和我们的《鼎堂与宇宙风》二文之暂不发表,就为了知堂的一言。及到后来鼎堂痛论彼此互讦之非,这两篇东西就自然扯去丢之字篓。他也继续为我们撰稿,长篇《北伐途次》中文稿,就在《宇宙风》上登完的。
知堂周作人的信件写于1936年2月27日,内云:
赐信均收到。鼎堂相见大可谈,唯下笔时便难免稍过,当作个人癖性看,亦可不必太计较,故鄙人私见以为互讦恐不合宜,虑多为小人们所窃笑也。偏见未必有当,聊表芹献耳。
据陶亢德的回忆可以知道,见周作人函后,“语堂的《我要看月亮》和我们的《鼎堂与宇宙风》二文之暂不发表,就为了知堂的一言”,意味着林、陶二人决定不与郭沫若“互讦”。郭沫若在《论“幽默”》中对幽默小品文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在开篇如此写道:“天虚这部《铁轮》,对于目前在上海市场上泛滥着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默小品’,是一个烧荑弹式的抗议。”8编者在发表该文时还在附记中如此写道:“郭先生久居国外,对于国内文坛的情形,不大明了。譬如林语堂先生主编的《宇宙风》,开初原是继承了《论语》和《人间世》,发扬‘幽默’和‘闲适’精神的刊物,对于进步倾向的攻击和诬蔑,却比《论语》《人间世》更为激烈,但是他们为了某种原因,也还是去拉郭先生的稿子。郭先生因为不知《宇宙风》的作风如何,答应投稿,因此《宇宙风》上就有起‘鼎堂’的连载的自传来。这一件事,曾经引起了许多青年的误会,以为郭先生本是前进的领导者,为什么竟跟反前进的‘幽默’‘闲适’派合作起来了?”加上郭沫若由于没有收到林的来函而一直没有回函,林、陶二人应该认为郭沫若不会再给《宇宙风》投稿,找个周转困难的理由要回预支的稿费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郭沫若在回函中如此写道:“目前你们的经济如难周转,前次汇来的稿费,自当如命奉还。”根据以下文字可以推断,该函是写给林语堂的:“今天接到你的信使我打破了一个闷胡卢,我还以为是你们有意和我决绝,故不回我的信,原来你是写了回信而在望我的回信吗?你的回信我却至今没有收到,大约是在前月尾上这儿发生事变的时候有了浮沉吧。你的意见是怎样的,我自无从知道了。”理由为:“大约是在前月尾上这儿发生事变的时候有了浮沉。”此处的回信当为回忆中林语堂“左派左派”一信。
由此可以断定,郭沫若该函是看见林语堂索要预支稿费函后写作的,而林语堂致函索要稿费则是看见周作人函后的事情。现在来推测一下该函的写作时间。由于周作人1936年的书信、日记未出版,我们只能根据鲁迅1936年1、2月的书信、日记来考查当时北京至上海通信需要多少时间:1月5日:“一月一日信收到”,“下午得靖华信,即复”;1月21日:“十四日信已到”;1月22日:“复靖华信并寄小说三包”;2月1日:“一月二十七日来信,昨已收到”,“午后寄母亲信”;2月1日:“一月廿八信并汇款,昨日收到”,“复靖华信并寄书一包”;2月10日:“四日信收到”,“得靖华信,即复”;2月29日:“二十五日信收到”,“得靖华信,即复”。9由此可知,这六函的投递时间分别为:5、8、5、4、7、5天,意味着当时北京至上海通信时间一般为5天。鲁迅曾在致许广平函中如此写道:“二十一日午后发了一封信,晚上便收到十七日来信,今天上午又收到十八日来信,每信五天,好像交通十分准确似的。”10由此可知,当时北京至上海通信所需时间一般确为5天。周作人致函时间是2月27日,陶亢德收到时间当为3月3日左右。根据回忆可以知道,陶亢德得信后与林语堂商量的结果是:“语堂的《我要看月亮》和我们的《鼎堂与宇宙风》二文之暂不发表。”第三函是写给林语堂的,由此可以推断林、陶二人商量的另一结果是由林语堂致函郭沫若:告知郭沫若,林语堂曾致函给他却未收到复函,并请郭沫若将之前收到的稿费退还。理论上算来,郭沫若3月8日左右能够收到来函,急于收到来函的他得函后会当天复函。但是,不但陶、周通信时间有可能延期,林、陶二人商量也需要时间,考虑到误差,可将该函的写作时间认定为1936年3月上中旬。
第四函
信接到。目前国难迫紧,文学家间的个人的及党派的沟渠,应该及早化除。我在贵志投稿,你们当在洞悉中,我是冒着不韪而干的。我的目的也就在想化除双方的成见,免得外人和后人笑话。近时的空气似乎好了很多,个中还有相当的酝酿,但请你们在这时也务要从大局着想。能够坦白地化除畛域,是于时局最有裨补的。比如发表我给××信,××加些按语来表白自己的抱负和苦衷等等(有忠告也是好的),是极好的办法。我对于你们是开诚布公的,请你也不要把我当成外人看待,我们大家如兄如弟地携起手来,同为文字报国的事,我看是最为趁心之举。只要你们能够谅解我这番意思,我始终是要帮着你们的,以后还想大大地尽力。这层意思请你同××过细商量一下吧。关于日本的文字前几天用给你的信札的形式写了两张,但总因忙也没写下去,我现在寄给你,你看可以补空白时,便割去补补吧。关于日本,现在很难说话,我预备坐它几年的牢。草此专颂
撰安。
郭沫若
该函简单地告诉收信人“信接到”后,立即转入“目前国难迫紧,文学家间的个人的及党派的沟渠,应该及早化除”,可以断定它与第二函有关:郭沫若在第二函中呼吁“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陶亢德、林语堂接读该信后“很为感动”,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复函是当然的,郭沫若立即写作该函也是当然的。现在就来考证该函的写作时间:前面已经考证出呼吁“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之函写作于3月8日左右,正常情况下,陶亢德们收到并复函的时间当为3月14日左右,郭沫若收到并回函的时间当为3月20日左右。考虑到误差,将该信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936年3月下旬。引文中的“××”应为语堂,所以,该信的收信人当为陶亢德。
第五函
发表费百圆早接到。
《海外十年》几次提笔想续写,但打断了的兴会一时总不容易续起来。我现在率性把一部旧稿寄给你们,请你们发表。我费了几天工夫清理了一下,删除了好些蛇足,在目前发表似乎是没有妨碍的。你们请看一遍再斟酌吧,如以为有些可删,请于不损害文体的范围内酌量删除,或用××偃伏。如以为不好发表,阅后请寄还我。
如可发表时,发表费能一次寄给我最好,因为我在右胸侧生了一个碗大的痈,已决心进医院去割治。如一次寄不足,能先寄两百元来也好。
郭沫若
考证该函的写作时间有两条线索:一、“我现在率性把一部旧稿寄给你们,请你们发表。我费了几天工夫清理了一下,删除了好些蛇足,在目前发表似乎是没有妨碍的”;二、“我在右胸侧生了一个碗大的痈,已决心进医院去割治”。
关于这部“旧稿”的情况,《宇宙风》第19期(1936年6月16日)的《编辑后记》有如此介绍:“郭沫若先生的《海外十年》停刊之后,读者深以为憾。现在我们请郭先生另惠他稿,蒙其俯允,稿已全部寄来,从下期起按期发表,题为——《北伐途次》。”第20期(1936年7月1日)发表的《北伐途次》开头有郭沫若写作的跋语,其落款为“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作者识”。结合信中的“我费了几天工夫清理了一下”可以知道,该函极有可能是在郭沫若写完该跋语后接着写的,也就是说,写作于1936年6月1日。
关于右胸生痈的情况,郭沫若1936年6月2日写作的《痈》有详细介绍。该文落款为:“1936年6月2日负痈抄。”11结合郭沫若为《北伐途次》写作跋语的时间是1936年6月1日、写作《痈》的时间是6月2日,可以进一步断定,该函是为《北伐途次》写作完跋语后接着写的,即写于1936年6月1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宇宙风》乙刊第2期发表的郭沫若致《宇宙风》五函的来龙去脉梳理如下:1935年8月6日左右,陶亢德致函郭沫若请为《宇宙风》写稿(该函迄今未见);郭沫若于8月12日左右复函同意写作并提出条件(第一函);8月18日左右陶亢德在复函中由郭沫若自己决定写什么并“汇去了一百元国币作预支稿费”(该函迄今未见);8月24日郭沫若致函《宇宙风》编辑部谈收到稿费事和自己“决计写《海外十年》”。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半月刊创刊,郭沫若在上面发表了《海外十年》之一《初出夔门》,在第3—6期连载了《海外十年》之二至五的《幻灭的北征》《北京城头的月》《世间最难得者》《乐园外的苹果》。1936年2月4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0期发表了郭沫若的《论“幽默”》,林语堂、陶亢德看见后“为之大怒”,陶亢德立即写信询问“鼎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该函迄今未见);“不久鼎堂回信来了,措辞并不如那篇序文的杀气腾腾,而只责语堂文中常多‘左派左派’字样”(该函迄今未见);“语堂回他一信,告以所以‘左派左派’者,是‘左派’先太欺人了,别人可噤若寒蝉,我林语堂做不到”,遗憾的是,该函“在前月尾上这儿发生事变的时候有了浮沉”;陶亢德在致函郭沫若同时,致函周作人询问郭沫若“究是何等样人”(该函迄今未见),周作人1936年2月27日左右回函告知,于3月3日左右得到该函后,考虑到林语堂致郭沫若函已有一段时间却未收到回函,以为郭沫若不再为《宇宙风》投稿,林、陶二人听从周作人劝告,“语堂的《我要看月亮》和我们的《鼎堂与宇宙风》二文之暂不发表”,同时致函郭沫若:告知郭沫若,林语堂曾致函却未收到回函,并请郭沫若将之前汇去的稿费退还(该函迄今未见);郭沫若接读该函后,知道林语堂的来函遗失了并在复函中同意将稿费“如命奉还”(第三函)。由于1936年3月16日《宇宙风》第13期要出版春季特大号,曾经“为之大怒”的陶亢德在致函郭沫若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于2月12日致函郭沫若请写作《日本之春》(该函迄今未见);郭沫若收到该函后并未立即回复,却在半个多月后的3月上旬致函陶亢德并转林语堂:“《日本之春》不能写,但《海外十年》是可以续写的,大约在贵志十四期上便可重与读者见面”,同时呼吁“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第二函);陶亢德、林语堂接读该函后“很为感动”,于三月中旬回函同意郭沫若意见(该函迄今未见);郭沫若收到回函后于3月下旬回函,简单告诉“信接到”后再次呼呼“目前国难迫紧,文学家间的个人的及党派的沟渠,应该及早化除”,并解释自己为《宇宙风》投稿的目的是“想化除双方的成见,免得外人和后人笑话”(第四函)。1936年6月1日,郭沫若致函告知:“《海外十年》几次提笔想续写,但打断了的兴会一时总不容易续起来。我现在率性把一部旧稿寄给你们,请你们发表。”(第五函)根据以上梳理可以知道,写于1935年8月中旬的第一函应该是写给陶亢德的,写于1936年3月上旬的第二函应该是写给陶亢德并转林语堂的,写于1936年3月上中旬的第三函应该是写给林语堂的,写于1936年3月下旬的第四函应该是写给陶亢德的,写于1936年6月1日的第五函没有材料说明到底写给谁。由此可知,这五函在收入《郭沫若书信集》时将收信人全部归入陶亢德名下欠妥。稳妥的做法是:全部归入《宇宙风》编辑部名下,若有必要,可在题注中标明第一至四函可能是写给谁的。
通过梳理需要考证写作时间的五函的来龙去脉,很自然地会发生以下疑问:一、郭沫若在《宇宙风》发表《海外十年》1—5后为什么不再供稿,并且在1936年2月4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0期发表《论“幽默”》严厉批评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小品文;二、郭沫若接到陶亢德2月12日请其写作《日本之春》的来函后,为什么不立即复函,半个多月后复函时,为什么呼吁“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接读陶亢德看了该函的回函后,郭沫若为什么再次呼吁“目前国难迫紧,文学家间的个人的及党派的沟渠,应该及早化除”?第一个问题笔者已在《郭沫若的〈论“幽默”〉与幽默小品文论争》12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此略,现在只谈谈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
二 日本“二二六”事件后的郭沫若
查《郭沫若年谱长编》,郭沫若收到陶亢德1936年2月12日来函后的一段时间里,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回函:翻译的“一部大东西”《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已于2月15日“译迄,并作《前言》”,2月28日、3月4日还各创作了一篇历史小说:《楚霸王自杀》《中国的勇士》。13实际情况则是:郭沫若收到来函后半个多月才回函,并且在回函中大谈“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执文笔的人”应该怎么办。对此,笔者曾经结合这两篇历史小说的内容,认为郭沫若于1936年3月上旬回函并在信中如此呼吁与日本的“‘二二六’政变有关”14。现在具体谈谈日本“二二六”事件后的郭沫若。
首先看看郭沫若在自己作品中对日本“二二六”事件的论述。据查,除《五十简谱》记录了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后自己“受日本宪兵审询”15、《洪波曲》回忆了国内曾经出现的西园寺跑到自己寓所里“避过难”的谣言16外,郭沫若还在《忠告日本政治家》(1937年9月9日《救亡日报》)、《抗战以来日寇的损失》(1938年6月23、24日《新华日报》)、《日本在崩溃途中》(1939年1月8日重庆《商务日报》)等文章中论述了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在其中一篇文章中,郭沫若是这样概括论述的:“日本的稍微有些理智的人,本来早就知道少壮军部的狂暴,是要危害他们自己本国的。满洲事变以来,他们用尽苦心地在想方法来约束少壮军部,使他们能够适可而止;但是,这苦心是失败了,经过了‘五一五’和‘二二六’的内乱,一直达到了目前,日本的老成派,明白地是已经失掉了他们的掌舵的力量,而只好一任少壮军部去横冲直撞,把国家的存亡来做赌博了。那些老成派觉悟了国家已经没有出路,只可断念下去,让少壮军部去拼个死活,拼得好,是侥幸,拼得不好是活该,这便是日本的老成派的心理,也就是精神丧失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是精神虚脱症。”17
再来看看当时也在日本的左联成员陈乃昌的回忆:
《文物》还未出版,“二二六”事变发生。东京的宪兵部竟亦“问道”于先生。是清早,一位高级官儿正装登门请驾,像下贱臣僚那么鞠躬有礼,又像是“礼多必诈”。到了宪兵部便请坐,奉茶;登堂却高坐一位头目,旁站立一个差遣,桌面还安放木棍一根,情景有点是款待上宾,更像是坐寨审票。问过“什么朋友往来”?又问过“对于事变的观感”?先生一如往常的朴质平易,而义正词严,则凛不可犯,“朋友往来的一切责任都在我,有事问我,不能麻烦我的朋友”;“事变是表现日本民族的勇敢精神,我佩服你们的勇敢,但又是政治失其常轨的暴乱,上轨的政治,不容有此暴乱。除果必须去因,遵循轨道,自应先去其故障,有如流水,平明无波,然遇阻则激起飞浪,势不可免者”。暴寇狼心,如此这般,前后四小时之久,终不能犯先生之尊。礼之来,仍礼之去。先生之骨气及其机智,保护他在日本平安的度过十年。18
该段回忆让我们知道了郭沫若在《五十简谱》所写的“受日本宪兵审询”19的具体情况。尽管引文中的郭沫若“凛不可犯”,他非常反感这种“审询”则是可以想见的。在《忠告日本政治家》中,郭沫若回忆了他当时听见播音员“那战栗而又亢扬的声音”后的感受:“‘二二六’之变,在当时,我是住在日本的,日本军部把东京播音局占领起来,用兵士提着枪逼着播音局员报告军部所发出的消息。播音员的那战栗而又亢扬的声音,听起来真令人可怜。”20根据陈乃昌和郭沫若的以上回忆可以知道,日本“二二六”事件直接影响到了郭沫若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陈乃昌的回忆还可以知道,郭沫若对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未来的可能发展是了解的。关于人们对此次叛乱意义的了解情况,有美国学者曾如此写道:“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那次叛乱不外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大屠杀,而了解其意义的人屈指可数。但苏联人却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左尔格21,他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将导致向中国扩张。”22笔者曾经根据郭沫若这段时间创作的《楚霸王自杀》(2月28日)、《齐勇士比武》(3月4日)、《司马迁发愤》(4月26日)、《贾长沙痛哭》(5月3日)4篇历史小说认为:“郭沫若是了解这次叛乱意义的‘屈指可数’的人之一。”23此可证诸陈乃昌的回忆:“他对我说,关东军现在成为日本军部队的主体,通过‘六二六’事件后,现正策划加紧侵略华北,军事行动可能会加强。”24
对郭沫若创作于1936年的历史小说,人们有如此评价:《楚霸王自杀》“通过乌江亭长对项王的功过得失作出评价,点明小说主题用意在于成败兴亡系于民心这个道理”;《齐勇士比武》通过齐国两名勇士不顾国家安危,一味争强斗狠,最后两败俱伤的故事,“抨击蒋介石等国民党军阀,怯于外敌,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勇于内战”;《司马迁发愤》“借主人公的高洁志行反遭屈辱缧绁之苦来抒发作者内心的愤懑”;《贾长沙痛哭》“可以说是作者借贾谊而发的抗日请缨檄文,此篇小说可看作是作者的‘国防文学’,和献给当局的一篇‘治安策’”。25在笔者看来,郭沫若在这个时候以如此快的速度创作历史小说,其目的是“借历史小说以提醒国人,并用以明志”26。
除“借历史小说以提醒国人,并用以明志”外,郭沫若还在其他文章中呼吁团结。1936年3月21日,郭沫若为周而复的《夜行集》写作序言,内云:“古人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样话究竟是已经过去了的话。我们今日的格言却似乎是:‘外侮翻过墙,内屠其弟兄’,尽你说得舌弊唇焦,尽你怒骂,尽你嘲笑,大刀依然不是坦克车的对手。你敢哭丧着一个面孔吗?邻国不是多么‘亲善’?民族不是正在‘复兴’?滚蛋,你们应该充分地来个‘反省’!旧时的人尊重礼让,尼采打了个价值的倒逆,说礼让是奴隶的道德。现在的中国人又来了一个倒逆的倒逆。在这儿秦桧是岳飞,岳飞是秦桧,文天祥是张洪范,张洪范是史可法。”27
现在回过头来看本文考证的五函,对其中三函的一些内容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郭沫若在第二、四函中呼吁团结的原因为: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后,郭沫若也“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将导致向中国扩张”,所以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写信向林、陶二人呼吁团结御侮,致使幽默小品文论争没有再次发生;第三函“你的回信我却至今没有收到,大约是在前月尾上这儿发生事变的时候有了浮沉吧”的意思为:林语堂的回信于1936年2月底寄到东京时,由于正值“二二六”事件,所以遗失了。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间是1936年2月26—29日,郭沫若为什么直到3月8日左右才致函陶亢德并转林语堂呼吁团结御侮?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日本“二二六”事件尚未结束,郭沫若就于2月28日写作了《楚霸王自杀》,3月4日又写作了《中国的勇士》,他“借历史小说以提醒国人”需要时间;二、他致函陶亢德后一直在等待复函28,由于该函“在前月尾上这儿发生事变的时候有了浮沉”,所以暂未致函,应该是在预计中的复函过了十天左右还未收到的情况下,郭沫若才写作了该函,这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写作该函的急迫心情。
注释:
1 沈学善编:《二十世纪国际问题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2 《宇宙风》乙刊第1期(1939年3月1日)发表了鲁迅的书简,题为《作家书简(一)》。
3 13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9~614、593~599页。
4 陶亢德:《知堂与鼎堂》,《古今》第20—21期合刊,1943年4月16日。
5 郭沫若:《致陶亢德(六函)》,《郭沫若书信集·上》,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在《致陶亢德》(《郭沫若佚文集》上册,王锦厚、伍加仑、肖斌如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中,认定该函写作年份为1933年,有误。
6 王锦厚:《郭沫若和这几个“文学大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7 郭沫若:《致叶灵凤(1933年4月3日)》,《郭沫若书信集·上》,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
8 郭沫若:《论“幽默”——序天虚〈铁轮〉》,《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0期,1936年2月4日。
9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593页。
10 《290522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11 郭沫若:《其他·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
12 廖久明:《郭沫若的〈论“幽默”〉与幽默小品文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
14 23 廖久明:《“便是阋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的”——略谈郭沫若1936年的三件事》,《郭沫若学刊》2005年第4期。
15 19 郭沫若:《五十简谱》,《郭沫若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549页。
16 郭沫若:《洪波曲》,《郭沫若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17 郭沫若:《抗战以来日寇的损失》,《新华日报》1938年6月24日。
18 陈乃昌:《沫若先生印象断片——为先生五十诞辰而作》,《新蜀报》1941年11月16日。
20 郭沫若:《忠告日本政治家》,《郭沫若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21 左尔格,《法兰克福报》非正式记者,德国驻日使馆武官秘书,苏联红军远东间谍网负责人。
22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4 杨凡:《与郭沫若在日本的交往》,《革命史资料》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据查,日本没有发生“六二六事件”,结合上段所写的时间“1935年冬”可以知道,引文中的“六二六”当作“二二六”。
25 秦川:《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7页。
26 廖久明:《也谈“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9期。
27 郭沫若:《序》,见周而复《夜行集》,上海文学丛报社1936年版。
28 即《知堂与鼎堂》中的以下两函:“不久鼎堂回信来了,措辞并不如那篇序文的杀气腾腾,而只责语堂文中常多‘左派左派’字样,后来似乎是语堂回他一信,告以所以‘左派左派’者,是‘左派’先太欺人了,别人可噤若寒蝉,我林语堂做不到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