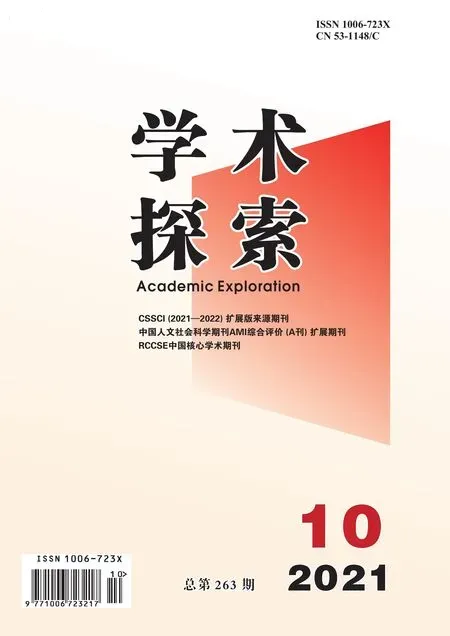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礼俗观念探析
——以民国报刊为中心
黎春晓,彭孝军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贵州大学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礼”在中国古代既是精神信仰,又是道德行为规范,既是一种文化形态,又是一整套政治与社会制度,经过历代统治者与知识精英不断重构和阐释,传统礼教越发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内核。“俗”则是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习惯风俗,其本身易受时代风潮影响,含有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知识精英往往通过以礼化俗,将正统文化理念自上而下地向社会普及,促使民众日常生活理性化,这既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以礼经世精神的体现,也是每逢社会失序、道德沦丧之际的普遍文化现象。清末民初,王纲解纽,专制和宗法制度受到抨击,旧有的“三纲五常”道德准则难以为继,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尚未陶成,面对内忧外患、欧风美雨,如何对古礼进行理性分析和取舍,以新礼化旧俗,重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是重整社会秩序、淳化风俗的当务之急,也是摆在民初知识分子面前的又一个时代课题。
前人有关民初礼俗观念的研究,从“大传统”入手者,以探讨民初国家礼制建设或梳理近代礼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为主。民初国家礼制兴革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譬如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鼓吹尊孔崇儒),并非以改良古礼、以礼化俗为最终目标,学术精英的礼学研究又过于专精,很少与改良社会礼俗的现实问题接轨;从“小传统”入手者,主要侧重研究婚丧嫁娶等社会礼俗的时代变革,对礼俗变革背后知识分子的导向作用则少有论述,对知识分子礼学思想与社会礼俗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更是乏善可陈。
事实上,大小传统之间、知识精英与大众生活之间以及“礼”与“俗”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叙述模式或聚焦于新文化运动,勾勒出一幅新知识分子抨击传统礼教的知识图景,或着墨于东西文化论战,着重凸显激进派与保守派在“西化”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二者皆以救亡图存为时代背景展开论述,并非客观探讨传统礼教的本质及古礼的近代转化问题。而在民初报刊业方兴未艾之际,曾有一批知识分子利用这一媒介平台,倡言他们的礼俗观,不仅进行纯粹的理论探讨,还试图借助报刊的宣传力量,实现以礼经世的人文关怀,然而,这一股时代思潮却被经典叙事模式的光芒所掩盖,本文将通过对民国报刊资料的考察,还原其历史轨迹。
二、对古礼本质的论辩与争鸣
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打倒孔家店”的代表性人物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1](P5)疾呼“仁义道德均将吃人”,吴虞次年撰文《吃人与礼教》[2](P6)响应之,抨击传统礼教。与此态度截然相反,梁漱溟则在同时期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一书中,论证礼乐传统可为东方文化之大用,甚至认为礼乐文明将来可以替代法律与宗教,东方文化可以引领世界文化潮流。民初知识精英对古礼的评判虽然如此轩轾分明,却都受到了时代风潮的巨大影响,国家内忧外患的加剧和西方思想文化东传,使民初学人很难以单纯的学术视角评判传统文化的优劣得失。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抨击传统礼教的真正目的,在于摧毁腐朽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思想体系。文化民族主义者则受内患外侮的刺激,极力鼓吹、抬高国学的“普世价值”,意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二者皆非理性探讨古礼的近代转化问题。然而当时仍有一批知识分子能够抛开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情感因素,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致力于辨明古礼本质,并视其为转变礼俗观念的第一要务,盛极一时的各类报刊则为这一论辩争鸣提供了宝贵的互动交流平台。
(一)是吃人的礼教还是东方瑰宝?
1922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撰写的文章《礼是什么?》,该文对激进与保守的古礼观均不赞同,认为“我们现在想明白礼教对于社会的利弊,预先需要知道礼的本质是什么……给礼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察考我们所下的定义与古人所说的礼合不合。”对于新文化运动者所宣扬的礼教吃人论,作者试图“就礼的本质体察其利弊,视其果能吃人否?如其果能吃人,此吃人果在何时?吾侪之所谓吃人端底有何意义?”而对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对礼乐文明的过分推崇,作者则试图探明“礼乐果能代法律和宗教与否?”[4](P126)
徐氏认为,“礼就是附于社会理想的行为的轨则”,[4](P129)这里所谓的“社会理想”指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伦理道德观念,他是可变的而非永久的,“礼”则是这一抽象伦理道德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变革旧礼教成为打破旧有伦理道德体系的关键。民主共和理想既然已经取代君主专制与宗法制,一些古礼就注定要从神圣的纲常礼法变为不合时宜的陋习,理当废除,在这一点上,作者并不以新文化运动者为非。
但关于礼教吃人论,徐氏则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文中将人分为三等,分别为只知饮食男女之事的机体人,囿于纲常伦理、名誉的社会人,以及为实现理想可作出牺牲奉献的理想人。由于礼是附属于意识形态的行为规范,因此他不仅能够提升机体人的人格,而且与社会人的品行相得益彰,但也因此成为理想人取得思想突破与进步的障碍。由于社会理想较为抽象,因此,打破旧有伦理道德体系必然要从攻击传统礼教做起,“到社会理想变化的时候,最受诟病的还不是理想的本身,却是附属于他的礼教……而抵制力最大的也莫若礼制。”因此,新文化运动者欲摧毁旧制度便先要拿礼教开刀,旧势力反对新思潮,也需用礼教来吃人,新旧势力在不断角力过程中,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作者不禁感慨:“今天理想革变,耗费维新志士无限的心血,把旧礼教推倒,明天新理想成立,新礼制又跟着成立,又要来吃后天革新的志士,社会演变的历史总是如此,也真是无可如何。”[4](P134)言下之意,“礼教吃人”不过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守旧势力面对新观念都会采取的抵抗措施,需看清古礼的保守性、落后性,但大可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为文化革命之目的而将其妖魔化。
对于梁漱溟认为未来礼乐文明可以替代法律、宗教的论断,作者反驳到:“礼教就是社会的制裁,膨胀社会的制裁,减少法律的制裁,本是儒家很好的思想,但是如梁先生所言之以礼教代法律却万不可能,因为梁先生既不能证明将来无直接危害社会组织的人,就不能以礼乐代法律。”换言之,礼教毕竟属于道德规训范畴,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力和惩罚机制,因此无法替代法律的作用。而“宗教、名教为体,礼乐为用,无论何种宗教、名教,全有礼乐,礼不过是一种的轨则,乐不过是一种怡人性情的美术品,他们怎么能够替代宗教呢?”[4](P135)作者强调礼只是一种规范,不可与宗教、名教相比论,可谓抓住了古礼的本质,褪去了礼教的神圣光环。
徐氏最后表明了对传统礼教的态度,认为礼教既然只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行为准则,那么不合时宜的古礼当然要全力革除,但礼只是纲常伦理的工具性载体,大可不必对他进行不必要的攻击,而是要把目光聚焦于伦理道德观念本身的革新上,“一方面要知道礼是一种工具,并且是一种容易骗人的工具。社会真正的进步不系于轨则的整齐,而系于向道德上的努力,我们应当向道德本身竭力前进,进以利用此工具,万不可偏重工具而忽略努力。”这里作者将社会道德与礼看作体用关系,作为工具的礼自当因时而变,而礼之精意——社会道德更需要与时俱进,成为革新的主题。此外,作者申明对学术界有关礼的探讨持开放态度,但强调无论对古礼或褒或贬,务必首先廓清对其本质的定义问题。[4](P135~136)
(二)理想化的“礼”与现实存在的“礼”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论礼各执己见,多有论辩,且常与个人道德修养问题紧密相连。秦汉以降,随着儒学的日益官方化,制度化的礼也逐渐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宋明理学兴起后,礼仪制度最终演变为“三纲五常”的行动指南,日益僵化。民初学人指出,后世歌颂礼乐文明者多是强调先秦时期理想化的礼,而非秦汉以降现实社会中意识形态化的礼,民俗学界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与江绍原就曾针对这一问题在报刊上展开对话。1924年,周作人在《雨丝》报撰文《生活之艺术》说道:“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5]周氏认为,礼本是对个人情操陶铸的过程,堪称生活的艺术,而所谓的礼仪、礼教不过是后人将礼改造成的行为规范,是为宗法专制社会的纲常伦理服务的,是堕落的礼。
对于这一说法,江绍原于该报撰文回应道:“先生讲中国固有的‘礼’的一段话,我却以为太把‘礼’理想化了。这‘本来的礼’……不知道先生倒推到怎样古的时代。”江氏认为,周氏只是为了攻击宋代以来的道学家,才搬出一个“本来的礼”“生活艺术的礼”,而古代社会未见得在全社会实践过这种理想的礼。若进一步推究古礼本源,则世界各地原始民族皆有礼乐,但更多展现的都是人类学意义上未开化文明的宗教、仪式、艺术等文化元素,并不先进,更不必推崇,中国古礼亦不例外。他最后讲道:“只怕无论怎样古的礼,若不用我们的科学、智识、道德标准和艺术与兴趣,好好的提炼一番,改造一番,决不能合我们今人的用。”[6]言下之意,不必将古礼神圣化,真正符合生活艺术、理想化的礼并不存在于遥远的古代,还需今人参酌古今,自行制定。
周作人再次回应江绍原时,也承认太把礼理想化了:“我所谓‘本来的礼’,实在只是我空想中以为应当如此的礼,至于曾通行于什么时代,我不能确切回答,大约不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也说不定。总之,我觉得千年以内是不曾有的,却也不能说千年以前一定有过。我同你一样,相信今日的生活法非由我们今人自己制定不能适用。”[7]
(三)附属于宗法社会的“礼”
中国古代狭义的宗法制度已随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的衰亡而解体,然而宗法制的内蕴,如冠婚丧祭、尊卑等差、男女有别等礼节,却渗透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深巨。可以说,绵延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仍旧是一个宗法社会。上文讲到,自秦汉以后,礼被渐次改造为“封建”纲常伦理的行为准则,为维护皇权专制与宗法社会服务。民初学人意识到,欲探究古礼本质,必须将其放置于宗法社会背景下进行解读。
1926年,毕业于北大法科,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民国学人陶希圣,在《新女性》杂志上发表题为《礼与宗法》的文章,陶氏认为,礼与宗法“相依为命”,“礼是宗法社会的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宗的系统只管亡废,宗法的实质如还未灭,则宗法社会的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礼,是应当存在乃至发挥的,如果说宗法应当改革,不应恢复,同时说礼教当振兴,那就矛盾了。”[8](P426)言下之意,传统礼教并非神圣不可动摇,他只是宗法社会的附庸,是存是废,要依宗法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存亡而定。
陶氏继而阐明,道德律与礼并非同义语,道德不过是礼的一部分,“礼仍以制裁人的外部行为为主旨……道德自内外铄,礼乃自外内籀,故礼重行为——节文,与道德重内心者异趣也。”[8](P432)如古礼中男尊女卑、亲权至上等准则就并非“自然法”,而只是附和于宗法社会的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不具有“普世价值”。不可否认,古礼中还蕴含着仁义、敬让、无我牺牲等精神,但“无奈礼的主要作用不在乎道德律,而在其‘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8](P431)近似于一种身份制,而时代的演进,已由这种身份制进化为契约制,故强调身份等级差别的古礼应与宗法社会一样,不宜恢复,对于社会道德重建仍有裨益的古礼则当留存。以上陶氏对礼与道德之差异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但宗法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是否能在短时间内裁汰?如若不能,古礼又当何去何从?作者对这一问题并未展开深入探讨。
由本节叙述可见,民初学人以各类报刊为交流平台,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理想与现实之礼以及礼与宗法社会的关系,对古礼本质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和论辩。虽然受时代与知识结构所限,他们对古礼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但相较于新文化运动激进分子和传统文化卫道士,他们对古礼本质的解读与认知显然要更为科学、客观、中肯。
三、对古礼局限性与社会价值的评判
上文依据报刊文章勾勒出民初知识分子对古礼本质进行探讨与对话的思想轨迹,下面将围绕他们对古礼的局限性与社会价值的评判展开论述,包括古礼本身所蕴含的局限性与“普世价值”,以及在民初社会时代背景下,古礼中可资借鉴与不合时宜之处。
(一)古礼的局限性
民初知识分子对古礼局限性的认识,一方面在于西学知识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来自国门打开后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对比。时任民国国会议员、北大教授的知识分子潘力山,在乘船赴美途中见同船西人旅客举止行为彬彬有礼,“人人有士君子之度”,顿感自愧不如,反思古礼优劣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礼”状况,作《论礼》一文,登载于学术刊物《学艺》杂志上。文中讲道,古礼的一大弊端在于“不下庶人”,这导致“中国一般社会几乎无礼”,因此难以达到以礼化俗的目的。放眼当时社会,无论贵贱,更是鲜有真正践行古礼者,“新礼未立,旧礼亦无有行之者,偶有行者,其形式非其实质矣。主客相见,未尝有东向西向者,酒食宴集,未尝有宾主百拜者,其形式亦不具矣。”[9](P58)
古礼的另一个弊端在于徒有繁文缛节,不切实用。儒家在原典礼论基础上制定繁文缛节,遂成僵化定制,不能为社会所用,即使是官僚阶层,也只是徒有虚伪仪节,而不知礼之精意,不拘礼节反而成为通达超脱之人的标志。所谓“儒者之说又使人厌苦不堪,且相沿无改,亦不能应社会之需要,相与俳优视之而已。在官者但知仪注,不知礼意,相尚以伪,达者耻之,反以通脱为高。”[9](P58)
此外,作者认为,民初社会普遍不遵循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古礼本身不近人情、不合时宜所致。如三年之丧期间不着华服或可遵守,而不准食肉、不准夫妻同房则少有遵守者;结婚之日行冠礼者有之,而为冠者赐字则不再实行。盖“不华服、行冠礼,皆形式之事,行之无伤。不食肉、近内,则生理有所不许,不字则习俗不便称呼,皆实际之事,不能行也。”[9](P58)食色乃人之本性,且今俗又与古风不同,古礼的局限性正在于有违背自然人性与不合今俗之处。
(二)古礼的社会价值
上接潘力山所撰《论礼》一文,作者在陈述了古礼的局限性之后笔锋一转,他讲道:“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有社会即不能无礼。礼者,秩序之谓,秩序与社会相终始,万无废理,惟其条目随时地而有变迁,不必同耳。”认为礼能维护社会秩序,故不能废除,但需因时而变,变更条目而取其精华。作者将古礼中具有“普世价值”且可为今用者,分列为如下几条。
“一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即愚前说合乎人情之中,使无过不及之意……人情之合乎中者即天理……宋儒以天理在人情之外,非是。”人情无过无不及即为天理,而非宋儒所讲在天理之外,而欲使人情持中节则需要礼来调节,此即礼为天理节文之意。用礼来调节人欲,使之符合民初社会的价值观,而非以礼教压抑人性,此为古礼价值之一。
“二曰:礼者,卑己而尊人者也,卑己不是鄙卑,是谦虚之意,谦虚为人类相接必具之条件。”潘氏认为,谦虚敬让为古礼可取之精神,对于维护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大有裨益。这一点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也多有论及,学人朱文叔认为,礼的最精意就在于“辞让之心”,他与新时代“牺牲的精神”最相契合。他讲道:“人决不能脱离社会,独营个体生活……有时个人不能不牺牲一己的福利,以维持社会全体的安宁,如果没有牺牲的精神,大家不辞不让,逞个人的私欲,无所不为,那社会的秩序就要破坏,个人的生活也不能安全。照此看来,礼实是共同生活的纲维。”[10](P25)此处作者撷取了古礼中的敬让精神,扬弃了尊卑等级观念。
“三曰:礼者,体也,礼贵实质,不贵形式。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意思是应摒弃古礼中的繁文缛节,继承礼之精意。正如前文所述,古礼被民初学者所诟病的关键点就在于它徒有形式而无实质精神。如若古礼泥古不化、不近人情,不能因时而变,就只能流于虚伪。
“四曰:礼者,履也。礼贵实践,不贵口谈。宋以后之人多能讲礼,不能行礼,非其本也。”[9](P59)这里主张摒弃无用的理论玄谈,躬行实践礼之精神。礼本身就注重由身体力行来表达、陶冶内在精神修养,此论可谓抓住了古礼的原始精意。
总之,作者认为“凡事当究其本质,不当拘其形式”,古礼中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理当去除,对人性情陶冶之精神则要继承,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之。
(三)乱世中的礼治与法治
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礼法关系可以概括为援礼入法,以法护礼。时值近代,追求平等自由的西方法治观念东传,对于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民初社会,礼治与法治孰优孰劣的古老话题,再次成为论争的焦点。
经历了民初“共和幻象”破灭的失望,知识分子推崇西方民主与法制的热情有所消退,转而关注西方政治制度与本国国情是否匹配的问题。1927年,署名陈拔的学者在政论性期刊《甲寅周刊》上发表文章《论法与礼》,结合时事对礼治与法治的优劣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法治虽是大势所趋,然而当时中国处于乱世,不可一味任法,“必曰法乎,自必先有强民,而后有强议会,有强议会而后强政府,议会虚矣,政府弱矣,煌煌法典非其人不行。”[11](P12)民初社会专制君权已废,议会制尚不成熟,组织混乱,“武将”又多方作乱,因此法治难行。“夫人世之大患,争也,争出于欲,乱成于争……乱世乃并无法,非无法也,有法而势不行也,救乱宜莫如礼。”[11](P12)作者认为,乱起于争,欲止祸乱,必先消弭争夺,然而乱世并无强力政府执行法令,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欲消弭争夺,还需以礼遏制人之私欲。总之,从当时国情出发,礼治胜于法治。
那么传统礼治是否与平等自由的时代精神完全相抵牾呢?作者反对这一观点,其观点如下:
乃今世不明礼者,宜其并不知法,不知法者,宜其更不明礼。于是有越法以言平等,破礼而谈自由,若近年来所谓群众运动也者。……余尝谓世界人类史中最自由者,宜莫如中国以其师儒重仁知之也。最平等者,亦莫如中国以其尚义知之也。试思世有夺人自由而能为仁者乎?有不守平等而能由义者乎?平等、自由西儒之所倡牵也,我则尊而神之。仁义,我国之所传习也,乃不恤,毁而灭之。于是借端平等者,自行其不平等之实,信口自由者,反成其灭自由之甚。而真金不磨,仁义犹在人心。[11](P11)
作者认为,古代礼治社会所崇尚的“仁义”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平等自由之精神,大可不必毁弃传统而取法西方。军阀混战之际,不懂礼法真意者实际上是为了一己私欲,以民主自由为噱头,行不仁不义之勾当。
作者进一步论述礼治于当时社会何以可行:
夫人之生,孰不欲安欲乐?安乐者治之赐,而非乱之效也。故好乱者绝非其人之本图也,惟迷瞀于心志,斯斗暴而不宁,苟自返焉,亦知罪矣。由是而进,挈矩可以平好恶,忠恕所以尽仁智,忠恕挈矩,礼之准也……礼以定分,则一身、家、国、天下,所与往来酬酢,匪争克让,以各敬其所天禀,各严其所自力,而秩然井然,太和自具,尚安有乱乎?[11](P12)
人心本质爱好和平,故以礼淳化其心,才是拯救乱世之良法。而“矫矫时彦犹动欲以法治救国,礼则莫言之,虽言之亦莫能听也,虽听之亦莫能信也,第相笑而坐以为迂腐耳,孰知迂腐者在尊法。”[11](P12)
最后作者指出,有效取法“以辅礼治之不足犹可”,而一味“任法者,衰世之征也。”[11](P12)作者以礼为主以法辅之的见解是否得当暂且不论,文中强调于乱世之中一味依靠羸弱政府实行法治,对于弥合战乱,整顿社会秩序有害无益,应代之以礼治,凸显古礼仁义、敬让、忠恕等价值,以淳化人心,整顿社会秩序,其见解确有独到之处。
综上所述,民初知识分子在学术报刊文章中,将古礼的价值和局限性与当时社会状况相结合进行考量,进而筛选出古礼可继承之处,为实现古礼价值的近代转化提出了颇有创建的观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受时代所限,民初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知识和文化背景尚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对古礼价值与局限性的评判只能回到古代经典中去找根据、做论证,导致许多观点失之偏颇,不够有说服力。
四、抨击社会陋俗及以礼化俗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身处民族危亡之际的民初知识分子群体,再次被激发出传统士大夫的经世精神,他们并不满足于对古礼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在廓清理论问题的同时,他们还试图借助报刊媒介的宣传力量和教化功能实现以礼化俗的目标,即以新的礼仪规范对社会旧有礼俗加以变革和改造。这种“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俗互摄,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12](P1~8)
(一)戒奢从简,彰显礼俗精意
下文将以《申报》所载丧祭礼俗改革为例,探究民初知识分子以礼化俗的经世思想。《申报》在近代史上曾对开启民智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出版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同时期其他报纸都难以匹敌,被誉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就本文来讲,《申报》对于揭露社会陋俗以及宣传知识分子抨击旧礼俗、提倡新礼俗的主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效应。
当时祭祀礼俗的陈腐愚昧风气,遭到知识分子的强烈抨击:
我国礼俗由来久矣,仅就祭祀一端而论,琐屑而无补于实事者,在在皆是。苟有人焉,出而倡议改革,则一辈智识简单、脑筋陈旧之流,必目之曰大不孝……生日也、忌日也、逢时轮节也,必设桌煮肴,燃点香烛,焚化纸箔,甚或纸糊起居日用之物,子孙叩拜如仪,起而一者,必大有人在也,其与慎终追远之始旨,岂不大悖哉?[13]
针对繁缛空洞的祭祀陋俗,知识分子提出了既经济又简化,且可凸显祭祀之礼内蕴的改良之法:
即家撰一文,详纪渊源系统,先人创业之艰苦,或一二嘉言懿行,足资后世矜式者,一一笔之。其文之长短,或采文言,或用白话,皆视其家人程度之高下以为准。凡遇春秋佳日,招族人于一室,人执一份朗诵之,但须了解意义,如有先人之遗像,亦一并张挂于四璧。于是睹人思行,感诲并施,其有益于世道人心,岂属浅鲜,亦不仅为一家一室已也。再以先人之遗闻轶事,轮流宣讲,藉加兴奋,庶几不感寂寞,寓祭祀于教育之中,得实益,省经济,减危险,一举而数善,备海内达人,何乐而不为哉?[13]
上述改良祭祀礼俗的建议,强调“寓祭祀于教育之中”,通过追溯祖先遗闻轶事与嘉言懿行,传承家风传统,为后辈追念效法。如此既可剔除烦冗、迂腐之陋习,又能凸显古礼慎终追远的祭祀精意,且符合中国人重视家族人伦情感的文化传统,可谓“一举数善”。
更有学人建议将传统祭祀礼仪改造为纪念会,以追念逝者。[14]与烧纸钱、贡献祭品、跪拜仪式、聚众餐饮这些或迷信、或空洞无意义的陋俗相比,于祭祀之日为逝者举行纪念会,一来可以宣扬其人格精神,给人以深刻的情感印象,二来可以扫除迷信思想,节省不必要的铺张浪费,实为良法。
还有一些学人建议,将用在父母丧祭礼俗上面的不必要花费用来支持教育慈善事业,如此既可使父母之名誉真正流芳千古,又为社会公益做出了贡献:
如果为子女的于良心上对于父母不忘,要报他那“罔极之恩”,又何必作这虚假的仪式,以饰修父母的名誉呢?与其作这消极的耗费,何若作下列积极的建设……就是把对于父母所愿意化费的钱额,省其十分之七八,建设学校或工厂,招集生徒在里边学习,声明是死者遗资捐助的学校,等到那生徒学了技艺智识,能自立以后,他是一定要追本求源,感恩他父母的。并且这学校、工厂要是组织得妥善,恐怕自己父母的名誉真要“流芳千古”“万世不朽”哩!比较用墓志铭等等造那假名誉,或拿酒肉来换亲朋乡党虚誉的价值,不更强吗?[14]
此外,有学人指出,丧礼中亲友所赠挽联往往千篇一律,不甚郑重,且丧礼结束后便付之一炬,徒费钱财,因此建议主人自制精致帖子,交与亲友填写挽词,如此制作而成的挽词既节俭、雅观,又饱含真情实感,可留永久珍藏:
盖人见以纸徵挽知,必意在装潢,且不使之化费,若草草钞录,恐难为情,自必着意书撰,不致如绫布之随意钞写,终归焚化。所得挽词写作俱佳者,必居多数,就中去其泛者,择其尤者装成折册,不但读礼之余可时出披咏以动哀感,即垂之后昆亦可追慕孝思。如此徵挽则于己心安,于人费省,于物又雅观,且可永久珍藏,一举而三善。[15]
以上学人对丧祭礼俗的改良意见对于革除社会陋俗、凸显礼之精意大有裨益。呼吁大众力行节俭、资助公益慈善事业,则展现了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笔者认为,上述变革礼俗的建议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取法西礼之优长
前文述及学人抨击民初礼俗盲目跟从欧风美雨,以致丢失了传统文化之根本。事实上民初知识分子并不反对借鉴西礼,只是抨击社会大众徒习浮夸之风,未能吸取西方礼俗真正的进步精神,如简约、卫生,人文关怀等,因此他们主张在“新旧过渡时代,则宜一方保存国粹,一方采纳欧化也。”[16]
西方礼俗观念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宣传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源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教徒面对基督教礼仪与中国传统礼俗的差异与冲突,进行了调和与创新。其中,将基督教礼仪的进步元素注入传统礼俗之中,加快了国人摒弃旧礼俗,崇尚新观念的步伐。仍以祭祀礼俗为例,学人董景安在基督徒家庭刊物《女铎》上发表文章《基督教敬祖礼》,文中讲道:“中国自古以孝治国,昔贤立教,大抵以慎终追远为尽孝报本之要道,古制相沿……其以为木本水源,溯洄忆念之意,固甚善也。惜乎节文太繁,徒尚形式,且不脱偶像之陋俗。洎乎晚近,迷信益甚,邪说寝炽,持谶焚槠诸恶俗,不一而足,习尚如此,甚可笑也。”而“基督教之入中国,以其事甚愚昧,有悖教育,悉行摒弃之。”打破旧俗虽为进步之举,却未能另立新礼代替之,这使得中国教徒尊祖敬祖的文化传统不得抒发,“而外教人更谓吾基督教徒薄视其亲,心存厌恶。”[17](P33~34)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在既不违背基督教义,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原则下,制定了新式敬祖礼,兹列于下:
1.纪念会。父母诞辰或值周或逢旬,可邀集亲朋开会纪念,其礼式略如平常礼拜,敦请老成主领讲说,以赞美主恩,赞美祖德为主,亦可精治肴馔,留饗众宾。盖会聚宴乐,固人生所应有,今藉此以纪念先人,殊为适当也。
2.纪念堂。凡每乡每邑宜设立纪念堂,由众教友醵资建之,此堂平时主日照常讲道,该堂楼上专备安置已故教友之照片,凡教中人卒后,以其照片并史略送置此堂,留作纪念。
3.捐助公益。凡财力充裕之人,于父母卒后,宜慨然解囊,捐办公益之事,如设教堂、造医院、建学校等,即以父母之名名之,以垂不朽。其家非甚富实者,亦当量力购置器具,赠送于公益之地……即自己无力而能向各亲友捐募,以成一善举,亦属极美。按西国之各种善业,有以人名为名者,大抵皆其子孙向人劝捐而成者也,盖藉慈善事业,以光耀前人,人谁不乐助之?以视我国习俗,亲死而有鼓乐铺张之妄费,僧道谶咒之谬举,得失相去远矣。[17](P35~36)
借鉴基督教礼仪,创建此新敬祖礼,既可消弭国人对中国基督教徒不敬祖的指责,又能剔除传统敬祖礼铺张、迷信之陋俗。借鉴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之优长,办纪念会、设纪念堂、捐助公益,更可谓善法。此法与前述学人对丧祭之礼的改革建议相类似,民初学人对旧礼俗改造之观点很有可能普遍受到过基督教礼仪的影响和启发。
此外,有学者在对比西方日常生活礼仪后,指出了国人不注重仪表整洁的问题:
吾国人素以修饰边幅为丈夫所不屑,王猛扪虱,自古传为美谈,后世士大夫有效之者,鹑衣垢面,不以为耻,甚至有故作褴褛之态,以博名士之头衔者,此非人情之正也。近来吾国人士沾染习气,亦有过事修饰边幅者,此固非所宜,然容貌整饬、衣冠清洁,自为文明人所应守之习惯,吾国人于此似犹有所欠缺。[18]
作者随后列举了当时社会上不注重个人仪表、举止礼仪诸陋习,并提出了改良之法:
1.须长不剃,状至蠢野,交际场中决不容有此。西人凡遇宴会等事,有不剃须者,即为大不敬,故常人皆自备剃刀,有每日剃须者,有三四日一剃者,其不剃者下流社会而已。吾国人未经习惯,于仿行之初或稍感不便,及既成习惯,当不以为苦也。
2.自民国以来,吾国人多戴西式帽,西式帽大概皆有阔边以遮护阳光,故燕居室中或饮食之时若不脱去,即如戴笠坐堂上,殊不雅观。窃以为,凡戴西式帽者,即应遵守西礼,入室即应脱去。
3.今人衣上之钮常有一二不扣者,而项下之钮扣者尤少,此虽小节,亦慢态之一种,足以为精神委靡之表示……至如军人戎服如有一不扣之钮,必遭长官之申斥,盖非此无以表示精神振作之态度也。
4.发宜整齐清洁,不宜多擦油脂,致耀光作亮,亦不宜有恶劣之香味。[18]
以上可见,民初知识分子提倡师法西方,端正仪表,根本目的在于振奋国人精神,这与民族危亡之际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民初知识分子亟亟于起衰振弊,从倡言国家礼治到变革社会陋俗,以至整顿个人仪表,事无巨细,皆有涉及,充分彰显了他们以礼化俗的经世精神。而相关报纸杂志则作为互动交流与宣传平台,对于沟通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群体,整合新旧、东西方礼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 论
民初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变革主张,新文化运动者走上了激进路线,主张彻底打碎旧制度,传统礼教遂成为有形的攻击对象,文化保守主义者为抵御欧风美雨的侵蚀,则刻意抬高传统文化地位,强调古礼的“普世价值”,二者的古礼观虽然迥异,却皆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近代史的撰写也以描绘这两大主流知识图景为主题,而非考察近代学人对传统礼教本质的理解问题,及其对古礼的近代转化问题的思考。而通过本文论述可以看到,民初社会存在另一个知识群体,与文化激进派和保守派侧重鼓动宣传不同,他们以兴盛一时的报纸杂志为媒介和平台,从纯粹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辩古礼的本质和优劣,进而探讨如何对其进行近代转化,实现以礼化俗的问题。此外,他们利用报纸杂志的宣传与教化功能,实现了知识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对民初社会礼俗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以礼经世的思想观念与知识图景,以及民初报纸杂志从中所起到的媒介效应,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新闻传播史的叙述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阐释,二者对古礼的近代转化、东西方礼俗观念的有机融汇所做出的贡献,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进一步展开探讨和研究。
——出土先秦《日书》所见礼俗史料的整理于研究(22BZS012)
——松滋礼俗——毛把烟、砂罐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