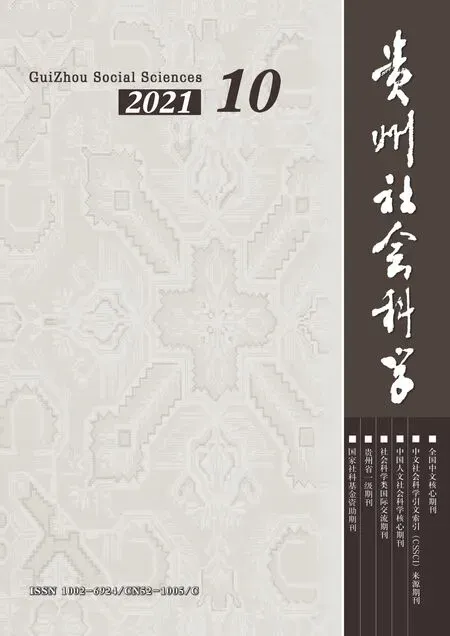谶语歌谣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机制
程梦稷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一、谶语与歌谣:谶谣研究的民俗视角
“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1],作为一种兼得“天意”与“民意”之妙的民间文学形式,谶语歌谣不仅在历代史籍、笔记中不绝于书,数量惊人且自成系统,足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前传媒的古代社会中,谶谣更是以一种“舆论性的预言”[2]5的形式贯穿并影响着社会与历史,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正因如此,不论是在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的整体架构下,还是在中国古代民间歌谣的讨论序列中,谶语歌谣都是难以绕开的关键词。
(一)传统观念中的谶语歌谣
谶谣,顾名思义,即带有谶示意义的民间歌谣,一方面具有“谶”的神秘预言性质,另一方面则以口头歌谣的形式在民间传诵与流行。作为谶谣概念的一体两面,“谶”与“谣”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各自得到记载与讨论。具体而言,“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3]而据《四库全书总目》:“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4]由此可知,“谶”的含义本为传说中的河图洛书等记有神秘预言的文献,后则泛指灾祥的预兆、预言,即如顾颉刚所言“谶,是豫言”[5]。有史籍记载的“谶”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
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6]
此处“秦谶”属梦谶,是对晋国未来国势的预言。可见,诸多关于先秦时期预言的传说记载已具有谶的性质。
“谶”“谣”概念的合用最早见于唐初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裴寂等又依光武长安同舍人强华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都卫元嵩等歌谣、诗谶。慧化尼歌词曰……蜀都卫元嵩,周天和五年闰十月,作诗……未萌之前,谣谶遍于天下。”[7]此处的“谣谶”泛指“歌谣诗谶”。最初定义“谣谶”的《书传正误》同样称其为“谣中杂谶”,并举出“《论语比考谶》、天监志公诗谶、陆法和书谶”[8]为其代表,可见,古人并未从民间歌谣的角度,对谶语歌谣作出独立、清晰的范畴界定,而是将谶言、诗谶、书谶杂于其中。这同样反映在谶谣的文献记载方面,如《青箱杂记》称:“谣谶之语,在《洪范》五行,谓之诗妖。言不从之罚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9],谶谣在史书中一般作为“诗妖”,同梦谶、诗谶等其他谶言形式一并记载在《五行志》《符瑞志》《灾异志》中,表现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关于谶谣的讨论乃是基于民间歌谣研究的需要,着眼于谶语这一观念系统中的歌谣文本,以及这种口传文学与社会历史、传统知识、信仰的相互关系。
古人对谶谣的认识虽然早在两汉就已出现质疑的声音,隋唐以降更是官方禁谶,但谶谣的相关记载仍然不绝于史,对此《金史·五行》开篇称:
两汉以来,儒者若夏侯胜之徒,专以洪范五行为学,作史者多采其说,凡言某征之休咎,则以某事之得失系之,而配之以五行。谓其尽然,其弊不免于傅会;谓其不然,“肃,时雨若”“蒙,恒风若”之类,箕子盖尝言之。[10]
也就是说,古人虽认识到谶谣穿凿附会的一面,却也因文献传统而始终保留在正史的《五行》《灾异》诸志中,并且相比起《礼乐志》《音乐志》中所录风谣而言,谶谣往往因其与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的关联而得到特别的重视。在史书之外,不仅笔记等文献同样多见谶谣异文,而且历代歌谣集亦对谶谣有初步整理。譬如《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间歌谣280余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预言的歌谣,尤其是不避嫌地收录了农民起义中作为动员工具的谶谣。《古谣谚》作为古代谣谚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收集了许多史书文献中的谶谣,这些都构成当前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
(二)现代学术中的谶谣研究
如果说作为“诗妖”的谶谣在古代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因此得到重视的话,那么现代意义上的谶谣研究则稍显暗淡。就歌谣进入现代学术肇始的“歌谣运动”时期而言,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五四同人们最初乃是以“民族的诗”为旨归,歌谣征集处最初所声明的诸如“有天然之神韵”“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11]等关于民间歌谣的理想化、纯粹化想象始终是五四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底色。邵纯熙的“七情分类法”[12]、朱自清所整理的十五种歌谣分类皆不见谶语歌谣的踪影[13],而周作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大体上比较的最适用”的“六分法”亦主动排斥对谶谣的讨论,认为“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之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14]4,“五行志一派的话,……在现代童谣集的序文里,便决不应有。”[15]在这种关于歌谣的价值预判下,谶谣便失去了其作为歌谣得到充分讨论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与谶纬相关的谶谣研究长期处于低谷。20世纪80、90年代以降,谶谣才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的范畴。其中,史学研究是目前谶谣研究的主流视角,即讨论谶谣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和其文化内涵,认为“谶谣就是一部简明的政治发展史,至少可以说是政治发展史的一个见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但这种思路不仅将谶谣概念泛化到史籍中所有带有预言性质的杂谶,而且只选取直接关联正史叙事的代表性文本加以概述而不及其余(如歌谣本事和异文),事实上造成了另一种窄化。文学研究虽自觉区分谣谶与诗谶,然而其落脚点则在于“谣谶说与诗谶说对于创作心态与叙事文学的影响”[17]。目前古代文学方兴未艾的,作为“一种重要结构模式”[18]的明清小说谶验叙事研究也是同样的思路。诚然,史学、哲学与文学研究对谶谣的关注都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与范畴界定,不过,基于目前的研究格局,谶语歌谣为何能够与所谓“政治发展史”保持深入而持续的互动,谶语歌谣又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一种“结构模式”而对文学史产生影响?传统的观念、信仰及知识何以支撑其成为一种难以忽视的文化传统,仍是亟待解决的症结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将谶谣还原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讨论其如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交流工具与话语资源,建立起观念层面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则能够为上述话题提供不一样的视野。
二、解释与建构:谶语歌谣的文本传统
(一)观念:文化传统的权威建构
民间歌谣与神启谶示的联系最早在“谣”与“爻”的考察中就已得到探讨[19],虽然爻占的核心为占卜未来的象,而歌谣的应验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两者并不等同,但古人对语言文字的特殊信仰乃至将其“神谕”化则是贯通其中的文化原型,歌谣的预言性质也在这种观念背景下自先秦以来就受到重视,譬如《国语·晋语》有载:
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20]387-388
歌谣的预言功能在这里得到了理性化的解释,即歌谣被视为民心所向的直接反映,并依托于上古贤王的做法“以古为正”,完成了其合法性论证。事实上,早在“诗妖说”等系统化的理论出现之前,歌谣便被看作一种先兆性存在,人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变故与自然界的变动一样,都存在着隐秘的前兆,而记录、解读这些包含着某种信息代码的预言则因此备受重视。如《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止于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21]
孔子依据“天将大雨,商羊鼓舞”的歌谣成功地从“一足之鸟舒翅而跳”中解读出天灾的讯息,事实上,如最初作为与祈雨仪式相伴的咒文吟唱而进入“童儿屈其一脚而跳”的游戏童谣,以及当代山东地区的商羊舞等都从属于这一知识-信仰共同体,而谶语歌谣正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用以解释自然现象之外,谶语歌谣在人事命运方面也有所表现,譬如“秦世谣”:
秦时有谣云:“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浆,唾吾裳;餐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焚书坑儒,乃发孔子墓,欲取经传。墓既启,遂见此谣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恶之。及东游,乃远沙丘而循别路,忽见群小儿攒沙为阜,问之:“何为?”答云:“此为沙丘也。”从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将死,遗书曰:‘不知何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据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22]
这则歌谣的异文还见于《论衡》《开元占经》等文献,均是讲述秦始皇的命运早已在孔子谶书与秦时歌谣中写定。一方面,歌谣的谶示意义得到“孔子”这一文化权威的背书,即所谓“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另一方面,歌谣、谶书的预兆表明人事、历史的命运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的,帝王尚且如此,万事万物的突发变故也就能够理解了。换言之,歌谣谶示功能的权威性最初正是基于人们理解自然灾变、个体命运以及政权更迭等异常物事的普遍心理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作为谶语的歌谣为自然、人事的变故提供解释,而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五行灾异说则将这种观念理论化,使之成为一套流行的解释系统。最早关于谶谣的古代理论“诗妖说”即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下提出的: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23]1376-1377
正如郑玄在为《尚书大传》中的“诗妖”作注时所言,“诗之言志也”,“诗妖说”与儒家诗学实际上都强调歌谣与现实的关联,只不过后者是将歌谣作为现实的反映,而前者则将歌谣视作征兆,所谓“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时则有白眚白祥”[23]1376,建立在天人感应观念基础上的诗妖说成为歌谣谶示功能的理论基础。自班固在《汉书》中首设“五行志”并安排“诗妖”之目以集中著录谶谣及相关异象、事件后,正史始终为其留有一席之地,在谶谣文本后附录应验情况成为固定的记录模式,甚至未能应验的歌谣亦附有合理化解释,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在“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24]后说明:
臣松之以为,童谣之言,无不皆验,至如此记,似若无征。谣言之作,盖令瓒终始保易,无事远略。而瓒因破黄巾之威,意志张远,遂置三州刺史,围灭袁氏,所以致败也。[25]
由这里所强调的“童谣之言,无不皆验”可窥传统谶谣观之一斑。史书文献关于谶谣的重视与集中记载固然与《汉书》的垂范有关,但同时亦折射出人们对于谶谣的信仰已经取得了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成为古人对于自然、人事之变的重要解释途径。
(二)信谶:历史想象的合法阐释
在这一谶谣观的基础上,古籍中的谶谣记载表现出信谶与用谶这样两种具体形态,前者表现为对于历史合法性的解释方式,而后者则体现为一种历史建构的话语工具。
谶谣在文献中最早见于《国语》中所记载的西周末年的“女童谣”:
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20]473-474
这则褒姒祸国的谶谣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史记》《古列女传》《金楼子》《北堂书钞》皆有其异文,并开启后世谶谣记载的文本传统,即在内容上一般与国家命运等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在形式上则为以预兆(或禁忌)为核心构成的因果叙事模式。
两汉时期谶纬依附经学一度兴盛,不少谶谣依附于阴阳五行等理论,如汉元帝时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23]1395是讲成帝时皇城井水溢出,井水属阴,灶烟属阳;而玉堂、金门是帝王居所,所以这则歌谣预示着帝位将被外戚窃取,而王莽篡汉便应验了谶谣的内容。再如“燕燕尾殿殿。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26],桂树为赤色,而汉属火德,色尚赤,王莽自云代汉者德土,色尚黄,故云黄雀,因此王莽篡汉即验其谶。这些歌谣集中出现在两汉之交及东汉末年,几乎所有重大史事都有与之相应的谶谣进行解释。不难看到,这些谶谣大都有着本身浅显平常的表层意思,其对于政治历史的谶示意义需要经过一番解释,由此推之,这些歌谣可能都各有其“本事”,或为故事歌之一节,或为儿童游戏歌谣,但被刻意割裂开来,改头换面附会为史事谶以证历史变动之合法性。例如“燕燕尾殿殿”这则谶谣的前半段有异文“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23]1395,后半段亦有异文“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23]1396,便可看到民间歌谣裁切、拼接,组合为新谶谣的痕迹。原始天命观与谶纬神学成为歌谣的历史解释功能得到合法化的纽结点,而这一点则构成信谶、解谶向有意识的用谶、制谶等工具形态转变的关键。
(三)用谶:社会建构的话语工具
魏晋及隋唐时期,统治者屡禁谶纬之学,然而民间流行的歌谣则不受这种限制,在分久合短的动荡时期,这类歌谣不论是数量还是参与历史的深入程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不少君主信谶不疑,甚至以谶谣指导行动,譬如司马炎因“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而任命小字为“阿童”的王濬为将军征吴[27]。正是在汉以降的信谶风气下,谶谣不再只是对既有民歌童谣的被动附会,而是也可以在政治意图下有意识地进行结撰。尽管无法武断地在历史坐标轴上区别信谶和用谶,然而,在那时候官方与民间用谶的双向互动仍然是谶谣的历史脉络中难以忽视的重要变奏。
在信谶不疑的观念基础上,谶谣首先成为古代政治家离间敌国或论证其自身合法性的舆论武器,这类制谶造谣见诸史籍的就有不少。譬如隋朝建立前就有大量隋文帝取代北周的谶谣以证明其代周为天意,如“白杨树头金鸡鸣,只有阿舅无外甥”[28]。值得注意的是,文帝登基之初便下达“私家不得隐藏纬侯图谶”[29]等禁谶诏令,可见在位者开始提防作为舆诵力量的谶谣,用谶同时更重于信谶。如果仅仅是从正史的收录情况来看,谶谣自唐宋以降看似趋于消歇,传统研究常据此断言谶谣“经过隋朝的禁毁”而“在唐宋元明清时期风力大减”[2]91。然而,正史记载谶谣必然有其史书性质带来的题材限制,内容无外乎帝王将相与国运盛衰,但那些看似无关大局的社会面向则在笔记、野史中有更复杂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民间口头流传的谶谣与见诸文字的谶言不同,难以一禁而绝,官方正史信谶观念的改变更不妨碍官方、民间“用谶”的增加。因此谶谣事实上并未衰落,而是在形态上发生变化,内容亦不限于国运兴衰,而是作为一种话语工具,更加广泛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儒生士子往往在试前先声夺人制造谶谣,形成所谓天意中举的舆论氛围,在自我宣传的同时也为士子与考官勾结舞弊形成保护伞。譬如《万历野获编》记载:
正统戊辰科会榜后,即喧传谣云:“莫问知不知,状元是彭时。”及廷试,彭文宪果为龙首,不三年而入内阁。[30]390
这种科举谶谣应验的“巧合”在明清屡屡发生,如《池北偶谈》载:“山东乡试,济南童谣云:‘三人两小,太阳离岛。’是科解元乃长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谣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31]都是用拆字制谶的简单方法为士子中举造势。此外,农民起义更是格外重视谶谣的作用,如元末红巾军起义时松江府一度传开“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士气大振而“不二月。破城。”[32];再如《纤言》中关于明末李自成起义的记载:
宏光初立时,浙中上台伪造一谶,云以安士民之心,且托言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有碑八句云:“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塘群鼠暂欢呼。中兴圣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二百十年丰瑞足,还逢古月照皇图。”甲申八月,予至南中,特往蟒蛇仓,见其屋宇如旧,讯之邻人,绝无此事,乃知作者之妄也。……是岂无端民谣,暗合天意耶?[33]
清末义和团运动时宣扬“神助灭洋”的歌谣[34]、革命党武昌起义前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等均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类似,可视作此类歌谣的变奏。
三、传统的话语:古代谶谣的结构程式
从谶语歌谣在历史文献中的文本脉络不难看到,如果说有关歌谣的传统观念乃至“诗妖说”构成信谶、释谣的基础,那么,与之共同构成古代谶谣形态一体两面的则是官方与民间动态交流、各取所需的用谶、制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谶语歌谣与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文类一样,同是用以交流特定观念的话语工具,不仅建立在传统的知识、语料资源库之上,而且更有其程式化的语法规则与表述机制。前者表现为民间歌谣的既有素材,而后者则表现为谶谣托言主体的神异性、权威性,以及谶谣结撰方式的模式化传承。
(一)作为知识资源的民歌本相
由裁切重组、附会阐释甚至编创结撰而来的谶谣大多有着浅显明白的表层含义,在知识脉络与历史机缘的凑泊中存在着官方与民间的复杂互动,结合乐府文献稍加考辨就能推想其所依据的民间歌谣的“本相”。譬如《隋书》载:“琮虽羁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尝与贺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诛,复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35]“萧萧亦复起”这则童谣被隋炀帝视作萧琮起事的谶谣,并因此废萧琮为庶民,然而考察其异文,则这首歌谣很可能与陈代初年的“御路种竹筱,萧萧已复起。合盘贮蓬块,无复扬尘已”[36]有关。可见这首所谓的“谶谣”本是前代民歌,从民间被收编利用并作裁切附会,脱离其原本语境,成为陷忌忠良的话语工具。再如《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文献通考》都有记载的唐初谶谣“侧堂堂,桡堂堂”:
调露初,京城民谣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侧者,不正;桡者,不安。”[37]
明唐再受命,比日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谣。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37]
然而据《乐府诗集》:
《乐苑》曰:“《堂堂》,角调曲,唐高宗朝曲也。”《会要》曰:“调露中,太子既废,李嗣真私谓人曰:‘祸犹未已。主上不亲庶务,事无巨细决於中宫。宗室虽众,俱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势不敌,恐诸王籓翰,为中宫所蹂践矣。隋已来乐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是唐再受命也。中宫僭擅,复归子孙,则为再受命矣。近日闾里又有侧堂堂、挠堂堂之谣,侧者不正之辞,挠者不安之称,将见患难之作不久矣。’后皆如其言。”按《堂堂》本陈后主所作,唐为法曲,故白居易诗云“法曲法曲歌堂堂”是也。[39]
可以推测,这首谶谣本是隋代《堂堂曲》及其在民间传唱的异文,原意可能是咏唱楼台气宇堂堂,然而李嗣真从中发掘出微言大义,把普通的歌谣附会为皇权旁落武后的征兆。这类由民间歌谣的资源库加以改编附会而来的谶谣不胜枚举,后汉桓帝初“为政贪”而作的童谣“城上乌”与乐府《乌生》[40],以及武则天夺权时的歌谣“武媚娘”与陈代歌谣“舞媚娘”等莫不如此,都是调用民间资源,附会以历史的微言大义来应谶。
(二)叙事主体的文化权威
在传统民间歌谣资源的“语料库”之外,谶谣同样有着便于交流的“语法规则”,正是由于这种程式化表达的存在,谶谣才得以作为一种话语工具,一方面在民间接受、传诵与流行,发挥其舆诵力量,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制谶造谣者利用,依循着这种“传统的语法”不断生成谶谣文本。
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针对珍珠港事件的谣言研究时所提出的“线性的范式”,如果说谶谣背后的既有民歌资源是在文本内容层面对集体记忆的激活,那么谶谣的结构程式所遵循的语法则类似所谓的谣言公式[41],以“权威的谶言发出者”与“程式化的信息制作”两方面获得最大的传播效力。
就“权威的谶言发出者”而言,史籍文献中的谶谣常以童谣的面目出现,正如晚清竹枝词所谓“听到童谣成谶语,满街争唱《下盘棋》”[42],时至清末,人们对于童谣即谶语的信仰始终根深蒂固。据周作人的解释,“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如乩卜之言”[14]4,如果说上古初民的神谕来自于具有巫祝身份的部落首领,那么在歌谣所流传的世俗世界,“儿童”则被视为神谕传达的媒介。与这种认识相关的当属“荧惑”观念的发展。《史记·天官书》曰:“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43],荧惑星的职司与“诗妖”在“上号令不顺民心”的意义上相通,《三国志》首次提出“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44],《搜神记》则记录了“荧惑化身小儿”的传说:
孙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忽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曳一疋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45]113
传说中的这则谶语为童谣“三公锄,司马如”,《宋书》《晋书》都有记载。荧惑传说成为后世童谣即谶语的理论依据,“儿童”被视为神谕传递的媒介,正是因为儿童作为天意代言人的权威身份成为文化观念中的共识,不仅“信谶”获得其合法性,而且“用谶”也往往托于儿童之口。基于这种文化观念的成立,谶语歌谣才能够表现出叙事主体的程式化特点。作为文化共识的“权威”而存在的谶谣叙事主体,除了以“童谣有之”“女童谣云”等模式化的开篇之外,常见的还譬如有“孔子将死,遗谶书云”[46]“凤皇衔书云”[47]“古碑,上有篆书云”“道士歌于市”[48]等。作为圣贤代表的“孔子”,以及作为“诗妖”出现的“疯人言”“道士言”,甚至出土的碑刻、山石上类似文字的纹理等,都是谶语歌谣的常见叙事主体。在一些文本中,儿童、孔子、僧道、碑文等元素甚至可能结合起来,如“孔子曰:‘丘闻童谣云……’”[49]“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45]112等,更增其神异性与权威性。
不论是具有介乎人神、生死之间特殊位置的儿童(荧惑)、疯人、道士,还是作为文化信仰象征的孔子,乃至自然界的异象、神物,这些处于日常逻辑之外、具有特殊身份的歌谣叙事主体对应着自然、人事的异常变动,人们对这些歌谣的谶示意义加以命运、天意乃至神谕性质的解读也因此获得合法性、权威性的保障。
(三)谶谣的传统程式与生成机制
就“程式化的信息制作”而言,谶谣虽然在谶示方法与语言特点上复杂多元,但在结构上却保持着强大的稳定性与传承性。
首先,谶谣一般遵循“预兆/禁忌”的因果叙事模式。譬如历史上流传颇广的“城门有血”,即秦时长水县陷落为湖的谶谣:
由卷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妪言其故。妪去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陷为谷矣。[50]
这则谶谣即由标准的禁忌加恶果的方式构成,而“城门有血”更是构成城市被湖泊淹没的固定预兆,不仅在《搜神记》《述异记》《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等后世文献中屡见异文,而且进入地方风物传说,成为人们解释湖泊成因的常见话语方式。换言之,禁忌、祯祥与特定命运的组合成为民间关于谶示意义的一种传统表达方式,并得到模式化的传承与接受。
其次,在谶谣制作的基本方法上,不论是阴阳五行阐释法,还是拆字、双关的文字游戏,都遵循着预言的“模糊性法则”。譬如东汉末年流传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51],“千里草”拼为“董”字,“十日卜”为“卓”,诸多异文虽文字有别,但在拼字为董卓之名这一点上却别无二致,人们因此把此类童谣视为董卓被杀的预言;再如东汉时的谶谣“赤九之后,瘿扬为主”[52],汉属火德,色尚赤,“九”指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瘿”指脖子上长瘤,因此谶谣就指代脖子上长瘤的汉高祖九世孙刘扬将得天下,而同为汉高祖九世孙的刘秀在当时同样制造过不少关于“赤九”的谶谣,都是以指代法制谶。绝大多数谶谣均是以双关、谐音、别名、生肖等指代的方式制造文字游戏,一方面增加其神异色彩,另一方面则以其谶示意义的相对模糊而在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起到对敏感信息的保护作用。
最后,正如民间传说有“盗宝”等话语类型服务于特定需要,作为民间口头讲述的谶谣同样表现出类型化的特点。譬如宋元丰年间,因贡院起火而状元姓焦而传唱的民间歌谣,在明代类似的历史语境下被激活并复制。据《老学庵笔记》:
元丰末,贡院火,而焦蹈为首魁,当时语曰:“火焚贡院状元焦。”[53]
此事在《铁围山丛谈》《能改斋漫录》《夷坚志》中都有记载,当时有人传唱“不因试官火,安得状元焦”[52]。在明代科场上这则歌谣一度风行成谶,如《万历野获编》载:
天顺癸未科以御史焦显监试,而火焚科场,说者以御史之姓应之,诏改是年秋会试。次年甲申廷试,于是时人为之语曰:“科场烧,状元焦。”比传胪,则彭教为龙首,其谣竟不验,唯庶吉中有焦芳一人,后至大学士少师,岂即此人应之耶。……宋时焦蹈登状元,是年棘闱亦被灾,时人云:“不因科场烧,那得状元焦。”癸未之谣盖祖此。[30]390-391
而《治世余闻》也载有异文:“又天顺癸未春御史焦显监试,有火灾。时人语曰:御史原姓焦,科场被火烧。”[53]这些都构成了一组“科场烧,状元焦”的歌谣类型。
此外,与革命、起义相关的谶谣更表现出强烈的类型化特征,譬如黄巢起义时的“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37]920,前半句象形为“巢”字,后半句则点出起义地点。这则“天下反”在元末韩山童起义时作为一种类型被再度激活,韩山童事先在河道工地埋下独眼石人,再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56]“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57]等“天下反”谶谣揭竿而起,自然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再如用简单的拆字法不断制造的“欲识圣人姓,欲知圣人名”类型。这种程式类型最初见于唐末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的谶谣: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生。”昌得之大喜。[58]
后来黄巢起义时,这则歌谣的程式框架被利用起来,只不过其中“董昌”的姓名被替换为“黄巢”:“(黄巢)令(皮日休)作谶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59]
不论是“科场烧”“天下反”,还是“欲识圣人姓,X;欲知圣人名,X”,都是抽离出原有语境的一套固定表达程式,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交流工具,在既有的话语框架下依据具体语境加以替换更新,生成新的谶谣文本。正如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形态类型,这些歌谣亦在固定的程式化、类型化表达中构成一种文化传统,在民众认同的观念前提下,成为运用一套现成规则即可进行沟通的话语工具。
正如近代竹枝词中有人曾发问:“是谁作此预言签,小小童谣可怕哉?”[60]谶语歌谣历来被视作藏匿在历史阴影里神秘而无解的文化幽灵。然而,从其作为民间口头表达的基本形态出发,在历史脉络下爬梳谶语歌谣的文本呈现,则不难钩沉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谶谣其权威性、合法性的建立过程,以及人们试图借此理解、阐释甚至建构历史的丰富话语形态。正是基于民间口头传统的知识资源与程式化表达,谶语歌谣才得以不断生成,作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独特现象,成为我们管窥口传文化与史籍文献、民间知识与历史叙事互动的绝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