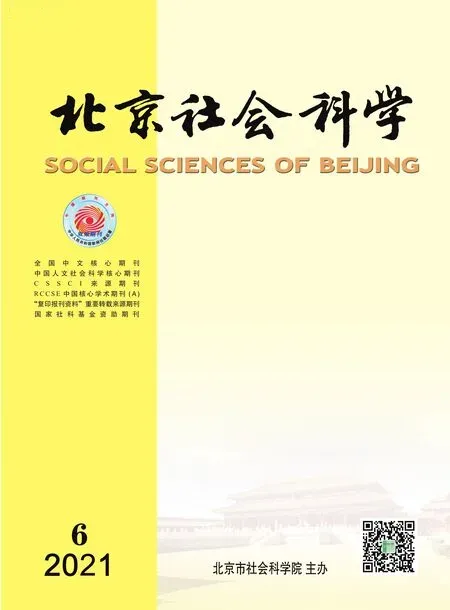“公意”与“美德共和国”
——论卢梭对“政治正当性”的探讨
李永刚
一、引言
何为政治?何为政治正当性?不同时代的人们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古典政治哲人来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政治乃是一种天然的事实,但人又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因而,合乎理性的政治形式就是正当的。基督教神学家将政治理解为一种世俗的生活样式,其正当性来源于上帝。现代政治哲人普遍拒斥了人具有天生政治性的观念,认为政治乃是一种人造物,是人类的一种必然选择的事实。因而,探究政治的正当性需追溯到人的前政治的本性,追溯到人类构建政治体的原初目的。一般而言,现代政治哲人的普遍共识是,人的本能是自我保存,而且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自我保存的最佳方式,正是这种进行自由选择的“自由意志”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的动物的特殊本性。人为了更好地自我保存而自由地选择了政治,而且,这种自我保存既是对人的生命、财产等有形物的保存,更是对人之作为人的特有本性,即自由意志的保存,因而,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就在于人的意志自由。作为一位现代政治哲人,卢梭同样将意志自由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但他在古今之争的氛围中力图综合古典与现代的二元因素,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哲人的智慧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民的同意的二元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公民自由与哲人自由,因而,他认为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在于自由,在于公民自由,更在于哲人自由。正是这种双重自由论使卢梭超越了同时代的启蒙哲人,也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新的可能性。
二、“烂苹果”与“好苹果”:“自由”的失落与重建
汉娜·阿伦特以“好苹果”与“烂苹果”的比喻精当地点明了社会契约论者,特别是卢梭的致思方式,“他们从社会腐败中推导出自然人的存在状态,就像一个对烂苹果了如指掌的人,可以通过假定一个好苹果的原初存在状态来解释它的腐烂。”[1]只是,作为“好苹果”的自然状态是否真实存在,社会契约论者之间存在争论。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个历史事实,彼时人作为类似于动物的“野蛮人”而自由自在地生活于大森林之中。但人毕竟不纯粹是动物,人之优越于动物者有二,即作为人的“天然禀赋”的自由与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在卢梭看来,正是人所得之于自然的自由禀赋构成了野蛮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之处,“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特别之处,与其说是理智,毋宁说是人作为自由施行者特性。自然命令着一切动物,野兽总是服从;人同样感受到自然的影响,但他自认为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且正是在这种自由意识中,人的灵魂的灵性才展现出来。”[2]野蛮人有意志的自由,而且能够意识到这种自由,正是这一点使野蛮人作为“次人”而区别于动物。自然的自由使野蛮人生活于幸福状态之中,但内在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与外在的生存的困难,使野蛮人逐渐走出了伊甸园般的自然状态,因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痛苦而构建了政治体。而现实的政治社会却是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如果说有自由的话,也仅仅是强者的自由,是弱者不得不服从的“自由”。作为一位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的政治哲人,卢梭对现实政治的专制与腐败这个“烂苹果”有着深刻的认识。
如果说自由是那个“好苹果”,那么,现代欧洲的专制的政治现实就是那个“烂苹果”。“专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早形成于古希腊政治哲人对波斯政体的认知,它的原初含义就是主人对奴隶的统治,这是波斯的政体形式,但在古希腊却是外在于政治的家庭统治形式。在古希腊,对奴隶的统治,使主人得以从生存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参与政治的自由和闲暇,因而,作为主奴关系的专制并不构成为一种政体形式,而是造就自由公民的前提条件。16-17世纪,为了论证欧洲殖民扩张和奴隶制的合法性,一些政治哲人论证了专制的合法性,其论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亚当的父权来论证君权的神圣性和正当性。作为人类最早的父亲,亚当对其家庭的专制统治就是一种政治统治,也就是作为君主的亚当对其“子民”的统治,而这种专制统治权来源于上帝的赋予,是神圣的、正当的。现实的君主们自称为亚当的嫡系后裔,依继承权而自动获得了神圣、正当的君权。对此,卢梭批判道,父亲与君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由于父亲与孩子在身体、理智上的天然的差别,由于父亲对孩子天然的爱,父亲具有合乎自然的权力,而君主与他的“子民”却并不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差别,也不存在天然的爱,恰恰相反,君主的利益正在于其子民的不幸,正如牧羊人是为了吃掉羊才保护羊群一样,因而君主的权力是不合乎自然的,也根本不可能是神圣的、正当的。论证专制合法性的另一种方式是,以主奴契约来论证专制的合法性。格劳秀斯认为,奴隶为了获得生命的安全而自愿地将自由转让给主人,由于这种契约关系是自愿的、合法的,因此奴隶制或专制也就是合法的。卢梭批判说:首先,自由作为人的本性,是不可转让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3]而且,这种契约关系由于违反了立约双方的平等性,也就根本不是一种契约。其次,战争凭借的是强力,征服者是凭借强力而使被征服者为奴的,但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服从是出于明智,而非出于义务,因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正当的统治关系。
18世纪,专制这个烂苹果在“开明专制”的口号下具有了“好苹果”的表象。伏尔泰等启蒙哲人为褒扬一些专制君主,如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等对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将其专制统治称之为“开明专制”,这就从文化上将专制合法化了。“开明专制”,也可译为“启蒙专制”,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启蒙的目的在于使人成熟到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于将政治奠基于人民的自由意志的同意之上,而专制恰恰是对自由的压制,是使别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启蒙哲人将启蒙的希望寄托于专制君主,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文化的发展非但不能使专制得以合法化,恰恰因科学、艺术的发展制造了种种欲望,给人类的沉重枷锁镶嵌上了聊以自慰的蔷薇花,以使人们觉得专制的锁链不那么沉重和难以忍受。卢梭之所以激烈地批判科学和艺术,批判启蒙哲学,其原因就在于伏尔泰等启蒙哲人背离了启蒙的本意,使启蒙哲学成为了“专制主义或绝对君主制的支柱”[4],给专制这个烂苹果敷上了一层炫目的光彩,使人更加难以看透其腐烂的内里。
既然走出自然状态是必然的,那么,批判专制这个“烂苹果”就仅仅是卢梭政治哲学的一个导引,关键是如何构建既能走出自然状态又防止“好苹果”腐烂的政治社会新方式,这就要在古典政治哲学的立法者的智慧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民的同意的二元基础上确立“公意”,重建已经失落或异化了的自由。
三、“立法者”与“公意”
既然人类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必然的事实,自由是衡量政治正当与否的唯一标准,那么,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政治社会就应是最能确保自由的社会。在卢梭看来,现实的政治社会非但不能确保人所禀有的天然的自由,反而造成了自由的失落和异化,而根据社会契约所构建起来的政治社会“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即带来了自由的发展:由天然的自由发展为了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天然的自由,仅仅是人的尚处萌芽状态的禀赋,它与作为“次人”的野蛮人的愚昧、孤立、无拘无束的游荡生活相适应。走出自然状态的“次人”发展成为了“人”,“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灵魂整个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他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5]而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是与人真正成其为人的状态相适应的,这两种自由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可统称为“公民自由”。从“次人”到人,从天然的自由到公民自由,是一场人性改造的结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在此意义上,卢梭是一位进步主义者。
那么,与人之作为人相应的“公民自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政治哲人们普遍把法律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在法律的规则之内行事才有自由,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6]在法律的框架内界定自由是一种普遍的共识,但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人们应遵守何种法律才真正是自由的?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前一问题来说,霍布斯认为是为了避免横死的危险,洛克认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总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保存。人们是迫于自我保存的压力而不得不遵守法律的,这样的法律仅仅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是自己极力想摆脱而又不得不遵守的有用的束缚,因而,如何使法律统治人的心灵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在政治学中将法律置于人之上,就好像在几何学中化圆为方。”[7]对后一问题来说,这种工具性的法律总是一种他律,即便是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也是习惯使然,是迫于相互监督的外在压力而不得不如此,遵守这样的法律所获得的仅仅是相互约定的自由,而非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所构建的“公民自由”。解决这两个难题的根本就在于构建起一种真正内在的法律,一种能够统治公民心灵的法律,卢梭认为,这样的法律源自于将个人意志公共化而形成的“公意”。法律作为“公意”的宣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自我立法,人们遵守法律就是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法律就是自由。
订立契约,宣告公意,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要将“次人”教化为人,使其能够认识到公意就是自己的意志,服从公意与法律,仍像自然状态一样自由甚至更为自由,完成“化圆为方”的艰巨任务,必然需要一种类似于“神明”的非凡人物,这就是古典政治哲人所说的“立法者”:“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8]卢梭所言具有非凡智慧的立法者,有两种原型:一种是哲学的或言辞中的立法者,如柏拉图;另一种是被卢梭所理想化的现实的立法者,如为斯巴达立法的莱库古。所谓立法或创制,表面上看是将一套法律或制度赋予某一民族,但内蕴于其中的根本任务是将其作为这一民族的无意识的“社会精神”,即风尚、习俗和舆论,提升为自觉的意识,从而使人们能够自觉地认同并严格地服从这种法律或制度,“使人民遵守国家法也像遵守自然法一样,并且在认识到人的形成和城邦的形成是由于同一个权力的时候,使人民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服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9]这样,立法就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即作为立法的形式因素的立法者的智慧,和作为立法的质料因素的人民的同意,正是形式与质料的相互适应造就了成功的立法。以形式与质料是否相互适应来看,柏拉图与莱库古是两类不同的立法者:柏拉图的哲人王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的统治,而且是一种源自于哲学的智慧的统治,它因超越于政治而具有普适性,单凭哲学的智慧自身就保证了制度或法律的正当性,作为质料的人民只要接受就好了;与此不同,莱库古的智慧则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智慧,他既不向往超越于政治的哲人生活,也不企图为所有民族立法,而仅仅是为斯巴达城邦立法。作为斯巴达公民,他理解自己母邦的社会精神,他知道何种制度适合其人民并能为人民所接受,“他将一副其他民族从来没承受过的枷锁强加在这个民族肩上,但他总是让他们背负这个枷锁,可以说,由此让他们依附于并认同这个枷锁。”[10]人民认同莱库古的立法典型地体现于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到的那位不为战死的儿子们哭泣而为斯巴达的胜利感谢神灵的“斯巴达母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理想国》中的阿德曼托斯替护卫者阶层申诉,因为他们对城邦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哲人王的创制。由此,立法者的智慧和人民的同意、形式与质料的相互适应,造就了莱库古立法的成功,而形式与质料的相互背离,造就了柏拉图的“哲人王悖论”,即哲人因对哲学智慧的爱而不愿意当王,人民因无法理解哲人的智慧也不愿意哲人当王。
卢梭既是一位柏拉图式的哲人立法者,又是一位莱库古式的民族立法者。在一定意义上,探讨政治权利原理的《社会契约论》就是对《理想国》的模仿,因为通过社会契约而构建起以“公意”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当的政治社会,就像柏拉图所构想的哲人王的统治一样,可作为一种形式原则普遍适用于所有民族;而卢梭为科西嘉岛、波兰立法就类似于莱库古为斯巴达立法,他在坚持“公意”统治的前提下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仅适用于科西嘉岛或波兰的特殊条款。那么,卢梭何以既能避免“哲人王悖论”而又在没有莱库古的权威的情况下实现“化圆为方”的重任呢?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将个人意志公共化为“公意”,并使人们认识到公意就是真正的个人意志,也就是将立法者的立法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立法,由此实现立法者的智慧与人民的同意、自由与服从的完美统一。对于卢梭来说,人的天然禀赋就是自由,人作为“自由施行者”而有其自由意志,即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幸福,但这样的自由意志并不像基督教神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恶的,而是良善的,因为自然人从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图。因而,形成公意并不需要像基督徒那样牺牲个人的自我意志以便奉献于上帝的普遍意志,而是要使个人充分认识到自我意志,即自我利益之所在,同时,由于人天生良善,在实现自我利益时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图,那么,由彼此熟悉的一小群人结合成的一个政治体,一个“大我”,也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利益或意见分歧,必然会有一种普遍的公共利益,这就是“公意”。公意并不外在于个人意志,它就是个人意志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个人意志中具有公共性的那一部分,即由智慧或理智矫正了的、排除了个人意志中任性部分、真正合乎个人利益的那一部分意志,这样,公意就既保存了意志的自由又限制了其任意性。这样的公意因为它永远是真正的个人意志,所以永远是正确的。如此,作为公意的宣告的法律就是真正的自我立法,服从公意或法律就是服从自我意志,也就是真正地实现自我的意志自由,自由与服从的完全一致造就了理想的政治体,为政治体赋予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而且,公意作为“大我”的意志,就是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公共的幸福,因而,自由与幸福是完全一致的,这保证了政治体的可实现性。正当性与可实现性的统一就是卢梭根据社会契约所确立的“政治权利原理”的本质特性,它既避免了哲人王统治的空疏性,又避免了莱库古立法的严酷性,是卢梭既奠基于又超越于古典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性贡献之所在。
与柏拉图、莱库古等古典立法者不同,卢梭作为一位现代立法者,将人民的意志作为最高权威,即人民有认同立法的自由,也永远有推翻立法的自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做主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因为,人民若是喜欢自己损害自己的话,谁又有权禁止他们这样做呢?”[11]这是一种集体的任性,但也是人民意志自由的最高宣示,对这种集体的意志自由,既应肯定又应严格限制。卢梭借鉴古典立法者的做法,借助于“公民宗教”来确立“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性”:一方面,它将社会契约和法律神圣化为“神”的意志,人民应像信奉神那样来遵奉法律,即便必须要改变法律,也应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并不是启示宗教,而是服务于政治的“公民宗教”,它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超越性的神,而是作为集体的人民,“人民的声音事实上就是上帝的声音”[12],因而,人民自身以神的名义确保了自我意志的最终自由。
四、“美德共和国”及其批判
凭借着立法者的智慧和人民的同意,社会契约得以订立,公意得以宣告,由此构建起了正当的政治体,即共和国。共和国的构建,使得作为个人意志主体的个人转变为公民。公民既作为整体经常地将自我意志公共化为公意,又作为个体即作为臣民服从于法律。主权者与臣民统一于公民[13],就是立法与服从法律的统一,也就是自由与服从的统一。如果说,自由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那么,公民就是共和国永葆自由的保障,“没有自由,祖国就不能维持,没有美德就没有自由,而没有公民就没有美德。如果能型塑公民,你们将拥有一切,否则,从国家首领开始,你们获得的无非只是卑贱的奴隶。”[14]因而,共和国开端后的根本的而且与共和国相始终的工作就是型塑公民。
型塑公民,是立法者立法或创制工作的一部分,它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公民的美德。卢梭认为,人是天生良善的,但这种自然的善并不就是美德,因为自然人处于对善恶的无知状态,他的善在于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图,而进入政治社会后,人的自然的自爱心腐化成为了自尊心,正是在与他人的虚荣的比较中,人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从而造成了人身的依附,造成了主人与奴隶之分。社会契约的订立改变了这一从自爱心腐化为自尊心的进程,因为立法者的立法或创制就是要“改变人性”,即将自然的个人型塑为公民,公民不仅是善的,而且是具有美德的,公民美德就在于“个人意志对公意的服从”[15]。如前所述,公意是个人意志的公共化,正是公意型塑了公民,因而,服从公意就是公民的本质属性,而对公意的服从本身恰恰就是公民之为公民的美德,所以,对公民来说,美德不是外在的、强加的,公民本身就是具有美德的。正如个人意志公共化为公意一样,人的自然情感即自爱和怜悯,随着社会契约的订立而扩展成为了对作为公共人格的“大我”,对同胞甚或是对人类的爱。但如同意志一样,情感或爱的强度是与其扩展范围成反比的,因而,爱是有界限的,其自然的界限就在于城邦。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现代思想家中没有人比卢梭能更好地理解polis[城邦]的哲学概念:polis[城邦]是与人的求知能力和爱的能力的自然界限相对应的完全的联合。”[16]在政治社会,共和国就是古典城邦的完美对应物。这种以城邦或共和国为界限的爱就是一种政治美德,就是爱国者的美德。立法者在立法或创制时应创制各种公共的游戏、体育竞赛活动、节日等使所有的公民和未来公民参与其中,在团结、欢快的氛围中保持、发扬公民的美德,并教育未来的公民养成对祖国的爱,使对祖国的爱充溢于每个人的内心,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爱内化为不自觉的、无意识的爱。“应当由教育把民族形式赋予心灵,并指导心灵的趣味和意见,以至于靠偏爱、激情和必要性心灵就具有爱国热情。一睁开眼睛,一个孩子就看见自己的祖国,直至他生命的终了。每一个真正的共和派在吮吸母亲的乳汁时,也在吮吸对祖国的爱,也就是对法律和自由的爱。这种爱构成了他的整个存在。他看见的仅仅是祖国,活着只是为了它。”[17]这种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的公民典范就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卡图(Caton),这位“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人”英勇地反抗凯撒的暴政,当事不可为时,他以自己的鲜血祭奠了罗马的共和政制。上文提到的那位“斯巴达母亲”同样是公民美德的典范。由类似于卡图和“斯巴达母亲”的公民组成共和国就是真正由美德来统治的共和国,即“美德共和国”。
卢梭的“美德共和国”因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美德的恐怖”相关联而备受批评。阿伦特尖锐地批判了卢梭的“美德共和国”及作为其基础的“公意”。阿伦特认为,卢梭政治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将“意志”等同于“利益”,“卢梭的全部政治理论,都依赖于将意志令人费解地等同于利益。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通篇都把它们当成同义词使用。他悄然假定,意志是利益某种自发的表述。因此,公意就是普遍利益的表述,是人民或民族整体利益的表述。”[18]为了构成公意或公共利益,卢梭悄然地引进了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这一概念,并将现实的政治斗争内化为个人内心的自我斗争。对于一个政治体而言,保持其团结或整体性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存在着一个时时威胁着其生存的敌人,当外敌构不成严重威胁时,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为了最大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威胁。对于公意或公共利益而言,最大的敌人不在自身之外,而是个人意志或利益,也就是个人的那些不想被公共化的意志或利益,可称之为“私意”或私利,正是这种私意威胁着公意,因而,公意或公共利益的形成取决于与私意或私利的斗争,“只要每个公民内心都装着共同的敌人,以及由这一共同的敌人所产生的普遍利益,就足以保证国家的同一性。这一共同的敌人,就是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或特殊意志。只要每个特殊的人起而反抗他那特殊的自我,就可以将他自己的对手,也就是公意,在自我中唤醒,这样他就将成为民族政治体的真正公民。”[19]这样,每个人的内心都分裂为了公意和私意两个部分,只有公意才是真正的个人意志,只有公意占据主导的公民才是真正的公民,因而,要成为真正的公民,或者说,要具有公民美德,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与自我内心的“私意”作斗争。这种发生于灵魂深处的斗争在法国大革命中充分地展现了出来。罗伯斯庇尔等卢梭的崇拜者以公意战胜私意的大公无私为政治美德,革命者之所以为革命者就在于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私意或私利,完全以公意或公共利益为依归,他们以这种革命美德的典范自居,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判所有人——但凡人们有一点私意或私利,就被认为背叛了革命,就是人民的公敌,就应该被推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等人以公意的代表自居,以美德之名实行专制统治,造成了“美德的恐怖”,最终也倒在了自己架设起来的美德的断头台上。
阿伦特准确地把握住了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即作为个人意志公共化的结果的公意才是真正的个人意志,在此确实蕴含着公意与私意斗争的意味,而这种蕴含于其中的斗争意味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演变为了“美德的恐怖”。因此,卢梭确实应对法国大革命承担一定的理论责任,但这却不是卢梭公意理论的主旨,卢梭强调的是个人充分展现其自我意志。既然人是天生良善的,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图,而且每个人都以实现个人的利益为旨归,那么,只要每个人都充分地表达自我的意志,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就必然会达成公意,公意就蕴含在政治体每个人的自我意志之中,所谓达成公意就是将蕴含其中的公意显现出来。“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20]这就表明,对于一个小型的共和国而言,公意的达成并不需要个人内心的斗争,因为个人真实意志的表达就是公意,这种个人意志的表达是一种意见交流、共同讨论、相互竞争的政治空间。意志总是自我的意志,它虽不可被代表,但并不排斥意见交流,意志的单一性、不可分割性并没有消除阿伦特所说的人的“复多性”。卢梭的“美德共和国”未必会带来“美德的恐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阿伦特所赞成的“参与式的”民主共和国,阿伦特因过多地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追溯至卢梭而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卢梭。
五、超越“公民自由”的“哲人自由”
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自由与美德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美德就在于个人意志服从于公意,而自由的本质就在于自我立法,也就是个人意志服从于公意。因而,服从公意的美德,或者说,公民美德就是公民自由,即卢梭所说的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如前所述,自由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正当的政治体就是自由的共和国,同时由于自由与美德的同一性,这种自由的共和国就是“美德共和国”。在卢梭的心目中,美德共和国的典范就是理想化的斯巴达、罗马共和国和日内瓦,它们都以美德和自由而成为典范。
施特劳斯认为,卢梭在其著作中呈现出两副面孔,即作为公民的卢梭和作为哲人的卢梭。公民卢梭借助于古典的城邦和公民美德来批判现代性,力图通过社会契约构建起现代的“美德共和国”,但在其构建“美德共和国”的扛鼎之作——《社会契约论》的开端,卢梭就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1]这一名言奠定了整部著作的基调,即一切政治社会包括根据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美德共和国”都是一种枷锁。这种政治的枷锁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并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自由地承担起来的公共幸福的“羁轭”。但对因禀有特殊的天赋而超越于普罗大众之上的哲人而言,这种政治的枷锁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了,它因要求公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事务之中而丧失了沉思的闲暇,同时,它将孤独的哲人视为“有害的人”而排除出政治社会,这样,政治社会就漠视了人在天赋上的自然的不平等而以同一尺度衡量所有人,这就是政治社会的非自然性。“自然”是卢梭批判现代性的另一标尺,也是更为根本的标尺,但这并不是要回归到前政治社会的自然状态,重获生活于大森林中野蛮人的“天然的自由”,而是要在“美德共和国”中保留哲人的生存空间,允许其作为“无用的人”生存于“美德共和国”的边缘。“于是,公民社会最终的合理性的根据就在于,它允许某种类型的个人通过从公民社会中退隐、亦即生活在其边缘而得享至高无上的幸福。”[22]因而,政治正当性的最终源泉在于哲人的自由。
卢梭是一个公民,更是一个哲人。公民卢梭以“立法者”的形象来教育民众,使其能够根据社会契约构建起美德共和国而赢获“公民自由”,哲人卢梭则以“教育者”的形象来教育那些具有优异天赋的儿童,使他们能够超越于公民自由而获得合乎其天赋的哲人自由。“爱弥儿”是卢梭所假想的一个智力寻常的孩子,通过采用“自然的教育”,或者说是“消极的教育”,爱弥儿成长为了一个生活于政治社会的自然人,“爱弥儿既没有祖国,也没有被教育成一个公民。他将遵守他所停留的国家的法律。他对社会契约的‘神圣性’一无所知。他的座右铭是:Uni bene, ibi patria[哪里好,哪里便是故乡]。”[23]但爱弥儿因其天赋所限而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人,这从《爱弥儿》的结尾,已经成年、应承担起做父亲的职责的爱弥儿仍需要“老师”的指导就可看出来。卢梭只是通过爱弥儿这个寻常儿童的教育事例,证明有天赋的儿童完全可以通过“自然的教育”而成长为生活于政治社会的哲人,成长为类似于卢梭本人的哲人。哲人们虽对政治社会“无用”,但并不是“有害的人”,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政治社会并不干涉他们,允许他们生活于政治社会的边缘,在孤独的沉思、遐想中实现哲人的自由。根据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美德共和国”并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它因排除哲人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然,只有允许哲人存在并给予其相应的尊重的“美德共和国”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因而,是否允许哲人存在,是否尊重哲人的自由,是衡量一个政治体正当性的最终试金石。
六、结语
施特劳斯派学者一般认为,哲学与政治由于本性不同而处于二元对立状态,但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哲学与政治、公民与哲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既然人的本性在于自由意志,在于自我立法,那么,政治体作为一个公共人格,作为一个“大我”,其本性也就是自我立法,政治体的意志就是“公意”,由于人天生良善,作为个人意志的公共化的公意就是最真实的个人意志,因而,公民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我的意志,就是自我立法;而哲人作为文明化了的自然人,其本性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立法,因而,政治与哲学在本性上是统一的。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人民整体,都会错失公意,这就需要作为“立法者”和“教育者”的哲人的指导,因而,从本性说,哲人高于公民,哲人自由高于政治自由或公民美德。所以,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在于自由,在于公民自由,更在于哲人自由,仅具有公民自由的美德共和国是不完全的。现实的政治体只具备有限的正当性,即便是理想化的美德共和国也仅具有不完全的正当性,而具有完全正当性的政治体是宽容哲人存在的美德共和国,这是一种奠基于自由意志的“理想国”,是哲人的智慧与人民的同意完美结合的美德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