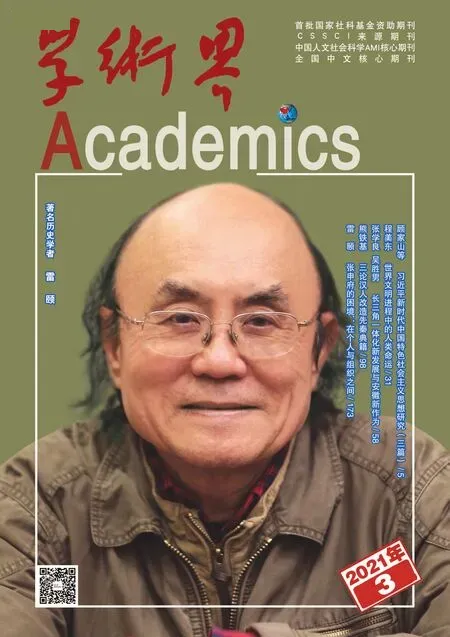儒家学脉中的王阳明〔*〕
胡水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王阳明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生活时代对应于欧洲“文艺复兴”盛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备受日本人推崇、对日本近现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古语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种用以权衡人物的“三不朽”标准,在一些人看来适用于王阳明一生,而自古以来同时满足这三项标准的人屈指可数。王阳明可谓一位道德与功业皆有成就、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未曾显出过大张力的人物。《明史》为王阳明作传,以转述的方式标示出王阳明在“气节、文章、功业”(《明史·王守仁传》)三方面的卓越成就。《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逝世后,王阳明谥“文成”,从祀孔庙,明朝的诰命认为,王阳明“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永为一代之宗臣,实耀千年之史册”。〔1〕这样的评价和礼遇,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说不高。然而,王阳明也是饱受非议并引发争论、长期难被理解的人物。有人说,“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在21世纪已经过去两个十年,如何看待这样的命题?究竟应当如何审视王阳明这个人物及其学说?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文化问题。
一、儒家学脉与道的系统
对于王阳明及其学说,无论是阳明后学,还是王阳明自己,都始终带着“道”的眼光。在阳明后学那里,王阳明是堪与孔孟比肩并论的人物。王畿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说,“阳明先师……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某氏,而端绪实原于孔子。……此学脉也。师以一人超悟之见,呶呶其间,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习,盖亦难矣。”〔2〕黄道周在《王文成公集序》中说,“明兴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晦庵当五季之后,禅喜繁兴,豪杰皆溺于异说,故宗程氏之学,穷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宋人之后,辞章训诂,汩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虽然,晦庵学孔,才不及孔,以止于程;故其文章经济,亦不能逾程以至于孔。文成学孟,才与孟等,而进于伊;故其德业事功,皆近于伊,而进于孟。夫自孔、颜授受,至宋明道之间,主臣明圣,人才辈生,盖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3〕董沄在《题〈传习录〉后》中也说,“斯道之在天下,虽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显晦,实由气数。文、武之后,斯道与王迹俱降,渐远渐微,不绝如线,历数百年,至仲尼一唱而天下响应。仲尼之后,至孟子没有遂绝,历战国、秦、汉,如灭烛夜行。……至于宋而濂、洛、关、闽诸大儒出而昌之,五星聚奎,斯道于是乎大明矣。然天下之士,见在上者之崇重乎此也,遂借之以为利禄之梯,讲之愈明,而失之愈远,大非先儒之初心矣。以至于今,而笃生阳明夫子,提天下之耳,易天下之辙,海内学者,复响应焉”。〔4〕诸如此类的评价,涉及王阳明与孔孟的联系以及与朱熹的不同,眼光并未集中于通常的气节、文章、功业方面,而是从儒家学脉的角度审视王阳明及其学说,将王阳明视为千百年间与孔孟遥相呼应、重新发现“道”的伟大人物。
对此,王阳明亦有明显、一贯而坚定的自觉意识。有人曾称赞王阳明说,“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王阳明却笑着回应,“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5〕由此可见王阳明对其学说的自知和自信。相比文章、气节、功业,王阳明更为看重其学术,一如他所讲,“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6〕这些话语,表达出王阳明以“道”融贯其文章、气节和功业的生命态度。孔子以“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总结一生,也可看到贯穿其间的“道”的线索。“道”也贯彻在阳明学中,以致用通常纸面上的学术研究来定位王阳明学说并不合适。王阳明说,“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7〕阳明学显然属于“讲之以身心者”,是与“见道”“明道”“体道”密不可分的“孔门之学”。对“道”的讲说、阐释和传播,可谓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坚持不懈、死而后已的事业。王阳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8〕而后即开始反复讲授孔孟心学。他时常感慨,“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9〕从王阳明的生平及其遗留著述看,王阳明是儒学传承过程中,重新真切发明道统,并自觉接续孔孟学脉的史上罕见的“道”的觉悟者、实践者和传播者。王阳明及其学说在当时受到肯定和推崇,并在后世获得新的发掘,应该说与几千年中国文化传承进程中绵延不绝的“道”或道体有着重要关联。
从历史看,对于道体或心体的觉察和把握,在儒学变迁史上有长期的中断,亦有明显的分歧。关于分歧,《韩非子·显学》提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在这段话中,韩非子以学说的分化和时间的久远,将儒家描述为支离破碎、根据也不牢靠的学派,由此对儒学与孔子乃至尧舜之间的准确联系提出理论质疑。然而,从后来实际的中国历史看,儒学终究回到孔孟以及尧舜那里,由此而形成的道统和道学也愈益明确坚固。在言及儒学历史时,韩愈采取“道”的视角,洞察到儒家道统的中断。他在《原道》中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所看到的这种道统的断裂,直到宋明时期通过理学和心学才得以弥合。宋明以来,自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始,接连出现《圣学宗传》《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学统》《道统录》《闽中理学渊源考》《清儒学案》等著作。犹如禅宗灯录对各祖师和成就者的言行汇编一样,这些著作整理儒家古今人物传记及其著述,使儒学源流脉络更为确定、清晰和丰满,由此日渐成为与尧舜孔孟牢固连接并以“道”贯通起来的道学系统。在此系统和源流中,王阳明称得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阳明后学如此看,到现代,基于中国文化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10〕的观测角度,王阳明仍被有些学者视为中国历史上五百年一出、具有时代分水岭意义的关键人物。
不过,对于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中此类重要人物的确定,历史上也存在不同意见。尤为典型的是,古今一些评论认为,宋明儒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不是王阳明,而是朱熹。《宋史》提到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并引述朱子后学的话来评定朱熹:“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朱熹传》)这一叙述和评价,显然也在儒学脉络中,从道统的角度,将朱熹推至极致。在朱子后学那里,被抬高到与孔子并立的“万世宗师”地位的是朱熹。明代薛暄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后世莫知所尊。周、程、张子之道,非得朱子,后世莫知所统。孔子之后,有大功于道学者,朱子也”(《读书续录》卷五)。到现代,钱穆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11〕不仅于此,清代一些有关儒家宗录汇编的书,带有明显推崇朱熹而贬抑王学的学术立场。张伯行在《道统录》下卷,只编周、程、张、朱,而未及王阳明。熊赐履在《学统》中,分学统为“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五种,将朱熹归为“正统”,而将王阳明列入“杂统”,批评“阳明未尝以佛氏为讳……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沦晦焉”,谴责阳明后学“立为三教一家之说以附和之,名为浑同、为调停,实则窜入尼山之室而据其座也。”〔12〕这样的归类和批评,与阳明后学对朱熹与王阳明的判断大相径庭,甚至不乏门户清理的意蕴。一如李振裕在为《学统》所作的序中所言,“曰‘杂’,曰‘异’,则非我族矣。名为统,而实无统焉者也。呜呼!一出一入,盖其严哉……‘杂’与‘异’之害道者不可胜计……‘杂’者挟持偏僻,而阴窜吾道之中……辨‘杂’之戾于正也尤难。”〔13〕王阳明在世时,阳明学即被一些人视为“伪学”“邪说”而遭受谤劾。清人所编《明史》,不讳谤议,援引讥评,亦断定王阳明“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明史·王守仁传》)。
关于王阳明以及儒家关键人物的不同判断和意见,体现出儒学发展进程中的源流分歧,以及把握儒学真义的难度。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学术形态,包涵有令后世感到困惑以致难以辨清、易生分歧的形而上学要素,由此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呈现出各种歧见和样式。道体及其作用原理,可谓引发分歧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看,在儒学从孔孟到宋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汉代的董仲舒是一个重要人物,但道体或心体看上去并未受到董仲舒的重点关注。宋明是孔孟心性要义得以重现的时期。对作为孔孟学说根本的道体或心体的关注,持续贯穿于从周敦颐,到二程,再到朱熹、陆王的宋明理学中,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质。《宋史》也因此在正史列传中开始专辟《道学》。应该说,宋明理学作为所谓“新儒学”的历史意义,正在于使儒学中以往被长期埋没的道体或心体这一因素重新发明出来。后至清代,康有为对道体或心体亦有所察觉,但他在学术上更多表现出对董仲舒儒学路径的追循,侧重于政治层面的公羊学。综合起来看,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康有为的公羊学,作为宋明以来儒学的重要发展,都触及儒学的“体—用”层面,但又各有侧重。相比而言,朱子学表现出对“用”的层面的礼教的僵化固守,这与对道体虽有所识见但未能透彻直见不无关联;阳明学表现出对道体的反复而一贯的阐述,虽然注意到“用”的灵活性和多变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着力于“用”的层面的大变革;晚清公羊学则表现出在世界背景下对“用”的层面的可变性,特别是政治变革的加强,而对道体的阐述显得不够充分。这是在现代条件下审视儒学,特别是阳明学,尤需看清的。
二、道体实践与主观识见
在道体及其作用这一关键主题上,阳明学与朱子学如同朱陆之别那样,呈现出重要而细微的差别。对此差别的洞察涉及对儒学乃至中国文化要义的真切把握。朱子后学对王阳明的歧视,以及阳明后学对朱熹的异议,看上去都同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差别有着紧密联系。就辨别儒学发展进程中的真义与歧见而言,洞察分析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异同,殊为必要和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对朱熹和王阳明及其学说的判定,所显现的实为判断者的学识、眼光和知见。现代无论是以朱熹比论孔子,还是以王阳明为孔门子路之类的看法,都很难说真正懂得了王阳明、阳明学以及朱陆之别。
就学术影响而言,王阳明身前身后一直存在较为强势的“朱子学”背景。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在南宋同起并称,而朱熹、陆象山过世后,象山心学“淹而未显”,〔14〕朱子理学则在元、明、清三代被长期奉为正统。到王阳明时代,“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15〕从儒学系统看,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有如禅宗的北派与南宗,前者成为得到朝廷支持的“官学”,后者则在沉寂近四百年后通过王阳明才得以重启复兴。新兴的“阳明学”,犹如象山心学一样,看上去与“朱子学”也存在张力。王阳明认定象山心学“得孔孟之正传”,〔16〕而紧随象山心学的“阳明学”亦直追孔孟,在明代成为“朱子学”的直接竞争者,并且后来居上,一时“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明史》记载,“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弛,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只是,复兴的“陆王心学”虽然盛开一时,但在王阳明过世百年后遭受堵塞,再次被“程朱理学”这一大背景所淹没。直至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晚清以来近两百年间,“阳明学”才再度崛起,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开启现代进程、引领近代变革的时代思潮,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程朱理学”淡出历史舞台。
“朱子学”与“阳明学”呈现出的历史影响和不同命运,看上去与两种学说的特性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朱熹与王阳明,以及“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存在重要差别,但“朱子学”与“阳明学”又明显同归儒学脉络,可谓儒学在宋明时期重新崛起的两个峰头或潮流。置于儒学系统看,“阳明学”与“朱子学”可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对这两种学术的分辨构成了明代以来儒学的重要内容。就同的方面而言,朱熹与王阳明都注意到道体或心体在儒学中的根本地位和重要性。在王阳明看来,“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明史·王守仁传》)因此,王阳明试图通过《朱子晚年定论》,来为朱熹对心体的觉察和重视提供些许证据,由此促成自己与朱熹的一致。《朱子晚年定论》煞费苦心地甄选出朱熹有关觉知心体重要性的诸多话语。例如,“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伯,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段处,有下功夫处。……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只是口说,不曾实体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大体未正,而便察及细微,恐有‘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之讥也”。这些话语,足以表明朱熹晚年认识到“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而且确已留意“道之体用”及其在儒学中的重要性,但以此印证朱熹晚年对心体的觉悟仍显得远远不够。〔17〕从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以及朱熹注解“四书”、《参同契》,编《伊洛渊源录》等看,对于作为儒学基要或核心的、形而上的道体或心体,朱熹与王阳明实有共同关注。也是在此“道”或道体意义上,王阳明认为,“朱、陆二贤者天姿颇异,途径微分,而同底于圣道则一”。〔18〕
尽管如此,与朱熹以及很多其他儒家人物相比,王阳明有其他人虽心愿往,但力所难及也终未至的独到之处。在对“四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的解释上,王阳明时常表现出与朱熹不同。经常被提到的典型例子是,朱熹讲“在新民”,王阳明则坚持贯通起来讲“在亲民”。即使王阳明有意通过《朱子晚年定论》来弱化乃至消除其与朱熹之间的隔阂,但差别也还是会从内在或外在方面突显出来。《朱子晚年定论》收录了朱熹有关“敬”的两段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仍映现出朱熹与王阳明之间难以破除的间隔或不同。这两段话是,“日用之间,痛自敛饬,乃知敬字之功亲切要妙乃如此”;“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19〕正如《宋史》所言,朱熹“为学……以居敬为主”(《宋史·道学》),亦如陈献章所言,“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白沙子全集》卷六),“敬”可谓“朱子学”一贯强调的基本修养,以致朱熹被一些后学描述为从早到晚、自少至老端整谨肃抑或拘谨克制的理学家形象。〔20〕而从《传习录》,可鲜明看到王阳明对于“敬”的不同态度。《传习录》记载:“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21〕在这段话中,“诚”看上去是表明意识主体自觉融合、突破主客观二元框架的语词,而“敬”所表明的则是仍然处在主观与客体的二元结构中、并且立基于主观的处境或状态。王阳明关于“诚”与“敬”的此种细微辨别,实际拉开了王阳明与朱熹以及很多其他儒家学者的差距。《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有老父问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庄,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父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而老父径去。”〔22〕后来,同样被人从“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予以评价的曾国藩,在著述中也留有很多“居敬”话语。
“敬”“诚”之别显示出朱熹与王阳明的精微差异。此种差异是长期存在的。朱熹注解“四书”“四十余年”,临终的前一天仍在琢磨和修改关于《大学》的注释,可谓“毕力钻研,死而后已”。〔23〕而从王阳明的著述中亦可看到王阳明念兹在兹地长年坚持。只是,与朱熹的文字注解不同,王阳明的持续实践看上去有着别样的内容和形式。王阳明多次提到其亲身实践。他说,“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24〕这些话语,透显出王阳明“久久成熟”“日见不同”直至“不须着力,不待防检”“不着覆藏”地步的“知行合一”实践。王阳明以《孟子》所讲的“常有事焉”“勿忘勿助”,以及《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对应和表达此种从生到熟的心学实践。〔25〕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明儒学案》卷十)的临终遗言看,王阳明至死都在坚持此种实践。这是独到的心学实践。《论语》中“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等话语,亦隐晦地折射出此种实践的一些讯息。这是儒家形而上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学不同于滞留于文字的纸上学术的基本方面。对照此种心学实践与朱熹的文字注解,结合王阳明的著述,足以洞察王阳明对道体或心体的真切体悟和契合,这迥异于对道体或心体的主观识见或文字研究。
三、道体与21世纪
王阳明的著述,特别是《传习录》,紧紧围绕道或道体展开。王阳明后来讲“致良知之学”,也是在讲道体。有人问,“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王阳明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26〕王阳明将“致良知”看得很重,其实旨即在于对道体的觉知。在王阳明看来,“千古圣人只有这些子……人生一世,惟有这件事。”〔27〕王阳明关于道体的阐述,通过大量书信和讲学记录留存于世,在诗作中亦可找出诸多印迹。诗这种形式看上去为王阳明直接而又幽微地表达道体提供了更加方便的途径,编著中有些似乎被有意隐去的话语在诗作中得以遗留。从文字看,诗作与道体相关的内容相对集中于道体及其觉悟,儒学真义的埋没与复兴,以及觉知道体的歧途等。
例如,在诗作中,王阳明表露了悟道的历程和信心。他说,“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谩对芳樽辞酩酊,机关识破已多时”,“而今始信还丹诀,却笑当年识未真”,“君不见,广成子,高卧崆峒长不死,到今一万八千年,阳明真人亦如此”,“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28〕关于道体,王阳明隐晦地写到,“洞里乾坤别,壶中日月明”,“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一窍谁将混沌开……须知太极元无极”,“一颗悬空黍米珠”,“青天白日是知心”。〔29〕诗中的“乾坤”“日月”,“圆圈”“针”“黍”,“青天”“白日”等意象,看上去与中国文化所蕴涵的诸如“天下归仁”“明明德于天下”这样的心性或道德结构是吻合的。〔30〕“坐久尘虑息,淡然与道谋”,“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31〕则又显示出王阳明对道体自觉自如地默契。在王阳明看来,道在自得,不在文字,不在知见,浑然天成,平常简易。他说,“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痛痒自家知”,“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自是孤云天际浮,箧中枯蠹岂相谋。请君静后看羲画,曾有陈篇一字不”,“悟到鸢鱼飞跃处,工夫原不在陈编”,“正须闭口林间坐,莫道青山不解言”,“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暗”,“坦然由简易,日用匪深玄”。〔32〕
王阳明对道衰学绝以及真义失传,多有感慨。他说,“丧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诗妙尽从言外得,易微谁见画前真”,“千年绝学蒙尘土,何处澄江无月明”,“须怜绝学经千载”,“圣学宫墙亦久荒”,“台上久无狮子吼,野狐时复听经来”,“圣路塞已久,千载无复寻。岂无群儒迹?蹊径榛茆深”,“淳气日雕薄,邹鲁亡真承。世儒倡臆说,愚瞽相因仍”,“世人失其心,顾瞻多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驰惊奔骛。高言诋独善,文非遂巧智。琐琐功利儒,宁复知此意”,“悠悠伤绝学”。〔33〕对于明道者少,传道不易,王阳明也流露出一种无奈。他说,“奇中之奇人未知”,“逢人休说坐春风”,“见人勿多说,慎默真如愚”,“本来面目还谁识,且向樽前学楚狂”,“痴人前岂堪谈梦,真性中难更说玄。为问道人还具眼,试看何物是青天”,“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洙泗辍金铎,濂洛传微声。谁鸣荼毒鼓,闻者皆昏冥。嗟尔欲奚为?奔走皆营营。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34〕
王阳明还写到,“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莫道仙家全脱俗”,“惭愧维摩世外缘”,“聊将肤浅窥前圣,敢谓心传启后人”,“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35〕从这些诗句,又实可见到一个留形于世间、不同于功利的尘俗之人、亦不同于古木青灯的释道中人、自得道趣而又长怀传道之忧的丰满人物形象。
或许,只有基于道或道体审视王阳明这个人物及其学说,才可真正理解“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的内涵和意义。对照来看,这一命题比20世纪80年代人们所议论的“亚洲世纪的到来”,看上去具有更浓厚也更根本的文化意蕴。很多人批评王阳明,认为他将道家和佛家学说引入儒学。此种说法未必准确。若细读王阳明的著述,可发现阳明学的内容其实都可从孔孟和儒家经典,特别是《孟子》那里找到渊源。如同象山心学那样,阳明学重新开启孔孟学说的心性内容,称得上地道的儒学。王阳明视孔孟、颜回为圣人,从“道”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儒家经典,认定儒学是关于道体并让人觉知道体的学问。“孔子,圣人也”,“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36〕这是王阳明对孔子和《论语》所下的两个简要判断,采取的是圣或道的视角。沿着这一视角,可看到从尧舜,到周文,到孔孟,到周程,再到陆王的流传以及由此形成的道的系统。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儒释道三家共通的根本所在。处在这样一个道的系统中的王阳明,适合作为道的发明者和传承者看待。21世纪,只有这样一种道的文明在中国,在亚洲,在东方,乃至在全球重新兴起,才可以说“王阳明的世纪”真正到来。
注释:
〔1〕〔2〕〔3〕〔4〕〔5〕〔6〕〔7〕〔8〕〔9〕〔14〕〔15〕〔16〕〔17〕〔18〕〔19〕〔21〕〔24〕〔25〕〔26〕〔27〕〔28〕〔29〕〔31〕〔32〕〔33〕〔34〕〔35〕〔3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81-1682,1503-1504,1793-1794,1763,1739,109、1088,85,42,1300、312,660,891,660,145-159,1728,152-153,44,65-139,93-95,228,1286,851-876,835-870,772-863,797-872,802-875,786-861,772-824,290、1008页。
〔10〕《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提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11〕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页。
〔12〕〔清〕熊赐履:《学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22-523页。
〔13〕〔清〕熊赐履:《学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李振裕序。
〔20〕朱熹关于“敬”的更多话语,参见钱穆:《朱子学纲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5-101页。
〔22〕〔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3页。
〔23〕参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说明。
〔30〕“蓬莱涉海或可求,瑶水昆仑俱旧游。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岳曾向囊中收。不信开云扫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驾风骑气览八极,视此琐屑真浮沤”;“脚踏破履五十两,身披旧衲四十斤。任重致远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刚身。夜寒双虎与温足,雨后秃龙来伴宿。手握顽砖镜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来拾得遇寒山,翠竹黄花好共看。同来问我安心法,还解将心与汝安”;“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像这样一些不避禅道风格、直引禅语道言的诗,也在讲道体,只是难以轻易看出。〔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46-865页。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