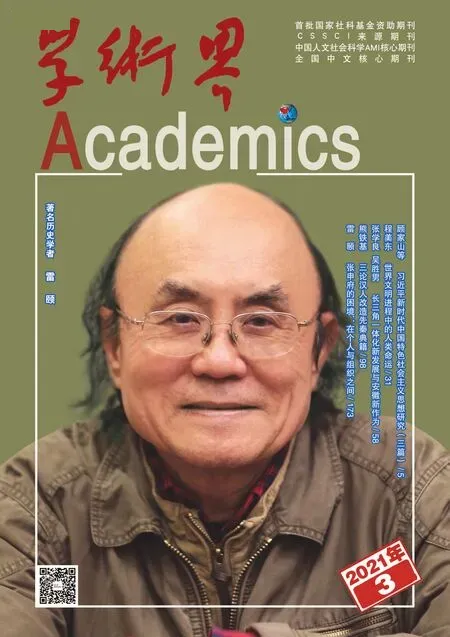三论汉人改造先秦典籍
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完成《秦汉文化志》〔1〕的写作之后,就开始考虑汉代学术史的问题,反复思考并曾与许多文史哲的年轻朋友一起讨论。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多次举行以新写论文为中心的研讨会。要写汉代学术史问题,当然首先要看的是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2〕,同时参考他主编的《古史辨》〔3〕等早年一些著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进行思考、讨论。2002年中安徽大学召开了一次历史文献学讨论会,在李学勤先生主持下,我作了一个“重新认识古书辨疑”的发言,同年12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2003年在我校学报百年华诞的特刊(第5期)上发表《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都是这种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在这后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经过了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甚至改造”,“汉代新的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与此同时,根据手稿记录,“2003.4.30下午开始(非常‘非典’时期)”写作《汉代学术史论》。到201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后10年。其中的一些章节曾以文章的形式发表。2005年7月1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就算正式提出来了。2009年8月因读到《文史哲》2009年第1期一篇文章〔4〕,而写了《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方法论问题》〔5〕。
这个问题的意义很大,少数学者,如史学理论专家李振宏同志,不仅关注而且有所发挥。〔6〕但是我觉得还未为较多的相关研究者所重视。这里我想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这个问题牵涉到先秦和两汉的学术文化思想,值得文史哲各方面的学者关注,涉及到有些问题需要改写甚至重写,因为留传后世的先秦典籍,都是经过汉人或多或少改造过的,已出土的一些先秦典籍或传世本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是被改造过了的,所以许多问题需要改写甚至重写。先秦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汉人如何改造?改造本身如何看?改造后的影响怎样?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意义重大,值得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者关注。
二、“改造”说比“伪造”说好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四处讲“改造”这个问题,2009年在台湾政大召开的“汉代文学与思想”研讨会上,我也讲了一下,有人提问“改造”说与过去的“伪造”说有何区别,我当时脱口而出:“改造”说比“伪造”说好。私下也有人和我说,用“整理”比“改造”也许更好一些。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如何看待汉代学术的问题。如果说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或者说“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体、主要内容的话,汉人的学问就是借先秦的经典表现的,故称之为“经学”。当时先秦经典就是五经、六经之类,其实也应该包括道经、法经、墨经等等,只是在“独尊儒术”之后,这后面的一些不太被重视罢了,其经典地位还是客观存在的。汉人在传承、解释、发挥先秦经典之义时,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从而有意无意地对典籍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改造,应该说大多是在整理过程中实现的,也不排斥少数的“伪造”。当然,“伪造”也有不同情况,如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之凭空伪造图谶,那也是极个别的,而借题发挥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顾颉刚先生对汉代学术问题的看法,有过较多的表述,例如他说:
现存的古书莫非汉人所编定,现存的古事莫不经汉人的排比,而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为谋他们应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来迁就他们自己,所以汉学是搞乱史迹的大本营。同时,汉代是迷信阴阳五行学说的时代,什么事都要受这学说的支配,所以不少的古代史迹被迫领受了这个洗礼。〔7〕
他也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自从晚清“新学伪经”的说话以后,许多古书像《左传》、《周礼》甚至《史记》、《汉书》都有了刘歆作伪和竄入的嫌疑,同时许多古史传说,像《月令》一系的五帝说,《左传》郯子所述的古史传说,羿、浞代夏以及少康中兴的故事,都有刘歆等人伪造的嫌疑。〔8〕
虽然这里明确说了“伪造”的话,但并不能概括成“伪造”说。顾颉刚先生的许多见解,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其作某种定性的概括,如同我曾说没有什么《古史辨》时代一样。〔9〕我写《汉人全面改造先秦典籍》也是如此,就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整理过程的改造,我在写《刘向校书详析》时有具体的说明,因为先秦以竹简为主书籍,单篇流传的情况很多,所以传承、搜集、整理中就会出现多种情况,保留下来的刘向所写的一些“书录”就可以说明,除了大量的文字错乱、篇目混淆等问题之外,义理上的问题就会明显地打上整理者的思想烙印,其《晏子叙录》〔10〕比较典型,这里再引述一遍并加说明: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一方面主观意识上目的性很强,“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可常置旁御观”;另一方面又有相对客观的整理之后,虽“不合经术”者,“亦不敢失”,予以保留。然而,篇幅更大的书籍,几十篇、几百篇,情况就更复杂些,这里就不一一详说了。总之,整理过程中是有不同程度改造的,涉及到书名、篇目、文字等多方面,是否“义理可法”就会使人有意无意地去改造流传中的典籍。
刘向的“义理”是“六经之义”,这是许多汉代学者的共同标准,当然也还有个人理解义理之不同。同样一部《诗经》,汉代人就有齐、鲁、韩、毛四家,学人就四家之异同进行过不少比较研究,“改造”典籍说的研究也在进行。这是一个大的方面。另外,也会有些非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学者,他们对儒家“六经”之外的经典如何整理?也是可以支持“改造”说的。目前,《老子》这个道家经典仍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的材料最多。虽然,《汉书·艺文志》所著《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和刘向《说老子》四篇皆亡,刘向校书时《老子》是什么样的?他看到过当今出土的当年流传的帛书本没有?均无从知晓,甚为可惜。但马王堆两种帛书本、郭店竹简本以及最近又有北大本的《老子》等实物资料,还有传世的《老子指归》《河上公章句》《想尔注》等等,足以说明《老子》在流传中被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上述《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也多少可以作为佐证。
总而言之,先秦典籍在汉代被全面改造过,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显然,仅仅只提“整理”,力度是不够的。“伪造”,甚至说汉人是“造伪能手”,似又有些过激。所以以“改造”说为好。
其实“伪造”或“造伪”和我所说的汉人改造先秦典籍并不是一回事。顾颉刚先生写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11〕,主要是讲古代一些人物、史事的伪造,当然也涉及古书所记人物和史事的造伪,特别是如三皇五帝史事的伪造。至于伪书,他注意到《汉书·艺文志》中就已经指出许多书籍是“依托”之作。这些和我所说的汉人改造先秦典籍不是一回事,但是又有关系,所以辨伪、辨疑的原则是相同相通的,例如顾先生在文章中说:
所谓“伪”固有有意的作伪,但也有无意的成伪。我们知道作伪和成伪都有他们的环境诱惑和压迫,所以也须认清他们的环境,辨伪的工作便已成了一半。
又说:
上面所讲的礼乐制度,我固然说它出于战国秦汉间人之口,很不可信;但我也敢做保证:这是不会全伪的。
还有:
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出这些谈话是不真实的上古史,然而确是真实的战国秦汉史,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捉住战国秦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就此在战国秦汉史上提出几个中心问题。
这些都是我讲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所想表达也曾不同程度表述过的思想和一些原则性的看法:传世的先秦典籍是不会全伪的;汉人的改造有“他们的环境诱惑和压迫”;我们辨疑出的问题,正好“捉住”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正好对汉代学术史提出几个中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改造”说的意义。
三、疑古与走出疑古问题
虽然我在有的文章中提到“走出疑古时代”的问题,老实说,我并没有拜读过有关的著作,不能妄加评说,只是模糊感觉到,这个问题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是有关系的,而我在撰写《汉代学术史论》时研读顾先生的著作,发现他晚年所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
又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历史,自宋至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这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12〕
顾先生说这些“过去”与否的话,应该是有当时背景的,说不定“走出疑古时代”就是从那时开始“走出”的,也许这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枝节”问题。
读了顾先生文章之后,我就更没有注意“走出疑古时代”的问题了,潜意识似乎认为:没有“《古史辨》时代”,当然也就没有“疑古时代”,没有“疑古时代”又何来“走出”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报刊上时不时又会出现一些讨论,什么“疑古”与“释古”,什么“古史辨派”,什么“疑古意义”,等等,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生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如此?这又给将来人留下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们现在还比较清楚,大体知道《古史辨》、“走出”之类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趁早把问题讨论得更清楚些,会更好一些,及时开展讨论是必要的。
疑,就是疑问,有疑必问,这才是学问。有的疑问是比较明显的,如出土文献《老子》与传世《老子》结构、文字等不一样,为什么?这是必然要问的。对此,人们必须作出回答,必须“释古”,我认为这就是汉人整理和改造的结果,要不然,那又是为什么呢?另外,对一些古代历史上的问题、古代历史人物、图书问题提出疑问,对一些问题作出解释,这也就是释古,或者说辨疑,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战国秦汉间人的辨伪”,“司马迁应为首功”。辨伪、辨疑工作是古已有之的,宋人、清人“疑古”之风不小,“疑古时代”何时开始?代表人物是谁?是写《天问》的屈原,还是宋人郑樵?再或者是崔东壁、姚继恒?
《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曾轰动一时,影响不小,但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顾先生说“《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被人们讲来讲去的问题,顾先生在世时已经发生,例如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写道:
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新的标准,凡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
也许当时就有人有这种派别的划分法,但顾先生也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这话也是客观的、正确的。
为了现在这篇文章,我再读了顾先生的几篇文章,越读越亲切,似乎思想更加明确一些。《古史辨》虽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的工作的确还需要继续做下去。我的思想就是要重新认识古书辨疑。
四、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因为读《文史哲》上浅野裕一的文章而引发我写“再谈”,曹峰同志希望我“再仔细些”谈对该文的看法,这里也不很仔细地谈,但可以谈点看法。该文从新出土文献的资料看思想史(主要是先秦思想史)应该改写,这原则上是对的,因《太一生水》《恒先》的发现说明学术思想出现有“同时性和多发性”,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看法,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这我在“再谈”一文中已经提到了。
浅野裕一之文的副标题是“兼论日本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日本学界的情况我并不很熟悉,我的疑问是:日本学界一直有“疑古派”和“释古派”吗?浅野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因为出土文献就可以对“疑古派及释古派各种观点的致命打击”,“颠覆”“元凶”“粉碎”之类的语言都用上了。在没有看到出土文献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可能有的说成没有,时间早的说成很晚,这是时代条件的局限所致,但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例如说“平冈武夫……认为《易》形成今天的格局是在汉以后,他同样推定《易》成为儒家经典是在进入汉代之后”。这种看法不能因为上博简中有58支《易》简,就“毫无成立之余地”。用我们“汉人改造先秦典籍”说看,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命题,特别是“成为儒家经典”的问题。另外,不知池田知久先生是否也属于“疑古派”?他关于“五行篇的研究”以及“《老子》编纂时间在战国末至汉初”等,当然可以具体讨论,但从典籍的“编纂”“成书”来看,明显地有汉人“改造”的痕迹,也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这些都属于“疑古”的话,我看这种“疑古”也是必要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传世文献及其影响,更好地认识汉代的学术和汉代人的思想。
出土文献是真实的,但出土文献所记事实是否全都真实?这仍然是可以疑问的,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点,如陈侯因资錞关于“黄帝”的铭文,画像石上的一些记载,还有墓葬中出土的《告地书》的记载,等等,不必再重复了。再说点新的意思,例如《老子》《太一生水》《恒先》说明先秦道家思想的“同时性和多发性”,可以“改写”这一部分思想史,但是除了我在“再谈”中所说还应该具体比较研究之外,又可以提问:为什么已有《老子》流传到后世了?《太一生水》《恒先》为什么未传?或者是如何消融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对汉代以及汉以后的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至于讨论出土文献的具体时间,鉴别稍晚一些就视为“疑古派”,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是用“疑古派”作为一顶“帽子”,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顾颉刚先生因为编《古史辨》在世之时和去世之后,都受到过不恰当的批判,在世时的情况,他的自述中有不少例子。去世之后,如果硬要弄出一个“疑古时代”,他会首当其冲的,但“疑古时代”不能成立。学术研究怎么不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呢?学术研究中,有的是主要方面是对的,细节中有可商榷之处;有的是主要方面或许不对,具体论述中又有可取之处。不一棍子打死,是有利于学术讨论和发展的。
五、“改造”说与出土文献
“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提出来,对准确地认识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有重要意义,对理解整个中国古代传统的学术文化也有重要意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种种不同,能够更好地说明“改造”问题之存在,所以我说:出土先秦文献越多,我的“改造”说越“正确”。现在知道的《易经》既有帛书本,也有上博楚简本;《诗经》也有竹简本,还有先秦文献中的许多轶诗;《书经》《礼经》的出土文献也有消息。一方面已出和新发现文献的深入比较研究,比较其与传世文献的异同,可以提供给“改造”说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进一步清理汉人对先秦典籍的传播和整理,将更具体深入地说明“改造”说的多方面内容。
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与传世的先秦典籍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属于某一经典,甚至是另有留存的。学界已分别作了不少研究,例如上面提到的《太一生水》《恒先》的研究,还有《六德》《语丛四》《性自命出》等的研究,有更早开始的关于帛书《五行》以及竹简《五行》的研究,等等。许多研究中都透露出汉人“改造”的信息,《六德》的研究就是如此,李学勤先生在《郭店楚简〈六德〉的文献学意义》〔13〕中说:
六行本于六法,六法又源于德之六理,这样的观点是《五行》全然没有的。可知贾谊虽然引据了《五行》篇,但对五行之说作了很大改造,甚至面目全非,并不是简单的移用。
贾谊《新书》之于《六德》,情形也是如此。
徐少华先生在《郭店楚简〈六德〉篇思想源流辨析》〔14〕中说:
《六德》的有关论述上承孔门,下启汉儒,具有明显的中间桥梁作用……在孔子言谈中有源可寻,而又开汉儒“三纲六纪”、“三从四德”之先河;不同的是,简文所论和语意皆较纯朴,未见汉儒所极力宣扬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
刘乐贤先生的《郭店楚简〈六德〉初探》〔15〕又是另一个视角,他认为“以往的儒学史研究,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在史料运用上颇受限制”。先秦儒学研究“局限于《论语》、《孟子》、《荀子》三书”,指出“也应重视《说苑》、《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书所保存的一些早期史料”。他是找出了“六德”在这些书中的对应文字。
我引用这么多论述,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六德》这样的文献,在汉代终于被淘汰了,它的思想内容被汉人吸收和改造了。汉人会用《新书》《说苑》《韩诗外传》等等,以“改造”的方式来表述其思想,也完全可能在编定原有各种典籍时来反映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想,对典籍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
关于儒家思想的著作是如此,关于道家思想的《太一生水》《恒先》等也是如此。我们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汉人对这些典籍内容的融撮与改造,例如,我在《对“神明”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曾指出,《太一生水》中的“神明”在严遵《道德指归论》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其实,汉初的《淮南子》一书,对先秦的许多道家思想,有比较广泛全面的继承,其“道论”之发挥也是很全面、很丰富的,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典籍的传承与整理。《老子》之称《道德经》,由明显的“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转变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仍有深入研讨的价值,我在《从〈老子〉到〈道德经〉》一文中(《光明日报》2007年6月1日),初步阐述了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能找到这个“改编”的“第一人”,从而分析其改编的原因与意义,那就更好,当然这不是很容易的。从出土文献看,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甲、乙本《老子》是不容质疑的,竹简本则有一个“编连”的问题,文字的释读更复杂,这是考古工作和简牍研究者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
这里我顺带谈谈我对出土文献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前面提到浅野裕一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中写道:“在中国,不作战国楚简研究的学者,被认为是‘落伍的学者’”,我就是这样的“落伍者”。简帛学专家陈伟教授偶尔请我去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知道我是“落伍者”,却帮我解嘲说我是“宏观把握”。我之所以“落伍”有一些原因,这里不能多说。但并非我不关心出土文献的研究,现在为了我所提的“改造”说,就急迫地盼望清华简中的《尚书》赶快整理出来。我主张对《诗》《易》乃至与《礼》有关的出土文献作深入的与传世本的比较研究,希望简帛研究者、历史学者、思想史专家共同努力。研究将有利于“汉代全面改造先秦典籍”之说的更加完善。
注释:
〔1〕大型丛书《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第一典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后改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3〕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后有罗根泽等人续编,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七册。
〔4〕〔日〕浅野裕一的《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
〔5〕《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
〔6〕他在《光明日报》《河南大学学报》上都写有文章。
〔7〕顾颉刚:《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顾序”,第21页。
〔8〕〔12〕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29页。
〔9〕参阅《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4日)等文章。
〔10〕〔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32页。
〔11〕顾潮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14〕〔15〕《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375、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