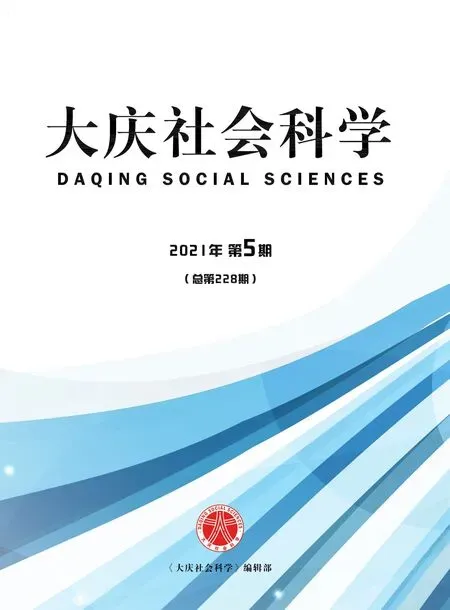试析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丛林精神
夏 丹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9)
一、丛林精神的内核:坚韧独立的民族精神
丛林精神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主题,它的内涵是澳大利亚人坚韧独立的民族精神。澳大利亚的开拓始于荒野的丛林,那些开拓者在艰苦奋斗中陶冶出的优秀品质,延伸到了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面。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具有一种表现坚韧、奋斗和崇尚自由的特征,这些鲜明的澳洲特征恰恰是人与环境斗争的经历体现,直接作用于澳大利亚人的性格上。
亨利·劳森,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丛林意识最为强烈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有意或无意识地描绘了丛林生活场景,这是丛林精神影响劳森的真实表现。在 《赶牲畜人妻子》 《丛林儿童》 ,以及 《伙伴情谊》 等文学作品中,亨利·劳森将丛林主题贯穿每个作品中,他试图通过冷峻的笔触描写荒凉恐怖的丛林环境,来凸显人与自然的斗争险恶,以此塑造丛林人物的坚韧独立的精神。例如,在短篇小说 《赶牲畜人妻子》 中,丛林女人不仅成功的在艰难的丛林中生存下来,更成为了丛林的征服者。亨利·劳森真实反映了丛林里艰辛的生活环境,充分展示出丛林人的坚强勇敢精神,这些精神也正是澳洲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1]再者,凭借处女作小说 《我的光辉生涯》 ,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坛先驱的迈尔斯·富兰克林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位丛林少女西比拉心理成长过程的故事,女主人公西比拉在与外部环境抗争中始终表现出意志坚定以及独立自主的精神面貌。以小窥大,这些作品中的丛林精神映射了澳大利亚整体的民族精神。
坚韧独立的民族精神,不仅在澳大利亚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在澳大利亚诗歌中同样有所表现。以佩特森的叙事长诗 《来自雪河的人》 为例,佩特森在诗中展现了独具澳洲特色的乡间艰辛生活,诗歌讲述了生活在这里的一个瘦小青年冲破艰险和打破偏见,凭借自身的勇气和驯马技巧,独自一人驯服野马的故事。纵然山上灌木丛生、道路崎岖、山涧陡峭,但雪河青年仍以猛虎下山的气势直落谷底平川。佩特森在这首诗中讴歌男性的力量和坚韧拼搏的精神,属于澳大利亚文学中典型的丛林精神。
丛林精神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一个标志,它从侧面反映了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内核。丛林精神是澳大利亚文化价值观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直至今天,它对澳大利亚文化与社会依然产生着影响。
二、丛林精神的衍生物:“伙伴情谊”的民族文化
“伙伴情谊”多指男人之间,尤其是在困境之时,男人共同战胜困难所感受到的深刻的手足情谊。“伙伴情谊”发端于丛林精神,是澳大利亚早期丛林生活的衍生物。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早期的澳大利亚丛林人在共度难关时,形成了一种同甘共苦的伙伴情谊,正如亨利·劳森在诗歌 《剪羊毛工》 中所写:“艰辛、干旱和无家可归,教育了丛林人要相互友爱;伙伴情谊来源于贫瘠的土地,来源于操劳、干渴和危险。”“伙伴情谊”被称为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男性行为模式,它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的一种民族文化,时常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中。
小说 《伟大的世界》 是戴维·马洛夫的重要作品,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人物:维克·科伦和迪格·基恩。他们同时在马来西亚被日军俘虏,在马来半岛和泰国的战俘营里共同经历生死浩劫,最终获救回国。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谈不上友情,却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便是作品着重刻画的“伙伴情谊”,虽然两人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敌意,但这种敌意恰恰是维克和迪格之间更为深厚的伙伴关系的反面表现。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男性作家才会关注“丛林精神”的“伙伴情谊”,女性作家的创作视角也会有意无意聚焦到此关系。以澳大利亚当代女性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为例,在 《荆棘鸟》 这部小说中,卢克与劳动伙伴阿恩的深厚关系属于“伙伴情谊”。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卢克与阿恩共同割甘蔗挣钱,形影不离。女主人梅吉曾为此恼火,她认为卢克应该和阿恩结婚,因为相比妻子,卢克更喜欢他的同伙。事实上,在情感的重要性上,阿恩的重要性确实远过于梅吉,否则,卢克不会在妻子离开时,心里仍不忘他的老伙计阿恩。从卢克的行为表现看出,卢克与阿恩的关系正是澳大利亚文学上特有的“伙伴情谊”,这种情谊属于典型的澳大利亚男性行为模式。此外,在考琳·麦卡洛的另一部小说 《摩根的旅程》 中,男主人公理查德·摩根被诬陷,成为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首批重罪犯。当他面对澳大利亚的群山林海时,他没有垮掉,而是被激发出了与众不同的“丛林精神”,他与其他犯人们在这片蛮荒之地建设起新的家园。正是澳大利亚的存在,才会让主人公理查德·摩根斯与蒂芬·多纳万成为了一生的挚友,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切感情的融合。[2]
诗歌方面,同样以诗人佩德森的诗歌 《来自雪河的人》 为例,这首诗完美再现了“伙伴情谊”的内涵,当那匹价值不菲的小马迷失在丛林中后,那些有名和无名的骑手纷纷赶来帮忙,当青年独自追赶马群时,那些处在高地的骑手纷纷为他呐喊。以此看出,佩德森在诗中将丛林男人们的患难与共,伙伴间的互助情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伙伴情谊”的发展不再是求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信条逐渐深入人心,它产生的深远影响涉及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象征。
三、丛林精神的悲剧性:女性“他者”的弱势地位
“丛林精神”通常被宣扬为正面的、健康的民族性产物,“伙伴情谊”中的平等主义思想也促进了澳大利亚民主的发展。但是,澳大利亚的女性作家对男性作家构建的澳大利亚文学表示不满,因为“丛林精神”的“伙伴情谊”是在排除女性、同性恋者以及土著居民等不同人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丛林精神”存在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其中最明显的是折射出了女性作为“他者”的弱势地位。特里·考林甚至认为,“丛林精神”的“伙伴情谊”意味着粗暴以及对“虚弱的”情感的一种蔑视。
首先,以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 《赶牲畜人妻子》 为分析对象,这位丛林妇女在险恶的丛林生存环境中,始终勇敢坚强地面对生活的一系列困难。小说表现出了丛林女性忍耐与勇气的精神,刻画了一位拥有劳动妇女美德的丛林女性形象。但是,透过女性伟大形象的表面背后,深入作品的深层结构,我们会发现另一种文学效果。丛林母亲的完美形象暴露了作者亨利·劳森的男权思想,这位丛林妇女至始至终没有走出男权的藩篱,她被囿于家庭中,没有选择生活的自由权利,她不知不觉中成为男性的 “他者”,这是女性的悲剧,体现了女性在“丛林精神”中的弱势地位。其次,聚焦点转回 《荆棘鸟》 这部小说中,梅吉与卢克婚姻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金钱,它还因为卢克排斥女性的情谊,与劳动伙伴阿恩相比,梅吉作为女性的陪伴是微不足道的。这不仅是作为女性梅吉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无数个在“丛林精神”背后的女性悲剧。当戴恩意外死亡后,梅吉认识到,女人没有一个能打败上帝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是一个男人。梅吉想要幸福的生活,她与男性、与命运艰苦的抗争,结果确是仍然没有逃脱掉男权的藩篱,自己仍是弱势的“他者。”[3]
“丛林精神”是平民们在一种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艰辛的生存条件中形成的品质。但是,“丛林精神”存在男权意识,使得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均对澳大利亚文学中包含的情感缺失做出过批评。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正是“丛林精神”的存在唤醒了弱势群体的觉醒意识,让“他者”能够重构自己身份,再现自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