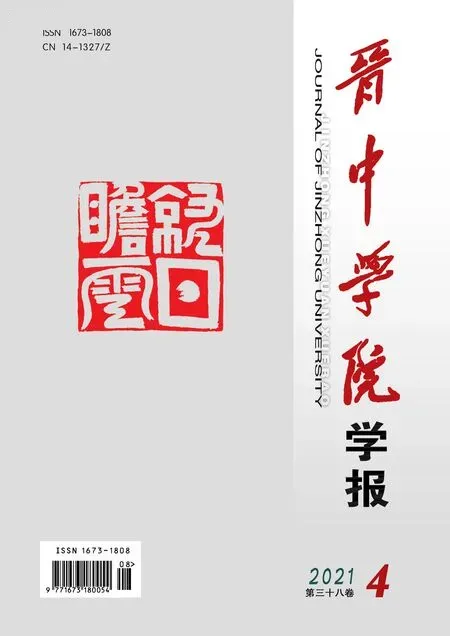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使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刘长明,宋泽楷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八千年前,青帝以八卦辟混沌而开文脉,天生地养,后冠之以中华;五千年前,中原以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据欧亚东郊而化四方蛮夷;两千年前,秦始皇揽八表同风,开中华大一统之格局,立千秋伟业;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开天辟地,挽革命于颓势,救黎民于水火。纵观古今,中华文脉因“使命”而浩瀚磅礴、延绵不绝。从家庭宗族到国家社会,每个中国人心中都秉持着一份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历经千年,薪火相传,最终内化为民族的文化自觉。诞生于革命战火中的中国共产党,承袭了中华文化的正统,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己任。使命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脉伴随着阶级与历史的变迁,也拥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主体。
一、使命感是传承千年的民族基因
汉字,以特有的形式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相传仓颉为黄帝官吏,深感结绳记事不便的他“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遂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的传奇,此后华夏子民跨出蛮荒步入文明。汗青碑文历历在目,十三经与二十四史永世流传,仓颉当初肩负的启迪民智的使命,如今又依托于汉字薪火相传。“上天有好生之德”(《论语·颜渊》)、“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中华文化最重传承,每个中国人自出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传承的使命,而汉字从最初只是纯粹的使用工具发展到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其所承载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
中华文化有两个代表性符号:汉字与《周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系辞下》)“三才之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核,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覆盖了人伦日用的各个方面。自鸿蒙初开至春秋战国,“三才之道”贯穿其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左传·成十三年》)这时的使命是遵守动作礼义威仪,目的在于维持命数。“三才之道”,人居其中,头顶一片天,肩负天赋使命,哪怕贵为天子,也只位居九五。天子治国,是肩负替天行道的使命,千古一帝秦始皇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见天道、使命影响之广远。于百姓言:则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天、道、人的概念构建了古人的使命架构,即顺天道,尽人道,是故八卦而六十四卦,除却乾坤两卦,其余皆是人之道。自古以来,帝王上承天道以家国一统为使命,百官承袭圣谕以造福一方为使命,百姓供奉手泽以光宗耀祖为使命。中国的使命感文化,初显于汉字、《周易》,却不止于汉字、《周易》。恰如鲁迅先生所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22这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民族基因使然。
二、使命文化的历史流变
在大历史观的视角下,传统的中国使命文化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齐头并进:一条伴随着社会主导阶级的变迁,使命文化的实践主体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也呈现出向基础阶层下移的趋势;一条伴随着政权的更迭,使命文化的内容在客观上呈现出民族化、大联合的趋势。
(一)使命文化的话语权与实践主体的变迁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178文化因此具有阶级性,使命文化的话语权与实践主体也因此只局限于当时的统治阶级。
东周以前,由于文化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使命文化的话语权只掌握在少数奴隶主手中。世人多认为既定的规则是源自天道与诸神,毫无疑问地遵循现有的制度就是世人最基本的使命。《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方命厥后,……殷受命咸宜。”此时的使命,是奴隶主奴役压迫奴隶合理化的文化工具,平民奴隶只知“命”而不知“使命”。至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室日渐式微,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阶级大洗牌登上舞台。农业生产的划时代发展,生产方式的变更,使一部分士大夫、平民的思想觉醒。其中,墨子与孟子对传统的使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墨子对使命文化的发展有以下几点贡献:第一,“尚贤”的提出否定了世袭的观念;第二,“非命”的提出鼓励广大劳动者摒弃逆来顺受的思想,敢于同命运抗衡;第三,“兼爱、非攻”思想以及“止楚攻宋”等实践让底层平民认识到即便布衣出身,组织起来依然可以影响一国之存亡。三点合于一处,指出了社会底层劳动者成为使命实践主体的可能性。此外,墨子带头“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塑造了墨者“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若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七十列传·游侠列传》)等富有极强使命感和担当的形象。与墨子牺牲个人而成全社会不同,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明确地指出了君子的使命与担当,对社会责任意识的较大范围觉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比激进的墨学,新兴的地主阶级更愿意接受与自己阶级诉求更近的当时的儒学。这样,使命文化的实践主体从曾经高高在上的天子诸侯等大奴隶主下移到了曾经的士大夫和平民。尤其是明清以来,封建制度逐渐僵化,阶级固化难以消解,农民百姓认识模糊,浑浑噩噩,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完全隔断,农民成为使命与担当的绝缘体,成为地主阶级使命文化话语权下的附属品,诸如太平天国运动这类带有使命色彩的农民运动,最终也不过归入封建罢了。即便如“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的忠孝一体理念,其最终落脚点依旧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忠”。直到“文化革新运动”[3]558的五四运动的开展,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才真正开始成为使命文化的实践主体,人民才有了直接行动的希望[4]。
(二)使命文化在国家层面的继承与发展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在周朝,世人尊称最高统治者为天子,所谓天子,指受天命而立、“父天母地”(《白虎通义》),肩负着“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使命的领袖。《左传·昭七年》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七年》)的贵族世官世禄之制[5]16。为了巩固周室的统治,周天子采取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左传·桓公二年》)的措施,使家和国通过宗法的血缘关系首次紧密相连,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思想。儒家有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6]399、“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6]14,表明了原本出于宗族情怀的使命与担当已经延伸至国家层面,家族与国家也因此形成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然而,家国同构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必多说。另一方面,统治者与家国同构也呈现出相异化的趋势:亡国就要亡家,从这一点来看,统治者肩负保护一国的使命,在最局限的范围内,也是作为家长保护家族成员的使命。
家国同构的观念下,针对如何稳固统治,如何用民的问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民本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自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民心的重要性,为了维护统治、名垂青史,统治者不得不将“民本”立为自己的使命。从“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再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民对于稳定统治的重要性,而民本思想恰是解决如何用民问题的最有效工具,于是,民本思想被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其兴,在于立君为民、与民休息;其亡,在于横征暴敛、渊鱼丛雀。因此,开明的统治者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会以“爱民如子”标榜自己,尽可能地去践行自己作为帝王应当担负的“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使命。
家国同构与以民为本的目的无不在于实现和巩固大一统的格局。大一统思想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先秦之际已有关于大一统思想的诸多论述,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荀子·霸言》)“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戎翟荒服。”(《国语·周语上》)诸如此类,形成了带有大一统萌芽色彩的天下观。及至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始皇本纪》)开帝制,始称皇帝。此后,统治者便多了一项“大一统”的使命。
中国的封建王朝几度更迭,在某方面却有着十分惊人的稳定性: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统治阶级的相对稳定、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这一切的稳定,使使命文化在国家层面得以延续与发展。家国同构思想、民本思想和大一统思想,在客观上逐渐突破了家族、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实有人类社会大联合之趋势,造就了中国人民对国家概念独有的认知。
三、中国共产党对使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使命文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其僵化是注定的。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的抱负难以有生存的土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祖训被抛之脑后,传统使命文化陷入低潮,亟待革新。
(一)传统使命文化的历史评价
传统的家国同构思想、民本思想甚至是大一统思想,围绕的核心都是地主阶级,梁启超曾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谈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可见所有的思想,于其主观而言,都不过是为了维护作为皇帝的身份并实现对百姓长久而隐晦的压迫罢了,区别只在于明君将百姓置于温水之中,昏君将百姓置于碳火之中,同是压榨,一般无二。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统治者作为地主阶级,其本质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压榨,前文所提的家国同构以及大一统思想,最终目的皆在于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建立属于自己和所属家族的千秋伟业,这种使命与担当具有相当程度上的落后性与狭隘性。相较之下,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来看,民本思想在客观上叩击了近代民主的大门。但民本思想仍具有不可否认的局限性:民本思想中的“民”本身就带有阶级歧视性,在古代话语体系的演变中,“民”在金文中最初意为“挖去双眼的终生奴隶”[7]8,即便到孔子生活的年代,“民”依旧包含下等人的意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世》)直至战国时期,“民”才被重视起来,例如“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即便如此,重“民”只是统治者用于巩固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如何用民,在于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对百姓进行长久的剥削。君与民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与矛盾;民本思想的根基并不稳固。
(二)中国共产党对使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了“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这是由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首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39这与以往的奴隶主、地主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拥有庞大的实践主体。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封建社会,“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连同雇农,却没有或只占有少量土地”[9]5。而在五四运动前,我国产业工人也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左右[9]11,农民渴望翻身的诉求与工人阶级的崛起预示着传统使命文化将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并迎来新的实践主体。
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余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青树,共产党人以批孔起家,却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一切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534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708-709同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根本上同以往地主阶级的民本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划清了界限,实现了传统使命文化从用民到为民的历史性突破。概括而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将传统使命文化也一并接引过来,并使其具备了无产阶级的进步属性。作为融贯古今中外先进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因此也就成为科学使命文化的开拓者。
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使命与担当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共产党人。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服务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10]136,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她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对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实现了从君民到人民的跨越——君民的话语体系本身就体现了带有两个主体的不平等的阶级对立性,而人民则是一个阶级,一个主体,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在于目的的转变。民本思想最终还是君本思想,民本思想的意义在当时只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与剥削,民本只是手段,君本才是目的。而人民,意味着目的与途径走向了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人民使命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在于中心的转变,传统民本思想在于统治平民,其中心一直围绕着地主阶级从未改变,而新时代“人民至上”的思想则以人民为中心。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家国同构思想和大一统思想的辩证发展:以家国的概念重构了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大一统发展为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使命与大国担当。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0]433,再一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大党的使命与担当——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历史的嬗变不断丰富着使命的内涵,“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10]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