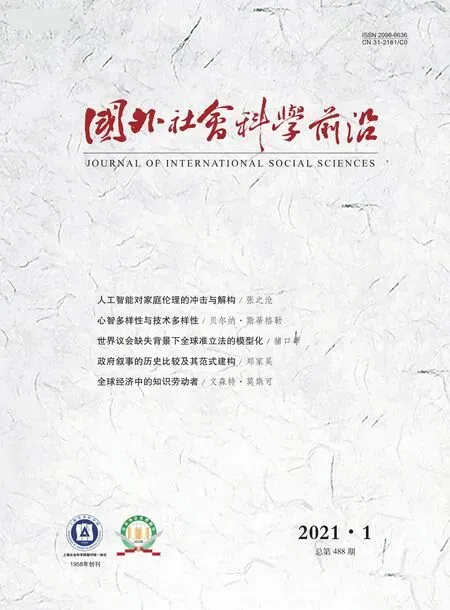阿甘本“生命—形式”范式的建构逻辑 *
刘 黎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生命政治理论表达了对世界政治再次遭遇“奥斯维辛”到来的担忧,他认为要躲过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不是求助于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引领,比如上帝、耶稣、救世主,也不是诉诸某种具有革命潜能的伦理主体或主权逻辑的彻底变更,亦或等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与崩溃。相反,他的救赎计划既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又具有政治本体论的意蕴,既表达了对弥赛亚事件的期待,又设想了一种“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亦或“即将来临的政治”。无论是弥赛亚事件还是即将到来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主权活动来思考躲避生命政治装置的控制,即思考一种生命与其形式不相分离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正是由于生命与其形式的紧密相连,致使主权逻辑无法再生产出赤裸生命,无法再迫使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bios 与zoē 相分离。因此,“任何不以主权逻辑为基础的未来政治必须使用这种生命概念,即不是基于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zoē与bios 的司法分离,也不是从赤裸生命中涌现出来的生命。相反,而是,必须使这种分离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生命—形式(form-of-life),在那里,生命的神圣性是被阻止的……不是要在共同体中建立司法包容性,这种结果无一例外是排斥的和暴力的……取而代之的是在神圣和亵渎之间的区分变得无效,不起作用,以至于神圣不再被用作于排斥机制。”①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2.
一、“生命—形式”结构体的语义内涵
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是欧陆哲学与科学哲学中的传统技术术语,该术语经常为20 世纪的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所用,它的语义内涵不同于20 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思潮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生活风格”概念,“生活风格”概念常被运用于文化哲学、精神、心理学方面。维特根斯坦与阿甘本在哲学兴趣与研究方向上存在很大差异,维特根斯坦哲学主要关注于逻辑学与语言哲学问题,而阿甘本对传统政治哲学、美学、宗教、伦理学、传统本体论问题感兴趣,但是维特根斯坦在阿甘本哲学研究道路上,尤其在阿甘本神圣人计划后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阿甘本的核心术语“生命—形式”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启发,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对遵循规则、“用”的重要性的强调,也对阿甘本能够在圣方济各会的隐修制度与生活方式中讨论反“有”的“用”的生命—形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对于其生活形式(form of life)概念并没有进行详细而又具体的界定,与其说他试图明确地定义其概念,还不如说他更加强调概念的使用过程。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两个基本点:第一,生活形式概念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高频率词汇,而且德语Lebensform 、Lebensformen、Form des Lebens(生活形式)中的Leben 具有双重意义,这有点类似于阿甘本对生命(life)bios 与zoē 的区分。Leben 既可以表达为中文中的“生命”概念亦可指示“生活”概念。这两个相异的Leben 内涵,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考古学式的界定,因此,将其理解为中文语境中的“生活”是有缺陷的,而是应该在“生活”与“生命”的两层意义上来把握维特根斯坦的Lebensform 范畴;第二,维特根斯坦不主张对概念进行定义,而强调应该在具体实践过程、具体使用背景中来把握其本质性的特征。对于生活形式,他将其置于语言分析过程中,生活形式概念在其著作中出现得寥寥可数,然而却在很多场合下是被应用于语言之中。因此,语言是理解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概念的主要基础,也是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最重要的理解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等等 。①[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12、17 页。这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生活形式关系的直接描述。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考察集中于语言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语言对世界的展现,但这不是一种抽象的、静态的、形而上学式的语言分析,而是一种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的语言游戏问题,即人在语言游戏中如何表现其主体性、如何对语言做出相应的反应,人的诸种情感、行为如何与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这就是说,语言不再是作为纯粹的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是人类实践活动、生活形式的表达与描述,语言需要脱离对词、命题、句子、意义、本质的固守,从而转向在人类生活不同语境、背景、环境中的运用与使用。费迪南·费尔曼(Ferdinand Fellmann)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指的就是“‘使用’,……说明了通过运用和习惯稳定下来的内部的行为和态度方式。这里没有产生出形式,也没有预给形式,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形式得到了私人情感的多变性并为这种多变性增加了一种内心的、可以设想的态度行为方式。”②[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华夏出版社,2000 年,第194 页。换言之,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呈现出多变性,在必须遵守相应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又可以在这种多变性与规则中衍生出另一种或多种意义,这也就是生活形式的演变过程。既可以促使某种行为方式得到保留,又可以在陈旧的行为方式中创造出全新的行为方式,生活形式也就预示着诸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虽然存在着诸多类型的解读方式,但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在论述其生活形式过程中将其与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是在语言游戏中探寻生活的内容与生命的意义,这对于阿甘本而言也是如此。阿甘本对语言与生命问题的关注一直贯穿于其整个思想研究过程。
对于生命—形式结构体,阿甘本在意大利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forme di vita”与“Forma-di-vita”,在英语、法语中一般将其转译为form-of-life,或者Forme-de-vie。生命—形式(form-of-life),阿甘本将其视为赤裸生命的对立面,一种具有完全意义的生命,一种司法政治无法捕获的生命,一种纯粹的人类生命,一种摆脱法律掌控的生命。从书写形式上来看,生命—形式(form-of-life)中的生命与形式之间以连字符形式书写,以强调生命与形式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明显地体现了海德格尔的表达风格。从内容上来看,阿甘本与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模糊定义不同,他将其界定为“一种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一种永远不可能隔离出某种类似于赤裸生命的生命。”③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p. 3-4.从语言差异的角度来看,生命—形式(form-of-life)异于生活形式( forma vivendi)、生命形式(forma vitae)、生命或法则(vita vel regula),生命—形式既不是生命的形式,也不是诸种生命形式,它是以单数形式而存在的生命—形式。“生命—形式(form-of-life)对立于以捕获zoē 为主要目标的生命的诸种形式(forms of life)……生命的诸种形式(forms of life)描述的是权力装置界定和控制生命的诸种方式。这种复数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确认了主权权力对生命的断裂与控制的多种方式。然而,生命—形式(form-of-life),是一种单一的生命,一旦分裂生命变得无效,那么这种单一的生命就会涌现出来。”①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2.生命的诸种形式呈现的是主权逻辑与生命范畴之间的捕获、控制关系,亦或是主权权力模式萃取生命内容的各种迥异的方式,它最终指涉的是主权对生命的否定关系。而至于生命—形式,虽然阿甘本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其是以抵御zoē 的政治化为目标,反抗bios 与zoē 之间的任何分离,但是阿甘本并没有赋予其任何具体性的内容,而是在与赤裸生命的对立关系之中来确认此种生命。因此,它只能通过其对立面来获得自身的内涵与指向,这也就意味着它通常是以一种潜在的、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其对立关系之中,只有当其对立面变得无效、变得不再起作用时,它才会露出真实面貌。生命—形式也就成为了阿甘本对那些误认为其是悲观主义者的反击,它也是阿甘本对人类生命摆脱生命政治法律逻辑控制的有力探讨。如果西方政治无法再离析出生物性存在的赤裸生命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崭新的政治与伦理学的到来,这就是即将来临的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就是一种幸福生活,“一种绝对世俗的‘充足生活’,这种生活使其自身的力量与可交流性达到了完美境地——一种凌驾于主权之上的生活,一种主权不再具备掌控生命权利的生活。”②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p. 114-115.生命—形式也就预示着一种“幸福生活”的到来。在如何发现生命—形式的问题上,阿甘本很抽象地言说道:“只有在某种生命的形式的事实性与物性中存在一种思想时,某种生命的形式才会转变为生命—形式,即在其中绝不可能离析出某种类似于赤裸生命的东西。”③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 9.阿甘本预设了生命—形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思想。思想是生命的诸种形式转变为生命—形式的媒介、中介,某种单一的生命的形式可以转变为生命—形式。因为思想本身具有“一种体验,一种实验”,而在这种体验与实验中,“它把生命以及人类智力的潜能特性视为其对象。”④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 p. 9.这是但丁意义上的思想权力,该种思想权力即是“使生命不断地与其形式重新联合,或不断地阻止生命与其形式的分离。”⑤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 11.“ 思想即是生命—形式,这种生命不能与其形式相分离;这种亲近的不可分离的生命可以出现在物质过程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物质性中的任何地方,在那里,只存在思想,在理论中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这种生命—形式……必将成为即将来临的政治的指导性概念与统一的中心。”①Giorgio Agamben, Mean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 2000, pp. 11-12.阿甘本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对生命—形式的简略而又抽象的分析上,他设定了一种生命—形式的典范,即圣方济各会的隐修生活形式,从而开启了从权力形式向生命—形式的政治神学思考。在圣方济各会的隐修生活与制度形式中,重要的“不是规则,而是生命,不是宣称信奉这种或那种信条的能力,而是以某种方式生活的能力,即愉快而又公开地过着某种生活形式的能力。”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3.阿甘本强调的是圣方济各会的生命与生命—形式,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规则或形式,这是反抗生命政治逻辑的巅峰体现,而圣方济各会隐修规则中的“最高的贫困”与“使用”的生活方式即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具体的生命—形式。
二、生命—形式的典范:“最高的贫困”
阿甘本生命—形式最基本的特征即是不受法律的控制,不是规范应用于生活或生命之中,而是生活或生命被应用于规范之中,在规范之中生存,或者说,形式、生命、规则进入了无差异的门槛地带。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把某种形式(或规范)应用于生命的问题,而是按照那种形式去生活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形式,接下来,让生命本身成为形式,并与之相一致。”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9.至于此种生命—形式类型的体现,阿甘本将其追溯到了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而且他直接地将圣方济各会中的隐修规则及其僧侣生活方式视为生命—形式的典范,认为圣方济各会中的法外生活规则为人类行为方式、追求“幸福生活”指明了方向。
与福柯晚期转向苦行传统类似,阿甘本对基督教隐修制度的探讨旨在“通过隐修生活的典型例子的研究——构建出一种生命—形式,也就是说,一种与其形式联系得如此紧密的生命,以致于这种生命与其形式无法分离。”修道院中僧侣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与必须遵循的诸种规则是思考阿甘本意义上生命—形式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规则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界定了一种装置,通过这种装置修道士们藉此来实现他们共同生活形式的理想。”④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因此,阿甘本认为正是隐修生活方式中对僧侣们的最细微、最直接的生命调节,使得规则、法律、仪式、生命之间变得模糊,使得僧侣们的生活实践成为“无差异领域”,世俗法律的禁止界限与修道院中对僧侣们生活的塑造变得不再可分,隐修规则脱离了其原初的禁止与惩罚的设定而演变为对僧侣们生活方式的最精细的关照。阿甘本试图通过对中世纪圣方济各会运动中僧侣们的共同生活的分析而努力探寻逃离现代政治法律机制对生命捕获与控制的机会,思索避免沦为赤裸生命命运的出口,最终摆脱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相一致的陷阱,走出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的逻辑框架。阿甘本对基督教早期隐修制度或圣方济各会的生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持有这样的立场,他们在努力地追求生命与其形式的统一,“坚持不懈地接近它的实现”,但是又“一直在错过它。”①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ii.虽然圣方济各会最终失败了,没有实现其生命与形式的完全统一,但这不会对阿甘本将其视为生命—形式的典范造成阻碍,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阿甘本对圣方济各会禁欲传统的描述集中关注了其贫穷状态,这不是从司法政治角度出发,也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来看待贫穷问题,而是认为贫穷言说着一种生命状态,一种存在状态。因而,阿甘本试图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来重新审视基督教生活模式,思考圣方济各会的行为方式。在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他们自愿选择贫困,他们的贫穷是一种“至上的贫穷”,“最高的贫穷”,不拥有任何权利,不占有任何东西,这就是圣方济各会的典型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罗马教廷的强烈反抗。
对于“贫穷”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第一,从修道院修道士的穿着习惯(habitus)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光鲜靓丽、绚丽多彩的衣物与装饰,但也不至于衣衫褴褛,他们有着自身的一套服饰规则,倾向于简洁、朴素的着装。阿甘本认为习惯(habitus)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存在方式或行为方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习惯变成了美德的同义词……似乎越来越多意味着穿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引导自己的方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在修道院隐修制度中,习惯渐渐地演变为一种着装习惯、生存状态,并与行为品德、指导自我的方式变得密切相关,这种装束习惯“已经呈现为一种教化过程,使得他们成为一种美德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或寓言。正因为如此,对外在着装的描述,就等同于揭示了内在的存在方式。”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阿甘本认为外在修饰的素雅、简单也就意味着个体内心存在的单纯、天真。在这个意义上,修道士的“贫穷”指涉的是服饰习惯的简单化与纯洁化对生命内部活动的隐喻,“贫穷”也是修道士形成此种生活习惯的前提条件,而不只是对着装简陋、材质粗糙的表达。“因此,僧人们日夜穿戴的小兜帽是让其‘不断保持小孩的纯真和天真’的训诫。亚麻长袍的短袖‘暗示了他们已经中断了这个世界的行为和工作’。穿过腋下的细羊毛绳使衣服紧紧地贴在修士的身上,表示他们已经为所有的体力劳动做好了准备。他们披在衣领和肩膀上的小披风或外套象征着谦卑。手杖提醒着他们‘他们绝不能在众多的恶犬中赤手空拳地走出去’。他们脚上穿的凉鞋代表着‘我们灵魂之足……必须时刻为精神上的竞技做好准备’。”④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15.修道院生活习俗把服饰转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样态,即着装与生活方式的不可分离。而且,“只有在修道院生活中,我们才可以目睹到服饰的各个要素被彻底教化。”①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因此,在阿甘本看来,隐修制度中穿着习惯的“贫穷”既是修道士们共同坚持的生活规则,也是事实上的穷困状态,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在这种贫穷中,他们能够获得一种纯真的、单纯的生活模式,这是贫穷造成的结果,也是趋向美德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也能够使其获得圆满的教化过程。换言之,在修道院服饰习惯中,贫穷并不意味着生活拮据的消极意义,而应看到贫穷带来的肯定性内涵。除此之外,贫穷在这方面也类似于福柯在其晚期著作中对关照自我的生存美学的探讨,比如,福柯极力倡导将生活塑造成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品,使生活成为艺术。早期修道院修道士的服饰内容也是一种对艺术与美的追求,它促使修道士生活在单纯、天真、纯粹的生活之中,这不是根据某种隐修规则而实现的,而是以这种生活方式而存在,抑或说,生命与规则相互渗透而使其不可区分。从伦理学与美学角度来看,贫穷也意味着一种生存美学,生活艺术,指向对自我的不断完善。在这个方面,修道士服饰习惯与其生活方式的不可分离,即是阿甘本意义上的生命—形式,这不是在赤裸生命语境中谈论生命—形式的内容,而是在规则与生命,教义、教制与生命关系中言说生命与其形式的不可分离。
第二,从法律角度来看圣方济各会的“贫穷”问题,圣方济各会没有任何财产所有权概念。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认为,“圣方济各派的信徒推崇‘教会法’——‘根据自然法,全部事物属于所有人’,‘根据神法,所有的事物都是共同的’。”圣方济各派反对财治,反对财产共和国,支持共享制度,共同体建基在共同财富基础上,②[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34~35 页。从根本上来看,这不是“所有权社会”而是一种共产主义形式。亦可说,圣方济各会一无所有,然而又“无所不有”,他们不占有、不拥有任何东西,没有财产,没有所有权,没有专属于自身的东西,但是,却能在共同中产生使用行为,这只是一种事实上的使用,而不是法律上所指示的使用权。“财产和所有的人类法律都始于人类的堕落和该隐之城的建设……在纯真状态下,人类使用了东西,但是没有所有权,在圣方济各会那里也是如此,以基督耶稣和使徒们为榜样,圣方济各会放弃了所有的财产权但保留了对事物事实上的使用……放弃权利(abdicatio iuris,这意味着回到堕落之前的自然状态)以及所有权与使用的分离构成了圣方济各会常常从专业角度界定他们所谓的‘贫穷’的特殊条件的基本装置。”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3.早期圣方济各会宣称要对权力、制度提出激进的批判,抵抗世俗世界的法律与权利,最激进的批判即是反对私有财产,反对个人所有物,反对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圣方济各会反对任何占有,反对任何私有物,拒绝拥有任何东西,这就是圣方济各会“最高的贫困”,亦即“至高的清贫”,这是一种自愿接受而让人无限向往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符合放弃所有权利(abdicatio omnis iuris)原则的实践,也就是说,人在法律之外而又没有任何权利而存在的可能性”。①Daniel McLoughlin (ed.) , Agamben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38-39.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圣方济各会必须坚持贫穷的‘征用’性……‘最高的贫困……是征用的,因为它不能占有任何共同的或个人的东西,既不能占有兄弟的东西也不能占有整个团体的东西’,并拒绝小修道会的任何占有意图(animus possidendi)。”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9.从对所有权的放弃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对创造经济价值、经济利润的私有财产的拒绝,也就无法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也就避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榨,这种生命体验,即是圣方济各会生命—形式的主要体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圣方济各会宣称要放弃任何权利,不拥有任何东西,不是通过废除既定的社会法律与规则来实现。相反,与其说是一种倡导取消现定法律与权利,不如说是一种逃离,一种不服从,一种对既定法律与权利的无视,从而使其自身处于法律、权利之外,使法律与权利自动失效,不再起作用,这也就是一种至高的贫困。因此,圣方济各会的“贫困”,既是一种生活习惯上的简朴,又是一种法律上对物权的舍弃,这不是根据某种世俗法律规定而生活,而是使其融入生活之中,成为自身的生活形式、生活内容,使此种生活形式与自身的生命存在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为“这种形式不是一种强加在生命之上的规范,而是在追随基督生活过程中,给予自身一种形式并使自身成为一种形式去生活。”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5.阿甘本将圣方济各会的“最高的贫困”视为一种拒绝任何形式所有权的生活方式,这是他建构其生命与其形式不可分离的生命—形式的一面,而其另一面则是“贫困的使用”,对“使用”问题的探讨反映了生命—形式具体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是阿甘本构建“生命—形式”范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使用(Use)”理论
阿甘本在生命政治理论中构建了主权、法律、规则对生命的控制与捕获,使得生命沦为了没有任何活力、激情、创造性、主体性的赤裸生命,为了摆脱主权权力逻辑与例外状态的全面束缚,使生命从法律、权力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他将之诉诸生命—形式的创造。与阿甘本将生命政治的典范锁定在集中营的做法类似,他将走出生命政治逻辑框架锁定在圣方济各会运动中,把圣方济各会的生活方式视为走向未来幸福生活的范例。圣方济各会运动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法律、规则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模糊,这两个明显充满差异的领域变得不可区分,成为“无差异地带”,从而切断了法律、权力、主权对生命控制与操纵的可能性。阿甘本认为法律概念之所以会在圣方济各会运动中失效,是在于他们对所有权的放弃,不再占有任何物的所有权,不再成为权利的主体,这是对传统罗马法律的反抗,以具有反“有”特征的“最高的贫困”的存在模式为抵抗武器。个体以“一无所有”的方式而生活,没有占有任何物的意志,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财产或所有权,不是自权人就不能生存。圣方济各会虽然不占有任何财产,但是,他们坚持共同使用任何物,使用任何共同物。“使用”范畴的革新,是圣方济各会生活方式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它体现的是法律、生命、所有权、权利之间关系的变革,因此,阿甘本意义上的生命—形式可能得益于“使用”理论的重新塑造。
从思想发展脉络角度来看,阿甘本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提及过“使用”概念,这是基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来探讨商品的神秘性。显然,他不是为了在马克思基础上来延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来继续分析商品是如何从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普通而又可感觉的物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8 页。。他关注的既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价值,也不是商品形式的物化与物象化过程,而是一种作为景观的商品秘密,“可见而不可见之物”对一切生命的全面统治。阿甘本认为当“商品容貌转变成着了魔的物体时,这是交换价值开始超过商品使用价值的标志。”②Giorgio Agamben, Stanzas: Word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 Translated by Ronald L. Martinez,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38.对此,杰西卡·怀特(Jessica Whyte)解释道,“虽然阿甘本早期将之解释为对使用可能性的腐蚀,但它依然是以克服使用价值的怀旧,挑战其潜在的功利主义预设为导向的。阿甘本对使用概念的最早解释考虑的是与物之间新关系的可能性,这种新关系既不是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也不是交换逻辑。”③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s.),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94.阿甘本确实想要摆脱功利主义与交换逻辑的话语,不过,在这里他并不是想要在马克思基础上重新思考“使用”范畴,或建构某种具体的“使用”理论。他谈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的论述,主要是为了将马克思塑造为景观批判的先锋,而不是重申马克思主义经济拜物教批判方式。因此,在此阶段,阿甘本谈论“使用”问题,更倾向于展现资本主义世界的景观统治,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超越,以至于最终成为操纵生命的绝对权威。与其说这是阿甘本对“使用”问题的最初解释,还不如说是他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批判的肯定。因为在20 世纪90 年代,阿甘本再一次回到了这个主题,高度赞扬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批判,并进一步讨论了“使用”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问题。根据阿甘本在资本主义极端阶段,即资本主义以景观展示其自身的社会,“一切使用都变得不可能并将一直不可能。”④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 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1.这是阿甘本对“使用”概念的实际应用,以分析资本主义在大众消费社会通过景观影像、资本影像对人类生活的全新操控。这也就预示了阿甘本对“使用”概念的运用要异质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分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阿甘本对资本主义领域“使用”问题的思考,是他在宗教领域中对圣方济各会生活形式分析的现实运用与延伸。换言之,要想更清楚地理解与掌握阿甘本的“使用”概念、“使用”理论的最根本特征,或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使用”范畴,就必须回到中世纪宗教领域中,回到圣方济各会运动中,回到生命—形式的典范之中,回到圣方济各会的“最高的贫困”之中。
具体而言,阿甘本构建的“使用”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使用与所有权的对立,以建构一种生命—形式为目标。“在圣方济各会对‘最高的贫困’的倡导中,他们宣称一种完全被移出法律领域的使用是可能的,为把这种使用与用益权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使用权区分开来,他们把这种使用称作事实上的使用(usus facti),实际使用(de facto use)(使用事实)。”①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2.这是异于物权法中的用益权、所有权的纯粹事实上的使用,这种纯粹的使用“是某种人们永远不可能拥有、也永远不可能把它当做所有物来占有的东西。换言之,使用通常指涉的是与某种不可能被占有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使用指涉的是那些不能成为占有对象的物。”②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s.Translated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 2007, p. 83.事实上的使用,亦或使用事实,强调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单纯的使用事实,即使用不是法律或权利问题而是事实、功能问题。与此同时,这又是一种“贫困的使用”,是一种实践行为与事实,是圣方济各会的生活形式,以“贫困的使用”来展示圣方济各会的最初的生活方式。简言之,圣方济各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反对财产所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所有权,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与世俗社会相联系。在这种“使用”范畴中,不是去鉴定“使用”本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使用”是作为一种生活实践行为,并使此种生活形式融入实践过程中,从而又可以生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形式。因此,阿甘本强调,“在这里,使用不再意味着纯粹而又简单的放弃法律,而是把这种放弃建构成一种形式,一种生活方式。”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2.也就是说,使用既是圣方济各会修道士们的具体实践,也是他们生命—形式的体现。第二,使用相异于使用权,使用即是没有权利的使用。在这方面,阿甘本受惠于13 世纪圣方济各会的哲学家与神学家彼埃尔·让·奥利维(Pierre Jean Olivi) 的“使用”概念。在圣方济各会的隐修制度之中,他们所呼吁的“最高的贫困”,不只是放弃拥有物的权利,还必须放弃使用物的权利,即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同时放弃。在奥利维看来,“使用和权利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用某个东西,但没有所有权或使用权,正如奴隶用他主人的东西,却没有任何所有权和用益权一样。”④[意]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钱立卿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35 页。圣方济各会修士们践行的是不占有任何物,不拥有独属于自身的任何东西,而是共同使用。在这里,使用不表示任何价值内涵,也不隶属于法律范畴,而是一种纯粹以使用为目的的使用。这是一种短暂的拥有,这种拥有除了表达使用的单纯行为不代表任何意义,也不是伦理或道德上的要求。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使用表现的是一种共享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被允许使用,但是不具有使用权,与奥卡姆(Guillelmus de Ockham)所言类似,“他们放弃了所有财产,放弃了所有占有的能力,但是并没有放弃使用的自然权利,因为它是一种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①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4-115.纯粹事实上的使用实践是个体本身具有的内在属性,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剥夺或放弃的权利。阿甘本试图努力地将圣方济各会的“使用”概念激进化,从而延伸奥利维与奥卡姆等圣方济各会理论家们对“使用”范畴的界定。在阿甘本看来,圣方济各会的失败在于“使用的事实性本身不足以保证法律的外在性,因为所有事实都可以转化为权利,正如所有权利都暗示着事实方面。……以这种方式他们又将他们自己越来越多地纠缠在司法概念中,通过这些司法概念他们最后将会被颠覆和击败。”换而言之,圣方济各会修道士们正“全神贯注地用司法术语来建构使用的正当性”②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9.。圣方济各会对处于法律、权利范围之外的诉求是一种纯粹地、绝对地放弃,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否定性,最终无法避免再次陷入司法领域。因此,圣方济各会最终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强势打压以失败而告终。阿甘本在圣方济各会运动中看到了其失败的原因,为了摆脱圣方济各会运动中遭遇到的法律困境,他认为“与律法的冲突——或更确切地说,试图使法律失效,通过使用让法律不再起作用,也同样处于纯粹存在层面上,在那里律法与仪式在有效运作。生活形式是纯粹的存在现实,这种纯粹的存在现实必须要从律法和职责或义务的封印中解放出来。”③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6.从这个方面来看,阿甘本看到了避免与法律发生冲突,逃离法律的可能性,那就是转向对圣保罗的思考,走向圣保罗对弥赛亚生活的界定。这也就是阿甘本“使用”理论的第三个特征,圣保罗弥赛亚的真正“使用”,使法律失效,使其不再发挥作用,以“要像不”(“好像不”)的方式来重新发现“使用”理论。以“要像不”使用的态度与立场来对待使用过程,而不是采取抵抗法律或违背法律的激进行为,旨在“创造一个脱离权力和法律掌控的空间,不和它们冲突,却能使它们停止运作。”④[意]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钱立卿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36 页。以“要像不”的方式让渡法律、权利、所有权、社会身份、特权,以“要像不”的使用方式而生活,“以‘要像不’的形式而生活,意味着丧失所有司法的和社会的所有权。”⑤Giorgio Agamben, The Use of Bodies, Homo Sacer IV, 2,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4.这也就意味着阿甘本对生命—形式的建构,从司法领域转向了宗教神学领域或经济神学领域,意味着阿甘本的政治旨趣并不是要创造或生成一个全新的共同体,而是能够如此的共同体,“这并不是另一个样子或另一个世界;它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的逝去。”①[意]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钱立卿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31 页。
四、结 语
在福柯生命政治理论背景下,阿甘本试图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探索中发现崭新的世界和生活方式。阿甘本一方面以主权权力、例外状态为核心构建了政治权力生产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图景,这是他对西方现代政治的病理诊断。另一方面,又试图在消除zoē 与bios,生命与形式的分割中创制与其形式不再分离的生命—形式,并将其作为抵抗生命政治捕获和控制生命的最高手段以及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有效路径。生命—形式不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意义上创造一切的纯粹生命,也不是奈格里、哈特意义上能够开展政治斗争的革命主体。在阿甘本这里,生命—形式不仅预示一种全新的生命存在样态的出现、幸福生活的到来,更意味着主权权力运作逻辑的失效、生命政治装置的终结。人不再是现实的或潜在的赤裸生命,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纯粹潜能。然而,在生命与其形式中涌现的生命—形式却是源于对政治神学传统的思考,以宗教神学话语批判方式代替现代政治的现实批判,这使得生命—形式难以克服神秘而虚幻的末世论基调。这严重损害了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逻辑布展和思想建构的效力与深刻性,从而使得这种思考沦为个人苦恼与焦虑的展现,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左翼激进政治确实面临难以解决的现实难题,只能屈从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