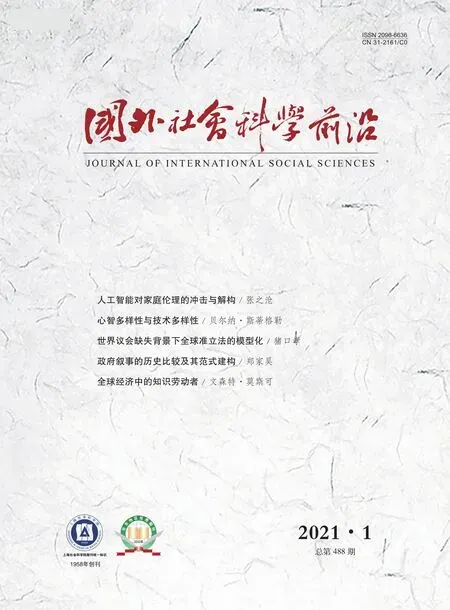全球经济中的知识劳动者:今天在本地,翌日就外包 *
文森特·莫斯可/文 徐偲骕 姚建华/译
[译者按]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从“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和信息业为主”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工作的(离岸)外包,特别是将美国知识和通信部门的工作岗位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做法日益兴盛,已经成为学术界、政策界和媒体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全球外包实践具有复杂性:外包业务并不完全从高工资国家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它到处流动,除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外,还受劳动者语言、技能和教育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爱尔兰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成为了全球外包实践的受益者;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全球外包任务的接受者,还同时开始成为领导者。对全球外包实践的抵制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协会,这些劳工组织通过合并工会和成立工人协会等多样化的方式阻止本土的工作岗位(尤其是知识产业岗位)持续向海外流失。此外,来自发达国家以外的抵制也在增加,全球抵制外包实践运动的声势正日渐浩大。
代编者按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加速了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此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将其大部分制造业流水线生产任务和低技能要求的服务工作分包给位于该体系边陲或者半边陲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承担,以实现产业转移的目标。学者们将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称之为“离岸外包”(简称“外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方面,外包有益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强化核心竞争力和扩大经济规模,因此成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选择;另一方面,全球外包实践的方兴未艾使得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注重劳动者就业水平、最低工资保障和基本社会福利的生产组织原则被“商业优先”的原则所急速取代(当然,这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去福利化并不是一回事)。在当前的世界生产和贸易图景中,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知识劳动者(甚至是高技能的知识劳动者)都直接面对着外包带来的巨大冲击。
进一步来说,全球外包实践孕育出一支规模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他们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和知识劳动者构成,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但在莫斯可看来,与上述现象相伴相生的是,多样化的抵制全球外包实践的策略正在形成,如合并工会与成立工人协会,后者正得到越来越多技术密集型工人和内容生产者的青睐。全球抵制外包实践运动的声势也日渐浩大。
诚如莫斯可在文末所揭示的那样,通过将全球外包实践的复杂性抽丝剥茧,我们不难发现,全球范围内受资本支配且不断加速的劳动力流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导型国家”和“依附型国家”的简单概念,因为即使是那些遭受贫穷和殖民主义最极端后果的国家,也有一些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外包实践中的“排头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不是由权力的陡峭高峰和低谷组成的,也不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日益平坦的世界,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复杂且极富变化的,但其主导力量依然是资本的积累与增殖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进入21 世纪之后,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德国的Clickworker、美国的MTurk 和Upwork 等大量众包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工、临时工、自由职业等非正规就业形式愈发普遍,“零工经济”(gig economy)井喷式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我们理解上述现象及其背后的内在机制与基本逻辑极具阐释力与启发性。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一、导言:知识工作的视角
工作的“离岸外包”(outsourcing,简称“外包”),特别是将美国知识和通信部门的工作岗位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做法日益兴盛,已经成为学术界、政策界和媒体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呼叫中心员工、大学教授和专业运动员虽然看起来迥然相异,但是他们在知识产业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制造业以外工作岗位数量的激增,这引发了他们对相关问题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争论。早期,学术界的重点是开发测量上述经济增长的工具,在这其中,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作为领导者之一,参与绘制了经济中数据和信息组成部分的扩张情况。①Fritz Machlup,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马克·波拉特(Marc Porat)以这项工作为基础,记录了以初级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三产业(服务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②Marc Porat,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77.不过,他们都没能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样,在复杂的理论层面上探讨这一转型背后更为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涵。③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根据贝尔的说法,我们经历的不仅是数据和信息的增长以及主要职业类别的转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现在,“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theoretical information)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一个由训练有素的科学技术工人组成的真正的知识阶层正在崛起,并最终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这样的社会不一定会更民主,但它意味着权力将建立在知识而不是家族继承的基础上。在贝尔看来,随着知识劳动者大军真正掌握和管理经济,以及技术算法和其他基于知识的(技术)手段持续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将持久衰落,围绕公共政策的政治斗争也将不断减少。虽然这样的社会依然存在内部张力,但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而非意识形态层面。唯一可能出现严重分歧的是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文化领域。正如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这本更为晦涩的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对后工业社会唯一的重大内部威胁是一种越来越深地陷入消费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信仰的文化。
不久,诸多学者纷纷意识到:不管是消费享乐主义还是非理性信仰的文化,后工业主义本身对大家来说无甚裨益。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直言道:后工业化意味着跨国媒体和电信企业的崛起,它们成为了美国价值观有力的支撑者,包括美国的军事和帝国野心,并通过日趋集中的市场力量清除其他选择。④Herbert Schiller,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PA: Beacon Press, 1973.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进一步论述道:对于服务、零售和知识行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他们会像在制造业中的流水线工人一样受到严格的管制,最终丧失专业化技能。①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的确,考虑到知识工作的非物质性,对“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进行分离,并把“概念”的权力(如设计和管理)集中在一个主导阶层的手里,这比在工业时代更容易做到。
与此同时,学者们发现,从农业和制造业工作到知识工作的转变不仅发生在发达社会中,一些发展中社会也开始出现这种变迁。毋庸置疑,农业和制造业工作虽然都需要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但今天与其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涉及“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在此,动态的技能丧失(deskilling)、技能提升(upskilling)和技能更新(reskilling)过程普遍存在于职业等级的各个阶段,虽程度不同,但有一点十分明晰:当工作岗位中的技能成分不断减少,或者自动化系统完全取代劳动力时,企业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在无法去技能化和裁员的地方,企业通过把就业机会转移到国内低工资地区或者国外,同样能够得偿所愿。这种流程通常被称为“外包”。例如,一家美国企业可以雇佣中国的数据录入工人、加拿大的呼叫中心员工或者印度的软件程序员,而与雇佣美国的工人相比,其劳动力成本大幅缩减。外包基本上是企业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霸权地位的延伸,这使得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在发达社会中盛行的“商业劳动社会契约”(business-labour social contract)②其基本特征为:有保障的工作、最低工资和一揽子社会福利。——译者注的生产组织原则让位于“商业优先”(business-first)的原则;并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名,削减就业岗位、工资,使社会福利远远低于今日保障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外包的支持者还对保护劳动者和工会的社会政策工具进行猛烈抨击,这就导致劳动者更难维护自己的权益。
诚然,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和就业机会的“外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 世纪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和劳伦斯两市的纺织工厂曾经是企业规划和家长式管理的典范,现在却成了博物馆和公寓的所在地。长期以来,工作机会流向了美国南方各州,现在又流向了中国和印度。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如今被外包的工作,大部分是电子服务,其纯粹的非物质性使得外包过程相对容易且极为廉价。此外,因为企业空前强大,当前对外包实践的抵制更加困难。随着华盛顿政府和美国各州政府对商业更加友好,在美国,劳动者和工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劳工组织的危机与外包的视角
2004 年,美国产业工人中工会会员的比例下降至12.5%。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的数据,这一比例在2003 年为12.9%(从1983 年20.1%的高位逐年下降)。私营部门的数据更低,约为8%,而政府工作人员为36%。加拿大的情况稍好一些,该国30%的产业工人是工会会员,其中公共部门工会会员比例为72%,私营部门为18%。但这一数据与1990 年的35%相比,也下滑了不少。①Statistics Canada, Study: The Union Movement in Transition, The Daily, August 31, 2004.
关于外包,有两种观点在公开争论中脱颖而出。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劳动者十分担心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加强对外包的立法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包括终止日益增多的政府工作外包,并要求从事外包工作的服务业人员,特别是呼叫中心员工说清楚自己的工作地点。WashTech 牵头发起了阻止美国高科技企业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行动,这是一家从美国通信业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CWA)剥离出来、旨在动员微软公司员工的高科技劳动者组织。然而,并非所有的工会会员都同意严格监管的要求。例如,安德鲁·斯特恩(Andrew Stern)就认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且是无用的,他呼吁管理层和劳动者团结起来,为需要不断自我改造的熟练工人提供替代收入和再培训项目。②Mike Langberg, Union Leader Makes Tech Pitch,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5.
另一种观点坚持捍卫自由贸易。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将自由市场奉为圭臬。他们笃信,开放商品和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应该限制劳动力外包,而是应该鼓励企业及其员工更聪明地工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造性、创新性和智力工作上,如重塑产品、引爆品牌期望,等等。
上述两种观点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只关注了国际劳动分工重大转型过程中的部分现象。准确且深刻地理解上述转型的全过程,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核心作用,离不开考察与分析全球外包实践这一复杂过程中的关键性维度。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外包”进行定义,并将它与“离境外包”(offshoring)这一概念做简单的区分。具体来说,“外包”是指企业将一部分生产流程从其运营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实体,通常是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而不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生产或者将生产转移到自己在外国的附属公司。当一家企业将工作转移到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时,外包可以发生在一国之内,或者就像“外包”这个术语通常意义上的那样,依赖于国外第三方供应商的生产。外国第三方可能是独立的当地企业,比如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将软件开发任务外包给印度的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或者可能是另一家跨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比如美国企业将其数据处理服务外包给加纳的ACS 公司。③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4.“ 离境外包”是一个经常与“外包”相混淆的概念,从技术上讲,“离境外包”是指一家母公司的生产任务由自己(在境外)的一家外国子公司完成,如德国敦豪快递服务公司(DHL)将其计算机工作转移到位于捷克布拉格的IT 中心,或者英国电信将呼叫中心工作派发到其在印度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两市的子公司。外包而非“离境外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三、知识工作的外包
要确定外包的范围并不容易。大多数外包发生在本国,只有1%~2%的业务流程外包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位美国信息技术协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America)负责人估计,当前全球跨国外包实践占比约为4%,但这个数字要攀升到40%并不是什么难事。①Janice Koch, Beyond Cost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Risks, The Conference Board, June 15, 2005.虽然相关数据和信息分散在各类商业报告和商业计划调查中,但外包显然是一种日渐壮大的现象。美国现在每年从印度进口大约价值50 亿美元的软件,这其中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在被问及为何将服务工作外包给海外企业时,约70%的企业认为,这既节省了劳动力成本,又省去了在少数几个特定外国地点整合业务而增加的生产成本。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国是外包实践的主要发起国,在所有出口导向型信息和通信项目中,美国约占2/3,其中就包括全球六成的呼叫中心项目。②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4.除此之外,全球有着很多媒体工作正在被外包的证据,但大多都是坊间传闻。路透社在新闻业中率先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印度。2005年,路透社宣布其足足10%的劳动力,即1200~1500 个工作岗位,正被转移至班加罗尔。其中,大部分工作都与整理新闻相关,这些新闻随后通过路透社的众多通讯社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发。③Heather Timmons, Reuters Plans to Triple Jobs at Site in Indi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04.好莱坞还将许多曾为美国南加州经济提供重要支撑的工作外包出去,比如动画制作流向亚洲,电影制作流向加拿大,不一而足。
(一)从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外包
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知识工作外包和离境外包的接收方是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其中爱尔兰和加拿大位居榜首。例如,2002—2003 年,超过一半的海外呼叫中心项目流向了以爱尔兰、加拿大和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2001 年,所有外包服务的市场总额为320 亿美元,其中仅爱尔兰就占了1/4。这些国家的企业能够向美国企业提供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且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优势明显。呼叫中心员工需要娴熟的沟通技巧和对出口国市场文化的基本了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加拿大是美国呼叫中心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总体而言,对于软件工程、建筑设计、财务分析和放射诊断等对劳动力要求越来越高的职业来说,教育和技能愈发重要。虽然上述领域的一些工作流向了中国和印度,但更多的工作转移到了爱尔兰、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察全球外包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时,它呈现出复杂性:大家通常会认为工作会从高工资国家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但现实是工作到处流动,确切地流动到哪里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就包括劳动者的语言、技能和教育水平,等等。
(二)印度的领导角色
就当前整体趋势而言,就业岗位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吸纳了大量低工资工作,依赖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而且也开始在全球外包实践中起到领导作用。例如,在印度的高科技部门,一些企业家不仅学会了如何吸引工作机会,而且学会了如何在外包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例如,总部位于印度的跨国公司ICICI OneSource 有限公司(隶属于印度的ICICI 集团)提供标准的本地和外包服务,包括客户服务、投诉解决方案和印度呼叫中心的电话营销。它也在美国芝加哥的办公室做市场研究和分析。2005 年,该公司收购了位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外的一家美国公司,后者为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处理“后期”信用卡还款业务。虽然近年来已有几家印度公司在美国开展了相关业务,但收购一家美国企业的举措还是头一遭。最初就有500 名美国员工的ICICI OneSource 公司任命这家美国企业的总裁为其全球业务主管,开始将美国业务整合到国际业务之中。对一部分人来说,外包只不过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延伸,但一家印度跨国企业启用其刚刚收购的美国企业的总裁作为它的“全球掌柜”,其意义不容小觑。
除了ICICI 集团,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了办事处,与加拿大企业竞争美国的外包业务,并为其国际客户培训技术工人。塔塔公司是印度第一家年收入超过10 亿美元的企业。温哥华也是继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之后,这家印度巨头进入的第四个加拿大城市。选择温哥华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它靠近美国西雅图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尤其是靠近微软公司。塔塔公司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签署了一项协议,该校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塔塔公司实习,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塔塔公司在北美拥有8000 名员工,并计划积极开拓全球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印度作为美国企业低工资工作“倾销地”的形象。①Petti Fong, India’s Largest IT Service Provider Expands West, Vancouver Sun, October 14, 2004.在印度,高科技行业工作中遍布着长工时、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压迫性的管理,但其领先企业已经很好地学会了如何在知识劳动领域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三)地域和文化的重要性
当ICICI 集团进入芝加哥、布法罗以及塔塔公司进入温哥华市场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地理终结”的想象在制造“神话”方面颇有市场,但地域仍很重要,文化也一样。②Vincent Mosco,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ICICI 集团决定收购布法罗的公司,并利用它来优化和拓展其在北美的账单清缴业务,就是出于对地域和文化的高度重视。据该公司北美业务负责人说,“在信用卡收款的后期,我们基本上面对的都是那些逾期120~180 天的账户,这样的话,工作在美国境内比较好开展,因为本地雇员更了解当地情况。”①Virginia Galt, India’s ICICI Catches the Onshore Wave, The Globe and Mail Report on Business, March 28, 2005.同样,塔塔公司将其总部设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决定表明,即使信息以光速移动,成功的公司也必须将其地理位置安排在商业活动的中心或者附近。塔塔公司同时承认文化在知识产业中的重要性。爱尔兰、加拿大和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外包实践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类似地,塔塔公司位于温哥华,这不仅意味着前者有了一家西方公司的“外表”,而且还意味着它有机会吸收高科技行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文化,同时也被该文化所吸收。
四、对全球外包实践的抵制
在全球范围内,对外包的抵制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在西方,作为抵制的重要来源,工会和从主要工会中分离出来的工人协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部门。上述组织的根本宗旨是帮助劳动者解决其所面临的普遍危机,但在现实中,它们的努力主要集中于防止工作岗位(尤其是知识产业岗位)流向海外。在美国,一系列媒体工会——国际印刷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报纸工会(Newspaper Guild)、全国广播员工和技术人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 Employees and Technicians,NABET)——都纷纷加入了CWA。CWA 是一种工会合并的模式,它代表着电信、广播、有线电视、报纸和有线新闻业、出版、电子和一般制造业,以及航空客户服务、政府服务、医疗保健、教育等领域的工人。CWA 成员的主要雇主中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美国通用电话电子公司(GTE)、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ies)、朗讯技术/贝尔实验室(Lucent Technologies/Bell Labs)、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以及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在加拿大,通信、能源和造纸工人工会(Communications, Energy and Paper workers Union,CEP)也采取了类似的合并模式。它已经与许多来自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在加拿大的部门、来自报业协会的加拿大部门以及加拿大的NABET 合并。此外,在加拿大,电信工人工会(Telecommunications Workers Union,TWU)历来代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电话工人,由于加拿大劳工监管机构认为当技术和产业出现融合情况时,各行业的工人最好由一个工会来代表,TWU 得以获得其对阿尔伯塔省电信工人的管辖权。这些工会在反对全球外包实践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劳工组织也将劳动融合视为一种尝试,以更好地利用工作性质日益趋同所带来的协同效应。②Mort Bahr, From the Telegraph to the Internet, Washington, D.C.: Welcome Rain, 1998.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认为,由于这些组织代表的工人在电子信息服务领域的生产任务具有极高的相似性,所以存在更合适的组织和谈判机会。从本质上说,技术和企业的融合使知识产业的劳动者走到了一起。①Catherine McKercher, Newsworkers Unite: Labor, Convergence and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s, Lanham, 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然而,这种策略并不总是成功的。例如,用以阻止录像和电影产业(如美国好莱坞)日益整合的关键办法之一,恰恰是合并代表这两个行业的工会,比如迪斯尼和福克斯这样的公司就曾利用合并后的权力来控制各自的员工。没有统一的劳动场所,这些公司可以更为便利地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开业,包括在多伦多和温哥华海岸拍摄电视剧和故事片,同时规定合同条款,明确收益(主要来自多次使用同一电视节目或者电影)的分配方式。具体而言,美国电视和广播艺术家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和美国演员行会(American Screen Actors Guild)原本可以合并,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尝试都折戟沉沙了,最近的两次是在1999 年和2003 年,结果都功败垂成。加拿大在其主要电信联盟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尝试也不是特别成功。全国通信工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munication Unions)的成立在CEP 和TWU 之间建立了正式的联盟关系,TWU 主要代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塔省的电信工人。但也许是因为后者有激进主义的前科(它曾在一次罢工行动中接管了温哥华的电话交换机),也因为TWU 回避了工会合并的想法,这两个工会并没有展开紧密的合作。
2005 年,工会合并问题在美国升温,当时,共和党在2004 年大选中获胜,工会会员比例不断下滑,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的主要工会之一扬言要退出,除非AFL-CIO 允许进行重大的新一轮合并和其他组织变更。具体方案是,美国发展最快的主要工会——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SEIU)——要求AFL-CIO 整合其几个成员工会,并将它的研究和政治活动的资金转移至基层。SEIU 坚持以退出相威胁,并得到了强大的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Union)的支持。AFL-CIO 通过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但该协议是否能长期维持下去,还有待观察。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最高级别的劳工组织中,人们普遍存在不满和怀疑,认为这种合并的方式既不是解决工会危机的有效策略之一,也不是帮助其更好地处理失业问题的最佳方法。
第二种回应是成立工人协会,在没有就集体协议进行正式协商的情况下为工人谋求福利。在组织工会特别困难的高科技行业,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如跨国游戏公司育碧(Ubisoft)法国分公司的电子游戏从业者组织了一个名为Ubifree 的工人协会。在“兼职永久员工”或者称为“永久性临时工”(permatemps)的群体中,工人协会的作用和影响甚为关键。传统工会很难组织这群人,因为差不多40%的高科技行业从业者以非标准的方式被雇佣。之所以称他们为“永久性临时工”,是因为他们从事全职工作,但按小时计酬,实际上不享受任何福利和加班费。这些工人协会的主要目标包括为高度流动的劳动力提供福利、终身培训、就业安置,以及为没有资格享受雇主支付福利的工人提供医疗保健计划,等等。
在知识部门,有两种类型的工人协会很突出,一种代表技术密集型工人,另一种代表内容生产者。前者的典型例子是WashTech,它是西雅图高科技产业协会的分支机构,由微软公司失意的永久性临时工组成。该组织成功地为其会员赢得了不少核心利益,直至微软公司取消了这种类型的岗位。①Danielle van Jaarsvel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among High-Tech Workers at Microsoft and Beyond: Lessons from WashTech/CWA,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43, no. 2, 2004, pp. 364-385.在高科技行业中,劳动者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许多人并不直接隶属于高科技企业,而是隶属于像万宝盛华公司(Manpower)这样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劳动力派遣的人力资源企业。WashTech 覆盖了程序员、编辑、网页设计师、系统分析师、校核人员、测试人员和工程师,他们的目标是“赢得更高的薪水、健康福利、假期、退休计划、折扣股票期权和工作培训”。总体来说,WashTech 在微软公司是成功的,这主要得益于它与倡导组织(advocacy groups)之间紧密的联系,比如变迁中的劳动力中心(Center for a Changing Workforce)及其为高科技行业从业者提供信息和在线组织的网站Techsunite.org。但WashTech 并没能成功地扩展到其他的知识部门。它还曾试图将线上书店亚马逊中长期不满的员工组织起来,不过失败了。如今,WashTech 当仁不让地参与了反对将科技工作外包到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并成功说服了一些州议员停止对政府科技工作进行外包。
工人协会在内容生产者中也日益走俏。“今日工作”(Working Today)就是这样一个倡导组织,它代表独立工人,包括自由职业者、顾问和临时工,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在高科技繁荣时期被称为“硅巷”(Silicon Alley)。它在为其成员提供基本健康保险方面尤其成功。又如,图形艺术家协会(Graphic Artists Guild)代表网络创作者、插图画家和设计师,他们尝试联合起来共同改善工作条件,并介入处理版权、税收和其他重要政策议题的决策过程中。再者,创作者联盟(Creator’s Federation)是自由作家的代表,它已成功要求出版商在将自由作家的作品放入数据库之前必须得到作家的同意。此外,美国全国作家联盟(National Writers’ Union)拥有5000 多名会员,为他们提供合同模版、与出版商讨价还价的建议,以及为没有社会保险的自由作家提供福利。在国际上,我们也看到了由国际工会网络(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UNI)领导的作为高科技行业从业者保护伞的组织纷纷崛起。UNI是一个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组织,于2000 年由四个横跨商业、金融、电信和媒体的联盟组成。
在高科技行业中,工人协会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老牌工会在组织工作方面乏善可陈。不过,在互联网繁荣的全盛时期,一些老牌工会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等工会就成功地组织网络工人参与皮博迪(Peabody)和奥尔布里顿(Albritton)等超市的在线配送服务。此外,AFL-CIO 还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名为“工作美国”(Working America)的会员组织,在全美拥有80 万缴纳会费的会员,这些会员同意支付年费,并承诺在政治和立法活动中与工会合作。这个组织的创始董事是凯伦·努斯鲍姆(Karen Nussbaum),她在20 世纪80 年代缔造了第一个女性办公室员工组织——“朝九晚五”(Nine to Five)。“工作美国”为何给人以希望,只需看它每月2 万名会员的增长速度就知道了。
此外,来自发达国家以外的对全球外包实践的抵制也在增加。例如,一家代表印度各地约100 个工会的组织成立了,它通过新工会倡议(New Trade Union Initiative)来运作。2004年12 月,它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与当地的工会和工人协会领导人会面,讨论处理外包的共同策略。印度工会支持在高科技行业和服务部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十分担心工作条件和此类工作的可持续性。正如该工会的一位领导者所述,“工作机会流向印度,不是因为工资差异,而是因为这些工作不受监管。印度没有关于最低工资或者工人最长工时的法律。跨国公司正在利用这一点……工人每天工作16 个小时,经常是晚上工作,强度是美国工人的五倍。”①Rimin Dutt, Visiting Labor Leaders Say Indian Workers Stressed, India New England, February 14, 2004.
对全球外包实践的抵制运动可能会越来越声势浩大,尤其是在外包实践的结果好坏参半的情况下。最近对全球外包实践的评估结果不太乐观,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2005 年的一份报告,“在所有外包业务中,有一半是注定失败的”,这警告企业不要在没有仔细规划的情况下仓促入局。②Janice Koch, Thinking Offshore Through, The Conference Board, February 15, 2005.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企业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的一项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企业外包的越来越多,如鱼得水的却越来越少,外包未能达到预期的情况愈发普遍。
五、结 语
总而言之,不管是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早期蓝图的愿景,还是他对互联网产业发展更为神话般的想象,我们都与之相距甚远。未来几年全球外包实践将如何发展尚不确定,仅仅基于高科技企业的战略计划来进行轻率的预测并不可行。外包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一面棱镜。许多外包实践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时也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内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企业正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展示自身强大的实力,这极大地挑战了外包如何运作的传统观点。此外,在全球外包实践中,决定性的力量并不囿于技术和工资,地域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关键。更为重要的是,融合不只是一种技术现象和对企业集中的婉转表达,它还适用于抵制全球外包实践的各种劳工运动和组织,包括北美的老牌工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劳工组织,以及得到全球信息和技术工人联盟支持的工人协会。
那么全球外包实践更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涵是什么呢?迄今为止的大量证据表明,外包是全球资本主义在深化和扩张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全球范围内不断加速的劳动力流动紧随资本的流动,并以此方式挑战了“主导型国家”和“依附型国家”的简单概念。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即使是那些遭受贫穷和殖民主义最极端后果的国家,也有一些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外包实践中的“排头兵”。世界不是由权力的陡峭高峰和低谷组成的,也不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日益平坦的世界。①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相反,关于全球外包实践的研究表明,当下的世界政治格局仍然是复杂且极富变化的,其主导力量依然是资本的积累与增殖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
文化后果也是如此。一方面,全球外包实践有助于消除文化差异。印度呼叫中心的员工接受过“西方”语言以及西方文化实践(从体育到购物)的“培训”,这证明外包实践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传播。但是,印度和其他非西方企业向美国西部中心地带的扩张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容易被克服。对于企业而言,要利用新市场,它们需要训练自己的员工理解不同的文化、适应文化之间的差异。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缩小了一些地域差异,但在此基础上,认识到技术的局限性以及适应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既必要又紧迫。
如果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容易划分为山头和谷地,那么政治后果可能会像地形一样复杂。西方工人对全球外包实践的态度是抵制还是拥抱,取决于他们是丢掉了饭碗还是获得了新的工作。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拥抱外包,因为外包往往意味着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当他们的工作通常情况下不包含限制工作时间、设定最低工资、提供职业安全和健康标准的监管性保护时,他们就改弦更张了。其结果是,一系列新形式的抵制运动对传统工会构成了挑战,并催生了新的劳工组织形式以及新的国际劳工合作形式。由于这些运动日益涉及知识、信息和媒体机构,传播学者将通过密切关注“文化劳动”的新形式而从中获益匪浅。②Michael Denning,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Book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