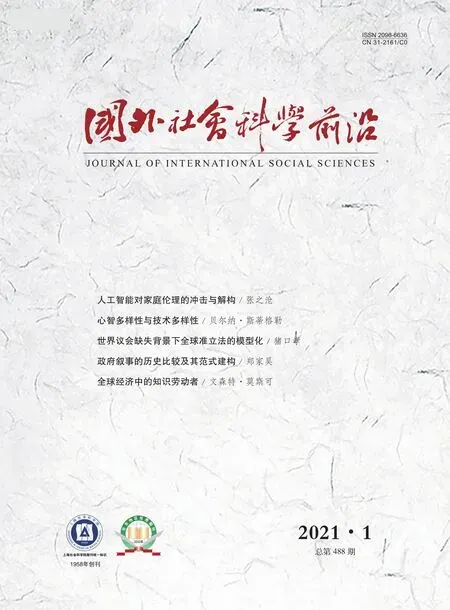世界议会缺失背景下全球准立法的模型化:日本“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性尝试 *
猪口孝/文 任 慕/译
[译者按] 本文回顾了自1945年以来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轨迹,并介绍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尝试,即“全球国际关系”这一概念。自21世纪初开始,“全球国际关系”这一概念已经在日本以及全球其他地区发展并兴盛起来。为研究“全球国际关系”,需要在“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和“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这两项要素之间建立全球社会契约的模型。在建立了二者之间比较牢固的关系之后,作者认为全球社会契约在实践上是存在的。未来,为阐释不断增加的跨国的全球性立法,还应进一步对全球准立法进行系统、科学地分析。
一、引 言
提及日本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首先要从历史、理论、地区和方法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①猪口孝《 国際関係の系譜》(猪口孝編《シリーズ国際関係論》,全 5 巻の第 5 巻, 2007 年,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原因在于日本带着历史的难题开启了国际关系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近代的日本以“富国强兵”这一口号为指引,致力于建设一个能够跻身于欧美行列的国家,当时的国际关系学呈现出何种特征呢?理所当然,引发日本学术界思考的首要问题是:欧美国家是如何发展至如此强大的?直接探讨这个问题的学科就是所谓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关于国家应当服务于何种目标、国家如何得以产生等方面的研究。尼克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认为,对于国家而言,牢固地掌握军队和法律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强调如果没有军队和法律,国家也就不复存在。②ニッコロ·マキャベリ《君主論》 東京:中公文庫,2002 年。对于那些在欧美的军事和经济威胁之下而开放的国家来说,军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加强军备便成为这类国家的首要任务。日本曾打着“帮助受欧美军事和经济威胁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旗号企图向亚洲地区扩张。在军队的建设上,日本陆军效仿德国,海军主要效仿英国。与此同时,虽然日本警察体制以德国模式为蓝本,但是负责东京的警视厅的建设遵循的是法国模式。
在法律层面上,日本曾被迫与欧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蒙受了极大的屈辱,且损失惨重。日本将治外法权让渡给欧美各国,关税自主权被剥夺。自1853 年开国(解除锁国政策)以来,日本不得不忍受60 余年的不平等条约。彼时,大多数欧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然而日本却无法在对外贸易中征收关税。为应对这种情况,日本在学习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以帝国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制定了诸多法律。
日本所拥护的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是殖民地学说。在实践上,日本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名义,为其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提供合理性。军事学也被视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19世纪后半叶,铁路、坦克、军用飞机、枪炮和军用战舰相继得以发展应用。以生丝为主的缫丝业在德川时代中期开始发展,是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柱。然而,在军事学的影响下,为因应国家需要,日本经济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能够满足铁路和武器制造需求的重工业。与对殖民地学和军事学的信奉不同,日本建立了以欧美研究模式为中心的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学会。国际法和外交史也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必修科目。
彼时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以国家理论为中心,国际法、外交史、殖民地学和军事学并存的学术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全面失败。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了日本,原有的学术体系随之被重新构建。《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并且废除军队。由此,国家理论分化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殖民地学和军事学转变成为经济发展论和军事史学。政治学虽保留了国家理论的浓厚色彩,但同时也受到影响力渐深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构建起来的国际关系学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国际关系学主要致力于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原因。因此,新建构的国际关系学以外交史研究为中心。
除此之外,国际关系学也将地缘相近的邻国作为研究的焦点,这一点与二战前情况相同。此后,日本与美国结盟,与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关系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席卷欧亚大陆。而未受共产主义影响的韩国,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军事政权都持有很强烈的反日情绪。相邻各国的不安和戒备构成了当时日本所面临地区环境的主要基调。随着时间发展,虽然各国经济的纽带不断加强,相互依存进一步深化,但是邻国对日本的不安和戒备这一基调一直持续至今。因此,历史和地区研究是新的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支柱。
美国作为世界的主导国,其文化和学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1950—1975 年间,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深受美国学界的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也强调国际关系学的另外两大支柱——理论和方法。这里所谓的理论是指国家理论,而所谓方法是指历史学的方法。虽然称之为历史学,但在实质上,一方面是从国家理论、殖民地学所继承的以精确而详尽的记述为主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随着英语和计算机在全世界的普及,美国式的理论和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在1975 年之后,日本的国际关系学也在美国式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得以扎实地重新建构起来。
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松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冲击
随着近代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国际关系学得以发展。①参见猪口孝“ 国際関係論の理論と展開” 及猪口孝“ 地球政治の秩序形成理論”(猪口孝編《 国際関係リーティンクス》,2004 年,東京:東洋書林),1~22 页;435~460 页。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天主教梵蒂冈教宗为主导的宗教世界体系和以封建领主所主导的世俗世界体系持续并存。而后,君主专制政体从封建领主当中脱胎而出并逐渐得以建立,这些君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土地。由此,君主专制政体和其管辖的领土为后来出现的“民族”这一概念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规模上来说,民族不像帝国一样庞大,也不像部落那样微小。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起的现代国家并不像基督教一样被赋予了超国家的力量,②这里的基督教是指统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译者注而是建立在其能够自由行事之构想的基础之上。将这一构想进行理论化的思想家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③トマス·ホッブス《 リヴァイアサン 1~4》 東京:岩波文庫,1982 年。君主专制制度被认为是解决那些中世纪封建体制所遗留的欧洲问题的关键。主权被视为最高权力,最大限度排除宗教的影响,以世俗国家为主要行为体来运行的国际政治体系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建立的标志是17 世纪初“三十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事实上,当时所谓“主权国家”的实际形态并不限于君主专制体制,而是呈现出宽泛多样的形态。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国际关系是通过外交和战争所建立起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理论与实际经验产生了背离。
同宗教问题一样,民族问题也难以解决。法国、西班牙及英国等国政治制度继承自罗马帝国,国家发展相对较早。而德国、意大利以及大部分中欧和北欧国家依旧在帝国体制之下,存在潜在的民族问题。神圣罗马帝国解体,留下了尚未统一的德意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直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俄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国联也准备推进该原则的实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国家间开始倾向于采取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外交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宣告失败。数千万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杀戮,20 世纪也因此被视为“史上最大的战争世纪”。联合国以国联的失败为戒,在安理会中赋予了五大战胜国否决权。虽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对峙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民族国家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式仍旧存在。
然而,如果不因应全球化这一潮流的要求,科技未能取得进步的话,世界经济就无法得到发展。因此,数字化是支撑全球化的要素。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促进了资本、服务和贸易在全球的流动。从一方面来看,移民和难民的增加以及接纳这些移民机制的建立使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分配。除此之外,多元化货币得以快速、大量流通及使用。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一旦自由贸易体系之下的投资行为走向极端,无数人会因此受到冲击;一旦移民和难民变得更易被他国接纳,就会有极大规模的移民和难民涌入接收国,接收国民众的不满声音将会加大。除此之外,虽然通过市场的调节使货币快速、大量地流动成为可能,但是通过赚取差价的投机行为将使资本流入国蒙受巨大损失。这些负面影响会抑制(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虽然各国采取自由贸易制度,但是为避免在两国、多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中受到残酷地冲击,卡特尔式的协议也在增多。虽说企业可以进行自由投资,但是国家可能会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关税制度来降低投资风险,以及控制那些不能增加其利益的投资。在移民和难民方面,国家制定移民政策限制不能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移民流入,并采取防止犯罪和冲突的政策措施。除此之外,在欧元区,一些避免因使用统一货币而导致国家破产的机制和行动也在悄然地建立和展开。这些措施和行动避免全球化朝着产生极端、剧烈冲击的方向发展。然而,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虽然民族国家是保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表象的外衣,但领土边界的存在无法全面地控制人、商品和资金的跨国境流动,绝对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在实践中被削弱。在超越国家的范畴里,因为无法以单一国家的政策来解决全球问题,所以事关人们切实生活、使人类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各种立法(规范和制度)正在增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超国家的制度、政策产生了极端的结果,对此结果进行抑制的行动就会增加。
三、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可与亚伯拉罕(Abrahamic) 和达摩(Dharmic)的教义相类比。①参见Takashi Inoguchi, Intellectual Tradition: Global, in T. Inoguchi (ed.), SAGE Handbook of Asian Foreign Policy,vol. 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猪口孝·原田至朗“ 国際政治研究者の専攻戦略”(柳井晴夫主編《多変量解析実例ハンドブック》, 2002 年,東京: 朝倉書店), 494~509 页。猪口孝“ 国際比較政治研究と計量政治学”(柳井晴夫編《 行動計量学への招待》,2011 年,東京: 朝倉書店),134~142 页。前者强调的是按照规则进行统一说明,参照一定标准、进行系统性地对比和比较。后者与之相反,更重视差异,关注这种差异产生自何处,在整体中这样的差异是如何持续存在的。前者多见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后者则是在佛教、印度教和神道教中有所体现。在社会科学中,如果未能在这两个取向上达成平衡,就会成为失之偏颇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观察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发展。1950—1975 年是国际关系学理论和方法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②Takashi Inoguchi, Social Science Infrastructure: East Asia and the Pacifci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James Wright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22, Oxford: Elsevier, 2015, pp.631-636. 此百科全书在2016 年获得了美国出版商协会的最高奖项——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The PROSE Awards)。直到20 世纪的前半叶,国家理论及其支撑起的国际关系学更为关注的是,为何在落后于欧美列强的国家中似乎只有日本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以及日本如何才能与欧美国家为伍而生存下去。因此,日本学界对欧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研究带有目的论的倾向,对欧美的国际关系研究亦是如此。这种研究基于特定的目的,平衡社会科学两种取向的意味较为薄弱。因为对政策目标的研究过于具体,所以学界比较容易受到对社会科学做出统一性解释的影响,或过于强调事件的罗列,而不是采取一种可能得出与政府意图背道而驰的结论的方法。如此种种是作者对于战前日本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观察。虽然战后这个基调并没有改变,但是20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探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趋势。至于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何时能在所有研究中都广泛地应用,还有待时日。
四、世界议会缺失的背景与民主制的实际样态
在回顾了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进展之后,本文进一步说明——世界议会并不存在。联合国在二战后得以成立,但联合国大会并不是成员国的“君主”。具有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五大战胜国。现在,也许需要考虑对这个规则做出改变: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在安理会表决决议时,把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都包括在内,整个安理会不再采取过半数的原则,而是十分之七决定乃至是五分之四的多数通过。无论是哪种规则,当今世界的实际形态是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或世界议会。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中也建立了各种规范和规则。也许我们可将此现象称为类立法或准立法。
如果思考政府、议会和立法的问题,首先就会浮现出民主的概念。如果思考民主这一概念在近代欧洲的起源,需要提及倡导直接民主制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提倡代议制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①ジャン·ジャック·ルソー《 社会契約論》東京:岩波文庫,1954 年。ジョン·ロック《 完訳 統治二論》東京:岩波文庫,2010 年。很多教科书上都写到:直接民主制起源于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市民社会,而代议制民主的始祖是近代欧洲。然而,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制,详细考察它们的内容我们就能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制度的运行都是被长老或者是精英所支配的。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只有公民这一特殊阶层才有权参与其中。同样,近代英国的代议制也不过是各个市郡和地区的名望之人和长老精英作为代表的制度,后来逐渐把这种制度称之为民主。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和英国近代的代议制都不是欧洲独有的产物,美索不达米亚、南亚、中南美洲等很多地域都出现了类似的政治形态,民主曾经出现过,后来又消亡了。同直接民主制相近的瑞士委员会制度也是以各地方的名门望族为基础而形成的。在民主制度最早扎根和实施的英国、瑞士以及瑞典,本土教会的力量非常强大,从户籍到纳税都是以教会为轴心来实施的。以教会为中心的长老精英统治很容易转化为民主制。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著作《生死民主》(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业已证明了这一观点。②ジョン·キーン《 デモクラシーの生と死 上下巻》 東京:みすず書房,2013 年。
五、全球民主的构造
在介绍了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制之后,下文尝试对全球民主的构造进行说明。③关于地球民主主义,参见猪口孝“地球政治の秩序形成論理”(猪口孝編《国際関係リーディングズ》,2004 年,東京:東洋書林),435~460 页。以直接民主制的框架来思考全球民主,考察的其中一个层面是“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另一个层面是“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主要通过舆论调查来完成。在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要使用电子邮件、推特的内容以及相关数据库。我们现在所用的是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④ロナルド·イングルハート《 静かなる革命:政治意識と行動様式の変化》 東京:東洋経済新聞社,1978 年;《 カルチャーシフトと政治変動》 東京:東洋経済新聞社,1993 年。“ 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这一项所考察的是在联合国登记的多边条约。达成双边条约与参加多边条约通常在性质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别。双边条约是两国政府间通过协商做出的决定。即使双边条约能够反映出两国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这些条约也必须在双方政府商议的基础上签订。所以我们考察120 多个国家之间的多边条约,以议题作为划分的标准,目前的多边条约主要分为环境、和平、交流、贸易、健康、知识产权和人权七大类。由此可见,至今为止所签订的多边条约的内容都与全球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来思考全球民主,因为实行代议制的国家也是在其社会内部依据特定规则选举出代表来进行政治运作的。在20 世纪90 年代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成员国接近200 个,其中有120 个国家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彼时,一个比较褒义的说辞是:“民主是城里唯一的游戏(Democracy is the only game in town)。”然而,到了21 世纪前十年,全球民主发生了倒退。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的研究表明,当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充分实施民主、不充分的民主制度、民主和威权主义的混合物、威权主义和专制独裁。
六、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式全球民主的体现
下文对前面所提到的代议制和直接民主制的倡导者——洛克和卢梭的理论做一点深入的思考。
铃木健的《平稳的社会及其敌人》提出了很有趣的观点。①鈴木健《 なめらかな社会とその敵》 東京:勁草書房,2013 年。“ individual”这个英文单词表示个人是不可进行再分的存在。然而从脑科学的最新发现来看,即使一个个体也总会同时进行不同的思考。以此来思考,以一个个体作为代表,如果他/她同时有几种想法的话,那么代议制民主的根基就会动摇。然而,即便全球有多种多样的代表,代议制本质的理念也不会消解。
东浩纪的《一般意志2.0》也做了一个有趣的思考。②東浩紀《 一般意志 2.0》 東京:講談社,2011 年。法国启蒙时代强调对事物进行理性思考,当时也涌现出了众多思想家,他们采用类似数学解题的方法来探讨问题。卢梭是典型的代表,他在瑞士日内瓦出生、活跃于法国巴黎,曾经是百科全书派的人物之一。据说《社会契约论》出版的时候距离社会契约这一思想的提出还是存在一定时间差,不过社会契约论有很多亮点。其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主张个人只要能够理性地思考,即使没有通过投票、共同协定等形式,社会全体的契约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与此相比,同时期稍晚一些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一个世纪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没有哲学的包装,而是从精神神经学和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提出人类存在无意识的行为这一新理念。从弗洛伊德理论的角度来看,卢梭的论点就可理解为诉诸理性、没有协定、没有投票,也就是说个体之间无意识地形成了社会契约。在当代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我们可以说个体之间通过网络(谷歌)无意识地、机械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以这个思路来看,全球规模的直接民主制有可能成立。
因此,在全球民主的范围内,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制的形式,都有存在的可能。
七、模型化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可以得到“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的数据,“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的数据则是根据多边条约数据调查而得出的。二者之间的逻辑联接是全球社会契约论最大的课题。作者曾在多篇学术文章中对这一逻辑联接作过论述。①Takashi Inoguchi and Lien T.Q. Le, Toward Modeling a Global Social Contract: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John Lock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issue 3, 2016. pp.489- 522. Lien T.Q. Le, Yoshiki Mikami and Takashi Inoguchi, Global Leadership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Empirical Testing of Cooperation without Hegemony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120 Multilateral Conventions Data Deposi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issue 4, 2014, pp.523-601.这种理论性与实证性兼具并利用大数据来建立的模型在世界上实属首创,且具有唯一性。
首先我们需要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做变量分析,然后在规定价值观和规范的条件下,确定该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维度。克里斯蒂·韦尔泽(Christian Welzel)曾在其著作《自由崛起:人类赋权和对解放的追求》中阐明了这种方法。②Christian Welzel, Freedom Rising: Human Empowerment and the Quest for Eman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第一个维度是“开放的”相对“防卫的”,第二个维度是“宗教的(精神的)”相对“世俗的”。下一步是对“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进行变量分析,在分析中所依据的维度如下:第一维度是“快速”相对“慎重”;第二维度是“全球共同体”相对“公民个人权利”;第三个维度是“理想主义纽带”相对“互相约束”。
“开放的”与“防卫的”这个维度作为谱系的两端,前者以对自由最大限度的认可为方向,后者以适度的自我保护为方向。“全球共同体”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说明。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载体,为了减缓全球变暖,人类应该将导致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最低,这种理念属于前者。后者的理念与之对立,提倡根据特定产业部门和计算劳动力数量来减轻自由主义普遍化所带来的种种危害。“互相约束”与“理想主义纽带”这一维度的含义如下:多边条约的参加者和签订者应该一起受到普遍规则,特别是惩罚性规则的约束。那么,其结果是参与者的数量将不会增加,且条约的精神很可能会被削弱。与之相反,“理想主义纽带”提倡让更多的人认同并维持条约的精神。
建立全球准立法模型的操作分为两步:第一,要得到158 个国家的“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变量分析的结果和“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变量分析的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第二,要确定158 个国家在这些维度中的位置是否出现大的偏差。
八、“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与“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的关系
考察二者的相关系数有两点需要加以注意。第一,考察“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这一变量的数据库中缺少一些国家的数据。因为世界价值观调查并没有在一些国家进行,所以需要将估算值直接计入。我们采用韦尔泽所提出的方法来确定数据缺失国家的估算值,即确定这些国家属于十个地理、宗教和文化区域中的哪一个,运用该区域的平均值作为推测值。第二,当考察“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的变量分析结果与“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的相关性时,还可以考察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从“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的选择上来说,有“开放的”对“防卫的”这个维度,“宗教的(精神的)”对“世俗的”这个维度,而就“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来说,有“快速”对“慎重”的维度,“全球共同体”对“公民个人权利”的维度,及“理想主义纽带”对“互相约束”的维度。我们要看“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中两个维度与“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变量中的三个维度彼此之间的正相关系数。结论显示,“开放的”对“防卫的”维度与“快速”对“慎重”维度的相关系数非常高。“宗教的(精神的)”对“世俗的”维度与“理想主义纽带”对“互相约束”维度的相关系数也非常高。除此之外的相关系数虽然为正值,但是程度不高。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公民的价值观和规范偏好”与“主权国家参加多边条约”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高。
除此之外,还要确保各国在每个维度上给定的位置具有合理性。具体而言,要确定各国在韦尔泽所划分的十个地理、宗教和文化区域中的隶属关系是恰当的,以及十个区域在每个维度中所处的位置。我们用以下两个案例加以说明:从整体上来看,处在东亚中国文化区域的国家在“宗教的(精神的)”对“世俗的”这一维度上和处于北欧的宗教革命后诞生的强大诸国(如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是一样的,显现出强烈的世俗性的倾向。与欧美大部分国家比起来,东亚国家的世俗性更强一些。东亚的情况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论述的内容比较相似。①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 《プロテスタンティズムの倫理と資本主義の精神》東京:岩波文庫,1989 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大西洋沿岸诸国,从“开放的”对“防卫的”和“宗教的(精神的)”对“世俗的”这两个维度上来看,虽然这一区域属于防卫性的,但很明显地显现出“宗教的(精神的)”这个倾向。如果将这些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美国在“宗教的(精神的)”维度上显现出更强的倾向性。在这一点上,美国与非洲、拉美以及伊斯兰国家相似性很高。
九、新国际关系学——对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导
国际关系学远超出了对国家的利益、志向、方针、范围、目标及意图的研究,而是探究主权国家外交和战争的相关政策。每个国家情况不同,其国际关系学所采取的方法也不同,特别是在向世界进行权力扩张的西方各国。近代,西方在发现新的地缘空间上发挥了先驱作用,为在工业革命中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霸权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创立了维持其学术文化长久发展的大学、出版社以及大众媒体等。西方国家的先驱者角色也体现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其中,在20 世纪后半叶成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显现出这个鲜明的特征。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之下。据估计,世界上数以万计的政治学研究者中,90%都在美国任教。美国吸引了大量外国学者,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过程中,这些研究者对美国式的概念、教科书、论文写作方法以及美国式的叙事耳濡目染。除了理论和方法以外,课程设置、专业书籍和学术论文等方式也使美国式学术的主题选择偏好得以推广至全世界。①作者作为多个英文学术期刊的编辑,有这种深切的体会。作者猪口孝是以下四本英文学术期刊的主编: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now);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SAGE Publications, 2006-no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95);Asian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Open access journal, 2013-now)。包括大学的出版社在内,美国以及英国的学术出版社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的评阅人也大多是在美国任教的学者。
美国学术共同体竞争力很强,因为不仅有九成学者生活在美国,而且根据美国的传统,大多数的著作和论文在出版之前都需要经过严格评审,所以其学术成果易产生影响力。虽然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涌现出了一些学术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很自然地受到了轻视。然而,如果人类的思考仅仅局限在一个社会,那么学术文化发展是难以健全的。想要追求真理、推进科学发展和技术革新,应该经常吸收和利用其他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技术。从学术角度来看,美国在20 世纪以后享有压倒性的影响力。②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成功企业脚下的基石正在崩溃。Schumpeter: The Great Divergence, The Economist,Nov. 12, 2016, p.58。因此,如果被誉为最强的学术共同体进行了长期的垄断,其一旦瓦解,学术发展将遭受重大的损失。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因此,为了让美国不再一家独大,也为了谋求美国以外的各国学术和文化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被一国所垄断的国际关系学,而是应该探求如何构建一个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