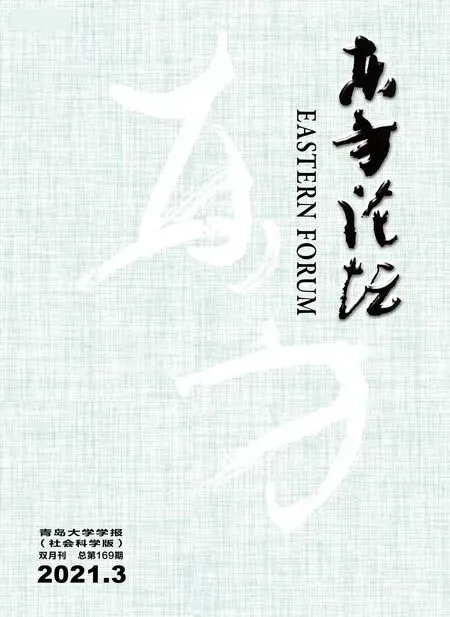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经文文法研究
郭超颖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
在经学话语中,儒家经典皆是圣人的立法之言,是带有立义旨趣的“作”,《礼记·乐记》所谓“作者之谓圣”。五经之中,《春秋》笔法有微言大义,《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仪礼》言词关涉名义,文、事、义兼备,二者同是汉代治世传统中的大宗,所载礼仪制度与事例裁断,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与比谊会意的作用,有其相通性。黄侃云:
五经应分二类,《易》《礼》《春秋》为一类,《诗》《书》又为一类。《诗》《书》用字及文法之构造,与他经不同,《易》《礼》《春秋》则字字有义。《诗》《书》以训诂为先,《易》《礼》《春秋》以义理为要。《诗》《书》之训诂明,即知其义;《易》《礼》《春秋》之训诂明,犹未能即知其义也。①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 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8页。
经有文法,是由经的性质决定的。中国早期核心经典,是具有价值期许与实践引导意义的事理文本经典。经有载史功能,但更体现早期文明对朴素哲理的制作。经的治世效用,就是社会治理与自我规正。治理的要义在于合理,使其有序,有法,有张弛。《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①《周礼注疏》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3页。事有梳理,则文有次序。对于《春秋》经来说,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事理逻辑则尤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事情本身是否符合道义。相应地,《春秋》文法也最显著。
《仪礼》经文文法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理路。首先,礼有尊卑亲疏大义,这不仅体现在仪制的不同,而且用字用辞也不相同。而且文、事、义三者本不孤立存在。其次,《仪礼》某些篇目两两相对存在,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仪节程序多重复伦类的情况,出于简明以及各自表述需求的不同,经文记述时就要有所裁剪。再次,礼仪活动关涉事情的周备,要有谨严谦敬的精神,体现在经文的记述要明白而没有误会,在名物仪节的千头万绪中,经文要有的放矢。以上都是《仪礼》经文文法特色生成的一些事理依据。
若《聘礼》记载使者行聘途中若经过其他国家,到达该国国境时就要派次介前去借道。次介执束帛至该国外朝表明奉命请求借路,言“请帅”,而后把束帛放在地上。所途经国的下大夫拿取束帛,入朝向国君禀报,出来向使者回复国君允许,经曰“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受币”。郑玄注:“言‘遂’者,明受其币,非为许故也。容其辞让不得命也。”②《仪礼注疏》卷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48页。遂,继事之辞也。经文曰“遂受币”,表明收受束帛是行礼仪程,不是因为同意借路。用“遂”字,就是容许出现推辞或辞让的情况。若《有司彻》侑俎,经曰“羊左肩、左肫”,“豕左肩折”;主人的阼俎,经曰“羊肉湆,臂一”,豕脀“臂一”,尸用右体,此二者皆用左体,而主人不言左臂,郑玄注云:“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③《仪礼注疏》卷四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208页。这是因为主人是大夫,位尊,左体贱,所以空其文以自明。《燕礼》君往西阶酬宾,经曰“宾升,再拜稽首”,郑注云:“此宾拜于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敌偶于君。”④《仪礼注疏》卷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18页。尊者俯就卑者,空其文。《春秋·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穀梁传》曰:“不言公,高傒伉也。”⑤《穀梁传注疏》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385页。《公羊传》曰:“公则曷为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⑥《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236页。《春秋·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穀梁传》曰:“不言公,处父伉也,为公讳也。”⑦《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404页。国君与大夫执礼会盟,是尊卑伉礼,经文在记述时便采取了空文这种方式,来为尊者隐讳。
经典的一字一辞,蕴藉着周备的义理,那精究圣人立法之言,即是解经的题中之义。“古之明者解经,莫不精究其立言之法。虞氏之于《易》,郑氏之于《禹贡》、于《礼经》,子夏之于《丧服》,三《传》之于《春秋》,某氏之于《夏小正》,皆是也。”⑧曹元弼著,周洪点校:《礼经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不仅章句传注,《尔雅》作为“六艺之钤键”的训诂之作、《说文》作为“经艺之本”的文字学之作,同样如此。郑玄先通《春秋》,又精《汉律》,对《仪礼》经文文法做了开拓性的工作。首要是为《仪礼》立法,即建立全然的经文文法系统;其次是借助文法训诂制度、析理仪节、阐述义理。魏晋南北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把《尚书》《诗经》归为一类,二者“诂训茫昧”,通《雅》则晓,而“寻理即畅”;与之相对,是《周易》《春秋》,《易》“入神致用”“言中事隐”,《春秋》“观辞立晓,访义方隐”。《仪礼》则片言为宝,“执而后显”。
刘勰对经文文法的分类,实质上体现了六朝时期经学系统论构建的学术风尚,贾公彦《仪礼疏》《周礼疏》在经注阐释的维度与层面上,并未偏失。而且贾公彦善于把握《周礼》《仪礼》关系,但唐宋以后,《仪礼》学学术风尚发生转型,文法是经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为新诠释体系的建立而破除,故而这一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清前期的礼学研究颇有气象,甚有呼应汉唐注疏的志趣,这包括他们对文法、注疏体例、礼义等多方面的关注。以《仪礼》文法为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对《仪礼·士昏礼》婿的称指异辞做出揭示,云:
“主人爵弁,纁裳,缁袘。”注:“主人,婿也。婿为妇主。”“主人筵于户西”,注:“主人,女父也。”亲迎之礼,自夫家而行,故婿称主人;至于妇家,则女父又当为主人,故不嫌同辞也。女父为主人,则婿当为宾,故曰:“宾东面答拜。”注:“宾,婿也”对女父之辞也。至于宾出而妇从,则变其文而直称曰“婿”。婿者,对妇之辞也。曰“主人”,曰“宾”,曰“婿”,一人而三异其称,可以见“礼时为大”,而义之由内矣。①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278页。
推重朱子的陆陇其在追随朱子读书之法时,从经注疏切入,自然地揭示出经注疏的立文之法。陆氏《读礼志疑》云:
疏内用字,如同时则云“俱时”,之类则云“之等”,如此字法,今人罕用,见《有司彻》“主妇荐豆笾”条。又据彼决此,疏内往往单用一“决”字,如《有司彻》“宾长献尸”条:云“不使兄弟,不称加爵,大夫尊也”者,此决《特牲》云长兄弟为加爵,又众宾长为加爵,不言献。②陆陇其:《读礼志疑》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6页。
陈澧言:“初读唐疏者,于此等每不能解。清献为指示之,亦有益于初学。”③陈澧撰:《学思录》,《子海珍本编》(大陆卷)第1辑第1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76—577页。然而乾嘉经学大盛在即,随之而起的专经研究体式,不在于恢复六经的汉唐经学系统,也不可能与汉唐注疏而成“羊体嵇心”。所以诸多呼之欲出的议题,便在时代风云中转瞬即逝。转而或成一部大的新疏,或据一端而成考据。这并不意味乾嘉考据对文法研究无所作为,只是其主要学术任务并不在此。
至章学诚欲融通经史之义,再提《易》辞通于《春秋》之例④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这是一个典型的风向,即重回归经文文法议题。道咸年间,陈澧受陆陇其启发,倡议“经注疏立文之例”与礼意⑤郭超颖:《仪礼文献探研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1—158页。,对于《仪礼》学来说,这是清代后期的重要节点。因为探求礼意,核心是经注,这就把焦点从辨析诸家之争,拉回经文本体,直接跳出了此前过度纠葛于敖继公《集说》的学术失误。此后,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已认识并可运用文法解决问题。如《仪礼》 郑玄厘定的宿戒礼仪,有“戒”“宿”“速”之别,黄以周云:
近人犹有谓宿、速音近通用,未达郑意者也。凡经言“宿”者,皆在期前,如《士冠》宿宾、宿赞,《特牲》宿尸、宿宾,文列“厥明为期”之上。诸言“速”者皆在即日,如《乡饮》《乡射》“主人速宾”,文次“羹定”之后。经语明显,胡可混也。①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9页。
又如,《周礼·司仪》记载诸侯相朝的礼仪,“宾三揖三让,登,再拜授币,宾拜送币。”郑玄注云:“‘登再拜授币’,‘授’当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孙诒让云:“郑意下文云‘宾拜送币’,则此不当云授币,且‘授币’与‘再拜’文相属,再拜属主君,则授币非指宾授玉可知,故必破‘授’为‘受’也。”②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6页。
曹元弼的《礼经学》就是在这些基础上,提出“经文例”的概念:
圣人既本之以为大经大法,详节备文而笔之为经,垂天下后世法,一字一句又皆准此以辨言正辞,故礼有礼之例,经有经之例,相须而成。凌氏释礼例,而未及经例,然经例不明,则圣人正名顺言、决嫌明微、精义所存,不著不察。而经文详略异同,若有与礼例不符者,何以解害辞害志之惑,而深塞离经叛道之源与?
故曹氏认为:“夫治《礼》如治《春秋》,亦如治律,《春秋》与律,一字不可忽也。故治《礼》者,必以全经互求,以各类各篇互求,以各章各句互求,而后辞达义明,万贯千条,较若画一。”③曹元弼撰,周洪校点:《礼经学》,第30页。曹元弼辑郑注之义,总结为50例。
在经文文法研究中,我们也还须注意到:“文法”是否可以直接称为“文例”,或文法之学是否等同于以往我们理解的礼事条例?条例之学一直是治经之法,礼学研究则更加看重“凡例”的总结,但对“例”的过度聚焦与路径依赖,同样是脱离本体的行为。因为“例”的背后侧重“事”,“法”的背后侧重“义”。事理法度、情理依据,并不是简单的条例,条例在于归纳,而礼义原则在于演绎。也正是因为缺乏更深入地探究原理,所以“例”的内容会流于繁杂,也会失于囊括内容的狭窄。这是我们应该重新检视的问题。
二
《仪礼》经文的简质,并不妨碍其意含的丰富。如《士冠礼》“筮于庙门”仅四个字,但是包含的意思却异常丰富。注云:“冠必筮日于庙门者,重以成人之礼成子孙也。‘庙’,谓祢庙。不于堂者,嫌蓍之灵由庙神。”为何于庙门筮,且又为何在门而不在堂?其一,在庙门筮日,是敬冠事而尊其礼。既重其事,则不敢专擅,所以于庙门筮,是自卑而尊先祖的意思。其二,仅筮于“庙门”,而不像加冠行于庙堂,是因蓍筮自有其灵。若蓍自有其神,却在庙堂筮,似乎是蓍之灵得于庙神,而所尊杂糅不明,是失敬之事。
同时,《仪礼》经文要记载的事理关系也并不简单。比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四篇都有设立司正的仪节。但其中的道理却存有差异。从礼仪内容来看,《乡饮》《燕礼》主于饮酒,《乡射》《大射》饮酒礼后有射事,其略于饮酒;从礼仪级别来看,《乡饮》《乡射》分属大夫、士礼,《燕礼》《大射》则属诸侯礼,所以仪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关于司正设立的环节,可概括为“爵备乐作”之后。对于《乡饮》,主人已向宾、介、众宾等献酒,升歌演奏都已完备,故郑注云“礼乐之正既成”。《乡射》不同于《乡饮》,不歌、不笙、不间,今有合乐,故郑玄云“爵备乐毕”,如贾疏言:“合乐讫是乐毕。以无升、笙与间,故不言乐成而云毕而已也。”《燕礼》君是真正的主人,其将为宾、卿、大夫举爵,且作乐也无简省,故郑玄云“君三举爵,乐备作矣”。《大射》主于射事略于乐,郑注云“三爵既备,上下乐作”。《乡饮》《燕礼》设司正时活动基本将要进入到燕欢阶段,《乡射》《大射》则还要进行最为核心的射事环节,所以司正设立时可称为爵备乐作后,且为监察相应礼仪环节的仪法。由此可见,即使相同的仪节,情理也可大不相同,经文笔法的处理即不同。
从整体来看,《仪礼》在叙事陈情、器物设置、仪节位处等方面的行文法度都有各自内在规范逻辑,还有各自情由下的类型区分,尊亲等杀、正名顺言、决嫌明微,各不相同。以下试举10例:
1.叙事不相夺伦。在程式主干叙述中,主、客方出现的先后次序,实际是仪节的归属问题,如该仪节段主旨在主方,叙述以主方领起,客方是承应方,不抢夺行文,整体行文不变化叙述逻辑。当仪节繁复,二者并行,先叙一事毕,再叙述一事,以与该阶段主题相映照的主要问题为先。
2.行为语序谦己敬人。《乡射礼》曰:“主人堂东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宾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阶,阶下揖,升堂揖。宾堂西,主人堂东,皆释弓矢,袭,及阶揖,升堂揖,就席。”郑玄注云:“将袒先言主人,将袭先言宾,尊宾也。”贾公彦疏云:“袒是尽敬之事,袭是修容之礼,故上经将袒先言主人,此经袭则先言宾,是尊宾故也。”①《仪礼注疏》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02页。
3.卑者省文因事得著。《聘礼》曰:“贾人东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上介。”②《仪礼注疏》卷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54页。前面开始行聘,宾入次,币陈在门外,贾人即面朝东站立其旁等待取圭,但上经没有交代,直到此才阐明,是事至而言,贾人卑贱,接着有事交代即可,举后明前。
4.文质尊卑异辞。《聘礼》 使者向主国君行聘享后,会请求慰问主国卿大夫。使者此次拜访卿有两个环节:一是赍聘君之币,致己君之辞命;二是宾以自己名义所行面卿的私礼。面卿,就如聘享礼中的“私觌”,郑玄注云:“觌,见也。”③《仪礼注疏》卷二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57页。前称“觌”,此称“面”,“面”轻于“觌”,也表示与私见国君相比威仪要简略。《乡饮酒礼》饮酒活动将要进入无算爵阶段,司正使二人举觯,分别向宾、介进酬酒。举觯二人分别进到他们席前,把觯放置在脯醢旁边,经文宾“取”觯,而介曰“受”④《仪礼注疏》卷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988页。,两种不同的表述是区别尊卑在文字选用上的体现。即设文用字,尊者和卑者同事而异辞,以不相因袭而凸显尊卑分明。
5.温婉曲言与质言。特谓之“侧”,全谓之“纯”,正立曰“疑立”。但谦敬之曲言的使用也有限度。《士昏礼·记》曰:“辞无不腆,无辱。”《日知录》:“‘归妹,人之终始也。’先王于此,有省文尚质之意焉,故‘辞无不腆,无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礼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为嗣续之基,故以内心为主,而不尚乎文辞也,非徒以教妇德而已。”①顾炎武撰,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6.详细仪节突显尊敬。《公食大夫礼》:“赞者东面坐取黍,实于左手,辩,又取稷,辩,反于右手,兴以授宾。宾祭之。”②《仪礼注疏》卷二十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81页。这里详细赞者仪节,尤其写明赞者“兴授”,而省宾“兴受”,是对宾的礼遇与尊敬。而下经授肺,经曰“宾兴受,坐祭”③《仪礼注疏》卷二十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81页。,明言“兴”,是重牲。
7.尊重大礼详其规格。《聘礼》主国君派遣卿向使者馈赠饔饩,经曰:“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牛、羊、豕、鱼、腊、肠胃同鼎,肤、鲜鱼、鲜腊,设扃鼏。膷、臐、膮,盖陪牛、羊、豕。”郑玄注云:“此馔先陈其位,后言其次,重大礼,详其事也。”④《仪礼注疏》卷二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59页。经文在叙述时,先言设馔的位置规格,然后再具体交代馈送之物及具体陈放顺序。这是因为饔饩是大礼,所以一是信息交代详细,二是讲求阐述的次序。
8.循序渐进程度有别。《聘礼》:“厥明,讶宾于馆。宾皮弁聘,至于朝。宾入于次。乃陈币。……摈者出请事。”郑注云:“既知其所为来之事,复请之者,宾来当与主君为礼,为其谦不敢斥尊者,启发以进之。”⑤《仪礼注疏》卷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53页。较近郊请行“谦不必也”,二者皆是知而示谦,前者为始来,是不期待必然来与自己聘;后者主君将与为礼,事定而请,是尊宾不直斥,取启发渐进之意。又:“及庙门,公揖入,立于中庭。宾立接西塾。几筵既设,摈者出,请命。”郑注云:“至此言‘命’,事弥至,言弥信也。”⑥《仪礼注疏》卷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54页。此则直言“请命”,事至言信,正问请命。
9.决嫌明疑。《有司彻》主人向兄弟献酒,经文:“辩受爵。其位在洗东,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荐脀设于其位。”⑦《仪礼注疏》卷五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214页。此节主人向兄弟献酒,长兄弟先升堂,经曰:“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饮,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辩。”“皆若是以辩”是经文因藉长兄弟受献,顺带总体上交代众兄弟受酒之仪。经文接言此条,在“辩受爵”承上文之意后转而谈及兄弟位处,众兄弟升堂受爵,毕竟与长兄弟不同,所以要单独说明是“升受爵”,没有拜仪。经文先交代“其位在洗东,西面北上”,而后再言荐俎在此,因为兄弟的位处此前经文没有言及,先著其位可明由此而升堂,得献后又于此设荐俎。若把位置放于设荐时交代,则有不知初位的嫌疑。
10.内外事权明确。《聘礼》:“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郑玄注云:“变‘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⑧《仪礼注疏》卷二十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68页。行聘,聘于其君与夫人,然各有所当。聘邻国君,使者受命于君,还则向君反命;聘于邻国夫人,当受命于夫人,然妇人无外事,实亦受命于君,但经不云“反命”,变“致命”,若本非君命,犹夫人之命。
目前,《仪礼》经文文法问题没有继续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一般是在研究郑玄注、贾公彦疏解经训诂方法时,有的条目涉及到某些经文例①如李云光教授《三礼郑氏学发凡》在探讨郑玄训诂时,对经文的省文、空文、略文、互文之例有过简要讨论。马楠教授的《比经推例》,以《春秋》、三《礼》为讨论中心,对汉晋比经推例的治经方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于三《礼》来说,这个例探讨的是礼例,但反向牵扯到《仪礼》经文文法的问题,主要还是互文、上下相照等。。
曹元弼《礼经学》总结的经文50例,尚有待继续审视和分析。这里面包括文例,还有经文立法之言的理论探讨,以及经史贯通研究方法的立论等。虽内容丰富,但所涉讨论归属范畴不同。具体文例也需进一步条理,如经文的“互见”法,总分为“有前后诸篇互见者”“有数节中互见者”“有一节中互见者”“有数语中互见者”“有一句中互见者”“凡互见之法《丧服》尤多”等计六例,这些是互见法的具体运用表现以及各篇中的应用情况总结。有些已经简单归类的文例仍需深入讨论。
如曹氏所列“异义不嫌同辞”例下,有《士相见》以“走见”为“出见”。这是经文在隆礼取急切之义时的用词法度问题。《士相见》曰:“若先生、异爵者请见之,则辞。辞不得命,则曰:‘某无以见,辞不得命,将走见。 ’先见之。”郑玄注云:“‘走’,犹出也。先见之者,出先拜也。《曲礼》曰:‘主人敬宾,则先拜宾。 ’”贾公彦疏云:“训‘走’为‘出’者,亦谓士见异爵,取急意而言走,其实非走,直出也。”②《仪礼注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978页。经文中“将走见”的“走”字,在此是“出”的意思,以出而言走,是士见异爵,取其急意而言走。下经曰“先见之”,是士即出门,且敬自屈尊而来的先生、异爵者,先行拜礼。元敖继公改“先见之”之“先”为“走”。③敖继公撰,曹建墩点校:《仪礼集说》卷三,《儒藏》(精华编)第4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清吴廷华云:“以本欲往见,今先见之于家,曰‘先’者,对往见为后也。”④吴廷华撰,徐到稳点校:《仪礼章句》卷三,《儒藏》(精华编)第4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3页。清胡培翚《正义》认为吴氏“其说亦通”。⑤胡培翚撰,段熙仲点校:《仪礼正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敖、吴二家说法皆非,仍当遵从郑义⑥《日知录》卷三十二“语急”例有“古人多以语急而省其文者”的观点,如《公羊传·隐元年》:“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如,即不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子鱼曰:“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正义》曰:“如,犹不如。古人语然,犹‘不敢’之言‘敢’也。”详见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830页。此后,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皆沿袭其说。笔者按,“语急例”也就是牵扯问题较多,目前缺少对“语急”概念的厘清,该问题尚需细致探讨,然而语言根据语境语义而有相应修辞文法是存在的,所以对“语急例”不宜轻易否定。《士相见》以“走见”为“出见”实质就是隆礼取急切之义。。
三
文法对先秦两汉经典文献意义非常。虽然史学独立发展之后,史藉自有体例章法,然而正如赵生群先生所论:“重视礼义,偏重价值判断,为明理而叙事,是《春秋》《左传》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区别于史书的共同特征。”⑦赵生群:《〈春秋〉〈左传〉区别于史书的几个特征》,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讲座,2021年4月14日。有鉴于此,经文文法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元典研究来说,应十分注意。
以《仪礼》来说,《仪礼》多名物度数,前贤论读《仪礼》之法,首在推重分节、绘图、释例三端,如陈澧、皮锡瑞、梁启超等都有揭示。作为方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不能视其为《仪礼》学的三个统摄性构成。这既不符合《仪礼》这部经书的历史地位角色,也有所偏离《仪礼》这部经书的思想精髓。事理逻辑与礼义法则,才是汉唐间礼学发展的主旨诉求,而文法是其中关键之一。
训诂经文经义,有自身的原则和章法,这在汉魏经师时代是比较明晰的。经师诠释经书字词时,有其基本依循的原则。黄侃曾指出:“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不同,“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一部分。经学训诂虽有时亦取其通,必须依师说展转求通,不可因猝难明晓,而辄以形声通假之说率为改易也”,是“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①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对黄侃这一经学思想主脑的理解,黄焯云:“盖一则可因声义之联系而曲畅旁通,一则宜依文立义,而法有专守故尔。清世高邮王氏父子深于小学,以之说经,实多精辟之义。乃承其业者,少究故训之原,而动言通假,凡于经义之难明者,辄云某与某通,某为某借,名为通经,实则改经乱经。”②黄焯:《毛诗郑笺平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简单来讲,从整体而言,五经就其性质内容,本有聚类分层,所谓读经次第,藉古注疏而识经文文法以及训诂的道理也就正在此。故而黄侃言: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③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 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第10页。
五经各有其经法道统,而其传者宜各有师法家法,所以经学训诂首在缘经作注,虽可博采众长,但应有所宗主。
经学与史学、子学皆不同,贵在经义,也就是中国核心的哲学思维方式。古人认为,经义无限接近事物本质,是哲学范畴上的最优存在,所以经义应该有常道定数。而经义的理解建立在经学、经文之上,这就决定了经学训诂的原则。在理解经典,宜意识到古说逻辑依据的学术文化背景。《左传·哀公十二年》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④《左传正义》卷五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170页。杜预注云“相辞”为“各以礼相辞让”,其隐含的语义背景是:诸侯相会正礼完毕之后接续的盛礼,盟主对其他与会者致送币帛,所会地主人致送饮食,所以“相辞”是相会盛事之后的礼宾宴欢环节。而杨伯峻理解为“辞别,告别”,显然是结束环节。那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以文字训诂直接取舍。
经学训诂里,包括名物、制度、文意,还有经义。以往对经义的认识和定义并不全面,更侧重目的和意义,但在此之外,还包括原因与依据,也就是经义包含着可以令人融汇贯通实践的法则。简单讲,就是事理法则。而事理法则倚重文法。《左氏》善于礼,体现在它记载了礼仪制度,其行事周折、经文法度也无不包含礼义。如《左传·昭公元年》载郑简公设享礼招待赵孟、孙叔豹、曹大夫: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①《左传正义》卷四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2021页。
这段文字就委曲有趣。《礼记·曲礼》曰:“偶坐不辞。”郑玄注云:“盛馔不为己。”②《礼记注疏》卷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243页。盛馔不为自己而设,作为陪客也没有推辞主客不当享用盛馔的道理。反之即是一种自我增加尊贵的行为,也将置人于难安的境地,无疑是失礼的行为。晋为霸主大国,文子为正卿,在诸侯国享有崇高威名。虢之会主要是晋楚霸权调平的会盟,赵文子代表晋国,是一方之主。经文也一语点题:“赵文子为客”,即为正宾的意思。这也是兼享情况下,赵文子请辞五献规格的前提。也就是说,郑简公的这次招待,无论哪个层面,赵文子都是正宾贵客,故文子当礼,是礼敬的主要受方,有请辞的主动权。从主人尊重宾的意思来看,也即有决定权。
段熙仲先生《春秋公羊学讲疏·属辞》谓:“孔子之修《春秋》,修其辞也,故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谓其义?因鲁史加王心之谓也。何以见之?则于属辞见之。”又云:“君子之修辞,何以若是其慎也?”③段熙仲著,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3—154页。原因在于:于文,有时而嫌;其不嫌者从同,则其嫌者必有以避之矣;有时而辞穷也,有不辞之当辟也,有不得已而言我之辞,此《传》所以言君子辞也。段先生还总结这种述传而言的体例文法说:
君子之于辞也,有正辞,有常辞,亦有微辞;有异辞、亦有同辞;有内辞、亦有外辞;有远近之辞,有褒贬之辞,有予夺之辞,有进退之辞,有贤之、善之、喜之、幸之之辞,有大之、重之之辞,有抑之、略之、贱之之辞;有恭辞,有卑辞;其尊尊也,亲亲也,贤贤也,有为讳之之辞;其不得已也,或从而为之辞。④段熙仲著,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第155页。
同样,《仪礼》经文文法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领域,仍有诸多方面可以展望。回归元典本身,充分尊重经传注疏的事理逻辑与经义诠释,未尝不是“往者虽旧,余味日新”的学术推进。
从礼学研究角度说,《仪礼》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它确立了中国古代仪典的大体范式,其丧礼服制奠定了中华传统法典的伦理化,这些都是以经注诠释为中心的。经文文法是经注理解的关隘,对文法的忽视与误读都会造成经义理解的偏失。所以从礼学、礼制、史学的角度,需要对其所本的《仪礼》的经文文法作以研究。《仪礼》学在清代大盛后也积累了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扯到名物制度等方方面面,许多都与经文文法有关系,亟需厘清,正本清源。
从经学研究角度说,经学上有“六经皆礼”的概念,对《仪礼》经文文法研究可以促进诸经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对《仪礼》述作之法的探求,不但丰富对儒家元典述作旨趣的认识,而且可以促进经学领域相关诸多问题的研究。章学诚推重《春秋》的惟义求之,并推至古文辞方面,《仪礼》经文的文法既然与《春秋》类似,则需要考虑它在经学、史学、文学上处于哪种维度之中。此外,宋人《春秋》学诠释仍然秉持着“比事属辞”的治经传统,而《仪礼》自唐代衰微以来,经文文例的风貌精神就堙没在历史之中,这无疑给唐以来的文学、思想带来影响。章学诚基于史学学统,对桐城派本于经学与文学的学统,或者说对韩愈忽于《春秋》教的道统的批判,同样与《仪礼》经文文法有着千丝万缕关系。
从文章学和语言学研究角度说。《仪礼》经文体现着礼的意涵,这种叙事行文上对尊尊、亲亲、长长、贤贤、男女有别大义的措置得恰好,可以加深对传统修辞学的认识。如果把《仪礼》文本理解为一种礼仪程序仪节的问题,这种文体简至幽微的风格特点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对它的研究可为史学、叙事、古文辞诸方面提供新的思考。先秦专书语言有很大相通之处,文法也是如此,《仪礼》经文文法的解读对先秦专书语言研究和义例研究有一定帮助。
综上所述,文法是语言思维的表现,《仪礼》作为记录礼仪程序的文本,它的仪典与文本特性都具有历史生命力。即使现代社会,各类日用文体,传媒形式,在反映典礼内容时,也面临着叙事手法和剪辑艺术的要求,同样蕴含着礼的精神。所以《仪礼》经文文法的经典样式可以加深对现代礼仪的了解,便于理解它背后的情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