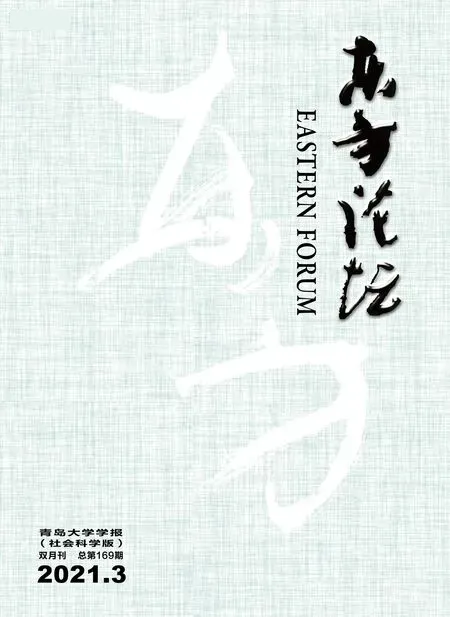《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
符杰祥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1903年,在日俄战争前夕,尚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的青年留学生周树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刊载在《浙江潮》第五期与第九期上。对于自己的“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①朱正:《鲁迅传》(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46页。,鲁迅并不乐意承认,而且在三十多年以后还坦白是“故意删掉的”②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对鲁迅来说,其难言之隐在于,除了这篇是翻译还是创作难以说清之外,确认小说身份的材源也始终无法找到。以至于在《斯巴达之魂》发表三十多年后,鲁迅因“记不起”这篇小说的“老家”,而有了“从什么地方偷来”之说:
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③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3、4页。
其实,正像他更早谈论的著名的“幻灯片”故事一样,鲁迅三十多年后的回忆也未必完全可靠。回忆不过是一种“忘却的辩证法”①符杰祥:《忘却的辩证法——鲁迅的启蒙之梦与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同样“可疑得很”。鲁迅自己也明确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从保留下来的鲁迅手稿来看,关于早年文章回忆的《集外集》序言有多处修改,比如这一段文字:“没有留存底子,或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鲁迅手稿原为:“是或者因为自己疑心是抄译”。“疑心”,说明鲁迅对自己的结论也不能完全确认,是“连自己也怀疑”的,只好用这样模糊的说法。遗憾的是,对这种模糊的说法,学界并未有太多的辨析与怀疑,在绝无怀疑中把“疑心”“好像”这样的模糊说法无限放大,以致无比清晰了。因为一直没有从鲁迅后设的回忆话语与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多年来的讨论,也一直集中在是否“偷来”、是翻译还是创作的争辩上。②符杰祥:《鲁迅早期文章的译/作问题与近代翻译的文学政治——从〈斯巴达之魂〉“第一篇”疑案说起》,《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被鲁迅本人所误导的讨论,并不妨碍近年来相关讨论所形成的学术价值。不过,倘若跳出鲁迅所设定的套路,从材源本身来看问题,也未尝没有新的意义。
鲁迅自言:“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③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固然说明初到日本的鲁迅外文程度不足,这是他的短处,但反过来看,现实的短处或许正可以逼出他既往的长处。因为“初学日文”,阅读明治时期读物的知识经验尚不能完全发挥,而过去在国内长期积累的知识地层与阅读经验反而会在一种“急就章”的写作中被充分调动与激发出来。由此发挥出来的中国知识与文化视野,就成了区别于明治日本风气的优长之处。在最初与明治日本相遇的时期,中国视野限制了他,但也让他有所发挥,大展长材。不可否认,明治日本的思想风气与知识经验对周树人从无名的留学青年成长为著名小说家,具有非常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意义。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东渡日本求学的留学生是带着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志愿而来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气息同样鲜明。尤其是对初到日本的青年留学生周树人来说,刺激他热血澎湃、奋笔疾书的初心是什么?是因中国或为中国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周边的核心是什么?是身处异域东京而相互影响的中国留学生圈。对于明治日本,作为中国留学生的鲁迅其实也是“在而不属于”的。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不见而见的、无物无形而无时不在的中国之影。这是他思考问题的背景源头,也是最终的归宿所在。
一、译/作之争与材源问题
《斯巴达之魂》作为一篇不被承认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因为来路不明,身份可疑。问题首先出现小说是“创作”还是“翻译”的争议上。是承认为“创作”,还是承认为“翻译”?作者自己尚且态度模糊、莫衷一是,论者也难免各执一端、相持不下。
先从署名来说,《斯巴达之魂》在发表时只署“自树”,未署原作者与翻译底本。而鲁迅同期联袂发表的译作《哀尘》则很明白,署为“法国嚣俄著 庚辰译”。但小说的引言,却出现了“译者无文”这样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起这篇小说,鲁迅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动摇,言辞之间开始模糊起来。鲁迅并没有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完全否认与推翻小说在《浙江潮》发表时的署名方式,他只是表示出一点因“年远失记”而发生的自我怀疑。这样的解释,自然不会澄清谜团,而只能留下更多的谜团。
《斯巴达之魂》的另一个“古怪”之处在于,自1903年发表始,相关评论与研究长时期以来几乎处于空白。直到1976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杨天石的《〈斯巴达之魂〉和中国近代拒俄运动》,才算打破了寂寞。而此后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是创作还是译作”的争论上。1987年,李昌玉发表《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一文,从“编集和署名”“许寿裳的回忆”“对照《斯巴达之魂》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三个方面入手,认为《斯巴达之魂》是创作而非翻译或改作。①李昌玉:《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东岳论丛》1987年第6期。此后,吴作桥、蒋荷贞等人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出“创作”说。吴作桥的“主证”有四:一是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所说的“悔其少作”,二是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称《斯巴达之魂》是“所作的东西”,三是《斯巴达之魂》的小序里有“掇其逸事”一说,四是署名“自树”与《哀尘》列出原作者不同;“旁证”即为许寿裳和沈瓞民的回忆。②吴作桥:《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上海鲁迅研究》第4辑,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年;吴作桥:《鲁迅随谈》,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96页。蒋荷贞的观点、论据与李昌玉、吴作桥的文章基本相同,认为《斯巴达之魂》和《故事新编》一样,都取材于古籍,是一种“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③蒋荷贞:《〈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9期。陈漱渝在《〈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一文中,指出小说引言中有“译者无文”一句话,④陈漱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在创作和翻译之间,相对合理的说法是编译、译述,也就是既有翻译的成分、也有创作的成分。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认为,《斯巴达之魂》“是一篇既是创作又是翻译的混合性作品”⑤[日]樽本照雄:《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岳新译,《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李文革和王瑞芳称为“改作”⑥李文革、王瑞芳:《从改写理论看鲁迅早期的“改作”及其成因》,《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期。,高旭东则提出“是带有编译性质的自创”⑦高旭东:《鲁迅:从〈斯巴达之魂〉到民主魂——〈斯巴达之魂〉的命意、文体及注释研究》,《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之说。
相对而言,重视实证的日本学者更注重材源问题,也做了大量详实而有价值的工作。樽本照雄以希腊史、波斯史的固有名词为线索,做了详实的考证,指出了鲁迅在编译《斯巴达之魂》时可能参考的相关日本文献资料。据其统计,鲁迅可能阅读的文献有宫川铁次郎的《希腊罗马史》(1890年博文馆印行)、涩江保的《希腊波斯战史》(1896年博文馆印行)、冈本监辅用汉文编纂的《万国史记》卷六“希腊国记”(内外兵事新闻局1879年印行)等几种。但这些尚属于旁证和猜测,樽本并没有找到和《斯巴达之魂》文字上完全吻合的原著。在西方史书中,关于温泉关战役最早、最详细的记载是有“历史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但在鲁迅写作《斯巴达之魂》之时,《历史》在日本并无完整译本。所以,樽本最后的结论是:“也许有一混合记述赫罗德托斯和普鲁塔尔考斯的原作(欧美文献)将其重译成日语的文章,那也是复数,鲁迅莫非从此得到的资料?果然如此,那是编辑翻译,也就是编译。”①[日]樽本照雄:《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岳新译,《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赫罗德托斯和普鲁塔尔考斯即通译的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中文译者对希腊史学显然不够熟悉。
另一位日本学者森冈优纪则在樽本照雄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考证与探讨,指出明治时代包含希腊史的几本世界史著作是鲁迅可能阅读与参考过的。如巴来(Peter Parley)的《万国史》曾多次印行。明治时期正式的希腊史译著应是楯冈良知等人翻译的《希腊史略》,该著于1872年印行,是日本最早出版的希腊史著作。《希腊史略》译自Elizabeth Missing Swell的A First History of Greece。另外,还有桑原启一编译的《新编希腊历史》(1893年经济杂志社印行)、涩江保著《希腊波斯战史》、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和《稿本希腊史》等。在希腊史著作之外,森冈优纪还详细考察了明治时期的流行的几种少年杂志与妇女杂志,如《少年文武》《日本之少年》《尚武杂志》《少年园》《妇女与儿童》等,指出其中记载的血战温泉关故事对小说《斯巴达之魂》的可能性影响。②[日]森冈优纪:《明治杂志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森时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卷,袁广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8页。
二、被忽略的中国知源
日本的实证研究做了很多富有价值的工作,但也存在重视日本忽视中国、重视历史忽视文学的不足。强调鲁迅与明治日本的知识联系及其影响当然是重要的工作和正确的方向,但如果仅限于此,而无法从全球视野与文明史看问题,也会忽略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之中日本之外其它国家知识界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法从更宏大和更完整的历史视野对斯巴达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的知识源流、传播影响做出全面分析与整体判断。
尽管晚清政府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封闭、保守、愚昧、颟顸、衰落、软弱,处处被动,处处挨打,但中国知识界同时亦兴起一种走向世界、译介西方文化的自强、维新潮流,甚至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维新潮流在晚清帝国那里尽管备受挫折与打击,但毕竟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风气,也培育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鲁迅能够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读书,进而去东京留学,新的知识养成与新的思想发生,就是这种新风气所孕育的成果。樽本照雄对《斯巴达之魂》几处虚构情节的指责,有的合乎史实,有的则毫无道理,多少暴露出其对希腊史的隔膜和中国视野的缺失。③樽本照雄对《斯巴达之魂》几处史实的错误批评,如爱慕者男青年克力泰士作为第三者追求女主人公涘烈娜的问题,仅仅根据普鲁塔克在《道德论丛》第十七章第五十三节第二十条所引用的一则传说,并不合乎斯巴达人的情爱观念。在斯巴达文化中,一切都是为了养育强健的男儿与战士,几乎没有贞节观念,也没有所谓通奸的概念。可参考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汉斯·利希特的《古希腊人的性与情》等书。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笔者会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详细论述。
晚清以来,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包含大量地理书、历史教科书的西学书籍开始在中国译介与传播。比如魏源传入日本的《海国图志》(1842—1852),是在林则徐的《四洲志》基础上完成的,里面就已有希腊国的记录。徐继畬在传教士帮助下辑著的《瀛环志略》(1849)则简要记录了希腊历史上有名的温泉关战役:
子泽耳士立(一做舍尔时斯),以三万人伐希腊,造长桥于他大尼里海峡,长二千长,以渡军。希腊大震,波斯欲招斯巴尔达降,斯巴尔达扼险拒之,人人决死战,呼声动天地,波斯军败走。①徐继畬辑著:《瀛环志略》(影印本),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489页。
波斯王薛西斯在书中译作“泽耳士”,斯巴达则译作“斯巴尔达(一作士帕大),”这要比1878年印行的冈本监辅著(编纂)的《万国史记》早近三十年。冈本监辅的汉文修养很好,《万国史记》 的编纂,从译名“泽耳士”看,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瀛环志略》的影响。
再如涩江保的《希腊波斯战史》,是鲁迅最有可能读到的底本。涩江保在1896 年翻译过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史密斯(Arthur H .Smith 1845—1932)的《支那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鲁迅认真阅读并大受“国民性”思考启发的一本书②李冬木:《关于羽化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4期。。周作人在1902年3月9日的日记中还提到,鲁迅在1902年刚到日本时就寄书给他,包括日本学者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严复翻译的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三册《原富》等,其中就有涩江保译的另一本书《波兰衰亡战史》。③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页。这些书都是由东京博文馆出版的。《希腊波斯战史》中关于斯巴达的翻译也是和《瀛环志略》一样,译作“斯巴尔达”。
涩江保的《希腊波斯战史》开首列引用书共八种,分别为:希罗多德(Herodotus)、乔治·格罗特(Grote)、Curtius、Smith的四种《希腊史》同名著作,法伊夫(Fyffe)的《希腊入门》 (Primer Greece)、Ollier的《插图世界史》,黑格尔(Hegel)的《历史哲学》,布吕姆纳(Blumner)《古希腊室内生活史》(The home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ce),Peter Parley的Tales of Greece and Rome。对勘之下,可以看出,这本书基本上是以希罗多德和格罗特的书为主要基础,参考其它书编译而成的。
其中关于法伊夫的希腊史著作,其实早在光绪十二年,亦即1886年,中译本就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编译出版了,题为《希腊志略》,是英国伦敦的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 & Co. of London)出版的由约翰·爱德华·格林(John Edward Green)主编的“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之一种。书中对斯巴达政事、地理风物、波希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等文章中,曾将这本书和《罗马志略》评价为“特佳之书”“不可不读”,湖南时务学堂亦列为“专精之书”。梁启超后来所撰写的《斯巴达小志》(1902年6月15日、7月1日,《新民丛报》 第12、13号)是现在所知道的鲁迅写作《斯巴达之魂》的材源之一,其中也有从《希腊志略》获得的启发,比如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对比,就是来源于该书的内容与方法。
森冈优纪认为,明治时期的少儿与妇女刊物对鲁迅撰写《斯巴达之魂》有直接影响。在他看来,《斯巴达之魂》的某些情节如二少年、王后戈尔果的故事,可能取自《少年园》《妇女与儿童》等刊物④[日]森冈优纪:《明治杂志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森时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卷,袁广泉译,第408页。,其实也不大可能。这样的故事在希罗多德、普鲁塔克的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而且在当时的日本已成为常识,这是不需要靠翻阅各种儿童刊物就能获取的历史知识。
在《浙江潮》1903年第4期的《留学界纪事·拒俄事件》中,记载有留学生组成的义勇队函电各方的文字记录。在致北洋大臣的电函中,有这样的表述:
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①《留学界纪事·(二)拒俄事件》,《浙江潮》1903年第4期。
通电以斯巴达三百勇士的“铁血”故事为典故,来激励国民奋勇抗敌,文中有云:“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说明温泉关的故事广为流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种常识了。
再举一例,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1899年出版《武士道》一书,是风行一时的读物,影响很大。梁启超等晚清思想家曾深深拜服,并立志学习,后来中国亦有《中国武士道》一书出版,并由梁启超亲自作序。书中提到,日本的儿童教育是“超斯巴达”的,也提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撰写希腊史的著名人物。②[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7、63页。这说明,斯巴达教育至少在日本学界,已不是陌生的新鲜事物了。
其实,斯巴达的历史常识,包括对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荷马等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的介绍,即使在中国,也早有所译介了。《六合丛谈》是英国伦敦传教士亚历山大·伟列亚力于1857年到1858年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其中的《土具提代传》《黑陆独都传》等文,就有希腊历史学家的评传了,而且也简要提到了斯巴达(译为士巴大)的历史。
如果说明治日本是青年周树人的周边,那么中国留学生圈则是周边的核心。鲁迅的《斯巴达之魂》的材源,中文有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这也是已经有数位学者论证过的事实了,毋庸赘言。其实,《斯巴达小志》还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中国问题与中国意识是一个更大的海面,而无数的材源沉浮于期间。影响鲁迅创作的,有日本明治思想的熏陶影响,也有周边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感染。
鲁迅对斯巴达的认知,对斯巴达精神的颂扬,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留学生文化圈及其鼓吹的风气的刺激。《斯巴达之魂》与拒俄事件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活动有直接联系,无需多说。鲁迅对斯巴达的认知,主要是受留学生文化圈的影响,从接受希腊历史知识的程序或层次来讲,首先是中国留学生周边的刺激与启发,其次才是在刺激与启发之下寻求新知,在中日文读物中获得新思想的。从《斯巴达之魂》来说,鲁迅不只是看到了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还有蔡锷、蒋百里等留学生对军国民主义、民族主义的鼓吹与宣扬。而在这一鼓吹与宣扬过程中,斯巴达是被反复提及的,如《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军国民篇》《军国民之教育》等系列文章。蒋百里为《浙江潮》撰写的发刊词、社说与《国魂篇》等文章,已反复提到“斯巴达”“武士魂”与“国魂”。鲁迅在这样的同乡会刊物《浙江潮》上发表文章,自然是要步调一致、风格一致的。《斯巴达之魂》在张扬鲁迅的文学个性时,亦受制于同人刊物的集体规约。相比于“五四”为《新青年》写文章、“听将令”的时期,这大概才是鲁迅的第一次“听将令”,第一声真正的“呐喊”。《斯巴达之魂》充斥着流血与呼号,正印证了鲁迅所说的“好文章”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政治与美学生态之下: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①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三、含糊其辞的背后
那么,鲁迅在三十年后,为什么对自己的“抄译”还是“创作”难以把握呢?隔着三十年的历史与观念变迁,时空的错位与风气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在晚清,意译是一种普遍的风尚,而且流行着一种比意译更过度的“豪杰译”。在这种风气下,鲁迅的《月界旅行》将原作删削一半来翻译,就是“不忠实”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像王宏志所说:“我们今天没法确定《斯巴达之魂》是翻译还是创作,则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在鲁迅当时心目中,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分野根本毫不重要,他并没有着意告诉读者这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因为相对于他但是‘制造’这篇作品的动机来说,这是无关宏旨的。”②王宏志:《重释信达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207页。因此,在翻译和创作缺乏严格分界普遍风气之下,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并非个案。周作人1904年翻译的首篇小说《侠女奴》,是现在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据考证,底本是英国劳特利奇公司(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890年发行的The Arabian Nights'Entertainments。③宋声泉:《〈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5期。周作人改了题目,改了结尾,主体部分还算是比较忠实的翻译,署名却是“萍云女士述文”,未注明原作者和出处。同样,周桂笙同时期的译作《毒蛇圈》不注明来处,不注明作者,也是如此。
明治时期的日本翻译界也是同样的风气。如《斯巴达之魂》的材源之一《希腊波斯战史》,据笔者考证,其实是涩江保在希罗多德和格罗特的底本上完成的编译,无论是数据,还是表述,翻译的痕迹特别明显,大多是照搬格罗特的风格的。其独创之处在于为希腊、波斯的王与英雄每章列了小传,这大概是受到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启发。但书名却署为“涩江保著”。
相较而言,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在前半部分所用的题材是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后世所有的材源都是来自希罗多德,鲁迅英文不精,材源之一可能是他熟悉的涩江保的《希腊波斯战史》中的第五编第四章。镇守山间小道的佛西斯人(Phocis)在鲁迅的小说中有“访嘻斯”和“佛雪”两种/处不同的写法,很能说明鲁迅当时的英文水平,也说明鲁迅阅读过的材源不止一种。小说译/作前半部分和史实相比相对忠实,鲁迅也紧扣核心,并未袭用涩江保的文字,做了大量的剪裁与微妙的变动,仅取列奥尼达与三百勇士在温泉关英勇抵抗波斯大军入侵、壮烈牺牲一段,突出塑造了斯巴达勇士与女性为国捐躯的高大形象与牺牲精神。后半部分更是一种自由想象,不拘泥于史料,完全是自己的一种虚构与发挥了。相比于简单的历史记录,逻辑严密的论说文章,鲁迅的小说译/作描绘更为丰富,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和涩江保、梁启超同类题材的著作相比,涩江保的是历史书,梁启超的是政论文,鲁迅的则是新小说。其文采飞扬、慷慨悲歌,远胜于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试验品《新中国未来记》的冗长寡味、沉闷无趣。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之魂》也是梁启超“新小说”理论一次不够成熟、但相对成功的创作实践。这正如在十五年后,《狂人日记》是对胡适的“短篇小说”理论一次最成功的预演一样。
那么,如何看待阅读的材源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呢?在主体论上,鲁迅阅读吸纳各种中外文材料来源,在潜移默化的阅读、学习与积累中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是从深怀忧患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意识出发的,有着逐渐自觉而独立的知识养成过程。在方法论上,我们还应注意到文献考证研究无法完成的部分。其一是有形、有限的文献所不能抵达的无形、无限的主体精神世界,其二是有形、有限的文献考证在方法论上无法抵达的相对开放或独立的文本世界。①符杰祥:《“狂人”/“小传”——鲁迅与“林译小说”的初遇,兼及〈狂人日记〉材源问题》,《东吴学术》2021年第1期。对周边与中心、创作与材源、文献与精神,都需要辩证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