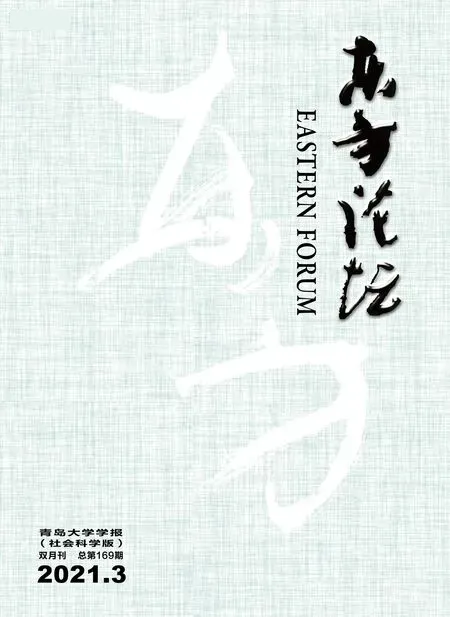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钱国旗 薛繁洪
1.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2.汕头市华侨历史研究中心,广东 汕头 515041
在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饮茶是一项清雅幽趣的休闲活动。茶作为传统文人寄托精神、抒发性灵的载体,表现出深厚的文化意蕴。明代中后期,以苏州府为核心的江南城镇文化地带,聚集了常州、松江、嘉兴等府的文人集团成员,这些文人皆以诗文书画闻名于世,同时又以茶人身份主导一代饮茶风尚,创造别样的饮茶生活。①参见吴智和:《明代茶人集团的社会组织——以茶会类型为例》,《明史研究》(第3辑),1993年,第110页。当时的江南社会弥漫着一股嗜茶品茗之风,文人雅士因性情、志趣、雅尚相契,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茶人群体。②相关研究成果见吴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中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晚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以及胡长春《明朝文人茶事概述——兼论明代江浙地区的文人饮茶集团》(《农业考古》2008年第2期)、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施由明《明清中国茶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论著。作为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精英群体,江南文人在个人饮茶实践和前人茶论的基础上,纷纷著书立说,研讨茶艺,掀起了浓厚的饮茶风尚。茶不仅是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文艺增趣的理想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
一、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中的茶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升华着文人的日常生活。
(一)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
由于茶具有破睡提神的功效,因此古人读书常以茶相伴。文人徜徉于经史子集中,在读书的片刻静品茶香氤氲。江南自古人文荟萃,重学风气浓厚,加之地处名茶产地,因此茶成了江南文人读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益思良品。明代中后期,文人读书并非只为科举一展抱负,也有出于自身性格、喜好,特别是隐逸文人,为隔绝世间纷扰,常常闭门读书,烹茶品茗,并从中追求雅趣。
苏州府长洲县人文征明(1470—1559),精于诗文,工于书画,嗜茶如命,自谓“吾生不饮酒,亦自得茗醉”①(明)文征明:《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一《五古》,周道振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页。。他的诸多茶诗记录了读书啜茶的乐趣,如“小院风清橘吐花,墙阴微转日斜斜。午眠新觉书无味,闲倚阑干嗽苦茶”②《崇义院杂题》,《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十四《七绝》,第386页。。又如“茗椀罏薰意有余,日长人散闭精庐。俄然屋角凉风顺,吹起新蝉乱读书”③《崇义院杂题》,《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十四《七绝》,第387页。等。文征明闭门读书,少了世间纷扰,静静享受着个人的美好时光,当读书困乏或午睡初醒之时,啜一杯清茶,让烦闷的心绪得到安顿,人格得到了升华。
洞庭西山张源,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嘉万年间隐于山林间读书烹茶,深究茶学,作《茶录》名垂茶史。顾大典为《茶录》作序时称:“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故所著《茶录》,得茶中三昧。”④(明)张源:《茶录》,载于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读书之暇品茗,为张氏枯燥的山居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
饮茶能清神益思。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松江华亭人,自幼颖异,志向高雅,工于诗文书画,集编《小窗幽记》讲述修身治学、为人处世之道,他回忆旧日生活时提及他品饮苦茶的心境:“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空灵,面上尘当亦扑去三寸。”⑤(明)陈继儒等:《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素》,罗立刚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0页。他自述与书为伴的饮茶闲趣:“茅斋独坐茶频煮,七碗后气爽神清;竹榻斜眠书漫抛,一枕余心闲梦稳。”⑥《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素》,第69页。其诗《赠醉茶居士》点出饮茶助学的强大功效:“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石枕月侵蕉叶梦,竹炉风软落花烟。点来直是窥三昧,醒后翻能赋百篇。却笑当年醉乡子,一生虚掷杖头钱。”⑦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晨起饮茶是他的日常清事,当醇香的清茶入喉,他不禁发出“醒后翻能赋百篇”的感叹,虽略显夸张之意,但说明了饮茶对日常读书具有提神助攻的作用。
午睡初醒,精神抖擞,此时若烹茶品茗,翻阅书籍,亦有一番乐趣。主要生活在明万历时期的浙江钱塘人高濂,以戏曲名于世,性嗜茶,幽居时“坐雨闭关,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爇,香霭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⑧(明)高濂:《遵生八笺》(下册)卷十二《燕闲清赏笺 中》,王大淳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34页。。张大复(1554—1630),苏州昆山人,以戏曲擅世。有一次,他闻得其子朗朗的读书声,毫无午睡困意,在煮茶品茗之后,令其子快读李贽的《焚书》,竟越发清醒。《梅花草堂笔谈》言:“料理息庵,方有头绪,便拥炉静坐,其中不觉午睡昏昏也。偶闻儿子书声,心乐之,而炉间翏翏如松风响,则茶且熟矣。……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儿子快读李秃翁《焚书》,惟其极醒极健者。”①(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上)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除了白天读书,夜读也是古人的生活常态,此时若无清茶提神,便让人感到困倦。松江华亭人莫是龙(1537—1587)认为:“人生最乐事,无如寒夜读书,拥炉秉烛,兀然孤寂,清思彻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瓯茗,神气益佳。尔时闻童子鼻息,足当数部鼓吹。”②(明)莫是龙:《笔尘》,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嘉兴人冯梦桢(1548—1605)喜欢啜茗夜读,其日记多处记载他夜读饮茶,如“(万历十八年四月)初六,雨,夜始不闻雨声,稍寒。作《潘去华报书》。贮天落水烹茶。天落水虽不及梅水,亦堪烹茶。夜读《选·赋》”③(明)冯梦桢:《快雪堂日记》卷四,丁小明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此外,在许多明人文集中亦常提及时人读书品茗、书茶相伴的史实。浙人章懋(1437—1522)在其文集中记录了逸轩处士周氏日常嗜书好茶之琐事。周氏“晚岁筑书室于西溪,而环以竹桧,日徜徉其间,客至则焚香煮茗,治具相饮,壶弈觞咏以为乐,虽久而弗厌也。室中所蓄,惟经史子集及百氏之书”④(明)章懋:《枫山章先生集》卷五《逸轩处士周君墓志铭》,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5—156页。。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载了一个叫何上舍的文人不仅酷爱收藏书文,还在阅书览卷时品茗助读:“何上舍道光独喜藏书,……焚香煮茗,哦咏万卷中”。⑤《梅花草堂笔谈》(下)卷十三,第861页。读书以茶相伴,以茶益思,不仅提高了文人读书的效率,还提升了文人的生活品味。
(二)文艺增趣的理想饮品
文人饮茶的形式丰富多彩,若与各种文艺活动,如琴、棋、书、画“四艺”等清事相配,文艺和茶事活动则更显幽雅清逸。
弹琴作为文人“四艺”之首,颇受文人喜爱。在古人交往中,悠扬的琴音是雅境和友情的象征。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1378—1448),曾构筑精庐,深自韬晦,鼓琴读书,以茶明志,其《茶谱》记载饮茶之余鼓琴弈棋的乐趣:“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陈笔砚。或庚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⑥(明)朱权:《茶谱》,《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152页。具有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弹琴品茗,恰到好处。评述晚明文人生活起居、文房用具的《考槃余事》记载:“弹琴之人,风致清楚,但宜啜茗,间或用酒发兴,不过微有醺意而已。”⑦(明)屠隆:《考槃余事》卷二,秦跃宇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9页。文人品茗时,若配上琴艺,茶助琴幽,琴助茶雅,无疑为茶境增添了艺术气息。
弈棋是传统游艺之一,文人相聚时,在品茗清谈之余,时常也过过棋瘾。饮茶能使下棋者提神益思,茶弈并行不失为一项清课雅事。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弈棋者众多,不仅有文人与文人间的对弈,有的文人还在山林禅院中与僧道下棋,出现了士僧对弈的情形。“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⑧盛敏、刘仲华:《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文征明茶诗中记录其与友人对弈品茗的情形:“山斋雨歇书沉沉,得与幽人一散襟。矮榻薰罏消茗碗,小窗棋局转桐阴。笑谈未觉风流减,违阔翻怜契分深。莫自匆匆骑马去,绕簷斜日乱蝉吟。”①《停云馆与昌国闲坐》,《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七《七律》,第144页。试想,黑白棋子在棋盘中变幻莫测,弈棋者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当一杯清茶过后,思路顿开,先前处于下风的弈棋者转败为胜,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是文人的看家本领。在烹茶品茗之余,泼墨挥毫,或练习书艺,或品题名画,无疑是一种艺术享受。江南名士王问(1497—1576)致仕而归后,闭门谢客,常以品茗弄墨为乐,“性不饮酒而喜啜茗。筑绿萝小迳,每遇风清月白,净几明窗,兴至举笔,或书或画,辄写数十幅,如有神助,自谓径丈大字,至老有进,凡仕宦过锡者,踵门求见,往往以疾辞,而独好静颐。”②(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二《高尚》,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影印本),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3年。王问鄙弃世俗的纷扰,在风清月白之际、净几明窗之旁,煮茶品茗,舞文弄墨,或书写或绘画,如有神助创作了数十幅书画,令人折服。
品茶绘画赏画也是一项高雅的艺术活动。江南文人绘画题材广泛,风格变化多样,他们以茶事活动作为题材,创作了诸多清幽空灵的茶画。除了品茶绘画,把卷赏画亦是日常雅事。陈继儒山居期间常饮茶观画,“独坐丹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炷,看达磨面壁图,垂帘少顷,不觉心静神清,气柔息定,濛濛然如混沌境界”③《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四《灵》,第52页。。高濂《遵生八笺》记述了江南文人晴日饮茶玩画的乐事:“茶以雪烹,味更清冽,所谓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时乎南窗日暖,喜无觱发恼人,静展古人书轴,如《风雪归人》《江天雪棹》《溪山雪竹》《关山雪运》等图,即假对真,以观古人摹拟笔趣。要知世景画图,俱属造化机局,即我把图,是人玩景,对景观我,谓非我在景中?千古尘缘,孰为真假,当就图画中了悟。”④《遵生八笺》(上册)卷六《四时调摄笺 冬》,第294页。品茗时舒展画卷,让人忘却世间纷扰,仿佛进入虚静空灵的画卷中。
饮茶与琴棋书画相结合,不仅增添了茶境的趣味,也提升了饮茶者的艺术品味。史载:“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⑤(明)文震亨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423页。煮茶品茗作为文人休闲时尚的一部分,进一步推动了文人阶层雅文化的发展。
(三)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
茶不仅是读书之暇提神益思的必备良品,也是文人社会交往中增进友谊的重要媒介,“有时还成为社交中一种凭借,以及士人身份价值获得提高的一种尺度”⑥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在江南文人社会交往中,茶成为待客必备之物,友人来访时便以茶迎客。文征明诗云:“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⑦诗后跋文: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传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文征明集》(增订本中)补辑卷十二《七绝》,第1069页。陈继儒山居期间,每当有客来访,便备茶招待,畅言一番,直至友人日暮而归:“垂柳小桥,纸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书一卷,客来则寻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归,不知马蹄为何物。”⑧《小窗幽记》(外二种)卷六《景》,第90页。文友相会必然诗文唱酬,抑或放声高歌:“客到茶烟起竹下,何嫌展破苍苔;诗成笔影弄花间,且喜歌飞《白雪》。”①《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七《韵》,第104页。冯梦桢常以茶待客,并深得饮茶方法,得到客人的称赞。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载:“冯开之先生喜饮茶,而好亲其事。人或问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彝鼎,如古法书名画,岂宜落他人手?’闻者叹美之。然先生对客谈辄不止,童子涤壶以待。会盛谈未及着茶时,倾白水而进之。先生未尝不欣然,自谓得法,客亦不敢不称善也。世号‘白水先生’云。”②《梅花草堂笔谈》(中)卷六,第374—375页。
作为文人社会交往的必备饮品,饮茶象征着人际交往中率性适趣、清淡洒脱的“道义之交”。③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李诩《真率铭》道:“弗尚虚礼,不迎客来,不送客去。宾主无闲,坐列无序,真率为约,简素为具。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适趣,冷淡家风,林泉清致。道义之交,如斯而已。”④(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真率铭》,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页。茶性清新高雅,待客时人数的多寡也不容忽视。张源认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⑤(明)张源:《茶录》,《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63页。
茶在文人社交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体现在茶叶的寄赠方面。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文人交往频繁,当面赠茶或托人寄茶成为文人联络情谊的重要桥梁。当文人收到友人寄送的茶叶后便试茶品茶,在享受茶韵芬芳之时作诗回馈以示感激。文征明收到好友吴大本寄来茶叶后欣然作诗表达谢意:“小印轻囊远寄遗,故人珍重手亲题。暖含烟雨开封润,翠展枪旗出焙齐。片月分明逢谏议,春风仿佛在荆溪。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诗肠万斛泥。”⑥《谢宜兴吴大本寄茶》,《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八《七律》,第173—174页。明代名臣、苏州长洲人吴宽(1435—1504)收到好友朱懋恭赠茶后抒发自己品饮龙井茶的愉悦之情:“谏议书来印不斜,忽惊入手是春芽。惜无一斛虎丘水,煮尽二斤龙井茶。顾渚品高知已退,建溪名重恐难加。饮馀为比公清苦,风味依然在齿牙。”⑦《谢朱懋恭同年寄龙井茶》,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第144—145页。徐渭(1521—1593),绍兴府山阴县人,平生落魄坎坷,玩世不恭,在其茶诗《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中抒发了他视赠茶人的友谊如冰心玉壶之纯洁:“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却从梅月横三弄,细搅松风灺一灯。合向吴侬彤管说,好将书上玉壶冰。”⑧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第156页。明代书画家、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浙江嘉兴人,著有《味水轩日记》八卷,实录其日常艺术生活,日记除了谈艺之外,多述交游及东南海事,其中还记录了不少僧人寄茶赠茶的史实。⑨(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可见,茶已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社交媒介,通过以茶待客、赠茶寄茶等形式,不仅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还促进了江南地区茶风的兴盛。
明代中后期,以茶会为形式的文人雅集之风在江南地区兴起,如较为著名的山水雅集茶会以正德十三年(1518)的惠山茶会为代表,文征明为此次茶会绘制《惠山茶会图》,书法家蔡羽在茶画上挥毫记录其事。⑩参见(清)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四《文衡山惠山茶会图卷》,柳向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当时春茶正兴,七人汲泉煮茗,吟诗酬唱,乐在其中。这次惠山盛会得到后世文人的吟咏,清人王权作《文衡山惠山茶会图七贤诗草卷子为农山观察题》盛赞吴中文人的饮茶趣事:“开卷飞泉响,行间岚气生。亭台山气入,朋辈竹林清。野鸟窥吟客,松风答沸铛。好诗皆画意,况复绘图精。世味争醲腻,诸公嗜好乖。云霞收茗碗,岩窦引芒鞋。绝境东南最,畸人六七偕。便同修禊饮,墨迹韵高斋。”①(清)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卷五《文衡山惠山茶会图七贤诗草卷子为农山观察题》,吴绍烈等校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四)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多以游山玩水休闲寄情,他们三五成群,携伴出游,徜徉于自然之中以忘却世俗喧嚣,享受着山水之乐而不再迷恋功名利禄,表现出恬淡安乐的生活状态。许多文人重视旅途品茶之乐,经常携带茶具出行,或泛舟水上,或在林下溪边煮茗,在山水揽胜中品味茶之神韵。如许次纾所言:“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觞。乃茗碗薰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托素交也。”②(明)许次纾:《茶疏》,《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84页。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许多文人钟情于舟游,往往携带简便的茶具出游,泛舟于江水湖泊之上,于舟上置茶具、览书卷,在饱览山水美景中享受品茗之乐,追求个人精神自由。龙膺《蒙史》言:“至若所云寒暑得中,体性无事,乘小舟,设蓬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宝、钓具而已,自称江湖散人,则窃有志而欣慕焉。”③(明)龙膺:《蒙史》,《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464页。文震亨(1585—1645) 《长物志》记载了时人携带茶具舟游的情景:“(舟)前仓可容僮仆四人,置壶榼、茗炉、茶具之属;后仓隔之以板,傍容小弄,以便出入。”④《长物志校注》卷九《舟车》,第344页。屠隆“用二画桨泛湖棹溪,更着茶灶,起烟一缕,恍若画图中一孤航也。”⑤《考槃余事》卷四《游具笺》,第98页。张岱《陶庵梦忆》多处描写湖中饮茶之事,如《西湖七月半》:“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⑥(明)张岱著,林邦钧注评:《陶庵梦忆注评》卷七《西湖七月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烟雨楼》写道:“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态度幽闲,茗炉相对,意之所安,经旬不返。”⑦《陶庵梦忆注评》卷六《烟雨楼》,第174页。在明人的许多文集中常见舟中品茗的记录。
松间竹下环境清幽,泉边石畔生机盎然,皆为文人出游途中理想的品茗之地。屠本畯《茗笈》云:“试相与松间竹下,置乌皮几,焚博山炉, 惠山泉,挹诸茗荈而饮之,便自羲皇上人不远。”⑧(明)屠本畯:《茗笈》,《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408页。沈周《是夕命童子敲僧房汲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诗云:“夜扣僧房觅磵腴,山童道我吝村沽。未传卢氏煎茶法,先执苏公调水符。石鼎沸风怜碧绉,磁瓯盛月看金铺。细吟满啜长松下,若使无诗味亦枯。”⑨(明)沈周:《石田稿》,《沈周集》(上),张修龄、韩星婴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63—464页。吴宽《游惠山入听松庵观竹茶炉》诗云:“与客来尝第二泉,山僧休怪急相煎。结庵正在松风里,裹茗还从谷雨前。玉碗酒香挥且去,石床苔厚醒犹眠。百年重试筠炉火,古杓争怜更瓦全。”⑩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卷五《明代茶文化经典·明代诗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08页。
寺院道观多居于深山幽林之中,远离世俗尘嚣,适应了文人对清幽环境的追求,自然成为文人品茗的理想场所。明代中后期,三教合流,文人与禅僧、道人交往频繁,文人在寺院道观饮茶过程中澄明心境,修心养性,参透人生之真谛。由于茶性清淡素洁,增进了儒释道之间的联系。如徐爌《茶居士传》所云:“茶氏世好修洁,与文人骚客、高僧隐逸辈最亲昵。”①吴康霖编纂:《六安州志》(下)卷五十一《杂体》,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688页。钱塘人许次纾与弟许世奇游龙泓山时至寺中与僧品茶,“日品茶尝水,抵掌道古。僧人以春茗相佐,竹炉沸声,时与空山松涛响答,致足乐也”②(明)许次纾:《茶疏》,《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73页。。钱塘人陈师在游山访寺之时也常与僧人饮茶:“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吴中,置磁壶二小瓯于案,全不用果奉客,随意啜之,可谓知味而雅致者矣。”③(明)陈师:《茶考》,《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20页。
另外,野外亭轩也是江南文人向往的品茗之地。松江华亭人何良俊(1506—1573)记录了他与友人出游途中在山中亭轩品茶之事:“余羁旅无聊,九日约仲交文学一登灵应观。余凌晨即行,仲交揣香茗,领客徐西涧继至,相与宴坐亭中,焚香啜茗。仲交和墨点笔,作云林小景,倦宫寂寥,人境俱绝,留连览眺,迨暮方归。”④(明)林应麒:《介山稿略十六卷补遗一卷》影印版,载于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七十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366页。
江南文人走出书斋庭院,在山水揽胜过程中煮茶品茗,到山水自然中享受人生之乐,或泛舟水上,或松间林下,或泉边石畔,或寺院亭轩,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样态。
二、茶与文人的隐逸情怀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繁华富庶,程朱理学式微,心学思想浸润着江南文士,使其心性得到舒展,加之仕途之路阻塞,江南文人心中“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发生动摇,他们开始投入世俗生活,有较多时间从事品茗这一高雅活动,希望在品茶中摆脱社会的种种束缚,追求自我意志独立,享受愉悦的人生。饮茶为文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在职文人常在公务闲暇之余静品佳茗,寻求心灵寄托。另外,纲纪废弛,奸佞擅权,朝政腐朽,世风日下,许多士大夫脱离宦海生涯,或遭贬而归,或主动告乞。走出官场后,他们择一地隐居,摆脱世事纷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茶事活动中,不仅亲自种茶、采茶,还热衷于煮茶、饮茶,在俗世中回归自然,愉悦心境,这是中晚明江南文人适情适性、乐天知命的普遍追求。
当时以茶寄隐的时代风气十分浓厚。晚明官员陆树声(1509—1605)面对朝政不振,不与奸佞为伍,以茶自娱表心迹:“树声居尝闭门宴坐,焚香啜茗,启处服御,笑饮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缀接里之执经问道,与士大夫东西行礼于其庐者,不择贤愚少长,皆意满去。王锡爵称其道不苦空而禅,不标炽而儒,不垢俗而隐。”⑤(明)何乔远:《名山藏》(下册)卷八十一《臣林记二十六 陆树声》,张德信、商传、王熙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54页。他谢绝众人挽留,欣然回归故里,在松江城南构建了适园,以追求闲适的生活,《适园记》记录了他恬淡清雅的生活趣味,同时也寄托了他的隐逸情怀⑥参见刘大杰:《明人小品集》,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第175页。。他还在园中修建了饮茶专用场所茶寮,“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中设茶灶,凡瓢汲罂注、濯拂之具咸庀”⑦(明)陆树声:《茶寮记》,《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14页。,时常与僧人韵士开展茶事,品茗赋诗。
嘉兴府嘉善县人姚公绶(1423—1495),成化年间历经宦海沉浮,后因母老奉养辞官归于故里。《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了姚公绶隐居期间的自在生活:“成化初,出知永宁府,解官归。公绶善书画,初水墨,后遂进唐品,得古意。作沧江虹月之舟,游泛吴、越间,粉牕翠幙,拥僮奴,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家设亭馆称是,作室曰‘丹丘’,自称丹丘先生。人望之亦以为神仙云。”①(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乙集《姚御史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弘治阁臣李东阳(1447—1516)在任时感叹仕途之艰辛:“十年宦游隔江海,此兴落落何由偿。”②(清)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第二册)卷九《李文正公东阳》,欧阳楠点校,沈道宽等校订,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63页。他致仕而归后过着率性而为、恬淡洒脱的饮茶生活,这从茶诗《东坡煎茶图次坡韵》中可以反映出来③《历代茶诗选注》,第145—146页。。明代文学家、太仓人王世懋(1536—1588)在公务之余常饮茶寄怀,他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其在南昌任上时,某日晚间月下品尝友人所赠西山云雾茶的情景:“时西山云雾新茗初至,张右伯适以见遗,茶色白,大作豆子香,几与虎邱垺。余时浴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儿汲新水烹尝之,觉沆瀣入咽,两腋风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路所有。”④陆廷灿《续茶经》引王世懋《二酉委谭》,《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864页。他饮下西山云雾茶后,顿觉神清气爽,飘飘欲仙,感叹宦途之人难能品味茶的清味。闽人谢肇淛(1567—1624)常与江南文人品茗赋诗,享受饮茶之乐。他为喻政题作的一首诗正是其心境的写照:“山僮晚起挂荷衣,芳草闲门半掩扉。满地松花春雨里,茶烟一缕鹤惊飞。石鼎斜支傍药栏,松窗白日翠涛寒。世间俗骨应难换,此是云腴九转丹。”⑤《为喻正之郡侯题〈烹茶图〉二首》,(明)谢肇淛:《小草斋集》(下册)卷二十八《七言绝句二》,江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4页。清逸幽静的田园环境,不为世俗名利所扰的心态,正是他所追求的。
明代茶书作者多为隐逸之士。长洲人顾元庆(1487—1565)隐居吴中,以煮泉烹茶为乐,删校钱椿年《茶谱》一书使之流传后世。作《茶疏》而闻名的钱塘人许次纾(1549—约1604)常携茶登山临水,煮茗为乐,与同样嗜茶的姚绍宪情谊深厚,时常交流品茶心得。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钱塘人陈师在职时亦有退隐之心,返归故里后,结交高人雅士,以茶为伴,终有《茶考》传世。宁波府慈溪县人罗廪(1573—1620)隐居山中期间,亲自植茶,历时十年,静坐山堂,鉴赏茶水,坚守隐士的品格。《岕茶别论》作者周庆叔为吴中名士沈周(1427—1509)密友,两人交往情深。周庆叔长期隐居于江南著名茶乡长兴,一生嗜茶,精于茶事,沈周在《书岕茶别论后》记载周氏居于山中恬淡自适的饮茶生活:“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而周庆叔者,为《岕茶别论》,以行之天下,度铜山金穴中无此福,又恐仰屠门而大嚼者,未必领此味。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恨鸿渐、君谟不见庆叔耳,为之覆茶三叹。”⑥陆廷灿《续茶经》引沈周《书岕茶别论后》,《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864页。隐逸之士热衷茶事,一方面在氤氲的茶香中获取超越人生困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种茶、制茶、品茶的经验不断得到总结和升华,由此推动了明代茶文化的发展。
有的文人隐遁山林后,仍与外界交流频繁。松江华亭人陈继儒三次科场失意后,对仕途心灰意冷,“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橼,焚香晏坐,意豁如也”⑦(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九八《隐逸·陈继儒》,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31页。。山居期间,安贫乐道,痴迷茶事,终有《茶话》《茶董补》等著作问世。他为江阴人夏树芳《茶董》作序时,不禁感叹茶隐生活:“何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耶?”①(明)夏树芳:《茶董》,《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420页。在他眼中,仕途已与他无缘,忙碌于山间采茶、煮茶、品茶,乃是人生一大快事,希望通过清逸的茶事活动“一洗百年尘土”。他以茶比德,坚守自己的高尚节操,如其所云:“茶类隐,酒类侠;酒固道广,茶亦德素。”②《小窗幽记》(外二种)卷五《素》,第79页。陈继儒身在山中,却名扬天下,尽管归隐山林,但仍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从他曾为应考士子题写《临场十策》可见,其身虽隐,心却未隐。钱谦益曾褒评陈继儒:“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③《列朝诗集小传》(下)丁集《陈征士继儒》,第638页。
有的文人一开始也有“学而优则仕”的追求,但是经过仕途受挫后心灰意冷,于是借饮茶来排除内心烦恼。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苏州吴县人唐寅屡次科举不售,又因宁王叛逆案所累,仕途的坎坷使他决定不再入仕。他所作《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五首》(其一)曰:“茅茨新卜筑,山木野花中;燕婢泥衔紫,狙公果献红。梅梢三鼓月,柳絮一簾风。匡庐与衡岳,彷佛梦相通。”④(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二《五言律诗》,周道振、张月尊辑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5页。这首诗明显表达了唐寅对隐于匡庐、衡岳等名山大川的向往之情。“怪才”徐渭也是坎坷之人,科场屡试落榜,因恐受胡宗宪案牵连,佯装疯癫,常在茶中寄托现实生活的苦闷。在《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一诗中,徐渭表现出率性而行的生活态度。他得到友人所赠的虎丘茶后十分欣喜,独饮佳茗,精致的紫砂壶泡上名茶,听上一曲“梅花三弄”,使得茶人完全沉浸在袅袅茶香之中。
三、茶性与文人的心性
饮茶不仅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感的物质消费,更是一项体现价值追寻的精神休闲。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的某些精神追求相互契合,相得益彰。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他们嗜茶爱茶,精通茶艺,在煮茶品茗中将人生理想与精神感悟寄托于茶,在日常饮茶清事中呈现其处世态度与人文情怀,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
(一)茶性平和冲淡体现文人淡泊自守
在中晚明江南文人心中,茶性平和冲淡符合其对仕途人生的淡泊。唐代文人裴汶在《茶述》一文中认为茶具有平和冲淡的特性:“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⑤(唐)裴汶:《茶述》,《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30页。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亦认为茶具有“祛襟涤滞,致清导和”⑥(宋)赵佶:《大观茶论》,《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94页。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⑦(宋)赵佶:《大观茶论》,《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94页。的功效。传统文人崇尚平和冲淡、含蓄沉稳的性格,并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采茶、煮茶、品茶都强调中和、冲淡,这也是茶叶本身所具有的品格。酒性热烈奔放,饮之易使人张扬个性,与现实社会产生对抗;茶性平和冲淡,饮之易使人清醒淡泊,缓和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明代中后期,纲纪废弛,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激烈,身处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难免会卷进政治纷争的漩涡,他们为坚守个人情操,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不愿屈服于蛮横强权,经常通过饮茶调理身心,安顿心灵。
吴中才子文征明,生于诗书世家,少时即享才名,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九次应举均落第而归,直至54岁那年,他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翰林院。四年中目睹官场腐败、人心险恶,仕途进阶之念在他心中逐渐黯淡,于是一再乞归,57岁回归故里,潜心诗文书画,只求淡泊闲适的人生。辞官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茶事生活中,创作了诸多涉茶作品。在他的茶画中,往往呈现与友人林泉品茗的场景,透露出脱离世俗纷争、栖息山林泉下的自守闲适之情。《品茶图》描绘了在清新空旷的山林下,文人间煮茶品茗的生活乐趣。《煎茶诗赠履约》体现了他闲适的饮茶生活:“嫩汤自候鱼生眼,新茗还夸翠展旂。谷雨江南佳节近,惠泉山下小船归。山人纱帽笼头处,禅榻风花绕鬓飞。酒客不通尘梦醒,卧看春日下松扉。”①《文征明集》(增订本上)卷十《七律》,第264页。煮茶品茗,使得文人心境宁静淡泊、适情适性。以文征明为代表的许多江南文人将满身才华融入世俗生活,追求诗情画意、清逸冲淡的艺术人生,生活中弥漫着参透人生真味后的淡淡喜悦。茶性平和冲淡正与他们的性情相契合,细啜慢饮、涤烦益思的饮茶生活有利于抚慰文人满怀激愤的身心,成为调和政治危机与个人处境的一种圆融策略和生活艺术。
(二)茶性提神醒脑促进文人静虑自省
饮茶除了调适文人士大夫的官场束缚之外,亦有一种反躬自省的韵味。自省是传统文人的品格之一。阳明心学主张的“心即理”“致良知”,强调的就是一种自省功夫,这对塑造中晚明文人性情有着重要作用。与酒性迥异的是,茶具有清凉苦寒、提神醒脑的功效。饮茶不仅使文人满足解渴除困的身体需求,还为文人提供了心平气和的内省空间,使其通过茶这一物质媒介进行清醒的人生反思和心灵沟通,以此平衡与调节文人内心的痛楚,满足其超尘脱俗保持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愿望。
浙江山阴人张岱晚年回忆起曾经的奢华生活时,似有一种反省的意味,“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②(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一《梦忆序》,云告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1页。。张岱自言其“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③《琅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第159页。,晚年隐居山中避世著书。山居期间,张岱生活困倦潦倒,甚至有断炊之难,但嗜茶之心不改。茶对他来说是精神的寄托,他自比卢仝好茶成癖:“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麈,用畅清谈;半塌焚香,共期白醉”④《陶庵梦忆注评》卷八《露兄》,第235页。。张岱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外有国破家亡危机,内有安身立命困扰,但他并没有放浪形骸,而是选择隐遁山林,著书立说,以此寻求人格独立,实现人生价值。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曾任吴县县令,万历二十五年(1597)解官后,常饮茶反省人生。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寄信给远在北京的好友李湘洲,诉说自己年轻时沉迷声色,劝慰好友勿重蹈覆辙。信中写道:“回思往日孟浪之语最多,以寄为乐,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纵幽崖绝壑,亦与清歌妙舞等也。愿兄早日警发,他日意地清凉,得离声色之乐,方信弟言不欺也。”⑤李鸣选注:《袁宏道》,《李湘洲编修》,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他感叹在职时因公务烦扰嗜茶之癖全无:“吏吴以来,每逢好事者设茶供,未尝不举以自笑。然务烦心懒,茶癖尽蠲,虽复倾国在前,而主人耄且瞆,较之瘿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⑥(明)袁宏道著,孙虹、谭学纯注评:《袁宏道散文注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0页。当友人问他辞官后有什么心愿,他回答:“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岕,陆、蔡诸公供事其中,余辈批缁衣老焉,胜于酒泉醉乡诸公子远矣。”①(明)袁宏道著,孙虹、谭学纯注评:《袁宏道散文注评》,第40页。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茶成了他的精神伴侣。
茶性清苦,与佛家倡导的“苦谛”相契合。面对政治腐朽,中晚明江南文人试图通过寺院饮茶寻求致静无求的心灵寄托,他们通过与僧人共同参禅摆脱尘俗污染,明心见性,以此获得参悟禅宗思想的愉悦即 “禅悦”,在参禅论道中淡泊心志,以平常心看待世俗人生。陆树声闲居期间与禅僧交往频繁,“时杪秋既望,适园无诤居士与五台僧演镇、终南僧明亮,同试天池茶于茶寮中”②(明)陆树声:《茶寮记》,《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14页。。李日华与道光禅师交往甚密,其《赠道光老禅》一诗不仅描绘了饮茶景象,还深具禅机佛理:“一室绝尘虑,焚香坐悄然。竹敲松子下,泉迸石痕穿。灯火身为伴,茶铛手自煎。谁言不出户,来往第三禅。”③(明)李日华:《恬致堂集》(上)卷五,赵杏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袁宏道《游虎跑泉》诗曰:“竹床松涧净无尘,僧老当知寺亦贫。饥鸟共分香积米,落花常足道人薪。碑头字识开山偈,炉里灰寒护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盏,芽茶烹得与尝新。”④(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5页。诗人与禅师在竹林松下饮茶,其景之清,心境亦清,不由地让人忘却浊世的烦恼,于自然朴素中蕴含着佛理禅机。王世贞《山行至虎跑泉庵次苏长公石刻韵》描写其秋后至虎跑泉寺与僧品茶体悟禅机:“百草沾风蚕月香,双鸠唤雨麦秋凉。过桥已觉世情少,到寺始知僧日长。拂藓石留行脚偈,挂瓢泉是洗心方。良公更有茶瓜在,禅悦能容取次尝。”⑤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通志》卷二七六《艺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767页。湖州文人丘吉《寄馆天宁寺》将品茶与参禅境界融为一体:“茶炉吹断鬓丝烟,借得禅林看鹤眠。不道秋风何处起,一堆黄叶寺门前。”⑥陈田辑撰:《明诗纪事》(二)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08页。其诗总体呈现一种幽雅清静的画面,给人以远离尘嚣之感,体现了作者追求心灵安宁慰藉的思想境界。茶性促进文人反省人生,在品茗谈禅中静心自虑,静静地体会内心的澄明与愉悦,回归本原的自然心性,达到禅悦的境界。
(三)茶性自然纯真契合文人贵真求真
茶生长于优良的生态环境中,承甘露之滋润,蕴日月之精气,大自然赋予其纯真清静的秉性,茶之色、香、味无不打上“真”的印记。明代中后期的多部茶书中都论及茶具有“真”的特点:张源《茶录》言:“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其真。如水中著咸,茶中著料,碗中著果,皆失真也。”⑦参见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263页。程用宾《茶录》言:“茶有真乎?曰有。为香、为色、为味,是本来之真也。”⑧参见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370页。黄龙德《国朝茶说》曰:“茶有真香,无容矫揉。……如是光景,此茶之真香也。少加造作,便失本真。”⑨参见杨东甫《中国古代茶学全书》,第525页。
茶性自然纯真契合了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贵真求真的精神。徐渭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中晚明文人“贵真”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写道:“夫真者,伪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声必希,听斯真矣,五色不华,视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于他,将未有不真者。故真也则不摇,不摇则神凝,神凝则寿。”⑩(明)徐渭:《徐渭集》第三册《徐文长逸稿》卷十四《赠成翁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徐渭坚持返璞归真,推崇“真我”,是对保守僵化的礼教扼杀天然本性的质疑与超越。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袁宏道提倡“性灵说”。他认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①《袁宏道集笺校》(上)卷四《识张幼于箴铭后》,第193页。与“真人”相应,晚明尤为重视“真心”,亦称“童心”“性灵”等。李贽是“童心说”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②(明)李贽:《焚书 续焚书》卷三《杂述·童心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页。这些观念对当时文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江南文人在饮茶生活中领悟茶的自然纯真秉性,追求自然本真、率性而行的生命状态。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人生追求因时局变化而发生动摇,茶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不仅点缀了文人日常生活的诗情画意,还融入了文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寻。作为明代茶文化的践行者,江南文人追求适情适性、清雅幽趣的饮茶生活,在煮茶品茗中赋予其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和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文化意蕴,他们推动了明代茶文化的发展,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