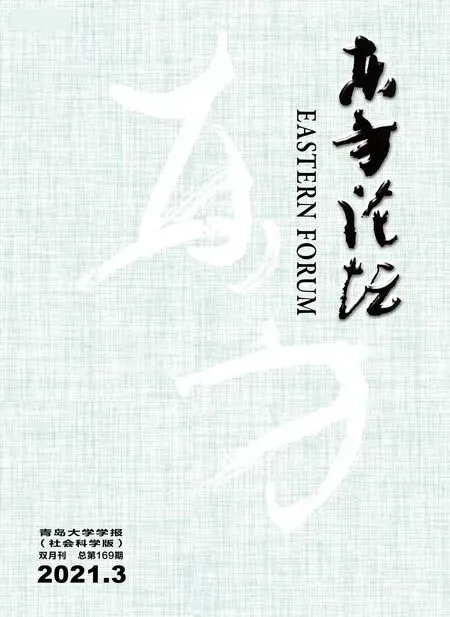晚清学人的《后汉书》阅读史
——基于时人日记的考察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纷乱之时代,学术文化变迁急剧,史学地位开始上升,史家著史总结前朝得失成败成为时代风尚。范晔生此离乱之时,以史家锐敏之眼光,“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正一代之得失”,撰成反映东汉王朝历史的名著《后汉书》,体现了高超的历史编纂艺术和独特的历史盛衰的观念,成为可以媲美《史记》 《汉书》的史学名著。范书成书后,后世学者绝大多数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梁刘昭说“范晔《后汉》,良跨众氏”,认为范书超过前人。唐朝刘知己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又说:“观其所取,颇有奇功”(《史通·补注篇》)。清代学者赵翼评论《后汉书》说:“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①赵翼撰、黄寿成校点:《廿二史札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页。,高度赞扬了其史论的突出成就。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云:“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釆,而惟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②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87页。其评论对范晔及其《后汉书》编纂思想和儒学观多有赞誉之词。
晚清以前,前人对《后汉书》的接受史和批评史表明该著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和魅力,在历代正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晚清以后,光气大开,中外互市渐成,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之风渐盛。在这样千年未有变局之下的学人,如何阅读传统史学经典,解读经典的内涵和学术价值,分析经典的得失,演绎经典传承的学术轨迹,成就了《后汉书》学术阅读史和评论史的景观。而在纪录这一景观的体裁中,日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日记以其记载的连续性和偏重日记主体内心的阅读感悟,更能呈现日记主人阅读生活的细节和习惯。更为重要的是,日记的私密性特征决定了日记主人可以较少顾忌,从而将本真的阅读体验笔之于日记中。对于史学评论史而言,这部分鲜活的史料弥足珍贵。因为从他们的评论中,可见他们对史学经典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可见他们批评的视角、方法和观点能否担当起史学经典的诠释和阐发。本文以晚清学人日记为主要史料,以学人阅读《后汉书》以后的感悟和评论为研究对象,力图再现《后汉书》在晚清日记世界的阅读场景,将他们阅读后对《后汉书》的接受、批评、反思串珠成线,展现晚清《后汉书》史学批评的独特风韵。
一、《后汉书》的阅读场景
范晔《后汉书》作为正史中的“前四史”,具有重要的地位。范氏自誉其书有“精意深旨”,评其为“天下之奇作”,虽有过誉之嫌,但历经一千多年该书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知识阶层注录、点校、评论该书,可以说累代皆有,也证明该书确有独到的价值。特别是清中后期,阅读该书的读者不断增多,各阶层都有。乾嘉学派兴起,考证之风充溢于学界,学者从考史的角度评论《后汉书》。降及晚清,欧风美雨冲击下的中国知识界仍然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典葆有温情和敬意,他们希望从史学经典中找寻应时修身的路径,提高明辨历史的智慧,进而在历史转折年代中求得心灵的慰藉。近年来,大量出版的学人日记生动地记录下他们阅读《后汉书》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下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困惑、反思和批评。
晚清湘军统帅曾国藩认为读书目的在于“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故其认为读书不必别汉学之名目,重在领略前人治学读书之门径。从其日记中可见,他从1844年8月18日开始读《后汉书》,每天二三十页几乎无间断,这和他的读书观念有关,他认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因此他能坚持四个月将《后汉书》百卷阅读一过,还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对《后汉书》作了批校。如《后汉书·臧洪传》载臧洪答陈琳书词稍繁冗,《后汉书》删节甚当,故录之。曾国藩读后,认为范晔的删削得当,这是他根据自己的学养做出的评价。再如《景丹传》:“秋,与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执金吾贾复……等从击破五校于羛阳,降其众五万人。”以迁、固文法推之,“大司马吴汉”五字均应有,不得但云吴汉也。他根据正史的笔法和汉代的官制,指出《后汉书》原文在官称上存在瑕疵。批校作为经典史著阅读史的素材,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批校一般是阅读者进行阅读时随手而写,颇能反映读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根据美国学者希瑟·杰克森在其所著《批校:书籍中读者的书写》中所说:“考虑到近来的研究兴趣从作者转向了读者和文本的生产、流传与接受,各个时代的批校对于学者来讲是一个潜在的金矿。”①Heather Jackson, Marginalia: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P.6.事实也是如此,曾氏在致兄弟的家书中,将其阅读《后汉书》的感受娓娓道来:“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①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国藩家书》,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36页。。以上是他读《后汉书》一个月后的感受,他喜欢读史,《后汉书》是他领会较深的一部史学名著。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兄弟的家书中他又说:“《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②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国藩家书》,第28页。他告诫诸弟做事一定要有恒心,他读《后汉书》日日用功,所以才有所心得。咸丰十年,曾氏在军中戎马倥偬之时,仍然抽出时间将《后汉书》通读一遍。曾氏是政治家、军事家,更是入过翰林的读书人,读书思考是他作为读书人的本色。他不仅自己酷爱读史学经典,反复摩挲玩味,还叮嘱其兄弟、子侄读史,从中领略古人的智慧。
与亦官亦儒的曾国藩不同,晚清科举知识分子或一般士绅阅读《后汉书》,主要是为了增益史学见识,或者为了排解战乱生活的愁闷,如高心夔和周腾虎就是其中的典型。高心夔(1835—1883),原名高梦汉,字伯足,咸丰九年进士。1860年7月6日,高心夔开始阅读《后汉书》,阅读到8月7日结束③高心夔著、张剑点校:《高心夔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5—15页。。不过,在高氏的日记中看不到他阅读《后汉书》的体验和见解,可见也是泛泛而读。和高氏相似,周腾虎的阅读只是为了排解因苏南地区战乱而带来的苦闷情绪。周腾虎(1816—1862),字弢甫,江苏阳湖人,嗜读书,通晓古今史事。据周氏的日记记载:今年(1860年)苏州城破,所携书籍数十百种尽弃焉。最可惜者,两年日记三本及朋旧各书札,如曾涤翁、郭筠仙、庄卫生、张仲远各书,均弃焉,殊可惜也。兹因道路艰难,仅携《后汉书》残本十九本、《杜诗笺》一部、《苏诗钞》一部、《钱牧斋诗》一部、《李安溪年谱》一部。日日翻阅,以遣岑寂④周腾虎著、肖连奇整理:《周腾虎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51—152页。。周氏嗜好读史,但从其日记中看不到他阅读以后真实体验,殊为可惜。
晚清日记中记载时人阅读《后汉书》,并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或者评论的要数郭嵩焘、周寿昌、孙宝瑄、张佩纶、梁启超等人。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焘根据他多年阅读《后汉书》的经验,结合他在西方获得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后汉书·西域传》所出现的古地名进行考辨,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大秦者,自西汉通西域时,闻其政教风俗而为之名,其所云‘一名犁鞬’,则当时所传之名也。罗马记载,并无此名。其初立国曰刺丁,后曰罗马,其本名则意大里也,似犁鞬为语言之讹。奄蔡一国,在今里海、盐海之间,其地无可考;而自《后汉书》已改名阿兰聊,当即今波兰国。波兰地当更循里海而北,积渐为俄人侵蚀,已早迷失其故境矣。”⑤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6页。郭嵩焘的这些分析得益于他长期对中国史学经典的研究和出使西方的亲身考察后得出的,所以其结论具有一定的价值。
周寿昌醉心于两汉史研究,他曾说:“余少学读史,两汉并治。近二十年专治班史,遂未旁及。然旧所读《后汉书》,本书眉行间,条缀件系,染墨略遍,不忍割舍”⑥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思益堂史学四种本。。经过其好友李慈铭及门人朱一新、缪荃孙删削、校勘,约成一册。后在缪荃孙的固请之下,再加别择,撰成八卷本《后汉书注补正》。他认为:“常念章怀以储副之崇策府,人才之盛,殚心萃力,专注此书,宜乎精确周密,固不逮师古之注班书,成于一人之手者”①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思益堂史学四种本。。他指出,章怀注本诸家皆臆度无据,因为他所召集的注家皆碌碌无为,无著作之才。鉴于前人注本存在的错误,周寿昌的《后汉书注补正》校正前人注本之错误,并申以己见。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中就有利用《后汉书》 研究的成果,进行考证的记录。如宋洪适《隶释》有云:“东汉循王莽之禁,人无二名。郭香察书者,察莅它人之书尔。小欧阳以为郭香察所书,非也。”余按:郭香见《后汉书·律历志》,“察书”作监书解,恐亦非是。既察他人书,何以察者转列名,而书者不列名耶?窃意“察”有详谨省察之义,“察书”若今敬书、谨书之类,且令察视所撰碑文,书之无令讹脱②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三,清光绪九年(1893)长沙思贤讲舍刻本。。通过考证,周寿昌指出汉碑书写无定例,有列书不列撰人者、有列撰而不列书人者、有撰与书并列者。后人误读“郭香察书”,就是因为没有掌握汉碑书写的规律。
陈绍箕,字幹庭,师从经学大师皮锡瑞问学,皮锡瑞勉励其“读有用之书,为经世之学”,其于史学经典颇有涉猎,其读史日记“思深而虑精,言婉而寄微”③陈绍箕撰、皮锡瑞评:《鉴古斋日记》卷首冯廷桂叙,清光绪二十八年长沙刻本。。陈氏对东汉历史的评论颇有见地,如评论杜乔、李固等人:
杜乔、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螽吾侯。使能立清河王,则汉室可以振兴,不至流于削弱。天不祚汉,清河不立而立螽吾,是为恒帝。汉室由是衰微,杜乔、李固由是下狱以死,‘直如 死道旁’。惜哉!此汉室存亡之大机也。李固之言曰:‘为天下得人难’。清河王有贤名,梁冀亦不能夺。而曹腾复怂恿梁冀以威胁廷臣立螽吾侯,胡广、赵戒不敢再争,而清河王与李杜皆不得其死,岂非一言丧邦耶!④陈绍箕撰、皮锡瑞评:《鉴古斋日记》卷二,清光绪二十八年长沙刻本。
梁冀欲立螽吾侯,太尉李固和杜乔欲立清河王,外戚和朝臣的矛盾由此冰炭不容,东汉王朝亟需一位能重振朝纲的人来承继大统。李固等在质帝崩后,立即联络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并要求梁冀召开廷臣大会,结果清河王刘蒜再次作为候选人被朝臣公卿提出来。梁冀虽欲立螽吾侯,却无法一意孤行。而中常侍曹腾等连夜前往梁冀处游说,陈说立清河王为帝的严重后果。曹腾的建议最终使梁冀下定了决心,于再次朝会讨论时,先罢免李固,后立螽吾侯。李固、杜乔确是忠义直臣,他们也确实以社稷之臣自勉自任,结果为奸臣所害,政柄倒持,非一二贤臣可以挽回。
孙宝瑄(1874—1924),字仲玙,浙江钱塘人,他是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的儿子,家饶藏书,学问涉猎广泛。一九〇三年正月十五日,孙宝瑄读《后汉书·刘宠传》时,有感于刘宠为会稽太守,“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孙氏发表评论:“民不见吏四字,竟为秦汉以下政治家之美谈,则吏如虎狼、如蛇蝎,其为民害,亦可知也”⑤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31页。。刘宠作为东汉太守政声清廉、治理有方,其治下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故孙宝瑄评论其当得起“民不见吏”的表率。但反观秦汉时期的酷吏政治,刘宠这样的人居然成为当时现实政治的反讽。正月十六日《日记》,孙氏针对汉灵帝“好文学,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发表评论说:“灵、徽皆亡国之君,而所好者如此,盖不知治天下之本,而专于艺术,亦与好声色狗马无以异也。”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631页。作为帝王,兢兢于治国理政,本为天子的职守,然汉灵帝“专于艺术”,忘记了天子的本职工作,其结果埋下了东汉亡国的祸根。
晚清名臣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有不少阅读《后汉书》的记录,他也利用《后汉书》对东汉史事、人物、制度进行考证。如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初七日记载:“后汉书,南单于于漠北遗窦宪古鼎,容五斗,其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安得如此巧合,此鼎非单于伪造,即班孟坚妄释以愚宪耳。近日讲钟鼎者,大率类此也”①张佩纶:《涧于日记》,转引自挹彭著、谢其章编:《东西两场访书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123—124页。。张氏认为古器作伪多,故提出质疑。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读《后汉书》的心得传授给学生。
光绪十年(1884),严修为准备问津书院考试留馆课程,向张佩纶请教,张佩纶将其为学读书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严修。严修在日记中将两人之间的学术对话记录下来,其中涉及到对《后汉书》的看法:“经学可以从略,小学则不可不讲。……若夫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史以‘前四史’为要。蔚宗《后汉书》四六骈语自然流出,乃文体之变,亦不可不知者也。”②严修著、陈鑫整理:《严修日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3—144页。。《后汉书》语言精致工巧,重用骈体文,在骈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张氏敏锐地捕捉到《后汉书》文体之变,他希望严修阅读时尤其需要注意这种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后汉书》的事实和文意,把握其语言叙述之美。
晚清新史学开山人物梁启超非常推崇《后汉书》,曾不惮溢美之词褒扬道:“《后汉》名节最盛,风俗最美,读之令人有向上之志。其文字无《史》、《汉》之朴拙,亦无《齐》、《梁》之藻缛,庄雅明丽,最可学亦最易学,故读史当先《后汉书》”③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34页。。梁氏对《后汉书》“尚名节”和语言表述给予高度评价。1902年,他撰写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1905年,他以《后汉书·班梁列传》为改写对象,改写了《后汉书》中有关班超平定西域的故事,其改写的目的在于提倡“尚武精神”以改造国民性。梁启超对《后汉书》适于初学者读史有自己的理解,故梁启超用《后汉书》引导其女儿梁思顺学习传统史学的兴趣,在其指导下梁思顺用了半年多时间,“补读《左氏传》、《后汉书》”,并要求梁思顺每日就自己的读书感受作札记数条。他之所以如此要求梁思顺,在于他认为包括《后汉书》在内的“四史”,“其书皆大史学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人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④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清华周刊》281期之“书报介绍附刊”3期,1923年5月,第9页。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操刀演示,希望调动他女儿阅读《后汉书》的兴趣,也能写出较好的读史心得。1910年2月的《双涛阁日记》中,就保留了梁启超为梁思顺写下的两则范文,分别题为《读〈后汉书·樊宏阴识传〉》与《读〈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兹以《读〈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为例,来说明梁氏如何写该传的读后感的:此孝义传也。后史率别标“孝义”之名,范书则否,此正以见孝之大也。孝为庸德,孝而别标传,则忠也、廉也皆宜别标传矣。传中诸贤,其从政莅民,皆卓卓有可表见,所谓“锡类不匮”也,岂徒独善其身而已!夫能独善则未有不能兼善者;不能兼善,斯所谓“独善”者,亦有未可信矣⑤梁启超:《双涛阁日记》宣统二年正月十五、十六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由引文可知,梁氏认为传中诸人具有相同的精神特质,即重孝悌,所以该传未标孝义,而实含孝义精神。
阅读史非常重视搜集日记、笔记、私人信函中所包含的学术文化史的内容,分析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心理、阅读感受。夏蒂埃指出:对于文本的阅读,其实是“依从于文本的一种设计(machinery)”,是“一种创作性的习俗”,“而其所创造的个别意义和涵意,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者书籍生产者的意图。阅读是一种回应、一种劳动形式”①罗杰·夏蒂埃: 《文本、印刷术、阅读》,林·亨特编: 《新文化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我们关注《后汉书》 经典文本的读者反应,就是要解读经典给他们传递了哪些独特涵义,他们又是如何在当时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潮流中精心重构他们所理解的《后汉书》,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回应。
二、晚清日记中的史论
广义的史论是指对客观历史或者史学自身进行商榷、质疑、反思、评说的史学体裁,狭义的史论专指对史事的评论。本文取广义史论概念来解读晚清学人如何理解和接受《后汉书》,他们对《后汉书》所涉及的人物、史事如何进行分析和评论的,又是如何从史学层面对《后汉书》几种主要体裁的得失、语言叙述是否得当等进行分析和批评。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是史论的双璧,这里史论的“史”,既可以作“历史”来解,也可以作“史学”来解。
从晩清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阅读《后汉书》的学人众多,既有前文已提到的曾国藩、高心夔、周腾虎、郭嵩焘、周寿昌、孙宝瑄、张佩纶、梁启超等人,还有李慈铭、王闿运、周寿昌、恽毓鼎、贺葆真、潘祖荫、王咏霓、吉城等人。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痴迷于历代正史的阅读,视正史为了解中国历史演进和主要王朝盛衰变化的基本史料,正史阅读供给他们有关传统史学知识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些人中阅读有深浅之分、评论也有高低之别,但他们的正史情结却是相通的。从阅读的系统性和评论的深刻性而言,个人以为史学名家的见解还是超过一般学人。其中,反复阅读、并提出别具一格见解的当数李慈铭和王闿运。李慈铭和王闿运都以喜读书,喜欢将阅读体验笔之于日记中而知名于当时和后世。且两人都有名士派头和狷狂的性格,对自己的读书和治学颇为自负。因此,将两人有关《后汉书》的阅读和评论合观,对于历史评论、史学批评以及晚清《后汉书》的接受史都具有典范价值。
李慈铭读史书常常一再反复,如其阅读《后汉书》,先后在咸丰戊午(1858)、咸丰庚申(1860)、咸丰辛酉 (1861)、同治乙丑 (1865)、同治丙寅 (1866)、同治辛未 (1871)、同治壬申 (1872)、同治癸酉 (1873)、同治甲戌(1874)、光绪乙亥(1875)、光绪辛已(1881)数次阅读,时间跨度有20余年之久,且每次阅读往往有不同感受。李慈铭喜于读史,而一生读史服膺近人考据的成果,对乾嘉汉学家的史学考证又时有超越。李慈铭喜欢一边读书一边记录读书心得,而且是“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鹜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他的读书笔记一般先记录文本本身,包括版刻、文字、作者等,随后就是对图书的优缺之处以及价值高低做评判,最后的环节就是对书的作者的学术水平做一个总体评价。他的读书笔记不是就书论书,真的是读后有感而发,对前辈学者的谬误敢于大胆进行纠正,也敢于鞭挞不良学风,所做出的评论比较中肯、公允、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晚清史评家在阅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接续前人历史评论、史学评论的优长之处,对《后汉书》所叙述的东汉历史及其《后汉书》自身的体例、笔法、结构、叙述技巧、编纂思想等,皆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敢于纠谬补偏,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对东汉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评论,足见评论者的历史见识和批评素养。李慈铭和王闿运选择东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评论。比如对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中邓绥的评价,范晔在本纪对其有褒有贬,在其他人的纪传中采用春秋笔法的方式委婉地加以记载。对此,李慈铭评论道:
和熹邓后之贤,亚于明德。史于后纪中,盛赞其徽美,然迹其有不肯立平原王,安帝已长,终不还政,俱有可议。史故于《安帝赞》中,指其计金授官诸弊政,而有哲妇家索之讥。又于周章杜根传中,一言其贪孩抱立殇帝,又平原王疾本非痼,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一言其临朝权在外戚。乃知史讳之于纪而散见他纪传中,盖以邓为贤后不欲加贬,固善善从长之义也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实际上,对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范晔在本纪中就以论赞的形式加以批评。但在本纪中,对邓后尊崇儒术、注意节俭、防止外戚专权、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也如实地加以叙述。引文中所论及的“计金授官诸弊政”,出自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范晔在《后汉书》对此有尖锐的批评:“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指责邓后开东汉卖官鬻爵之恶例。至于“贪立幼主,希揽政权”,后世史家亦有讥评。李慈铭认为没有明晰地指出,而是在其他篇章中指出,盖“为贤者讳”,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事实上,对东汉和熹邓皇后及其事迹,后世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她体现了坚守妇道、依经治国的“贤者”;有人则认为她是称制终身、政略失当、信用宦官。故东汉在永元之隆的鼎盛之后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对此邓绥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后汉书》在民族传的编纂方面体现出“剪裁精当,体统分明”的特点,其民族传(外国列传)更加精细化和条理化,体现出编纂方面的高超技巧。不过,由于范晔为南朝宋人,对南朝以外的少数民族留意不够,搜集史料不足,且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故在民族传的叙述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李慈铭给予了较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既不掩其美,也不避讳其缺憾:“范史于外国传殊不经意,盖蔚宗生江右,不知西北事,故诸传多失考核。然叙致严谨,接续分明,自是良史”②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22页。。范晔《后汉书》民族传序论颇具特色,体现出他对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交往和战争的精深思考,对相关史事和人物的评论鞭辟入里。对窦宪燕然之捷的评论,需要立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后世的影响,惟其如此才能对其功绩大小作出合理的评判。公元73年,当时许多国家与北匈奴断交,北匈奴的社会经济因此受到重创。公元89年,窦宪为了立功赎罪、获取高官厚禄进行北伐,故其难度较之汉武帝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几次战役,窦宪统率的军队几乎没有受到北匈奴强有力的抵抗,战果更谈不上辉煌。而熟知北伐情形的班固,对此竭力褒扬,尤其对窦宪极尽阿谀之能事。作为亲历者的班固由于同窦宪的特殊关系,没有严守史家的客观立场。而范晔评论该事时专就事实真相发论,纯为中正客观之褒贬:“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观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后汉书》卷八十九《南越匈奴列传》)。窦宪集团一场含有水分的胜利,使得其威名大胜,促成其集团更加飞扬跋扈、蔑视纲纪、威福专横,而其对南北单于处置失当,由此而带来了西晋以后五胡乱华的局面,则被当时的亲历者所忽视。范晔生于南朝宋,距离燕然之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从后世史家的眼光来透视窦宪及燕然之捷,更能明见其功过,也更能理清它对后世的影响。范氏的史论,受到晚清史学批评家李慈铭的赞赏:“又读《西羌传》序论、《西域传》序论,辞义并精。其论西羌,追咎赵充国之迁先零于内地,马文渊之徙当煎于三辅;论匈奴,致罪窦宪燕然之捷,不复南单于于阴山,而更立北单于于故庭,遂令南虏久居河西,终乱华夏,皆识见绝高,不仅为当时中原未复,创深索虏言耳”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22页。。评论燕然之捷,立论旨趣与范氏的史论一脉相承,并称誉范氏史论叙述文辞和史义皆精深确当,洵为至论。
东汉王朝被后世学人称赞为中国历史上“风化醇美、儒学最盛”的时代,与儒生出身的光武帝刘秀大兴儒学、推崇气节有关,高层的推崇在社会上形成推崇气节、奖掖儒术的风气,涌现了一批如李膺、陈蕃、范滂、黄琼、黄琬等坚守儒术气节的刚直之士。范晔对儒术气节怀有温情和敬意,故他在《后汉书》中为这些儒术气节人物设立传记,表彰他们“扶名教、振清议”的功绩。《儒林传》表彰“通经名家”二十七人,梳理东汉儒学名教之风盛衰沉浮的原因。在《党锢列传》中,范晔评论李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可见其重视自身的气节和操守,范滂等人也与此相类。李慈铭熟读《后汉书》,对前人关于《后汉书》论赞的评论了然于胸,自身又有名士情结,故他对《后汉书》儒林气节的评论颇有见地:
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予尤爱者,其中如《儒林传论》、左雄周举黄琼黄琬传论、陈蕃传论、《党锢传序》、李膺范滂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推明儒术气节之足以维持天下,反复唱叹,可歌可泣,令人百读不厌,真奇作也!其他佳制,固尚不乏,而数篇尤有关系。范《书》以外,惟欧阳《五代史》、欧宋《新唐书》诸论赞,虽醇疵互见,文亦时病结轖,然究多名篇,可以玩味②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21页。。
李慈铭对《后汉书》推崇备至,誉“蔚宗最为良史”,在“前四史”中成就最高,个人以为有过誉之嫌。然而范书论赞确有独识特见,其洞见以儒学价值观为评判标准,依东汉儒学自身的脉络和系统,阐发其时代价值,表彰气节之士维持名教的功绩。可见,史学评论的高下不仅在于评论人的学力涵养,更在于他是否熟悉文本,并且对文本所产生的时代思潮要有清醒地剖别,如此才能对其得失成败做出中肯的评价。
范晔为东汉经学大家马融独立设传,以表彰其经学成就,足见他对东汉大儒学识的倾慕之情。然而他对马融害怕得罪外戚梁冀而作颂词的行为,以及马融为讨好梁冀不惜陷害李固,不敢苟同,认为这完全不符合东汉儒家的名节观念。对于这些私德有亏的行为,范晔虽有所针砭,但辩护的色彩更浓:“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之所以曲为之讳,即在于马融为东汉时期经学“通儒”,范晔怜惜其才,故“颇有恕辞”。正如李慈铭所说:“《马融传论》,虽贬其屈节梁氏,然颇有恕辞。盖季长大儒,不欲深斥,故别创议论,为留余地。而辞曲旨晦,其义未安。末后数语,尤为乖谬,全失史家惩劝之旨。蔚宗良史,其议论尤别白忠佞,无少隐贷,独于此传失之,足见作史者不可存私意,而文人自相回护,亦结习使然”③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24页。。史家职责在于褒贬惩劝,修东汉王朝的历史,当然应秉持“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的精神。范晔《后汉书》总体上可称得上据事直书、褒贬得宜,然对马融的评论中确有曲笔回护之处,失去史家“彰善瘅恶”的本旨。
史书编纂有明确的史法,史家编纂史书要谨以体例,力求前后统一。范晔编纂《后汉书》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传一卷时,在编纂方法上出现前后屡出、归类失当的弊病,李慈铭对此批评可以说不留情面:
蔚宗作传虽略依时代,而仍以类叙,故往往先后杂糅,自非史法。此卷所区,盖以清节,然自宣秉至承宫,皆世祖、显宗时人。惟郑均,肃宗时人,而均一出即归,在朝日少,与诸人迥异。又其平生以至行称,故与毛义并冢旌显。范氏既于刘平、赵孚诸人传序,附见义事,则均亦宜入之彼卷,以著同风,今厕此中,已为不类。尤可异者,赵典生当桓世,行事迥殊,且籍在党人,名列八俊……典既丽名,夫岂录录?乃蔚宗于典传绝不及其被党锢。于《党锢传》则但云赵典,名见而已,致令读者异为两人……蔚宗此事,可谓失之眉睫,羼入此卷,弥为不伦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29页。。
从李慈铭的批评中可知,李慈铭不赞成将郑均列入该传,理由在于郑均为肃宗时人,与以上诸人为不同时期的人,与毛义一样以品行高洁著称,且生平事迹已附于刘平、赵孚诸人传序中,不应该厕入该传,造成重复叙述、入传不够谨严的疏漏;赵典归类到本传中更是遭到李氏的强烈批评,谓为“羼入此卷,弥为不伦”,赵典行事笃行隐约,敢于当面谏诤,与以上诸人迥然有别,似乎更应该在《党锢传》叙述其生平事迹,而于本传中叙述可以说是严重错位。李氏的批评有理有据,可令人信赖。
李慈铭对东汉官制的分析和评论,能够紧扣当时东汉政治运作的实态,提出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东汉尚书之权,重于三公。故自安顺以后,大将军及三公秉政者,皆加录尚书事,始于章帝即位,以赵(憙)为太傅,并录尚书事。至安帝延光四年,北乡侯即位,司徒刘为太尉,参录尚书事。云参录者,盖其时阎后临朝,以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专政必以愿录尚书,故三公仅得参录。其后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以镇东将军初至洛阳,自领司隶校尉,即录尚书事,遂专汉政。讫于南北朝,凡篡祚移鼎者,无不先录尚书事,称为录公②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26页。。
东汉开国后,光武帝刘秀开始对中央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自东汉末的仲长统首揭示此意以来,对三公与尚书权限轻重的研究,成为东汉官制研究的重要命题。我们认为,东汉三公与尚书共掌宰相职权,东汉三公仍保留丞相的部分职权,但尚书对其有制约。尚书地位的上升,从东汉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央权力变革的显性风向标,是封建帝王限制相权的必要举措。
东汉迄南朝刘宋,正是经学式微、玄学大盛之时,东汉考据学之风受到一定冲击,时代学术思潮对范氏著史产生重要影响。李慈铭作为史评家批评范氏《后汉书》不甚重考据,所以产生了“三事之失”:
大抵南朝自刘宋以后,不甚讲考据。范蔚宗《后汉书》足称良史,又承武子家法,最重郑学,而《后汉书》中有三事之失,关于学术不浅。郑君传不举其所注《周礼》而载其《孝经》,致历齐及唐,辩论不决,此一失也。《儒林传序》称《熹平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致古今聚讼,此二失也。《卫宏传》言宏作《毛诗》序,致宋以后人集矢《小序》,此三失也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31页。。
郑玄是否注释《孝经》,从南朝齐到唐朝一直聚讼纷纭,很多目录学著作否定郑著《孝经》,理由是《孝经注》与郑康成注五经不同,所以李慈铭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儒林传序》载《熹平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是范晔著史失于考证,实际上《熹平石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刻于石上,为一体石经。关于《毛诗序》作者的问题,比较有根据的有三说:①子夏作;②卫宏作;③子夏、毛公、卫宏合作。《后汉书·儒林传》指出:“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 (《后汉书·儒林传》)。《毛诗序》作者出自卫宏之手的观点,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民国和当代学者也有很多人支持这一观点,所以李慈铭武断地批评该事,可能存在偏颇。李慈铭的批评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湘中大儒王闿运喜读正史,一生中两次集中阅读《后汉书》,并将阅读感悟记于日记中,其对《后汉书》 的评论与批评可以反映其性情和学识。东汉后妃专政,祸积于前,而贻于后。对邓氏号令自出,王闿运也和李慈铭一样提出了批评:“前书令昭后受请经,后邓后临朝,亦诏刘珍等五十余人校传记奏御。身从曹大家受经书。邓后作伪以终其身,而窃贤名,范史传之,有微旨也”②王闿运著、马积高等校点:《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8页。。王闿运认为邓后“窃贤名”,所谓的“贤”是表象,其“贤”体现在“小物之俭约、小节之退让而已”,在柄国理政方面缺乏谋略,擅国昵私,任用庸劣之才。正如王夫之批评的:“后之始立以贤名,后之终总大政以贤著,干愚贱之誉,而蠹隐于中,蚀木不觉,阴始凝而履霜,亦孰知坚冰之至哉?”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8,王夫之著、伊力译:《读通鉴论》,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460页。所以评判后妃临朝称制,不能以其贤否作为评判标准,更应该看她处理国政的具体举措。
对《后汉书》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或者入传原则、史料剪裁的批评,都能彰显王闿运史学批评的洞见。他对马融的批评:“马融以饥寒附邓氏得官,仍申伉直,及忤邓忤梁,再废几死,然后改节,以终富贵。女乐纱帐,以终耄期,天之劝恶沮善如此邪!”④王闿运著、马积高等校点:《湘绮楼日记》第一卷,第10页。他认为马融初期还能“申伉直”,后期因为怕得罪邓后与梁冀而变节以终天年,从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说私德有亏。再如对杨政列于儒林传的批评很有见地:“杨政劫见马武,足快平生之意,然列于儒林,不亦忝乎。”⑤王闿运著、马积高等校点:《湘绮楼日记》第一卷,第11页。杨政师从大儒范升攻习《梁氏易》,后招收生徒聚众讲学而名动京城,有“说经铿铿”的美誉。杨政为人豪侠,生活中不拘小节,尤其是“劫见马武”这一情节,更体现出侠者风范,与儒家谦谦君子、文质彬彬的形象相去甚远。惟其如此,王氏认为范晔将杨政列入儒林人物颇感困惑。再如对《后汉书》不加剪裁录入儒者的奏疏的批评:“西汉论政,学者皆对策上书,足以裨治。东汉王符、崔寔、仲长统诸儒,动足数万言,以诱民俗,其文必繁,范史载之,未为通识也。”⑥王闿运著、马积高等校点:《湘绮楼日记》第一卷,第10页。《汉书》多载有用之文,《后汉书》模拟之,不知东汉以后学者奏疏动辄数万言,如照录必然影响本传的连续性和可读性,也难见作者对相关人物的评论与态度。
三、结语
晚清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①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东方论坛》2020年第6期。,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世变时变不但没有降低近代学人对传统史学经典的兴趣,相反因为史学经世和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输入,他们对包括正史在内的传统史学经典阅读、重新解释和评论产生更强烈的内在冲动,出现了许多读史日记和笔记。这些日记和笔记是当时他们阅读史学经典心影的记录,也是他们阅读经典时反思、质疑、困惑、批评的直接记录,是史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部分史料关注不够,总嫌它们零碎分散不够系统,解读起来很难将有关史料串联整合,故只愿偶然引用,不愿以学人日记为主要史料来研究史学批评史,这是很可惜的情况。
近代学人日记大规模影印出版,为我们研究《后汉书》在近代的阅读史和史学批评提供了不竭的研究素材。阅读《后汉书》的读者群体较广泛,既有儒官、学养深厚的学者,也有一般的知识阶层。他们阅读目的各异,有的是增加历史闻见,有的是从历史中找到淑世修身的门径,有的是为了读书休闲。更有一些人以研究的眼光阅读《后汉书》,对《后汉书》涉及的王朝兴衰演变的重要人物、制度、史书编纂的得失等,从晚清人的史学观念出发作出分析和批评。学人日记中呈现的阅读实态的史学批评话语,展现了这一时期《后汉书》接受和批评的独特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