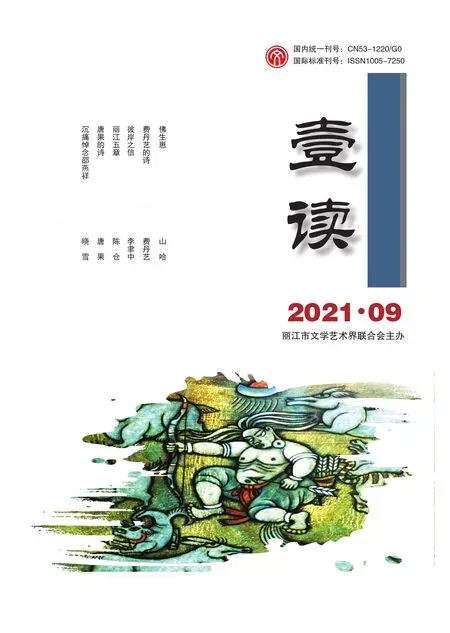丽江五章
◆陈仓
红色樱花
接到去丽江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等待着“死刑”的判决。前些天,身体非常不适,嗝气,拉稀,胃胀,偶然还有一些腹痛,就跑到医院做了检查。原来一直联系的专家不在,就挂了一个普通门诊医生。她很美,很年轻,看到我的彩超,说是非常不乐观,建议预约核磁共振,进行进一步确诊。我看她的眼神和言下之意,预感情况非常不妙,似乎是癌症什么的。从医院回到家,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如果被确诊的话,最多再活三五年。等待着核磁共振的那几天,可以用“绝望”来形容心情。每天晚上黑乎乎地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伤心,流泪,反思自己的一生,心想如果不离开小县城,来大城市闯荡,或者只是写写诗,不写小说的话,也许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了。再仔细一想,之所以害怕恐惧,倒不是放不下自己,而是放不下儿子和爱人,儿子那么小,七岁多,没有父亲应该怎么办?爱人嫁给自己还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我曾经安慰过患有不治之症的朋友,人人都会死,所以看淡一点,利用最后时光,背着包,去旅游,把那些向往的地方都走一遍,也算是死而无憾了。但是真正大难临头,才发现那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对吃,对旅游,对爱情,对人世间的一切,顿时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接到去丽江采风的邀请函,我开始是一点情绪都没有,直到几个小时以后,胶片和初步诊断出来了,最坏的情况被排除了,我才算一下子活过来了。我高兴地大吼大叫,然后迅速回复了邀请:我愿意!像结婚时对着牧师的回答。
我真正喜欢丽江,是从飞机快要落地的那一刻开始的。从飞机舷窗望出去,大地似乎被染了颜色,或者铺就了一层赭红色的地毯。等真正地走出机场,才发现那是本来的颜色,泥土似乎被一场大火烧红,火焰还没有熄灭,炽热的温度还没有冷却。机场高速两边的红土地里,青草并没有完全返绿,却开出了一树树的花。我开始怀疑会不会是假花,这种怀疑也是由颜色引起的。能有什么花开得如此红艳呢?比桃花红,比木棉花红,比玫瑰花红,用火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仔细一问,司机告诉我,那是樱花。上海是有樱花的,我在日本和韩国也看到过樱花,多数都是粉嘟嘟的,带着许多胭脂味,而丽江的樱花却如此之红,红得有些不可思议,红得超出人世间的许多颜料。如果用性别来定位,我以前看到的樱花都是雌性的,这里的樱花是中性的,甚至是雄性的,有一股子男人的激情、大度和火热。原以为只有变异的几棵,但是到了酒店才发现,大门前,院子里,墙角,街道两边,有许多高大的樱花树,而且樱花开得格外的耀眼,把天空都烧得红艳艳的,不注意去辨别的话,还以为空气中掺杂着淡淡的釉彩呢。我站在樱花树下,终于明白了,枝丫是红色的,花瓣是红色的,再一低头,发现根是红色的,根下边的泥土是红色的。原来,这些红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染出来的,是土地燃烧出来的,是从土地里蓬勃生长出来的,是无法脱离土地而单独存在的。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自然养出了一树树红红的樱花。
我们入住的是一家别墅型的酒店,名字叫悦云别院。也许因为一个“别”字,让人感觉格外的亲切。我刚刚出了一本《上海别录》,也有一个“别”字。别名,别称,分门别类,是旁边的意思,也是特别的意思,更是别有洞天的意思。院子里有几个池塘,池塘里种着荷花,此时荷花还没有开放,只有几片荷叶浮在水面,池塘中间是几条九曲回环的石板小路,铺着的石头五颜六色,都隐隐地透出了玉的质地,也许那本身就是玉吧,走在上边发出的脚步声,也显得温润了不少。
我是第一个到达的,因而住着第一号房间,这是一个单门独户的小院,院墙也是由石头磊起来的,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每一块都充满着诱惑。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石头里的人,真想把它们抠出来,仔细地把玩一番,然后挑几块带走。院门是木板的,阳光打在上边,斑驳得像一幅岁月久远的壁画。门齐胸那么高,没有安锁,只有一个门闩,此时正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并且发出吱咛的声音。几十年前生活在农村,家家都是这种木板门,出门进门,都能听到这种声音,随着这种吱咛声,总会响起“我回来啦”,或者“你回来啦”的问候。但是进城以后,再也看到木门了,更别说这样的吱咛声了。城里的门都是铁的,都是上着锁的,在那一关一开之间,只有钥匙转动的咔嚓声,只有冰冷的哐当声。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卧室,墙上挂着许多画,有些是风景,有些是告示,不过都不是中文,而是神秘的图案。尤其是浴房中间,摆了一个白色浴缸,造形优美而高雅,墙上挂着的那一幅“书法”,每一个字都像一幅画,我问过当地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这是纳西族文字。他们的文字是象形的,看上去确实如画一样美。
最令人心动的,是无论从客厅还是卧室看出去,窗外都是红艳艳的樱花,随着风轻轻一吹,如雾如烟一般涌动着,再越过树梢望过去,竟然就是玉龙雪山,积着皑皑白雪的山顶,远远望去像戴着皇冠一般。入住这样的地方,无论坐在房里眺望,坐在院子里喝茶,还是下楼走动一下,一草一木都是那么静,静得连一声鸟鸣一只虫吟都没有,静得可以听到空气流动的丝丝声,静得看到一朵花瓣飘落的时候都有些惊心动魄。关键是没有叫卖声,没有匆匆的脚步声,没有汽车的轰鸣声。这不就是世外桃源吗?有朋友问我,丽江怎么样的时候,我由衷地告诉他们,那颗躁动的心随之也静了下来,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脏均匀的跳动声。
吃过晚饭后,大家相约着去古城,说没有去古城算不得到过丽江,等着打车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夜色初起、游人如织了。不过,我还是挺失落的,无非是霓虹艳影,无非是售卖特产,无非是酒吧茶座,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不安,到处充斥着商业气息,这和江南古镇有什么差别呢?尤其酒吧一条街,妖艳的歌女,失态的游人,放肆的酒徒,嚎叫声和吵闹声响彻天际,让人听了看了格外地烦躁起来。于是,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离开了,打车回到了悦云别院,在樱花树下流连,在荷塘边徘徊,在落地窗前矗立远望,仔细地享受着只有神仙才有的清静。
蓝色程海
上海的路名多数是以全国各地地名而取的。云南路在黄浦区,是小吃一条街,丽江路在闵行区,直插黄浦江北岸。刚刚查了一下地图,永胜路也是有的,不过非常偏僻,非常狭窄,也非常短,几百米长吧。所以,我是第一次听说永胜县这个地方。从丽江前往永胜县的汽车上,我是不以为然的,但是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被窗外的景色震住了。山本来就不大,却有一半被淹在水下,就显得更加矮小了,因而公路差不多是从山顶通过的,蜿蜒崎岖得像舞起来的一条飘带。山与山之间并不宽阔,像一个不规则的浴盆,里边注满了水,那水是浅蓝色的,蓝得十分纯粹,蓝到了树林深处,蓝到了人的心里,阳光洒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被微风轻轻一吹,像在抛洒着无数的金币。
我问,那是水库吗?朋友说,这啊,叫程海。我以为叫陈海,和我是同姓的,所以就特别的得意。但是,很快就被朋友纠正了,人家姓程,和我这个姓陈的并非一家。我抚摸过许多海,东海,南海,渤海,黄海,波罗的海,加勒比海,基本上都处在低处,是河流们的归处,是世界的尽头。但是永胜县的程海,却被众山托举到了高处,托举到了半山腰,似乎要托举到天上去,要和天空举案齐眉似的。朋友进一步介绍,程海的水面海拔1500米。我忽然想到自己在上海爬过一座山,它是上海唯一的山,也是最高的山,海拔不过99米而已。我说,这也太牛了吧?朋友却很认真地说,它叫海,却不是海,只是一个湖泊而已。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太小了。我看了看沿着公路向前延绵不绝的湖水,有些怀疑地问,感觉不小啊。朋友说,南北长只有25公里,东西最大宽度5公里,平均水深25米,总面积不到80平方公里,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叫海,在古代只能叫程河,是四周的泉水汇聚而成的,再向下游流去就汇入了金沙江。我在心里想象了一下,突然感觉到朋友所谓的“小”,原来竟然是这么的大。他似乎并不是谦虚,相对于绵绵不尽的群山,相对于这片广阔的红土地而言,这确实是小了点,但是它在我的心头,真是够大的了,不仅一眼望不到头,也是看不到底的。
我过去见识的那些海,确实无边无际,但是一片浑黄,远远看上去,总误以为是茫茫的沙漠戈壁,没有几滴水是清澈而澄蓝的,而且水上的船,岸边的树,上边飞翔而过的鸟,是映照不出倒影的。但是再看看程海,它的心胸里还折叠着另一个世界,树在水中摇晃着,鸟在水中飞舞着,白云在水中漂浮着,阳光在水中搅拌着。一草一木只要靠近它,甚至连清新的空气和雾岚,都能从水中找到另一个自己。而且,它不把自己设为终点,让每一条投奔自己而来的涓涓溪流,在自己的怀抱里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向着外边的世界流淌着,流出了亘古不变和源远流长。
在我的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海,这颜色才是海的颜色,这境界才是海应该具备的境界。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非常得意地告诉家人,我在云南丽江的永胜县看到了真正的海,它的名字叫程海,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自然生长螺旋藻的湖泊。家人笑着说,你说漏了吧?它不过是个湖泊而已。我拿出当地的特色食品,是用螺旋藻加工的,让他们尝了尝。我不知道真正的海应该有什么标准,只是希望他们从中尝出那浅蓝色的味道。
书记杨晓敏
告诉我们程海很小的人叫杨晓敏,大家正在犹疑之间,他对自己的名字又做了进一步注释,他说自己在百度查了一下,和他同名同姓的人实在太多了,其中有一个河南作家是最大的人物,而自己是一个最小的人物。小小说作家杨晓敏,我是非常熟悉的,二十五六年前就知道了,而且在西安匆匆地见过一面。他当时是《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的主编,是小小说创作最早的推动者之一,许许多多著名的小小说作家,都是经由他们培养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小小说,题目叫《老猎人》,大意是有一个猎人,他从来没有打死过一只猎物,他老婆很生气,说打不到猎物那就别回家了。他一个人住在山里,但是仍然打不到猎物,不是枪法不好,而是每次看到猎物都不忍心下手,就朝着天上的白云打一枪。后来,他老了,想家了,于是狠狠心,准备打一只猎物回家,万万没有想到,他闭着眼睛朝着猎物开了一枪,应声倒下的,竟然是前来喊他回家的儿子……正因为被作家杨晓敏他们转载以后,受到了比较高的关注,也为我后来的小说创作埋下了种子。
作家杨晓敏在文学界,尤其小小说界威望极高,而且身材高大魁梧,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永胜县的这个杨晓敏,他个子不高,有些瘦弱,裤腰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发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这不就是司空见惯的农民形象吗?所以,我暂时也就相信了他的话,他对作家杨晓敏的敬仰之情,不太像是开玩笑的样子。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上当了,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杨晓敏竟然是永胜县的最高长官——县委书记。
我喜欢这个县委书记,因为他说起永胜这片土地,说起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说起自己的同事们,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清纯的光。这光,有爱惜的成分,也有伤感的成分。尤其是他讲起永胜县脱贫攻坚的故事,我们都被深深地震撼住了。他是2015年年末到永胜县报到的,宣布任县委书记的当天,就去昆明参加了全省脱贫攻坚大会。他下乡的第一站,选择了鲁地拉,那是当年永胜县边远、艰苦、贫穷的代名词。他清楚地记得走进东乐村傈僳人家时候的情境——感受不到生活的气息,简陋的茅草屋里,老人蜷缩在火塘边,苦扛着日子的艰难,餐具与猪食混杂一地,年轻人怕生,都躲到邻家去了。他无法与他们沟通,看看住的地方,两层茅屋,一楼是畜圈,二楼住人,盖的被子单薄,粪气扑鼻。第二天,前往格克,一路走走停停,不见一丝绿意,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一派苍茫、悲壮,唯有那狗的叫声依稀传来生命的抗争……经过考察,他把首战定在解决交通与就近安置两件大事上。
说到狗叫声,我翻开永胜县编辑的一本《唱给扶贫战士的歌》,杨晓敏书记有一首诗《我的2018——写在元旦新年》:我属狗/2018年是狗年/我像狗一样守望着/山里的贫穷与寂寞//每当听见深山里的狗叫鸡鸣/我再也找不到唐诗里的意境/只落下一地的凄凉/我甚至觉得/哪里有狗的叫声/哪里就有贫穷与落后/再见了,又一个狗年//永胜的2018/是焚烧尘封岁月的一年/我不想回忆/还是忘记了的好……这是他来到永胜两年的时候写的,我们从诗句中,可以读出他当时的心情沉重、忧伤。他在诗里不想回忆的,是一年前的2017年,脱贫成效被考核为“一般”,他和县长被省扶贫领导小组集体约谈,向丽江市委常委会深刻检查反思,组织问责处理了一批干部。2018年9月18日,他在决战脱贫攻坚誓师大会上举起右手,向永胜人民进行了宣誓:坚决打赢永胜脱贫攻坚战。他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正在带领我们参观食用菌培育场。他激动而又深情地告诉我们,这是他这辈子第三次宣誓。第一次是小时候对着母亲宣誓,一定好好学习,第二次是长大后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时起,为了不违背誓言,他不曾离开永胜一步,不曾离开他的战士们一步,不曾离开过贫困群众一步。那一年冬天,他的爸爸重病住院,他只能在电话里等到病情的好转。那一年,他们彝族的新年,他在48年中第一次没有回家团聚。那一年,他年迈的母亲以为他出事了,非要到永胜见上一面才安心。那一年,他三岁的儿子,每天都要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只能告诉儿子,等到永胜脱贫,爸爸就回家了。儿子不知道什么叫脱贫,就天天打电话问:永胜脱贫了没有?
我问起牺牲在扶贫路上的干部,杨晓敏沉默了,眼里充满了泪水。我们不知道这些扶贫英雄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仅仅凭着永胜县委副书记吕开家的一首诗,足以打动所有人的心。这首诗同样收录在《唱给扶贫战士的歌》里,题目叫《一个不会笑的女孩——记扶贫英雄之女杨江燕》:从走进你的家门/你就一直双眉紧锁/你双手放在小膝头/像个犯了错的小朋友/小伙伴说,她以前老爱笑/笑得灿若星河/自从她爸爸走后/她就不会笑了/常常凝视远方,双眉紧锁/我不知道突然消失的笑里/你小小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伤痛/在你紧锁的眉头里/有一种倔强的沉重/你自豪地说你是班里第一/你说你长大后像爸爸一样/当一个村干部/你说你从未走出过山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轻轻地牵着你的小手/走过你家房前屋后/有十几只羊,两匹马/还有半坡的花椒树/你说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妈妈带着你一起干活/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个十一岁的女孩/为什么有双38码的脚/你不停地回望山头/说那是爸爸的坟头/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他为僳僳山寨太奔波/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两行泪水从脸颊滑过/却依然是双眉紧锁/一个不会再笑的女孩/多么让人心碎心痛//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一定要让你的笑灿若星河/我可能很快就老了/但我还有老婆孩子/他们都是你的家人/我自认一个“挂包帮”/世袭的“挂包帮”/让你走进大学,走回大山/当一个村干部/并且笑若星河。
2020年4月,永胜县以“零错评、零错退、零漏评”、满意度99.56%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国家第三方评估验收,5月16日,云南省正式批准永胜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顶戴了多少年的贫困帽子终于摘掉了。我问他,接下来是不是可以休息一阵子了?杨晓敏的回答是:根据上边的精神,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美丽乡村建设。我不禁在想,再过几年过来,永胜县应该美不胜收了。至于个人的未来,这个曾经当过多年老师的汉子非常认真地说,自己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把县委书记这一岗位视为人生的顶点。如今永胜县已经脱贫摘帽,他已经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如今最想去的地方是像文联这样的清雅部门。我有些不信,他于是拿出了自己写的诗,说自己也想当一个诗人。
最近看了《庄子·达生》里有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用瓦器做赌注,他的技巧就十分高超,如果用带钩(贵重的装饰)做赌注,他心里会有疑惧,技巧就会变差,如果以黄金做赌注,他的头脑就很容易发昏。杨晓敏是一个没有下注的人,无欲无求,心怀满足,在未来的路上应该更加轻松,哪怕真成了诗人,也是更有想象空间的诗人。
边屯文脉
在永胜县,我们意外地发现,毛泽东的先祖是从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一直迁徙下来的,而我的老家与华州区仅仅隔着一座秦岭而已。
永胜县被金沙江自北向西再向南环绕着,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先秦时期开始,云南便首开实边屯垦先河,也就是移民大开发,而到了两汉前后,从游牧发展为农耕,尤其明朝洪武年间实施“寓兵于农,屯民实边”政策,调派大量军户、民户进入永胜,开荒种地,戍卫边疆,开创了永胜农耕文明史的新纪元,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交融的屯边文化。2011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主席诞辰日,位于永胜县毛家湾村的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开馆,当地的朋友介绍起来很自豪,因为这是永胜县第一个AAA级旅游景点。博物馆设有序厅、边屯云南、云南明清历史文化名人、永胜非遗记忆、翰墨丹青话边屯、北胜州与澜沧卫、沧阳春秋等七个部分。其中,最吸引我停足注目的一张展板,上边列明了从西汉至清代的云南人口变化:西汉元始二年929132人,东汉永和五年2395334人,晋太康元年510360人,南朝宋大明八年35827人,隋大业五年75006人,唐天宝十四年167837人,南宋嘉定十六年268607人,元至元十三年5740020人,明天启五年1468465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2720000人……我又查阅了相关资料,西汉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近6000万,云南占到了近93万,而到了东汉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40年,全国人口虽然下降到近5000万,而云南人口一下子上涨到了近240万,人丁的兴旺从某种角度可以发现,当时屯垦戍边的兴盛发达。
随后的人口数量增增减减,多数都与战乱有关,从一个侧面看出了每朝每代的和平安宁程度。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6亿,云南省人口1750万,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10亿,云南人口为3250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达到13.39亿人,云南省人口达到4600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未公布,专家预计全国人口将超过14亿,预计云南省人口将超过4900万。看看这些数据,再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到来,云南省人口一直处于稳步上升,体现了各族百姓在党的领导下,生活稳定,安居乐业,生命得到足够重视,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
走出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我不停地琢磨,为什么博物馆会选址永胜县的毛家湾村呢?在接下来的游览中很快就得到了解答。原来,边屯文化博物馆只是这个旅游景点的一部分,加上毛泽东祖先纪念园和毛氏宗祠,共同组成了边屯文化博览园。在毛泽东祖先纪念园里,系统地展示了毛泽东主席的第二十代先祖毛太华及其后裔,500多年来创立的毛氏文化。据相关资料介绍,毛太华在元末明初时期,为避乱而从江西吉水县迁至如今的永胜县。因为是逃难中,没有确定的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明朝初期才到达永胜县,因为当地海拔较高,加上当地世居的是彝、僳僳、白、纳西、普米、傣和苗等土著民族,社会相对安定,所以毛太华等人就此停了下来。毛太华开始靠帮工度日,由于特别能吃苦耐劳,又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深受当地土著民族的赏识和好评,日子过得很安稳。洪武十五年,明军平定云南,为巩固领地,确保一方稳定,就地招募了一批军士扩充队伍,毛太华应招从军,开始了农耕、练兵、作战的屯戍生涯。这期间,毛太华娶当地纳西族王氏为妻,安家落户,并已提升为百户长,居住地也命名为“毛家湾”。后来,毛太华因为参加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筑城工程,并立下军功,受到嘉奖,赐封为“武德将军”。
毛太华在永胜毛家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随同湖南人迁到了湖南湘乡县,十余年后,毛太华去世,其长子毛清一和四子毛清四再迁到湘潭定居,这便是后来扬名天下的韶山冲了。毛氏宗族在山清水秀的韶山繁衍下来,传到第二十代孙,便出了伟人毛泽东。毛太华的次子毛清二和三子毛清三,当年则留在永胜县继承军户,便一直延绵嗣续至今。在《毛氏族谱》中,毛太华被韶山毛氏奉为始祖,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实为一脉,所以,永胜毛泽东祖先纪念园前矗立着的一座毛泽东铜像,便是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请回来的。
在纪念园参观时,有一张“毛泽东世家迁徙路线图”,详细标明了毛泽东世家的来龙去脉。矗立在地图前,我这个陕西人显得比任何人都要激动,因为顺着毛太华再向前追溯,他的血脉源头竟然在陕西华县。华县隶属于渭南市,2015年改为了华州区,离西岳华山不到三十公里,北临渭河与大荔县相望,西北不到一百公里是富平县,南依秦岭与洛南县交界。洛南县和我老家丹凤县同属商洛市,也就是说,我的老家与毛泽东的先祖,只隔着一座秦岭而已,车程也不过两个半小时,许多生活习性和风俗民情都是相同的。回头想一想,这一发现也不足为奇了,因为陕西是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我们的最后一个景点,由毛太华后人带领着参观了毛氏宗祠。永胜毛氏宗祠和韶山毛氏宗祠一样,大门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为“注经世业”,下联为“捧檄家声”。根据相关资料,上下联分别出自一个典故,上联说的是汉代大儒毛亨、毛苌曾经为《诗经》作注,下联说的是,东汉人毛义,大家都知道他是孝子,有一次张奉去拜访他,刚好上边的任命文书到了,要毛义去任守令。毛义拿到“檄”,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张奉因此看不起他。后来毛义母亲去世,毛义不再出去做官,张奉感叹自己知他不深,他不过是为了母亲才出仕为官的。联系典故,上下联可以理解为,毛氏要把诗书作为传世家业,以奉孝出仕彰显家族声望来光宗耀祖。这么一解释,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与词人,独领风骚国内外,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毛氏宗祠的香堂上挂着一幅匾额,“敦本堂”三个金色大字,更是令人深感震撼。“敦”字可以解释为“敦厚,厚道”;“本”字可以解释为“根本,根源,始终”。“敦本”结合起来,这里的大意应该是,以厚道为传家立世之根本,这也许就是毛太华毛氏一族能够在二十代后出现伟人毛泽东的又一个原因吧?
红麦深情
在丽江的最后一站是去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纪念馆建在半山坡,四周是古色的村落,房子都是红泥黛瓦,因为正是早饭时间,屋顶还冒着袅袅的炊烟,春天的阳光十分温暖,稠稠地照耀着,院子外边的篱笆上正开着黄色的野花,有一群鸡在快乐地觅食,显得无比地安静而祥和。纪念馆前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名曰“金沙水暖”的铜像,反映了红军与群众依依惜别时的情景。大家一时兴起,纷纷模仿着雕塑的姿势拍照留念。站在雕塑下,向山坡下望去,透过青青的杨柳,可以看到一条宽阔而纯净的河流,呈“之”字形流过,这就是有名的金沙江,被誉为长江第一湾。
我被深深打动的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座墓碑,墓碑中间刻着一行字——无名红军战士永垂不朽。据解说员介绍,这是一座无名战士的坟墓,位于太安乡红麦村。1936年4月,贺龙和萧克两位将军率领红二、六军团,从大理前往丽江石鼓镇,准备东渡金沙江。红军途经红麦村的时候,当地两个纳西族姑娘和世根、和继妹,发现一位战士因为身负重伤掉了队,便把他隐蔽在山上,村里十几户人家轮流着给他送饭、疗伤,但是终究因为缺医少药,这个战士伤势太重,还是没救过来。乡亲们在山头安葬了他,但是因不懂汉语,不知道战士的名字,只能叫“无名红军墓”。如今的无名红军墓,是后来重新修建的,不仅有了大理石墓碑,坟头上还栽植了四季长青的松树。
看到“红麦”两个字,我的心里为之一颤。我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种过多年的麦子,也收割过多年的麦子,每到夏天麦子成熟的时候,看到一片金黄色的麦地,尤其是穿过一片金黄色的麦地,吹麦笛,吃麦颗,扎草帽,打完麦子以后,在麦秸垛里捉迷藏,像沐浴着阳光一样明媚而欢快。但是,我所见过的麦子一定是金黄色的,如果遇到暴雨和狂风,倒伏的麦子还会腐烂发霉。而如今,在丽江这块土地上,却出现了“红麦”,难道这里的麦子,受到红土地的影响,也变成红色的了吗?解说员解释,红麦村当时并不叫红麦村,而叫螳螂坝,因为红军经过的时候,正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已经壮浆的麦粒饱满而深红,像一滴滴战士流下的鲜血凝结而成。这名无名的红军战士墓就静静地躺在山上,四周是绿了又红、红了又绿的麦地,村民们就干脆把螳螂坝改成了红麦村。原来,红麦的“红”字是双关语,既表明此地的麦子确实是红色的,也表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听完故事,我的心血澎湃,觉得“红麦”是一篇文章绝佳的题目,可是当地的朋友说,目前以《红麦》为名的电影已经拍好杀青,故事讲述了红军战士田双妹,被纳西族青年木老三相救后,经历了惊险曲折的感人故事。我听到这个消息,并不觉得遗憾,而是深感欣慰。不仅因为纳西族人大仁大义的精神被发扬光大,更因为红军伤员不再无名无姓,而是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田双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