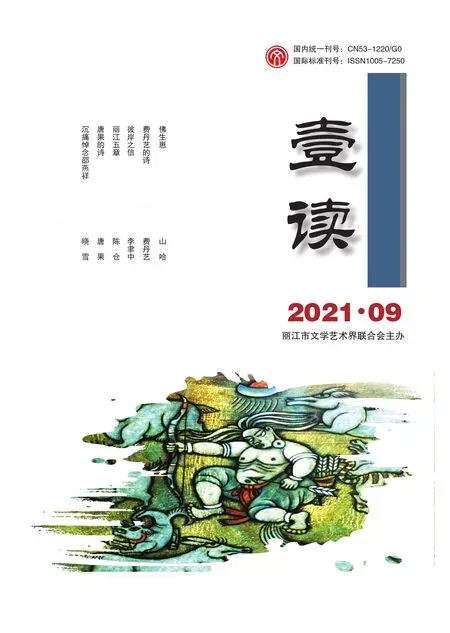沉痛悼念邵燕祥
◆晓雪
2020年8月13日,我正在读邵燕祥最近签名赠我的新著《胡同里的江湖》(北京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为他87岁还有这样惊人的记忆力和写作热情而赞叹不已,却突然有朋友电话告知:邵燕祥已于最近去世,你怎么不知道?!我大吃一惊,不敢相信,立即挂通北京他家里的电话,是他女儿和他夫人谢文秀同志接的。果然,燕祥是7月31日晚入睡后因心梗没有再醒来,8月1日早晨家人才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诗人就是这样无痛无疾、无声无息、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人间。因在疫情期间,没有向中国作协领导报告,没有发讣告,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8月3日即火化后由家人把他送了。我向他夫人和女儿表示慰问后就放下手机,陷入了难言的悲痛和沉思……
邵燕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才华横溢、激情澎湃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声歌唱而成就卓著、影响广泛的青年诗人之一。他早慧、早成名,10岁左右开始读到鲁迅的作品,13岁(1946年)那一年就在《新民报》“北海”副刊上发表了40多篇杂文,14岁开始在《世界日报•学生生活》《华北日报•华北副刊》《平民日报•星期艺文》《诗创造》等报刊发表大量的诗歌、散文。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诗人从少年跨进青年时代,他以更热情饱满而又豪壮嘹亮的歌声,歌唱“金黄的太阳”和“人民的春天”,歌唱“北京城十月满城春风”“永定河从此真个永定”。1951年,他18岁时华东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
我跟燕祥是同辈人,只比他小两岁,但当我还在高中和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活跃于新中国诗坛的著名青年诗人。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喜欢他的诗。“我们是火,燃烧着火热的青春。”他的诗,如火一般点燃着我们的心灵。记得当年在那红叶满山的美丽的珞珈山上和碧蓝透明、垂柳依依的东湖边,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朗诵他那豪情满怀、激荡人心的诗篇:《到远方去》《英雄碑下》《青春进行曲》《中国张开了翅膀》等等。
我们的年纪十八、十九,/顶多不过二十挂零;/有一个波涛澎湃的大海,/歌唱在每个人宽广的前胸。——《在夜晚的公路上》
中国的土壤是温暖的土壤,/有什么样美好的种子不能发芽?——《我们爱我们的土地》
大踏步地跨过高山,/跨过河底、洼地和平原,/跨过农业合作社的田野,/跨过重工业城市的身边;/跨过阴雨连绵的秋季,/跨过风刮雪卷的冬天,/跨过高空、跨过地面,/大踏步地跨过时间……/在我们每一步脚印上,/请你看社会主义的诞生!——《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
这样的诗,反映的是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表现的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朝气勃勃的青春形象,抒发的是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新一代青年的革命情怀;这样的诗,歌唱的是祖国的青春和青春的祖国,描绘的是创造春天的人民和人民创造的春天,赞颂的是排除万难胜利前进的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豪迈步伐和坚定信心。年轻的诗人同解放了的人民一起前进,同新生的祖国一起歌唱。他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夜晚的公路上”,他迎着东升的朝霞“登上脚手架”,听见“歌声起落在脚手架上,脚手架披满了金色的阳光……光荣的劳动——歌中之歌,呼唤着每个人参加合唱!”诗人的心贴着祖国的胸膛,他“伏在沙岸上倾听着”黄河那像“万马奔腾的”涛声,他了解祖国“昨天和今天的道路”,也了解祖国“明天的走向”,所以他是那样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的呼吸和时代的脉搏,又是那样强烈地表达出最能集中地反映一个民族和时代精神面貌的年轻一代的志气、理想和感情。
正当邵燕祥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激情歌唱、而且越唱越好的时候,1957年的风暴却把他打入另册。意外的打击,尽管也使他一度困惑不解,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他却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怀着深挚的感情。他有一颗“像泪水一样明净,像欢笑一样单纯,比鲜血更殷红,比钢铁更坚韧”的“战士的心”。他《心中的誓言》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党,/我是你永不改悔的儿子。/惟其我爱你,一如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爱为真理而斗争的同志,/我才不能爱母亲身上的痈疽,/不能爱恶人、棍子和骗子。”他在自己被误解、受压抑的时候,仍歌唱着有“一把一把发亮的种子,一串一串闪光的花朵,一片一片橘黄的果实”的“灿烂辉煌的祖国”;高唱着“永远在呼唤,永远在瞭望”,“一往无前地”“飞向风波浩渺的远方”的海燕。在“历史蒙羞,祖国蒙难,人民蒙尘”的那些“四害横行”的黑暗岁月,他更“不指望个人有更好的命运”,但他那“流徒四方的灵魂”仍坚持:“可以忍痛,不可以呻吟,哀歌不符合战士的性格和身份”。他宣告:“可以剥夺我的一切权利,但割不断我与人民的血缘。”《一九六八年的一封家书》中,他向亲人诉说:“尽管我们有一千种不幸,升沉在时代的漩涡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所以,当那“不可阻挡”的春天又重新到来,他又“继续歌唱,关于真理,关于历史,关于同志和敌人”的时候,多年郁积于心的思考、感悟和激情,就如解冻的河流,如自己的瀑布,奔腾不息,一泻千里,并带着“永不消散的雷声”,比早年“歌唱的小溪”唱得更高亢嘹亮而又沉洪有力了。我们看见他“迎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又“不知疲倦地”走上“一条风雨的长途”。他把自己比作“停住脚步”“就失去自己”的风,要“走遍世界,寻找我的歌声”。他“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万马奔腾,去找到更新的节奏,更美的格律!”(《中国又有了诗歌》)。于是我们读到了他重新歌唱劳动和建设,歌唱“七十年代的拓荒者”,歌唱地质队员和林区工人的诗,读到了他《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为青春作证》《如花怒放》《迟开的花》《岁月与酒》《也有快乐,也有忧愁》等等那一本又一本倾注着赤城的热血、更凝聚着浓烈厚重的感情和深刻独到的思想的诗集。种子在心灵的沃土上孕育了二十年,如今迎着春风春雨,很快就开出了一朵又一朵、一丛又一丛“成熟的花”,并结成了饱经忧患的“酸、甜、苦、辣”的“神秘果”。我们感到作者还是那个写《到远方去》《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的邵燕祥,但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天真和单纯,而是变得更理智、更成熟、更丰富、更深沉了。
在经历了从狂喜到痛定思痛的阶段之后,我们的诗人进入了思想活跃、感情凝重而心灵平静的最佳创作时期。他不再一般地“絮聒冬天的故事”,“也不会唱轻浮的喜歌”,而是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宏阔博大的情怀,来抒写他对历史现实、时代生活、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独特感悟和深深思索。短小的诗章,已不足以容纳他炽热的激情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的丰富内涵,他便较多地采取了洋洋洒洒上百行以至数百行的诗歌形式,连续写下了一系列抒情长诗,如《不要废墟》《长城》《走遍大地》《怀念篇》《北京与历史》《劳动》《我是谁》《与英雄碑论英雄》《海之歌》《十四岁:什么是我的事业》《南京》《命运》《荒原》等等。这些诗,尽管主题不同,题材各异,但不论是怀念自己分散在各地的朋友,不论是献给开拓荒原的地质工作者,也不论是探讨自己和人民的命运,或歌颂十四岁——青春的起点,诗人都努力把历史和现实、把生活和理想、把宏观和微观、把自己和人民有机地自然地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体现出一种引人入胜、令人深思的艺术境界和哲理深度,体现出一种强烈深沉而又博大恢宏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谁说这是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以人民命名的时代;我们的英雄/诞生在普通劳动者之中。”“英雄的人民是浩渺的银河系,/正闪烁起千千万万英雄的星。”“为你所爱的人民而献身——/或是电光石火的一瞬,或是艰辛劳动的一生。/生为理想贡献一切,死把理想留在人间。/不是为了死后让人纪念,/要趁生前多作有益的事情。”
高度的概括,以生活的积淀作基础;深刻的警句,以历史的反思为源泉;凝重的深情,为理性的光辉所照亮。诗人在坎坷的道路上同人民一起经受锻炼而成熟起来,他懂得“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都不再是我自己”,他懂得了如何“从深邃的源泉/不断地奔向遥远的目的”,因而他的一系列长诗绝不停留在表面地浮浅地赞美一下建设图景、新人新事和山水风光,而是常常以一种震撼灵魂的声音和耐人寻味的诗句,传达出“来自人民心灵深处的历史的召唤”,启发你“去发现世界的秘密,去发现无穷无尽的真理,去发现中国的明天,人类的未来。”读着邵燕祥这些直抒胸臆、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我们感到,不仅“五十年代的精神”“还在八十年代的胸膛里燃烧”,不仅“中断了二十年的歌”又接着唱起来,而且烧得更红更旺盛、唱得更好更响亮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在这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诗人“放开历史的长河”,“把目光投向了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宏观、微观”,他的诗不断创新突破而达到了我们时代的更新更高的水平。
燕祥从小喜欢读鲁迅的书,他一生写诗、作文、做人都以鲁迅为导师和榜样。面对现实生活中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尖锐矛盾,他在写诗的同时,从1980年开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一篇篇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他一手举着诗歌的火把,一手点燃杂文的烈焰,向自己的新的艺术高峰攀登。六十岁以后,更是以杂文、随笔为主,先后创作出版了《忧乐百篇》《会思想的芦苇》《自己的酒杯》《无聊才写书》《小蜂房随笔》《杂文作坊》《邵燕祥杂文自选集》《捕捉那蝴蝶》《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卷》(三卷本)《邵燕祥文抄》《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我的诗人辞典》等十多部杂文、随笔集,总字数约300万字之多。1996年,《邵燕祥随笔》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人邵燕祥同时成为我国当代创作最活跃、成果最丰硕、最引人注意的杂文大家之一。
燕祥在《为郭小川杂文集作的序》中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他的杂文针砭时弊,揭露瞒和骗,鞭挞假恶丑,文风犀利,尖锐活泼,爱憎分明,痛快淋漓,使人猛省,给人启迪,引人深思,靠的就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他的杂文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有深刻的思想艺术力量。他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像鲁迅那样,用解剖刀无情地解剖民族的劣根性、解剖社会痼疾、解剖骗子、坏人和各种黑恶势力。但同时,他也像鲁迅那样“时时解剖自己”。1988年他写了《梦醒后的启蒙》。他有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他在评胡风诗的《气势》一文中坦诚地说:“我也随声附和地写过声讨的诗,伤害过曾经带我上路的人”。在评论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时,他说,自己成了右派“减少了我伤害人的机会”,“如果不成异类,依我的社会存在和思想状况,则我会积极响应所有号召……纵横冲杀,伤害好人……”。从《沉船》到《人生败笔》,再到《找灵魂》,他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解剖和修正自己。他说:“我在再一次批阅归宗卷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和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惊。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么除了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只有把真实留下,我们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痛苦。”
在《一要活着,二要活得明白》一文中,邵燕祥这样说:“知彼和知己,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主观世界,都是没有穷尽的。”他衷心感谢前人和朋友们写文章,“帮助我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正是由于他们的启蒙,我才像一首诗中所说:知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我在中国的位置’。”
我完全同意燕祥的好友、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过的话:“邵燕祥是当代中国文坛少数几个继承了鲁迅和巴金精神的作家之一,是少数几个敢于把自己的灵魂摆在案上,严格解剖自己的文人之一。”
燕祥从事文学创作,从13岁开始发表杂文算起,已经有74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1979年1月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上。因为通过阅读作品,彼此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交谈甚欢,相见恨晚,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为他1981年出版的诗集《为青春作证》写了序:《燃烧着火热青春的诗》,后来又应约写了《邵燕祥论》(刊于1987年第2期《当代作家评论》)。在1995年12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为我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他认真写好的发言稿《晓雪的魅力从哪里来》也给我热情的鼓励(刊于1996年第一辑《诗探索》,后来又被他收入了大象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的他评点古今中外诗人的文集《我的诗人辞典》。)1993年6月9日,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间隙,去他家里看望,他留我吃晚饭。酒过三杯,他爱人单独端出一碗面给他,他才笑着说今天是他六十周岁的生日。我意外地碰上他花甲诞辰,真是缘分,极为高兴,再次举杯,祝他生日快乐,身笔双健。1987年4月6日至24日,他率中国作家访问团来滇西采风,团员有汪曾祺、张又君、柳萌、谢明清、叶延滨、曹杰、李锐、王行之、韩映山、吴桂风等,我全程陪同。到我的故乡大理后,他填了一首词:《满江红•大理纪游》,用毛笔书法写成条幅送给我。词的下片是:“鱼龙动,风波起,金梭静,船如织。问将来潋滟可能如昔?我爱万年风雪月,更憐一海烟霞水,莫等闲辜负好河山,佳丽地”。他赞美大理山水风光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要保护好洱海、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问题。这张条幅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燕祥无可挽回地走了,但他87岁的坎坷人生,他74年的文学道路和创作实绩,他留下那么多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永远闪光的优秀著作,已确立了他“在中国的位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