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徒史(组诗)
刘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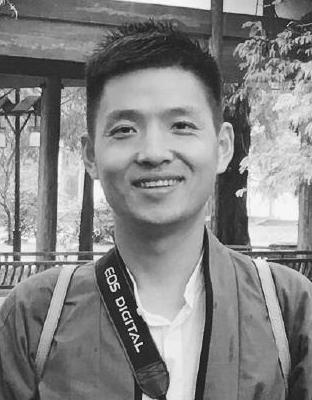
夜 雨
撑伞的人在往回赶,长路漫漫,
骤雨何时停歇。一辆车从他身旁 经过,
雨水积地,仿佛蹚过的是一面湖泊
我在道路右侧,一座两层寓所的
阳台
夜幕遮挡了大部分视线,但仍能
看到
一簇簇欢快的白光在地面迸溅
——久违的平静正从四处向我涌来
如果这场雨水的指向不是一个
特定的群体
那为何会有那么多灯火同时熄灭?
黑暗中,趿水夜行之人寥寥无几
我能猜想到他们的顾虑——
怀珠者必受其累。于是,一把雨伞
下的律动
开始变得节制,像一朵浪花拍打着
另一朵浪花。我在阳台倾听着一切
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安静,唯独剩下
这些浪花碰撞的声音
衰亡史
一个黎明的到来始于黄昏之后
其间,它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要在黑暗中度过。正因如此
雅利安人信奉的太阳神,会在
最深的暗夜里为自己的信众
注入光源。哦,火,这文明的
一种,似乎并未料到有朝一日
它会焚烧自己的子民。锡尔河的
河水不足以浇灭它的愤怒
还有积雪和冰山,仁慈从不
划分物类。穹底的对抗折断了
它的锐角,火烈鸟飞过帕米尔高原
秩序的锁链仍未断开。他们
得到了什么?一座废弃的王城或者
无上的荣光。历史的镜像在
消亡中逐渐黯淡,有人自烈火中
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一张
移动的版图,在冰河里缓缓下沉
一 天
最后一片落叶被风吹走,我想到了希尼
那个在树林里独自取火的男人,会不会也
感到孤独。木屋就在不远处,他有
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用来出神。为此,
我用一封信的头尾部分,记录下了
这个伟大的时刻:1939年,都柏林街头的
一枚浆果突然掉落,若干年后,它的果仁
又回到了德里郡的枝头。这是爱尔兰
北部的一座小城,漫长的想象和等待
每天都在发生,我在信中闻到了浆果的
香味,但仍无法从大片的空白中认领
被隐去的那天——大风吹走了落叶,落叶
被用来引火,一个男人在火堆旁
铺展开信件。他也闻到了浆果的香味,
并回想起若干年前的那个夜晚,他曾在
一株果树下做過短暂的停留,只是
那时还没有爱尔兰
迁徙史
一枚星子的升降不会影响
整盘棋局的走势。同样,
一座山峰的塌陷也不会阻断
这片地脉的延伸。雅利安人
在祭台旁告别了自己的先祖
——一个拥有古老智慧的
婆罗门种,乌拉尔山脉的游牧者
战争为他的后代划分了新的
归属,冬月的最后一天
大陆的版图由西向东。有人在
烙铁,火红的焰光在黑夜里
升腾。深肤、浅肤,阿姆河
勾连起锡尔河,中世纪的岔口
在火光中渐次清晰
食草者和食肉者在同一片平原
角逐落日,壑沟与战火
烈马和獒犬,文明与文明的种子
在里海里沉浮。只有一种跫音
在梵语里悄然滋生,那是某种
不可役使之物的流连之声
战争仍会以碎裂的形式
蔓延向东。而棋盘的星子,
最终会落向哪里?
水 手
他们在欢呼胜利,在破旧的
帆船上频频举杯。只有尚未经历过
死亡的年轻水手才有这样的朝气
老波德将杯中的红酒倾入大海
一种鱼鳞般的反光刺入眼睛——
多么平静,仿佛它从来没有
吞噬过生命。年轻人们在甲板上
挥舞手臂,鲜活的力量就要穿过
他曾经逃离的部分,一片褐色的云
和被它笼罩的曦光——
这闪电的一种,在风暴止息前的一刻
钻入云层。它并没有消逝
像一道闪过的寒光,沾满了
死亡的气息
在雨中
那个在雨中穿行的身影像极了
我的一位故人。安娜,你需要一把雨伞
用以抵住时间下坠的力量。在大雨
收摄之前,我们仍需穿越一条
狭长的甬道,才会在约定的地点
见到光源。只是夜晚尚未降临,
那颗承诺现身的星子也势必会为
阴云所阻。这是一个人力所不能抵达的
境地。接受它,并以回转的方式
替代沮丧。一定会有新的光源
在暗中生成,像雨水倾尽后仍能
再度汇聚,我们也要拥有长足的耐心
在一次次溃退中回到原点,等待甬道
再一次显现。而那个为你递伞的人
也不要认为是个巧合
证 物
年少时的那枚纽扣再一次被我取出
希尔,现在我要将它缝上你的衣袖
作为一个归人曾经消失的物证
它必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比如夜莺,夜晚降临前从不轻易飞出山林
再如飞蛾,灯火燃尽时方能从罅隙穿过
而这只是象征之一,蝴蝶仍未
在时间的一端为我振动翅膀。有时会有
跫音传来,你所说的命运也远不止
离合那样简单。它曾带我
去往一枚纽扣的凹面,并从中
捕捉那些针线穿行时留下的痕迹
这也是象征之一,我仍未在蝴蝶敛翅前
回到过去。而作为一枚纽扣未曾消失
的人证,我也要试着说出我的过往
何以为家
离开的人事又逐渐回到了眼前
像许多条纵横交错的幽径,始终没能
绕开这片树林。有时会以为
归期将至,所谓坦途也不过是门庭之一
而我已许久未见,那些送别时
又约定回返的背影。他们都去了哪里?
一条指向不明的道路会不会通往
另一扇门窗?落叶回旋,我听到了
落锁的声音。当母亲们再一次
从林中走来,腹中的胎儿已能记起来路
——回去吧,那间无数次徘徊过
却未能留下羁痕的居所。它仍矗立在
树林的中央,等待一个又一个
离开后又承诺回返的旅人,周遭
是大片的空,以及空所带来的回响
罔 替
响铃会提醒我时之将至,而流速
却并未因此而减缓。给时间设置一道
枷锁,无非是为了印证不可抗拒下的
徒劳。父亲们仍在劳作,日复一日
将一块巨石推往山顶。他们的孩子
已经长大并也拥有,推动巨石的力量
悲哀之事在于,还未有人学会
在昏昧中抬头,巨石就已从坡顶
滚落下来。我尚沉浸在拥有力量的喜悦
却不知巨石已压过头顶。有多少父亲
曾和我一样,坚信依靠一双臂膀
就能抵住下坠的力量。如今他们
仍在山顶,在一次次循环往复的推动中
日渐沉默。我们的确拥有抵住巨石的
力量,并会以父亲的方式延续下去
直至山体倾圮
夜之赋格
一个人在荒原守着日落,等待时之将至
鸟兽归巢,世界的秘密被收入腹中——
夜晚就要来临,语言在赶来的途中又
折身而返。他什么都没有说,面对这
空旷的大地,唯有星盏自地平线冉冉升起
一个人的疑惑需要多久才会得到解答?
许多年前,当一枚红日从天边垂落
荒原的夜晚曾向他发出过邀请,
那是只有死者才能听到的声音,关于死亡
和终结,似乎有一场盛会永远都在这里等他
作为受邀者,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同伴
仿佛通往终点的路径彼此交叉,而他
错过了所有的节点。该如何交付自己的灵魂?
有人悲泣,有人欣悦,也有人在静默中
守着最后的谜题。像这星月通明的一夜,
荒原的穹顶和大地保持着危险的距离
仿佛纵身一跃,就能回到它们中间
而答案只有一个,在这场奔袭的竞技
誰才会是最后的赢家?
一个飞翔故事
如何让帆船腾空,凌越于大海之上?
老水手克里斯掌握了空中航行的技巧
——首先是一尾摇帆,用以托扶
劲风吹拂的巨力;其次是一杆轮舵,
避开穿云时对冲的气流。当然,
一段玄奇瑰丽的想象也必须拥有
它能让你的故事听起来更加精彩
一个水手的经验之谈无外乎如何穿行于
风暴,而克里斯曾在云端看到过
更大的海:长风鼓荡,一座云岛接连
另一座云岛,那些消失已久的同伴
都栖居于此,他们学会了新的技艺
——往一片海中注入更多的水,但
从不溢出。他终于明白
那些被大海卷走的帆船都去了哪里
并非他们忘记了抛锚,而是在风暴
骤起前,就剪断了绳索
凤栖梧
百鸟归巢,时间落在了
梧桐之外。有没有一小蓬焰火
在枝头燃烧?栖身之心让我
倍感羞赧——它可能是种多余
也有异兽随夜潜入,等待
离巢的王者再度降临
它会不会来?乔木高耸入云,
一襟晚霞遮住云天。我也有
登临之心,在某个
近乎虚妄的时刻,谜面变得
有迹可循——有谁见过
一场大火自一个人的内部燃起
高温在背部撕裂出新的羽翼
我感受到了某种轻盈,像
微风穿过树梢,就要落在
那根缀满新叶的孤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