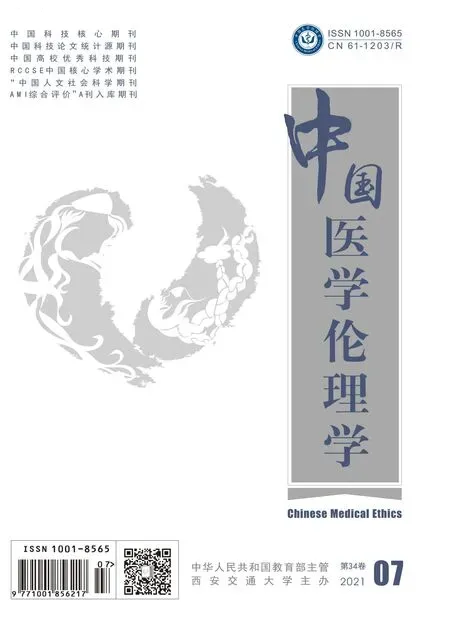中西医学人文的变迁、比较与启示
杨嘉懿
(中山大学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080,852481445@qq.com)
当代医疗科技突飞猛进,方法手段和模型工具极尽精巧,药剂设备推陈出新、品类富集。同时,临床医疗实践过程重塑人文关怀的呼声日渐高涨[1],主张强调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与实效;另一方面也需注重增进诊治过程的人文体察,真正使医学和医疗在以人为本、仁心仁术、减除痛苦、守护健康的终极追求上实现理性复归[2]。中西医学人文各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发展亦多迂回曲折。复兴人性化医疗,借助中西医学人文理论溯源与比较探索,从中发掘有益的思想养分,提炼共性,融会贯通,将有利于启迪和指引临床应用实践。
1 中西医学人文变迁的轨迹
1.1 中华医学人文的学说发轫、沿革及其精髓
中医学发轫于古代道家元气论和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逻辑,将人和自然、社会、心理看作统一整体系统进行综合诊疗,体现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中华医科理论集大成文献汇集《黄帝内经》中,“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观点,表明早在周秦两汉医学人文思想已奠定了深厚的学理根基;另其“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传于后世,无有终时”等理想构建,为后世培固坚守医者仁心、救世济民的临床核心价值观树立了典范;且其“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病理辨析阐发,系统揭示了心理精神层面以及社会人际交往等多重诱导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至今仍有实践探索启迪意义[3]。
其后经历融合儒家等各派主流哲学思想,中华医学人文绵延发展至唐代,孙思邈以《大医精诚》高度弘扬儒学重要仁爱伦理,指“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4],反映当时行业社会对医德情操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医患关系的合作构建上,其主张“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充分强调临床过程应一视同仁,行医贵在奉献付出的无私品格[5]。自此渲染定立医者仁心的基本底色,并不断有后继者将先贤开创的医学人文精义或以学说述著,或以行医实践传承。明代李时珍就有“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的传世善举[6]。潜心提升医技修为,秉持悬壶济世的赤诚,拯救民众于疾病困厄之中,是中华医学人文的价值枢纽与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并经广大行医者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事实上,古代医家极力宣扬和深入践行的大爱无疆、救死扶伤的伦理价值,反过来赢得患者的更多信任,促进了医患和谐,潜移默化中有助于诊疗绩效的提升。
1.2 西方医学人文理论渊源、演进及思想内核
一般认为,西方医学人文肇始于公元前五世纪临床医学之父——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所奠基的“科斯”学派(Cos school)理论。其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法则,主张以患者实际切身利益出发,尽可能避免盲从不成熟可靠的疗法,重视临床的基本人文关怀和讲求医学的人性温度。希波克拉底对西方医学的影响深远[7]。希波克拉底对医学人文的另一贡献是开启了西方医学伦理基本框架的构筑。《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二十世纪中叶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的思想启迪源泉。二者共同之处如此之多,乃至不同点也是希波克拉底医德精神的延伸和拓展:尊师敬业、不违良知、患者利益为先、众生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二者之中彰显的这些医学伦理其内在核心价值追求,长期成为西方从医者警策共勉的执业信条[8-9]。
及至公元二世纪的古罗马时期,西方医学人文出现另一代表人物——被誉为希波克拉底之后“第二位医生”的盖伦。如果说希波克拉底是西方理性医学的开创者,那么,盖伦则是将医学推向对生物结构系统的全面认知,并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辩证方法原理的科学体系奠基人。他有治无类、行医为善等理念亦是与希波克拉底一脉相承。盖伦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地践行患者拥有平等的医疗权利,并应当成为关爱对象的临床价值观。医学必须秉持公正的伦理观、维护患者权益的道德情操、临床注重倾听与安慰的方法论是盖伦医学哲学的最大人性化亮色。盖伦的人文理念和医德精神影响绵延横跨欧洲中世纪[10-11]。
到十七世纪,以英国著名医师托马斯·西登纳姆(Thomas Sydenham)为代表,大力驱动了医学解释从定性到定量的伟大转折,将疾病研究转向本体论层面。这一时代的医学,致力于探索运用认识论去解决临床经验,以及统计类推等方面的实践困难[12]。直至近代,美国医生特鲁多(Trudeau)诠释医疗的论述中,“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所传递出来的共情体验与理性认知,无疑是西方历代从医者恪守传承人本主义医学伦理观的真实写照[13]。
2 中西医学人文的共通点
2.1 价值取向的意合相通
中医学自古早有身心共治的朴素临床诊疗整体论思想萌芽。传统中医所阐发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学说原理,实质就是强调人、自然、社会、生理、精神心理等健康决定要素应尽量保持均衡调和。当其失调致病,在临床手段上,亦应以辩证施策、实行标本同治,通过恢复人体内外诸因素的和谐统一状态来达致健康目标。传统中医所尊奉的价值理想与境界追求,本质乃是人与天地四时、苍生万物的协调共生。
当代医学人文概念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多个大学创立医学人文系,反映西方逐渐重视开拓和发展技术与人文“两只翅膀”在医学教育和临床上寻求“两翼齐飞”的协同效应。到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第67界世界卫生大会发布全球首个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决议,提出应充分获取体恤患者个人和文化因素的信息,呼吁增强姑息治疗在生命全程综合性治疗中的作用,折射出临床人本主义诉求与政策主张获得业界和社会更广泛的认同。
诚然,中西医学皆有悠久深厚的人文基因,在对以患者为中心、尊重生命个体、人性化诊疗等诸多方面,中西医学其核心价值理念不谋而合,精神实质意合相通。在充分理解与致力减轻患者痛苦的共同指针下,中西医学客观上不约而同地综合运用人体免疫力等自然治愈力、手术与对症药物等科技治愈力,以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恰当的情绪安抚等人文治愈力,践行以守护生命健康为主征的人类终极关怀、实现人性的整体提升。中西医学人文虽远隔时空,却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贯穿着鲜明的人本主义价值主线。
2.2 理念认同历程的曲折性
中医所经历的盛衰更替、迭代发展颇具传奇色彩,深为人知。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中医的应用价值曾受到西医强大的技术冲击,在“科学主义”思潮的裹挟下,使得主要运用经验感知方法、不倚重数理模型推导,且不易重复验证的中医学一度被置于边缘化地位。其后重要的转机是随着青蒿素的发现,中医药应用获得世界医学主流的普遍认同,其“非科学性”被证伪,中华传统医药学说体系连同其人文伦理等诸多弥足珍贵的理论积淀,一同迎来价值重新发掘的重大历史机遇。
西方医学人性化理念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思辨光芒闪耀,辗转迂回到欧洲中世纪医学神性排斥人格的中途迷失路向。及至文艺复兴开启医学重归人性化的航程,为近现代医学以科学理性精神探索人与自然的奥秘开辟道路。特别近现代以来,伴随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西医临床成果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到如今,西方医学正逐渐演进融汇入生命科学的研究视域,敬畏生命机体系统的精微庞杂、潜心探究其隐秘未知领域,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与长期致力的目标。
事实上,曲线式发展、螺旋式上升,中西方医学毫无二致。纵观中西医学人文的发展变迁轨迹,可以勾勒一个清晰的共性演化脉络:获得价值认同与形成理念共识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众多挫折、非难甚至否定。直至当代,西方医学与生命科学至少在理论研究层面,二者的边界已被频繁突破、交错穿越,形成学科充分溶和、相互渗透的良性发展局面。恰恰传统中华医药自古以来尊奉“相生相克”的辩证学理,中医临床应用据以深植于复杂系统论的思维土壤,强调人与生态环境调和适配、追求自然万物协同共生的意念更是根深蒂固、并历久弥新。于是,历经千年,中西医学人文在生命科学求索的新征途再次不期而遇。
3 中西医学人文的差异之处
3.1 演化路线殊途
中医学人文观绵延数千年,而调和天人世态、平衡四时内外等充满自然主义色彩的健康理念持续居于主流并影响至今。纵使在遭受质疑与责难的至暗时刻,中医依然默默坚守救死扶伤的济世情怀,秉持传承数千年来行医无差别对待的人性化信条,竭力使药石驱除病痛的恩泽普施大众。人文为体、医技为用,是中医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标签底色。并且随着当代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医临床手段的丰富与拓展,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的普及应用,“大医精诚”情怀志向的达成与技能目标的实现更获得前所未有的来自技术层面的实质性助益。
西方医学人文伦理的价值取向在不同时期留下了迥异的历史印记,其变迁呈现跌宕反复的动态轨迹。早期是古希腊临床诊疗技术路线的分歧——“尼多斯”学派(Knidos school)施行“病症细分+特定诊断+专业治疗”与“科斯”学派采用“平衡自愈+普通诊断+被动疗法”并强化患者照护及重视预后作辅疗手段的理论方法分立对峙。这些诊疗思想的分殊实际也映照了后世“技术至上”与“人文为先”的临床理念冲突雏形。在当时医学所处的蒙昧时代,解剖与病理等医科基础研究远较当今薄弱,“科斯”学派富于人文特色的“综合-保守”疗法避免了“尼多斯”学派不少基于错误理论模型的不当诊疗,反倒更见成效。继后,随着实验、解剖等科学方法的应用,现代西方医学走上强盛的科技跃迁之路。突破自然规律极限、技术主义至上,裹持科研转化成果的利器意图征服一切疾患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在经历科学认识论的理性回归后,医技全知全能思想武装下临床手段可达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之境地实践证明只是盲目的幻觉。过度医疗带来的心灵创伤,医患关系冲突加剧,人与自然及社会其庞杂的主客体系统中大量未知,以及超越现有认识水平的领域与范畴,凡此种种,尚需深入探究,亦已逐渐成为当今西方医学的共识。
综上可见,中西医对临床中人性化医疗的运用,各自奉行的技术路线,乃至演化形态不尽相同,呈现本色分明、流变殊途的进化特征:中医人文恪守仁心济世渡困、仁术救死扶伤的执业信条,矢志不渝,慎终如始,鲜有反复,且随中医临床技术进步递次增强;西医人文历尽发展嬗变之起伏波折,当前似有重回敬畏生命、体恤心灵的复兴古典主义朴素人本关怀的迹象。复兴古法表象的背后,本质却是当代高度技术文明推动的、对健康更深层次的理性认知、生命意识概念的跃进与彻底跨越。
3.2 理论基石的区别
中医的理论基石,源于“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自然哲学思想,学说始点是将人的身心视作一个有机整体。人的身心与自然、社会相互紧密联系又彼此影响作用。中医由此得出因应个体差异与环境系统,针对单个患者机体的内外失衡来实施以纠偏归正为核心对策的功能调节。中医一再强调“扶正固本”在临床施治中的关键作用,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质是指引一种根本策略思路——将恢复人的身心情志,以及与四时内外的调和均衡作为一般诊疗的出发点与最终依归。
西医主要基于生理解剖和试验测度,借助数理工具模型,围绕逻辑推导和实证分析展开其诊疗理论。西医临床过程高度依赖数据检测与影像观察,通过逐一描述、评估人的实体性状及器官结构系统与解剖基准及统计回归求得的标准量值间的背离度,从中发现指标偏差,并及时采取经严密验证的规范化应对措施执行纠错程序。
从学理本质的视角审视,中西医学方法论的显著差别及其逻辑分化具体表现在:中医更多基于经验,主要运用归纳法,去构建一种调和人的机体功能与自然状态平衡适配的学说体系;而西医则依循解剖与实验,主要采取演绎法,形成一套精准、系统的可重复验证的推理框架,据以解析和指导临床诊疗实践。
3.3 临床策略方法不同
中医素来主张因应患者个体差异实行临床辨证整体施治,避免将病患机体等同受损的机器或零件施行分解割裂式处理。中医临床上始终承袭保留诊疗过程医患间双向直接密切沟通,“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传统方法更是天然易于拉近医者与患者的距离。同时,中医临床治疗倾向采用对人体伤害较小的方案,尤重以体恤安抚、心境疏解等情感交流方式来协助改善和增进临床疗效。东汉名医华佗就曾有鞭辟入里的经验总结——“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而这一深切省察人之情志与体疾的辨证联系的临床诊疗思路事实广泛影响世代医家。
西医临床的人文体察更多反映在借助和运用心理学原理开展精神性辅助诊疗。例如在盖伦生平年代,某些临床症状就被发现纯粹归因于“情感障碍”,在他看来,愤怒与焦虑情绪是致病根源。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间,随着近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医学的蓬勃发展,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属两类截然不同实体的观点一度被视为应有之义。直到如今,这一二分法仍有一定影响,例如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在其新近的标准研究计划中,亦仅选择以生物学方式来解释疾病[14]。只不过,西方现有大量研究提供的疾病模型愈加表明,疾病的经历和疾病的机制不仅由病理生理学驱动,而且同样由心理和社会互动过程驱动。当前,西方多数临床医生认同健康问题兼具有生理和心理、情感认知方面的因素,从而需更多关注患者的生活经历,疾病叙述和社会文化背景;诊断、预后和干预的基本临床任务不能一次性完成,而必须在与患者的持续互动中进行,以不断合理调整[15-16]。
概括起来,中西医学人文在临床手段方法上实现途径迥异:中医更偏重以患者个体为中心,考察疾病形成和发展的内外诱因,推崇以最小化的身心损伤措施来缓解疾患引起的痛苦;西医侧重发挥其擅长的分析建模、数理推导等科研范式的技术优势,同时借助知识发现的代际累积效应,最终将病理学、心理学等复合交叉学科的发展研究成果加以综合运用,临床应用上则通过侦测排查、发现及消除致病障碍等系列标准化、程式化的策略措施来抑制和克服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冲击。
4 启示与展望
4.1 医学人文的当代复兴与价值重塑
当今医学已发展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新医学模式”反映人体患病与社会心理、精神挑战等因素形成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复合整体。这一临床观念的更新,意味着单纯把疾病本身视作诊疗唯一对象的认识,已经被更完整全面的人性化医疗理念所取代。无论是致病的生物性成因如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或各种入侵人体引致感染的寄生虫,甚至疾病所依附的载体——人的机体本身,确乎都具有共同的特性——生命体征。
以“医病医身”的一般客体视角观照,临床实践所作用的受体对象无一例外均为生物体。包括医治手段,诸如传统中药方剂,从取材的主要动植物来源看,自身就具备鲜明的生物学特性。但若据此仅将医学归结为单纯处理生物问题,无疑将陷于狭隘认识论的泥淖。疾病伤害首先侵扰人的生理机体,同时通常还会伴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另外,在社会性作用下,疾患形成后实际还会施加连锁负效应,例如向患者亲友等相关者传递扩散消极情绪、产生脆弱心境牵连等诸多衍生问题,甚至还可能对患者本身产生二次逆向强化反应,形成循环累积性伤害。
综上可见,多元因素的交织与相互作用,共同创设了医学人文赖以存续的客观条件。诚如新医学人文观所指出的,医学不应只有自然科学属性,同时也应该具有心理学、社会学属性;医疗则是技术服务与医学人文的有机完整结合。这一具有二重性特征的临床理念输出,成为当前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价值体现,同时反过来为之提供关键实现路径指引。医学人文应用的终极目标是守卫个体生命健康,于临床实践全程倾注人性关切、谋求闪动人本主义光辉势必是医学人文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4.2 医学人文的中西融合
以中医学视角观照,华夏文明素有称颂从医者仁心仁术的高尚品格,其中折射出中医强调技艺与医德并重的普遍价值追求,暗合了上述西医倡导的基于“身-心-社会”三维认识观所开创的“新医学模式”。当代认识论的新视界启示,作为有机整体的生命世界,其内涵既囊括了微观粒子范畴又远超这一范畴。在透析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有序性、和谐协调性上,当今中西医学人文形成了渐趋一致的系统观与方法论。这些理念与方法的交汇融合、互补共促,在临床实践中潜移默化、形成“医疗物化”“医学利益化”等现实发展价值偏离现象的有效纠错机制。
回归患者利益至上的医学原初价值模态,临床诊疗可能更需要医学的温度,而非全盘陷落于冰冷机械的化验数据分析与影像图表推理的路径依赖。临床实践尤需还原以人为中心、大道至简的朴素人本主义理念追求,在这一层意义上,医学理论和方法无分中西。应当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医学的限度”,离弃惟对抗论式“患病-施治”的临床思维定式与单一化诊疗道路,将疾病放诸现实多因素复合影响的真实世界,以平衡心理情绪、调和机体免疫、加强预防保健、科学精准诊疗等诸合力的共同作用,最终达成以防治疾病、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性为依归的、倍加珍视与尊重生命个体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