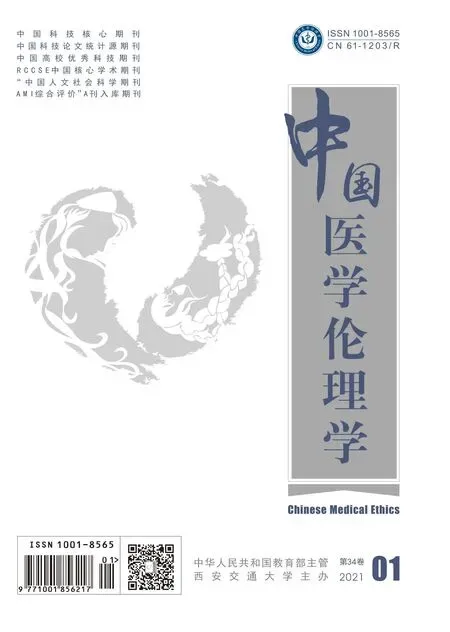抗疫中的利他行为与价值内驱
王一方,张瑞宏
(1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wyf6959@163.com;2 昆明医科大学医学人文教育与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1 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利他境遇
作为医学职业精神的核心内容,医务活动中的利他行为备受关注,它既是理论命题,也是实践命题,既是职业生活的本色,又在各种世俗思潮的纠缠下发生认知漂移[1]。人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导师,利他信念的坚定性与利他人格的光彩常常在各种灾难与危机救援中得以最大的彰显。当全球遭受新型冠状病毒的突袭时,医务界的利他情怀与利他行为再一次成为医学伦理研究的热点。与2003年的“非典”流行不同,新冠肺炎虽然毒力、致死率不及SARS病毒,但扩散之快、感染人数之多、重症变化规律之无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具备特有的体制优势,举全国之力奋力“抗疫”,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4万余名医护人员的火速驰援一线,并辅以搬家式的设备、物资大调动,率先控制了局部疫情,阻止了向全国扩散的势头。疫情牵动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心,波及每一个社会细胞,大到国家层面的组织动员,小到个体层面的应对,都凸显出人道的力量、人性的光辉。回首抗疫精神,其核心价值是利他主义。它既是职业精神(初心)的惯性驱动,也是新形势下利他价值的全新诠释。
诚然,当代中国医务界的利他初心源自80多年前抗战援华医疗队的奉献与牺牲,那是一份关于白求恩大夫的不可磨灭的记忆,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特别提及他身上有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秉性,才成就了他后来的高尚与纯粹。更可贵的是白求恩因此而获得了生命中的最大的快乐与成就感(他在中国战区做了他平生有限时间内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手术,在最简陋的环境中做了难度最大的手术)。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弥留之际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援华抗战的心境“……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2]人们不禁好奇,白求恩的利他行为怎么会有快乐?这份快乐的源头何在?价值支撑何在?这份利他快乐又如何持久?时至今日,这样的伦理拷问依然有意义。
同样,援鄂抗疫战士的媒体报道与日记(自述)都诉说了利他快乐的心情,有许多“虽累犹乐,虽苦犹甜”的叙事,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心灵独白:虽苦犹乐,甘之如饴。抗击疫情需要我们迎难而上,这是青年之担当。
回首抗疫中的利他时刻,首先就是志愿出征,逆流而上、闻风而动,因此,被称颂为“最美逆行者”,其实,对于临床医护志愿者而言,这还不是艰困时刻,真正的艰困时刻是“无亲人陪护”救助格局,患者被隔离,病情在发展,而危症床前无亲人,患者处于失亲、思亲不得的状态,医护人员必须在繁重的技术救助之外,扮演亲人般的料理、陪伴、抚慰、安顿角色,这种职业角色的泛化必然带来劳作强度的倍增,还带来责任伦理的延展、关怀伦理的拓界。
大凡经历过这样的“无亲人陪护”救助格局,才能体会践行全人医学模式之艰难。医生才意识到护士岗位、危症照顾工作的重要。此情此景,医护人员跳脱出单纯的技术救治境遇,进入一个全新的“无陪护”复合干预轨道,对未成年的儿童患者,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对白发苍苍的老龄患者,既当儿子,又当女儿。ICU里,一次翻身/换床都需要付出平时5~6倍的劳作。此时,仅有药物是不够的,仅有呼吸机也是不够的,还需治疗之外的共情,护理之外的料理,支持之外的关怀,救治之外的救赎。此时此刻,医护肩头承载着责任伦理与关怀伦理的双重担当。
与最狡猾的病毒交手,“冒死救人”绝不只是一句阵前誓言,而是实实在在的利他险境,暴露在病毒污染之下,医生随时可能成为患者,在湖北就有3000余位本地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多人殉职,他们中有院长、有专家,也有中青年骨干、护理人员。平时里,医患的角色是两分的,一个是医疗服务者,一个是医疗服务的接受者,而新冠疫情使医患角色融合,医生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享用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知者又穿越疾病蒙难程,获得情感、意志、道德的升华。从而获得双重体验、双重理解。医患共感体验的道德意义在于唤起医生内心深处的道德崇高与利他意识,对他者-自我一体痛苦的领悟、理解、实践,完成利他主义的道德内化与伦理升华。
2 医者利他行为的内驱机制
戴维·斯隆·威尔逊在他的《利他之心:善意的演化和力量》一书中对利他主义有这样的界定:“利他主义是一种无私地为他人谋福利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同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人们的感受中,日常(平常)境遇的利他并不“显山露水”,但非常(危难)境遇中的利他则熠熠生辉,让人刮目相看,就分明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其实,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观上的勾连,没有日常境遇中的利他行为教养,也就不会有危急时刻的利他精神爆发,从利他意识萌生到利他情怀的养成,再到利他人格的锻造都需要阅历的熏陶。威尔逊还将利他分解为利他行为、利他感受与利他思维,勾勒出人类利他精神发育的逻辑递进关系[3]。首先是利他快感的咀嚼,其二是利他快乐的发现,其三是利他幸福(利他主义的幸福观)的形成,最终是利他人格的铸造。在这里,快感在感官(本能)层面,快乐在心理层面,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幸福(体验)在精神层面,涉及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利他人格(情怀)则表现为某种职业惯性与行为偏好,四个层面相互影响,互为促进。
这背后潜藏着难以回避的“达尔文难题”,即“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食弱肉、优胜劣汰”,利他行为与个体利益最大化发生不可调和性矛盾,利己与利他的博弈无所不在,最终的结局是利己成为优先选择,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本能,不过,达尔文自己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群体选择”思维,后来逐步进化为“群体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解释了群体结构何以支持更高层次自然选择,群体的进化需要将群体嵌入形式多样的关系结构中,也就是说,利他行为只有放在群体利益(社群、民族、国家)的评判与考核中,才是合理的,值得倡导的。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必须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之网中通过互惠机制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利他行为分化为三个层次:一是亲缘性利他(亲缘关系,约定回报),二是互惠性利他(有道德的利己,又包含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如口碑、名誉、回报),三是纯粹利他(无血缘关系,无期许回报),在这次抗疫行动中,医患之间,亲缘性利他机会不多,更多的互是惠性利他与纯粹利他[4]。
利他作为一种内生偏好,许多文献都指出,利他源自共情体验的咀嚼与升华,由此获得一份自我满足感(自爱)、分享感,继而产生一种拯救感,提升其社会适应度(亲社会人格)[5],即不忍心别人受苦的恻隐之心,同理之心,一旦遭遇共情腐蚀(麻木),则会导致利他退缩。
在利他行为中,一定伴随着自我体验的咀嚼、评估,它是境遇伦理学的重要关注点,也是利己与利他行为抉择、人格塑造的扳机,此时此刻,一定存在着双向诱惑、双向解读、双向辩护的空间,究竟是快感,还是忧伤;是快乐,还是痛苦;是幸福,还是不幸;利他者荣耀,一个向善的社会总是给利他者以荣耀。
无疑,利他的职业精神需要多元价值支撑,国家荣誉、社会褒扬是重要的支撑,此次,对于抗疫英雄的隆重授勋与表彰凸显了这一激励效应,但外在化的利他激励总是短暂的、有限的,必须寻求内源性的激励,不断开掘利他快感、利他快乐、利他幸福的生成机制。内外合力,久久为功,才能培育良善的社会风尚。我们的确需要加大政府、民间、社会褒扬激励机制(物质奖励+荣誉认同+尊重、尊严体系构建)全社会培育、形成“关怀-感恩”(你有恩情,我有回报,知恩图报)机制,但是,心流效应(沉浸效应)的咀嚼必不可少,要让更多的年轻医者通过志愿救援享受奉献、享受成长、学会担当。同时,要重视医者职业神圣感、庄严感、荣耀感的发现,将抗疫中的利他、奉献行为内化为职业精神的核心价值。
3 利他快乐的呈现:心流效应
著名心理学家希斯赞特米哈伊(Mike Csikszatmihalyi)凭借对幸福、创造力的研究和畅销书flow而闻名。其中心流/福流(flow)效应的提出,揭示了利他时刻从快感到快乐的心理密码,也解释了职业技能养成与职业幸福的内在关系,彰显出人生追求中从满意到惬意、从愉快到愉悦、从渴望成功到享受过程的快乐原理。
医护心流效应的若干征象:其一,目标指向明确且单一(十分纯粹,只有救人);其二,项目具有挑战性(救治难度高);其三,高度自信,对结果有完美期许(我一定能救活患者);其四,完成项目需要高难度的身体技术(技艺超凡);其五,全身心地投入,注意力高度集中(全无杂念);其六,过程中有驾驭感(控制欲得到充分满足);其七,干预行为有即时反馈(病情随医疗干预而逆转,失干预而恶化);其八,境遇神圣,被带入一种忘我(无私)境界,时间凝固,偶得最优体验。这一进程如同徒手攀岩者的心流感受:痛并快乐着。他们越往上爬,就越感觉到愈加完美的自我控制,产生一种痛快的感觉,不断逼迫身体发挥所有的潜能,以达极致,直到全身隐隐作痛;然后你会满怀敬畏地回望自己攀过的岩壁,回味自己的艰辛与超越,一种强烈的征服感油然而生,一股暖流在心中奔涌,一种狂喜在荡漾。既然这一绝壁可以征服,其他挑战也将不在话下。此时此刻,利他的快感通常不是作为目标而浮现在人们的追求面前,而只不过表现为目标既达的某种附带现象[6]。
神经生物学的长足发展,逐步揭开了利他行为的神经网络机制,有研究表明:利他行为的产生与强化需要共情网络、情绪调节网络,以及奖赏网络的共同参与。首先,苦难叙事增强利他者对他人不幸的共情反应,从而提升共情动机,激发利他行为;其次,苦难叙事促进利他者情绪的有效调控,过度分享他人的消极情绪会导致个人痛苦,从而阻碍利他行为的产生,因此,情绪调节(消化痛苦,转化消极情绪)在利他行为的产生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其三,苦难叙事提高利他者的亲社会动机,面对他人的痛苦遭遇,苦难叙事可以激活脑内的奖赏网络,有助于提高利他者帮助他人脱离痛苦,获得内心温暖和满足的期待,激发其亲社会动机,继而产生利他行为[7]。
此外,心流效应下的身心境遇研究还帮助人们厘清一些偏见,如专注于某一事业,倾心投入某一项活动,一定很苦很累。其实不然,专注的人因为关闭了其他信息通道,摒弃了杂念,反而更轻松,更有机会获得过程乐趣,这个过程就是“自得其乐”。或者认为从事挑战性的工作通常压力很大,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恰恰相反,不具挑战的重复性工作常常会产生厌倦感,迷失人生的意义,不断挑战,才能超越自我,获得新生的感受。
4 利他人格与情怀的锻造
在亲缘(互惠)利他、社会互惠(回报)利他与纯粹利他(无血缘、无回报)的三种境界中,前两者的利他者都会赢得互惠,互惠让人快乐,在这个过程中,利他者享受服务乐趣,提升服务技能;相反,失去服务机会则有无聊感、空虚感、价值支撑感。同时感受到利人与利己的统一,利他将成为一种有道德的利己,培育利他互惠机制,关怀与感恩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缔结(受尊重,有口碑)。但纯粹利他者超然于互惠(回报)之上,因此,也最令人仰慕,利他者纯粹,纯粹就是回报,但持良善(纯粹)之心,不求即时回报,内心平衡,继而心安理得。此时,利他者蓦然感悟人生的意义,正是这一份职业生命的意义让人快乐,当然,在医疗救助中,利他者见证痛苦与死亡,超越痛苦,豁达生死的觉悟让人获得终极的快乐。
这份终极快乐也被称之为灵魂愉悦,精神拔节,即精神性的升华,它更多地与个人的内在追求和信仰有关,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答案、超越体验的追寻。它是一种信念召唤,一个信仰和态度体系,洞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赋予生活以新的目的和意义。它也是个体对于内在和外在整合感、联通感(神圣、卓越、巅峰)体验,品味爱与意志的伟力。它还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内驱力),是自我超越的潜在能力,通过这份能力,个体可以参与到比自身存在更有意义的事业之中。结合我们的抗疫群英们的精神发育,可以细分为以下五种感受:
①神圣感:他们坚信生命神圣、医学神圣、医者神圣。
②敬畏感:他们不仅敬畏生命,也敬畏疾病,敬畏生死。
③悲悯感:一缕悲伤,引出悲切、悲壮、悲怆多种情愫,悯是悯惜、怜悯、恻隐。
④使命感:在他们心头,使命召唤,使命必达,使命荣光。
⑤平衡感: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利他与利己,体验与升华。
情感现象学家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探究了人的一生所能企及的生命位序与精神位格,由此来揭示生命价值的腾跃高度,如何从小快乐到大快活,从互惠利他到纯粹利他,继而从职业快感、快乐到职业幸福。舍勒的人生金字塔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感官价值(欲望,类植物性、动物性快感),第二层级是功利算计(是非、得失、商业理智,财务自由);第三层级是崇高感的体验(高下、荣辱、清浊,心智性、精神性享乐),最高层级是神圣感的沉浸、笼罩(福流,精神愉悦);许多人终极一生只迈上第二台阶,偶尔感受到第三层级,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迈上第四台阶,成就人生的巅峰体验,很显然,舍勒给我们的引领是拒绝物化、异化,更关注人的本质、人的宇宙位置,人的价值所在[8]。医者的纯粹利他行为(而非亲缘利他、互惠利他)恰恰是精神位格脱颖而出的价值阶梯。我们的抗疫英雄群体就是这样一批能够跃上人性巅峰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