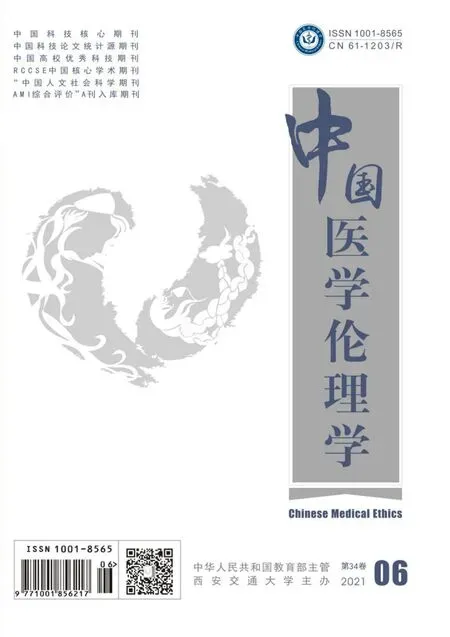叙事医学在医疗决策中的价值启示及路径探析*
刘玉玲,谭占海,甘代军 ,唐 君
(1 遵义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1519251988@qq.com;2 遵义医科大学人文医学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0)
医疗决策就是为患者的诊断、治疗作出决定,在众多可以采取的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使患者获得最大利益[1]。医疗决策是医务人员临床工作的重要内容,体现其职业价值的重要方面,并对患者预后具有重大影响的医疗活动。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医生在医疗决策中具有绝对的地位与权威。随着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丑闻被披露,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知情同意成为广泛推崇的重要的伦理原则[2]。然而,在目前的一些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往往沦为医方对患方决策主权宣示和冷漠告知,患方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临床决策中;医生在关于临床决策的信息交流方面,往往注重患者的“同意”而非“知情”,这导致了患者并未获得决策的充分信息和出现决策失误等。
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概念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内科学教授丽塔·卡伦(Rita Charon)于2001年提出。叙事能力是一种承认、吸收、解释、回应他人故事和困境的能力,叙事医学则是对其的临床实践[3]。叙事医学强调医者应尊重患者的疾病叙事和决策中他们的情感体验,因为临床决策也是患者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并饱含其疾苦观和生命抉择。叙事医学有利于激发医生的共情、促进医患沟通、构建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出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临床决策。
1 影响有效医疗决策的问题分析
1.1 医患社会角色的差异
在医疗实践的各个环节,患者必须依赖医生解除病痛:医生的诊断是安排治疗方案的前提,服药须有医生的医嘱,医生的健康教育和随访对患者的康复也非常重要。这种依赖与被依赖的不平等角色导致医患在医疗决策中的强势和弱势地位。此外,医生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而患者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医学知识匮乏、经济条件不一,这也导致了某些医生在临床决策中常见的家长主义作风,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患者的主要需求和选择偏好,患者在决策中主体性地位弱化和“失声”。
1.2 医患对躯体和疾病的认知差异
高质量的临床决策需要医患之间达成趋同的认知,然而在躯体和疾病的认知上,医生与患者分属于两个世界。“正如一个人并不直接体验‘疾病状况’一样,一个人也无法直接体验其作为科学对象的躯体”。事实上,只有医生才会将其作为一个科学的对象来理解患者,医生也是按照其用各种医疗设备看到躯体的内部情况来解释临床症状及考虑治疗方案,而患者多从躯体的外表及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及程度来考虑可接受的治疗方案,医患之间对躯体理解的这种重大区别对临床决策也有很大的影响[4]。在医生的认知框架中,疾病是与健康相对立的概念,躯体仅是疾病的载体,“治愈”及保存生命便成为所有临床活动的终极目标。然而,患者多是从个人生活经验的角度来看待疾病:疾病不仅使自己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感、对未来的确定感,而且伴随着个人社会角色的退化,因此还承受着生理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无奈、恐惧、绝望等不良情绪。患者就医和接受治疗的目的也在于恢复作为社会人的完整性,而不仅仅是躯体的修复。医患之间的这种认知差异影响了临床决策的质量,医生的医疗决策依据多为各项生物学检查所体现的病症,决策方法则基于同种疾病的治疗经验和临床推理等一般性规律,往往忽视患者的个体独特性和疾病对其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导致患者抵触参与和遵循临床决策。
1.3 医患对疾病的归因机制差异
医生作为具有系统化、专业化医学知识的群体,他们将疾病当作是“病变的实体”,在疾病的病因认识上会执着地追溯其病原学和病理学等相关的生物学理论为医疗决策做支撑。患者对病因的追寻则回归于具有复杂性和多样化的个人生活,在诉说和反思中接纳“为什么厄运降临在我头上”的生命诘问。医生胶着于病因的确定化和客观化容易导致其在医疗决策中的固化思维,忽视了患者从自身角度来探寻、接纳疾病的叙事过程,不利于患者有效遵循医疗决策。
1.4 医患道德情感的缺失
医患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以关怀和关心为核心的道德,可以潜在地以一种建设性的、和谐的方式服务于医疗行业,因为它与临床医疗情境中的决策过程和情感反应联系紧密”[5]。医学不仅需要理性的思维方法,更需要人性的温度,只有医生发自内心地关心患者、关怀其被病痛折磨的身心状况,才能在医患沟通中聆听患者的叙事、不断完善医疗决策。然而,医患道德情感的缺失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医学技术和循证医学的迅猛发展,有些医生陷于医学的工具理性思维,在临床决策中“去情感化”,对患者的疾病叙事“去隐喻化”,医疗决策中更加关注的是疗效的最大化、技术的最优化。医患沟通和医疗决策沦为了一种机械而形式化的程序行为,决策过程中的知情同意也成了规约双方的利益合同书。医患双方成了利益共同体而非道德-情感共同体。此种道德情感的缺失使患者对医生在医疗决策的动机抱有不信任的态度,阻碍了临床决策的制定。
2 叙事医学在医疗决策中的价值启示
2.1 叙事医学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就是当两个主体,或者说两个真正的自我相遇时发生的情形,在我与他者相遇中复活。查尔斯·泰勒写道:“人们不能单独成为自我……自我只存在于我称之为‘对话的网络’中。”[6]在互动的医疗决策过程中,每个个体自我都是由对方的认知所建构的,叙事行为实现了双方世界的联动。通过讲述、聆听与见证,医生才能从对技术的关注回归对患者疾苦的关怀,真正与患者共情;患者才会“知情选择”,从而以正确的心态评估医生的决策方案、以信任的态度接受决策方案。在叙事医学的视野下,医患成了谋求最佳医疗决策的治疗同盟而非不平等的强弱势角色,以叙事为桥梁达成共识、实现医疗决策“以人为目的”的服务宗旨。
2.2 叙事医学的独特性
患者直接体验的独一无二的特性正是临床中医患之间认识、情感、伦理和行为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4]。医疗决策中的一些偏差正是在于医生忽视了患者的独特性、寻求普适性的治疗指南,而叙事医学则凸显了每位患者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比较性。医疗决策不是患者生活中的孤立事件,它贯穿于患者的整体叙事之中,如患恶性肿瘤的患者是否同意住院治疗、选择化疗还是放弃治疗、保守治疗还是手术等决定都是基于患者叙述下这些事件对其生活的意义。医疗决策是在具体情境下、面对个性化的患者所实施的医疗活动,通过倾听千差万别的患者的叙事,医生才能了解这些患者的疾病世界、情感世界,为制定医疗决策提供客观真实的依据。叙事医学要求医生关注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和其疾病叙事,在叙事情节中把握其主要需求、期望和偏好,优化诊疗思维、共同作出最符合患者利益的医疗决策。
2.3 叙事医学的因果联系/偶然性
临床实践充斥着情节化,诊断本身就是努力将情节置于不连贯的事件和情节上[6]。患者的主诉就是向医生展现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叙事过程,帮助医生将患者疾病发作的情境、身体反应、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等各种情节串联起来,提高医疗决策的准确性。所以,忽略患者叙述中情节间的因果联系可能会导致无效的医疗决策。
虽然医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人类对疾病的探索和攻克是任重而道远的事。医学的科学性和生物学特点有自身的局限性,叙事医学则为解释疾病的偶然性提供了开阔和多元的视野。尤其是在制定癌症和临终患者的医疗决策过程中,叙事医学为医患双方领悟生命无常、疾病无解提供了慰藉和救赎力量(接纳人之必死的共同归途),有利于制定更加人性化的医疗决策。此外,医学并不总是指向治愈,如慢性病的治疗决策往往意味着患者必须接纳与疾病长期相处的事实,医生的倾听和见证能够帮助慢性病患者恢复健康。叙事医学要求医者以“叙事”的形式全面记录、了解患者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全面综合地作出诊疗方案,这无疑能使患者,尤其是慢性疾病患者获益[7]。
2.4 叙事医学的伦理性
由叙事所建构的主体间性中包含了伦理关系,必然导向医疗中伦理关系的反思,文学(讲故事、听故事)行为将强化个体的伦理认同,尤其是对他者的责任[8]。目前,医患在临床决策中道德情感的缺失问题在于医患关系的对立性定位,个别医生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防御性医疗,将医疗决策权完全推给无助和茫然的患者及家属,此种行为表面是对患者自主权的绝对遵从,实际上是推卸医者的伦理责任。叙事致力于构建超越这种对立性契约关系的尊重、共情和信任的伙伴关系,使医生重新思考医患关系、医疗决策中自身对患者的伦理责任。医者通过倾听与见证患者的疾苦来体会患者的处境、真诚地与其沟通,共同作出高质量的临床决策。
3 叙事医学在医疗决策中的实现路径
叙事医学顺应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对临床决策提出了新要求[9]。叙事医学要求下的医疗决策流程大致划分为信息交流阶段、方案协调阶段和达成共识阶段。
3.1 信息交流阶段
任何医疗工作都始于对患者的关注,关注始于倾听。医生接诊患者后,应关注患者的语言、姿势和面部表情,发自内心地重视患者的叙事。医生通过倾听患者及家属的诉说,了解患者丰富的生命故事,如对疾病预后的担忧、对后续治疗的负担、经济压力、陪护工作等。在叙述与倾听中医患主体相遇,医生走进患者的世界、接纳患者的疾苦故事,见证患者的痛苦,从而了解患者的需求与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明确患者的诊断和病情就是在患者的疾病叙事中探寻疾病成因的过程。由于患者叙说生活话语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医生在倾听患者诉说时,应对患者碎片化或跳跃性的讲述,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因果关系一致的表述。另外,医生应辨别患者语言背后可能隐藏的信息,力求从患者的叙说中找到致病原因(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为确诊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医患沟通在医疗决策的信息交流阶段具有关键的作用。在我国,患者和家属共同参与临床医疗决策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患者的直系家属。医生应重视和患者家属的沟通,了解患者家属的观点态度、家庭经济情况和患者更为全面的信息。通过医患沟通,医生对患者作为有社会关系的人有了深刻的认识,使医生更加清楚患者和家属所处的困境,医生因此对患者产生深度的理解与共情,作为一个能够倾听和关爱患者的人来为他们提供真诚的帮助[6]。
3.2 方案协调阶段
叙事医学关注的是一个个有不同社会关系、情感和故事的患者,所以叙事医学要求下的临床决策应符合个体化的原则。为了作出符合个体化原则的临床决策,医生不仅要考虑患者的年龄、体重、身体素质等个人因素,还要考虑其经济条件、家庭情况、心理承受力等社心理因素。医生应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来告知患者可选的医疗决策方案及其利弊,还可利用图片、视频、宣教手册等工具为患者提供决策支持。患方从医生这里了解到自身的疾病特点等,根据个人的情况对医生提出的诊疗方案表达看法、提出疑问。医生对患方疑问一一进行回应、打消其顾虑,也可以根据患者的偏好再次调整方案,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个体化方案。
叙事医学关注的焦点是人,特别是人的情感,是在技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医学中关注人的情感的医学实践[10],因而叙事医学要求下的医疗决策协商过程应是充满人性的温暖、理解和共情。在此过程中,医生应尊重患者和家属对不同诊疗方案的意见,关怀、理解他们,与他们的情感融合在一起,设身处地地为患者考虑,并对患者的顾虑进行心理疏导、提供情感的慰藉;同时,医生应反思自己对不同医疗方案的观念和态度,换位思考,从而理解患者的担忧和疑惑,从而尽力寻求患者和家属都接受的诊疗方案。
3.3 达成共识阶段
融合的叙事行为促成了良好的医患关系、为二者达成决策共识奠定了基础。医患之间的叙说与倾听、沟通与反馈形成了和谐的医患关系,正如一位肿瘤科医生所描述:“患者其实很喜欢和医生聊天,当他住院的时间长了他就会把家里的一些事情,甚至是隐私的事情都会和你聊,然后这时候你就需要去倾听,他还是相对会有一个信任感的……当患者信任你的时候,他会知道你是全心全意为他好。其实我觉得医生是最希望患者好的,甚至比他的家人还要关心他,当他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依从医生。”[11]这位医生表达的就是由叙事行为形成的医患间相互信任的归属关系。在此基础上,医患相互理解并达成决策共识,共同制定最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医疗决策。
上述便是叙事医学要求下实施的医疗决策流程。在此过程中,医生了解患者的疾苦、知晓患者的需求并清楚患者主要家属的诉求。医患双方通过倾听、吸收、阐释、反思和共情建立相互信任的同盟关系。在此基础上,医生传递医疗决策相关的信息并作为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进行双向沟通和协调,与患方一起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最后选择最利于患者且医患双方都接受的决策。
4 结语
叙事医学弥合了技术与人文的鸿沟,其“独特性、主体间性、因果联系/偶然性、伦理性”的四大特征为解决目前医疗决策的问题提供了新的价值启示,为医患作出最佳医疗决策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实践叙事医学有利于解决医疗决策中的困境并提升患者满意度。然而,叙事医学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现有的中文文献以概念和价值的介绍居多,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的数量不足[12]。所以现阶段相关机构和部门应积极推动学校教育和医院培训,促进叙事医学真正落地并得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