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到银幕:《暗恋桃花源》的跨媒介叙事研究
阎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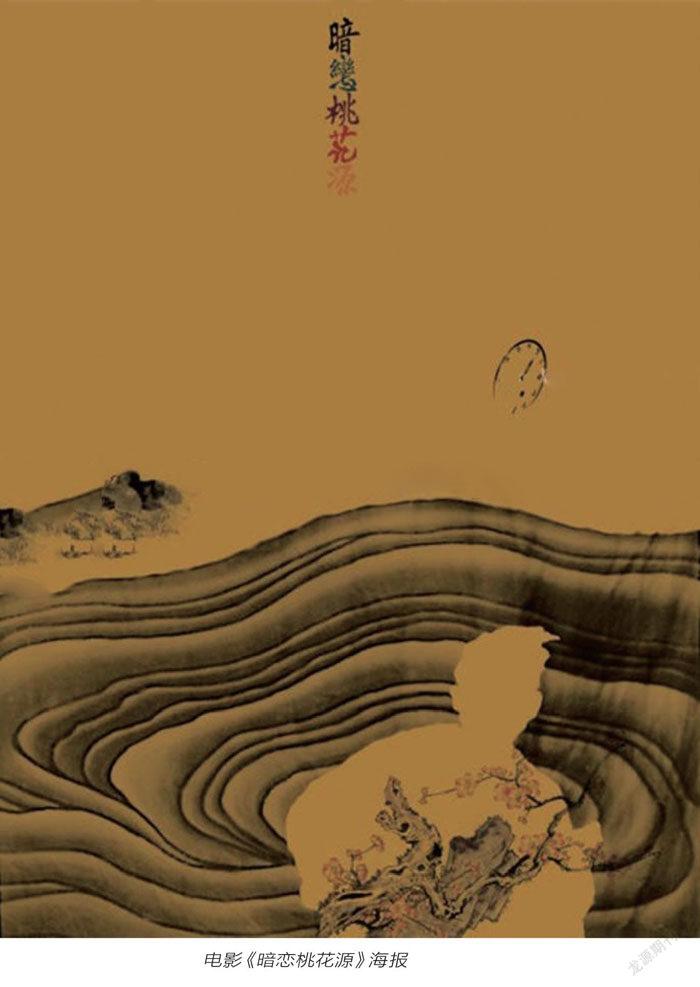
赖声川导演的话剧《暗恋桃花源》首演于1986年的中国台湾,而电影版则于1992年首映于中国台湾。令人惊喜的是,赖声川把这部经典话剧搬上大银幕,不仅没有使其变得不伦不类,反而将舞台语言、台词语言和电影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丰富了电影的层次感。并且,导演用这种套层结构,让观众不停地入戏、出戏,营造出一种不在戏中却又在戏中的感觉,给观众一种真实的体验式感觉,让观众更能站在边界之外去思考这部电影。
电影主要讲述了在一个剧场里面有一个《暗恋》剧组在排练,但是在并不顺利的排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桃花源》剧组出现,并且这个剧组也要在剧场里排练。由于两个剧组间互不退让,于是一悲一喜两出戏轮流在舞台上出现,令观众啼笑皆非。一边情意绵绵、缠绵悱恻,而另一边却鸡飞狗跳、嬉笑打闹;一边锦书遥望盼归人,另一边却是咒骂怨怼闹相逢。但是就是在这种情节和内容的都十分混乱的情况之下,两出混乱的戏剧竟然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似乎是毫无逻辑的,它涉及到剧场中演员情绪、台词和表演的错误,导演故意把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了一起,但就是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东西,逐渐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它们之间的秩序。渐渐两边情节能相互映衬关联,高潮处台词也能合上,达到一种诙谐的和谐。电影版《暗恋桃花源》改编于话剧版《暗恋桃花源》,但它并没有拘泥于原有话剧的格式和内容,反而通过全新的演绎,创作出了一部电影佳作。在不改变故事情节的基础上,电影版《暗恋桃花源》做出了诸多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内容与形式的二次回归
作为叙事类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戏剧和电影虽然在理论上已经从20世纪早期的理论家们那里被定下了“分道扬镳”的结论,可时至今日,两种艺术形式仍然在内容的表现方式上呈现出彼此借鉴、彼此“越界”的情形。这样的情形非但没有让戏剧和电影走向不伦不类的混沌,反而从不同的层面促进了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在《暗恋桃花源》前后都出现了大量戏剧和电影的互相改编(尤以电影改编戏剧为多),但没有哪部作品比《暗恋桃花源》更加直接地使用两种艺术形式来呈现几乎是同一个故事内容的。由此,我们更加能够借助《暗恋桃花源》的话剧版和电影版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作品,窥探到戏剧和电影既相互交融又相互独立所带来的问题与思考。
正如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在讨论戏剧与电影的改编问题时所提出的观点:“编剧除了要考虑到电影的特殊条件外,特别是在一般结构方面还要遵循与电影有关的其他艺术的创作法则。一个电影剧本可能是以戏剧的格式结构的,因此,他应该服从戏剧结构的法则。”由此可见,电影与戏剧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暗恋桃花源》从话剧改编成为电影,其内容和形式上有什么变化?内容和形式的相互作用,是否能够促成两部作品的二次回归呢?
正如电影版本和戏剧版本相互纠缠的关系一样,《暗恋桃花源》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故事,它不仅可以用戏剧或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和喜剧的相互碰撞。《暗恋桃花源》由三个故事组成,从舞台上的《暗恋》到《桃花源》,再到舞台下的两出戏剧碰撞出的第三个故事,将近代的爱情悲剧和古代的爱情喜剧相互糅杂在一起,却似乎是在无意之中碰撞出了别有新意的火花。当两出戏同台彩排时,双方台词的巧妙对称,体现出的是古今中外的悲欢离合,其深层隐藏的却是深厚的悲剧内核。无论是戏剧还是电影,整个故事的张力都在这种杂糅于一处的矛盾中一步步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一出悲剧,一出喜剧,从深沉哀婉到荒诞不羁,不同风格的碰撞所塑造出的最终的故事,将这两出戏放在了同一个舞台,让观众忽然意识到,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其实只是正反两个面而已,越是在情节和风格上相悖甚远,其所带给观众的冲击也就越深。这样复杂的审美任务放置在戏剧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之中,又进一步呈现出了不同的美学效果。
电影与话剧的剧情相比,增加了老陶之妻春花和袁老板之间的对手戏份,更大程度地把喜剧的荒诞元素放大化。话剧跟电影的表现形式不同。这部话剧和电影受布莱希特叙事体戏剧理论影响极深,在电影改编中,导演运用了间隔化效果,利用陌生化和历史化的表演方法来处理戏剧和演员,使演员与角色存在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演员可以随时进入角色,生活在剧中人物的天地,又可以随时跳出角色。观众逐渐从被光影支配的配角成为了主动去观看的主角,他们能够从舞台幻觉中反复惊醒,从而更能够清醒又深入地去思考这部电影,这也是电影形式的一大优势。这部影片复杂的形式依托于舞台表演而生,也在事实上呈现出的是一个“戏味儿”十足的故事,可当这个故事表现在电影之中时,却似乎也天然性地适配这一艺术形式。仅从表面来看,似乎《暗恋桃花源》的电影版只是将舞台版的故事原封不动地使用摄影机录制下来,甚至会显得和舞台版的影像记录差别不大,但却在细微处下足了心思。舞台版《暗恋桃花源》中所来不及呈现的诸多细节都在电影所特有的特写镜头中完整地展现在了电影观众的面前,而电影对于原故事中情节铺陈的精简,也在符合戏剧原情节脉络的基础上,叙述了更精致、更明确,同时也更符合电影艺术形式的故事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二、叙事空间畸变的三次重塑
电影和戏剧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它和戏剧所使用的媒介是不同的,电影采用摄影机来充当观众的“眼睛”,因此具备了空间取材方面的自由,戏剧则被框定在舞台之上,空间和时间的取材能力天然性地弱于电影拍摄的生成方式。这一基本的差别,造就了两种艺术形式在叙事铺展的根本区别。在电影中,一切表现物都会被“技术化”,通常而言,电影会“尽量地把道具真实化,观众比较容易把看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真实”[1];而戏剧的舞台形式则与此完全相反,戏剧的舞台上,所有的道具和布景都会被高度的“符号化”,几乎每一样道具都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对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众需要能够快速理解每一个符号的表征意义,更加快速地接受戏剧舞台所表现出的虚构的意境,才能快速融入戏剧舞台的表意空间之内。在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往往三五個演员的列阵动作就代表了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主要角色绕着舞台走一周,往往就代表已经跨越过了千山万水。对于空间表意功能的实现,戏剧和电影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表意系统。因此可以说,戏剧是“真的”变“假的”,电影是“假的”变“真的”,二者在这一点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叙事本质的不同。为什么我们认为《暗恋桃花源》的融合是成功的,就在于这部作品的两个版本巧妙地结合了戏剧和电影的不同特质,将这个故事分成了三个空间,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最终以“戏中戏”的形式叠加在了一起。“戏中戏”并不是一个少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但是将“戏中戏”的手法演绎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的,《暗恋桃花源》绝对算得上经典之一。这样的形式原本就是从一个完整的叙事空间中割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虚构的层面中再添加一层虚构的意义,让观众不停地随着故事游走在不同层面的虚构之中,并从不同的故事里感受不同的精神内涵。《暗恋桃花源》正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出一个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故事。gzslib202204040000无论是话剧版还是电影版,《暗恋桃花源》的三个故事都将整部作品切分为了三个不同的空间。在故事中,悲剧剧组《暗恋》和喜剧剧组《桃花源》反复出现在故事的舞台之上,在时间和空间中交替出现,作为故事主线的舞台争锋中,两出戏的导演和演员则又回归到了同一个空间之中,彼此争执着演出排练的时间。随着故事当中时间的愈发紧迫,两出戏不得不同台演出,《暗恋》和《桃花源》剧组各占舞台一侧,一边是现代跨越几十年的悲情离别,另一边是古代奇幻不羁的荒诞喜剧,两个原本毫不相关的叙事空间被突兀地挤压在一起,坐在台下的观众或是坐在银幕前的观众不得不接受这一画面,将两个故事被动地糅杂在一起,而两出故事中恰如其分的台词拼接,又将这两个故事空间巧妙地拼凑在了一起,以至于悲剧之哀痛和喜剧之荒诞都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合理性来。两个叙事空间的畸变重塑出了第三个新的空间——悲喜交加的叙事空间,通过演员的表现和台词的拼接,又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叙事空间。偌大的舞台上,三次叙事空间的塑造以“戏中戏”的形式呈现而出,相比于戏剧,《暗恋桃花源》似乎更深谙于使用电影叙事空间的常见手法,几次重复的“入戏”与“出戏”,是营造不同画面空间的有效手段。事实上,电影艺术天然地集合了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在二维的平面世界中塑造三维的立体事件,是电影必须完成的任务,虽然电影叙事内在的包含着时间叙事,但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看,导演所做的首要工作却是如何设计和捕捉一个合乎故事需要的空间概念。在《暗恋桃花源》这部影片中,空间的设置是表现和突出的重要部分,在固定比例大小的画面中,如何呈现故事信息,是叙事者们首先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允许观众看到部分信息的同时又要向观众隐藏部分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影的内容和意义本身就需要靠空间才能传达出来,电影中的镜头及其剪辑、结构及其叙事、节奏和蒙太奇等等都是电影叙事空间的组成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使得电影具有表意功能和情感联结。
三、时代与作品的双重叙事呼应
根据赖聲川本人在《无中生有的戏剧——关于“即兴创作”》一文中所指出的,戏剧版《暗恋》的创作和传统话剧的创作方式不一样,他直接“带着演员从舞台开始,利用集体的即兴表现,来呼应出整体的故事框架,最终再由此形成剧本格局”[2]。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很难不承认,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曾受到过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影响,为什么暗恋男主角是一个来自东北的老人,为什么爱情悲剧和爱情喜剧能够巧妙地碰撞在一起?这诚然是在赖声川所带领下剧团众人的集体艺术成果,但当这样一群时时刻刻受到时代浪潮影响的戏剧工作者们聚集在一处时,他们所象征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社会反思。在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历史时局时时刻刻都在对新旧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建构,反过来讲,这也是文化创作对于政治时局的反映。
尽管话剧版的《暗恋桃花源》和电影版的《暗恋桃花源》所讲述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却因为艺术形式和叙事空间的问题,而不得不分开讨论。在厘清两部作品之中内容与形式、时间和空间两组关系后,进一步探讨这两部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就很有必要了。尽管这两部作品所叙事的内容基本一致,却是不同时期所做出的产物。尽管两部作品仅仅相隔6年,但在中国台湾风雨飘摇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部作品的上映已经可以说出生于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政治形势影响下,创作者一定会有意无意间借助作品来做出自己对于时代的理解和讨论。1991年,中国台湾开放了内地探亲,因此电影版在内容和主题上,都有新的拓展和延伸。所以在电影版之中,《暗恋桃花源》在影片一开头就增加了一个内容:《暗恋》导演的学生问一个老人:“王伯伯,你不是回大陆去了吗?”这就是导演在一开始就想跟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赖声川探讨这个问题跟自身经历是有关系的,他祖籍是江西会昌。他在父亲去世之后才与大陆的叔叔取得联系,在他给叔叔写的一封家书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的思想来源:“我们打开了一扇朦胧的窗,从此不再是一棵没有根的树。”所以赖声川在戏中借江滨柳的这个角色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身在台湾,但是心中一直挂念着东北老家,在病榻上仍不忘交代妻子将自己的骨灰带回老家。这是电影版和话剧版的一个不起眼的改变,但却隐含了那个时代下,台湾同胞对祖国故土的无限眷恋和怀念。
将这部作品拆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来看,《暗恋》是属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话剧的,内容形式都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操作运行的。但是《桃花源》不一样,它不遵循传统,表演风格和台词都与传统迥异,虽然我们在《桃花源》这个故事中看得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痕迹,虽然这部作品里有诸多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表演程式,但其本质仍然是一部荒诞不羁,甚至略显通俗的作品。在电影中可以明显看见,当双方剧组矛盾激升的时候,双方的导演都在批判着对方的作品,两个导演是水火不容、相互蔑视的,都想借着否定对方来肯定自己。但是“‘自我永远无法获得完全的自主性”,一种文化试图通过在与另一种文化的交谈中占据主动和成为权威,是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胜者。显然,赖声川作为一个处在这样社会变革中的艺术家,深受其影响,并且以其敏锐的觉察力和富有艺术性的创造力创作了这个富于时代性的经典作品。
结语
正如赖声川自己曾表达过的,他的作品中一直有“拼贴”的概念,其实剧场本身就是拼贴的艺术。《桃花源》有许多华丽的东西不断掉下来,落在《暗恋》当中,两出戏中的故事相互碰撞,由此形成了“戏”本身。电影版本的《暗恋桃花源》沿袭了舞台版本的整体框架,叙事的过程却通过电影语法重新编译,通过镜头的组接,这个版本的电影书写出了别样的精彩。事实上,无论是戏剧、电影还是小说、连环画,一切叙事类艺术的发展和形成都有可以追溯的源头,叙事类艺术作品之间天然性地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也只有这样互相的融通和交结,才能拓宽这两种艺术的表意空间,从根本上把握叙事艺术的魅力,解放艺术创作者,让电影和戏剧的创作者们真正通过艺术去实现愉悦人、教化人的作用。《暗恋桃花源》的两个版本分别从戏剧和电影的体裁出发,将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结构中阐释出不同的意义。电影版《暗恋桃花源》将原本来源于戏剧的故事重新演绎出来,利用电影的艺术特质贡献了一部新的杰作,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者而言,这两个作品的改编就具有了新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窦小忱.从《暗恋桃花源》看电影与戏剧在结构上的融合[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01):49.
[2]赖声川.无中生有的戏剧——关于“即兴创作”[ J ].中国戏剧,1988(0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