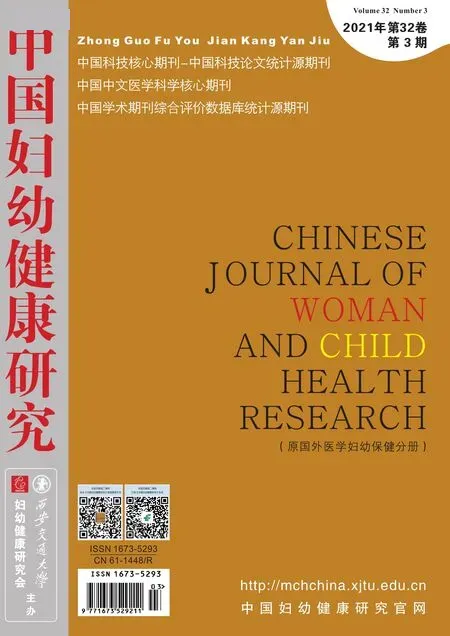新产程标准下临产前及临产后急诊剖宫产妊娠结局分析
——基于临床数据回顾性分析
许 扬,侯燕燕,陈 磊,郭 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胚胎源性疾病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0)
伴随二胎政策的开放,前次剖宫产再次妊娠引起的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先兆子宫破裂、产后出血等妊娠不良结局及远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增加,以及再次剖宫产术后危及产妇生命的血栓性疾病发生概率增加,对目前产科医生的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做好初孕妇首次分娩方式的选择,促进阴道自然分娩是产科医生当下的职责。Zhang等[1-2]2010年的研究显示,初产妇和经产妇在宫口扩张6cm之前产程进展是相似的,宫口扩张6cm之后的产程,经产妇比初产妇进展快,故认为宫口扩张加速在6cm。《新产程标准及处理的专家共识(2014)》[3]将宫口扩张6cm作为活跃期的起始点,同时延长了第一产程和第二产程的时长,减少了产程过程中的临床干预。采用新产程标准,延长了产程时长,增加了旧产程中因活跃期停滞及潜伏期延长剖宫产的阴道试产机会,对总产程超过24h的产妇也可以阴道试产,极大地促进了自然分娩,降低了剖宫产率[4-5]。关于新产程标准实施之后,母婴并发症的发生率是否会增加,目前尚存在争议。郑媛媛等[6]研究认为在新产程标准下,随着产程时长的延长,孕妇极易疲劳,进而子宫收缩乏力引起产后出血,但杨淑芳[7]研究认为新产程标准减少了临床干预的同时降低了剖宫产率,并不会增加产后出血的发生风险。
对于新产程标准下临产前与临产后急诊剖宫产母婴结局的分析,目前国内尚无同类的临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已实施新产程,现将我院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新产程标准下急诊剖宫产妊娠结局进行分析,探讨新产程标准下临产前及临产后急诊剖宫产对产妇及新生儿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急诊剖宫产的853例产妇的临床资料,将产妇分为临产前组(565例)、临产后组(288例)。两组产妇年龄、孕次、产次、身体质量指数(BMI)、新生儿体重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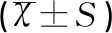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单胎、头位,产妇无生殖道畸形,产妇有阴道试产意愿且无阴道试产禁忌症;排除标准:瘢痕子宫(包括前次剖宫产及子宫肌瘤剥除术);绝对性骨盆狭窄;前置胎盘、胎盘早剥;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无阴道试产意愿及有阴道试产禁忌症者。
1.3方法
1.3.1采用新产程标准观察产妇的产程进展情况
以宫口扩张6cm作为活跃期的起点,孕妇宫缩良好且破膜之后宫口停止扩张≥4h时,当宫缩乏力(宫缩间歇期<3min,宫外压<80mmHg)或宫口停止扩张>6h时,诊断为活跃期停滞,可视为剖宫产指征。初产妇第二产程>3h(硬膜外镇痛分娩>4h)、经产妇第二产程>2h,且产程均无进展,诊断为第二产程延长,为剖宫产指征。潜伏期延长不再作为剖宫产指征。本研究以宫口扩张6cm作为分组依据,宫口扩张6cm前为临产前组,宫口扩张6cm后为临产后组。
1.3.2宫内感染的诊断标准
产妇产时体温≥38℃,白细胞计数≥15×109/L,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所占比例≥90%,同时伴有胎儿心动过速(胎心率>160次/min),则诊断为宫内感染[7]。
1.3.3产褥感染的诊断标准
产褥感染是指产褥期内生殖道受病原体侵袭而引起局部或全身的感染,常发生于分娩结束24h至10d,每日测体温4次,每次间隔4h,其中有2次体温达到或超过38℃且排除其他感染。临床表现为发热、宫体压痛、伤口红肿裂开等[8]。
1.3.4胎儿宫内窘迫的诊断标准
胎心监护显示胎心延长减速、胎心率持续>160次/min或<110次/min或胎心率重度变异减速、频繁的晚期减速、基线变异消失、正弦波[9-10]。
1.3.5产后出血的诊断标准
剖宫产术分娩出血量≥1 000mL。产后出血量的测量方法:术中采取容积法,术后采用称重法[11]。
1.3.6新生儿生后1min、5min Apgar评分标准
依据新生儿的肤色、呼吸、心率、反射和肌紧张程度进行Apgar评分。若新生儿生后1min、5min Apgar评分为8~10分,则判断为正常;若Apgar评分为4~7分,则判断为轻度窒息;若Apgar评分<4分,则判断为重度窒息。
1.4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产妇剖宫产指征、产后出血量、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变化值、产褥感染、术后住院天数及新生儿Apgar评分。
1.5统计学方法

2结果
2.1两组剖宫产指征比较
临产前组剖宫产指征排序为胎儿宫内窘迫(66.19%,374/565)、产前发热(17.88%,101/565)、巨大儿(8.67%,49/565)、重度子痫前期(1.24%,7/565)、引产失败(6.02%,34/565)。临产后组剖宫产指征排序为胎儿宫内窘迫(50.70%,146/288)、相对性头盆不称(36.80%,106/288)、产前发热(10.76%,31/288)、巨大儿(0.35%,1/288)、重度子痫前期(1.39%,4/288)。
2.2两组母婴结局比较
两组产妇产后出血量、血红蛋白(Hb)下降值、产褥感染发生率、术后住院天数及新生儿Apgar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两组母婴结局比较
3讨论
3.1新产程标准实施后妊娠结局及剖宫产手术指征变化
本研究显示在新产程下临产后急诊剖宫产者产后出血、产褥感染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较临产前剖宫产者增高。临产后手术中Hb下降值较临产前高,临产后手术出血量较临产前多,本研究中共发生4例产后出血,出血原因均为宫缩乏力,其中1例发生于临产前,因计划分娩,催产素引产、宫颈球囊扩张引产、人工破膜等引产,引产3天未临产行剖宫产,术中出血1 530mL,行宫腔水囊填塞压迫止血,术后予以输血治疗。其余3例均发生在临产后,1例因相对性头盆不称,持续性枕后位行剖宫产,术中出血1 200mL,予以药物及按摩促宫缩止血,术后予以输血治疗;1例因胎心监护可疑Ⅲ类,胎儿宫内窘迫行剖宫产,术中出血1 400mL,予以子宫Blynch缝合止血,术后予以输血治疗;另1例胎膜早破行催产素引产,因临产产前发热,胎儿宫内窘迫行剖宫产,术中出血1 770mL,予以宫腔球囊压迫止血,术后予以输血治疗。临产后组产褥感染率较临产前组增高,住院天数也较临产前组增加,新生儿1min Apgar评分临产后组较临产前组低。临产后组剖宫产指征变化也不同于临产前组,两组均居首位的剖宫产指征是胎儿宫内窘迫,临产前组占66.19%,临产后组占50.70%;临产前组剖宫产指征是产前发热的占17.88%,临产后组为10.76%;临产前组剖宫产指征是巨大儿的占8.67%,临产后组为0.35%;重度子痫前期在临产前组占1.24%,临产后组为1.39%。
3.2临产后剖宫产者产后出血、感染及新生儿窒息的原因分析
新产程标准的实施,延长了产程时长,阴道试产时间过长,产妇疲劳,极易因子宫收缩乏力而导致产后出血,同时阴道试产时间长,胎头压迫子宫下段时间过长,极易出现子宫下段水肿,手术难度及术中裂伤概率增加,产后出血的风险相应升高[6]。因此剖宫产术中,轻柔操作,轻取胎头,避免损伤,胎儿娩出后及时应用宫缩剂促进子宫收缩,熟练掌握宫腔填塞及子宫捆绑止血等处理,必要时及时输血纠正失血,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研究显示,第一产程超过12h可增加产程中发热的风险,加之部分孕妇因产程中宫缩较差行催产素静滴加强宫缩,均可使产程发热的发生率升高[12];其次较长的产程往往伴随大量能量消耗,而过度通气,加之硬膜外镇痛、分娩应激刺激的影响,产时发热发生率亦升高[13]。分娩时生殖道环境改变、机体抵抗力下降、低蛋白血症或者贫血均可使定植于生殖道的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等病原菌繁殖导致感染[14-15]。分娩时外界病原菌进入产道可引起感染,如胎膜早破、产程时间过长、阴道检查次数大于5次(Maharaj于2007年的研究)等均增加了感染发生的可能,另外由于产妇体力消耗,术后免疫功能下降,同时若合并慢性病、贫血或者有产前产后出血,均可增加产妇产后感染发生的概率[14,16-17]。由于对感染的治疗,术后住院天数增加,住院费用也随之增高,更有产妇因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愈合不良再次入院伤口清洁换药,加重了产妇及家属的经济负担。脐带因素(如脐带绕颈、脐带打结、脐带过短、脐带受压等)使胎儿在宫内出现缺血缺氧等情况,进而影响胎儿血液循环。特别是临产后,宫缩加强,随着产程进展,脐带不断变短,进而引起胎儿缺血、缺氧,最终导致新生儿窒息[18]。有研究显示羊水过少易伴羊水污染,分娩时新生儿易吸入胎粪,且胎儿缺乏羊水的缓冲保护[19],宫缩时,宫内压力直接作用于胎儿脐带,且羊水过少时胎盘老化引起胎盘功能降低,均影响胎儿与母体之间胎盘的血液循环,加重了胎儿的缺氧程度,进而加重新生儿窒息程度。另有报道显示第二产程的延长与5分钟Apgar评分低有关[20]。第二产程持续时间较长与新生儿出生窒息相关的并发症有关,增加了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概率[21]。
3.3新产程背景下改善妊娠结局的有效措施
首先,产前检查要注重产科与营养科、内分泌科及心血管科等多学科合作,加强亚专科力量,注重高危孕妇产前筛查,及早发现各类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并及时给予干预及有效处理。加强孕期健康宣教、饮食营养指导,特别关注肥胖症孕妇孕期体重增加及营养指导,控制胎儿体重,减少巨大儿的发生率。临产前应关注孕妇骨盆与胎儿大小的匹配情况,及早发现头盆不称,尽可能地减少临产后由于产程停滞或相对性头盆不称而导致手术。
其次,产程中关注孕妇宫缩强度变化,及时纠正不协调性宫缩。加强人文关怀,关注孕妇生理及心理状态的变化,对于产程较长、疲劳的产妇,及时予以能量及液体的补充,及时给予分娩镇痛、家属陪伴及助产师心理疏导等措施,减少初产妇对阴道分娩的恐惧及焦虑。产程中注重无菌操作,尽可能减少阴道检查次数及人工破膜等有创操作,加强团队合作,提高医护人员专业技能,增强对异常产程状态的辨识度,识别不良产程及异常胎心监护,及时终止妊娠,减少母婴不良预后的发生。